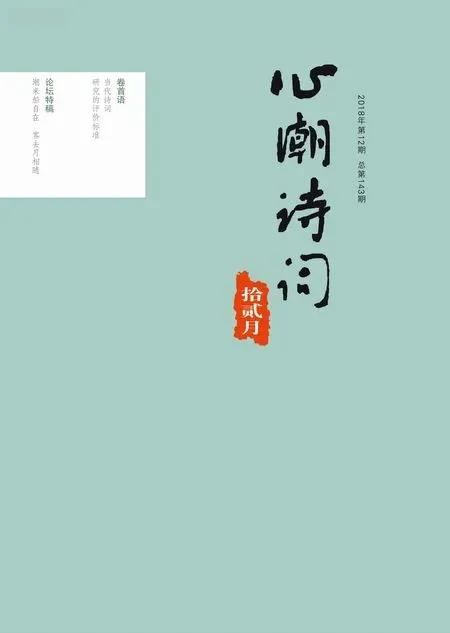現實主義與理想情懷
——當代詩詞創作形態及其作品批評芻議①
當代詩詞在幾十年的繁榮發展中,已經形成較為穩定的創作群體以及審美范式,涌現出許多優秀詩人及作品,比如我們所熟悉的老一輩詩人聶紺弩以及青年詩人姚泉名、李子老師等人,他們是撐起當代詩壇的臂膀和血液。但與此同時,當代詩詞也與其他文學形式一樣,由“快車道”發展進入了亟需調整、規范的階段,“全民化”參與的詩詞作品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審美趨同、形式泛化、語言俗白、立意淺薄等流弊,這些問題都需要從事詩詞研究的學者們加以關注,在審美觀念、形式規范等方面給予學理性探討,引導當代詩詞創作能夠在繼承傳統的同時更好地融入當代文化精神、現代人文風貌及個人理想情懷,由此創造出更具有生命意味、現實深度和文化底蘊的詩學風貌。
本文結合詩詞文本,對當代詩詞的作品創作及審美形態進行剖析。文章中所選作品雖有掛一漏萬、管窺之見的嫌疑,似不能代表當代詩詞創作的全貌,但在一定范圍內也具有普遍性意義,基本能夠反映大多數詩詞創作者們的文化審美觀。筆者并在此基礎上討論當代詩詞如何結合當代文化精神,以及詩詞創作文化趨向和精神旨趣,旨在梳理當代詩詞創作的類別或形態。
一、當代文化精神與詩詞創作的關系
文化精神是一個民族國家在發展歷史過程中形成的文化體系中特有精神氣質,代表著民族國家的文化身份和精神信仰。誠如張岱年先生所說:“精神本是對形體而言,文化的基本精神應該是對文化的具體表現而言。就字源來講,精是細微之義,神是能動的作用之義。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發展過程中精微的內在動力,也即是指導民族文化不斷前進的基本思想”。可見,文化精神對于促進民族國家發展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簡而言之,筆者以為文化精神起碼有兩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方面,文化精神是民族國家生生不息的血脈,它引導著人們在文化傳承中代代繁衍;另一方面,作為一種全民性的文化信仰與文化指導,文化精神又會在不同的發展歷史階段,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要求進行著調整和完善,每一歷史階段都會呈現出不同于其他各個階段的文化發展要求。
那么,當代文化精神是什么呢?簡單地說,就是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的文化形態。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改革開放開始,中國開啟了國家興盛、民族復興的歷史階段。伴隨政治生活的昌明盛達和經濟發展的不斷調整,當代文化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長期被忽視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于國家未來發展、民族精神信仰的重要性逐漸凸顯出來。從“繼承民族優秀傳統”到“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再到“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偉大目標,當代文化精神日漸清晰明確。而在博大精深、燦爛輝煌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包含著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當代文化精神即是這樣一種在繼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同時,又要融入當代文化符碼,從而創造出符合當下國家發展需要和大眾需求的一種文化形態,它指導并影響著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可以說,當代文化精神的基本內涵需要呈現以下三個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方面是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著緊密的內在關聯,包括情感的、形式的和哲思的等;另一方面是它必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代表,具有引領和典范的作用;第三方面是它同時又是社會民眾文化生活的精神家園,反映社會民眾的精神訴求。它們之間并非是各自獨立的,而是相互之間有著必然聯系,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那么,當代文化精神與當代詩詞創作之間又有什么關聯呢?他們之間的關系又如何理解?
中國作為以詩為內在文化精神核心的國度,在不斷發展著的各個歷史階段創造出輝煌的詩歌成就,比如古代詩歌開端的“詩三百”、浪漫主義代表的“楚辭”、承前啟后的高峰“唐詩”,以及創造了“漢語文詩文學發展的最高形式”的“宋詞”等,都是我們今天需要繼承并發揚的優秀篇章。王國維在他的《宋元戲曲史·序》中總結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后世莫能繼焉者也。”可以看到,中國的歷史長河為我們積累了深厚的詩學經驗和理論基礎。
因此,這里我們所談的當下“一代之文學”,就是在二十一世紀正在走向國家富強與民族復興的新時代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文學,當代詩詞創作也同樣處于這樣的時代框架之內。因此,當代文化精神必然要通過詩詞中表現出來,反之,詩詞創作中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呈現出當代文化精神的符碼。比如馮崢嶸創作的《巫山紅葉歌》中以“秋葉再紅”來寄予中華民族復興的精神,詩句呈現出氣勢磅礴、波瀾涌動、內涵厚重的中華民族的文化底蘊:“江山旺氣壯民魂,中華代有興邦力。璀璨文明卓不群,每從宇內樹奇勛。斯世圖南醫積弱,民心如沸事如焚。”姚泉名的《登明堂山》以探尋“漢武遺蹤”和“嵚崖”“松響”等意象回望歷史,“壯心爭可哀”的抒發可謂是以古喻今的點題:“嵚崖何所若,攢若寶蓮開。松響麒麟石,云生吳楚臺。天隨飛棧起,海駕烈風來。漢武遺蹤處,壯心爭可哀。”再如何少秋的《清潔工》以工整的古體形式和輕松的語言情調描寫了早起辛勞工作的“清潔工”形象:“早起身披四月風,輕哼小調掃西東。雖無嗩吶扶清韻,卻有心花綻碧叢。繭手躬勤清穢物,襟懷坦蕩對長空。長街凈送晨行爽,一抹新陽照桔紅。”這首詩雖然是關注社會普通勞動階層的工作狀態,但詩歌的視角在時間、空間的轉換與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以小見大,獨辟新徑,從而把當下社會中的新人物與新境界通過詩的意境展現出來,讓人讀來不禁耳目一新。
提舉上述形式風格不同的詩歌,旨在說明不論從那一類形式、哪一個角度、哪一種思維去創作,詩歌都要能夠保持與當代文化精神的內在氣韻相關聯。因為從現實意義來講,如果二者不能有機結合起來,或者當代詩詞創作無法表現當下的文化精神特征,則一定不會成為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創作,就像艾略特曾經說的那樣,“沒有任何一種藝術能像詩歌那樣頑固地恪守本民族的特征。”這里的“本民族的特征”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個民族國家發展歷史階段中的文化精神,它一定是既有傳承因子又有現實主義價值的精神形態。
從這樣一個角度來看,當代詩詞創作大體上分為兩種類型:一方面,是具有大視野、大主題的宏大敘事,這一類詩詞的內質是承襲著民族傳統的詩教傳統,以“關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為創作思維,表現出“頌”“刺”“諫”的形態特征。因此,這種創作的視角有分為兩個方面:一是站在形而上的立場中與國家民族的發展保持一致,對當下的大事件、大熱點問題表現出極大的關注熱情;一是承襲杜甫、白居易等一代傳統士大夫關注現實、關心民瘼的詩學精神,深切體察民間風物、百姓疾苦;另一方面,是以創作者個體的精神體驗為內核,在面對紛繁復雜的社會中反觀詩人自我內心的感受和經驗。這一類詩作與傳統詩教思維保持了一定的距離,又不似陶淵明式的“山水田園”風格。既有“出世”的飄逸又有“入世”的焦慮,是當代詩詞中的一個創作形態。
二、形而上的詩學觀與理想主義激情
傳統文化觀中的“文以載道”思維在人們的精神中亙古不變、歷代相承。與西方以“模仿—再現”的詩學傳統不同,中國傳統詩學更加注重形而上的社會功用性,孔子提出“興觀群怨”,清人程廷祚也指出“詩人自不諱刺,而詩之本教,蓋在于是矣。”“若夫詩之有刺,非茍而已也。蓋先王之遺澤,尚存于人心,而賢人君子弗忍置君國于度外,故發為吟詠,動有所關。……豈若后世之為詩者,于朝廷則功德祥瑞,于草野則月露風云,而甘出于無用者哉。”白居易更是直陳詩歌應“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在當代詩詞中的創作形態中,以傳統詩文觀作為作詩內核的占有很大的比重,即采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詩人們以“不絕于天地間者”自居,詩文創作以“曰明道”“紀政事”“察民隱”為己任。比如聶紺弩早期的詩,他身陷北大荒農場改造時仍通過詩歌托物言志,“寄寓了對政治運動中錯劃、誤判的看法和心情”。《鋤草》《挑水》《削土豆》等詩都屬于此類,總能在幽默、自然、平淡的詩句中寄予詩人關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其中,《鋤草》寫“何處無苗無有草,每回鋤草總傷苗。培苗長恨草相混,鋤草又憐苗太嬌。未見新苗高一尺,來鋤雜草已三遭。停鋤不覺手揮汗,物理難通心自焦。”這種傳統詩文觀讓許多心存家國情懷的詩人們即便身處逆境仍以詩為口,凸顯出強烈的士大夫心態和滿篇的“頌”“刺”“諫”詩作。
如果說聶紺弩的詩作表達的是上一代特殊歷史狀態中的所感所知,那么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詩人面對的是更為多元繁復的社會狀態和國家復興的歷史階段,詩的視野也同時進入一種紛繁復雜的多維度時空。如何尋找詩性的生長點?如何抒發時代節奏要求的詩歌?可以說,時代在發展,文明在進步,社會多元化與全球一體化讓人類步入一個前所未有的生存空間。然而,作為中華民族傳統精神內核之一的理想主義的家國情懷,在許多詩人內心深處卻一直存在著,不論社會如何變化。詩人的身份也決定了他們必然要比社會普通人更加具有憂患意識、擔當意識和反抗意識。同時,在某種意義上說,采用舊體形式創作的詩人們也比新詩作手多了一些“入世”的激情,或許是這種傳統形式中內嵌的現實主義內動力因素使然,并且凸顯出強烈的理想情懷。
人類賴以繁衍生息的精神之一便是內心深處激蕩著的理想主義作為原動力。“理想”作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之一,其深邃的積極的思想魅力和烏托邦式的生命魅惑交織在一起,歷來是傳統士大夫與現代知識分子在“出世”與“入世”之間的最高精神追求。理想主義激情促使著詩人們用詩句表達對民族復興、對國家發展的參與熱度。如《巫山紅葉歌》(馮崢嶸)、《賀珠港澳大橋通車在即》(李養環)、《江孜宗山古堡》(盧象賢)、《蓮花山謁鄧公銅像》(周學鋒)、《南巡》(韓開景)、《港珠澳大橋》(華慧娟)、《致中印邊界邊防戰士》(楊懷勝)、《喜迎十九大》(林向榮)、《軍人之夢》(朱轉娥)、《詠米神—袁隆平》(劉沐清)、《高原架線工》(王興貴)等詩作,均以形而上的維度或抒發當下發生的熱點事件,或情鑄歷史民族英雄的愛國故事,其詩學內核是以主流文化精神為主導,突顯愛國主義情操。馮崢嶸的《巫山紅葉歌》以奇特的想象、磅礴的氣勢和思通古今的筆觸勾勒出巫山的氣勢,并以此表達詩人對中華民族復興大業的堅定信念:
巫山橫劈一江開,不盡江濤萬古來。壁立林深猿嘯急,峰回峽轉水徘徊。西接高原連雪域,東瞻海氣望蓬萊。遠溯鴻蒙龍骨在,高撐碧落柱瑤臺。方圓九峽三千里,洞壑縱橫云霧起。奇峰縹緲絕凡塵,傳聞自古有仙人。旦作朝云暮為雨,高唐一賦雅無倫。今日仙人何處覓?百丈陽臺空寂寂。尋遍巫山十二峰,唯見江楓紅欲滴。漫山烈烈似驅寒,高擎如炬報秋安。擊石凌風生劍響,烘云照水卷文瀾。巫山何以多紅樹?嬌嬈應是仙魂駐。昔聞紅葉可題詩,倩誰題此江山句?君不聞、夔門水拍起罡風,自古名標天下雄。白帝城高霜磬冷,一聲史唱入秋紅。君不聞、屈祠云外楚騷聲,秭歸巖上柏松鳴。三灘舀盡西陵水,如何題得古今情?對此不由長太息,生生不竭思何極。江山旺氣壯民魂,中華代有興邦力。璀璨文明卓不群,每從宇內樹奇勛。斯世圖南醫積弱,民心如沸事如焚。恰如良木經霜后,高華美質吐清芬。我以霜吟踏秋水,秋生顏色水生文。指看高峽平湖外,萬千紅樹正繽紛。
全詩以巫山“秋葉再紅”的意象貫連,其中“江山旺氣壯民魂,中華代有興邦力”“斯世圖南醫積弱,民心如沸事如焚”等詩句無疑是詩人意欲表達的愛國主義熱情,具有激昂向上的理想主義精神品質,充分表達出詩人現實主義的理想情懷。
在對當代國家事件、熱點問題的書寫中,詩人們的關注視點大多集中在“頌”的形態而少有“刺”與“諫”,這似乎已經成為詩人們當下創作的共識。比如寫中央軍改和強軍建設的《改隸調整感賦》《圓夢》《老兵》《軍人之夢》《破陣子·強軍夢》;寫國家建設的《港珠澳大橋》《賀珠港澳大橋通車在即》《參觀江漢運河》《中衛印象》《興凱湖引水工程感吟》《高鐵》《八聲甘州·高速隨想》《八聲甘州·游長江三峽并遠觀大壩》;寫對外發展的《絲綢之路頌》《觀絲綢之路亭口車轍感一帶一路》;頌懷偉人及革命先輩的《蓮花山謁鄧公銅像》《瞻仰深圳鄧小平塑像》《賦陳德將軍》《抗日名將錄之鄧世昌》《瞻韶山毛主席遺物館》《西江月·有感習主席為農民香包捧場》等詩作都是以“頌贊”為主調,對中國改革開放及迅猛發展的抒懷之作。這一類形態的詩作并非當代詩人的新創,早在上世紀建國初期的五十年代,詩歌領域中的“頌”風便盛行一時。不論新體詩人還是舊體詩人的創作,都表現出一致性的歌頌熱情,似乎應和了傳統中“君上有令德令譽,則臣下相與詩歌以美之”的風范。然而現代社會發展已呈多元并存態勢,社會矛盾也日漸突出。詩人們如果僅僅以“頌”為主調,而忽視社會中凸顯的矛盾與人們生活中的困苦,則并非是合格的詩人,其詩作也不能起到“聞之者足以戒”的“言志”目的。
相比較而言,在關注現實、關心民瘼的詩作中,能夠深切體察民間風物、百姓疾苦的作品卻少之又少,在眾多的詩作中,《詠蕭縣“水泥妹”》一詩讀來倒是別有一番苦澀的滋味,詩中對為救夫而負重女子的充滿情感的描寫,如果不嚴格糾結詩的結構、格律等傳統律絕規則,僅看詩作抒發的理想情懷則多少有一些杜詩的氣息與激憤之感:
千古愛情奇聞多,難盡悲歡惹嗟哦。今有驚魂鄉妹子,身背水泥究為何?灰衫灰褲嬋娟罩,垢面難辨嬋娟貌。百斤壓在弱肩頭,救夫哪管丑還俏。眼中射出堅毅光,一袋一袋負重扛。有夢焉知疲和累?只盼夫君命延長。藥費如獸噬人盛,首飾家俬已賣凈。唯憑苦力多掙鈔,任他泥汗漉頭頸。步履沉沉腰已彎,卻念愛人命如懸。一步心中一念想:愿他多陪我幾年。孩兒一雙逗人愛,小辨卻無花兒戴。不是媽媽不心疼,只想桌上多個菜。饑時徒自墻腳蹲,饅頭就水和淚吞。淮水能載愁幾許?可載我愁去幾分?形若雕像目若呆,前景渺茫莫能猜。恨不將身替郎痛,三生石可證情懷。曾經是郎心上寶,亦寵亦嬌日日好。五載相歡太匆匆,為甚病魔擊郎倒?何故天教大難臨,挺將玉姿似高岑。且憑柔骨擎天起,幾人愛如此般深?愛縱深,意縱厚,怎奈天價醫難就。一介民女情如山,強撐能否夫君救?嗚呼!含悲銜恨問青天,底事渾然不見憐?但祈貧黎皆康健,不求富貴惟愿能平安。
全詩以敘事為主,語言俗白,把“水泥妹”的形態與境遇表達的清晰明暢,最后落筆“怎奈天價醫難就”是詩人意欲表現的重點,由此點題升華為“含悲銜恨問青天,底事渾然不見憐?但祈貧黎皆康健,不求富貴惟愿能平安”的期許,達到了現實與理想的高度融合。周達的《詠黃花崗木棉》一詩借“黃花崗木棉”的意象歌頌先輩的革命精神,“簪纓”“碧血”“烈炬”等代表英烈形象的詞匯連接后面的“先賢遺夢埋千古,我輩何顏說大同。惟有木棉終不負,年年崗上照人紅。”使全詩有了豐富的意喻,在“頌”中有“刺”有“諫”。
從詩的形式來看,對普通人的關注似乎新詩體更能寫出溫度來,如張先州的《砌磚工》,把普通建筑工的勞動場景嵌入進對兒女、父母的真情實感表達:
一樁樁心事
種在磚頭的縫隙里
如雨的汗水澆灌
夢里生根發芽
兒女的路
在瓦刀劃過的弧線上延伸
年邁父母的病
在撫平灰漿中療養
日子在一天天敲打中
結實起來
墻,一高再高
錯落有致的詩體就像壘砌的“墻,一高再高”,“女兒的路”“父母的病”都是“一樁樁心事”,然而生活是在一天天地像砌磚工壘砌的“墻”一樣“結實起來”,錯綜的筆法和深邃的意象疊加在一起,使詩歌在現實與理想的貼合中獨具陌生化的美感。另一首同樣寫建筑工人的舊體詩《土建工人贊》,雖然也是抒發對底層群體“位卑猶有夢飛揚”的禮贊,但因形式與語言的雙重限制,讀來似乎缺少意境化的陌生效果,少了一種幽深的意境:“晨餐風露晚披霜,一片丹心系建房。涂料鋪開多彩路,土方筑起萬重墻。三輪車奏平凡曲,滿手繭凝榮耀光。無畏緇塵經歲苦,位卑猶有夢飛揚。”
再看梅早弟的《清潔工》:“底層身處未徬徨,默默無言四季忙。兩只車輪推日月,一枝竹帚掃炎涼。幾番風雨雷驚頂,數度須眉汗滯霜。但使鵬城添靚麗,何辭污垢染吾裳。”詩中可見用詞是有了斟酌和錘煉,身處底層的身份并沒有讓清潔工“彷徨”,依舊默默地奉獻著,“炎涼”是說社會狀態,“風雨雷驚頂”“須眉汗滯霜”是寫清潔工的狀態,然而最后的“添靚麗”“染吾裳”的起調卻又落入了俗套。
由此可見,在形而上詩學觀統攝下的詩詞創作,詩人極容易進入一種觀念至上的陷阱中。因此,在書寫國家發展、民族復興進程中宏大主題(包括社會熱點、政治事件等)的價值評判的詩之“頌”“刺”“諫”要避免空泛、虛無的概念化、模式化應景之作,從而把宏大主題中不同事件的豐富細節和多元價值完全遮蔽掉了。
三、向內轉的“小情調”與現實化精神訴求
在當代詩詞的創作中,還有與形而上的宏大敘事主題創作有所不同的是我稱之為“小情調”一類創作。這里的“小情調”并非指稱詩壇流行的那些打著“抒發個人性靈”名義而拘泥于自娛自樂、自艾自怨、自言自語的小文人詩歌。這一類詩歌大多是從“大我”的姿態回歸“小我”的內心感受,以詩人的一時一感為抒發點,追求詩人自我內心對某一情緒的即時性感受,視角是向內轉的精神關注。王乾坤在談到詩歌的個人化自由創作時認為:“文學的存在理由不是直接干預社會,其本業不在直接的社會改造,而在文學性回歸,藝術審美的回歸……如果文學的創造者將這種回歸理解為一種對于時態的逃避情形,而恰恰可能是與美背道而馳,因為這種逃離只是意味著畸形偏安,而不是自由”。
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一類“小情調”的詩作與傳統文人的“避世情緒”和上世紀八十年代新詩思潮中的“個人化”寫作又有所不同。所謂“個人化”寫作,是一些詩人對“政治化”“觀念化”大行其道的反駁,是對群體性公共發言者的“疏離”,以自我內心的性情感知為主導,從而強調“詩貴性情”(沈德潛)的創作路徑。這種觀念也讓許多詩人因此“誤解了詩與現實的關系,認為詩與政治、現實無關,只需按照自己的個人視角來打量世界即可,也就是說不客觀、全面地把握世界,而只是抓住自己所感受、體驗到的一個或幾個側面來揭示自己對世界的認知”,從而進入自我劃定的一山一水的小天地之中。可以說,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個人化”寫作在疏離政治性話語、顛覆崇高性藩籬的同時,并沒有遠離現實和拋棄理想,也正是如此才讓新時期以來的詩歌精神指向有了生命的意味和理性的深度,“從淺層的自我表現(詩的個人化)流向深層的自我表現(向意識深層進軍)”。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非常遺憾的當代詩詞創作場景,不論是宏大主題敘事還是個人化自我抒情,都存在著空洞無物、無病呻吟,尋章摘句、風花雪月、模山范水、歌功頌德、人云亦云的寫作之風盛行。當然,在這樣普遍流于形式的詩詞環境中,也會有一些相對不錯的作品,雖然很少。
從當代詩詞的“小情調”寫作來看,一方面是詩人自身以這種“田園式”的形態表達情感寄托的手段,如“池邊楊柳未萌芽,室內山茶已綻花。許是樓高近瑤界,春光早進老農家。”(《農家新居》)“曲岸分明鏡未磨,游魚驚起野天鵝。螺峰弄影秋光里,一葉輕舟剪碧波。”(《題星火水庫》)“綠是春蘭紅是花,柴扉半掩舊籬笆。客驚黃犬迎人吠,燕剪紫薇依水斜。幾縷閑思融筆硯,滿腔雅趣共鄰家。炊煙小院送香晚,一醉鄉情詩酒茶。”(《鄉歸》)等詩作。黃全知的《村雪》:“寒氛連夜鎖煙波,吹落梅花贈素娥。百步猶聞香蕊淡,初妝自帶玉顏酡。鄰家稚子嘗新雪,隔岸田翁拍短蓑。悄探西疇棉絮下,麥芽應比去年多。”通過雪降大地的姿態描述,暢想“瑞雪兆豐年”的年景。這類創作大多是以詩人自我對世界的感知為核心,把對“大我”的關注轉向一種適度的“小我”狀態,更多地是追求詩歌的意境與語言的錘煉,盡量避免盲目抒情與宣泄的混亂情緒。
另一方面,向內轉也是當下許多詩人在處理詩歌與社會關系、現實關照時所采取的一種方式,即以“逃避姿態”或“個人化”寫作來揭示自己對現實的理解和變化。因此,詩人在內斂化的田園抒情與精神扣問寫作中,內隱的依然是在身體出世后的精神入世情結,因而詩歌內核中總會或顯或隱的凸顯出現實主義的理趣。
黃曙楚的《鄉歸》是一首抒發個人情趣的詩,把詩人回歸鄉里的情思通過“花”“燕”“舊籬笆”“黃犬”等鄉間常見事物烘托出來,寄予了濃濃鄉情與閑思雅趣:“綠是春蘭紅是花,柴扉半掩舊籬笆。客驚黃犬迎人吠,燕剪紫薇依水斜。幾縷閑思融筆硯,滿腔雅趣共鄰家。炊煙小院送香晚,一醉鄉情詩酒茶。”侯明的《游福永鳳凰山》、羅金龍的《秋登大雁塔放歌》是詩人登山、登塔時的感受,與前一首不同的是,兩首詩在情感的視角上有著較為一致的落點,即對現實的闡發。我們看原詩為:“鳳凰山上覓仙途,幽處喈喈鳥自呼。芳草牽人花色暖,瓊林布蔭葉光敷。近攀玄石嘆高絕,遠眺白云知不孤。更待修持生兩翼,乘風一舉出青梧。”(《游福永鳳凰山》)“乘風來上最高樓,認得題名在上頭。一局江山存氣象,百年事業壯春秋。欄桿拍遍情何已,楓葉堆成韻欲浮。好是長安形勝地,重開絲路寫風流。”(《秋登大雁塔放歌》)通過詩歌可見,前一首是在寫景寄情中自喻“鳳凰涅槃”的壯志,而后一首則是以登“高樓”、看“江山”來凸顯“指點江山”的豪氣。
還有許多詩人的創作是“以物寄懷”,即通過對某種物像的感悟而抒發自己對現實的態度。比如王連生的《木棉樹》:“老樹孤高秀出林,丹霞萬朵入云深。三千里外天風滌,數百年間海雨侵。此日滿城同仰首,當時一面早傾心。落花亦帶英雄氣,觸地還傳叩石音。”以木棉樹的“孤高”喻指歷史的輪回與自己的心境;曹治果《讀〈西游記〉札記》是一首用俗白語言寫出的“打油詩”:“一路西天屢劫災,百般請得救兵來。神仙擺下玩猴陣,哪個妖精無后臺。”這類詩大多是借某種事件或情緒,揭示當下的某種狀態,有“以古喻今”的目的。《讀〈西游記〉札記》這首詩就是借孫悟空“屢劫災”來諷喻現實社會中的“后臺”現象。
當然,這種“向內轉”的詩歌創作能夠避免大而空、口號式的弊端,但如果詩人的精神生活不能完全脫離于世俗生活之外,而又在精神錘煉與情緒沉淀中無法把握現實社會的變化規律,或者不能理解豐富多元的事物發展過程。那么,在“出世”與“入世”的矛盾中也極容易造成詩歌創作內涵空泛、抒情無趣或者言不對物的現象。比如劉洪云的《悟萍》,詩人的本意是寫“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塘中青蓮,寫青蓮在“浮塵”中的“清明”“風華”與“寂寞”,借此抒發詩人在塵世間被俗事所累的心態,然而偏偏要提氣寫出了“水險由他三尺浪,風高任爾百帆橫。云開霧去縱零落,偏有秋心蓮長成”的句子,看似豪邁的氣象卻因脫離寫意的情境,不僅沒有達到詩意升華的效果,反而完全破壞了清淡舒緩的詩境。再如向言強的《月亮灣》:“燈光燦爛映檐楹,玉殿瓊樓頌太平。昔日偉人揮手處,一輪皓月照新城。”雖然其意是對城市發展新貌的頌揚,但這種貌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頌歌”卻是既無詩性又無內涵的口號詩,基本上是脫離現實的失敗作品。不僅詩詞創作如此,即便新詩也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如馬向虎的《礦工》一詩:“礦工/一束光/跌落千米地下/在黑暗的驚恐中抖索//礦工/一咬牙,一甩肩/用汗水拯救出深鎖經年的光明//一池清水/沖走戰斗后的疲憊/穿上陽光回家”。這首以“礦工”為抒情主題的詩歌雖然以看似意象豐富、內涵深刻,但并沒有產生陌生化的效果,反而使人讀來索然無趣。可以說,這種隨意抒情的現象在當代詩詞創作中大行其道,即便是我們不考量詩詞寫作的遣詞、用典、聯句及氣韻轉合等作詩基本因素,也應該以老老實實的態度認真探求自己內心的真切感知,切合自己周圍的現實生活狀態。
四、對當代詩詞批評的一點反思
中國人歷來重視反思,比如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荀子也說“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一般來說,對文學作品的批評,無外乎是基于研究者的學理性知識或者對于當下創作的一種感知和判斷,這種感知與判斷同樣也是一種反思的過程,雖然不一定會全部正確,但總歸是在眾言多元思想中的一種反思性自省。
應該說,當代詩詞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它在傳統形式的規約下蹣跚前行、步履艱難。時至今日,正處在傳統與現代的關鍵轉型時期,如何在繼承中創造新時代的新詩詞形態,是每一個創作者與研究者的歷史使命。我以為,對于當代詩詞的傳承與創新,應該在以下幾個方面加大力度:
首先,對于當代詩詞創作中的代表詩人及其優秀文本,研究者應該下大力氣去研究和推廣,而對于其中所出現的種種問題,研究者也應該力圖做一深刻的剖析和正確的引導,而不僅僅是一味地表揚、跟風地頌贊。
其次,突破當前所謂研究學科的壁壘,不論是古代文學研究學者,抑或現當代文學的研究學者,都應該以客觀、開闊的視野面對當代詩詞的創作與研究。在當前國家大力倡導優秀傳統文化回歸的契機下,特別是我們的教育促使許多學者并不能融通古今學養的現狀中,更應該各自發揮一己之特長,共同把古今學科的優勢發揮出來,為當代詩詞的創作與發展做好指路標、墊腳石工作。
再次,對于詩歌創作者及其作品而言,應該從作品的外在形式和思想內涵兩方面入手構建一種有效而務實的美學評價體系。在舉賢排差的基礎上,對當代詩詞的立意之境界、情感之真誠、思想之深刻、態式之嚴謹、美感之悅目、文風之趣味等條件加以系統研究。我們無意做某種形式上的“權威”,但我們應該以此來引導當代詩詞的良性發展。
不可否認,詩歌創作是一種極具個性化的藝術創造。但是,我們不能也不應該以“個性化創作”的理由來拒絕人類對美的共性的認知,因為美的標準是人類精神審美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共同遵奉的范式,就像我們傳統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與西方“你想別人怎么對待你,你就怎么對待別人”的“同理心”一樣共同屬于人類的“道德金規”(Golden Rule)。詩歌創作也會有人類共同認同的“道德金規”,只是這個“道德金規”我們還沒有建立起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