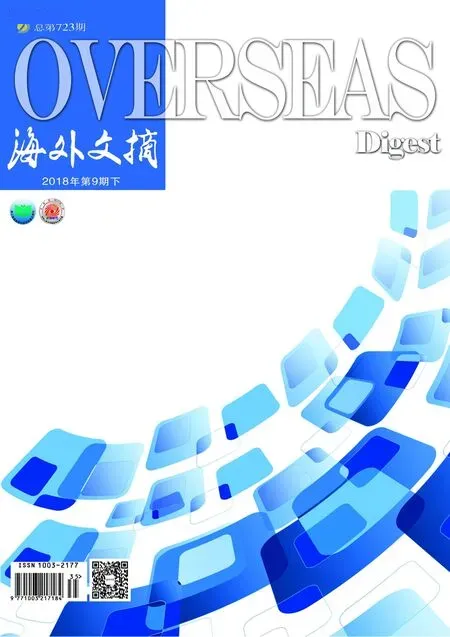中韓集體記憶的影像建構對比分析
——以電影《鬼鄉》和《二十二》為例
魏曉涵
(中國傳媒大學,北京 100024)
1 媒介建構集體記憶
集體記憶是指特定的社會群體共享往事的過程和結果。哈布瓦赫認為記憶不是客觀事實,它通過語言這種工具來實現,在事實的基礎上由社會框架重新建構,記憶是過去、現在和未來。包括電影在內的大眾媒介在集體記憶的構建中起到重要作用,社會群體在交流過程中獲得認同,“媒介與集體記憶”成為一個研究分支。
本文聚焦的“慰安婦”這一集體記憶發生在二戰時期,涉及許多亞洲國家,其中中韓兩國受害者的數量占較大比重。兩國文化淵源相近,但在幾十年的發展進程中,和侵害國日本的外交關系、本國的社會發展演化出較大的差異,對同一記憶的媒介呈現和受眾反饋亦不同。慰安婦受害者陸續離世,所剩無幾,近十年兩國戰后一代的作者都生產了相關影像。韓國以慰安婦為題材的影像作品包括《最后一個慰安婦》《鬼鄉》等,中國有《二十二》《軍中樂園》等作品,有紀錄片、劇情片等。
韓國的《鬼鄉》和中國的《二十二》分別公映于2016和2017年,是兩國首次登上大銀幕的慰安婦題材的影像作品。《鬼鄉》調動韓國七萬五千民眾募集了12億韓元填補投資空缺,上映后連續兩周登頂票房冠軍,引發整個韓國社會的討論。《二十二》同樣是通過民眾自發的眾籌填補資金缺口,在播出前后引發大量媒體關注和全民話題討論。本文對比兩部作品的影像敘事,及兩國的輿論表現,試圖分析中韓兩國民眾對集體記憶的構建差異,及原因所在。
2 影像敘事對比
2.1 主題及隱喻
《鬼鄉》以少女成長作為故事主線,采用雙線結構,分別敘述了兩個時空里少女貞敏被抓走成為慰安婦和少女恩京被潛入家中的匪徒強暴的故事。將兩個同樣被強權傷害的故事交錯敘述,最終以歸鄉的儀式結尾,完成兩人跨越時空的對話,深化了侵略給個體和民族帶來的傷害。
《二十二》以戰爭受害者為主角,讓老人口述,這些記憶不僅僅通過言語表達,更展現在她們的動作、習慣中;此外觸角涉及受害者晚年生活。
當下通過慰安婦話題控訴日本二戰侵略暴行,爭取道歉和賠償,已不再是媒介的主體訴求。它們不約而同地淡化了控訴戰爭傷害的主題,而進行對外延展。《鬼鄉》將對“慰安婦”的傷害延展到對“女性”的傷害,增加社會性別視角,講的是不同時代的女性遭受的傷害和苦難,在影片中,即使生活在現代的慰安婦老人也因為歷史受歧視;《二十二》則關注“慰安婦”身份之外的“農村老年人”身份,中國的慰安婦分散在全國各農村地區,并非像韓國慰安婦由政府統一照料。展現她們生活中的困境,弱化了歷史傷害這一因素的影響程度。
這樣的主題表達構成一種隱喻,即走出傷痛的歷史記憶,實現自我療愈和救贖。但仔細分辨,兩者對歷史的認知是截然不同的,《鬼鄉》的基調更為沉重,通過跨時空的多重詢喚,讓集體記憶中的苦難更沉重。《二十二》則淡化苦難,老人們回憶過去的篇幅越來越少,展現當下平靜生活的畫面越來越多,表達趨于輕盈,呈現對苦難逐漸解脫的趨勢。
2.2 畫面與敘事
《鬼鄉》的畫面構圖精巧,用了大量鄉間唯美風光的鏡頭;《二十二》使用了大量空鏡頭交代老人生活環境,兩部電影節奏都相對緩慢。
存在區別的是,《鬼鄉》沒有避諱傷痛記憶,長短鏡頭結合、多角度敘述。如長鏡頭俯拍,還原少女們在慰安所受到傷害的場景、她們的哭泣聲、尖叫聲、身上的傷痕、害怕的神情等,轉而切換到鄉間唯美畫面,兩者交替襯得現實殘酷,外露且煽情。《二十二》使用了大量的長鏡頭和固定鏡頭,少有短鏡頭。影片對歷史的還原通過老人口述、尋訪原址實現,過程破碎,沒有完整敘事線。此外加入許多對受害者個人命運的敘述,歷史記憶反而被隱去。
兩部影片都存在批判視角,《鬼鄉》中老人試圖尋求政府的幫助,受到的卻是年輕人的白眼;《二十二》用環境畫面呈現老人心酸的晚景。
對比兩部影片的鏡頭語言和敘事方式,差異較大。《鬼鄉》試圖尋找這種歷史記憶與現實生活的關聯性,不否認這種傷害的殘酷與深遠影響;而《二十二》則選擇淡化歷史記憶帶來的傷痛,同時將歷史傷害也隱去,營造出和諧平靜的氛圍。
2.3 身份與認同
“殖民身份”是影片中慰安婦最基本的身份認同。影片分別從不同的角度豐富了對身份認同的闡釋。
《鬼鄉》在“殖民身份”的基礎上強化了主人公的民族身份。影片使用了大量民族符號,如薩滿祭司、韓國傳統曲藝、韓服,宣泄對故鄉的依戀、對家人的依賴,跳脫出在“受害”和“侵害”的對立中形成的身份認同,個人命運被視作民族苦痛的縮影。而在最后的部分,通過一場祭司舞蹈隱喻苦難的升華,達到民族的集體認同。
在民族認同的表達上,《二十二》是失語的,集體記憶獨立成為個體化的境遇,沒有形成聯結。她們的身份認同通過和政府、家人的互動中構建起來;例如老人樂于表露自己“女紅軍”的身份,談到家人會流淚。這些互動通過側寫的鏡頭來展示,對“家”的認同感比對“民族”更為接近現實。
值得一提的是,兩部影片對對方國家的記憶的呈現。《鬼鄉》中和主人公一起關在慰安所的還有中國女孩,《二十二》中有一位受訪老人來自南朝鮮,并在晚年受到韓國志愿者的幫助。集體記憶跳脫出國家和民族的層面,在全球的語境下尋求身份認同感。
3 對集體記憶的消費與民族主義
總的來說,兩部影片對慰安婦集體記憶的呈現和表達的文化主張是截然不同的。雖然都存在救贖過去、展望未來的積極態度,《鬼鄉》的傾向于深化歷史苦難,喚起民族共同的情感和記憶;《二十二》則隱去了苦難,個體化,回歸人性的層面,民族集體意識在其中鮮少出現,也并未得到強化。
影片的文本抵達受眾后激發的輿論截然相反,各自與文本的建構方式背道而馳。
《鬼鄉》渲染鄉土情結和民族身份,韓國社會反而關注受害個體。民眾開始反思是否對這個群體有足夠的關注,輿論落實到個體化的層面。
在《二十二》中被隱去的民族主義情緒引起了一次劇烈的輿論爆發,自媒體熱議的焦點多集中在不忘民族苦難,銘記歷史。民眾自發捍衛“受害”身份,深化集體記憶中的恥感,曾一度出現看電影時笑出聲來的觀眾受到其他現場觀眾的人身攻擊,被批為“不愛國”的新聞。
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進行解讀。上世紀90年代初,韓國慰安婦問題才開始受關注,一度被男權社會認為是“不潔的”,更早的時候這些戰爭受害者甚至被當局以有傷風化的罪名逮捕。受到關注后,韓國輿論的議題集中在如何扭轉社會的刻板印象。
《鬼鄉》上映恰逢日韓就慰安婦問題達成一致的節點,日方若履行承諾,韓方則同意終結慰安婦問題,一度引發社會不滿和挫敗。自上世紀90年代慰安婦議題在韓國出現后,一度成為日韓外交之間的絆腳石。韓國政府的外交姿態相當強硬,將其定性為“反人道主義的非法行為”,韓國憲法法院2011年裁定其政府未努力解決慰安婦問題,直接對韓國政府造成巨大壓力。
民間團體認為日方推卸責任,舉行大量游行示威,也給韓國政府造成了壓力。《鬼鄉》是民間表達的一部分。媒介的常態化表達,讓觀念更新和強化,甚至倒逼政府做出優化和改變。
中國語境下,慰安婦從屬于戰爭問題,常常以弱者的形象出現,這種形象標簽化、反生活常態,借以激起民族主義情緒。《二十二》出現之前,慰安婦的議題在國內媒體中很長一段時間不受關注。政府在外交上的態度趨于中庸,進一步激化民眾的民族情緒,即使影片本身弱化了這方面的表達,“敏感仇外的民族主義”依舊在網絡輿論中迎來一次大爆發。
4 結語
在地文化的潛移默化、歷史現實等因素的綜合影響影響了媒介對集體記憶的表達,反映在慰安婦問題上,基于和平的大環境,中韓的媒介建構都呈現出治愈傷痕、期盼未來的希冀;不同的是,前者試圖抹去傷害,后者則在強化傷痛的記憶。受眾對媒介的記憶建構并非全盤接受,而是基于現實語境和歷史記憶對媒介的表達進行二次解讀,演化出新的群體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