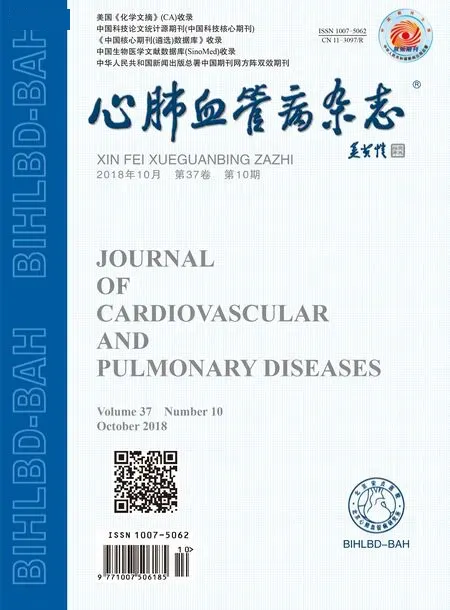關注免疫炎癥及其標志物在動脈硬化性心血管病中的作用
程仕彤 王綠婭
免疫是機體抵抗外敵感染和入侵的自我保護行為,適當的免疫反應能清除病原體,有利于機體,但免疫反應過度則對機體產生傷害,炎癥反應就是劇烈的免疫反應的結果。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炎癥與動脈粥樣硬化(arteriosclerosis,As)的關系已成為近年的研究熱點。大量研究證實,炎癥就是免疫的過程,免疫細胞中單核/巨噬細胞、肥大細胞、自然殺傷細胞、中性粒細胞和樹突狀細胞,廣泛參與As過程。As是由脂蛋白、高血壓、高血糖、自由基、感染性微生物、吸煙等損傷因素誘導內皮細胞功能紊亂進而引發炎癥。系統性炎癥可通過加速As、降低斑塊穩定性、導致血管內皮功能障礙等多方面作用增加個體罹患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血管病(arteriosclerotic cardiovascular disease,ASCVD)的風險[3-5]。 眾多研究均證實炎癥標志物水平與升高與ASCVD發病率和死亡率密切相關[1];實驗研究顯示,增強炎性反應可增加As程度,且抗炎藥可延緩甚至減輕As[2-3]。因此深入了解免疫炎癥在As發生發展中的作用及其機制,將有助于探索應用合適的抗炎藥物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風險,甚至有望早期阻止或逆轉血管炎癥狀態以預防ASCVD發生。
本文將對免疫炎癥對ASCVD的作用及其機制及炎癥標志物的最新研究進展加以綜述,旨在從免疫學角度更好的理解炎癥的過程及炎癥標志物的作用,有助力針對性開發新型抗炎藥物及心得干預措施。
1.免疫炎癥與動脈粥樣硬化
(1)免疫細胞:免疫細胞包括淋巴細胞和各種吞噬細胞等,T淋巴細胞是一個多功能的細胞群,調節性T淋巴細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s)是控制體內自身免疫反應性的T細胞亞群、效應T細胞(effector T cells,Teffs)是接受抗原刺激后經過增殖分化形成的T細胞亞群,可介導殺傷作用,同時還能釋放出免疫活性物質—淋巴因子,如白細胞介素,干擾素等。參與免疫應答的細胞還有漿細胞、粒細胞、肥大細胞、抗原呈遞細胞及單核吞噬細胞系統的細胞。免疫應答細胞是機體抵御微生物和異物入侵的第一道防線,廣泛參與As中泡沫細胞形成、斑塊內基質降解、細胞凋亡、血管新生和斑塊破裂等事件。
(2)炎癥與動脈粥樣硬化:炎癥反應包括急性、慢性、以及亞健康的輕度系統性炎癥,都可對血管內皮細胞功能以及動脈血管的機械性能產生影響。在炎癥環境下招募大量單核細胞進入動脈分化為巨噬細胞,其生物學功能得以激活,無限制的吞噬脂質并分化成泡沫細胞,不斷融合組成As斑塊脂質核心;進而炎癥細胞因子和活性氧擴大炎癥反應,釋放更多的炎癥信號從而造成晚期病變的壞死核心[6]。同時,炎癥刺激血管內皮細胞降低對一氧化氮(nitric oxide,NO)的生物利用度和增加內皮素-1(endothelin-1,ET-1)的水平促使As加重,NO水平降低又可以增加單核細胞粘附,周而復始惡性循環[7]。內皮細胞受損后在 IL-2,IL-8等促炎細胞因子(proinflammatory cytokines,PCs)的協同作用下,引起粘附分子表達增加并促進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 1,MCP-1)產生和白細胞的遷移及活化[8]。 樹突細胞(dendritic cells,DCs)和效應T細胞等抗原呈遞細胞在這類細胞因子的合成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促進 As斑塊進展[9]。
另一方面,炎癥可以促使血管纖維化和血管平滑肌細胞增殖[1]。血管平滑肌更能在炎癥基礎上向成骨細胞表型轉化并促使動脈中層的礦化和鈣化[10]。同時炎性細胞可以產生多種細胞因子和金屬蛋白酶來調控心血管結構的改變:當血液中炎癥標志物水平升高,金屬蛋白酶得以激活并促使血管壁的彈性蛋白和膠原蛋白降解[11]。炎癥還可以進一步促使斑塊破裂導致急性冠脈綜合征的發生[8]。促炎細胞因子也可以通過活化血小板和內皮細胞進而增加心血管事件的風險[12]。系統性亞臨床輕度炎癥也被證實與動脈粥樣硬化、動脈彈性缺失,以及大多數心血管風險因素都密切相關,尤其是高血壓和糖尿病[13]。也有研究在應用抗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藥物的類風濕患者中發現降低炎癥水平可以改善動脈硬化情況[3]。
總之,炎癥在內皮細胞功能障礙、平滑肌遷移、氧化應激、血管鈣化、彈性蛋白水解、膠原蛋白降解等眾多方面對As至關重要。
2.炎癥標志物與動脈粥樣硬化
(1)白細胞計數:As是由血管壁內各類白細胞間的慢性炎癥反應所導致的一種綜合征,機制十分復雜,但相關的血漿炎癥標志物是很有潛力的心血管風險預測工具[14]。在慢性低強度炎癥的影響下,受炎癥刺激的白細胞可粘附于血管內皮并輕易穿透血管內層造成毛細血管白細胞淤滯和血管阻力增加,還可釋放多種可能導致血管損傷加重的水解酶、細胞因子和生長因子,所以白細胞總數計數一直是一個成本低且應用廣泛的炎癥狀態評估指標[1]。已有多個報道證實白細胞計數增高與As和ASCVD密切相關[15],但白細胞總數受種族和性別影響較大難以界定統一的參考區間[16]。
越來越多證據表明,白細胞分類計數在預測ASCVD風險方面更優于白細胞總數[17],尤其是中性粒細胞,已經被推薦作為絕經后高血壓女性患者的心血管疾病預后標志物應用于臨床[18]。研究報道,As與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和白細胞總數計數都相關[19-20]。研究也發現中心動脈壓增強指數(central augmentation index,CAIx)僅與女性的單核細胞計數密切相關,而動脈內膜中層厚度(intimamedia thickness,IMT)僅與男性的中性粒細胞計數密切相關,可能與不同性激素對血管功能的影響以及人體測量學指標(如體脂分布、平均身高、主動脈長度)的影響等有關[21]。家族性地中海熱(familial Mediterranean fever,FMF)是一種罕見的遺傳病,以反復發熱和腹膜炎為特征,也有較少表現為胸膜炎和心包炎。研究該病人群中同樣發現了其反復和持續的炎癥狀態與As程度密切相關,與炎癥標志物包括白細胞總數計數、C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血細胞沉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ESR)、纖維蛋白原和中性粒細胞-淋巴細胞比值(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NLR)等密切相關,而與基因突變無關。
NLR是白細胞分類計數即可獲得的一種高性價比的炎癥及動脈粥樣硬化進展標志物和心血管并發癥的系統預后標志物,對于心血管疾病的預測能力明顯強于其他白細胞計數類結果,在心肌梗死和冠心病的預后方面尤為突出[22-23]。近期也有研究報道了NLR和冠狀動脈鈣化評分存在獨立的相關性,或可成為心血管風險評估的附加檢測指標[24]。Yaman等學者還發現成功接受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的 ST段升高型心肌梗死(ST-segment elevated myocardial infarction,STEMI)患者中,其 As程度的降低與 NLR的降低密切相關[25]。
中性粒細胞計數和NLR的風險預測和疾病預后能力尤為突出。考慮到血細胞檢測的成本低易操作應用范圍廣等特點,未來或可將其作為附加評價指標納入心血管疾病的風險評估和疾病預后評價體系當中。
(2)細胞因子:細胞因子可以通過刺激血管平滑肌細胞和間質細胞的增殖來激化增生性血管疾病的進展,而白介素是一類由免疫細胞產生的具有促炎作用的細胞因子,可以通過持續的招募并活化白細胞和刺激纖維母細胞增殖來激發急性炎癥反應[6]。 IL-6,IL-1和 TNF-α可以通過阻礙 NO的內皮下釋放以及以劑量依賴性方式增加內皮細胞釋放ET-1來調節血管緊張度[1]。ET-1既是血管收縮劑又是平滑肌細胞和成纖維細胞的促細胞分裂劑,而IL-6和IL-1則分別是最有可能的和最弱效的ET-1釋放刺激劑[26]。有研究報道在代謝綜合征患者中IL-6水平與As的發展和微血管功能障礙密切相關[27],但目前關于IL-6與血管內皮細胞功能障礙之間的關系尚存爭議[8,28]。
除IL-6外,其他很多細胞因子與心血管疾病之間的相關性也都存在爭議。近期有研究報道并未在有先兆子癇妊娠史的女性患者中發現多種炎癥標志物的水平,包括1型可溶性TNF受體,與先兆子癇或系統血管狀態之間存在關聯[29]。IL-18曾被定義為冠狀動脈事件的獨立預測因素并與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的形成、進展及其脆性軍密切相關[30],且與代謝綜合征患者的As程度密切相關[31],這類標志物也有可能成為ASCVD風險的評估和疾病預后的檢測指標或成為抗炎性心血管疾病藥物的開發靶點。
(3)CRP和高敏感度CRP:CRP是一種提示慢性輕度炎癥的生物標志物同時也是用于預測健康人和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心血管事件的急性期反應物,是唯一與血管壁生物學相關的循環生物標志物[12,33-34]。 有研究報道 CRP與血流介導擴張(flow mediated dilatation,FMD)相關且其水平在不同種族人群中都被證實與動脈血管功能的指數相關[14],也有研究報道CRP升高與動脈血流速度密切相關,提示炎癥與動脈硬化之間存在關聯[35]。但是涉及到CRP可能導致動脈血管功能障礙和動脈粥樣硬化的病因學研究的結果卻存在爭議,有研究報道在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癥患者中并未發現CRP與血管功能障礙的相關性[36-37],也有研究報道在校準了其他心血管風險因素后CRP與動脈硬化程度之間并無相關性[38]。
與CRP相比,hsCRP被認為是更好的ASCVD風險預測標志物,已有多個研究報道hsCRP與As相關[11,39-41]且與高血壓、肥胖、血脂異常等多個傳統的心血管風險因素和白細胞計數、IL-6、纖維素原等炎癥標志物水平均相關[39],但日本人群的研究報道并未發現此種關聯[38]。
CRP和hsCRP在代謝綜合征、腎移植、糖尿病和類風濕患者中均被發現與動脈硬化密切相關并且如減重、鍛煉、戒煙、服用降脂藥物等多種可以降低心血管風險的干預手段也被發現同時降低了hsCRP水平[14]。這提示CRP和hsCRP或許可以成為如代謝綜合征和類風濕患者這類特定人群的心血管疾病預測和預后標志物或者藥物干預靶點,但在其他人群的應用價值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4)環氧合酶-2:在炎癥過程中,磷脂酶將白細胞膜上的磷脂水解成花生四烯酸,促使前列腺素通過環加氧酶途徑合成,這個過程涉及環氧合酶-1(cyclooxygenase-1,COX-1)和 COX-2。 通過 COX-2途徑合成的前列腺素通過上調動脈粥樣硬化病灶的巨噬細胞來延續炎癥反應并將其他炎癥介質的影響放大[42]。微粒體前列腺素E2合成酶-1(microsomal prostaglandin E2 synthase,mPGES-1)是與 COX-2進行初級耦合的一種合成酶,在發炎的組織中明顯上調,且和COX-2一樣在頸動脈斑塊的脆弱區域明顯上調,是As和中風發生發展過程中的關鍵酶,也許對斑塊的穩定性產生負面影響[43-44]。

圖1 動脈粥樣硬化相關的炎癥標志物及作為相關標志物的適用范圍[14]
在肺循環過程中提示了COX-2和血管重構之間的相關性。COX-2在肺動脈平滑肌細胞缺氧期間上調,且與內皮素受體的上調和血管內巨噬細胞的聚集相關[45-46]。有研究報道選擇性的抑制COX-2會損害血管介質的平衡并促使血管增生重塑和血小板沉積,還會促進血管內血栓形成,與多個心血管事件相關聯[46]。
雖然眾多研究證實了COX-2與炎癥和As之間的相關性,并且可以得到相關分子作用機制的理論支持,但是長期的COX-2抑制卻并沒有觀察到改善動脈硬化的結果,這可能與COX-2可能對血管產生的如促血栓等其他負面作用相關[14]。研究與COX-2的表達和分子機制方面均有作為醫療干預靶點的可能性(圖 1)[14]。
(5)其他:除上述幾類炎癥標志物外,還有眾多針對細胞粘附分子(cell adhesion molecules,CAMs)、microRNAs、口腔炎癥與As之間相關性的研究[14],現將研究結果簡單總結如下:CAMs中血清P-選擇素、血清血管細胞粘附因子-1(vasc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1,VCAM-1)、血漿血管粘附蛋白-1(vascular adhesion protein-1,VAP-1)、細胞間粘附分子-1(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ICAM-1)等均被報道與As相關,主要集中于周圍血管病患者、頑固性高血壓患者以及60歲以上的人群[47-48]。
口腔炎癥中,有報道提示牙周炎患者有更高的ASCVD風險,且As程度和相關風險與牙周炎的嚴重程度呈正相關。但是尚未見牙周炎和As的共生關系,也未見As化與牙源性炎癥相關的報道[49]。
在眾多針對炎癥相關microRNA與As的研究發現,miR-126、miR-10a、miR-663、miR-181b、miR-92a、miR-21、miR-1185等均可直接或間接通過作用于本文闡述的幾類炎癥標志物和炎癥通路,進而對ASCVD的發生發展產生影響[14]。但是,考慮到人類目前對非編碼RNA的具體作用和功能了解都還十分有限,將microRNA作為醫療干預靶點或手段應用于臨床尚為時過早,但是仍可以考慮其作為提示血管功能結構發生改變或者斑塊不穩定性的預測或預后性標志物投入臨床應用。
3.總結與展望
免疫炎癥與As之間的相關性已經成為了共識,As是一種炎性疾病,低強度的炎癥反應參與血管內皮功能障礙至斑塊形成、破裂和急性血栓形成的全部過程[14]。炎癥標志物反應機體對于刺激的一種防御反應的狀態,大多已經成為臨床常規檢測項目且技術成熟成本低廉,非常適合臨床應用,并有助于完善現有的心血管風險預測模型,提高臨床對心血管事件高危人群的識別和管理能力。但尚需進行大量現有炎癥標志物在不同人群的ASCVD風險評估方面的適用性研究。同時,還需要針對各類炎癥通路中涉及的關鍵分子及相關作用機制進行更深入的科學研究,并開發用于逆轉As或穩定斑塊等方面的抗炎藥物或干預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