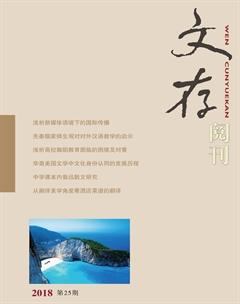老家·老物·老相思
趙紫伶
我們這里的人稱呼故鄉不用故鄉,太文縐縐了。我們叫它,老家。
至于老家為什么叫老家,其實很顯而易見。老家往往是農村,住在那里的人又往往是老人。老家自己也著實老了,里面都是老了的人,嘮著和他們一樣老的家常,耕著比他們更老的田。老家就像一個垂暮之年的老人,端著煮得溫熱的稀飯,向火坐在煤爐邊,拉著不知哪家長與哪家短。
我們的回歸往往能使忙著農活的老家增添幾分朝氣。然而朝氣的根雖然是這里,但總是無法與這里融合,像是個過客,卻又偏偏想在這里找到那么幾分似有似無的歸屬感。
我的老家很簡單。回蕩在綿延竹林里的蟬鳴,從冰涼溪水上空略過的熱浪,有著銹藍鐵皮禿嚕嚕冒著黑煙的火車,記憶就這樣帶著它們從夏日的尾巴尖上劃過。
事實證明,孩子的折騰能力是無窮的。在把家里能摸的東西摸個遍,能翻的東西翻個遍后,我被家長三下兩下趕出了家門,“去去去,外面玩去,晚上回來吃飯就是。”明明是被趕出去卻如蒙大赦的我,在屋后的田坎上追雞趕鴨嚇狗,掰玉米穗扯野花揪枯草到處亂扔。撒歡不過一會兒,雞狗見我都躲得遠遠的,生怕我再來找他們麻煩。找不著樂子的我只好改換場地,頂著熱浪踏著鄉間公路沿山面行走。邊走又邊踢著大貨車經過抖下在路面的小石子,踢著踢著又差點因用力過大把自己絆倒,悻悻作罷,垂頭喪氣地好好走路。
不多時,就尋到一個看起來簡陋的舊火車站,但所幸還在使用。一下子發現新大陸的我趕緊買了張最便宜的往返車票。售票員大媽面前瓜子殼已經“堆積成山”,旁邊還放有一些新鮮蔬菜,像是農家剛采摘下的。一見著我,售票大媽像是一下子找到了解悶兒的人,我剛剛買完票就迫不及待地問起了我:“欸!放假了啊!你是哪家的啊?”受寵若驚的我支支吾吾蒙混回答了幾句,大媽也看出我尷尬的樣子,繼續磕起瓜子笑著給我指了一下候車室。我拿著車票從盛情中逃了出來。
看了看地名,下一站是旁邊的另一個小村子。坐在候車室里,百無聊賴地打量著這里。說是候車室其實都是官方說法了,這里看起來更像是一個廢棄了的教室,后面黑板上還貼有火車的時間表和行駛軌跡,后門早已不知所蹤。兩側的墻壁上還貼著大紅標語,窗戶上貼著飄飄欲落的春節窗花。椅子是長條木凳,一看就知道是農村家家戶戶都有的那種。地上還有一些零零散散的碎菜葉,上面沾染著新鮮的露水與泥土。搜尋一遍毫無收獲,最終跳出窗外。陽光穿過縫隙,試圖還原窗花的樣子,卻最終和著熱量一起破碎在寂靜里。
“噗——”火車在外面停下。我起身迎了上去。已經不存在什么書中的綠皮火車了,但它依舊顯得老舊,并相當落后于城市里的火車。墨藍色的外殼上有著幾處銹掉了的空缺,直愣愣地露出鐵皮來,窗戶合應著鐵皮,也大打開著。它喘著黑煙停下,最后兩節車廂似乎還是裝有煤的貨廂。
車上還有些老農和老婦拉著家常,每個人前面又都有一個或空或滿的背簍或籃子,老農們用自己的大草帽扇著風。我自己單獨守著一個窗子,只覺著自己到來得突兀。座位上的膠皮已經泛黃,有的還偶爾翹起個一些邊角來宣告自己的悠長歷史。座位還有些熱度,我小心翼翼地拉過有些破舊的藍色窗簾,半遮半掩住陽光,偷聽著不屬于我的家常。
“欸你們家的豬咋樣了嘛?我那屋里頭那只這幾天就是不咋個能吃,我還急得很。”“莫得事!幾天的事情,過幾天就好了!”“你的包包菜賣得好多錢啊?”“5角一斤!我這一背簍才幾十塊錢!”“李老頭!你才去賣啊?場都要散嘍!你搞快些喔!”
一句一句說的是簡簡單單的農家瑣事,承載的卻是農民一整個年頭里的盼望與滿足。蔬菜賣幾角錢一斤啦、誰家的豬怎么又不吃東西了、哪家的雞又被不知道哪的人給偷了呀……這些都不曾屬于我,這些東西只屬于老家,屬于老家里的老人。我只能在旁邊默默觀望,看著老家這個老人與他朝夕相伴、一生未曾背離的土地絮絮交談。我們是后繼者,卻在遠方失掉家鄉,找不到和它交談的方向。我們就只能遠遠地看著它一步一步老去,無論春夏,還是秋冬。
火車在山間爬行,哉悠哉地顛簸,不疾不徐地穿過一個個山洞。不多時,火車就走到了那個小村子。我等著車上的老農老婦們互相說著分別的問候,在最后下車。車上的老農老婦有的把身體探出窗來,拉著喉嚨邀請著下車的誰誰誰明天去他家吃個飯。猛然一提醒,我才發覺已近飯點。
于是很有耐心地等著返程火車,再一顛一顛地顛回出發站。車上也是一些老農老婦們與他們的背簍和籃子,以及不絕斷的家常:“今兒個又收一筐,下午賣了就好回去吃飯嘍。”每一輛火車都走走停停,在每一站都帶上些許希望,又還回村莊些許滿足。涌動在火車上的,絕不只是家常。
到站,下車。我站在飛舞的塵土中,看著火車繼續吐著黑煙在陽光中顛簸著,它的影子被拉長,逐漸伸長,直到長過鐵軌,長過希望與遠方。
手中攥著車票的票根,一路上追著不知哪家的老貓東跳西跑,帶著回歸的滿足,沖回了家。
“回來了?搞快添飯,我們都上桌了,就等你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