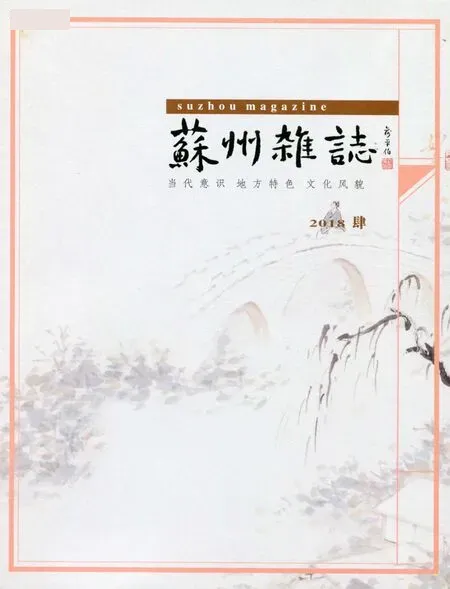消失的書場
潘益麟

鳳苑書場對面的醋庫巷
蘇州是評彈的發源地,從業者多,演出的書場也多。上世紀五十年代,蘇州城里城外的書場,可謂星羅棋布。自懂事后,我跟大人進書場去見識評彈;學評彈后,我進書場去表演評彈,雖然接觸的書場不多,卻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一、 濂溪坊“怡鴻館”
《紅樓夢》里賈寶玉住的地方是大觀園里的怡紅院,而這家書場的名字叫做怡鴻館,“紅”與“鴻”的讀音相同,最后一字雖然讀音不同,卻還是同一個韻,因為怡鴻館會使人聯想到怡紅院,因此這家書場的名字使人很容易就記住了。怡鴻館的真正位置其實是在街(上塘)與巷(下塘)之間,你可以在濂溪坊糕團店隔壁的大門里走進去,走過架在河上的木板廊橋,就到了所在下塘的書場了。住在附近甫橋西街或者鵝頸灣、司長巷、草橋頭一帶的老聽客都是從下塘進入書場的。
我的家在甫橋南堍,向西拐彎進桐橋浜,就到怡鴻館了。五十年代是我的童年時光,正是說書最興盛的黃金時期,我的爺爺奶奶、我的父母親、我的好幾個叔叔都喜歡聽書,我的舅舅更是自己買了一把琵琶,經常在家里自彈自唱、自娛自樂。
父親酷愛聽書,平時要做生意,走不開,沒時間去書場聽書,所以他特意買了一臺收音機放在店堂里,一邊做生意一邊聽上海電臺的大百萬金空中書場節目,節目主持人名叫萬仰祖。一面做生意,一面忙中偷閑店堂里聽書,真是一舉兩得,居然還吸引了一些喜歡聽書的過路人,帶動了店里的生意。店堂里賬桌上放有《大百萬金彈詞開篇集》和《原子藍布新開篇集》,父親經常一邊聽收音機里說書先生的彈唱,一邊看所唱開篇的唱詞。
在這樣的環境里,“被聽書”成了我童年生活的重要內容。也可以說,我對評彈的興趣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不知不覺地培養出來了。
但只聞其聲,不見其人,說書究竟是何種形式,琵琶三弦的形狀是怎樣的,怡鴻館成了我的啟蒙老師。
近在咫尺的怡鴻館,是一家陳舊的茶館書場,場內中間是一長條“狀元臺”,兩邊都是方桌,聽客坐的一律是長凳。進門處有一張賬桌,聽客在這里付錢買票、拿茶杯。北面沿河一排長窗,夏天時窗戶都被打開,不時有農民的賣西瓜船緩緩搖過。書臺后面的墻上,兩邊掛著兩塊黑色的水牌,上面寫著白色的字:某某某、某某某先生,彈唱什么書目,很是醒目。
有一個人,他不需要買票也能自由進入書場,他就是專門為聽客服務、賣小吃的老徐師傅。他就住在我家附近,他的女兒還是我小學的同班同學呢。雖然他姓徐,但大家都不這樣稱呼他,因為他燒的五香豆、焐酥豆非常好吃,口味很獨特,所以大家非常親熱地稱呼他為“小五香豆”。小落回了(上半場結束演員短暫休息一下),“小五香豆”將一個竹編的盤子頂在頭上,在狹窄的場子里穿來穿去,有人招呼要作成他生意時,他將竹盤放下來,五香豆、焐酥豆、脆梅、山楂、金花菜……花色品種很多。
我們這些小孩,不買票是不能進去的,一般都會選擇站在木板廊橋欄桿邊的位置,從沿河的長窗往里瞧。在我腦海里,至今還清晰地記得,有一次,竟然看到了說書還有“三個檔”。上手是一個男的中年人,下手是一個女青年,中間坐的卻是一個小姑娘,見她梳了兩條小辮子,瓜子臉,眉心中間還點了一點紅記,唱的聲音蠻好聽。聽大人說,小姑娘叫徐雪玉。想不到數年之后,我在評彈團與雪玉姐成了經常一起演出的同事。
在我童年的記憶中,還記得一年中有一個特別的日子,我會隨父親到怡鴻館去,那就是農歷初一早上喝橄欖茶。
年初一早上起床后,趕緊換了新衣服,吃好了母親燒好的年糕圓子湯,父親就帶了我出門。進入桐橋浜,一路上鄰居與父親都會相互致意問候:“恭喜恭喜!”沒幾步路怡鴻館就到了。這時怡鴻館內坐滿了茶客,人聲嘈雜,煙霧騰騰,都是喝早茶的男人,其中很多都是平時相識的街坊鄰居。父親在靠右墻邊的方桌旁坐下來。我看到我的爺爺——甫橋北堍濂溪坊牌樓邊豆腐店老板,還有惠生、岳生、菊生幾個叔叔也坐在那里磕著瓜子。我喝了一口小茶盅里的茶水,覺得有些苦澀,爺爺說,今天泡的是“元寶茶”。當時我搞不懂,后來知道,這“元寶”,其實就是產自福建的青橄欖。爺爺、父親都是開店的生意人,都希望生意興隆,元寶賺得越來越多。小小年紀的我,也懂得抓住這個寶貴的機會,趕緊給爺爺叔叔們拜年拿壓歲紅包。我看到堂倌不停地四面來回招呼、沏茶、傳毛巾,有茶客起身要走,他們還不忘拉生意,要他們下午早些過來聽日場,是某某某大響檔,來晚了擠不下的。父親坐了一會就起身告辭了,帶著我還得去趕“場子”!大年初一的,要到哪里去呢?究竟是個什么差事呢?原來,這是要到甫橋西街往南、鳳凰街鳳苑書場斜對面財神弄內的水仙廟去燒香!
文革開始,這家書場關門歇業了,場地派了別的用場,變成了一個街道的手工生產作坊。
九十年代初舊城改造,拓寬改建干將路,從此,古老的濂溪坊、臨河的怡鴻館在人們的視線中永遠地消失了。
二、南倉橋鳳凰街“鳳苑”
評彈藝術在蘇州民間的流傳根深蒂固,當你行走在一些小街小巷里,不時會傳來愛好者叮叮咚咚的弦歌之聲。當然,一些評彈從業者的居所更是星羅棋布一般點綴在蘇城內外。從我家附近濂溪坊周圍,再一直往南幾百米的距離中,就居住著俞筱云、徐麗仙、尤惠秋、曹漢昌、龐學卿、龐學庭、邢瑞庭等許多評彈名家。
這里要說的是,就在甫橋西街往南大概一站多汽車的路程,南倉橋鳳凰街口,邢瑞庭先生寓所斜對面,有一家名為“鳳苑”的書場。這家門面朝西的書場,設施條件要比怡鴻館好多了,一排排的靠背椅子,扶手上有一圓洞,可放茶杯。書臺上也有燈光布置。書場周邊環境相比觀前地區要僻靜一些,窗外南邊是一條幽靜的小河。附近有大學、中學、醫院的緣故,聽客中不乏較多的高級知識分子。在六十年代初的一段時間里,曾經有一個尊貴而神秘的聽客經常光顧鳳苑書場。
我第一次見識鳳苑是在一個冬日的晚上,做完功課后,我隨母親到鳳苑去聽夜場。當時我小學還沒畢業,但跟著收音機已經學會了《六十年代第一春》、《劉胡蘭就義》等開篇唱段。
那天鳳苑書場的夜場是兩檔書,頭檔是蘇州市評彈團羅介人、楊雪虹的現代長篇書目《紅色的種子》, 這回書的詳細內容已記不清楚,好像講一個賣木梳的人,冒充地下交通員,來與書中的主角華小鳳接關系什么的。當時60年代初,評彈界說新創新還剛開始,這部從同名錫劇移植改編不久的長篇書目,寫得比較簡單粗糙。小落回后的第二檔是傳統書目,由江蘇省曲藝團的名家徐琴芳與侯莉君彈唱長篇彈詞《落金扇》。侯莉君自成一格的侯調華麗、纏綿,風靡書壇,當時圈內藝人和圈外崇拜者對侯調極盡效仿和追捧。當晚鳳苑書場里的聽眾應該都是沖著她去的,盡管初冬的夜晚已經彌漫著襲人的寒氣。
徐琴芳、侯莉君的演出非常成功,上手說表灑脫大方,下手的彈唱娓娓動聽,而且侯莉君臺風好,在燈光的照耀下,眼神、表情分外動人。
散場了,饑腸轆轆的老聽客們不約而同地涌向街對面的“天湘園”面店吃夜宵,也有一些聽客在一個大家親熱地喚為“長子”的駱駝擔前停下腳步。
說新書后,盡管生意清淡,鳳苑還苦苦經營著。有一個夏天,每天午后看到蘇州評彈團的薛君亞,拿著三弦,走過我家門口,去鳳苑上場子,因為剛編的書,好像是《紅色娘子軍》,又是放單檔,一路沉著頭走路,一路嘴里還念念有詞呢。
哦,講到這里,讀者要問了,前面你所說的那位尊貴而神秘的聽客是誰呀?他就是后來成為我們評彈學校名譽校長的陳云同志!當時他住在蘇州南林飯店養病。蘇州評彈團的陳瑞麟老先生正在鳳苑演出日場,單檔彈唱他家祖傳的長篇彈詞《倭袍》,老首長就成了陳老先生的忠實聽眾,而且風雨無阻,每天都來。為了不擾民,他戴著帽子,戴了口罩,不帶隨從,再加上一身樸素的衣著,竟然沒有一人能看出他來。因為沒有聽到全部《倭袍》,后來他讓陳瑞麟把《倭袍》去蘇州電臺錄了音,寄到北京,讓他慢慢研究。
1966年,文革開始前,我們評校學生也曾經來到鳳苑書場實踐演出。我與小李同學的長篇彈詞《趙五嬸》、小尤同學的長篇評話《節振國》,兩檔合作,連續演了十多個夜場。
文革中,關門停業的鳳苑書場,成了所屬蘇州曲藝管理組的評彈藝人集中搞運動的場所,辦起了給偉人像章上漆的工場。
鳳苑書場在文革的狂風暴雨中壽終正寢了。
三、葑門橫街“椿沁園”
這是一家歷史悠久的書場,它坐落在蘇州葑門外歷史同樣悠久的橫街的中段。橫街的東南就是盛產茨菰水芹蓮藕的成片水田河塘和一個個農家村落,“椿沁園”自然就成了忙完農活或者賣完農產品的農民們聽書、喝茶、小憩的絕佳場所。照例,家在甫橋頭的我,不大會舍近就遠趕到橫街去的。但進入評校第二年(1963年)冬天的寒假里,那天晚上,我跟著我校擅唱《描金鳳》的景文梅老師一起來到橫街椿沁園書場,我們是來演出的。從以前的進書場聽書,到今天的進書場說書,我覺得自己真的是像在做夢一般!

葑門橫街
我們背著琵琶三弦,坐了三輪車,從學士街天官坊景老師家緩緩出發,經道前街、十梓街、鳳凰街、十全街,出葑門,在夜色闌珊中到了橫街。雖說是蘇州人,橫街我還是第一次來。窄窄的小街,店鋪林立。三輪車在書場門口停了下來,書場老板已在迎候。只見書場門口的海報上赫然寫著“春節會書”幾個字,每天晚上由不同的演員演出豐富多彩的傳統折子書目。幾年過去后才知道,這樣一貫以傳統書目展演的評彈界春節會書,這個1963年的春節會書注定成了文革前的最后絕唱,因為評彈界從1964年開始說新創新、說現代書了。
進了后臺休息室,聽到前面臺上頭檔大書(評話),已經開始在表演了。
那晚,景老師和我臨時拼檔,演出長篇彈詞《描金鳳》中的一折《金圖遠父子相逢》,他演父親金圖遠,我演兒子金繼春。這回書是學校排書課教材,就是由景文梅老師親自傳授的。這回書我平時是與我的同學排的,今天要與景老師拼檔,心中難免有些緊張。景老師看到后,就安慰我說:“倷定心好哉,勿要緊格,說得慢點……”“金繼春的官白‘啊,老長,小生要借問一信’,這一句盡量要說得慢一點,注意動作配合……”
景老師年輕時外表儒雅清脫,天然一條好嗓子,音色明亮清脆,定音高,《描金鳳》是他的拿手,藝術功底深厚,有人說他是活的徐惠蘭。1963年秋天,他還利用評校放暑假,在蘇州人民路怡園書場單檔連續演出了一個月《描金鳳》,天天滿座,有口皆碑。當時,我們評校學生每天去觀摩,他演的徐惠蘭、陳榮老將軍、俊巧丫頭、江北阿二、唱的“夏(荷生)調”等都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演出傳統書,都得穿長衫。我當晚穿的那件深藏青色的嗶嘰長衫,是這年秋天開學后,學校特地為我們幾個小男生專門量身定做的。說起這家專門做長衫、旗袍的裁縫店,應該是在觀前街宮巷口乾泰祥綢布店隔壁,門面朝西,老裁縫做工嫻熟考究,蘇州評彈界說書先生的長衫旗袍大多出自他的雙手。龐學庭老師與這位師傅很熟悉,因此我們幾個男同學的長衫都是由他自告奮勇帶去做的。
很快第一檔評話結束了,輪到景老師與我上臺了。這時,聽眾意想不到出場的老先生居然帶了一個小下手,且這個小說書還像模像樣地穿了件小長衫,場子里頓時情緒高漲起來。在聽眾的掌聲鼓勵下,我加唱了幾句蔣調《鶯鶯操琴》。有景老師掌舵,演出當然非常圓滿成功。
在文革的暴風驟雨中,椿沁園與蘇州其它許多書場一樣難逃厄運,只能凄然關門。
直至1979年,椿沁園終于重新恢復。與我同屆的評彈學校六十年代的畢業生、說評話出身的顧祖康同學成了新書場負責人。八十年代初,地處黃天蕩復校后的評校學生還時常會去椿沁園聽書觀摩。
令人遺憾的是,好景不長,沒有幾年,不知什么原因,椿沁園又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
四、太監弄“吳苑書場”
太監弄的吳苑書場與北局的蘇州書場一樣,地處繁華的觀前,都是得天獨厚的黃金地段。它的前門在太監弄,后門在珍珠弄,聽眾進出非常便捷。六十年代中期的““吳苑”書場,進行過一次翻新改建,設施條件比原來好多了,場子里都裝上了吊扇。
我們經常去那里聽報告、看演出。文革前,我們在那里觀摩過一臺蘇州評彈二團的現代書目演出,其中一回三個檔的農村題材短篇彈詞《小算盤與樣樣管》,人物形象生動,生活氣息濃,笑料多,給我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們評校學生學習生涯中一個重要而又不同凡響的環節是在吳苑書場完成的。那是1965年秋末冬初,評彈學校62級、63級彈詞和評話班同學在那里作考試公演,這是一次建校后評彈藝術教學成果的集中展示。
這次考試公演從11月14日開始,足足演了17天,連續客滿了17天,社會反響很大。
有一天夜場,演出中篇評彈《家庭問題》,一共三回書,我在第一回中演父親。離上場沒有多少時間了,我們演第一回的三人正在調音,等候上場。
這時,“篤篤篤……”化妝室門外有人在敲門,門開后,我回頭看到走進來的竟然是我父親!當時,他才四十歲出頭。原來,因為書場已經客滿,買不到票了,這“老書迷”進來是找學校領導商量幫他解難的。他對值臺的老師說,如果實在沒票的話,能否讓他坐在臺邊幕后聽?
我知道,他今天來聽書的真實目的,是要來看他兒子藝術上是否比原來有了進步,將來成名成家是他對我最大的企望!
這時,我看到學校總務處王謂川主任走過去,笑瞇瞇地從口袋里拿出一張書票給我父親。原來,這是每場演出預留給重要來賓客人的備用票,而且這幾張票位置好,不前不后,中間靠前。哈哈,想不到,沒有買到票的父親,那晚卻享受到了吳苑書場貴賓的待遇!
翻開我至今珍藏的考試公演節目單,已經泛黃的紙頁上是這樣寫的——
親愛的聽眾們:我校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入學的評話和彈詞兩班學員,曾于去年春季在蘇州書場舉行過考試演出,當時,蒙許多聽眾對這批革命評彈接班人懷著關切的心情,蒞臨觀摩指教,使我校的教學工作受到莫大的鼓舞和鞭策。茲為廣泛地吸取各方面的意見,不斷改進教學工作,以求適應文化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現訂于本月14—30號(每天夜場)在吳苑書場再次舉行考試公演,屆時歡迎光臨指教。此致,敬禮!
蘇州市評彈學校
1965年11月8日
吳苑書場的考試公演受到了社會各界和聽眾的廣泛關注和好評,大家為評彈事業后繼有人而感到由衷的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