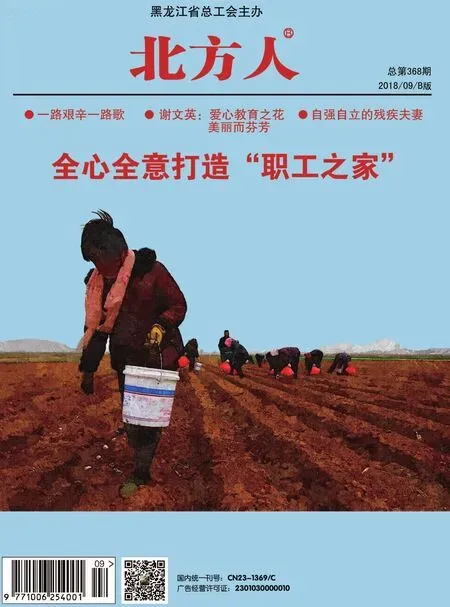世界很年輕
文/尹萌美

我認識朱一葉的時候,她已經不旅行了。但她還在寫著與旅行有關的小說,先是《死于象蹄》,接著是《綠洲》。這種時間和空間上的滯后性,讓故事情節既依托于真實事件又有恰到好處的疏離感,讓讀者對作者真實經歷的好奇和對閱讀故事的期待形成了非常有趣的化學反應。
同名小說《死于象蹄》是一個簡單的故事,一對情侶陸路過境肯尼亞,為了及時抵達馬賽馬拉大草原度過女朋友25歲的生日。像很多發生在路上的故事一樣,小說在爭吵、和好以及漫長旅程中的心態失衡等狀態中循環前進。打破這個環的,是作者在一開始埋下的一對藍色的寶石耳墜。這是一個非常有效的道具,因為男女主人公對生日和這對耳墜不同的期待,導致后面所有的情節都籠罩在它的淡藍色霧氣的陰影之下。而它再次出場簡直是整個故事最精彩和高潮的地方,男朋友在由游客們組成的臨時慶生會上通過煽動陌生人祝福的方式將女朋友的情緒推向最高點,接著,“我將握著耳墜的手伸在她的面前,我看到她的眼睛彎彎的,忽遠忽近,那表情又像笑又像哭,她的鼻翼抽動著,她用一個手背擋住了自己的嘴巴,我微笑著打開了自己的手掌,我和她一樣驚訝于手中竟然什么都沒有”。隨著一聲咒罵,喧鬧突然歸于寂靜。
讀者很容易沉浸在朱一葉營造的酷的語境中,她常用男性第一人稱敘事,偶見女性,這些主角有著相似的特征,敏感、脆弱、生機勃勃,追求一切意義又很容易陷入虛無,嗯,還愛好搖滾樂。于是,以身涉險或者危險的想法成為了書中常見的景象。《綠洲》中講述的美國游客和大象同時跋涉過河、河水慢慢漫過胸口的危險又迷人的場景;《尋找安妮》里背包客們普遍認為“恐怖分子的威脅只會令背包客更加興奮,簡直是不要錢的贈送項目,會為乏味的旅行增添談資”。
最令我著迷的始終是她的幽默。《綠洲》里有一段“我”和一個丹麥游客在滿是蚊蟲的情況下幾近交心,丹麥小伙兒進屋取了一趟煙,一陣尷尬后,他說,我根本不是丹麥人,我是加拿大人,那么你還是中國人嗎?“我當然還是中國人。”“我”有點生氣,這一幕卻因為極其尷尬產生了強烈的喜劇效果。
朱一葉的幽默,有的來自于焦慮。正如她在征文大賽頒獎禮上的發言,她說她之前設想了99種失敗的可能性,于是變得憂心忡忡。這種由于擔憂產生的幽默效果,在《兔子》這篇有了相對集中的體現,一個膽小如鼠的女孩,為了練膽,跑去斯里蘭卡獨自旅行。這個故事從開始就定下了荒誕不經的基調,于是她做出任何奇怪的事情——跳進沖浪區域游泳差點淹死、擔心被猛虎組織跟蹤卻誤傷同伴,等等,就不足為奇了。
比起那些對自己有明確期待的寫作者,朱一葉的混沌狀態會讓她保持快樂,卻恐怕還沒有讓她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已經在文學上留下了小小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