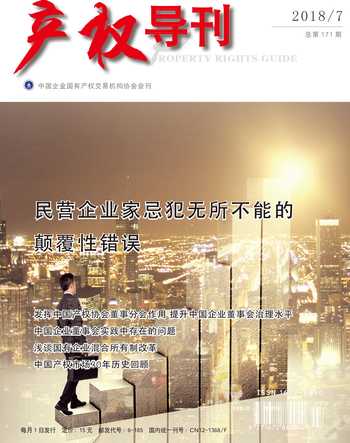超越式發展模式的中國尋路
禾刀
最近一段時間,中興事件就像是過山車,讓人膽顫心驚。據變化無常的川普自我披露,中興有望解禁,前提是滿足美方提出的條件。中興雖屬個案,但此次也曝出了中國“芯”痛的真正命門。一些專業人士不無憂慮地指出,中國芯片技術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之遠不是一點兩點的問題。
這并非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雖然近年華為發展勢頭迅猛,但中興的技術實力至少在國內同行中仍舊首屈一指。“2010年至2017年,中興通訊已連續8年位居國際專利申請量全球前三,是唯一連續8年獲此殊榮的中國企業”。即便如此,中興坦言,如果美國禁令不取消,中興完全有可能休克。更有甚者悲觀地指出,那樣的話中興將會“猝死”。
中興命運最終歸宿仍舊撲朔迷離,可以肯定的是,中興之痛不僅折射出中國芯片行業的普遍短板,這一事件同時也為本書觀點提供了有力的佐證,即一個國家要想實現跨越式發展,必須啃掉技術這塊骨頭,必須努力構建創新與市場完美結合的全新體系。換句話說,在同一行業里,后發優勢雖不無道理,但不能因此而無視領先者的諸多優勢。事實上,在講究持續投入,持續積累的尖端技術行業,踏踏實實地追趕或許才是真正的捷徑。
經濟學本來也是一門規律學科,未來發展趨勢往往蘊藏于過往的歷史之中。作者許濤梳理了英國、德國、美國、法國、蘇聯和日本等國發展歷程,通過分析這些國家發展特點,總結出一條超越式增長規律。因為超越式增長,所以英國和美國等才會成長為一個時期的全球經濟霸主。
所謂超越式增長,就是經濟增長模式和路徑越出原來的軌跡,提升至新的軌跡,并帶來經濟效率的顯著提升,以及經濟活動廣度和深度的明顯拓展。不難看出,許濤定義的超越式增長必須具備這么三大特點:一是經濟增長模式明顯區別于傳統模式,因為東施效顰永遠無法成為西施,更別談超越;二是經濟增速顯著,顯著的程度足以支撐國家持續高速發展,直至成為全球經濟的領導者;三是經濟活動變化不僅僅局限于少數幾個行業,而是對幾乎整個社會均會帶來深刻的影響。
許濤認為,實現超越式經濟增長至少要滿足兩個條件,“首要的決定因素,就是突破型技術的產生及應用”,正所謂“科學是第一生產力”。其次是巨大的“市場容量”,畢竟市場才是檢驗突破型技術效益的“試金石”。
有必要說明的是,許濤這里所說的突破性技術并非頭腦發熱的天馬行空,其源頭是熊彼特提出的“創造性破壞”概念。熊彼特所指的創造性破壞本是價格競爭的結果,落腳點是創新。許濤在這里將熊彼特的觀點進一步具化到技術層面,認為正是因為一些顛覆性技術的持續出現,才使得英國、美國等國經濟實現飛躍式發展。如“18世紀末19世紀初,以蒸汽機為標志的第一次技術革命浪潮,促使英國帶頭實現了產業革命”,使得英國國力突飛猛進,一躍成為世界頭號強國。還有,“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30年代,在美國,以愛迪生發明電燈為開端,以電力技術為代表,形成了突破型創新的連鎖反應,使1860年以前還處于落后狀態的美國,只用30年的時間便躍居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并超過德國成為新的世界科技與經濟中心”。從電氣時代到網絡時代,美國是全球當之無愧的技術領跑者,這也是中國擺脫“芯”病的有力鏡鑒。
相比之下,歷史上,“葡萄牙、西班牙、荷蘭都曾經是占有大量殖民地的‘大國,但由于缺乏科技創新的支撐,只能‘曇花一現”。而德國、前蘇聯和日本雖然在經濟發展上也曾迎來了“史上最好的增長時光”,但由于他們只是對國際既有尖端技術的模仿,即便做到極致,再往前是難以實現對傳統技術的顛覆,所以無法有效培育出足以影響全球的創新產業,自然無法真正超越前行者。
有趣的是,雖然第一次工業革命在本書中被大書特書,但荷蘭烏特列支大學經濟史教授揚·盧滕·范贊登曾經冷靜地指出,“工業革命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經濟增長和結構轉型過程的結果”。“自中世紀晚期以來,西歐在制度、人力資本形成以及經濟績效三個方面都具有(持續)突出的表現”,而“工業革命是內在激勵、經濟結構、知識積累和人力資本形成之間特別互動的產物”,因此,“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階段(才)是通向‘騰飛的工業革命的一條‘漫長的跑道”(《通往工業革命的漫長道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3月版)。
順著范贊登的邏輯思索我們不難得出,如果沒有各種社會機制形成的這條“漫長的跑道”,英國就不可能培育出那么多優秀的創新人才。如果沒有社會對創新人才的尊重乃至物質激勵,創新就很難形成良性循環。不知什么時候,“美國衰退論”此起彼伏,似乎美國垂垂老矣,奄奄一息——中興事件無異于醍醐灌頂。
許濤推崇技術,但又不迷信技術因素決定論。他清醒地認識到“歷史上很多在技術創新方面走在前沿的國家并未因此而實現大發展。如古代中國、16世紀的意大利、17世紀的荷蘭,它們都曾在某些技術創新方面走在世界的最前列,但由于這些技術關沒有太多改變人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僅僅被用于某些特殊的領域或特殊的群體,最終停止了發展的腳步”。
我們的歷史上并不缺乏這樣鮮活的案例。1793年,當英國使臣馬戛爾尼送給乾隆上千件象征工業革命成就的商品作為禮物時,乾隆以“奇技淫巧”之名將這些禮物深鎖庫房。七十多年后,當第一條鐵路出現在北京城外時,引得朝廷上下驚恐萬分,結果一拆了之。可以想見,在極度畏懼新生事物的環境中,死守落后顯然更有利于生存。
許濤指出,“技術創新尤其是突破型的技術創新,是經濟增長的主觀原動力,而市場容量則是經濟增長的客觀原動力。二者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缺一不可”。擴大市場容量的路徑有兩個,即城市化和全球化。
許濤寫本書,本意是為中國發展尋路。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40年來,中國經濟持續保持高速發展,而隨著各種“紅利”逐漸見頂,轉變發展動能自然成為新的著力點。大力推進突破型技術創新是首先必須直面的課題。從英美等國家發展規律來看,實現這一突破需要持續改善社會環境,逐漸形成最有利于激勵創新的氛圍。
相比之下,擴大市場容量方面我們仍有巨大潛力可挖。截至2017年底,我國城鎮化率61.55%。而發達國家城鎮化率普遍在80%以上。當然城鎮化率不是簡單的洗腳上樓,還涉及城鄉差距等多方面的復雜問題。突破這些問題,意味著身份差別減少,意味著生活環境的公平,本質上就是市場擴容。而“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既是對中國西部欠發達地區的激活,同時也是借此為“絲路”沿線欠發達國家的一次“賦能”。
有一點也許可以肯定,超越式發展并非一條觸手可及的坦途,相反,需要數十年的持續改進,這就像范贊登所描述的英國工業革命后經濟騰飛一樣。真正的困難或是,那些好不容易駛入超越式發展軌道的國家,很難再像以前那樣勇于不斷地進行自我革命,而是偏向于借助自身實力優勢,對后來者要么使絆子,要么赤裸裸地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