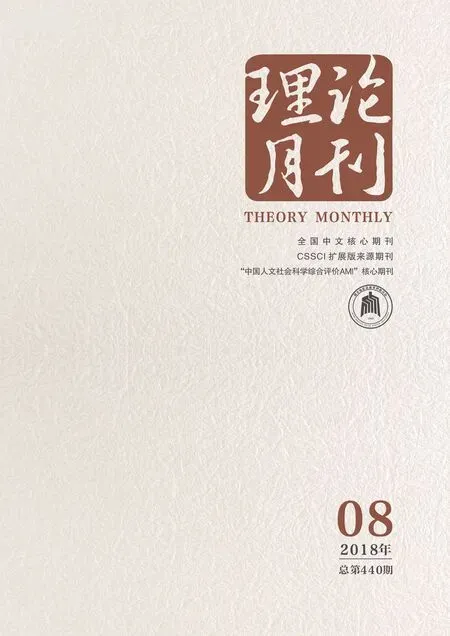唯物史觀下的“法律移植主義”
——從中國(guó)近代法學(xué)領(lǐng)域的兩大問(wèn)題說(shuō)起
□白雪峰
(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歷史唯物主義認(rèn)為,法和法律是人類歷史進(jìn)程中物質(zhì)生產(chǎn)實(shí)踐的產(chǎn)物。特定歷史時(shí)期的法及法律現(xiàn)象的科學(xué)化研究,建立在相應(yīng)歷史時(shí)期人類物質(zhì)生產(chǎn)實(shí)踐的研究基礎(chǔ)之上①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shí)形態(tài)》中指出,“如果像霍布斯等人那樣,承認(rèn)權(quán)力是法的基礎(chǔ),那么法、法律等等只不過(guò)是其他關(guān)系的(它們是國(guó)家權(quán)力的基礎(chǔ))的一種征兆,一種表現(xiàn)。那些決不依個(gè)人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個(gè)人的物質(zhì)生活,而且在一切還必需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階段上,都是完全不依個(gè)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這些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系絕不是國(guó)家政權(quán)創(chuàng)造出來(lái)的,相反地,它們本身就是創(chuàng)造國(guó)家政權(quán)的力量。在這種關(guān)系中占統(tǒng)治地位的個(gè)人除了必須以國(guó)家的形式組織自己的力量外,他們還必須給予他們自己的由這些特定關(guān)系所決定的意志以國(guó)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現(xiàn)形式。”參見(jiàn)《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77-378頁(yè)。。20世紀(jì)以來(lái)的中國(guó)試圖通過(guò)法律移植來(lái)實(shí)現(xiàn)從傳統(tǒng)法到現(xiàn)代法的轉(zhuǎn)型。之后的一段時(shí)期內(nèi),中國(guó)法治實(shí)踐和理論中所凸顯出來(lái)的“法的規(guī)范和現(xiàn)實(shí)生活不調(diào)和”“法理學(xué)與解釋學(xué)之不統(tǒng)一”以及“法的理想與法的實(shí)踐之間的分離”等問(wèn)題所引起的探討一直持續(xù)到當(dāng)下②清末法制變革之初,國(guó)內(nèi)對(duì)于法律移植所可能引起的問(wèn)題已經(jīng)展開(kāi)了比較廣泛的討論。例如,對(duì)于引進(jìn)西歐的罪刑法定原則,進(jìn)而廢棄中國(guó)傳統(tǒng)的“比附援引”制度而言,贊成引進(jìn)“罪刑法定原則”的理由是,“立憲國(guó)非據(jù)定律不處罰其臣民,此為近世東西各國(guó)之通例”;反對(duì)的一方則認(rèn)為,中外風(fēng)俗不同,“人民程度亦多差等,……如刪除比附以杜意為輕重,……恐程度不及,亦不免援引失當(dāng),出入人罪。”詳細(xì)內(nèi)容可參見(jiàn)高漢成主編:《〈大清新刑律〉立法資料匯編》,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3年版,第480頁(yè),第202頁(yè)。。但是,這些探討不能掩蓋的一個(gè)基本的歷史和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是,“中國(guó)法的‘近現(xiàn)代化’與引進(jìn)外國(guó)法密不可分。”[1](p97)中國(guó)法的“現(xiàn)代化”并不能等同于中國(guó)法的“西方化”。法律制度層面的移植能否單獨(dú)推動(dòng)中國(guó)法的“現(xiàn)代化”值得探討,這涉及法律制度和法學(xué)理論是否能夠僅僅從理論層面去探究的問(wèn)題,或者說(shuō),對(duì)于人類的法律發(fā)展史的認(rèn)識(shí)是否能夠從其本身入手。如果認(rèn)為,人類在生產(chǎn)實(shí)踐過(guò)程中創(chuàng)造了有利于自身生存的相關(guān)制度、文化等范疇,那么,單純從歷史文化視角、政治主權(quán)視角、社會(huì)學(xué)視角等來(lái)分析“法律移植”現(xiàn)象則明顯存在著“斷線風(fēng)箏”似的“飄忽不定”的局限。
國(guó)內(nèi)關(guān)于近代以來(lái)“法律移植現(xiàn)象”的探究大體上采取了以下幾種視角,即歷史文化視角①具有代表性的著述如葉秋華、王云霞、夏新華主編:《借鑒與移植:外國(guó)法律文化對(duì)中國(guó)的影響》,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綜合哲學(xué)、社會(huì)學(xué)、歷史文化學(xué)、經(jīng)濟(jì)學(xué)、政治主權(quán)等多重視角②現(xiàn)有的相關(guān)研究大多基于多重視角來(lái)審視法律移植現(xiàn)象,即綜合哲學(xué)、社會(huì)學(xué)、歷史文化學(xué)、經(jīng)濟(jì)學(xué)、政治主權(quán)等視角來(lái)認(rèn)識(shí)法律移植。關(guān)于這方面的研究可以參見(jiàn)何勤華:《法的移植與法的本土化》,載何勤華、屈文生、崔吉子主編:《法律翻譯與法律移植》,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93—108頁(yè);高鴻鈞:《法律移植——隱喻、范式與全球化時(shí)代的新趨向》,載何勤華、屈文生、崔吉子主編:《法律翻譯與法律移植》,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頁(yè);張仁善:《近代中國(guó)法律移植效用的三重阻力》,載何勤華、屈文生、崔吉子主編:《法律翻譯與法律移植》,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28—144頁(yè);朱蘇力:《這里沒(méi)有不動(dòng)產(chǎn)——法律移植問(wèn)題的理論梳理》,載何勤華、屈文生、崔吉子主編:《法律翻譯與法律移植》,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155頁(yè);張德美著:《探索與抉擇——晚清法律移植研究》,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版;何勤華等著:《法律移植論》,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版;何勤華主編:《法的移植與法的本土化》,商務(wù)印書(shū)館2014年版,第91—105頁(yè)。,社會(huì)學(xué)視角③從這種社會(huì)學(xué)的理論視角來(lái)看,“在任何社會(huì),法律從來(lái)都不是一個(gè)自治的獨(dú)立王國(guó),雖然古羅馬法和中世紀(jì)的英國(guó)法表現(xiàn)出同其他社會(huì)要素相分離的傾向,但是并沒(méi)有達(dá)到脫離社會(huì)情境的自治程度。”參見(jiàn)高鴻鈞:《法律移植——隱喻、范式與全球化時(shí)代的新趨向》,載何勤華、屈文生、崔吉子主編:《法律翻譯與法律移植》,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頁(yè)。。此外,還有研究通過(guò)生物學(xué)和醫(yī)學(xué)上器官移植的隱喻來(lái)分析法律移植的概念和可行性④參見(jiàn)高鴻鈞:《法律移植——隱喻、范式與全球化時(shí)代的新趨向》,載何勤華、屈文生、崔吉子主編:《法律翻譯與法律移植》,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09—111頁(yè);亦參見(jiàn)陳傳法:《法律移植簡(jiǎn)論——從發(fā)展的觀點(diǎn)看》,載何勤華主編:《法的移植與法的本土化》,商務(wù)印書(shū)館2014年版,第3—5頁(yè)。。具體而言,從內(nèi)容上看,現(xiàn)有的研究可以歸納為以下四類。第一,從歷史文化視角來(lái)看,有學(xué)者得出結(jié)論并認(rèn)為,中華法系的解體緣于外國(guó)法律文化在中國(guó)的廣泛傳播⑤參見(jiàn)葉秋華、王云霞、夏新華主編:《借鑒與移植:外國(guó)法律文化對(duì)中國(guó)的影響》,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第99—163頁(yè)。。宏觀方面來(lái)講,一些學(xué)者以歷史文化的發(fā)展脈絡(luò)為主線,分析了外國(guó)法律文化的形成背景和基本特性,總體考察了不同階段外國(guó)法律文化對(duì)于中國(guó)的影響,同時(shí),對(duì)于近代中國(guó)移植他國(guó)歷史上法律的精華展開(kāi)了論述和分析⑥參見(jiàn)高尚:《清末修律變法與法律移植——移植與變法的具體分析》,載何勤華主編:《法的移植與法的本土化》,商務(wù)印書(shū)館2014年版,91—105頁(yè);張仁善:《近代中國(guó)法律移植效用的三重阻力》,載何勤華、屈文生、崔吉子主編:《法律翻譯與法律移植》,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28—144頁(yè);葉秋華、王云霞、夏新華主編:《借鑒與移植:外國(guó)法律文化對(duì)中國(guó)的影響》,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何勤華、屈文生、崔吉子主編:《法律翻譯與法律移植》,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95—96頁(yè)。。在微觀方面,以法的觀念、法的原則、法律制度以及立法技術(shù)等方面為切入點(diǎn),從具體內(nèi)容、表現(xiàn)形式以及表現(xiàn)特征等方面闡述并考察了外國(guó)法律文化對(duì)于中國(guó)法的影響。這些研究本質(zhì)上可以認(rèn)為是一種“文化決定實(shí)踐”的論調(diào)①例如,有學(xué)者認(rèn)為,“在西方強(qiáng)勢(shì)文化改造中國(guó)的過(guò)程中,西方法學(xué)伴隨著基督教的傳播而傳播,為中國(guó)近代法學(xué)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礎(chǔ)。”參見(jiàn)葉秋華、王云霞、夏新華主編:《借鑒與移植:外國(guó)法律文化對(duì)中國(guó)的影響》,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頁(yè);“中國(guó)近代對(duì)西方法的移植,始于對(duì)傳統(tǒng)觀念的突破與轉(zhuǎn)變,使中國(guó)法律的發(fā)展走上了不斷移植外來(lái)法的道路。”參見(jiàn)馬建紅:《法律移植中的觀念因素——以中國(guó)近代以來(lái)的法制變革為例》,載何勤華主編:《法的移植與法的本土化》,商務(wù)印書(shū)館2014年版,第187—195頁(yè)。。第二,從政治意志的考量層面來(lái)看②例如,相關(guān)學(xué)者認(rèn)為,在清末,“出國(guó)考察政治的大臣對(duì)于大陸法極度推崇”“德國(guó)的迅速崛起使晚清政府深信移植德國(guó)法能使國(guó)家強(qiáng)大”“日本等國(guó)移植德國(guó)法的成功范例”等因素的考量是晚清政府選擇移植大陸法的部分原因。參見(jiàn)何勤華等著:《法律移植論》,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120頁(yè);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問(wèn)題與中國(guó)國(guó)家獨(dú)立主權(quán)的爭(zhēng)取是晚清法律移植的部分動(dòng)機(jī)。參見(jiàn)張德美著:《探索與抉擇——晚清法律移植研究》,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162頁(yè)。,一些學(xué)者認(rèn)為,總體上來(lái)說(shuō),一種政治力量推動(dòng)了中國(guó)近代以來(lái)的法律移植。即統(tǒng)治階級(jí)把法律移植作為促進(jìn)社會(huì)發(fā)展的手段之一,同時(shí),他們期望通過(guò)法律移植維持中國(guó)社會(huì)穩(wěn)定的秩序。此外,伴隨著中國(guó)工業(yè)化實(shí)踐的開(kāi)展和中外貿(mào)易量的增加,中國(guó)社會(huì)自上而下逐漸容納并接受了西方的政治法律思想③“西方列強(qiáng)的威逼利誘”和“鞏固皇位的需要”被認(rèn)為是法律移植的部分動(dòng)因。參見(jiàn)葉秋華、王云霞、夏新華主編:《借鑒與移植:外國(guó)法律文化對(duì)中國(guó)的影響》,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113頁(yè),第125—126頁(yè);亦參見(jiàn)張德美:《探索與抉擇——晚清法律移植研究》,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1頁(yè)。。第三,從社會(huì)學(xué)視角來(lái)看,“在任何社會(huì)中,法律都不可能同社會(huì)中的其他要素相分離,進(jìn)而達(dá)到脫離社會(huì)情境的自治程度。”[2](p35)當(dāng)今的全球化時(shí)代,法律的發(fā)展已經(jīng)具有一種超越特定民族傳統(tǒng)和民族精神的趨勢(shì),“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社會(huì)環(huán)境、地理、氣候等環(huán)境差異不足以構(gòu)成法律移植所不可逾越的障礙。”[2](p35)第四,從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理論視角來(lái)看。有學(xué)者通過(guò)這種視角分析認(rèn)為,法律移植是法律普遍性的必然表現(xiàn)[1](p98-p99)。近現(xiàn)代全球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與全球化擴(kuò)張趨勢(shì),中國(guó)傳統(tǒng)法律無(wú)法適應(yīng)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需求是法律移植的原因之一[1](p98)。“半殖民地經(jīng)濟(jì)形態(tài)下的法律移植符合中國(guó)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趨勢(shì)。”[1](p98)經(jīng)濟(jì)全球化的背景下,今日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國(guó)家所確立起來(lái)的經(jīng)濟(jì)、政治制度是我國(guó)將來(lái)需要確立的經(jīng)濟(jì)、政治制度④詳細(xì)論述參見(jiàn)何勤華、屈文生、崔吉子主編:《法律翻譯與法律移植》,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98頁(yè);亦參見(jiàn)何勤華等著:《法律移植論》,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版,第221—226頁(yè),第267—271頁(yè)。。
從以上相關(guān)的研究綜述來(lái)看,目前對(duì)于從社會(huì)生產(chǎn)實(shí)踐或經(jīng)濟(jì)現(xiàn)實(shí)視角總體來(lái)審視中國(guó)近代以來(lái)的法律移植現(xiàn)象仍然不夠充分。上文綜述的前三種視角是單純的“從意識(shí)中分析意識(shí)”的認(rèn)知邏輯。第四種視角雖然對(duì)于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現(xiàn)實(shí)的重要性予以一定的重視,但是,這種理論分析過(guò)分重視“法律的普遍性特征”,從而認(rèn)為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法律制度將伴隨著全球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落地生根于“第三世界國(guó)家”或發(fā)展中國(guó)家,其并沒(méi)有從中國(guó)經(jīng)濟(jì)現(xiàn)實(shí)的角度系統(tǒng)地分析并解決法律移植后中國(guó)社會(huì)中所產(chǎn)生的“法制變革與法律傳統(tǒng)之間的糾葛”以及“新法治和舊禮俗之間的緊張”的問(wèn)題,例如,這種理論視角并不能解釋為何在南京國(guó)民政府時(shí)期,新的民法典頒布施行后,在一些地方的司法實(shí)踐中常常是遵守著舊的處理糾紛的方式[3](p187)。可以說(shuō),這種理論視角漠視了“法律的特殊性”,而對(duì)于這種“特殊性”的把握,則需要從特定的生產(chǎn)實(shí)踐——中國(guó)近代以來(lái)的經(jīng)濟(jì)現(xiàn)實(shí)來(lái)入手。
本文的研究嘗試以唯物史觀為視角,從中國(guó)近代以來(lái)的法律移植所引起的法學(xué)領(lǐng)域的兩大問(wèn)題——“法制變革與法律傳統(tǒng)之間的糾葛”以及“新法治和舊禮俗之間的緊張”入手,從唯物史觀的視角對(duì)產(chǎn)生以上兩大問(wèn)題的原因作出解釋。同時(shí),基于同一研究視角,文章對(duì)于新時(shí)期,即新中國(guó)成立以來(lái)的法律移植與中國(guó)法學(xué)理論的本土化建構(gòu)指出了具體的方向,并特別指出了這一時(shí)期中的中國(guó)法律傳統(tǒng)在中國(guó)法學(xué)理論建構(gòu)中的作用和地位。
一、中國(guó)近代以來(lái)的法律移植所引起的兩大問(wèn)題
一般認(rèn)為,接受外國(guó)法被認(rèn)為是法律體系現(xiàn)代化的一個(gè)過(guò)程[4](p57)。然而,從中國(guó)清末以來(lái)在引進(jìn)外國(guó)法律制度的過(guò)程來(lái)看,更多地表現(xiàn)出一種“驚慌”“無(wú)奈”甚至是“惆悵”的情緒。這種情緒既言表于理論層面,也生發(fā)在社會(huì)生活層面。如果說(shuō),清末法制變革之初的糾葛主要存在于引進(jìn)新法與保留中國(guó)法律傳統(tǒng)之間,那么在新法施行以后,司法實(shí)踐中凸顯出來(lái)的是新法治和舊禮俗之間的緊張關(guān)系。
(一)清末法律移植——法制變革與法律傳統(tǒng)之間的糾葛
清朝末期,法制變革成為當(dāng)時(shí)統(tǒng)治者的必然選擇,中國(guó)法律傳統(tǒng)的存舍是法制變革過(guò)程中的糾結(jié)點(diǎn)。清末法制變革之初,倉(cāng)促激進(jìn)的法律移植伴隨著清朝政權(quán)的傾覆難見(jiàn)新法規(guī)范社會(huì)生活之實(shí)效。從留予后世的資料來(lái)看,只是一些關(guān)于立法原則的理論層面的爭(zhēng)論,這些爭(zhēng)論雖有涉及新法和中國(guó)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是否適合的問(wèn)題,但是,由于大部分新法未予施行,所以,主要爭(zhēng)執(zhí)的焦點(diǎn)落在了修訂新法的主要宗旨之上。如果認(rèn)為,傳統(tǒng)中國(guó)注重以禮俗教化民眾,沈派憑借移植西法來(lái)建設(shè)新法治的過(guò)程中遇到了傳統(tǒng)的阻力,那么可以認(rèn)為,新法治與舊禮俗之間的巨大反差反映到理論層面便是法制變革與法律傳統(tǒng)之間糾葛的問(wèn)題。但是,按照史料的記載,如果從這種糾葛中嚴(yán)格劃分出“沈派”和“反沈派”,進(jìn)而從兩者絕對(duì)對(duì)立的視角來(lái)分析問(wèn)題,例如,從蔡樞衡的著述中可以看到這種研究路徑①按照蔡樞衡的觀點(diǎn),近代以來(lái),接受外國(guó)法律制度的全部“功績(jī)”應(yīng)該歸于以沈家本為代表的沈派,相應(yīng)地,反沈派只是留下了“失敗”的歷史記錄。參見(jiàn)蔡樞衡著:《中國(guó)法理自覺(jué)的發(fā)展》,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頁(yè)。,那么不可避免存在著以偏概全的弊病。原因在于,從歷史視角來(lái)看,“沈派”的觀點(diǎn)中并非剔除掉了全部的中國(guó)傳統(tǒng)禮教風(fēng)俗,“反沈派”也不是絕對(duì)的“原狀復(fù)古”論者,兩者的觀點(diǎn)有重合的部分②例如,當(dāng)時(shí)維護(hù)禮教傳統(tǒng)的清政府認(rèn)識(shí)到了變法的必要性,他們認(rèn)為,“今寰海大通,國(guó)際每多交涉,故不宜墨守故常,致失通變宜民之意,但只可采彼所長(zhǎng),益我所短。凡我舊律義關(guān)倫常諸條,不可率行變革,庶以維天理民彝于不敝。”參見(jiàn)高漢成主編:《〈大清新刑律〉立法資料匯編》,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3年版,第469頁(yè);對(duì)于沈派而言,新刑律的修訂也考慮到了中國(guó)本土的風(fēng)俗。例如《大清新刑律》所附《暫行章程》5條,一方面,迫于反沈派的壓力,另一方面,也有沈派自己對(duì)于本土禮俗的關(guān)照。參見(jiàn)高漢成主編:《〈大清新刑律〉立法資料匯編》,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3年版,第597—600頁(yè)。。當(dāng)然,蔡樞衡對(duì)于“沈派”和“反沈派”的分類具有理論觀點(diǎn)的相對(duì)指稱意義,但是,這種稱謂上的區(qū)分并不能代表兩者理論觀點(diǎn)上的絕對(duì)分野。修訂新法的原則或立法精神方面的分歧并不能掩飾兩者對(duì)于通過(guò)法律移植來(lái)實(shí)現(xiàn)國(guó)家“求富”“求治”“求強(qiáng)”的出發(fā)點(diǎn),甚至沈派自身對(duì)于法制變革的主導(dǎo)精神也存有疑問(wèn)③1902年,沈家本在《刪除律例內(nèi)重法折》中提到:“現(xiàn)在各國(guó)法律既已得其大凡,即應(yīng)分類編纂,以期克日成書(shū),而該館員等僉謂宗旨不定,則編纂無(wú)從措手。”最后,就刑律的修訂而言,沈氏認(rèn)為“仁”可以成為修訂宗旨。參見(jiàn)沈家本著:《寄簃文存》,商務(wù)印書(shū)館2015年版,第2頁(yè);民國(guó)時(shí)期的楊幼炯也認(rèn)為,國(guó)民政府成立以前,“我國(guó)立法事業(yè)多缺乏一貫的獨(dú)立立法政策作基礎(chǔ),大都重模仿而少創(chuàng)造,無(wú)一定立法原則可循,因此,對(duì)于我國(guó)立法前途沒(méi)有多大貢獻(xiàn)。”參見(jiàn)楊幼炯著:《近代中國(guó)立法史》,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第247頁(yè)。。在沈派看來(lái),中國(guó)應(yīng)該通過(guò)法律移植來(lái)修訂新法,革除部分舊禮俗,吸收西方的法學(xué)理論和法律制度,廢除和西方各國(guó)簽訂的不平等“商約”以圖自強(qiáng);反沈派也認(rèn)為,“國(guó)內(nèi)民怨,對(duì)外列強(qiáng)瓜分”的時(shí)局之下,“為治之道,因時(shí)制宜”,法律移植成為必要的抉擇,但是,新法的修訂應(yīng)該符合中國(guó)傳統(tǒng)的禮教精神。
從沈家本的著述中可以了解到,變法修律的“政治工具”論傾向使得沈派在認(rèn)可西方法治文明的同時(shí),對(duì)于傳統(tǒng)舊律及其精神也表現(xiàn)出些許“不舍”。首先,清末的變法修律有一種明顯的“政治工具”論傾向,即通過(guò)變法來(lái)維護(hù)中國(guó)的司法主權(quán),進(jìn)而“求富”“求治”“求強(qiáng)”[5](p36-p38)。沈家本認(rèn)為:“西人訾中國(guó)的重法為不仁,借口于此不受中國(guó)法的約束”,來(lái)華的東西洋各國(guó)與中國(guó)相繼簽訂了不平等的商約,雙方在商約中約定,俟中國(guó)修訂了法律以后方能撤回其本國(guó)的治外法權(quán),這在當(dāng)時(shí)的中國(guó)看來(lái),是一個(gè)通過(guò)變法來(lái)實(shí)現(xiàn)自強(qiáng)的機(jī)會(huì)[6](p2)。楊度也認(rèn)為,撤銷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是改訂刑律的理由之一①參見(jiàn)高漢成主編:《〈大清新刑律〉立法資料匯編》,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3年版,第592—593頁(yè)。。其次,在修訂新律的過(guò)程中,沈家本對(duì)于西方的法治理論和法律制度持有肯定的態(tài)度,刪除了一部分體現(xiàn)中國(guó)傳統(tǒng)禮俗的法律制度。例如,對(duì)于“無(wú)夫之?huà)D女犯奸”的行為,他認(rèn)為這種行為有關(guān)風(fēng)化,“當(dāng)于教育上別籌辦法”,不宜用刑罰科制②“無(wú)夫之?huà)D女犯奸,歐洲法律并無(wú)治罪之文,……。此事有關(guān)風(fēng)化,當(dāng)于教育上別籌辦法,不必編入刑律之中。”參見(jiàn)高漢成主編:《〈大清新刑律〉立法資料匯編》,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3年版,第788頁(yè)。。在廢除奴婢身份和買(mǎi)賣(mài)人口方面,沈家本認(rèn)為:“現(xiàn)在歐美各國(guó)均無(wú)買(mǎi)賣(mài)人口之事,系用尊重人格之主義,其法實(shí)可采取”[6](p15-p24)。此外,在新律的修訂過(guò)程中,也可以看到沈家本立足中國(guó)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和重視中國(guó)法律傳統(tǒng)的一面③沈氏在《法學(xué)名著序》中提到,“夫吾國(guó)舊學(xué),自成法系,精微之處,仁至義盡,新學(xué)要旨,已在包含之內(nèi),烏可弁髦等視,不復(fù)研求……無(wú)論舊學(xué)、新學(xué),不能舍情理而別為法也,所貴融會(huì)而貫通之。”參見(jiàn)沈家本著:《寄簃文存》,商務(wù)印書(shū)館2015年版,第210頁(yè)。。例如,從《禁革買(mǎi)賣(mài)人口變通舊例議》一文中可以看到,沈家本基于中國(guó)的法律傳統(tǒng)和法理考量并認(rèn)為,買(mǎi)賣(mài)人口的舊習(xí)俗應(yīng)該革除掉。他說(shuō):“中國(guó)三代盛時(shí)無(wú)買(mǎi)賣(mài)人口之事,……。我朝定例,逐漸從寬”[6](p15)。以上分析可以印證相關(guān)學(xué)者的一些說(shuō)法,即“對(duì)于出身正統(tǒng)之學(xué)的沈家本而言,清末修律過(guò)程中所體現(xiàn)出的與中國(guó)法律傳統(tǒng)的割裂現(xiàn)象或許并非其本意。”[7](p129)
從正史史料的記載來(lái)看,在清末修訂新律的過(guò)程中,法律的激進(jìn)變革遭遇到了傳統(tǒng)的阻力,但是這種阻力本身并非絕對(duì)反對(duì)法律變革,其將更多的關(guān)注點(diǎn)放在了中國(guó)法律傳統(tǒng)之上。在清末的統(tǒng)治者看來(lái),在當(dāng)時(shí)“寰海大通”的時(shí)局之下,東西各國(guó)之間的來(lái)往密切,在法律制度的層面應(yīng)該有所改革。就中國(guó)傳統(tǒng)的刑罰制度而言,其本身存在的社會(huì)基礎(chǔ)之一便是維護(hù)中國(guó)傳統(tǒng)的禮教民情。因此,清政府認(rèn)為,法律制度變革的過(guò)程中,中國(guó)傳統(tǒng)的禮教精神仍然應(yīng)該是修訂新律的主要原則④當(dāng)時(shí)的清政府認(rèn)為:“今寰海大通,國(guó)際每多交涉,固不宜墨守故常,致失通變宜民之意”。“刑法之源,本乎禮教,……。凡我舊律義關(guān)倫常諸條,不可率行變革,庶以維天理民彝于不敝。”參見(jiàn)高漢成主編:《〈大清新刑律〉立法資料匯編》,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3年版,第469頁(yè)。。另外,在包括清政府在內(nèi)的傳統(tǒng)勢(shì)力看來(lái),中國(guó)本來(lái)為“籌備立憲、統(tǒng)一法權(quán)”而修訂新律,對(duì)于修訂后的法律制度,其主要規(guī)范的對(duì)象是中國(guó)人自身。以《大清新刑律》為例,如果說(shuō),修訂新刑律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收回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進(jìn)而舍棄中國(guó)固有的傳統(tǒng)禮俗,另設(shè)《暫行章程》專門(mén)用以規(guī)范中國(guó)人的行為,那么,這樣看來(lái),如此修訂的新律是專門(mén)為外國(guó)而設(shè),即“專以模仿外國(guó)為事”,不得不承認(rèn),這是一種本末倒置的做法⑤《大清新刑律》(草案)附則第二條規(guī)定,“中國(guó)宗教尊孔,向以綱常禮教為重,……,況奉上諭再三告誡,自應(yīng)恪為遵守。如大清律中“十惡”、“……各條均有關(guān)于倫紀(jì)禮教,未便蔑棄。如中國(guó)人有犯以上各罪,應(yīng)依照舊律辦法,另輯單行法以昭懲創(chuàng)。”高漢成主編:《〈大清新刑律〉立法資料匯編》,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3年版,第583頁(yè)。勞乃宣針對(duì)大清新刑律的草案提出了反對(duì)之辭,他說(shuō):“修訂新律,本為籌備立憲,統(tǒng)一法權(quán)。……是此法律,本當(dāng)以治中國(guó)人為主。今乃依舊律別輯中國(guó)人單行法,是視此新刑律專為外國(guó)人設(shè)矣。本末倒置,莫此為甚。草案案語(yǔ)謂修訂刑律,所以收回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故所修刑律,專以摹仿外國(guó)為事。……。今中國(guó)修訂刑律,乃謂為收回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必盡舍固有之禮教風(fēng)俗,一一摹仿外國(guó)。則同乎此國(guó)者,彼國(guó)有違言,同乎彼國(guó)者,此國(guó)又相反,是必窮之道也。”參見(jiàn)(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四十二《刑法志一》,中華書(shū)局1977年版,第4190—4191頁(yè)。。可見(jiàn),在這種傳統(tǒng)的勢(shì)力看來(lái),中國(guó)的修律應(yīng)該“量體裁衣”,在引進(jìn)外國(guó)法律制度的同時(shí),應(yīng)該對(duì)于本土的傳統(tǒng)禮俗予以充分關(guān)照,或者說(shuō),一種歷史的理性足以為修訂新律提供一種理論支撐。
(二)民國(guó)司法實(shí)踐——舊禮俗與新法治之間的緊張關(guān)系
如果認(rèn)為,清末的法律移植所引起的爭(zhēng)論只是停留在了新法與中國(guó)法律傳統(tǒng)之間,那么,民國(guó)政府成立以后,從司法實(shí)踐中新法的運(yùn)行實(shí)效來(lái)看,這期間更多地突出了新法治和中國(guó)舊禮俗之間的緊張問(wèn)題。根據(jù)相關(guān)學(xué)者的研究,在民國(guó)時(shí)期,西安的司法實(shí)踐中凸顯出“立法與社會(huì)的脫節(jié)”的問(wèn)題,地方法院的推事則通過(guò)“變通訴求”、嚴(yán)厲懲治危害中國(guó)傳統(tǒng)倫理的犯罪行為、在民事審判中注重民間慣習(xí)的收集與認(rèn)可等方式來(lái)彌補(bǔ)“立法與社會(huì)”之間的沖突①具體內(nèi)容參見(jiàn)侯欣一:《創(chuàng)制、運(yùn)行及變異:民國(guó)時(shí)期西安地方法院研究》,商務(wù)印書(shū)館2017年版,第515—532頁(yè)。。這種“立法與社會(huì)”之間的脫節(jié)或沖突本質(zhì)上可以歸結(jié)為新法治與中國(guó)舊習(xí)俗之間的“緊張”關(guān)系。
這在婚姻家庭法律實(shí)踐中表現(xiàn)得更為明顯。清末以來(lái),雖然說(shuō),婚姻觀念和家庭結(jié)構(gòu)在中國(guó)的社會(huì)中已經(jīng)發(fā)生了較大的變化,但是,在這一時(shí)期內(nèi),舊的婚姻家庭結(jié)構(gòu)并未完全消解,同時(shí),中國(guó)社會(huì)內(nèi)部還沒(méi)有建立起新的婚姻家庭結(jié)構(gòu)。在中國(guó)的法律傳統(tǒng)中,婚姻被認(rèn)為是兩個(gè)家族的“結(jié)合”。根據(jù)瞿同祖先生的研究,中國(guó)傳統(tǒng)的婚姻并不以個(gè)人為中心,而是完全以家族為中心[8](p97)。這從《大清律例》中規(guī)范婚姻關(guān)系的律文規(guī)定中可以觀察到②“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有殘疾、老幼、庶出、過(guò)房、乞養(yǎng)者,務(wù)要兩家明白通知,各從所愿,寫(xiě)立婚書(shū),依禮聘嫁”。參見(jiàn)馬建石、楊育棠主編:《大清律例通考校注》,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1992年版,第442—443頁(yè)。。1931年民國(guó)民法典的《親屬編》和《繼承編》施行以前,一直保留著清代婚姻須經(jīng)父母許可的舊規(guī)定,結(jié)婚并不是僅僅通過(guò)男女雙方個(gè)體自由選擇的事情。此外,對(duì)于30歲以下要離婚的男女也必須征得其父母的同意。
與中國(guó)傳統(tǒng)法律的規(guī)定不同,南京國(guó)民政府1931年頒行了新民法典之《親屬編》和《繼承編》,法律從此承認(rèn)了男女在婚姻家庭關(guān)系中處于平等的地位。民國(guó)民法典第九百七十二條規(guī)定:婚約應(yīng)由男女當(dāng)事人自行訂定。“國(guó)民黨法典把婦女想象為獨(dú)立自由的自主體,她們像男人一樣繼承財(cái)產(chǎn),在結(jié)婚離婚上享有與男人同樣的權(quán)利。”[3](p58)民國(guó)民法典的總則規(guī)定了“男女平等之原則”,“成年女性具有完全的民事行為能力,對(duì)女性擁有個(gè)人的財(cái)產(chǎn)、處分個(gè)人財(cái)產(chǎn)予以法律上的承認(rèn)和保障。”[9](p756)此外,“法定財(cái)產(chǎn)制”和“約定財(cái)產(chǎn)制”成為新的民法典規(guī)定的兩種夫妻財(cái)產(chǎn)制,其中,法定財(cái)產(chǎn)制效仿了瑞士的做法,目的在于“便于維持共同生活,保護(hù)雙方之利權(quán)”[9](p784-p786)。
當(dāng)然,不可否認(rèn)的是,以上關(guān)于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上的修改很好地回應(yīng)了19世紀(jì)末期以來(lái)西方進(jìn)步的女性主義趨勢(shì)[10](p135)。但是就這種制度改革本身而言,從頒行后的一段時(shí)期來(lái)看,其實(shí)效甚微。套用相關(guān)學(xué)者的話來(lái)說(shuō),民國(guó)民法典中更多地體現(xiàn)了政府和法律精英的意志,“體現(xiàn)了法律家繼受外國(guó)法的強(qiáng)烈偏好,民眾現(xiàn)實(shí)生活的基本要求則被忽略了。”[5](p256)如果說(shuō),在民國(guó)以前的社會(huì)中,婚姻關(guān)系存續(xù)期間的女性的行為能力受到丈夫的節(jié)制。“社會(huì)習(xí)慣和法律對(duì)于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限制很?chē)?yán)格”,“妻子只能按時(shí)從丈夫處領(lǐng)得定額的家用,然后在一定范圍內(nèi)支配這些資財(cái)。”[8](p114)那么,從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生活現(xiàn)實(shí)來(lái)看,并沒(méi)有因?yàn)橄冗M(jìn)完備的民法典的頒行而得到多大的變革。民國(guó)民法典頒行后十多年間,新舊婚姻家庭觀念的沖突依然存在。例如,1946年北京地區(qū)發(fā)生的一個(gè)關(guān)于“重婚罪”的案例,原告人牛某是一名參伍軍人,留妻子胡某在北京家中,牛某每月寄回自己的部分薪資給北京家中的胡某補(bǔ)貼家用。抗日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以后,“戰(zhàn)況吃緊,陷區(qū)禁止匯兌,有錢(qián)但不能寄回家中”。胡氏生活困難,于是改嫁李某。后牛某訴胡某犯重婚罪。胡某辯稱:“我等了幾年,生活無(wú)著”,“那時(shí)候小孩病得要死,我無(wú)法,求李蘇氏(中間人)替我找主兒。”此外,胡氏還辯稱,自身的“私奔”是根據(jù)牛某本人的意思,有書(shū)信為證,信中提到,“因中日作戰(zhàn)郵政不能匯洋,……,這許多日期未給你寄錢(qián),……,每天想起你跟夫受的罪,實(shí)在可憐。……如妻在家竟餓著,無(wú)人管,可就自己隨意嫁人等等。”[11](p183-p185)在雙方當(dāng)事人的言辭之間,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婚姻家庭在他們的觀念中仍然停留于民國(guó)以前。在他們看來(lái),丈夫養(yǎng)家是一種“天然的責(zé)任”“妻子只能按時(shí)從丈夫處領(lǐng)得定額的家用”。夫妻之間的關(guān)系并非如新法規(guī)定的那樣,堅(jiān)持“男女平等”之原則,雙方“維持共同之生活”。
二、從經(jīng)濟(jì)現(xiàn)實(shí)看近代中國(guó)的法律移植
表面看來(lái),以上提到的法律傳統(tǒng)與法制變革之間的艱難抉擇、新法治與舊禮俗之間的緊張可以尋求一種“法律實(shí)證主義”或“歷史法學(xué)理論”當(dāng)作自己的理論辯解。但是,如果認(rèn)為,這種“法律實(shí)證主義”或“歷史法學(xué)理論”本身生發(fā)于特定的社會(huì)生產(chǎn)實(shí)踐,那么,以上兩大問(wèn)題的解決變得相對(duì)容易了。一般認(rèn)為,這種研究進(jìn)路在歷史唯物主義中表現(xiàn)得很充分。對(duì)于法或法律產(chǎn)生的過(guò)程,馬克思認(rèn)為,如果認(rèn)為權(quán)力是法的基礎(chǔ),那么法、法律只不過(guò)是那些“不依個(gè)人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個(gè)人物質(zhì)生活”的一種表現(xiàn),在物質(zhì)生活中產(chǎn)生的人們之間相互制約的生產(chǎn)方式和交往形式是國(guó)家的現(xiàn)實(shí)基礎(chǔ),這些現(xiàn)實(shí)的生產(chǎn)生活關(guān)系創(chuàng)造了國(guó)家權(quán)力①參見(jiàn)馬克思、恩格斯著:《德意志意識(shí)形態(tài)》,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2—33頁(yè),第367—368頁(yè)。。這種理論視角在龐德的《法律史解釋》中被稱為法律的經(jīng)濟(jì)學(xué)解釋,它預(yù)設(shè)了法律制度在歷史進(jìn)程的決定性因素——經(jīng)濟(jì)現(xiàn)實(shí)②相關(guān)內(nèi)容參見(jiàn)(美)龐德著:《法律史解釋》,鄧正來(lái)譯,商務(wù)印書(shū)館2013年版,第124—125頁(yè)。。
(一)從歐洲18、19世紀(jì)的經(jīng)濟(jì)看法律的“發(fā)達(dá)”現(xiàn)象
從這種理論視角來(lái)看,19世紀(jì)歐洲法律的發(fā)達(dá)現(xiàn)象決定于該特定時(shí)期的工商業(yè)經(jīng)濟(jì)現(xiàn)實(shí)。18世紀(jì)之前,歐洲的城市商業(yè)和制造業(yè)的發(fā)展、農(nóng)業(yè)耕作方式的變革以及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體制的變革等因素使農(nóng)業(yè)的專業(yè)化程度提高,相應(yīng)地,農(nóng)業(yè)的生產(chǎn)率也得到了提高③詳細(xì)內(nèi)容參見(jiàn)(英)布勞德伯利等編著:《劍橋現(xiàn)代歐洲經(jīng)濟(jì)史:1700—1870》(第一卷),何富彩等譯,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第125—134頁(yè);亦參見(jiàn)(英)約瑟夫·庫(kù)利舍爾著:《歐洲近代經(jīng)濟(jì)史》,石軍、周蓮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0年版,第35—98頁(yè)。。但是,從18世紀(jì)初期到19世紀(jì)中葉的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可以看到,農(nóng)業(yè)的相對(duì)重要性在歐洲各個(gè)國(guó)家均有所下降④根據(jù)學(xué)者的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來(lái)看,從1705年到1870年,歐洲農(nóng)業(yè)的相對(duì)重要性在英格蘭、蘇格蘭和比利時(shí)下降得最快。參見(jiàn)(英)布勞德伯利等編著:《劍橋現(xiàn)代歐洲經(jīng)濟(jì)史:1700—1870》(第一卷),何富彩等譯,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第124頁(yè)。。總體看來(lái),“19世紀(jì)中葉以前,歐洲的大部分地區(qū)已經(jīng)經(jīng)歷了一次工業(yè)革命,現(xiàn)代技術(shù)的發(fā)展和應(yīng)用促進(jìn)了工業(yè)產(chǎn)出的增加和生產(chǎn)率的提高”,與此同時(shí),歐洲的整體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也發(fā)生了較大的轉(zhuǎn)變⑤關(guān)于這一時(shí)期歐洲整體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轉(zhuǎn)變的具體內(nèi)容參見(jiàn)(英)約瑟夫·庫(kù)利舍爾著:《歐洲近代經(jīng)濟(jì)史》,石軍、周蓮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153頁(yè)。。以1870年歐洲的工業(yè)為例,英國(guó)、法國(guó)、比利時(shí)和瑞士的工業(yè)產(chǎn)值占本國(guó)GDP的比重高于30%⑥參見(jiàn)(英)布勞德伯利等編著:《劍橋現(xiàn)代歐洲經(jīng)濟(jì)史:1700—1870》(第一卷),何富彩等譯,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第139頁(yè)。。此外,在歐洲各國(guó)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的背景之下,城市化率也在逐年上升⑦詳細(xì)內(nèi)容參見(jiàn)(英)布勞德伯利等編著:《劍橋現(xiàn)代歐洲經(jīng)濟(jì)史:1700—1870》(第一卷),何富彩等譯,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第213頁(yè)。。在這期間,歐洲工業(yè)化的加快,現(xiàn)代生產(chǎn)方式的應(yīng)用,其越來(lái)越產(chǎn)生了進(jìn)行大規(guī)模生產(chǎn)的必要性,促使世界市場(chǎng)不斷擴(kuò)大,促進(jìn)了商人資本發(fā)展的大革命[12](p371-p373)。
在歐洲近代以來(lái)工商業(yè)的發(fā)展過(guò)程中,科學(xué)技術(shù)所取得的巨大進(jìn)步為一種“人本主義”的產(chǎn)生提供了依據(jù),這種人本主義的興起與發(fā)展標(biāo)志著封建社會(huì)的那段蒙昧“信仰”時(shí)期的終結(jié),這種新的時(shí)代精神相信人類憑借自身的理智與情感可以建設(shè)一種“善”的世俗生活秩序⑧相關(guān)內(nèi)容可參見(jiàn)(美)詹姆斯·W.湯姆遜著:《中世紀(jì)晚期歐洲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史》,徐家玲等譯,商務(wù)印書(shū)館2009年版,第2—28頁(yè);(英)亞·沃爾夫著:《十六、十七世紀(jì)科學(xué)、技術(shù)和哲學(xué)史》,周昌忠、苗以順、毛榮運(yùn)、傅學(xué)恒、朱水林譯,周昌忠校,商務(wù)印書(shū)館2009年版,第5—16頁(yè);(英)亞·沃爾夫著:《十八世紀(jì)科學(xué)、技術(shù)和哲學(xué)史》,周昌忠、苗以順、毛榮運(yùn)譯,周昌忠校,商務(wù)印書(shū)館2009年版,第11—14頁(yè)。。如果認(rèn)為,19世紀(jì)之前所發(fā)明的蒸汽機(jī)在陸路和海上的運(yùn)用,加速了歐洲國(guó)家間的自由貿(mào)易和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⑨See James Foreman—Peck,A History of the World Economy: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since 1850,Sussex:The Harvester Press,(1983),pp.33—62.。那么,相應(yīng)地,“自由主義于19世紀(jì)在所有西歐國(guó)家取得勝利,合同法得以創(chuàng)立且最大限度地滿足了自由主義的條件。”[13](p6)在公法領(lǐng)域,通過(guò)公共機(jī)關(guān)對(duì)于這種自由予以認(rèn)可和保障。以刑法為例,刑法存在的正當(dāng)性之一在于保護(hù)“法益”,這種法益“建立在國(guó)家民主憲法所蘊(yùn)含的社會(huì)倫理價(jià)值之上”,如“生命”“所有權(quán)”和“占有權(quán)”等①參見(jiàn)(德)韋塞爾斯著:《德國(guó)刑法總論:犯罪行為及其構(gòu)造》,李昌珂譯,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頁(yè)。。
(二)從中國(guó)19世紀(jì)上半葉的經(jīng)濟(jì)看法律的相對(duì)“落后”現(xiàn)象
與近代西歐的自由主義傳統(tǒng)不同,鴉片戰(zhàn)爭(zhēng)以前,中國(guó)的法律制度維護(hù)的是儒家視閾中的倫理等級(jí)秩序。這種倫理等級(jí)秩序被儒家認(rèn)為是“天秩”的表現(xiàn)②例如,儒家經(jīng)典《尚書(shū)》中說(shuō):“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參見(jiàn)(清)孫星衍撰:《尚書(shū)今古文注疏》卷二《皋陶謨上》,陳抗等點(diǎn)校,中華書(shū)局1986年版,第85頁(yè)。。在長(zhǎng)期的生產(chǎn)實(shí)踐當(dāng)中,中國(guó)先民對(duì)于自然界的天和地有一種十足的敬畏感,他們類比天地的運(yùn)行樣態(tài)設(shè)計(jì)了一套適宜于自身的生產(chǎn)生活秩序③例如,《唐律疏議》的《名例》中即提到:“輕刑明威,大禮崇敬。易曰:‘天垂象,圣人則之。’觀雷電而制威刑,睹秋霜而有肅殺,懲其未犯而防其未然,平其徽纆而存乎博愛(ài),蓋圣王不獲已而用之。”參見(jiàn)(唐)長(zhǎng)孫無(wú)忌等撰:《唐律疏議》,劉俊文點(diǎn)校,中華書(shū)局1983年版,第1頁(yè)。。為己或修身是整個(gè)社會(huì)生產(chǎn)生活秩序建構(gòu)的邏輯起點(diǎn),以血緣為紐帶的倫理等級(jí)秩序崇禮而輕利,刑罰制度只是用來(lái)維護(hù)這種生活慣習(xí)的手段。這種生產(chǎn)生活秩序是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的體現(xiàn)。19世紀(jì)中葉以前,中國(guó)社會(huì)基本上是以自給自足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為主。這種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以家庭為經(jīng)營(yíng)單位,每個(gè)家庭內(nèi)部很少存在與家長(zhǎng)不具有親緣關(guān)系的外來(lái)者。土地產(chǎn)權(quán)的相對(duì)集中與農(nóng)業(yè)經(jīng)營(yíng)的分散狀態(tài)等因素決定了每個(gè)家庭的小規(guī)模經(jīng)營(yíng)④經(jīng)濟(jì)學(xué)領(lǐng)域的相關(guān)學(xué)者研究認(rèn)為,清代統(tǒng)治階級(jí)中的貴族圈占土地、商人對(duì)于土地的投資等因素促使了土地的集中,“地主階級(jí)占有的全國(guó)50%的耕地中,除其中10%的土地由自己經(jīng)營(yíng)外,其余90%的土地分成若干小塊租給具有人身自由的貧苦農(nóng)民耕種。”此外,大部分族田、旗地、屯田也租給農(nóng)民家庭分散經(jīng)營(yíng)。總的來(lái)說(shuō),地主按照農(nóng)民家庭的勞動(dòng)力情況較為平均地分配土地的經(jīng)營(yíng)權(quán)。每個(gè)農(nóng)民家庭的土地經(jīng)營(yíng)規(guī)模較小。參見(jiàn)王詢、于秋華編著:《中國(guó)近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史》,東北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出版社2004年版,第7-15頁(yè)。。此外,作為商品的部分糧食、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作物以及手工業(yè)品也以家庭為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單位。“這種經(jīng)營(yíng)單位都直接生產(chǎn)自己的大部分消費(fèi)品,他們?nèi)〉蒙钯Y料大多是靠著與自然的交換,而不是與社會(huì)的交往。”[14](p17-p24)這種自給自足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國(guó)與外國(guó)的貿(mào)易。例如,清政府采取海禁、限制通商口岸、行商制度等政策限制了同外國(guó)的貿(mào)易。但是,根據(jù)相關(guān)經(jīng)濟(jì)學(xué)學(xué)者的研究,鴉片戰(zhàn)爭(zhēng)前的半個(gè)多世紀(jì),中國(guó)一直在和西方國(guó)家進(jìn)行著貿(mào)易往來(lái)⑤具體內(nèi)容參見(jiàn)許滌新、吳承明著:《中國(guó)資本主義發(fā)展史》(第二卷),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94頁(yè).。從19世紀(jì)上半葉的中西貿(mào)易的情況來(lái)看,“中國(guó)對(duì)于外國(guó)的商品的需求量不大,而西方國(guó)家對(duì)于中國(guó)的茶、絲等商品需求量卻很大。”中西貿(mào)易中,中國(guó)一直有大量順差,西方國(guó)家有大量逆差⑥在19世紀(jì)上半葉,英國(guó)是中國(guó)的主要外貿(mào)對(duì)象。從相關(guān)統(tǒng)計(jì)資料中可以看出,19世紀(jì)上半葉的中英貿(mào)易中,英國(guó)歷年都有逆差。參見(jiàn)王詢、于秋華編著:《中國(guó)近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史》,東北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出版社2004年版,第52—56頁(yè);亦參見(jiàn)嚴(yán)中平等編:《中國(guó)近代經(jīng)濟(jì)史統(tǒng)計(jì)資料選輯》,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12年版,第3頁(yè)。。在中外貿(mào)易過(guò)程中,中西法律之間的巨大差異使得西方資本主義國(guó)家的商人產(chǎn)生了抵制的情緒,在來(lái)華貿(mào)易的外國(guó)商人看來(lái),中國(guó)的法律“很不公正”⑦根據(jù)楊鴻烈先生所援引的案例,“法國(guó)之先例”“英國(guó)之先例”“美國(guó)之先例”,“生息于近代最進(jìn)步的羅馬、英美法系的人,很急于脫離中國(guó)法系的支配。”詳細(xì)內(nèi)容參見(jiàn)楊鴻烈著:《中國(guó)法律發(fā)達(dá)史》,范忠信等校勘,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9年版,第491—492頁(yè)。。
(三)中國(guó)近代的經(jīng)濟(jì)現(xiàn)實(shí)與法律移植
在鴉片戰(zhàn)爭(zhēng)以前,中外貿(mào)易的嚴(yán)重不平衡誘發(fā)了西方資本主義國(guó)家的殖民意圖①“中國(guó)的地主制經(jīng)濟(jì),比之歐洲的領(lǐng)主制,較有靈活性,它能較大限度地適應(yīng)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能較大限度容納商品經(jīng)濟(jì),在生產(chǎn)關(guān)系上進(jìn)行某些調(diào)節(jié),以延長(zhǎng)自己的壽命。”明朝的所謂禁海,主要是禁止私人出海貿(mào)易。政府方面,先后有鄭和七次下西洋。外國(guó)船只來(lái)華,采取貢舶制度。清朝在臺(tái)灣歸順以后,放開(kāi)海禁,采取嚴(yán)格限制海外貿(mào)易的政策。鴉片戰(zhàn)爭(zhēng)前半個(gè)多世紀(jì),中國(guó)一直在和西方國(guó)家進(jìn)行著貿(mào)易往來(lái)。以英國(guó)為例,中英貿(mào)易極不平衡,中國(guó)輸英貨物利潤(rùn)很大,為平衡貿(mào)易,英國(guó)的鴉片輸華量逐年增加。英國(guó)為了獲取像在印度那樣的貿(mào)易權(quán)力,發(fā)動(dòng)了一場(chǎng)蓄謀已久的鴉片戰(zhàn)爭(zhēng)。參見(jiàn)許滌新、吳承明著:《中國(guó)資本主義發(fā)展史》(第二卷),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94頁(yè)。。如上文所指出的,“商人資本發(fā)展的大革命”推動(dòng)了19世紀(jì)經(jīng)濟(jì)全球化的進(jìn)程。在這一過(guò)程中,篤信“市場(chǎng)在資源配置過(guò)程中具有支配作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guó)家根據(jù)自己指定的“自由貿(mào)易規(guī)則”憑借市場(chǎng)和武力先后打開(kāi)海外市場(chǎng),亞洲的印度、中國(guó)先后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guó)家最主要的市場(chǎng)擴(kuò)張對(duì)象②“在近現(xiàn)代社會(huì)發(fā)展進(jìn)程中,世界貿(mào)易對(duì)于經(jīng)濟(jì)的貢獻(xiàn)率越來(lái)越大,越到后來(lái),先發(fā)工業(yè)化國(guó)家對(duì)海外貿(mào)易的依賴性就愈強(qiáng)。”參見(jiàn)仲偉民著:《茶葉與鴉片:十九世紀(jì)經(jīng)濟(jì)全球化中的中國(guó)》,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2010年版,第263—272頁(yè)。。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一方面,使得中外貿(mào)易格局發(fā)生了很大轉(zhuǎn)變。在19世紀(jì)80年代以后直到新中國(guó)成立以前,中國(guó)在對(duì)外貿(mào)易方面一直存在逆差③詳細(xì)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請(qǐng)參見(jiàn)王詢、于秋華編著:《中國(guó)近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史》,東北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出版社2004年版,第68—69頁(yè)。;另一方面,西方國(guó)家設(shè)本國(guó)法庭于中國(guó),專門(mén)處理其本國(guó)公民的有關(guān)生活糾紛④例如,1858年中英締結(jié)的《天津條約》第十六條規(guī)定:“英國(guó)人民有犯事者,皆由英國(guó)懲辦;中國(guó)人欺凌擾害英民,皆由中國(guó)地方官自行懲辦。”參見(jiàn)楊鴻烈著:《中國(guó)法律發(fā)達(dá)史》,范忠信等校勘,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9年版,第492頁(yè)。。外國(guó)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的設(shè)立對(duì)于中國(guó)的司法主權(quán)造成了嚴(yán)重的侵害,也反映出中外法律觀上的巨大差異。
表面看來(lái),以上不同的法律觀之間的差異可以通過(guò)武力來(lái)抹平,這種由軍事強(qiáng)權(quán)所保障的貿(mào)易擴(kuò)張給中國(guó)“推銷”了一種不得不選擇的新的法學(xué)發(fā)展模式。1901年,《中英追加通商航海條約》第十二條規(guī)定:“中國(guó)深欲整頓律例,期與各國(guó)改同一律。……一俟查悉中國(guó)律例情形及其案斷辦法,及一切相關(guān)事實(shí),皆臻妥善,英國(guó)允棄其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15](p492)此后,在1906年,清政府宣示了“籌備立憲”的決心,其中,“將各項(xiàng)法律詳慎厘定”成為預(yù)備立憲的基礎(chǔ)之一,他們認(rèn)為,在當(dāng)時(shí)的中國(guó)社會(huì)中,“規(guī)制未備,民智未開(kāi)”,等待數(shù)年以后,立憲的基本條件“粗具規(guī)模”后,“參用各國(guó)成法,妥議立憲實(shí)行之期限”[16](p44)。如果說(shuō),預(yù)備立憲的宣言書(shū)里面所傳遞出來(lái)的信息是清政府統(tǒng)治者的循序漸進(jìn)的籌備立憲計(jì)劃,那么,從后來(lái)“操切”地引進(jìn)西方法律制度的過(guò)程來(lái)看,這種激進(jìn)的法律移植本身只是迎合了外國(guó)資本主義國(guó)家的在華利益需求。從以下表1,即“近代以來(lái)部分法律法規(guī)的引進(jìn)情況”的時(shí)間先后順序可以看出,早在《宣示預(yù)備立憲先行厘定官制諭》公布之前,清政府已經(jīng)開(kāi)始著手起草《商人通例》和《公司律》,相對(duì)早于《大清新刑律》和《民律草案》的起草,這和清末修訂律例的初衷——使西方國(guó)家撤銷治外法權(quán)是一致的,客觀上為滿足外國(guó)資本主義國(guó)家在華獲取工商業(yè)利益需求提供了制度上的條件⑤按照清政府的說(shuō)法,1902年,在《著沈家本、伍廷芳修訂律例諭》中說(shuō):“現(xiàn)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沈家本、伍廷芳,將一切現(xiàn)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參酌各國(guó)法律,悉心考訂,妥為擬議。務(wù)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高漢成主編:《〈大清新刑律〉立法資料匯編》,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3年版,第3頁(yè)。。
從以下表1中也可以看出,清政府和民國(guó)時(shí)期的法律精英對(duì)于日本的法律制度抱有一種“青睞”的態(tài)度。但是,他們并沒(méi)有覺(jué)察到,在1910年前后,日本已經(jīng)基本上完成了產(chǎn)業(yè)革命。根據(jù)相關(guān)學(xué)者的研究表明,“日本在1886年至1910年的25年的時(shí)間里,走完了原生型產(chǎn)業(yè)革命發(fā)生國(guó)大約需要一個(gè)世紀(jì)的路程。”[17](p72-p92)“20世紀(jì)初的日本經(jīng)濟(jì)已經(jīng)初步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的一部分在運(yùn)轉(zhuǎn)了。”[17](p74)相對(duì)比而言,1910年左右,中國(guó)的現(xiàn)代工業(yè)有所發(fā)展,但是在工業(yè)生產(chǎn)中占有的比重比手工業(yè)要小很多。例如,“在1913年調(diào)查的21 713家工廠中,使用機(jī)械動(dòng)力的占1.6%,不使用機(jī)械動(dòng)力的占98.4%”[18](p201)。鴉片戰(zhàn)爭(zhēng)以后的十多年里,中國(guó)社會(huì)本土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開(kāi)始了緩慢地分解。但是就全國(guó)范圍來(lái)說(shuō),中國(guó)本土的基本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沒(méi)有顯著的變化①例如,相關(guān)學(xué)者研究認(rèn)為,“當(dāng)時(shí),除了幾個(gè)通商口岸如廣州、廈門(mén)和上海附近的手工棉紡織業(yè),由于洋紗、洋布的輸入受到打擊以外,就全國(guó)范圍來(lái)說(shuō),小農(nóng)業(yè)和小手工業(yè)相結(jié)合的基本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還沒(méi)有顯著的變化。”參見(jiàn)孫健著:《中國(guó)經(jīng)濟(jì)通史》(1840—1949年),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版,第744頁(yè)。。甚至“在整個(gè)民國(guó)時(shí)期,農(nóng)業(yè)仍然是中國(guó)經(jīng)濟(jì)的主體。在工業(yè)中,傳統(tǒng)手工業(yè)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傳統(tǒng)手工業(yè)的生產(chǎn)方式與以前相比沒(méi)有太大變化,農(nóng)民家庭仍然是基本的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單位。以1933年為例,有資料表明,當(dāng)年的農(nóng)業(yè)凈產(chǎn)值為187.6億元,占國(guó)內(nèi)凈總產(chǎn)值的65%,農(nóng)業(yè)勞動(dòng)力占全部勞動(dòng)力的比例高達(dá)80%以上”②詳細(xì)內(nèi)容參見(jiàn)王詢、于秋華編著:《中國(guó)近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史》,東北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167頁(yè)。。從這種經(jīng)濟(jì)現(xiàn)實(shí)來(lái)看,20世紀(jì)以后中國(guó)引進(jìn)了資本主義國(guó)家的法律制度,用以調(diào)整本土社會(huì)中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和手工業(yè)占主體地位的生產(chǎn)生活關(guān)系,法律制度和生產(chǎn)實(shí)踐之間存在著抵觸與不適。相對(duì)比而言,在中國(guó)半封建性質(zhì)的經(jīng)濟(jì)形態(tài)下,解放區(qū)的土地革命實(shí)踐和相應(yīng)的法律制度建設(shè)為社會(huì)生產(chǎn)的發(fā)展清除了障礙③在1922年7月,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第二次全國(guó)代表大會(huì)指出,“中國(guó)三萬(wàn)萬(wàn)的農(nóng)民,乃是革命運(yùn)動(dòng)中的最大要素。農(nóng)民因?yàn)橥恋厝狈Α⑷丝诔砻堋⑻鞛?zāi)流行、戰(zhàn)爭(zhēng)和土匪的擾亂、軍閥的額外征稅和剝削、外國(guó)商品的壓迫、生活程度增高等原因,以致日趨窮困和痛苦。”舊中國(guó)的半封建性,決定了中國(guó)民主革命的基本內(nèi)容是土地革命。參見(jiàn)藍(lán)全普編:《解放區(qū)法規(guī)概要》,群眾出版社1982年版,第87頁(yè);例如,1930年,全國(guó)蘇維埃區(qū)域代表大會(huì)通過(guò)了《土地暫行法》,內(nèi)容包括沒(méi)收地主和反革命活動(dòng)者的土地,歸少地或無(wú)地的農(nóng)民使用。參見(jiàn)藍(lán)全普編:《解放區(qū)法規(guī)概要》,群眾出版社1982年版,第90—93頁(yè);參見(jiàn)韓延龍、常兆儒編:《中國(guó)新民主主義革命時(shí)期根據(jù)地法制文獻(xiàn)選編》,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84年版,第7—9頁(yè)。。通過(guò)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國(guó)傳統(tǒng)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占有主導(dǎo)地位的現(xiàn)實(shí)與外國(guó)資本主義國(guó)家軍事強(qiáng)權(quán)保障下的貿(mào)易擴(kuò)張決定了法律移植過(guò)程中傳統(tǒng)與變革之間的艱難抉擇,也決定了新法治與舊禮俗之間的緊張關(guān)系。

表1:近代以來(lái)部分法律法規(guī)的引進(jìn)情況
三、法律移植與當(dāng)代中國(guó)法的理論和中國(guó)法律傳統(tǒng)
如果說(shuō),在新中國(guó)成立以前,自給自足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在面對(duì)被迫引進(jìn)外國(guó)“發(fā)達(dá)”法律制度之時(shí)表現(xiàn)出一種“慌張”“無(wú)奈”甚至“消沉”的情緒。那么,在新中國(guó)成立以后,自覺(jué)的法律移植或立法和新的經(jīng)濟(jì)現(xiàn)實(shí)將會(huì)型塑出自生的現(xiàn)代化法學(xué)理論樣態(tài),這種法學(xué)樣態(tài)也將會(huì)自覺(jué)地承續(xù)損益之后的禮俗傳統(tǒng)。
(一)法律移植與當(dāng)代中國(guó)法學(xué)理論
新中國(guó)成立以來(lái),在廢除了民國(guó)舊法體系的基礎(chǔ)之上,新中國(guó)法學(xué)工作者運(yùn)用馬克思主義立場(chǎng)和方法繼承了革命根據(jù)地的法制建設(shè)經(jīng)驗(yàn),總體上接受了前蘇聯(lián)的法制建設(shè)模式。1950年以后相繼制定并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婚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工會(huì)法》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土地改革法》等法律法規(guī),基本上滿足了社會(huì)主義改造和建國(guó)初期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的需要①參見(jiàn)蔣傳光等著:《新中國(guó)法治簡(jiǎn)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134頁(yè)。。但是,在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huì)召開(kāi)以前的一段時(shí)期內(nèi),“由于對(duì)蘇聯(lián)法學(xué)理論的教條式理解”和無(wú)視中國(guó)經(jīng)濟(jì)現(xiàn)實(shí),法制建設(shè)曾處于徘徊不前的狀態(tài)②參見(jiàn)蔣傳光等著:《新中國(guó)法治簡(jiǎn)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4頁(yè).。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解放思想,實(shí)事求是,一切從實(shí)際出發(fā),理論聯(lián)系實(shí)際”成為我國(guó)社會(huì)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的指南之一,相應(yīng)地,人民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提上了建設(shè)日程③參見(jiàn)《毛澤東、鄧小平論中國(guó)國(guó)情》,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18—522頁(yè)。。直到2011年,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從1978年算起,這30多年的法治建設(shè)仍然離不開(kāi)參照并引進(jìn)東西洋各國(guó)的法律制度。
當(dāng)代的法律移植應(yīng)該摒除新中國(guó)成立以前的那種被動(dòng)的思維模式,自覺(jué)地關(guān)注中國(guó)自身的法律移植是全面依法治國(guó)的必然要求。如果認(rèn)為,法律是那些不依個(gè)人意志為轉(zhuǎn)移的人與人之間相互制約的生產(chǎn)方式和交往形式的體現(xiàn)④參見(jiàn)《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77頁(yè).,獨(dú)立自主的民族國(guó)家完全可以根據(jù)本國(guó)的生產(chǎn)實(shí)踐來(lái)引進(jìn)他國(guó)的先進(jìn)法治建設(shè)經(jīng)驗(yàn)。這種引進(jìn)也可以說(shuō)是一種間接的立法。十九大報(bào)告中指出,要“推進(jìn)科學(xué)立法”,“以良法促進(jìn)發(fā)展、保障善治”⑤參見(jiàn)習(xí)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huì),奪取新時(shí)代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偉大勝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8—39頁(yè)。。這里的“科學(xué)”“良法”和“善治”等范疇的提出,顯然應(yīng)該對(duì)于中國(guó)現(xiàn)實(shí)發(fā)展過(guò)程中的“發(fā)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wèn)題給予充分地關(guān)照。從目前的社會(huì)發(fā)展現(xiàn)實(shí)來(lái)看,中國(guó)的城鎮(zhèn)化進(jìn)程較快,但是從城鎮(zhèn)人口所占的比重來(lái)看,中國(guó)的城鎮(zhèn)化水平相對(duì)于美國(guó)、德國(guó)、日本等國(guó)家明顯滯后。此外,中國(guó)的城鎮(zhèn)化滯后于工業(yè)化進(jìn)程、城鄉(xiāng)差距與區(qū)域差距較大等問(wèn)題很突出⑥參見(jiàn)國(guó)家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huì):《人口和社會(huì)發(fā)展報(bào)告2014——人口變動(dòng)與公共服務(wù)》,第22—25頁(yè)。。由此看來(lái),在全面依法治國(guó)的布局中,對(duì)外國(guó)法律制度采取“拿來(lái)主義”態(tài)度的同時(shí),需要根據(jù)生產(chǎn)實(shí)踐給“以德治國(guó)”留有一定的伸縮空間。
基于中國(guó)自身的自覺(jué)的法律移植與中國(guó)的生產(chǎn)實(shí)踐將會(huì)型塑出一種現(xiàn)代化的中國(guó)法學(xué)理論樣態(tài)。用鄧正來(lái)的話說(shuō),“中國(guó)法學(xué)之所以無(wú)力引領(lǐng)中國(guó)法律、法制的發(fā)展,而只能致使西方法律、法制在中國(guó)的移植與拓展,實(shí)是因?yàn)樗艿搅艘环N源出于西方的‘現(xiàn)代化范式’的支配”[19](p265)。如上文所指出的,19世紀(jì)以后的中國(guó)被動(dòng)地卷入世界經(jīng)濟(jì)體系之中,這一體系生成的所謂“現(xiàn)代化范式”強(qiáng)勢(shì)地支配著中國(guó),由此,法律制度的引進(jìn)成為一種迫不得已的選擇。隨著改革開(kāi)放的深入,“尤其是中國(guó)在加入WTO等國(guó)際組織以后”,“中國(guó)在承諾遵守世界體系的規(guī)則的同時(shí)也獲致了參與修改或參與制定世界體系規(guī)則的資格。”[19](p19-p24)中國(guó)在倡導(dǎo)國(guó)際關(guān)系民主化的背景之下,將會(huì)繪制出基于自身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法律理想圖景”,這種“法律理想圖景”的繪制,需要關(guān)照當(dāng)代的經(jīng)濟(jì)現(xiàn)實(shí),也需要重視中國(guó)的法律傳統(tǒng)。
(二)法律移植與中國(guó)法律傳統(tǒng)
表面看來(lái),在這種“法律理想圖景”的繪制過(guò)程中,一種可以經(jīng)過(guò)“損益”而存世的中國(guó)禮俗傳統(tǒng)與當(dāng)代的法律制度之間存在著“斷裂地帶”,在這一“斷裂地帶”里面,我們所能看到的只是并不適合于中國(guó)近代經(jīng)濟(jì)現(xiàn)實(shí)的“外來(lái)法”,這也是勞乃宣們?cè)谇迥┓ㄖ谱兏镏蹙陀械膿?dān)憂。如果認(rèn)為,人類的歷史是各個(gè)世代片段的鏈接交替,每一代都在利用以前各代留下來(lái)的物質(zhì)資料、生產(chǎn)力以及意識(shí)形態(tài)⑦馬克思主義認(rèn)為,在人類歷史進(jìn)程中,每一代人在完全改變了的條件下繼續(xù)從事先輩的活動(dòng),同時(shí),每一代人又通過(guò)完全改變了的活動(dòng)來(lái)改變舊有的條件。參見(jiàn)馬克思、恩格斯著:《德意志意識(shí)形態(tài)》,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3頁(yè);亦參見(jiàn)恩格斯著:《自然辯證法》,于光遠(yuǎn)等譯編,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頁(yè)。。那么可以說(shuō),在中國(guó)社會(huì)的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過(guò)程中,城鎮(zhèn)化和工業(yè)化步調(diào)的加快,基于經(jīng)濟(jì)現(xiàn)實(shí)的法律移植與自生性的立法決定了法律秩序的一種自覺(jué)的歷史轉(zhuǎn)向。
在自覺(jué)的轉(zhuǎn)向過(guò)程中,傳統(tǒng)的禮俗經(jīng)過(guò)歷史過(guò)程的損益之后,和新時(shí)期的法治共同形成一種“法律理想圖景”,這種“理想圖景可以為人們?cè)u(píng)價(jià)、批判或捍衛(wèi)立法或法律制度提供基礎(chǔ)和判準(zhǔn)”[19](p41-p48)。在孔子看來(lái),夏商周三代之禮經(jīng)過(guò)損益而相承,以至于認(rèn)為,“繼周者”之禮“雖百世可知”,但是,從一些正史史料的記載內(nèi)容來(lái)看,井田制下的禮制和封建地主制下的禮制明顯存在著區(qū)別。在生產(chǎn)力相對(duì)低下的西周社會(huì)中,藉團(tuán)體之人力來(lái)提高生產(chǎn)效益,由此呈現(xiàn)出一幅建立在“井田制”基礎(chǔ)之上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教化齊同”的社會(huì)秩序①《漢書(shū)》中記載了“井田制”的生產(chǎn)模型,即“建步立畮,正其經(jīng)界。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余二十畝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chǎn)可得而平也。”參見(jiàn)(漢)班固撰:《漢書(shū)》卷二十四上《食貨志第四上》,(唐)顏師古注,中華書(shū)局2000年版,第945頁(yè)。。隨著社會(huì)生產(chǎn)力的提高,貧富差距的擴(kuò)大,“壞井田,開(kāi)阡陌,急耕戰(zhàn)之賞”,呈現(xiàn)出一幅新型的“身份等級(jí)秩序”②“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kāi)阡陌,急耕戰(zhàn)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wù)本之故,傾鄰國(guó)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萬(wàn),而貧者食糟糠;有國(guó)強(qiáng)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漢)班固撰:《漢書(shū)》卷二十四上《食貨志第四上》,(唐)顏師古注,中華書(shū)局2000年版,第949頁(yè);“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jí),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漢)司馬遷撰:《史記》卷六十八《商君列傳第八》,(宋)裴骃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jié)正義,中華書(shū)局2000年版,第1765頁(yè)。。甚至在中國(guó)封建社會(huì)的末期,有學(xué)人開(kāi)始對(duì)于這種不適應(yīng)于社會(huì)生產(chǎn)實(shí)踐的禮制教條展開(kāi)抨擊,他們認(rèn)為,應(yīng)該廢除一些“不可使民富的”的“習(xí)俗”“蠱惑”“奢侈”,以工商為本,即“夫工固圣王之所欲來(lái),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蓋皆本也。”③參見(jiàn)(清)黃宗羲著:《明夷待訪錄·財(cái)計(jì)三》,中華書(shū)局1981年版,第40—41頁(yè)。此外,他們把明亡的教訓(xùn)歸責(zé)于“清談務(wù)虛”與“不宗當(dāng)代之務(wù)”④參見(jiàn)(清)顧炎武著:《日知錄集釋》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黃汝成集釋,欒保群等點(diǎn)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02頁(yè)。。相應(yīng)地,根據(jù)相關(guān)學(xué)者的研究,這一時(shí)期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為近代資本主義在中國(guó)的發(fā)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chǔ)⑤參見(jiàn)許滌新、吳承明著:《中國(guó)資本主義發(fā)展史》(第一卷),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07年版,第519-571頁(yè);參見(jiàn)毛澤東著:《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631頁(yè)。。由此看來(lái),中國(guó)傳統(tǒng)的禮在特定的生產(chǎn)實(shí)踐發(fā)展過(guò)程中通過(guò)損益而發(fā)展。這種禮并不因人類自身的喜好而舍棄或存留。由此,中國(guó)新時(shí)代的法治也將會(huì)呈現(xiàn)出自覺(jué)的文化樣態(tài)。
四、結(jié)語(yǔ)
如果說(shuō),自14、15世紀(jì)以來(lái),歐洲地中海沿岸逐步興起的資本主義促進(jìn)了全球性的商人資本發(fā)展的大革命,封建生產(chǎn)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的過(guò)渡使得“法律后進(jìn)國(guó)家”的法律移植成為一種歷史的必然,那么,從20世紀(jì)上半葉的經(jīng)濟(jì)現(xiàn)實(shí)來(lái)看,中國(guó)當(dāng)時(shí)靈活的自給自足的地主制經(jīng)濟(jì)遠(yuǎn)遠(yuǎn)未達(dá)到劇烈變革的程度,西方國(guó)家由軍事強(qiáng)權(quán)所保障的全球貿(mào)易擴(kuò)張為中國(guó)“推銷”了一種不得不選擇的新的法學(xué)發(fā)展模式。這在中國(guó)引起了法制變革與法律傳統(tǒng)之間的糾葛和新法治和舊禮俗之間的緊張關(guān)系。新中國(guó)成立以來(lái),特別是中國(guó)加入WTO以來(lái),中國(guó)應(yīng)該沖破這種被動(dòng)的制度建構(gòu)模式,以一種自覺(jué)的意識(shí)關(guān)注自身,在倡導(dǎo)國(guó)際關(guān)系民主化的背景之下,繪制出基于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法律理想圖景”,在這一過(guò)程中,中國(guó)傳統(tǒng)的禮俗也將會(huì)在全面依法治國(guó)的布局之中發(fā)揮一種經(jīng)過(guò)損益之后的制度功效。
- 理論月刊的其它文章
- 被保險(xiǎn)人權(quán)益保護(hù)的必要
——以規(guī)制免責(zé)條款的濫用為邏輯起點(diǎn) - 基于個(gè)體感知的文化遺產(chǎn)地社區(qū)旅游增權(quán)效果評(píng)價(jià)
——來(lái)自兵馬俑景區(qū)周邊社區(qū)的追蹤研究 - 基于增加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的農(nóng)產(chǎn)品供給側(cè)結(jié)構(gòu)改革的路徑研究
- 構(gòu)建網(wǎng)絡(luò)綜合治理體系:應(yīng)對(duì)網(wǎng)絡(luò)輿情治理風(fēng)險(xiǎn)的有效路徑
- 科技風(fēng)險(xiǎn)的基本特征及其防范對(duì)策
- 社會(huì)工作介入流浪乞討人員社會(huì)救助中的倫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