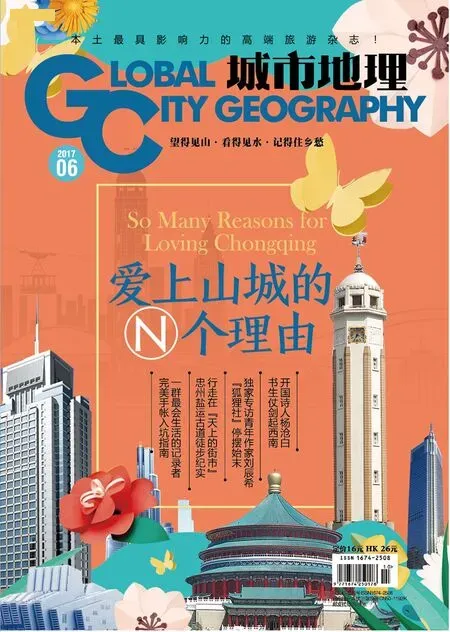天水的古巷 綿延千百年的人間煙火
圖+董瑞君
說到古巷,人們首先想到的或許是南京秦淮河畔的烏衣巷。作為王導和謝安等豪門大族的居住區,烏衣巷在東晉時一度繁華煊赫至極,但在歷史的興廢嬗變中,只留下了“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蒼涼悲嘆。
與朱門繡戶的江南古巷相比,天水的古巷更為樸實,也多了一份清貧:巷子里的居民以普通百姓為主,房屋多為土墻灰瓦的普通宅院,碎石 地的路面上,狹窄的小徑僅容兩三人并行。
盡管如此,歷史悠久的天水古巷,積淀了深厚的人文底 ,令人耳目一新:在士言巷,你會看到 漆大匾上寫著古老的 世格言,“隴南文宗”的遺風猶存;飛將巷里虬枝 曲的老槐樹,時至今日依舊昂首云天,守衛著大將軍李廣的故里;二郎巷深處的織 臺,更是曠世奇文《璇璣圖》的誕生地……

行走在天水不假雕飾的古巷里,不禁讓人發出“古巷月高山色靜”的蒼涼興嘆,卻也不乏“牛羊歸古巷,燕雀繞疏籬”的美好遐想。

這些祖祖輩輩生活在這一條條古巷深處的人們,靜靜地享受著古巷賜予他們的平和與寧靜,過著和從前一樣暗淡清貧,卻又溫情襲人的日子……
士言巷:“隴南文宗”的遺澤
天水的建城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688年的秦武公時代。在城垣面積并不大的天水古城,歷朝歷代拓延并保存下來的百年古巷,竟有160條之多。其中,東關的百年名巷有忠武巷、仁和里、尚義巷等,北關的澄源巷、西方寺巷、十方堂巷等,歷史上與19世紀在天水盛行的西方宗教有些瓜葛,而作為天水老城中心的西關,唐宋以來一直商鋪如云,民居彌望,數百年以上的古巷更是密如織網,比如飛將巷、玩月樓巷、古人巷、折桂巷……它們縱橫交錯,里勾外連,如古城的血脈,吐故納新,迎來送往,咀含了上啟秦漢、近及明清的萬千氣象。
曲折、幽深的古巷,猶如靜靜流淌的小河,無聲無息地穿行在秦磚漢瓦覆蓋的城區。那一座連一座的深宅古院,好似泊在河岸的古船,緊緊依偎在小巷兩岸,相依相偎,把一支支古老、悠遠的謠曲,從古巷深處吹送到街市上,彌漫向全城。于是,這古色古香的小巷便從古城悠遠的歷史中蜿蜒而出,一直延伸到了現在。
一直以來,由鱗次櫛比的古老宅院簇擁著的小巷,原本是城里百姓進出行走的普通街道。忽然有一日,從這小巷深處走出的某個人中了舉、做了官,或拼著性命在外邊干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業,這尋常小巷便名聲大振,平日里為柴米油鹽累得愁眉不展的左鄰右舍,此刻也難得敬備喜筵,整條街巷的大人小孩都聚攏到一起,披紅慶賀。這種場合,少不了要從城里請幾位德高望重的名人雅士來壯壯聲威。酒過三巡,有人提議說這巷子百來年就出了這么個人物,得請人給這巷子改個名,一為小巷揚名,二可昭示后人。一些時日之后,這巷子里便建起了堂堂皇皇的牌坊,高懸起了一塊烏黑發亮的雕漆大匾,沿用了幾輩人的巷名就被一個名字、一句警世格言或是一個古詩意境取代,小巷也像是開創了新紀元,一夜之間從許多密布的街巷中脫穎而出,成了滿城的榮耀。從此,祖祖輩輩居住在這條巷子的人們,從這一如既往的巷子里走出來之際,便被人抬舉,受人尊敬。其后的方志史書,或許就避不過了,得費點筆墨,把這巷道的變遷史和與之有關的人事記錄下來,成為古城的另一種歷史。
位于西關伏羲廟路南的士言巷,原來叫“南巷子”。清同治年間,這巷子出了位官至戶部主事的進士任其昌(字士言)。任先生品高行端,不甘與腐朽官場同流合污,“告老歸里”后主持天水書院,成了名振隴上的“隴南文宗”。任其昌去世后,百姓感戴他對當地文化教育事業的貢獻,便取其字“士言”,改他居住過的南巷子為“士言巷”。一個世紀以來,不論世事如何紛亂,士言巷在天水百姓的心中,永遠都是一個蘊含了詩意和華美文采的地方。

這些祖祖輩輩生活在這一條條古巷深處的人們,靜靜地享受著古巷賜予他們的平和與寧靜,過著和從前一樣暗淡清貧,卻又溫情襲人的日子……

這些祖祖輩輩生活在這一條條古巷深處的人們,靜靜地享受著古巷賜予他們的平和與寧靜,過著和從前一樣暗淡清貧,卻又溫情襲人的日子……

往巷子里的深處走去,巷口的喧鬧就漸漸消失了,隨之而來的是涼嗖嗖、陰森森的寂靜,恍惚間,讓人有一種穿越幽深古道的錯覺。
寂寞身后事——“飛將軍”李廣故里
一片古舊屋舍,幾座朱紅大漆門庭,正南正北地簇擁著一條碎石鋪地,狹窄僅容兩三人并肩行走的小徑,這便是天水古巷常見的格局。
小巷臨街,巷口車水馬龍,市聲喧天,一旦進了巷道,卻又是另一番天地。悠悠的巷道把你領向曲徑通幽處,兩旁的古老宅院便顯得壁立高大起來。重重疊疊的屋檐從長滿青苔的深墻上伸出來,把天空切割成一條窄窄的藍色飄帶,幽幽地在頭頂上飄著。巷子漸走漸深,巷口的喧鬧不知被拋到了何處,涼嗖嗖、陰森森的寂靜迎面撲來,恍惚間,你會有一種穿越幽深古道的錯覺。如果你不收住腳步,繼續往巷道深處走去,原本平直的巷道忽然急急地轉了個彎,你會覺得猶如置身于清風拂面的魏晉時期,或是雍容華貴的漢唐年代。那種愈走愈深沉的寧靜和寂寞,以及偶然從巷道另一頭悠閑踱來的一兩個行人,都會使你陷入一種迷茫的狀態,讓你無從知曉自己到底是身處鬧市,還是在天高地遠的鄉村漫步。
于是,你放慢了腳步,原本煩躁不安的身心像經歷著一次菩提灌頂般的洗禮,不思塵世,不念六根,只是靜靜地承受著古巷深處彌漫著的輕松和安靜。這時你才會明白,祖輩們依戀不舍的幽幽古巷,原本就是安放疲憊心靈的好去處。
在司馬遷的筆下,漢代的飛將軍李廣既是一位開疆拓土、功高蓋世的大英雄,更是太史公心中理想人格的典范。一直以來,人們都認為李廣故居是在伏羲廟附近的李家巷。大約在李廣死后一千多年的宋代,故鄉人民改李家巷為“飛將巷”,并在巷口立起一座牌坊,同時種了兩棵槐樹,為屈死千里沙場的英雄招魂。
我第一次尋訪李廣故里時,“漢飛將軍故里”的牌坊早已不知去向,并不幽深的巷子里也不見一座飛檐翹角的豪宅,巷口唯一一座能讓人感懷千古歲月的門樓,如今也已是殘敗至極,門檐上長滿了萋萋青草。不過,守護巷口的那兩株千年古槐卻依舊老枝蒼勁,昂首云天,為整座巷子帶來一地凝重而爽朗的綠蔭。
面對古老、破舊的飛將巷,我反而認為,對于在司馬遷眼里“悛悛如常人”的李廣來說,身前和身后都懷抱令人隱痛的遺恨,這或許本來就是他的宿命。好在有了這條小巷,有了冷月夕照下始終與小巷相依為命的鄉親父老,李廣孤獨而高貴的靈魂也就沐浴在人間永恒的溫情之中了。

往巷子里的深處走去,巷口的喧鬧就漸漸消失了,隨之而來的是涼嗖嗖、陰森森的寂靜,恍惚間,讓人有一種穿越幽深古道的錯覺。

對于世世代代沿巷而居的老百姓來說,這小巷既是他們的根和生死難離的故土,也是他們最初和最后的精神歸宿。
戍邊將士的赤誠熱血
旗桿巷是天水城區眾多古巷中并不出名的一條小巷,但作家楊聞宇一聽這個名字便感嘆道:“這巷子應該是造旗桿而不是插旗桿的,專門有一條街為作戰的軍士制造旗桿,這天水的戰斗氣氛該多么火烈,多么濃郁,多么迷人!”
楊聞宇先生的這個推斷應該是成立的。歷史上,天水一直是西域少數民族東進中原的第一道屏障,胡漢雜居,戰事頻繁,即便是在大唐盛世,杜甫在天水時所看到的景象,也依然是“降虜兼千帳,居人有萬家”的臨戰狀態。兩千多年以來,天水一帶到底發生過多少戰事,從天水西征遠行的戍邊將士到底把多少白骨留在了漫漫沙場,史書方志沒有記載,但我相信,旗桿巷腳下的泥土,一定還浸染著首尾相接、列陣西行的戍邊將士的鮮血和淚水。
此外,已經改名為“馬廊巷”的雪恥巷,象征回漢友好相處的親睦巷,留下19世紀末天水城手工業興起的淡淡回聲的染布巷……千百年來,小城所經歷的每一個日子,都被這一條條小巷如數家珍般地藏在內心深處,供后來者反復揣摸、品味、回憶。
戰爭的硝煙早已遠去,從歷史的煙塵與血淚中款款走來的古巷,如今也變得如此蒼老而破爛。然而,對于世世代代沿巷而居的老百姓來說,這小巷既是他們的根和生死難離的故土,也是他們最初和最后的精神歸宿。我有一位朋友,他的父親是忠實的佛教居士,祖輩在北關西方寺巷留下一處宅院。老人還健在的時候,每天都會端坐在一樹梨花下捻珠念佛。前幾年老人去世了,西方寺巷開始拆遷改造,他的兒子一家便四處投親寄宿,苦苦等待返遷西方寺巷故居,好終生陪伴遺落在小巷深處的父親那顆孤單的靈魂。

對于世世代代沿巷而居的老百姓來說,這小巷既是他們的根和生死難離的故土,也是他們最初和最后的精神歸宿。

對于世世代代沿巷而居的老百姓來說,這小巷既是他們的根和生死難離的故土,也是他們最初和最后的精神歸宿。
魏晉才女蘇若蘭的眼淚
古巷里的居民,以貧民百姓居多,即便是在玩月樓、醉白樓、折桂巷這樣聽起來充滿詩情畫意的巷子里,也沒有幾戶人家有把酒吟月的雅興。因此,巷子里最常見的樣式,便是土墻灰瓦的普通宅院。走著走著,如果對面豎起一座飛檐脊獸的樓,那必是明清時代富戶名門的古宅。這樣的宅院往往門套門,院套院,占去了大半條巷子。
青石鋪地的庭院里,廳院、耳房、廂房、門庭相互呼應,自成一體。庭院里影壁回廊,門窗雕花,庭院中間秋菊春蘭,四時皆景,假山盆景,飛瀑清流,儼然一處精致的江南園林。倘若是春風乍染,小雨初歇,清風把庭院里的竹梅之韻吹送出來,整條巷子便有了千古不絕的芬芳。
古巷是一首古老的歌謠,曲曲折折,纏纏綿綿,留下了無數幽怨深深的故事。二郎巷深處的織錦臺,至今都回蕩著一代才女蘇若蘭深閨思夫的嗚咽之聲。盡管這位魏晉時代的才女用淋漓情愛織成的《璇璣圖》,最終為她與負心郎竇滔的愛情故事畫上了一個大團圓的句號,但時隔一千多年以后,每當我走進這條早已空蕩蕩的二郎巷時,我都會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對于現代社會那些以理智而冷靜的心態、盡情消費愛情快餐的青年男女來說,蘇若蘭曾經在漫漫長夜里流下的淚水,還能不能打動他們干枯的心?
十幾年前,在一個驟雨初歇的黃昏,當我孤身一人從空蕩蕩的澄源巷里走出來的時候,巷口之外正是一片萬家燈火的光景。這些祖祖輩輩生活在這條條古巷深處的人們,在一盞盞蒼黃的燈光下,圍坐在先人留下的一張桃木方桌旁邊,靜靜地享受著古巷賜予他們的平和與寧靜,過著和從前一樣暗淡清貧,卻又溫情襲人的日子,這個場面至今讓我難以忘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