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學(xué)”后面的隱形人
——記敦煌學(xué)專家孫國璋
屈全繩
原成都軍區(qū)副政委

1975年,孫國璋(右二)與段文杰等考察新疆石窟
最近筆者收集敦煌學(xué)專家的資料時(shí)才發(fā)現(xiàn),孫國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位從北京大學(xué)歷史系考古專業(yè)畢業(yè)的女學(xué)生,是離開中國科學(xué)院北京考古研究所投身莫高窟研究最早的女學(xué)者。大象無形,大音希聲。在敦煌研究院從事了二十年石窟考古工作,研究了一輩子莫高窟藏經(jīng)洞藝術(shù),孫國璋至今不認(rèn)為自己是敦煌學(xué)專家,只承認(rèn)自己是個(gè)有敦煌工作經(jīng)歷的普通研究人員。然而歷史已經(jīng)公正地給孫國璋的學(xué)術(shù)地位定格,作為研究佛教造像藝術(shù)的專家和敦煌學(xué)專家,孫國璋是當(dāng)之無愧的。
孫國璋,1930年10月出生于山東蓬萊。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著名佛教藝術(shù)專家、敦煌學(xué)專家。1958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xué)歷史系考古專業(yè)。60年代初調(diào)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從事佛教藝術(shù)研究,多次深入印度、西藏和內(nèi)地考察,對印度佛教、藏傳佛教、漢傳佛教藝術(shù)有頗深的研究和獨(dú)到見解,研究重點(diǎn)為佛造像的發(fā)展與演變。1978年調(diào)入中國歷史博物館,繼續(xù)從事佛教藝術(shù)研究。目前為北京數(shù)所大學(xué)兼職教授。主要著作有《敦煌莫高窟窟前建筑遺址》《中國佛教早期圖象》《簡明中國文物辭典》《中國古代史參考圖錄》《觀世音菩薩》《敦煌——絲路文化瑰寶》《魏晉南北朝文化——宗教篇》。
時(shí)下隱身北京鮮為人知的孫國璋,在即將叩開90歲大門之際,依然治學(xué)不輟,誨人不倦。她常年閉門謝客,卻對登門求學(xué)的弟子照舊傳道授業(yè)解惑,對心馳神往的莫高窟依然關(guān)注有加。她以“操千曲而后曉聲,觀千劍而后識器”自勉,手不釋卷地閱讀最新考古圖書文獻(xiàn),捕捉最新出土文物信息。她在數(shù)以千萬字的莫高窟筆記中鉤沉探微,吹沙淘金,把其中最為珍貴的資料送給學(xué)生,激勵(lì)他們攀登敦煌學(xué)研究的高峰,讓敦煌這顆世界文化遺產(chǎn)皇冠上的明珠,綻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一
知徒莫若師。孫國璋的嫡傳老師宿白先生認(rèn)為,在敦煌學(xué)研究的現(xiàn)代名人榜上,孫國璋的名字是不可缺少的。今年2月剛剛?cè)ナ赖乃薨紫壬钱?dāng)代中國考古界的泰斗,桃李滿門,閱人無數(shù),他對孫國璋的抬愛,不光是看重她的學(xué)問底蘊(yùn),更看重她的人品操守和治學(xué)態(tài)度。宿白先生是在孫國璋心田中播下研究敦煌學(xué)種子的第一人。
1951年秋,在北京大學(xué)歷史系考古專業(yè)的教室里,宿白先生給剛剛?cè)胄5膶W(xué)生們講課時(shí)說,敦煌文物遭受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等西方人掠奪一百多年了,而發(fā)源于中國的敦煌學(xué)比西方的研究也落后了一百多年,就是和日本比還有五六十年的差距。敦煌文物被盜和敦煌研究滯后,是中華民族應(yīng)當(dāng)反省的兩大教訓(xùn),是籠罩中國文物考古工作者心頭的煙云。被掠奪的文物難以追回,但我國敦煌學(xué)的研究一定要趕上西方和日本,實(shí)現(xiàn)這個(gè)目標(biāo)的希望就寄托在你們這一代人身上。
溫婉嫻靜的孫國璋聽著老師聲情激越的講課,和同學(xué)們一樣心潮澎湃,朦朦朧朧地意識到,她們這一代人很可能是敦煌學(xué)研究新局面的開拓者。讓孫國璋始料不及的是,十年之后她真的走進(jìn)敦煌學(xué)研究人員的行列,并在那里實(shí)現(xiàn)了為中國文物考古發(fā)掘貢獻(xiàn)綿薄之力的夢想。
因緣際會,孫國璋是在一個(gè)偶然機(jī)會中和莫高窟結(jié)緣的。1958年秋,孫國璋修完考古專業(yè),以優(yōu)異的成績走出北京大學(xué)校門。因?yàn)榧沂吕p繞,五年制的考古專業(yè)她整整學(xué)了七年。孫國璋還沒來得及考慮畢業(yè)后的去向,中國科學(xué)院北京考古研究所已經(jīng)把學(xué)習(xí)考古專業(yè)的3名學(xué)生的檔案提走了。因?yàn)閷W(xué)過漢語系佛教、藏語系佛教和印度佛教,考古專業(yè)理論扎實(shí)、稔熟英語、粗通俄語,又有攝影、測量、繪畫基礎(chǔ),幾位老專家打算把28歲的孫國璋作為業(yè)務(wù)骨干用心培養(yǎng)。
然而等待孫國璋的既不是整理考古資料,也不是從事野外發(fā)掘,而是和另外兩個(gè)同事上蘭州出差,參與中國科學(xué)院西北分院的組建工作。具體任務(wù)是接收從西安向蘭州搬遷的陜西省考古研究所、歷史研究所、文學(xué)研究所、地理研究所……盡快充實(shí)西北分院的科研力量。孫國璋突然間面臨一項(xiàng)全新的考驗(yàn),她的責(zé)任心和執(zhí)行力遇到了挑戰(zhàn)。完成這項(xiàng)任務(wù),需要與不熟悉的組織和人員打交道,還得了解科研機(jī)構(gòu)異地搬遷的政策、程序、問題和應(yīng)對困難的辦法。面對完全生疏的工作,孫國璋沒有畏懼,她把蘭州之行看成是補(bǔ)充自己知識缺陷和素質(zhì)短板的機(jī)會,抓緊時(shí)間做足功課。
出發(fā)前,孫國璋詳細(xì)了解接收工作的政策規(guī)定,預(yù)判可能遇到的各種困難,向上級和周圍同事請教做思想工作的經(jīng)驗(yàn)。規(guī)定出發(fā)的時(shí)間一到,她把兩個(gè)不到5歲的兒子托付給母親,丟下千絲萬縷的牽掛,忐忑不安地登上了西去的列車。
蘭州——絲綢之路上的重鎮(zhèn),西北重要的商埠,因?yàn)榈叵虏亟穑晕鳚h起就被稱為“金城湯池”。孫國璋完全擁護(hù)國家在蘭州設(shè)置中科院西北分院的決策,但能不能動員陜西幾個(gè)科研所搬遷到蘭州,她確實(shí)底氣不足。從北京出發(fā)時(shí),她的校友和愛人——已經(jīng)在蘭州和劉家峽水庫工地上往返了三年多的工程師于克禮告訴她,蘭州經(jīng)濟(jì)發(fā)展落后,地理環(huán)境、工作條件、生活水平都比西安差,要她作好鎩羽而歸的思想準(zhǔn)備。
實(shí)際情況被于克禮不幸言中。孫國璋和北京考古所的兩位同事以鍥而不舍的精神,前后耗費(fèi)了兩年多時(shí)間,在西安和蘭州之間往返。他們不厭其煩地去西安進(jìn)行搬遷動員,但事情卻沒有多少實(shí)質(zhì)進(jìn)展。西安考古研究所的同道告訴孫國璋,陜西是文物大省,西安是十三朝古都,八百里秦川遍地都是歷史遺存,連老百姓的房檐上下都可能有秦磚漢瓦,搞考古的跑到蘭州是棄長就短。任憑孫國璋說得嘴巴起泡,西安考古所沒一個(gè)人愿意去蘭州。
孫國璋一行陷入無奈之中,在煎熬中等待國家文化部和文物局的最后決定。在蘭州兩年多的時(shí)間里,孫國璋沒有輕擲光陰。工作之余她四處搜集文物考古圖書文獻(xiàn),在中科院西北分院情報(bào)研究所查詢資料,用剛剛學(xué)會的打字技術(shù)打印整理,為以后的學(xué)術(shù)研究儲備知識。孫國璋在蘭州等待接收陜西幾家研究所的消息不脛而走,敦煌研究所常書鴻所長聽到后,專門到蘭州考察孫國璋的業(yè)務(wù)能力。經(jīng)過幾次面對面交流,常書鴻對孫國璋的專業(yè)知識十分欣賞,懇切動員孫國璋去敦煌實(shí)現(xiàn)考古發(fā)掘的抱負(fù)。孫國璋當(dāng)然高興,她向常書鴻表示,只要上級有調(diào)令,她隨時(shí)可以去敦煌報(bào)到。常書鴻兩次上北京,想說服文化部、文物局和考古研究所把孫國璋調(diào)到敦煌去工作,但都無功而返。孫國璋見去敦煌的希望可能落空,陜西幾家研究所又沒有搬遷的動靜,只得作好返回北京的思想準(zhǔn)備。
1961年秋,孫國璋正在蘭州街頭漫無目的地躑躅,驀然間發(fā)現(xiàn)北京考古所的馬德志老師也在街頭散步。馬德志是孫國璋上大學(xué)時(shí)主講考古發(fā)掘課的老師,見到孫國璋又驚又喜,得知接收工作一時(shí)沒有眉目,當(dāng)即表示由他向北京考古所領(lǐng)導(dǎo)反映,讓孫國璋隨他去敦煌搞莫高窟窟前建筑遺址的發(fā)掘工作。馬德志告訴孫國璋,這是國家文物局下達(dá)的任務(wù),是國家立項(xiàng)的課題,讓孫國璋參與發(fā)掘?qū)λ院蟮陌l(fā)展有好處。考古所考慮到孫國璋老懸在蘭州也不是辦法,時(shí)間長了難免荒廢業(yè)務(wù),便同意了馬德志的要求。不久,孫國璋跟隨馬德志走進(jìn)了她夢想中的藝術(shù)殿堂莫高窟。
孫國璋面前的敦煌,植被稀疏,四顧荒涼,野風(fēng)經(jīng)常卷著沙土撲面而來。可是一踏進(jìn)莫高窟窟區(qū),孫國璋才知道什么是文化瑰寶,什么是藝術(shù)殿堂,她仿佛置身于梵天凈土,被各種造型的佛像和壁畫吸引得目不暇接。馬德志為了在天冷之前搶時(shí)間發(fā)掘,不等孫國璋細(xì)看洞窟,便指定她負(fù)責(zé)發(fā)掘53號洞窟前的建筑遺址。
53號窟是盛唐時(shí)期開鑿的一座大窟。據(jù)文字記載,與之匹配的窟前寺廟規(guī)模亦恢弘壯觀。遺址被好幾米厚的沙土覆蓋著,馬德志經(jīng)過測算,大體劃定了遺址位置,孫國璋隨即開始了她平生獨(dú)立發(fā)掘遺址的工作。上大學(xué)時(shí)老師曾領(lǐng)著他們幾個(gè)學(xué)習(xí)考古專業(yè)的學(xué)生參與過幾次考古發(fā)掘,但發(fā)掘的遺址是王侯將相的墳?zāi)梗瑢W(xué)生們只能看著老師和民工小心翼翼地挖坑剖土,自己動手的機(jī)會很少。時(shí)下孫國璋獨(dú)當(dāng)一面負(fù)責(zé)發(fā)掘,既可以動口又可以動手,高興的心情可想而知。她一邊指導(dǎo)民工掀開層層沙土,一邊仔細(xì)扒拉每一鍬沙土中的小件文物,從中發(fā)現(xiàn)諸如耳環(huán)、織錦、銅扣等容易遺漏的衣飾。不到十天,當(dāng)埋在沙土下面的唐朝方磚露出地面時(shí),遺址的規(guī)模和結(jié)構(gòu)展現(xiàn)在孫國璋面前。在馬德志先生的指導(dǎo)下,孫國璋以嚴(yán)謹(jǐn)?shù)膽B(tài)度實(shí)地測算、拍照、繪圖、制表,并做出詳細(xì)筆記,一次采集的數(shù)據(jù)和資料達(dá)5萬多字。一個(gè)多月后,孫國璋根據(jù)實(shí)地發(fā)掘觀察的情況和采集的資料數(shù)據(jù),撰寫了《莫高窟窟前建筑遺址》的學(xué)術(shù)報(bào)告。這是莫高窟窟前建筑遺址研究史上的第一篇報(bào)告,是敦煌藝術(shù)研究領(lǐng)域的一次突破。馬德志十分看好這篇報(bào)告,并把它推薦給《考古》雜志發(fā)表。
進(jìn)入10月,民工回鄉(xiāng)過冬,窟前遺址發(fā)掘只得暫時(shí)停止。發(fā)掘興致正高的孫國璋又跟隨馬德志回到北京,第二次踏進(jìn)了考古研究所的大門。
三年多時(shí)間過去了,從北京到蘭州,從蘭州到敦煌,孫國璋正在一步一步地向著預(yù)設(shè)的專業(yè)目標(biāo)靠進(jìn)時(shí),又回到了她熟悉的北京。她臉上留著被戈壁風(fēng)沙婆娑過的痕跡,手上留著被鐵鍬把子磨礪的老繭,再回到北京考古所時(shí),倒是有些不適應(yīng)了。說不清是離開莫高窟的惆悵,還是對再回莫高窟的向往,總覺得自己已經(jīng)同那座魅力無窮的藝術(shù)寶庫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在孫國璋眼里,那里的每一座洞窟都是一座文物富礦,都是考古工作者可以大有作為的地方。
已經(jīng)上小學(xué)的兩個(gè)兒子,怯生生地看著風(fēng)塵仆仆歸來的母親,眼里露出迷茫的神情。孫國璋能看出孩子對母愛的渴望,但她沒有把更多精力和時(shí)間放在孩子和家務(wù)上,她要抓緊時(shí)間給自己“充電”,為可能再回莫高窟工作儲備知識。孫國璋把所里有關(guān)莫高窟的書籍和文獻(xiàn)搜集起來,潛心鉆研,請教師友,釋疑解惑,從理論和實(shí)踐的結(jié)合上弄通了一些在莫高窟窟前遺址發(fā)掘中沒有解決的問題。
二
孫國璋在工作中表現(xiàn)出來的品格和才學(xué),給常書鴻留下了深刻印象。孫國璋返回北京后,常書鴻多次同國家文化部、文物局和北京考古研究所信函聯(lián)系,希望調(diào)孫國璋去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精誠所至,金石為開,通過長時(shí)間的不懈努力,1963年秋天,常書鴻終于把孫國璋從北京考古所“挖”到了敦煌。
調(diào)令下達(dá)之前,孫國璋征求愛人和父母的意見。于克禮支持孫國璋服從組織安排,認(rèn)為去敦煌學(xué)當(dāng)其用,能發(fā)揮考古專業(yè)的特長。母親擔(dān)心敦煌生活環(huán)境艱苦,要女兒考慮成熟后再作決定。父親對母親的說法不以為然,認(rèn)為敦煌當(dāng)?shù)?萬人能安家立業(yè),生兒育女,孫家的女兒為什么就不能去?工作調(diào)動是組織的決定,不是自己可以選擇的。留戀城市生活,不想去艱苦地方工作,是沒有出息的表現(xiàn),也不是孫家的家風(fēng)!孫國璋后來多次講過,父親是個(gè)寡言少語的人,留在她記憶里的話并不多,但這幾句話卻像警鐘長鳴,隨時(shí)都會在她腦子里發(fā)出響聲!她理解父親是為了化解母親顧慮說這番話的,當(dāng)即表示自己不怕艱苦,只要能在敦煌藝術(shù)研究中做出成績,就是多吃幾公斤沙土也心甘情愿。
莫高窟成了孫國璋的宿命。1963年深秋,孫國璋告別父母和孩子,給遠(yuǎn)在劉家峽水庫工地上的于克禮發(fā)了一封電報(bào),第二次登上西去柳園的火車,從那里轉(zhuǎn)乘汽車,前往敦煌文物研究所報(bào)到。孫國璋到研究所才知道,一個(gè)多月前她的學(xué)妹樊錦詩也到敦煌來了。樊錦詩被分配在美術(shù)組,孫國璋被分配在考古組。樊錦詩是在孫國璋畢業(yè)之后進(jìn)入北大歷史系學(xué)習(xí)考古專業(yè)的,兩人相見恨晚,一見如故,從此結(jié)下了終生不渝的友誼。
在外行眼里,考古發(fā)掘就是挖墳盜墓,一輩子和沙土泥巴打交道,工作又臟又累,能搞出多少名堂!但在孫國璋看來,考古發(fā)掘是對中華歷史文明的敬畏,是對祖宗勤勞智慧的禮贊,更是對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追尋。孫國璋始終認(rèn)為,文化是國家的根本,是民族的血脈,文物又是文化的重要載體,搶救文物就是搶救文化,傳承文化。秉承這個(gè)理念,她再次全身心地投入到窟前遺址的發(fā)掘工作中。從此,這個(gè)身高只有1米50的年輕女子,身上沒有名牌大學(xué)的影子,臉上沒有富家小姐的痕跡,有的只是三伏天的汗水、三九天的凍傷。
老子講過,“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xì)。”讓孫國璋想不到的是,這項(xiàng)看起來不難不大的發(fā)掘工作,一干就是四年多。四個(gè)春夏秋冬,她和同事們嘔心瀝血,精心發(fā)掘,不僅從40多座窟前遺址的地基磚石中找到了一些洞窟開鑿的年代依據(jù),為研究窟內(nèi)建筑、造像和壁畫提供了新的佐證,還繪制出了模擬遺址結(jié)構(gòu)的平面圖。后來請中央工藝美術(shù)學(xué)院的師生,依據(jù)這些圖紙縮小比例,做成了窟前建筑坍塌前的模型,為莫高窟增加了一道古老而新穎的景觀,也為瑰麗的敦煌藝術(shù)增加了新的內(nèi)涵。令人遺憾的是這幾十具飽含孫國璋心血的模型,多數(shù)已經(jīng)被歲月吞噬得殘缺不全,孫國璋相信,總有一天這些窟前建筑的復(fù)制景觀還會同游人見面。

60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人員在莫高窟220窟前進(jìn)行考古發(fā)掘
就在孫國璋埋頭發(fā)掘遺址時(shí),她耗費(fèi)心血撰寫的論文《敦煌莫高窟窟前遺址》也在《考古》雜志上發(fā)表了。文章發(fā)表后國內(nèi)反響不大,但在國際敦煌學(xué)界引起轟動,日本敦煌學(xué)界反響更大。這篇發(fā)掘報(bào)告讓全世界知道,敦煌不僅有莫高窟、藏經(jīng)洞,還有曾經(jīng)輝煌過的窟前建筑,而沉睡遺址中的瑰寶,又隱藏著中華文明多少秘密呢?全世界的考古學(xué)界再一次把目光向敦煌聚焦。
堪稱石破天驚的《敦煌莫高窟窟前遺址發(fā)掘報(bào)告》后來在國際學(xué)術(shù)會議上宣讀,再次引起轟動,國內(nèi)外專家紛紛申請要去敦煌勘察。就在這時(shí)候中國發(fā)生文化大革命,剛剛興起的莫高窟窟前建筑遺址研究熱潮,被“文革”的烈焰吞沒了。
孫國璋獲得了殊榮,但沒有人知道生活煎熬留在她心底的灼傷。最使孫國璋焦慮的是兩個(gè)孩子的教育問題。“養(yǎng)不教,父之過;教不嚴(yán),師之惰。”這是《三字經(jīng)》留給后人的遺訓(xùn)。可這兩條都讓孫國璋犯難。丈夫于克禮作為水利部的骨干工程師,常年在劉家峽水電站的大壩工地上操勞,連一年一度的探親假也落實(shí)不了。10歲的大兒子于建達(dá)一個(gè)人住在劉家峽水電站蘭州辦事處上學(xué),日常生活完全靠自己打理。9歲的小兒子于建橋跟著孫國璋,在敦煌縣城上學(xué)。縣城離莫高窟50里,孩子吃住都在敦煌文物研究所設(shè)在縣城的辦事處,星期六晚上接回,星期天晚上送走。一家四口分散四地,孫國璋身為人妻人母,難免為丈夫和孩子牽腸掛肚。
于建橋初到與北京有著天壤之別的敦煌時(shí),根本不相信四野蒼涼、草木稀疏、飛沙走石的地方,將是他要長期生活的地方。再看看母親的房間陳設(shè),除了泥臺子書架和硬板床,剩下的就是土爐子、泥墩子,連吃飯的筷子也是用紅柳枝削成的。晚上不光沒有電燈,煤油也要定量供應(yīng),燈捻子撮得又細(xì)又短。于建橋背著孫國璋同幾個(gè)從內(nèi)地剛到研究所的小朋友合計(jì),準(zhǔn)備找機(jī)會逃離敦煌,返回北京。可是當(dāng)聽說莫高窟附近白天晚上都有狼群出沒時(shí),孩子們再也沒有過逃離莫高窟的念頭。
于建橋所在的小學(xué),敦煌的同學(xué)不會說普通話,于建橋又聽不懂敦煌話,整天生活在陌生孤單的環(huán)境中。為了使孩子盡快適應(yīng)新的生活,孫國璋鼓勵(lì)孩子主動和本地同學(xué)交朋友,同時(shí)利用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給孩子補(bǔ)習(xí)功課。學(xué)校教學(xué)質(zhì)量上不去,盡管孫國璋耗費(fèi)心力補(bǔ)課,小兒子的成績還是上不去。晚年的孫國璋回憶起這段艱辛日子時(shí)不勝感慨地說,小學(xué)教育是人生的起跑線,起跑時(shí)沒有跟上去,再朝前追就困難了。六七年過去了,孩子雖然能說一口流利的敦煌土話,但北京和敦煌巨大反差在兒子心中留下的陰影一輩子也沒有徹底消失。長大后兄弟倆能理解父母的無奈和苦衷,但劉家峽和莫高窟卻使兩個(gè)兒子的命運(yùn)離開了于克禮和孫國璋希望的軌跡,而且掙扎了一生也沒能逆轉(zhuǎn)。
“文革”開始后紅衛(wèi)兵大串聯(lián),學(xué)校停課鬧革命,正上初中的于建橋被送到鄉(xiāng)下,成為宕河水庫大壩上接受再教育的下鄉(xiāng)知識青年,那一年于建橋只有14歲。后來水利部有個(gè)干部到宕河水庫檢查工作,得知于建橋是于克禮的小兒子,嚴(yán)肅批評了敦煌的做法,將未成年的于建橋調(diào)到張掖學(xué)開汽車,使這個(gè)少年有了一門終生受益的實(shí)用技術(sh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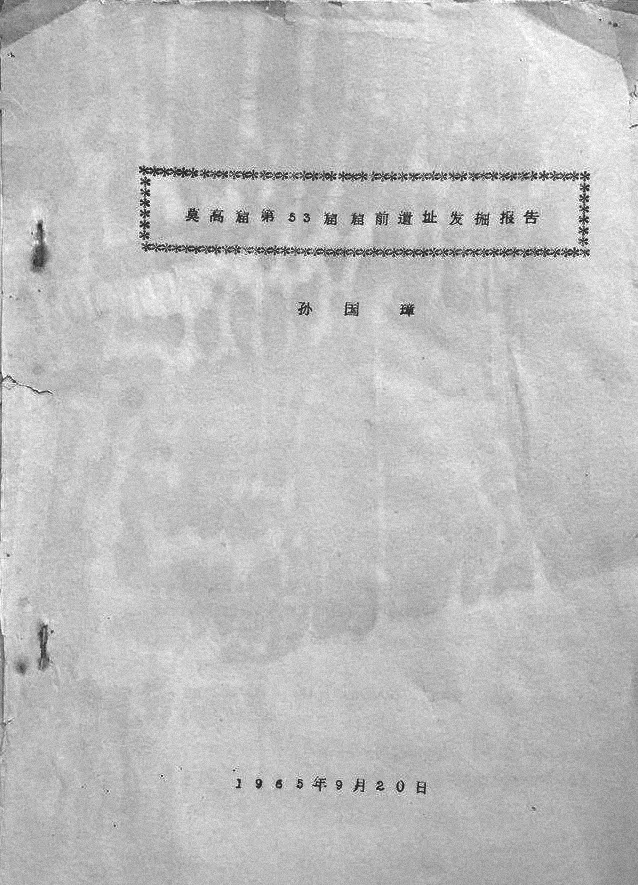
孫國璋撰寫的《莫高窟第53窟窟前遺址發(fā)掘報(bào)告》
被于克禮帶到石門水庫工地接受再教育的大兒子于建達(dá),勉強(qiáng)讀了初中,16歲時(shí)被鐵道部寶雞電化器材廠招工錄用,后來與師傅在當(dāng)?shù)剞r(nóng)村的侄女結(jié)婚成家。郁悶的心情與生活的重負(fù),使這個(gè)兒時(shí)充滿夢想的翩翩少年,安葬完父親的骨灰還未滿三周年,自己就在花甲之年走到了生命的終點(diǎn)。孫國璋在痛苦中大病一場,又堅(jiān)強(qiáng)地挺了過來。于建橋雖然按政策規(guī)定回到北京,并與一名普通女工結(jié)成連理,但受初中文化程度限制,只能從事一般性的工作。父母都是北京大學(xué)的高材生,又都是各自專業(yè)領(lǐng)域里的權(quán)威專家,于克禮還是世界水利大壩委員會兩個(gè)中國委員中的一個(gè),而兩個(gè)兒子和兒媳卻只有初中文化,孫國璋埋在心底的痛楚是可想而知的,但她坦然接受了命運(yùn)的安排,囑咐兒子一定要做好本職工作,什么時(shí)候也不要讓組織為難。
孫國璋告訴筆者,她能在敦煌靜下心來搞專業(yè),是受了父親家國情懷的影響。父親是北京教會學(xué)校畢業(yè)的中學(xué)生,又是留學(xué)日本七年的心外科醫(yī)生,但學(xué)成后毅然回國。盧溝橋事變后,在北京同仁醫(yī)院工作的父親不說日語,不和日本人交往,不為日本人做事,連在中國的日本朋友也斷絕了關(guān)系,在醫(yī)院只說漢語和英語。張家口戰(zhàn)役之后,政府一聲號召,他和醫(yī)院幾位同事立即奔赴東北救治傷員。臨走前父親告訴全家老小,這是國家的安排,是我為國家效力的機(jī)會,我不能提任何條件,克盡全力救治傷員,是我這個(gè)外科醫(yī)生的責(zé)任。這些話在孫國璋腦子里打下了很深的烙印。有一段時(shí)間,孫國璋得知丈夫和孩子都渴望全家人能生活在一起,而且北京好幾個(gè)單位也希望她回去,便動了把兩個(gè)孩子帶回北京讀書的念頭。可這個(gè)念頭一萌生,父親的話就像北斗星一樣在她腦子里閃爍。從此,她再也沒有想過要離開敦煌。即使在生活、工作最困難的時(shí)候也沒想過要與命運(yùn)抗?fàn)帯T趯O國璋看來,工作崗位是國家根據(jù)需要安排的,你不服從安排想調(diào)動,不是與命運(yùn)抗?fàn)帲桥c國家抗?fàn)帲∵@樣做不是她家的家風(fēng),也不是父親的遺傳,更不是她的性格。“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孫國璋暗自下定決心,要像春蠶吐絲那樣,把自己的一生獻(xiàn)給莫高窟,獻(xiàn)給敦煌學(xué)。
三
孫國璋在敦煌最難熬的日子是十年“文革”期間。運(yùn)動開始后,“破四舊”的風(fēng)暴席卷全國,連世界洞窟藝術(shù)皇冠上的明珠莫高窟也未能幸免,窟前建筑遺址的發(fā)掘被迫中斷。修復(fù)洞窟的工匠們由于對研究所知識分子們喜歡侍弄花花草草有看法,對研究人員秋季還能分享窟前果園收獲的四五百斤蘋果、梨有意見,以“破四舊”為名挖掉了窟前的全部果樹,鏟除了草坪和花壇。但對洞窟的“四舊”誰也不敢動一镢頭。泥瓦工清楚,莫高窟的文物是國家的寶貝,有些文物還是工匠們經(jīng)手修復(fù)的,對洞窟的保護(hù)意識和研究人員一樣強(qiáng)烈。當(dāng)研究所按照上級要求,動員全所人員用土坯和泥巴封閉洞口時(shí),泥瓦匠成了骨干,不分晝夜地加班加點(diǎn),只用了半個(gè)多月就把該封的洞窟大門全部封死。
孫國璋和她的同事們本以為,把洞窟封死,莫高窟就不會遭到厄運(yùn),但蘭州傳來的消息卻讓大家陷入新的驚恐慌亂之中。消息說,蘭州大學(xué)要組織造反團(tuán)到敦煌“破四舊”,把莫高窟里的“牛鬼蛇神”砸得片甲不留。噩耗傳來,全所群情激憤,個(gè)個(gè)心如火燎。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經(jīng)請示上級同意,研究所再次全員動手,同當(dāng)?shù)剞r(nóng)民齊心協(xié)力,把敦煌到莫高窟的公路挖斷了幾公里,使汽車根本無法通行。同時(shí)準(zhǔn)備自己動手毀掉一座洞窟,將窟內(nèi)的佛像和壁畫置于斷路的敦煌一端,然后拍攝照片,派人把研究所壯士斷臂、自己毀洞“破四舊”的消息傳給蘭州大學(xué)。學(xué)生們聽到消息、看到照片皆大歡喜,知道敦煌研究所并不是一座頑冥不化的封建堡壘,研究人員也不是封建迷信的衛(wèi)道士。于是放棄了勞師遠(yuǎn)征、上莫高窟“破四舊”的計(jì)劃。其實(shí)局外人哪里知道,對研究所的同志來說,由自己親手毀掉洞窟,無異于飲鴆止渴。這是一個(gè)十分痛苦的兩難抉擇,如果自己不下手毀洞,學(xué)生找上門“破四舊”,40多人的研究所哪能擋住造反派喪失理智的瘋狂;如果自己毀洞,誰能忍心動手!最后報(bào)經(jīng)上級批準(zhǔn),所領(lǐng)導(dǎo)決定,還是把明朝開鑿的洞窟拆掉,以阻止造反派進(jìn)入窟區(qū)縱深破壞。
莫高窟南北兩區(qū),明朝開鑿的洞窟僅此一座。這座洞窟規(guī)模宏大,布局合理,佛塔結(jié)構(gòu)精巧,佛像栩栩如生,從門品、窟墻到窟頂,所有的壁畫都是礦物質(zhì)顏料。壁畫中的經(jīng)變故事,無論是佛天凈土還是凡塵世俗,無論是佛陀菩薩還是飛天舞伎,無不精彩絕倫,呼之欲出。孫國璋每次走進(jìn)這個(gè)洞窟,頓覺神清氣爽,不知不覺中便融入到壁畫之中,靜下心時(shí)連自己的心跳都能聽到。然而就是這樣一座獨(dú)一無二的洞窟,在孫國璋目不轉(zhuǎn)睛的痛苦中被毀掉了。盡管有了充分的思想準(zhǔn)備,拆毀前又進(jìn)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拍照,而且為日后復(fù)原留下了豐富的文字資料。但臨到泥瓦工動手廢窟那一刻,包括孫國璋在內(nèi)的許多同志還是止不住流淚。多么精美的洞窟呀!此洞被毀,等于前秦以降歷代開鑿的洞窟唯獨(dú)缺了明朝。五十多年后孫國璋談起這樁往事仍然唏噓不已。她不無感慨地說,明朝這座洞窟的佛教造像和經(jīng)變壁畫,為研究漢藏交融、漢風(fēng)藏韻、漢魂藏脈提供了最為直觀真實(shí)的歷史見證。但大勢所趨,在劫難逃,不毀掉一個(gè)洞,很可能要?dú)У羰畟€(gè)洞,一百個(gè)洞!令人慶幸的是,正因?yàn)橄铝藲У粢粋€(gè)洞的決心,才讓莫高窟躲過了有可能是歷史上最大的一場浩劫。

孫國璋與古代造像專家、國家鑒定委員會委員步連生在鑒定文物
莫高窟幸免大劫不久,孫國璋和一部分同事被下放到敦煌縣一個(gè)公社勞動鍛煉。孫國璋和同事們分頭住在社員家里,與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聽社員傾訴輕易不對外人說的心里話,關(guān)系親密得像一家人。時(shí)間雖然不到一年,但卻使她終生受益。在同社員們實(shí)行“五同”的日子里,孫國璋還學(xué)會了一些農(nóng)活。農(nóng)民純樸的品格,吃苦的精神,勤儉持家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凈化了孫國璋的心靈,讓她看到了自己的差距,為她準(zhǔn)備在敦煌呆一輩子打下了堅(jiān)實(shí)的思想基礎(chǔ)。
俗話說,早起的鳥兒有蟲吃。從公社勞動鍛煉回來,洞窟沒有啟封,書籍不知去向,孫國璋卻沒有浪費(fèi)年華,立即把工作重點(diǎn)轉(zhuǎn)移到整理過去積累的資料上。這些資料是洞窟被封前采集的。當(dāng)時(shí),考古組和美術(shù)組的研究人員,每人都有一套洞窟鑰匙,可以隨時(shí)進(jìn)入洞窟臨摹或考證。冬季遺址發(fā)掘工作停工之后,洞窟便成為孫國璋的唯一去處。她每次選擇最有代表性的洞窟,零距離地觀察、測試、計(jì)算和拍攝照片。而后把窟內(nèi)的雕塑、佛像,壁畫的年代、規(guī)模、質(zhì)地、色彩和故事內(nèi)容記錄下來,晚上去陳列室,圍著一盞汽燈和20盞煤油燈,對照佛教經(jīng)典,查尋窟內(nèi)塑像和壁畫所展現(xiàn)故事的來龍去脈,考證確鑿無疑后再整理成文字保存。日復(fù)一日,年復(fù)一年,孫國璋在青燈黃卷中采集整理了南區(qū)100多個(gè)洞窟的完整資料,各個(gè)洞窟中佛像的前世今生,壁畫的故事梗概,孫國璋大都了然于心,這為她后來撰寫《敦煌——絲路文化瑰寶》打下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也使她成為研究佛教造像藝術(shù)的專家。
孫國璋秉持人生有涯學(xué)無涯的求學(xué)理念。莫高窟洞窟啟封后,她又把研究的重點(diǎn)轉(zhuǎn)移到佛教造像上。她從學(xué)習(xí)佛教造像演變歷史入手,觀察窟內(nèi)不同時(shí)代佛像的趨同與差別。時(shí)間久了,孫國璋漸漸能夠分辨出各個(gè)朝代佛像的主要特征和細(xì)微節(jié)點(diǎn)。由于敦煌地處古代絲綢之路的要沖,是通往西域和吐蕃的重鎮(zhèn),吐蕃轄治敦煌又長達(dá)六十余年,因此,莫高窟的佛像不僅表現(xiàn)出不同王朝喜好的風(fēng)格,而且也表現(xiàn)出相連地域的不同風(fēng)格。中亞、印巴次大陸,印度、巴基斯坦、克什米爾地區(qū)、阿富汗、尼泊爾、孟加拉以及中國新疆、中原地區(qū)的佛教造像,都不同程度地影響了莫高窟的佛教造像藝術(shù)。有比較才能鑒別。比較研究的時(shí)間久了,孫國璋漸漸發(fā)現(xiàn),不同時(shí)期塑造的佛像,有斯瓦特風(fēng)格、東北印度風(fēng)格、克什米爾風(fēng)格、尼泊爾風(fēng)格的影響,也有西藏本地造像風(fēng)格和中原造像風(fēng)格的影子。孫國璋更加深刻地認(rèn)識到,莫高窟造像風(fēng)格的演變過程,實(shí)際上反映的是佛教中國化的過程,是佛教中國化的載體,是我國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見證。
對莫高窟佛教造像的深入研究,使得孫國璋具備了鑒別佛教造像的扎實(shí)功底。后來她被甘肅省博物館借調(diào)了一年多,又讓她有機(jī)會親眼目睹、親手觸摸、親自鑒別歷代不同風(fēng)格和工藝的金銅佛像,孫國璋識別佛像的知識和鑒定佛像的眼力,得到國家文物局和文博同行的充分肯定。段文杰就任敦煌研究院院長以后,又帶領(lǐng)孫國璋等人去新疆考察了鄯善吐峪溝、庫車庫木吐拉和拜城克孜爾等佛教石窟。新疆之行的一個(gè)多月,豐富了孫國璋對西域佛教洞窟文化的了解,她也成為國家博物館物色佛教造像鑒定專家的不二人選。
1978年8月,經(jīng)過幾輪專家評定和逐級報(bào)批,孫國璋帶著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別了她為之奮斗拼搏過的莫高窟,成為國家博物館鑒定佛教造像的首席專家,同時(shí)成為國家文物委員會佛教造像鑒定專家組成員。
離開本來一輩子也不想離開的莫高窟,回到生于斯長于斯學(xué)于斯的北京,主修考古和佛教藝術(shù)專業(yè)的孫國璋被分配到國家博物館陳列部工作。陳列部是研究展品陳列的部門,有關(guān)佛教藝術(shù)品的陳列內(nèi)容并不多,但館藏文物中則有不同材質(zhì)、不同年代、不同風(fēng)格、不同尺度、不同工藝的佛像、法器和唐卡,有些唐卡上的佛教故事竟與莫高窟壁畫中的故事同宗同源,這使孫國璋大喜過望。
調(diào)到國家博物館工作后,她多次在北京大學(xué)、中央民族大學(xué)等高校和國家博物館、全國縣級文物局干部培訓(xùn)班講課,對莫高窟建筑、雕塑、壁畫中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常能信手拈來,精彩迭出。學(xué)生們普遍反映,聽孫老師講課,有一種跟著教授級導(dǎo)游參觀莫高窟的感覺。
孫國璋治學(xué)嚴(yán)謹(jǐn),即使是熟悉的專業(yè)領(lǐng)域,她也不囿于自己整理的資料。每次接到授課邀請,她都要盡可能搜集新資料予以補(bǔ)充。她要求自己在做學(xué)問上絲毫不能摻假,那怕不拿片紙只字能講兩三個(gè)小時(shí)的課,事前也要寫成講稿,以備經(jīng)得起學(xué)生查問和同行檢驗(yàn)。
“加強(qiáng)文物保護(hù)利用和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傳承,讓中華文化展現(xiàn)出永久魅力和時(shí)代風(fēng)采。”是習(xí)近平總書記向13億中華兒女的倡導(dǎo)。即將邁向九秩年華的孫國璋先生堅(jiān)信,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一定能生生不息,綿綿不斷!一定能魅力無窮,風(fēng)采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