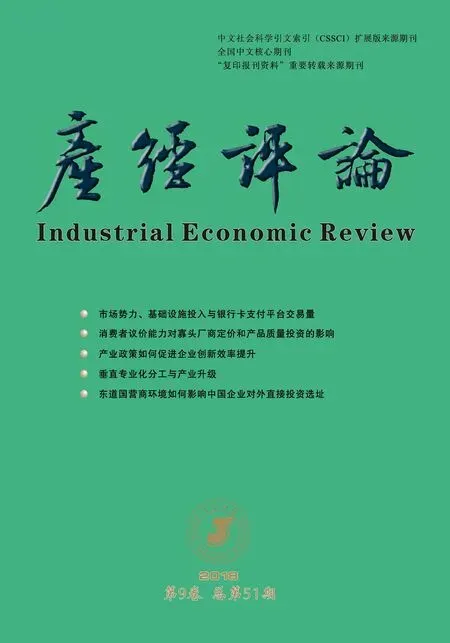市場勢力、基礎設施投入與銀行卡支付平臺交易量
一 引 言
以基礎設施為杠桿撬動并改寫行業競爭位序的案例不勝枚舉,突出表現在電信、電影、航空、銀行卡、連鎖零售等網絡型產業。其中尤以銀行卡支付平臺最具代表性、爭議性和啟發性。全球銀行卡支付平臺具備典型的寡頭競爭特征,維薩、美國運通、萬事達、發現卡、中國銀聯、日本JCB六家銀行卡支付平臺在清算服務環節形成了六足鼎立格局*花旗銀行旗下的大萊國際銀行卡支付平臺于2008年被發現卡集團并購。,平臺之間旨在爭奪交易量的渠道競爭從未停歇且有愈演愈烈趨勢。其中,格外引人關注的渠道沖突事件是維薩封殺銀聯風波。維薩平臺2010年5月濫用其在國際支付清算環節長期以來擁有的市場優勢地位,要求其全球會員收單機構在中國大陸境外的ATM、POS終端受理維薩-銀聯標志的雙幣信用卡時,必須且只能經由維薩的網絡通道清算交易,否則將重罰收單會員。不過,維薩利用其基礎設施網絡對銀聯的“堅壁清野”行動反而倒逼了中國銀聯在境外市場獨立發展自己的收單會員、鋪設海外支付網絡。歷經5年多的基礎設施投資,原本弱勢的中國銀聯于2015年首度逆勢超越老牌銀行卡巨頭維薩,成為全球發卡量最大、交易量最大的國際化銀行卡支付平臺。頗為巧合的是,美國運通支付平臺也曾依靠持續的基礎設施投資實現了交易量逆勢反超萬事達平臺的商業奇跡。
有鑒于上述特征事實,本文的研究問題及其系列追問是,市場勢力如何影響平臺交易量?在市場勢力決定交易量的過程中,平臺基礎設施投入是中性的嗎?如果不是,它究竟起著何種作用?政策含義方面,隨著國內銀行卡支付市場全面放開,市場勢力日趨弱化的本土支付平臺在國內市場該如何應對交易量分流威脅?為此,本文構建了一個獨特的寡頭銀行卡支付平臺面板數據集,分別運用調節效應模型和中介效應模型,實證考察基礎設施投入在市場勢力決定支付平臺交易量過程中的潛在作用,以期更加全面地理解雙邊平臺交易量的決定機制,為平臺運營商和規制部門提供經驗證據和政策建議。
本文以下內容安排:第二部分為文獻綜述,介紹本文的工作基礎并凝練邊際貢獻;第三部分為理論分析,重點闡述市場勢力、基礎設施投入與銀行卡支付平臺交易量潛在的作用機制(研究假說);第四部分基于理論假說建立基準回歸模型;第五部分為實證檢驗;第六部分進一步討論內生性、敏感性和穩健性問題;第七部分總結全文并歸納管理啟示。
二 文獻回顧
既有文獻如Tan和Floros(2013)[1]基于單邊市場視角研究發現,平臺市場勢力增強會抑制交易量擴張;其背后邏輯是,平臺會利用其強大的市場勢力榨取用戶剩余或者拒絕必要的投資從而對需求量產生負面影響。然而,正如Rochet和Tirole(2006)[2]、Wright(2004)[3]、Evans(2003)[4]所言,銀行卡支付平臺具有雙邊市場特征,單邊邏輯下的結論在雙邊市場中未必成立,甚至可能會對政策設計產生誤導作用。因而,務必秉持雙邊市場邏輯來審視市場勢力與交易量之間的關系。
在雙邊市場情境下,為數不多的理論文獻探究了平臺市場勢力對交易量的影響機理。其中, Chakravorti和Roson(2006)[5]分析指出,通過引入競爭削弱銀行卡支付平臺的市場勢力有助于降低價格總水平從而提升交易量。然而,現實并非如此,決定雙邊平臺交易量的是價格結構而非價格水平。程貴孫等(2006)[6]、嚴曉珺(2009)[7]闡明了具有市場勢力的平臺企業如何設計傾斜性價格結構去刺激平臺交易量,發現交叉補貼策略通過改變用戶感知價值進而作用于平臺交易量;駱品亮和殷華祥(2009)[8]揭示了銀行卡支付平臺行使市場勢力平衡雙邊市場需求的機理,平臺憑借其市場勢力相機調整交換費從而調節收單和發卡機構的成本收益關系,最終起到平衡平臺交易需求的作用。李偉倩(2012)[9]發現持卡人的多方持有行為和銀行卡產業的排他性規則鑄就了全球三大卡組織的市場勢力,但平臺交易量的釋放則是由交叉網絡外部性增強引致的;戴菊貴和蔣天虹(2015)[10]研究發現,交叉網絡外部性增強會削弱壟斷平臺的市場勢力從而促進雙邊用戶交易需求擴張;曲創和朱興珍(2015)[11]則指出,交叉網絡外部性增強會強化平臺市場勢力但能推動雙邊用戶數量增長,進而影響潛在交易量。Hagiu和Halaburda(2014)[12]進一步認為,平臺市場勢力增強有助于倒逼雙邊用戶形成靈敏的價格預期,任何一邊微小的價格下降都有助于擴張雙邊用戶的交易需求。
實證研究方面,雙邊市場相關文獻基于結構化或者簡化式計量模型檢驗了平臺市場勢力對交易量的影響方式。其中, Argentesi和Filistrucchi(2007)[13]利用意大利報業平臺數據,建立結構化計量模型來估算市場勢力的經濟后果,發現平臺市場勢力增強將顯著地促進交易量提升; Song(2006)[14]基于雜志行業數據進行并購模擬研究,發現市場勢力提高將強化平臺交叉補貼能力,由此提升雙邊需求(廣告閱讀量/點擊量)并改善社會福利。Fu et al.(2012)[15]對中國銀行卡市場“封轉開”帶來的市場勢力強化效應及其后果進行了實證檢驗,發現市場勢力增強顯著降低了銀行卡支付平臺交易量。
如果說上述文獻重點考察了平臺市場勢力對交易量的直接影響,那么,后續理論研究則開始注意到其他中間變量(如平臺基礎設施投入)對該決定過程的潛在作用。楊煜等(2013)[16]考察了基礎設施投入對網絡運營商市場勢力和交易量的影響,發現基礎設施投入對全業務運營商市場勢力的提升作用明顯、對專業化運營商市場勢力的提升作用則有限;盡管如此,基礎設施作為一種防守型競爭手段依然有助于維持專業化運營商的市場需求。Economides和Hermalin(2012)[17]、Kr?mer和Wiewiorra(2012)[18]的研究均表明,具有價格歧視能力的非中立運營商會更多地進行網絡投資、擴大網絡容量以吸引更多用戶交易,增進社會福利。Njoroge et al.(2013)[19]分析發現,非中立運營商憑借市場勢力攫取剩余的行為會降低用戶參與水平,但其網絡基礎設施投資行為卻能夠吸引更多用戶加入平臺。
現有理論提供的邏輯理路增進了人們對市場勢力與平臺交易量之間直接關系和間接關系的理解,然而相關命題、論斷或假說尚需綜合性凝練歸納和嚴密的實證檢驗。為數不多的文獻試圖推動實證工作(Argentesi和Filistrucchi,2007[13];Song,2006[14];Fu et al.,2012[15]),但存在三項明顯的不足:一是決定機制方面討論不足。現有研究將平臺交易量的決定歸因于市場勢力時,只注意到直接效應卻忽略了中間變量引致的間接效應,片面理解平臺交易量的決定機制可能會錯誤估計市場勢力的作用。二是內生性問題考慮不夠。既有研究承襲了哈佛學派所信奉的“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市場績效”(SCP)之間單向決定邏輯,未考慮芝加哥學派所揭示的雙向(反向)決定關系,對模型內生性、機制敏感性等問題缺乏必要處理。三是研究對象的代表性不強。既有文獻多數局限于純壟斷平臺或者壟斷競爭平臺,缺乏常態化的寡頭平臺樣本,難以準確捕捉到網絡型產業寡頭競爭的典型事實。
與既有研究不同,本文以典型的寡頭銀行卡支付平臺為研究對象,在考慮內生性問題的前提下,集中研究基礎設施投入作為中間變量在市場勢力決定交易量過程中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比較分析發現,平臺是否擁有市場勢力只是一種客觀狀態,實際上,能否有效地發揮其市場勢力激活交易量,會受到網絡規模、終端節點、支付介質等方面基礎設施投入高低的制約。從供給側角度看,平臺基礎設施投入具有沉沒成本的性質,容易構建起進入壁壘,有助于增強市場勢力對交易量的影響力度與持久度;從需求側角度看,平臺基礎設施是實現交叉網絡外部性內部化的瓶頸因素,會影響交易服務可獲性和需求方(交易量)規模經濟效應的開啟。因此,平臺基礎設施投入在市場勢力與交易量之間并非中性的或者無涉的:一方面,可能與市場勢力交互在一起,共同決定交易量;另一方面,也可能作為市場勢力的一種傳導介質,作用于交易量。前一種情況下,基礎設施投入發揮調節作用;后一種情況下,基礎設施投入發揮中介作用。為此,本文遵循哈佛學派的結構-行為-績效(SCP)范式(后續穩健性分析中則會轉而沿襲芝加哥學派的決定范式),將平臺的基礎設施投資行為作為中間變量,基于中介效應模型與調節效應模型實證識別基礎設施投入在市場勢力決定平臺交易量過程中的作用,判斷其影響方式,以期更加全面而深入地理解平臺交易量的決定機制,更為準確地估算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
三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一)市場勢力對平臺交易量的直接影響
在傳統單邊市場上,廠商市場勢力主要體現在其對價格水平的控制上,經典的勒納指數便是例證。雙邊市場中,平臺型廠商的市場勢力則集中表現為對價格結構的調控上。Rochet和Tirole(2006)[2]定義雙邊市場時指出,在價格總水平一定的情況下,雙邊市場實現的交易量因價格結構或者相對價格水平而變化,即價格結構非中性說。按照“價格結構非中性說”,具有市場勢力的雙邊平臺通過調節(或者說操控)價格結構便能直接影響平臺交易量。因此,本文推斷,平臺市場勢力的強弱將直接決定交易量高低。
具體到銀行卡雙邊市場中,較之于弱勢支付平臺,擁有強市場勢力的支付平臺能以較高的自主性與能力對刷卡費率和商戶扣率進行調節,使價格總水平在持卡人與特約商戶中合理分配,更好地平衡雙邊用戶需求以實現更高的聯合交易量。特別地,為了增強持卡人刷卡意愿和商戶受理動機,強勢支付平臺往往能夠憑借其市場勢力設計“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王學斌等,2006)[20]的歧視性價格結構,將一邊用戶的費率設定在平均成本以下、另一邊用戶的費率設置在平均成本以上,這種“蹺蹺板式”的交叉價格補貼方式能夠實現“四兩撥千斤”效應,有力地撬動平臺交易量,被稱為“顛倒原理”(Topsy-turvy Principle)或者“杠桿原理”(Seesaw Principle)(Rochet和Tirole,2006)[2]。因而,本文預期,在如圖1(I)所示的主效應關系中,市場勢力正向影響平臺交易量。

圖1 市場勢力、基礎設施投入與平臺交易量關系假說
(二)基礎設施投入在市場勢力決定平臺交易量中的潛在作用
考慮到基礎設施投入形成的網絡經濟效應,有理由推斷,在市場勢力決定交易量的備擇機制中,基礎設施投入的作用絕非中性。如果市場勢力對平臺交易量的影響取決于基礎設施投入強度,即基礎設施投入的高低影響了市場勢力和平臺交易量之間關系的強弱,那么,基礎設施投入發揮著調節作用;倘若市場勢力是通過基礎設施投入間接地影響平臺交易量,即基礎設施投入是作為“連通器”搭建起市場勢力與平臺交易量之間的因果鏈條,那么,基礎設施投入充當了中介功能。于是,關于基礎設施投入在市場勢力決定平臺交易量的過程中有何潛在影響,理論上存在調節效應假說和中介效應假說兩項備擇假說。
按照調節效應假說,平臺基礎設施服務的可獲性和經濟性會強化市場勢力決定交易量的固有機制。如前文所述,寡頭支付平臺能行使市場勢力操控歧視性、傾斜式價格結構,擴張雙邊俘獲型(Captive)用戶基礎、增加用戶多樣性,提高市場濃度、降低轉換成本,增進交易機會和交易量。平臺基礎設施在該決定過程中發揮調節交易速率和匹配效率的作用,如圖1(II)所示。此外,依據交易費用理論和搜尋匹配理論,平臺的基礎設施投入越完備、網絡規模越龐大,網絡服務可獲性就會越便捷,更能有效地緩解負向網絡外部性造成的擁擠和過載,節約搜尋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更為直觀的表述是,如果將市場勢力決定交易量的過程視為一項化學反應,基礎設施投入則是該項化學反應的“催化劑”或者“抑制劑”,其完備性會加速或者減緩反應進度。倘若平臺市場勢力增強且基礎設施投入完備,平臺交易量自然上升;倘若平臺市場勢力減弱但基礎設施投入保持擴張,只要基礎設施投入力度超過市場勢力弱化幅度,平臺雙邊用戶完成交易的頻率和效率仍然能夠提高,平臺交易量依然有望攀升。反之則反。
根據中介效應假說,平臺市場勢力通過基礎設施投入影響交易量。支付平臺憑借市場勢力實施交叉補貼,將作為支付服務需求方的持卡人和商戶吸引至并維持在平臺,但有效需求的釋放(交易行為的發生)需要通過支付平臺及其成員機構供給的POS機具、ATM終端機、結算系統等基礎設施載體加以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基礎設施是實現交叉網絡外部性內部化的“轉換器”和“管道”(Norman,2008)[21],如圖1(III)所示。事實上,無論網絡型平臺的市場勢力有多強勁,都要求其基礎設施投入達到必要的最低門檻,才有可能觸及或者實現最大化平臺交易量進而最大化收益的目標(Trebing,1994)[22]。按照網絡經濟基本理論,當雙邊用戶基礎積累到一定量級之后,平臺基礎設施容易成為瓶頸資源。一旦持卡人和商戶因基礎設施瓶頸被分割為孤島,則會阻滯市場勢力所凝聚的正向交叉網絡外部性轉化為交易量。因此,隨著網絡型平臺市場勢力的持續增強,俘獲型用戶基礎將越龐大、網絡越復雜,越有必要投資并預留出更充足的基礎設施產能滿足潛在的交易需求。一般而言,強勢支付平臺擁有更加雄厚的實力投資于基礎設施,更能有效地突破瓶頸資源,實現“持卡人-基礎設施-商戶”的雙向互動,推動交易量的強勁增長。總而言之,基礎設施投入是內嵌在市場勢力與平臺交易量因果關系鏈條上不可或缺的中間環節,發揮著間接傳導作用(中介效應)。
盡管調節效應假說與中介效應假說對基礎設施投入的作用方式存在分歧,但兩者均認為基礎設施投入在市場勢力決定平臺交易量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中間作用。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除卻市場勢力,平臺基礎設施投資又會受到哪些關鍵因素的影響?特別地,Casadesus-Masanell和Llanes(2005)[23]指出,封閉式支付平臺的基礎設施投資激勵明顯強于開放式支付平臺。既然如此,支付平臺的所有制類型(開放或者封閉)是否會進一步影響基礎設施投入的中間作用?如果基礎設施投入的中介效應會因所有制類型而呈現出異質性,那么基礎設施投入的中介效應就是一類被調節的中介效應,如圖1(IV)所示。或者,如果基礎設施投入的調節效應會進一步通過平臺所有制傳導,那么基礎設施投入的調節效應就是一類被中介的調節效應。
事實上,在不同的所有制安排下,支付平臺的決策目標、治理結構、運行機制、投資模式存在明顯差別。首先,運行機制方面,封閉式支付平臺是一類一體化網絡組織,開放式支付平臺則是一類非一體化網絡組織(傅聯英和駱品亮,2016)[24],前者避免了成員機構利用市場勢力進行雙重加價問題,后者則容易頻現雙重加價現象以及成員機構利用市場勢力對抗平臺市場勢力的行為。其次,基礎設施投資模式方面,開放式支付平臺的所有權歸屬于會員機構,因而基礎設施由成員機構共同投資建設,私有化的封閉式支付平臺則由平臺運營商自己投資建設或者購買第三方機構的基礎設施服務。最后,在決策目標方面,開放式支付平臺的最終決策目標就是實現交易量最大化,而封閉式支付平臺的最終決策目標是追求壟斷利潤最大化,中間目標才是實現交易量最大化。可見,交易量最大化目標在開放式支付平臺和封閉式支付平臺的內部治理約束中具有不同地位。考慮到上述三項差異,本文認為,如果中介效應假說成立,那么平臺所有制將進一步對基礎設施投入的中介效應產生調節作用。
四 變量說明與模型設定
(一) 數據與變量
考慮到數據可獲性,本文選取了四家國際性銀行卡支付平臺維薩、萬事達、美國運通和發現卡作為研究對象。綜合利用了Bankscope數據庫、PaymentsSource數據庫和各家平臺發布的年報,匹配得到2006年第一季度至2013年第三季度的非平衡面板數據集,分析樣本包含91個觀測值。
1.被解釋變量:平臺交易量(vol)。平臺交易量是銀行卡持卡人和商戶雙邊有效需求的真實反映。不同于傳統市場中廠商面臨的單邊需求量,作為雙邊市場的銀行卡平臺,其需求量的特殊之處在于它是一類聯合需求且具有“雞蛋相生”特征。持卡人和商戶都是平臺用戶,兩者必須同時對支付服務產生需要才能形成有效需求。
2.核心解釋變量:銷售毛利率(pm)。市場勢力是一種控制價格或者排除競爭的力量,勒納指數是市場勢力的一項技術性表達。然而,由于無法直接觀測到邊際成本,傳統的勒納指數只具有理論意義而沒有操作意義(Aghion et al.,2005[25];曲創和劉重陽,2016[26])。因此,作為替代,本文參照Novy-Marx的做法,采用銷售毛利率(Gross Margins,價格高出平均成本的程度)作為市場勢力的代理變量(Novy-Marx,2013)[27],刻畫寡頭支付平臺對價格的控制能力。在國外反壟斷實踐中,墨西哥聯邦政府下設機構聯邦競爭委員會(Comisión Federal de Competencia Económica)2012年正是以銷售毛利率為判別指標,判定電信運營商Telcel具有支配性市場勢力。
3.中間變量:(1)基礎設施投入(fa)。銀行卡支付平臺90%以上的投入用于網絡樞紐和終端設施建設,被列入固定資產。作為固定資產的物理網絡和終端設施投資數據獲取較為便捷且精確,是衡量平臺基礎設施投入力度的良好指標。(2)平臺類型(type)。開放式支付平臺由成員機構共有,共建共享基礎設施網絡;封閉式支付平臺則為運營商私有,獨立投資基礎設施或者購買基礎設施服務。基于該項差異,本文設置二元虛擬變量刻畫平臺所有制類型,1為開放式支付平臺,0為封閉式支付平臺。
4.控制變量:基準模型中,采用各家支付平臺的市場份額(ms)控制支付產業的外部市場結構和競爭態勢。穩健性檢驗中,進一步引入支付平臺其他業務收入、平臺所有制類型控制平臺的多元化經營戰略和所有制差異,詳見后文。
(二)基準模型設定
1.主效應模型
主效應模型揭示了市場勢力對銀行卡支付平臺交易量的直接影響,按照研究問題建立如下回歸方程:
lnvolit=αi+b1lnpmit+b2lnmsit+uit
(1)
其中,被解釋變量lnvolit是各支付平臺交易量取對數,解釋變量lnpmit是平臺銷售毛利率(市場勢力)取對數,lnmsit為市場份額取對數,uit為隨機擾動項。
2.調節效應模型
調節效應假說刻畫了“市場勢力對平臺交易量的影響在不同情形下的異質性作用”,認為基礎設施投入影響市場勢力與支付平臺交易量之間的強度和(或)方向。為檢驗基礎設施投入在市場勢力決定平臺交易量的過程中是否發揮了調節功能,本文建立以基礎設施投入為調節變量的調節效應模型,包含式(1)、式(2)與式(3)。
lnvolit=α0i+c′1lnpmit+c′2lnfait+c′3lnmsit+uit
(2)
lnvolit=α1i+c1m_lnpmit+c2m_lnfait+c3PMFAitc4lnmsit+uit
(3)
調節效應檢驗通過引入變量交互項來實現(溫忠麟等,2005)[28]。在進行估計前,調節效應模型要求對核心解釋變量(市場勢力與基礎設施投入)進行中心化處理。其中,m_lnpmit是中心化后的平臺銷售毛利率,m_lnfait為中心化后的基礎設施投入,交互項PMFAit是中心化后的銷售毛利率與中心化后的基礎設施投入的乘積,其他變量含義同上。若c1、c2、c3均顯著,則基礎設施投入作為調節變量的調節效應顯著。
3.中介效應模型
中介效應假說闡釋了“市場勢力通過(經由)何種渠道影響平臺交易量”,基礎設施投入作為中介變量解釋了市場勢力(自變量)與支付平臺交易量(因變量)之間為何相關或者(以及)如何相關。為檢驗基礎設施投入是否在市場勢力決定平臺交易量的過程中發揮中介作用,本文建立以基礎設施投入為中介變量的中介效應檢驗模型,包含式(1)、式(4)與式(5),各項變量的名稱及其含義同上。
lnfait=α3i+e1lnpmit+e2lnmsit+uit
(4)
lnvolit=α2i+d1lnpmit+d2lnfait+d3lnmsit+uit
(5)
與主效應模型以及調節效應模型不同,中介效應模型采用極大似然法對結構方程(4)和(5)進行估計。當b1、e1、d1均顯著時,中介效應顯著。進一步地,若d1不顯著,則基礎設施投入作為中介變量產生了完全中介效應;若d1顯著但小于b1,則基礎設施投入作為中介變量產生了部分中介效應(MacKinnon et al.,2007[29];Fairchild和MacKinnon,2009[30])。
五 實證檢驗
(一)初步分析:支付平臺基礎設施投資的經驗事實
2008年以前,美國運通一直堅持獨立發卡、獨立收單的封閉式經營模式,其網絡設施和受理終端的規模長期滯后于維薩、萬事達等競爭對手。盡管如此,由于美國運通的本土持卡人主要是“有錢有閑”的旅行娛樂消費者,此類缺乏需求價格彈性的尊享類顧客深受特約商戶的青睞(傅聯英和駱品亮,2016)[24],故運通支付平臺在美國持卡人和商戶兩端均維持著強勁的市場勢力。然而,受制于海外收單網絡瓶頸,美國運通銀行卡在美國本土以外的受理市場(特別是歐洲和亞洲)頻遭商戶拒絕,阻滯了交叉網絡外部性轉化為實際交易量。
為突破基礎設施瓶頸,美國運通于2008年11月10日啟動了平臺開放戰略,在世界范圍內吸收、并購了眾多的發卡機構和收單機構,納入其全球基礎設施網絡體系。在發卡市場上,美國運通銀行卡的境外發行采用多元化的國際策略,主要依靠各國商業銀行、獨立發卡機構、第三方發卡公司的分支機構和零售終端發行。與此同時,在收單市場上,美國運通創造性地提出了雙重會員制規則,在全球160個國家與地區陸續簽約了148家收單合作伙伴,形成了較為完善的POS、ATM、NFC閃付等受理渠道網絡。
2010年11月完成“平臺開放”改革后,美國運通支付平臺的全球交易量一躍超過萬事達(見圖2),改寫了國際支付市場位序格局。彼時,美國運通公司成為傳統銀行卡支付市場中位列維薩之后的世界第二大銀行卡支付平臺。
無獨有偶。在境外曾備受基礎設施網絡掣肘的中國銀聯于2012年開啟突圍戰略,在海外支付市場特別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拓展卡基受理網絡等基礎設施。到目前為止,中國銀聯的全球受理網絡覆蓋了海外157個國家和地區,全球特約受理商戶超過3400萬家、ATM終端達到200萬臺。盡管在全球支付體系中尚缺乏足夠強力的定價權,但長期的基礎設施投入產生了顯著成效,中國銀聯平臺總交易量于2015年首次超越維薩平臺,成為了全球交易量最大的國際性銀行卡支付組織。
美國運通支付平臺和中國銀聯支付平臺基礎設施投資的歷史軌跡及其成功經驗啟迪我們(或者說佐證了本文的一個基本判斷),作為一項中間變量,基礎設施投入在市場勢力與平臺交易量之間扮演的角色絕非是中性的或者是無涉的。至于基礎設施投入在市場勢力決定銀行卡支付平臺交易量過程中究竟起何種作用以及發揮了多大作用,需要進一步基于式(1)-式(5)展開嚴密的計量檢驗。

圖2 全球四大支付平臺交易量變化軌跡
數據來源:Bankscope——全球銀行與金融機構分析庫。
(二)計量分析:基礎設施投入的潛在作用檢驗
模型設定與選擇方面,主效應方程式(1)的Hausman檢驗結果顯示,卡方統計量為8.85、伴隨概率為0.012,說明選擇固定效應模型更為合理。調節效應方程式(2)的Hausman檢驗結果顯示,卡方統計量為9.24、伴隨概率為0.0263,說明選擇固定效應模型更為合理;調節效應方程式(3)的Hausman檢驗結果顯示,卡方統計量為5.45、伴隨概率為0.2444,說明選擇隨機效應模型更為合理。需要指出的是,中介效應方程式(4)與式(5)需要通過結構方程模型方法(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進行估計。完整的中介效應檢驗除了方程式(4)與式(5)外,還需包含單獨估計的主效應方程式(1)。數據方面,修正的Wald截面異方差檢驗結果顯示,卡方統計量為1.74、伴隨概率為0.7830,不能拒絕所有個體同方差的原假設;Woodridge面板數據序列自相關檢驗結果顯示,F統計量為0.866、伴隨概率為0.4208,不能拒絕不存在序列自相關的原假設。
接下來,基于式(1)-式(5),對基礎設施投入在市場勢力決定交易量過程中的作用方式進行計量檢驗。對公共的主效應方程式(1)進行估計,估計結果如表1第二列所示。總體來看,面板數據模型擬合優度為22.74%,擬合效果良好。系數方面,估計方程中核心解釋變量市場勢力的回歸系數為0.1043,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由于變量均采用對數形式,回歸系數的經濟意義就是彈性值。在控制了市場結構后,市場勢力(lnpm)每提高1%,將促進支付平臺交易量(lnvol)增長約0.104%。由于彈性值小于1,說明平臺交易量對市場勢力變動的反應缺乏彈性。

表1 基準模型回歸結果
注:(1)***、**、*分別表示1%、5%、10%的顯著性水平,-表示缺失,括號內數值為標準誤,下同。(2)主效應方程和調節效應方程采用面板數據固定效應模型估計;中介效應通過結構方程加以檢驗和估計,不報告擬合優度R2。(3)Hausman檢驗、修正的Wald截面異方差檢驗、Woodridge面板數據序列自相關檢驗等結果在正文中用文字陳述,未列入表中。
當在主效應方程中加入基礎設施投入變量(lnfa)之后,市場勢力與平臺交易量之間的關系和強度將發生何種變化呢?基礎設施投入在其中是發揮調節變量作用還是充當中介變量功能?如果是調節變量,那它是不是被中介的調節變量?如果是中介變量,那它是不是被調節的中介變量?
1.基礎設施投入是調節變量嗎?不是。
調節效應方程式(2)和式(3)的回歸結果見表1第三列和第四列。由方程式(2)結果可以發現,將基礎設施投入變量加入到主效應方程式(1)后,基礎設施投入顯著地正向影響平臺交易量,市場勢力與平臺交易量之間的關系依然顯著為正,但強度有所下降。值得注意的是,方程式(2)中,市場勢力的回歸系數與基礎設施投入的回歸系數之和約等于方程式(1)中市場勢力的回歸系數。據此,本文推測,較之于方程式(1),方程式(2)中市場勢力對平臺交易量的正向影響之所以下降很可能是被平臺基礎設施投入分流或稀釋了。
由方程式(3)結果可知,加入交互項PMFA后,基礎設施投入對平臺交易量的影響依然保持顯著,交互項PMFA的偏回歸系數在10%的水平下顯著為負;但是,核心解釋變量市場勢力對平臺交易量的影響不再顯著。因而,可以得出一項基本判斷,即基礎設施投入不是調節變量。
2.基礎設施投入是中介變量嗎?是。
中介效應方程式(4)和式(5)采用結構方程模型方法估計,回歸結果見表1中的第五列和第六列。由方程式(4)可以知道,市場勢力顯著地正向影響平臺基礎設施投入。將基礎設施投入作為中間變量加入主效應方程式(1)后,得到方程式(5)的回歸結果。不難發現,核心解釋變量市場勢力對平臺交易量的影響系數變得不再顯著。按照中介效應原理,此種情形下,市場勢力對平臺交易量的影響被基礎設施投入完全中介了。因此,基礎設施投入是(完全)中介變量。
既然基礎設施投入是一項完全中介變量,那么,它的中介效應究竟有多強?進一步在因果中介效應框架下,運用Hicks和Tingley(2011)[31]提供的解構方法對市場勢力影響平臺交易量的總效應進行分解,結果見表2。

表2 市場勢力影響平臺交易量的效應分解:基礎設施投入作為中介變量
市場勢力對支付平臺交易量影響的總效應為0.0421。其中,直接效應不顯著,間接效應(平均因果中介效應,Average Causal Mediation Effect)顯著為正。市場勢力通過基礎設施投入對平臺交易量產生的作用強度為0.0178,該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比率達到42.28%。Hair et al.(2016)[32]將中介效應效能(中介效應與總效應之比)分區的臨界值設定為0.2和0.8。其中,低于0.2為低效能中介效應,0.2-0.8為中等效能中介效應,超過0.8則為高效能中介效應。按照上述標準,基礎設施投入的中介效應強度屬于中等效能層級。總效應分解結果的經濟意義在于:揭示了市場勢力對平臺交易量的間接影響方式,明確了其核心機制是基礎設施投入而非其他競爭性機制(直接效應所指向的其他影響因素)。
3.基礎設施投入僅僅是中介變量嗎?不是。
如前文所述,開放式支付平臺與封閉式支付平臺在基礎設施投資模式方面存在明顯差異。那么,對于不同類型的支付平臺,基礎設施投入的中介效應是否會呈現出顯著的所有制異質性?為了回答該問題,本文進一步考察了平臺所有制類型差異如何影響基礎設施投入的中介效應。加入所有制類型變量type(1表示開放式,0表示封閉式)及其與各變量的交互項,重新對中介效應方程進行回歸,結果見表3。

表3 基礎設施投入作為中介變量的所有制異質性

(續上表)
主效應方程的分組回歸結果表明,無論是開放式支付平臺還是封閉式支付平臺,市場勢力均顯著地正向影響平臺交易量。值得注意的是,中介效應在不同所有制平臺中出現了明顯分化。方程(5)結果顯示,就開放式支付平臺而言,核心解釋變量市場勢力變得不顯著,表明基礎設施投入的完全中介效應在開放式支付平臺情境下仍然顯著;就封閉式支付平臺而言,核心解釋變量市場勢力雖然顯著但是系數變小了,表明基礎設施投入在封閉式支付平臺場景下發揮的是部分中介效應。上述結果充分說明,基礎設施投入的中介效應被平臺所有制類型調節了。因此,更加準確地說,平臺基礎設施投入是一項被調節的中介變量(Moderated Mediator)。

表4 市場勢力影響平臺交易量的效應分解:基礎設施投入作為被調節的中介變量
表4為基礎設施投入作為中介變量在兩種所有制場景下的異質性作用及其效應分解。基礎設施投入的完全中介效應僅僅在開放式支付平臺場景下顯著,其效應強度占總效應強度的比例高達64.63%,這有力地說明開放式支付平臺市場勢力對其交易量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基礎設施投入間接地實現。封閉式支付平臺市場勢力對其交易量產生的直接效應高于其間接效應,直接效應解釋了總效應的67.49%。
六 進一步討論
(一)內生性問題:采用GMM估計處理內生性
在中介效應分析中,可能存在兩類潛在的內生性來源。理論上,芝加哥學派以及新產業組織理論均批評哈佛學派“S-C-P”范式中的線性、靜態、單向因果鏈條,認為廠商行為(如基礎設施投資)與市場績效(如交易量)之間存在雙向因果關系,此為互為因果引發的內生性問題。方法上,中介效應分析所依賴的序貫可忽略假設潛藏著內生性問題。所謂序貫可忽略假設類似于因果推斷中的非混淆假設,指的是潛在結果變量和潛在中介變量條件獨立于處理變量、觀測到的結果變量條件獨立于觀測到的中介變量(VanderWeele和Vansteelandt,2009)[33]。當存在不可觀測的遺漏變量導致方程(4)的干擾項和方程(5)的干擾項相關時,序貫可忽略假設就不成立,內生性問題也就隨之產生。盡管前文在估計中介效應方程時所采用的結構方程固定效應模型實際上已經初步考慮了內生性問題,但是作為穩健性檢驗,本文進一步采用GMM方法對中介效應方程進行估計,結果見表5。

表5 GMM方法估計中介效應模型結果
表5回歸結果顯示,即便改用GMM方法估計模型,市場勢力依然顯著地正向影響基礎設施投入;將基礎設施投入加入主效應方程后,市場勢力對平臺交易量的影響依然會變得不顯著;回歸系數與基準模型以及異質性分析中開放式場景模型的系數接近。由此可知,基準模型的結果具有相當強的穩健性,更加充分地驗證了前文基準模型論斷,即基礎設施投入在市場勢力決定平臺交易量的過程中充當(完全)中介變量的功能。
(二)敏感性問題:模型結果對序貫可忽略假設的依賴性
如前文所述,序貫可忽略假設在中介效應分析中至關重要,但本文無法基于數據判斷其是否滿足。為此,需進一步分析,如果序貫可忽略假設不成立,那么,中介效應結果是否依然成立抑或會如何變化。作為一種替代方法,在中介效應敏感性分析中,現有文獻采用中介變量回歸方程擾動項與結果變量回歸方程擾動項之間的相關系數Rho直觀地刻畫序貫可忽略假設是否成立,并根據因果中介效應強度和方向隨Rho變化的軌跡判斷中介效應的敏感性(Hair et al.,2016)[32]。圖3描繪了平均因果中介效應(ACME,間接效應)對序貫可忽略假設(Rho)的依賴性。

圖3 平均因果中介效應的敏感性
注:陰影部分表示95%的置信區間。
圖3中,水平虛線表示序貫可忽略假設成立時(Rho=0)相應的平均因果中介效應強度。灰色陰影內部的實曲線表示不滿足序貫可忽略假設時,平均因果中介效應的變化軌跡。中介變量回歸方程殘差項與結果變量回歸方程殘差項相關系數Rho必須達到0.2098時,平均因果中介效應才會等于零(或者說間接效應消失,與零無差異);超出臨界值0.2098后,平均因果中介效應的符號才會發生變化。
平均因果中介效應的敏感性分析存在一項不足,即未能提供具體的門檻值用以判斷結果是否可以接受。Keele et al.(2015)[34]建議通過比較同類研究來評價敏感性。Imai et al.(2011)[35]在分析平均因果中介效應敏感性時提供了兩則案例,平均因果中介效應與零無差異時對應的臨界Rho分別為-0.20和-0.39。對比可知,本文結果是可以接受的且具有一定的穩健性。
(三)穩健性問題:引入更多控制變量以及非線性形式
為了讓模型更加飽滿同時避免遺漏重要變量可能導致的模型設定偏誤,本文根據相關經濟理論和經驗事實,盡可能引入更多的控制變量以及變量的非線性形式。首先,控制支付平臺的多元化經營行為。國際四大銀行卡支付平臺中,維薩、萬事達和發現卡是專業性的支付清算商,美國運通則是集旅游服務、信息處理、信用卡、簽賬卡以及旅行支票等金融服務為一體的綜合性支付平臺。相關多元化經營賦予的范圍經濟優勢通常會增強平臺基礎設施投資激勵、有助于提升平臺交易量,非相關多元化經營及其潛在的范圍不經濟則很可能會抑制平臺基礎設施投資并降低交易量。因此,引入除銀行卡業務以外的其他業務收入(lnoor)作為控制變量表征平臺的多元化經營戰略。其次,控制市場競爭的非線性影響。本文遵循哈佛學派傳統,采用各家支付平臺的市場份額刻畫市場結構及其競爭態勢,為了捕捉市場競爭的非線性影響,本文基于新奧地利學派的過程分析范式理論,加入了市場份額的平方項(lnms-sqr)作為控制變量。最后,控制平臺所有制類型。考慮到基礎設施投入的中介效應在不同所有制情境下呈現出明顯的異質性,本文在部分中介效應的穩健性檢驗中引入了平臺所有制類型(type)加以控制。引入上述控制變量后,基于結構方程模型方法對中介效應方程進行回歸得到的估計結果見表6。

表6 引入更多控制變量的穩健性檢驗結果
注:主效應方程(1)與前文結果相同,此處省略。
表6結果顯示,在控制了支付平臺多元化經營行為、平臺所有制類型以及市場競爭的非線性影響后,基礎設施投入的完全中介效應以及在不同所有制類型情境下的部分中介效應依然顯著,強度系數也與前文回歸系數接近,彰顯了基準模型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七 結論與啟示
本文運用一個獨特的寡頭銀行卡支付平臺數據集,實證檢驗了銀行卡支付平臺市場勢力、基礎設施投入和交易量三者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發現,銀行卡支付平臺市場勢力增強能夠顯著地促進交易量擴張,但這種直接作用可能誤估了市場勢力的影響力度。進一步分析發現,銀行卡支付平臺市場勢力決定交易量的過程受到其基礎設施投入的影響,基礎設施投入在其中作為中介變量而非調節變量發揮功用。銀行卡支付平臺市場勢力通過基礎設施投入對交易量產生的間接作用(平均因果中介效應)強度為0.0178;作為一項中介變量,基礎設施投入解釋了市場勢力決定平臺交易量總效應的42.28%。然而,基礎設施投入又不僅僅是一項純粹的中介變量,而是一項受到了銀行卡支付平臺所有制調節的中介變量,中介效應呈現出顯著的異質性。基礎設施投入在開放式銀行卡支付平臺場景下依然是一項完全中介變量,在封閉式銀行卡支付平臺情境下則是一項部分中介變量。
上述研究結論對中國銀行卡市場二次二重改革、對本土銀行卡支付平臺戰略轉型的管理啟示非常明顯。2015年6月起,中國銀行卡支付市場業已全面開放,維薩、美國運通借助國內商業銀行以及第三方收單機構早已開始在線下布局。既然市場開放已成定局,那么,在流量為王的銀行卡支付產業中,本土銀行卡支付平臺該如何應對交易量分流威脅?
本文認為,要維持乃至提振交易量,本土銀行卡支付平臺應該重視平臺基礎設施投入的中介作用。具體來說:(1)從增量角度看,本土銀行卡支付平臺(中國銀聯)可以和成員機構共建共享、加大基礎設施投入。中國銀聯可以嘗試對其成員機構提供基礎設施投資補貼,激勵其擴大交易終端網絡的覆蓋范圍、提高網絡服務的可獲性,進而形成強大的網絡經濟效應以對抗國外銀行卡支付平臺的交易量竊取效應;進一步地,強大的網絡經濟效應將會形成和強化用戶間的交叉網絡外部性,有效地降低持卡人的搜尋成本,吸引更多的消費者加入網絡并鎖定交易、增強用戶粘性,最終實現平臺交易量的持續增長。(2)從存量角度看,中國銀聯作為開放式銀行卡支付平臺需要以更加開放的姿態推進產業鏈各方的合作,特別是可以嘗試盤活第三方收單機構既有的、閑置的線上和線下基礎設施,消化冗余網絡資源。為此,中國銀聯務必摒棄收編第三方收單機構的壟斷思維、果斷舍棄備受詬病的直連模式,逐漸退出競爭性的銀行卡收單環節;通過重新協定利潤分配方案完善“價值網”治理契約,化對抗為合作,充分激活并利用好第三方收單市場網絡。
雙邊市場情境下,就交易量最大化目標而言,銀行卡支付平臺的市場勢力乃至壟斷地位并不必然引致低效率后果。特別是在銀行卡支付行業面臨基礎設施瓶頸時,適度的壟斷勢力反而有助于促進交易量擴張。因此,規制當局需要根據銀行卡支付平臺市場勢力的來源,有區別地馴服市場勢力。一方面,破除依靠行政壟斷占據戰略性網絡基礎設施形成的市場勢力,防止平臺濫用市場勢力拒絕交易以及從事排他性交易;另一方面,呵護在競爭過程中通過基礎設施投入等形成的市場勢力,維持平臺市場勢力與成員機構市場勢力之間的必要制衡,前瞻性地防范平臺市場勢力失控引致雙重加價、抑制或拒絕交易行為,遏制市場勢力增強侵蝕雙邊用戶剩余。
本文的不足之處在于:研究資料局限于平臺間層面,且由于PaymentsSource數據庫自2014年起不再發布銀行卡支付平臺的運營數據,導致未能獲取平臺內成員機構(發卡銀行和收單機構)的加價能力和網絡基礎設施投入數據。因而,本文尚無法分析平臺內成員機構的市場勢力對平臺市場勢力的對抗效應,無法確定成員機構市場勢力對銀行卡支付平臺交易量會產生何種影響,未來的研究可以基于更加精細的數據對此加以識別。
[參考文獻]
[1] Tan, Y., Floros, C.. Market Power, Stability and Performance in the Chinese Banking Industry[J].EconomicIssues, 2013, 18(2): 65-89.
[2] Rochet, J. C., Tirole, J.. Two-sided Markets: A Progress Report[J].TheRANDJournalofEconomics, 2006, 35(3): 645-667.
[3] Wright, J.. One-sided Logic in Two-sided Markets[J].ReviewofNetworkEconomics, 2004, 1(3): 44-64.
[4] Evans, D. S.. The Antitrust Economics of Two-sided Markets[J].YaleJournalonRegulation, 2003, 20(2): 325-382.
[5] Chakravorti, S., Roson, R.. 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The Case of Payment Networks[J].ReviewofNetworkEconomics, 2006, 5(1): 118-143.
[6] 程貴孫, 陳宏民, 孫武軍. 雙邊市場視角下的平臺企業行為研究[J]. 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 2006, (9): 55-60.
[7] 嚴曉珺. 基于交換費機制的多方博弈下的銀行卡定價模型[J]. 金融發展研究, 2009, (1): 18-20.
[8] 駱品亮, 殷華祥. 支付卡網絡跨行交換費的利益博弈與規制研究[J]. 管理科學學報, 2009, 12(4): 23-34.
[9] 李偉倩. 雙邊市場中的定價機制與平臺競爭[D]. 濟南: 山東大學, 2012.
[10] 戴菊貴, 蔣天虹. 基于雙邊市場理論的P2P平臺定價研究[J]. 財經問題研究, 2015, (9): 52-57.
[11] 曲創, 朱興珍. 壟斷勢力的行政獲取與高額利潤的市場獲得——對銀聯身份變遷的雙邊市場解讀[J]. 產業經濟研究, 2015, (1): 101-110.
[12] Hagiu, A., Halaburda, H.. Information and Two-sided Platform Profits[J].InternationalJournalofIndustrialOrganization, 2014, 34: 25-35.
[13] Argentesi, E., Filistrucchi, L.. Estimating Market Power in a Two-sided Market: The Case of Newspapers[J].JournalofAppliedEconometrics, 2007, 22(7): 1247-1266.
[14] Song, M.. Estimating Platform Market Power in Two-sided Market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Magazine Advertising[R]. SSRN Working Paper, No.1908621, 2006.
[15] Fu, L. Y., Yu, L. H., Luo, P. L.. An Empirical Study of Organizational Reform of China’s Bankcard Industry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J].ChineseManagementStudies, 2012, 6(3): 413-425.
[16] 楊煜, 秦雙全, 胡漢輝. 三網融合背景下網絡基礎設施升級的理論與實證研究[J]. 管理工程學報, 2013, 27(4): 186-195.
[17] Economides, N., Hermalin, B.. The Economics of Network Neutrality[J].TheRANDJournalofEconomics, 2012, 43(4): 602-629.
[18] Kr?mer, J., Wiewiorra, L.. Network Neutrality and Congestion Sensitive Content Providers: Implications for Content Variety, Broadband Investment and Regulation[J].InformationSystemsResearch, 2012, 23(4): 1303-1321.
[19] Njoroge, P., Ozdaglar, A. E., Stiermoses, N. E., et al.. Investment in Two-sided Markets and the Net Neutrality Debate[J].ReviewofNetworkEconomics, 2013, 12(4): 355-402.
[20] 王學斌, 趙波, 寇宗來等. 失之東隅、 收之桑榆: 雙邊市場中的銀行卡組織[J]. 經濟學(季刊), 2007, (1): 227-252.
[21] Norman, P..PlumbersandVisionaries:SecuritiesSettlementandEurope’sFinancialMarket[M].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2008.
[22] Trebing, H. M.. The Networks as Infrastructure——The Reestablishment of Market Power[J].JournalofEconomicIssues, 1994, 28(2): 379-389.
[23] Casadesus-Masanell, R., Llanes, G.. Investment Incentives in Open-source and Proprietary Two-sided Platforms[J].JournalofEconomics&ManagementStrategy, 2015, 24(2): 306-324.
[24] 傅聯英, 駱品亮. 開放還是封閉: 基于利潤比較的支付平臺轉型策略研究[J]. 南方經濟, 2016, 34(3): 36-53.
[25] Aghion, P., Bloom, N., Blundell, R., et al..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n Inverted-U Relationship[J].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 2005, 120(2): 701-728.
[26] 曲創, 劉重陽. 平臺廠商市場勢力測度研究——以搜索引擎市場為例[J].中國工業經濟, 2016, (2): 98-113.
[27] Novy-Marx, R.. The Other Side of Value: The Gross Profitability Premium[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 2013, 108(1): 1-28.
[28] 溫忠麟, 侯杰泰, 張雷. 調節效應與中介效應的比較和應用[J]. 心理學報, 2005, 37(2): 268-274.
[29] MacKinnon, D. P., Fairchild, A. J., Fritz, M. Z.. Mediation Analysis[J].AnnualReviewofPsychology, 2007, (58): 593-614.
[30] Fairchild, A. J., MacKinnon, D. P.. A General Model for Testing Mediation and Moderation Effects[J].PreventionScience, 2009, 10(2): 87-99.
[31] Hicks, R., Tingley, D.. Causal Mediation Analysis[J].StataJournal, 2011, 11(4): 605-619.
[32] Hair, J. F., Hult, G. T. M., Ringle, C. M., et al..APrimeronPartialLeastSquaresStructuralEquationModeling(PLS-SEM)[M].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2016.
[33] VanderWeele, T., Vansteelandt, S.. Conceptual Issues Concerning Mediation, Interventions and Composition[J].StatisticsanditsInterface, 2009, (4): 457-468.
[34] Keele, L., Tingley, D., Yamamoto, T.. Identifying Mechanisms Behind Policy Interventions via Causal Mediation Analysis[J].JournalofPolicyAnalysisandManagement, 2015, 34(4): 937-963.
[35] Imai, K., Keele, L., Tingley, D., et al.. Unpacking the Black Box of Causality: Learning about Causal Mechanisms from Experimental and Observational Studies[J].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 2011, 105(4): 765-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