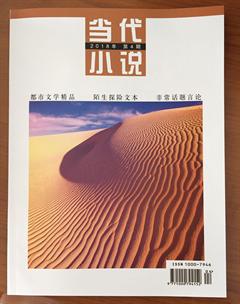生命不能承受之輕
張瑞
從最近讀過(guò)的小說(shuō)來(lái)看,作家們大多把關(guān)切的目光投射到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小人物身上,深入挖掘他們的內(nèi)心世界,在碎屑的日常生活中感受他們的疼痛與悲傷。而我比較關(guān)注的是那些描寫(xiě)女性在現(xiàn)實(shí)生活困境中如何掙扎、自救的作品。閱讀這些作品,就像是在經(jīng)歷一場(chǎng)旅行,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我們目睹了世間百態(tài),理解了生而為人的不易,更懂得了悲憫的力量。
付秀瑩《閏六月》,《時(shí)代文學(xué)》2018年第1期。 《閏六月》是實(shí)力派作家付秀瑩的最新短篇小說(shuō),在這篇小說(shuō)中,她用細(xì)膩、敏銳的目光洞察了北漂女性那復(fù)雜而隱秘的內(nèi)心世界,展現(xiàn)了其生存的苦澀與不易。農(nóng)村女孩劉小改,憑借著自身的努力來(lái)到北京上大學(xué),本以為自此能夠改變貧窮的命運(yùn),然而現(xiàn)實(shí)生活的艱辛與殘酷讓她明白北京城不只有詩(shī)和遠(yuǎn)方,還有眼前的茍且,恰恰是這眼前的茍且讓她選擇了妥協(xié)。為了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有個(gè)依靠,她妥協(xié)于大徐的有車(chē)有房;為了能夠在北京城落地生根,她利用大徐對(duì)她的愧疚(大徐隱瞞了已婚的事實(shí)),得到了在北五環(huán)之外的一個(gè)小郵局工作的機(jī)會(huì)。這一切看似都朝著她所期待的方向發(fā)展著,然而現(xiàn)實(shí)的沉重和生活的瑣細(xì)依舊壓抑著她的身心,就像閏六月的天氣讓人感到煩悶與窒息,生活的無(wú)力與無(wú)奈感撲面而來(lái),不免讓人感到悲涼,而小說(shuō)的結(jié)尾處更將這種情緒推向了極致。小改在人潮洶涌的地鐵口看見(jiàn)了常來(lái)郵局匯款的那個(gè)女人,不同于往日的衣著精致,她展現(xiàn)給小改的是一副邋遢、平常的面孔,對(duì)此小改感到震驚,甚至是恐懼,轉(zhuǎn)身跑進(jìn)了地鐵口。小改的落荒而逃從表面上來(lái)看似乎是驚訝于那個(gè)女人形象的兩極轉(zhuǎn)變,其實(shí)更多的是一種自我命運(yùn)審視后的一種逃離與無(wú)可奈何。無(wú)論是小改還是那個(gè)女人,都是這個(gè)社會(huì)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縮影,她們的苦痛與掙扎,終將會(huì)被淹沒(méi)在時(shí)代的喧囂中,命運(yùn)的齒輪依舊按照各自的軌跡運(yùn)轉(zhuǎn)著,正如小說(shuō)中的一句話:“這世上,每個(gè)人都要學(xué)會(huì)認(rèn)領(lǐng)自己的命運(yùn)。”
方如《人間四月》,《北京文學(xué)》2018年第1期。方如的小說(shuō)一向以洞察人心見(jiàn)長(zhǎng),文字雖質(zhì)樸簡(jiǎn)練,卻能直達(dá)人的靈魂深處,從而將讀者與作品之間的聯(lián)系構(gòu)建起來(lái),從作品中窺視自我人生。這篇小說(shuō)以“我”在英國(guó)的求學(xué)經(jīng)歷為線索,講述了女留學(xué)生四月的人生故事,塑造了一個(gè)既精明能干又自甘墮落的女孩形象。作家將目光聚焦在四月的情感糾葛上,寫(xiě)她與五六十歲的臺(tái)灣老頭兒胡先生同居,她與已婚男人單斌背德的婚外戀情,絕非是為了講述情感故事,而是想要透過(guò)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愛(ài)糾葛看到女性在生活泥淖面前的彷徨與掙扎,疼痛與感傷。深入剖析這個(gè)小說(shuō),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造成四月人生悲劇的原因除了自身因素之外,就是父系形象的缺失。“父親”對(duì)于一個(gè)人來(lái)說(shuō),不單單具有生理上的意義,還有更高層次的心理意義,它意味著力量與依靠,這恰恰是四月用一生去尋找卻得不到的東西。對(duì)依靠感的執(zhí)拗,不但扭曲了她的愛(ài)情觀(交往的每一任男友都比她大上許多),甚至還讓她對(duì)女性自身存在的意義產(chǎn)生了排斥心理,她認(rèn)為這世上的誘惑、危險(xiǎn)那么多,女性要承擔(dān)的后果也那么多,所以她并不想結(jié)婚生子,即便生孩子也不生女孩……或許,女性的柔弱注定了女性在生活的壁壘面前要比男性承擔(dān)更多的苦痛與不易,但是我們同樣也應(yīng)該看到女性特有的韌性與強(qiáng)大的生命力,讓女性的人生更加豐盈。雖然我們不知道生活的意義到底歸于何處,但只要認(rèn)真地對(duì)待生活,生活終究不會(huì)沒(méi)意義。
張春瑩《鋼琴別戀》,《湖南文學(xué)》2018年第1期。自古以來(lái),關(guān)于愛(ài)情和婚姻的討論從未休止過(guò),愛(ài)情的滾燙和婚姻的恒溫能否相互交融,困擾著無(wú)數(shù)男男女女。青年作家張春瑩在這篇小說(shuō)對(duì)這一問(wèn)題給予了關(guān)注和思考。小說(shuō)的主人公薛智明是一位鋼琴老師,從小練習(xí)鋼琴,造就了她不愿妥協(xié)的性格。工作上她寧愿多辛苦一些,也不愿放棄以鋼琴為職業(yè),愛(ài)情上更是如此,她想要的是一份不愿將就的愛(ài)情。面對(duì)余輝的殷勤周到,她并非沒(méi)有心動(dòng),只是出于對(duì)愛(ài)情的慎重,想要進(jìn)一步考驗(yàn)余輝。也許愛(ài)情的脆弱性早已注定這份感情經(jīng)不起考驗(yàn),當(dāng)她對(duì)余輝的求愛(ài)沒(méi)有明確回應(yīng)的時(shí)候,余輝瞞著她到按摩店里尋找安慰;當(dāng)她把捏造的“家族遺傳病史”和“臃腫”的身體呈現(xiàn)在他的面前時(shí),甚至想只要他能夠接受這些,就與他在一起時(shí),這個(gè)男人卻一改往日的溫柔體貼,落荒而逃。盡管我們不能對(duì)余輝的行為作出任何道德上的評(píng)價(jià),因?yàn)槊總€(gè)人都有選擇自己生活的權(quán)利,但是在愛(ài)情面前,逃兵式的行為不免令人感到遺憾和唏噓。在時(shí)代巨變的今天,還有多少空間能夠容納純粹的情感,愛(ài)情是否又必須和婚姻劃清界限?我們是否應(yīng)該繼續(xù)堅(jiān)守愛(ài)情理念呢?作家在小說(shuō)的結(jié)尾給出了自己的回答。小說(shuō)結(jié)尾處寫(xiě)薛智明并沒(méi)有一蹶不振,以一場(chǎng)大病來(lái)與這段無(wú)疾而終的感情告別,重新找回自我,再次愉快地彈奏鋼琴。至于薛智明未來(lái)是遇到真愛(ài)還是重蹈覆轍,這并不是我們所關(guān)切的。作家用這種積極的人生態(tài)度意在告訴讀者,只要心中秉持著最純真的信念,生活即便再瑣碎、庸常,也能聽(tīng)到美妙的聲音。
但及《愛(ài)馬仕圍巾》,《福建文學(xué)》2018年第1期。人到中年,似乎一切都已成定數(shù),中年人大都早已失去了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激情和勇氣,他們追求的是生活的安穩(wěn)與和諧,尤其是女性。然而這一切對(duì)于小說(shuō)中的女主人公來(lái)說(shuō),早已成為了泡影。中年喪女讓她嘗到了世間最烈的孤獨(dú),而與她相濡以沫二十年的丈夫卻在女兒下葬的當(dāng)天與她攤牌,要求與之離婚去守候另一個(gè)家庭,讓她再次墮入無(wú)邊的黑暗中。對(duì)于女人所承受的痛苦,作家并沒(méi)有用文字具體去描述,而是將這種深入骨髓的痛楚用對(duì)比的方式表現(xiàn)出來(lái)。二十年前結(jié)婚時(shí)的濃情蜜意與二十年后逼離婚時(shí)的惡言相向相對(duì)比,在不動(dòng)聲色間將女人的凄涼與痛苦、丈夫的冷酷無(wú)情表現(xiàn)出來(lái)。如果作家止步于這里,這個(gè)小說(shuō)很可能就變成了現(xiàn)代版的“陳世美與秦香蓮”的故事了,藝術(shù)感染力并不是很強(qiáng)烈,顯然并非如此。作家借助具有雙重意義指向的“愛(ài)馬仕圍巾”,來(lái)引出“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好友于茜。圍巾一方面給她帶來(lái)溫暖,就像于茜時(shí)刻給予她的溫暖與關(guān)愛(ài),另一方面圍在脖子里的圍巾又像一條繩索緊緊地勒住了她的脖子,讓她窒息,就像于茜插足她的婚姻帶給她的致命的一刀,于茜的虛偽徹底將她推向深淵。作家將小說(shuō)的情節(jié)安排得很是緊湊,在一天之內(nèi)讓女主人公遭受喪女、失婚、好友背叛三重打擊,給人以精神上的強(qiáng)烈沖擊,鞭撻了人性的復(fù)雜與丑惡。除此之外,作家對(duì)“吃瓜群眾”的描寫(xiě)也頗有意味。當(dāng)看到有人要跳水塔時(shí),眾人帶著興奮與好奇站在塔下面指手畫(huà)腳;當(dāng)女人因?yàn)榻^望將手機(jī)跌落塔下時(shí),眾人亂作一團(tuán),紛紛去撿那散了架的手機(jī)……作家將看客們的丑相刻畫(huà)得淋漓盡致,物質(zhì)利益驅(qū)動(dòng)下的人的冷漠與麻木,不免令人感到悲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