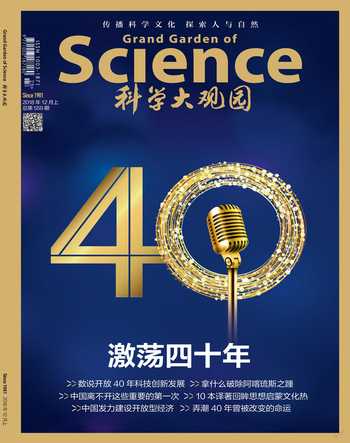魯白 為祖國獻出最好的自己
世界上有影響的著名神經科學家。
“我無法想象,作為一名華夏子孫,我沒有為祖國的繁榮貢獻出自己的最好,或者沒有成為這正在形成中的偉大歷史的一部分。”
2009年7月1日,當魯白決定辭去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神經發育研究室主任后回國定居,并出任中國葛蘭素史克研發部副總裁時,一石激起千層浪,人們開始紛紛推測他在學術生涯頂峰時期做出這一重大轉變的動機:工業界優厚的待遇?中年危機?……
魯白畢業于華東師范大學生物系;1985年在上海第一醫科大學讀碩士;1990年獲美國康奈爾大學醫學院博士學位;1990年到1993年在美國洛克菲勒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進行博士后研究;1993年至1995年底,出任美國羅氏公司分子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及哥倫比亞大學生物系助理教授;1996年到2009年,為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兒童發育研究所神經發育研究室主任。十幾年來,魯白在大腦發育和精神健康領域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科學發現,成為世界上有影響的著名神經科學家。為什么要放棄已爐火純青的學術研究去從事藥物開發?為什么在海外生活很多年后要回到中國?
2010年2月5日,魯白在自己的博客上發表了題為《我決定回國的心路歷程》的英文文章,講述了自己作出人生中這一重大決定的動機。
當我回到上海,開始在一家跨國公司的研發部門工作時,許多人問我:在學術生涯的頂峰時期,為什么會作出轉向工業界這樣一個如此之大的決定?為什么在美國生活這么多年后要回到中國?這個看起來似乎是非常私人的決定,激起了人們許多的好奇和興趣,甚至在最近的一次公開演講中,一個學生也向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
一位老朋友曾經打賭說,公司不可能聘請到我,“因為魯白是一個鐵桿的學院派人物”;許多同仁則表示了遺憾:科學界失去了一位很有潛力的科學家和虔誠的信徒;在我社交圈之外的人則猜測著一個顯而易見的答案:公司慷慨的工資和福利,誘惑我離開了并不富裕的學術界;部分所謂的知情人士則相信,這是解決我個人困境的一種方式。
我無意為自己的動機辯護,但回顧一下我在作出這一重要決定時的心路歷程,也許可以觸動一些人的思考。
在進入生命中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后,許多成功人士會經歷中年危機,這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中年危機表現在:離婚率升高,一些人離開了看似非常成功的事業,放棄了相當舒適的生活,開始做一些富有挑戰性的甚至是自己從未做過的事情。追求新奇是科學家的一個基本特質。但對我來說,這些理由都太簡單了!我作出這種決定是基于一些更重要的因素。
首先,是我在更高層次上追求我對科學的興趣。在我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里,我一直從事神經營養因子特別是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BDNF)的研究。這種研究經歷了兩次重大轉變。一次是從基礎研究(basic research)轉向“臨床轉化”研究(translational research)。一直以來,好奇心驅動著我探索BDNF調控神經發育和腦功能的機制;2003年,我與美國國家精神健康研究所(NIMH)的同事合作發表了一篇論文,報告BDNF基因的一種遺傳變異如何改變了人的記憶功能。這項研究被美國《科學》雜志選為2003年度“十大科技突破”的第二名,也激發了我將對BDNF分泌的細胞機制的研究“轉化”為對神經性或精神性疾病的認識研究的想法。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創立了“基因、認知和精神疾病”項目,我被任命為項目副主任。這個NIH有史以來最大的“臨床轉化”研究項目加速了我的這次轉化。
之后,日復一日與第一流的臨床科學家們打交道,我已經比較擅長將自己在細胞神經科學方面的知識和專長應用于疾病機理的揭示。現在已經很明確,BDNF與多種嚴重疾病相關,如帕金森氏癥和抑郁癥等。因此,我決定實現科學生涯的第二次轉變:從“臨床轉化”研究轉向“應用”研究,即藥物開發的研究。我憧憬著有朝一日,能利用自己在BDNF方面的知識和專長,開發出以BDNF為基礎的藥物,以治療神經性或精神性疾病。然而,在學術界工作不可能做這樣的事,我的挫折感日益增加。
研制藥物的夢想可以追溯到我的研究生時期。在紐約康奈爾醫學院的第一年里,我在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輕科學家手下工作。不久后,他辭去教授工作,創辦了一家名為Regeneron的生物科技公司。如今,這家公司在生物技術界已是大名鼎鼎鼎、眾所周知。讓我著迷的是:一位科學家如何從一個新的科學想法開始制定商業計劃,尋找天使基金、風險資本,并推動股票上市集資(IPO),然后在很短的時間內招兵買馬、延攬人才,組成一個非常高效的公司,從事藥物研發。
后來,我遇見了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的一位對生物高科技頗有研究的教授,他建議我看一本書——《基因夢想:華爾街、學術界和冉冉升起的生物技術》。這本書描述了美國第一家生物技術公司Genetic Systems的興起和衰落,故事復雜有趣,我因此得以縱覽生物制藥業的全貌,從而對這個令人著迷的行業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博士后訓練結束后,我加入了羅氏公司分子生物學研究所。這是我學術職業生涯的開端。這個由制藥業巨子羅氏集團所贊助的頂級研究所位于新澤西州的納特利鎮,與羅氏制藥公司毗鄰而居。通過與羅氏人的接觸,我了解到,從靶標的鑒定、藥物候選者的選擇到臨床試驗,制藥是一個異常復雜的事業。除了前沿的藥物發現能力外,制藥還需要醫學化學、藥物效應動力學、配方設計等知識,還需要同精通產業、商業、法律和金融的專業人士協同合作。通常情況下,一種新藥的成功研發需要大約10億美元的經費和10~12年左右的時間,而一個成功的藥每年的利潤收入也有近5億~10億美元。
研制出第一類新藥的社會和經濟影響力是巨大的,它給科學家帶來的滿足感有時不亞于諾貝爾獎。對真正解決與醫學疾病有關的問題的學術興趣,和對應用自己的科學知識和專長幫助患者的愿望,點燃了我新的理想和抱負,促使我在職業生涯中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加入制藥業。因此,當機會來臨時,我自然而然地迎接了它。
作出這一決定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希望發展自己的領導能力。一般來說,大多數科學家非常專一,對于其研究領域以外的事沒有太大興趣。而所謂領導者,則希望對一個組織機構以及社會有影響,并視該組織及部下的成功為自己的事業。無論在中國還是在美國,在職業生涯的很早時期,我就對領袖的觀念和領導能力的培養比較注意。羅氏公司分子生物學研究所前所長辛迪·尤頓弗雷德(Sydney Udenfriend)是一位著名的生物化學家,他曾就領導能力的話題與我有過一番討論。他認為,人的一生中有為數不多的機會,可以跳躍式地進入下一個人生階段。他說:“你必須準備好邁進下一個階段,否則你就會錯過成長的機會。幾年后,你會發現自己與過去的同行已經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層次上了。”他還告訴我“彼特原理”:你應該向前看得遠一些,但決不要一下子跳進自己現有能力之外的領域。他告訴我,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曾邀請他出任衛生部部長的職務,他拒絕了,因為他認為那是超出自己當時能力之外的事業。
從1995年開始,我多次應邀幫助參與中國的科學和技術發展,包括制定科學機構的改革計劃、招聘高級科學領導、創建新的科學機構等。我也曾參與國家的中長期科學和技術戰略規劃的討論。少數幾次,我發起和參與組織了一些項目、活動,如高登研討會,海外學人評審自然科學基金,起草了重大改革的議案(建議書),等等。而大多數時候,我的角色是咨詢顧問。在美國,從2003年起,我基本上每年都會被邀請擔任科學領導職位,如大學的系主任、研究所所長,等等。我也經常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如果被置于一個需要處理危機或作出艱難決定的位置,我會做什么,怎么做?
一天,有一位領導對我說:“魯白,如果要有真正的影響,你應該坐在駕駛員的位置上。做一個顧問,無論你的想法、建議有多好或多壞,你都不需要為之負責。但是,如果你是作出關鍵決定的人物之一,那么你就生活在這個結果之中。當你作出的決定改變了一個機構或幫助改善了許多人的人生時,你所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獎賞。”這句話對我產生了震撼。我相信我的人生已經走到了一個需要躍進的階段了。我應當將自己的領導能力應用于實踐。如今,我很高興,一個規模適中的機構為我提供了一個學習和實踐領導能力的非常好的機會。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回到中國,為中國的發展和進步做一些長期性的工作。除了情感和文化的理由之外,我還有一個強烈的訴求。中國是我出生和成長的地方,她正在以史無前例的速度發展。在我們的有生之年,很可能將看到中國發展到她歷史的巔峰,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毛澤東主席曾動情地描述:“它是站在地平線上遙望海中已經看到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這一天已經到來。每當我想到這些,我感到自己被一種超我的力量所驅動。
我無法想象,作為一名華夏子孫,我沒有為祖國的繁榮貢獻出自己的最好,或者沒有成為這正在形成中的偉大歷史的一部分。如果繼續留在美國,我也許在科學上會有更深的造詣,并在個人事業上有更大的成就;而在中國,我會有更多的機會幫助別人。在中國建設現代化文明國家的今天,我能夠更好地用自己的知識和專長,來推動中國科學及社會的進步。中國也將為我提供更大的舞臺,展示和發展我的天賦與能力。想到我能幫助培育中國學生、營造科學的文化氣氛,甚至在更大程度上影響社會發展,我感到非常激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