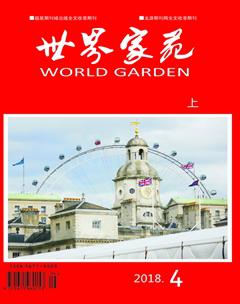封建法體系的特點
(一)客觀性和普遍性
1050年——1150年間,封建法的發展呈現出客觀性和普遍性的特點,伯爾曼先生以采邑的繼承為例子,論證了當時封建法律的發展。在9世紀之前,封臣死后,他的后嗣是否可以繼承他的采邑需要領主的新的授權,而這種方式逐漸演化為一種習慣,這種習慣又逐漸成為了習慣法,最終成為封建法的一部分,封臣死后其采邑自然的被后嗣所繼承。這種演變自然也是力量的博弈,騎士階層的崛起,迫切的需要土地,而騎士階層所代表的軍事力量是領主所覬覦和需要的。反之,“11、12世紀軍事形勢和法律形勢都更加有利于騎士階層,因而也更加有利于封臣,因為領主有賴于他們去裝備服役的騎士。”12世紀的晚期,英國法院以特殊令狀的形式確立下繼承人對采邑的占有權,其他地方也確立了長子繼承權。
(二)領主權利和封臣權利的互惠性
“主要是在1050年和1150年之間這一段時間,封臣對領主各種形式的人身依附轉變為各種財產義務,同時,領主對封臣各種形式的直接的經濟支配權轉換為征稅,這實質上,是給封臣留下了更多的人身自由和經濟自主。”這種轉變便是近代化的發展方向的趨勢,封建化的色彩逐漸的淡化,領主與封臣之間的關系逐漸趨向于平等。
11世紀形成了“實際占有”的概念,以刻劃那些“持有”土地或物品但并不擁有他們的人的占有權,可以將其理解為一種不完整的所有權,在不享有所有權的基礎上持續占有動產或者不動產。“實際占有”概念的產生從法律上明確了封臣所享有的絕對排他的權利,“這些朝著權利具體化方向發展的法律顯然促進了封臣的經濟自主性的增大。”“然而,對封臣日益增加的法律保護不應該解釋為是一個經濟階級對另一個經濟階級的勝利”,因為領主和封臣式相對的,領主是他人的封臣,而封臣是他人的領主。
“這些朝著增大封臣的人身自由和經濟自主性方向的發展,尤其表現在使領主——封臣關系中的互惠性因素合法化上。”而這種“契約性互惠”是基于某種身份上的,很多法學家將其類比為婚姻契約,基于婚姻關系的忠誠契約,不過這里需要注意區分效忠與忠誠,“效忠上的互惠是由這樣的實施構成的”,前文講到的通過儀式確立領主與封臣關系,而“封臣保證對領主忠誠則是另一回事,他的報酬是領主也保證對封臣的忠誠,而且領主還常常授予封臣一處采邑。”
(三)參與裁判制
上文提及,歐洲并沒有中央司法機構,因此司法權同樣在地方,“每個領主都有權主持法庭,即有權在法庭訴訟中統轄他的封臣——或統轄他的佃戶而不管他們是否是封臣。”國王或者皇帝曾嘗試回收審判權,但是經過法律訓練的官員所作出的裁決并不能被人們所認可,因為當時的審判原則規定“一個被指控犯有謀罪或應承擔某種責任的人有資格獲得他的同伴——地位相等者——的裁判”,正是基于這種原則,領主裁判的公正性才能體現,即使出現領主與封臣之間的爭議的情況下,領主既是法官又是當事人,因為一個人有權得到“與他地位相等的人的判決,而使得這樣的案件同樣能夠保證公正。”
這種領主與封臣之間的互惠性最重大的意義是對西方法律意識發展的貢獻,這種法律意識由于牢固地附屬于作為一種解決糾紛方式的對權利的正式裁判而區別于許多非西方文化的法律意識。
(四)整體性
“‘封建法律整體性這一用語指的是西方法律意識的這樣一種發展,這種發展使人們有可能也有必要把與領主——封臣關系相聯系的各種權利和義務看作是構成了一種相互結合的統一體的東西。”即封建法律逐漸的體系化,獨立完整的法律體系的產生,這種法律體系包括“效忠和忠誠、利甘替、所謂的封建負擔(服兵役或兵役免除稅、采邑繼承稅、捐稅、婚姻、監護和其他義務)、采邑的可繼承性和可轉讓性、土地轉歸領主規則、撤回忠誠、法院訴訟、以及其他相關的概念和制度。”這些規定又由各種特許狀的頒布成為成文法的淵源。
(五)發展性
封建法的發展性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封建法一旦在11、12世紀得以系統化,就迅速發展起來。”“封建法與11世紀晚期和12世紀新的教會法共有許多基本的法制特性,這些特性給處于形成階段的西方法律傳統打上了烙印”。二是封建法與教會法相比,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較之于教會法,封建法在系統性、自覺意義上的完整性、專業性和精確性這四個方面都更為遜色”“另外,封建法是世俗法,是仍然處于緩慢而痛苦的被拯救過程的塵世的法律”,因此作為調整領主——封臣關系的封建法,它不僅是與教會的宗教法相對而言的世俗法,而且還只是若干個并列的世俗法體系的一個。
作者簡介
李雪穎,單位:煙臺大學法學院,法學碩士在讀。
(作者單位:煙臺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