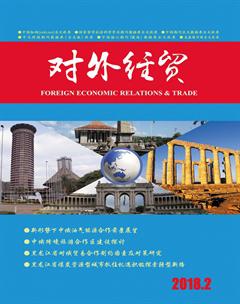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結構圖景及其演進動力
張純威 戴本忠 張啟
[摘 要]基于2003—2016年面板數據進行靜態圖景描述發現,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OFDI傾向于投向大市場國、低成本國和近鄰國。計量分析顯示,東道國實際GDP、人均國民收入及其與中國的距離是這種結構形成的決定性因素,中國實際GDP、對東道國工程承包、國際貿易及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也具有正向作用。據此判斷,隨著中國及東道國經濟增長、中國對外工程承包和對外貿易擴大及“一帶一路”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中國對沿線國家OFDI規模必將持續擴大,并更多地流向經濟增長快、低成本優勢突出國和遠距離國。因此,在發展策略方面,對外投資企業應與其他對外經濟主體密切協作,努力推動東道國經濟增長。政府應統一規劃、整體布局、協調推進各種對外經濟活動,維持、擴大和提升與各國的友好合作關系,以創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
[關鍵詞]“一帶一路”;對外直接投資;投資動機;投資環境
[中圖分類號]F125.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283(2018)02-0077-07
Abstract: By the static view describing based on the data during 2003 to 2016, it is found that China's OFDI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s mainly invested in the big market, low-cost producers and near abroad. According to the econometric analysis, the real GDP, per capita income of the host countries and the distance from China are the decisive factors for the structure, while the real GDP, overseas project contracting and trade of China and bilateral investment protection agreement exerting promoting effect.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China's OFDI to the Belt and Road will expand continuously and greater share will be invested to the countries with faster economic growth, more outstanding low-cost advantage or long distance along with economic growth and China's overseas project contracting and trade expansion and the developing of infrastructure connectivity in the area. So, as a development strategies, each oversea investment enterprise should work closely with other foreign economic entities and try to contribute to the host country economy, and governm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unified planning, overall layout and coordinated progress for all kinds of external economic activities, maintain, expand and enhance the relationship of friendly cooperation to create a goo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Keywords: the Belt and the Road; OFDI; Investment Motivation; Investment Environments
一、引言
隨著越來越多國家的參與,“一帶一路”已經成為由我國倡導的面向全球、開放的合作機制與平臺,其所涉范圍已遠超最初的地理界定。但為了便于比較和獲取統計數據,不與全球范圍相重合,本文仍沿用最初的界定,即包含亞、歐、非66個國家和地區。
自從2013年9月習近平主席提出倡議以來,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OFDI迅速扭轉相對落后狀態①,其流量占中國對全球OFDI比重由2013年的26.53%提高到2015年的34.71%。但從2016年6月起卻出現了同比下降,全年下降2.12%,2017年1-11月同比再降7.3%。這樣看來,我國對沿線國家OFDI的波動性較大。那么,這種波動主要由何種原因導致?或者說對哪些國家的投資對這種波動起了決定性作用?厘清這些問題,對于采取正確的發展策略具有重要意義。本文通過結構圖景描述和演進動力分析來加以闡釋。
通過中國知網文獻搜索發現,截至2017年12月31日,含關鍵詞“一帶一路”和“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與管理科學類期刊文獻共94篇,論證所涉范圍主要有:“一帶一路”倡議對國內不同地區對外投資的影響,對沿線國家OFDI的風險、空間布局戰略、與我國產業結構的關系,我國對沿線各子區域的OFDI等。雖然缺乏針對結構的專門研究,但部分學者關于我國對沿線各國OFDI決定和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對這一問題有所涉及。
按照主要關注因素不同,已有研究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基于投資動機展開,另一類基于投資環境展開。無論基于何種視角,在模型構建方面,為了準確界定各主要關注因素的影響,一般都會加入控制變量,因此,大部分實證模型中的解釋變量都既包括動機因素,也包括環境因素。盡管考慮的變量、依據的樣本及數據有所不同,研究結論也有所差異,但還是有些一致之處的。
在動機類因素影響方面一致性相對較為明顯:東道國市場規模(GDP)和自然資源豐度(燃料、金屬、礦石等產品出口占比或初級產品出口占比)構成正向影響②,而東道國生產成本(人均GDP或人均國民收入)構成負向影響,也就是說中國對沿線國家OFDI具有明顯的市場尋求、資源尋求和效率尋求動機,而技術尋求動機不明顯(孟慶強,2016;翟卉、徐永輝,2016;張亞斌,2016)。在環境類因素影響方面,研究結論差異較大,因為環境因素眾多,學者們考慮的范圍和偏重有所不同,代理變量的選擇也不盡相同。但關于以下三個因素的影響,研究結論相對一致:東道國基礎設施水平(航空和鐵路運輸客運量總和,百人Inter網用戶)構成正向影響(孟慶強,2016;姜慧,2017),東道國經濟開放度(外貿額與GDP之比)也構成正向影響(王軍、黃衛冬,2016;韓民春、江聰聰,2017;姜慧,2017),東道國與中國的地理距離構成負向影響(王軍、黃衛冬,2016;張亞斌,2016;韓民春、江聰聰,2017)。
總體上來看,已有研究對我國對沿線國家OFDI結構問題少有涉及,對影響OFDI因素的選擇具有一定的隨意性,往往不夠全面。本文將在綜合考慮各種影響因素的基礎上,對我國對沿線國家OFDI結構特征及其形成動力進行深度分析,并據此提出政策建議。
二、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結構圖景
OFDI是由作為投資主體的企業分散決策的集合結果。從邏輯上講,企業是在綜合考慮以下三類因素的基礎上做出決策的,一是對外投資需求,即對外投資動機;二是對外投資環境,即東道國營商條件;三是對外投資能力,即企業走出國門、直接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前兩者對OFDI結構形成直接的、決定性影響,因此,先基于這兩類因素考察我國對沿線國家OFDI的結構狀況。
(一)基于需求視角的中國對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結構圖景
對外投資需求可以用Dunning(1998)提出的四大動機來概括,即尋求自然資源、尋求市場、尋求效率和尋求戰略資產,分別以東道國資源豐度、市場規模、生產成本和技術水平對OFDI的影響作為判定依據,并分別以初級產品出口占比、實際GDP、人均國民收入和高技術產品出口占比作為代理變量。按照各國各類指標歷年均值大小,將沿線國家分為高、中、低三個陣營,分年度計算中國對每個陣營OFDI存量的總體占比,由此得到各種結構圖景③。
1.基于東道國資源豐度的投資結構。將初級產品出口占比高于60%的視為高資源國(23國),30%~60%之間的視為中等資源國(23國),低于30%的視為低資源國(18國)④。如圖1所示,2006年前我國對高資源國的投資占主導地位,并呈上升態勢,2007年后占比逐漸下降,2015年后退出主導地位,而對低資源國的投資占比則呈反向對稱的變化態勢。這表明:2006年前我國對沿線國家OFDI具有資源尋求特征,之后這一特征逐漸消失。
2.基于東道國市場規模的投資結構。將實際GDP高于1400億美元的視為大市場國(14國),400~1400億美元的視為中等市場國(14國),400億美元以下的視為小市場國(36國)。如圖2所示,我國對大市場國的投資一直占主導地位,并呈持續上升態勢,表明我國對沿線國家OFDI的市場尋求特征突出。
3.基于東道國發展水平的投資結構。參照世界銀行2015年的分組標準,將2015年人均國民收入高于12735美元的視為高收入國(19國),4125~12735美元的視為中等收入國(22國),4125美元以下的視為低收入國(25國)。如圖3所示,2006年以前我國對中等收入國的投資占主導地位,2007年起這一地位被對低收入國的投資所替代。由此來看,我國對沿線國家OFDI具有一定的效率尋求特征。但動態來看,對高收入國的投資占比總體上呈現上升態勢,這可能與我國勞動力成本不斷提高情況下某些高收入國對我國的OFDI也具有了低成本吸引力有關。
4.基于東道國技術水平的投資結構。將高技術產品出口占比高于9%的視為高技術國(17國),3%~9%的視為中等技術國(17國),低于3%的視為低技術國(30國)。如圖4所示,我國對高技術國的投資占比一直處于主導地位,且呈波動上升態勢,對中等技術國的投資占比一直很低,對低技術國的投資占比呈波動下降態勢。看起來我國對沿線國家的OFDI似乎具有一定的戰略資源尋求特征。
(二)基于環境視角的中國對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結構圖景
對我國OFDI構成影響的東道國營商環境因素眾多,這里主要考慮東道國基礎設施條件、經濟制度質量、社會安全程度及其與我國的地理距離遠近,分別以東道國綜合交通運輸能力、經濟自由度、國家風險和東道國首都與北京的距離作為代理變量⑤。與前述類似的方式計量我國對各類國家的OFDI存量占比,從而得到如下投資結構圖景。
1.基于東道國基礎設施的投資結構。將綜合運力值高于6.5的視為基礎設施發達國(21國),3~6.5的視為中等水平國(18國),低于3的視為不發達國(26國)。如圖5所示,以東道國基礎設施水平為分類依據,我國對沿線國家OFDI呈現兩個突出特征:第一,總體上兩極化,即對中等國投資很少,主要投向了不發達國和發達國;第二,動態上,對發達國和不發達國投資占比的一升一降對比態勢明顯,從而使二者在2006年發生了主導地位更替。據此來看,我國對沿線國家OFDI有一定的基礎設施偏好。
2.基于東道國經濟自由度的投資結構。將經濟自由度高于65的視為經濟制度高質量國(18國),55~65的視為中等質量國(26國),55以下的視為低質量國(20國)。如圖6所示,我國對三類國家的投資占比總體上相對均衡,但主導地位呈現由低到高的轉換過程,轉換時點分別為2007年和2015年,且對高質量國投資占比總體上升態勢相對明顯。這表明我國對沿線國家OFDI的經濟制度質量偏好雖然總體上不強,但逐漸有所顯現。
3.基于東道國風險的投資結構。將國家風險大于3.5的視為高風險國(11國),2.5~3.5的視為中風險國(23國),低于2.5的視為低風險國(31國)。圖7揭示了兩個突出特征:第一,對高風險國的投資占比總體上呈持續下降態勢,第二,對中等風險國的投資一直占據主導地位。這表明我國OFDI對沿線國家的風險并不敏感,避險意向主要表現在減少對個別高風險國的投資。
4.基于地理距離的投資結構。將距離6000公里以上視為遠距離國(33國),4100~6000公里視為中距離國(16國),4100公里以下視為近距離國(16國)。如圖8所示,對遠距離國的投資占比不斷下降,而對中、近距離國的投資占比不斷上升,其中對中距離國的投資一直處于主導地位,且近年來占比升速有加快趨向。這表明我國對沿線國家OFDI符合引力模型規則,呈現由近及遠的發展態勢。
綜合前述各種結構演變趨勢可以推斷,2016年下半年以來我國對沿線國家OFDI規模下降可能主要是因為對高資源國、中小市場國、中低收入國、低技術國、基礎設施不發達國、中等經濟自由度國、中高風險國及近距離國投資減少導致的,由此看來,我國對沿線國家OFDI目前正處于結構優化期。
三、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結構演進動力分析
前述結構圖景是基于各單項指標的分類考察,而現實中的投資結構是各種影響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并且這種結構是動態演進的。下文針對我國對沿線國家OFDI結構演進的動力展開量化分析。
(一)模型構建、樣本選擇與數據說明
首先構建包括前述投資動機和投資環境因素的面板數據模型,此為模型1。為了解決因個別國家經濟自由度EF數據缺失而使樣本量縮小問題,在模型1基礎上剔除EF,得到模型2。
現實中,影響OFDI的因素不止上述兩類,為了進行更全面和準確的分析,這里將其他影響因素作為控制變量加入模型。主要考慮以下三類因素:1.企業對外投資能力。微觀上,每個企業能力各異,宏觀上,如果說要找一個反映所有企業對外投資能力的代理變量,那自然非GDP莫屬,因為我國OFDI隨綜合國力增強而擴大的事實異常清晰。2.與OFDI密切相關的其他對外經濟活動:對外貿易和工程承包。對外工程承包與OFDI理論上應存在互補關系。對外貿易與OFDI或互補、或互替,因地、因時而異:當企業基于繞開貿易及非貿易壁壘、便利獲取原料動機而到國外投資時,二者構成互替關系;當企業基于搭建出口促進平臺、參與當地資源開發以保障國內原料供應動機而到國外投資時,二者構成互補關系。3.政策因素。這里以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及避免雙重征稅協定的簽署作為代理變量,以虛擬變量形式加入模型。理論上,協定的簽署意味著政府為OFDI創造了更為有利的環境條件,理應構成正向影響。在模型1中加入控制變量因素后得到模型3,在模型3基礎上剔除EF得到模型4。各變量的符號、含義、預期影響及數據來源如表1所示。
樣本方面,由于巴勒斯坦、不丹及東帝汶部分指標缺乏數據;2006年南斯拉夫解體塞爾維亞和黑山,為了不因此縮短面板數據時長,2006年前南斯拉夫數據列在塞爾維亞名下,不再把黑山加入樣本。以下基于2003—2016年中國對62個樣本國的直接投資及相關影響因素數據展開實證分析。
(二)實證結果分析
基于計量分析的技術需要,對規模變量指標OFDI、BRGDP、LED、CRGDP、OPC及TRD進行對數化處理,對GD進行倍數縮減處理:GD-adj=GD/1000,并進行以下檢驗:1.共線性。各模型框架下的檢驗結果(表2的2、3列所示)表明各解釋變量之間不存在系統多重共線性⑥,可以進行線性回歸分析。2.異方差。檢驗發現各模型存在異方差,直接OLS回歸估計不可用,為此本文采用穩健(robust)估計方法。3.估計方法選擇。F檢驗及LM檢驗結果(表2所示)表明各模型框架下都拒絕混合估計方法;采用自助法進行Hausman檢驗顯示:各模型下都拒絕隨機效應假設,也就是說應采用固定效應估計方法。考慮到地理距離為非時變變量,政策因素為虛擬變量,本文采用最小二乘虛擬變量(LSDV)估計方法。
分析各模型的實證結果(如表3所示),有以下發現:
1.從模型1、2的實證結果來看,四個投資動機因素中:lnBRGDP和lnLED系數的符號與理論假設相符,并具有統計顯著性,RPPE的影響不具有統計顯著性。這與前面結構圖景描述相一致,表明市場尋求和效率尋求是我國對沿線國家OFDI結構形成的主要驅動因素,而資源尋求則不是。這與張純威等(2017)關于我國對全球OFDI區位結構的分析結論基本一致。
2.就模型1、2中有關東道國環境因素影響的回歸結果來看:GD系數的符號與理論假設相符,并具有統計顯著性,CR、EF系數的符號與理論假設不符,但不具有統計顯著性、或者顯著性不高。這也與前面圖景描述基本一致,或者說并不矛盾,表明地理距離是我國OFDI結構形成的主要驅動因素,OFDI由近及遠的分布特征明顯,而東道國風險和制度質量的影響不顯著。
3.分析加入控制變量后的模型3、4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第一,除DTA外,其他控制變量系數的符號都與理論假設相符,并具有統計顯著性,其中中國GDP的影響最為突出。第二,加入控制變量后,除地理距離和技術水平外,其他東道國因素的影響都不再具有統計顯著性,而這兩個因素都呈負向影響。這表明來自中國方面的因素是主要推動力量,它們甚至覆蓋了東道國方面因素的影響。由此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釋我國對沿線國家OFDI規模自2016年下半年以來有所下降的原因:我國GDP增速2010年后持續放緩,2011年、2012年、2015年相繼跌破10%、8%、7%,2016年再降至6.7%;對沿線國家貿易額2015年同比下降11.6%,2016年再降11.9%;同時,工程承包增速也有所回落。當然,為應對人民幣貶值壓力而加強資本管制這種臨時性因素可能發揮了更大作用。
4.RHTE和IFT系數的符號與理論假設相反,且具有統計顯著性,也與圖景描述相矛盾。由于圖景描述中三類國家是以2003—2015年各指標平均值作為劃分標準的,可以說是一種基于靜態視角的總體觀察,而計量分析則綜合反映各國各種解釋變量變化對我國OFDI的影響,因此,這里的矛盾實際上反映的是靜態總體觀察與動態個體觀察的矛盾。各指標值的動態變化使一個國家不會總停留在一個層級,所以圖景描述的結構狀況可能與實際情況有所出入,這就是說,當兩種觀察結果發生矛盾時,應以動態結果為準。RHTE與lnOFDI負向相關,說明我國對沿線國家的OFDI并非為獲取東道國技術,這與多數學者的研究結論相一致。從現實情況看,沿線各國技術水平整體偏低,2003—2015年期間其總體平均的高技術產品出口占比為7.69%,遠低于全球和中國的18.41%和27.4%,區域內高于全球和中國的分別只有5個和2個國家,這使其對我國的OFDI缺乏吸引力。IFT與lnOFDI之所以負向相關,可能與我國對沿線國家的OFDI相當一部分投入到了支持東道國基礎設施建設有關,并不意味著其對東道國基礎設施有負向偏好。
四、結論、啟示與對策建議
(一)我國對沿線國家OFDI靜態來看主要投向了大市場國和低成本國,動態來看與東道國經濟規模和發展水平分別呈正、負相關關系,從而使其市場尋求和效率尋求驅動特征顯著。啟示:我國對沿線國家OFDI規模上具有巨大增長潛力,結構上將傾向于投向那些經濟增長快、相對于我國低成本優勢明顯的國家。因為,第一,目前沿線國家總體人均GDP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34%,而中國人均GDP相對于多數國家更快的上升勢頭仍將保持相當長一段時間,這使得區內多數國家相對于中國的低成本優勢得以保持。第二,沿線多數國家(62個)正處于工業化時期,經濟增速相對較高,2000—2015年平均經濟增速高于全球近2個百分點。低起點、高增長使“一帶一路”成為一個充滿活力、從而對我國OFDI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地區。對策建議:我國對外投資企業在追求盈利及其他微觀目標的同時,要努力對沿線國家經濟增長有所貢獻,由此使OFDI形成自加助力式的良性發展。
(二)地理距離是我國對沿線國家OFDI結構形成的決定性因素,它與OFDI之間顯著的負向相關性清晰揭示了我國OFDI由近及遠的分布狀態和發展路徑。這與企業基于降低交通費用等成本角度考慮的自然選擇有關,也與我國注重搞好近鄰關系所創造的良好政治及外交環境有關⑦。啟示:隨著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推進,交通成本將不斷降低,從而使地理距離的負向影響趨于弱化,以中近距離國為主導的OFDI結構將逐漸改變。
(三)我國對沿線國家OFDI與東道國經濟自由度及國家風險相關性不高,但并不意味著其對東道國經濟制度和社會穩定不敏感,可能是因為這些因素的影響被我國與東道國建立的良好外交關系和經濟合作關系所覆蓋,基于這種關系,東道國為我國投資提供了特別保護和便利。截至2016年,我國與之建立各種伙伴關系的近80個國家中41個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而且,越是周邊國家,伙伴關系層次越高,對伙伴國的OFDI占對所有沿線國家的比率由2003年的64.74%提高到了2015年的96.79%。對策建議:與沿線更多國家簽訂友好關系條約,建立、維持和提升伙伴關系,為我國OFDI向更大區域、以更大規模拓展創造良好國際環境。
(四)伴隨國力增強的企業對外投資能力提升是中國對沿線各國OFDI增長的首要推動力。啟示:隨著國力的進一步增強,中國對沿線國家OFDI的總體規模必將進一步擴大,從而持續助力于“一帶一路”建設。
(五)中國對沿線國家的工程承包和國際貿易與OFDI之間存在顯著的相互促進關系。對策建議:微觀上,各對外經濟主體應密切溝通、相互支持、合作開拓、共同發展;宏觀上,政府對我國在沿線國家的各種經濟活動要進行統一規劃、整體布局、協調推進。
(六)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對我國在沿線國家的OFDI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目前我國已與域內近50個國家簽訂了該項協定,建議盡快根據條件成熟情況與沒有簽訂的國家達成協定,并保持協定的持續性和擴大保護范圍。
[注釋]
① 與中國對全球OFDI同比增速相比,中國對“一帶一路”OFDI增速2013年低27.42個百分點,2014年低6.75個百分點,2015年則高出20.29個百分點。
② 括號中為該解釋變量的具體統計指標。
③ 圖中數據依據各分類指標及分國別的OFDI數據計算得到,相關數據來源見表1。
④ 個別國家因缺乏相關數據而未列入考察范圍。在其他結構考察中作類似處理。
⑤ 各國綜合交通運輸能力是對海、陸、空三方面運力的加總平均。三者分別以人均集裝箱吞吐量(CPT)、人均鐵路里程(RL)和人均航空運量(AT)為代理變量。三者平均值的計算步驟如下:首先計算2003—2015年三個變量所有國家的平均值CPT、RL和AT;然后以AT為基準進行統一量綱處理:RL=RLit/(RL/AT)CPTit=CPTit/(CPT/AT);最后計算各國綜合運力:IFTit=(RLit+CPTit+ATit)/3。各國國家風險基于世界銀行全球治理指標體系(WGI)的數據計算。該指標體系包含6個子指標,各子指標取值范圍為(-2.5~2.5)。為消除負值現象,進行以下變換:各子指標變換值=5-(指標值+2.5),變換值越高,說明風險越高。用6個子指標變換值的均值計量一國風險。
⑥計量檢驗的經驗法則是,只要最大方差膨脹因子VIFmax不大于10,就說明不存在系統多重共線性。
⑦目前我國與陸上接壤的14個國家中的11個簽訂有睦鄰友好合作、友好合作互助、友好互助、和平友好、友好和互不侵犯等各種形式的睦鄰友好條約。
[參考文獻]
[1]韓民春,江聰聰. 政治風險、文化距離和雙邊關系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基于“一帶一路”沿線主要國家的研究[J].貴州財經大學學報,2017 (2).
[2]姜慧.東道國基礎設施水平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基于“一帶一路”國家的系統GMM研究[J].對外經貿, 2017 (3).
[3]孟慶強.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動機的實證研究[J].工業經濟論壇,2016(2).
[4]王軍,黃衛冬.東道國制度質量對中國OFDI的影響[J].產業經濟評論, 2016(6).
[5]翟卉, 徐永輝.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直接投資影響因素分析——基于東道國角度的實證研究[J].投資與合作,2016(9).
[6]張純威,戴本忠,姚捷.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結構特點及其形成動因[J]. 金融經濟學研究, 2017(2).
[7]張亞斌.“一帶一路”投資便利化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選擇——基于跨國面板數據及投資引力模型的實證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16(9).
[8]Dunning,J.H.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Geograph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1998,26(1):47-69.
(責任編輯:張彤彤 梁宏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