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發現與中國女性的自我畫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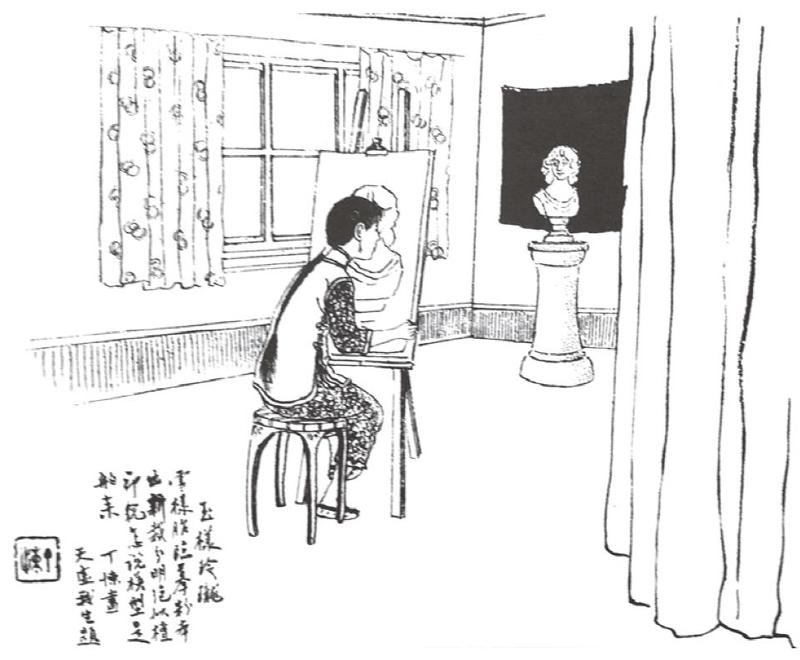
一
歐洲的個人主義誕生于公元一五00年前后。這個時期,鏡子的發明使人們第一次從鏡中看到自己清晰的面貌。之后,鏡子成為歐洲世界重要的文化象征物,從一種“器物”發展為一種“概念”。它讓人們了解自己,劃出自己與他人的界限,構造關于自我與他者的種種喻說,人的自我感由此確立。鏡子的使用讓人們認識自己的同時也推動了藝術表達的進程,自畫像正受惠于這一發明。對著鏡子,藝術家不僅摹寫從鏡中看到的那個自己,更由之而內省自身。數百年間,自畫像表達由外而內,由表及里,不斷深化,構成藝術表達的歷史鏈條。在歐洲,自畫像的出現與個人主義的誕生幾乎同步,鏡子是催生二者的媒介。一五00年以后,白畫像成了歐洲繪畫藝術家自然而然的表達樣式。文藝復興時期流行的自畫像理論是“每位畫家畫的都是自己”,一如幾百年后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作家郁達夫所言:“所有的文學都是作家的自敘傳。”個人主義熱潮興起之后,無論在歐洲還是在中國,都有過一個強調藝術是自傳的時期。蒙田在為自己《隨筆》的自傳性做辯護時說:“一日我在巴勒迪克看到勒內王將自己的自畫像贈予弗朗西斯二世國王作為留念。就像他用畫筆描繪自己一樣,我用文筆描繪自己又有何不可?”(蒙田《隨筆》前言)于其時,自我摹寫幾乎成為不同種類的藝術共同采用的方式。在繪畫領域,文藝復興時期伊始至其后幾百年間,自畫像一直引領風騷,不同時期的大師們都深諳此道,從丟勒到倫勃朗,從戈雅到庫爾貝,從塞尚、高更到凡·高、蒙克,從馬蒂斯到畢加索到達利,不同歷史階段的大師們都在自己獨一無二的藝術創造中留下了以自畫像為構形樣式的代表作。他們以“我”為形象展開各種思想演述和藝術實驗,手法各異,觀念多元,但殊途同歸,顯示了對以“我”為中心的人類精神本源的共同興趣。
與西文individual相一致的現代意義上的“個人”一詞,最早出現于中文世界是一八九八年梁啟超在流亡日本期間翻譯的日人柴四郎小說《佳人奇遇》:“……然法人輕佻,競功名,喋喋于個人自由。內閣頗行更迭,國是動搖。”此為“個人”一詞在中文中的首次出現。這個“個人”有權利主體內涵,可以喋喋于“自由”。金觀濤、劉青峰據“數據庫”檢索還發現,一九0一年以前,極少有人使用“個人”一詞,一九0二年突然由前一年的二十二次增加到一百一十次。而且“個人”明確與西方individual相對應的情況,發生于一九00至一九0二年間,表明個人觀念在一九0二年開始普及(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之后,關于“權利”“個人”的近代啟蒙言論迅速鋪開,并隨著思想啟蒙的深入獲得更加充分的闡述。
于“個人”確立而言,言論上的啟蒙仍是一種紙上談兵。它必須借助相關的工具和途徑,才能將觀念落到實處,變成事實,就像歐洲人借助鏡子而發現個人一樣。在中國,近代啟蒙最有效的辦法是興辦新式教育。新式教育不僅從“道”上更從“術”上教人自立。一九0五年隨著科舉制度的廢除,現代學堂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新文化與新技術攜手,構成現代教育的兩駕馬車。與西方的白畫像盛行激發個人主義熱潮類似,二十世紀初,在新式學堂中占據一席之位的圖畫課于近代啟蒙實施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二十世紀頭十年,圖畫課已經是新式學堂的常規課程。光緒二十八年(一九0二),由光緒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其中預備科課程分“政”“藝”兩科,“藝”中“圖畫”列第九;光緒三十二年(一九0六)頒布《通行各省優級師范選課章程》,有“圖畫課”的規定;光緒三十三年(一九0七)頒布《女子師范學堂章程》有“圖畫課”規定;宣統元年(一九0九)頒布《檢定小學堂章程》,規定了圖畫教員的考試科目。可見“圖畫課”在新學中的分量和位置。其時全國各地開辦的女子學校,更是以圖畫、刺繡、手工為主科。如一九0三年創辦的上海城東女學、湖南民立第一女學,一九0四年創辦的杭州公立女學校、上海啟明女學校,一九0六年創辦的天津北洋女師范學堂等,莫不如此。早期的女子教育,基本在女學堂和師范學堂兩條軌道上進行,圖畫課是女子教育的必修課,不僅教給女學生繪畫技能,更推動了女性個人主義啟蒙的展開。
二
作為一種“西技”,圖畫課在世紀初的新學中舉足輕重。沿著晚清經世致用的實學潮流,二十世紀頭十多年,西洋圖畫以寫生為方式的寫實路徑備受推崇。兩代文化啟蒙者,從康有為、梁啟超到陳獨秀、呂徵,都倡導美術的寫實主義。在后者那里,“寫實”不僅是一種技術,更是一種新文化。“畫家必須用寫實主義,才能夠發揮自己的天才,畫自己的畫,不落古人窠臼。”(陳獨秀:《美術革命——致呂徵》,《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他將寫實與發揮“天才”、標榜自我獨立性相提并論,強調“寫實”的精神內涵。隨著新文化運動的到來,寫實主義從原來的追求繪畫逼真效果,提升到具有“科學與民主”精神的高度來認識。寫生是講究科學性的行為,自我摹寫和自我表達是民主的表現。在這種背景下,人物寫生、透視素描、明暗造型,都具有文化性、精神性含義。至此,人們對繪畫尤其是肖像畫的理解,進入一個新階段。肖像畫與個人主義時代的自我張揚相呼應,拓展出一片新天地來。美術教育既是一門人文教育,又是一門技術性相當強的課程,一種用畫面摹寫景觀、摹寫人事萬物的技能。這種技能的掌握讓人的表達如虎添翼,技術促進了覺醒。在技術的協助下,自我摹寫變得輕而易舉,自畫像也開始流行。
一九0五年開始接受中國留學生的日本東京美術學校設有一項常規性體例:“西洋畫科的畢業生在畢業時都應該給母校留下一幅自畫像。”(劉曉路:《檔案中的青春像:李叔同與東京美術學校》)日后追尋該校早年中國留學生行蹤的學者,就以保存于該校檔案館的畢業生自畫像為線索,確認這些留學生是否完成其學業等情況。自畫像逐漸成為研習西洋畫學生常規的訓練方式,甚至是早年學生進入美術院校的必考科目。其對自我形神準確勾勒的難度,考量著每位習畫者的功底和實力。這種訓練方式讓繪畫者獲得表現技巧的同時,更激發其自我感,催生其自我意識。它引導畫者深入地觀察自己,敏銳地捕捉自己瞬間的形神,并加以心領神會的摹寫。自畫像是以繪畫方式對“我是誰”“我怎么樣”“我為何”等進行敘述和表現,是繪畫的自敘傳。這一自我形象的摹寫過程與其說是寫真性的仿寫,不如說是創造性的表現,帶有個人主觀的情緒色彩。從某種意義上說,自畫像的盛行標志著個人主義時代的到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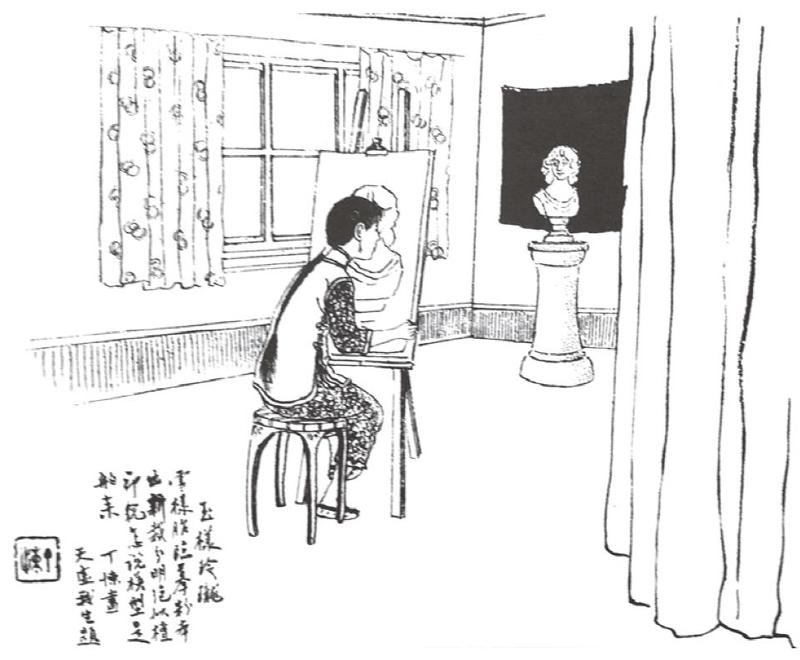
民國初年進入學校主修圖畫、手工課程的女子,也學習這種技能。一九一六年上海國學書室出版丁悚的《上海時裝百美圖詠》,仿照當年吳友如的《海上百艷圖》,記錄其時滬上女性生活風情的白描畫作。其中有一幅題為《自家寫影》,畫一女子站在畫架前,手持畫筆和調色板,凝視墻上“自家寫影”的畫作,那是一幅全身自畫像。邊上還有一幅半身肖像。畫中題跋寫道:“自家寫影最傳神,小立亭亭識愈真,若與檀奴比風度,半身終不及全身。”可見早期女性習畫,已出現白畫像。自家寫影最傳神,最能傳達“我”的精神氣息,也將“我”亭亭玉立的風姿顯現。一九一八年丁悚又出版《百美圖外集》,書中有一畫,畫一女子在家里對著石膏像寫生。畫中題跋寫道:“玉樣玲瓏雪樣胎,臨摹粉本出新裁,分明絕似檀郎貌,怎說模型是舶來。”臨摹石膏像,凝視久之,覺得石像分明就是自己的如意郎君,道出了肖像臨摹凝神移情的特點。還有張宇光的一幅,畫一女子對著女模特寫生。上述三畫透出一些信息:早期女子習畫,或寫生,或臨摹,均熱衷于肖像或白畫像。
這種熱衷,于一九二九年民國教育部在上海舉辦的第一次全國美術展覽會上得到盡致顯現。從清末民初的興辦女學,到一九二0年前后國內美術專科學校開始招收女生,到一九二九年的首屆全國美展,中間經歷十多年的時間。一九二九年首次全國展覽會是晚近十多年女性圖畫教育的一次檢驗,是其總實績的一次展示。有三十多位女子的近百件作品參展,其中,研習西畫的女作者,潘玉良、蔡威廉、方君璧、方勻、周麗華、翁元春、唐蘊玉、梁雪清等,多數以肖像或白畫像參展,顯示了早期女性繪畫的特色。這種現象既與這個時期女子接受西畫科班教育的訓練路徑有關,也與整個文化環境以及她們的個人心理成長有關。
近百年間,中國女性藝術千變萬化,唯一不變的是女性藝術或多或少帶有自畫像的含義和意味。于表達而言,自畫像的內傾性、自戀性、自傳性與中國女性在漫長的歷史格局中形成的心理特征——對自我世界的守護,與外部世界的顧盼——有契合之處。伍爾夫曾說:“對于別人我們素昧平生,對于自己的相貌特征,我們簡直太熟悉了。那就開始吧。可是,剛一動手,那筆可就從我們指頭縫里掉了下來——原來這是一件極難、極奧妙、人力不能勝任的事情。”(弗吉尼亞·伍爾夫:《蒙田》)這段話恰好道出“五四”前后中國女性的情況:對自己的熟悉使自我摹寫成為她們熱衷采用的方式,而現代繪畫技法的掌握,又使她們在某種程度上有可能勝任這種表達。
三
拙著《自我畫像:女性藝術在中國(1920-2010)》(以下簡稱《自我畫像》)以“自我畫像”為主題詞和問題線索,對二十世紀中國女性美術史展開考察和解讀。具體以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接受現代美術科班教育的女性藝術創作起步為時間上限,以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的女性藝術活動為時問下限,橫跨近一個世紀。所謂“自我畫像”,既指狹義的——畫家以自己為描繪對象所作的自畫像、自塑像,也指廣義的——蘊含藝術家自我形象或自我敘述意向的繪畫、雕塑作品,其形象并不局限于畫者本人。在這里,“自我畫像”與其說強調某種畫像的類型,不如說強調“自畫”的屬性——自我摹寫、自我分析、自我命名、自我身份確立的含義和方式。與歐洲的白畫像歷程相比較,二十世紀中國女性白畫像的步履雖更為緊湊,其過程卻頗為相似。畫像者經歷了驚喜地發現自己、狂熱地摹寫自己、強制性地隱匿自己到解凍后多元地敘述自己等幾個階段。這種階段性變化與社會演進、思潮激蕩息息相關。
二十世紀頭二十年,是中國現代女性藝術起步的階段。女學興起,西畫素描、寫生技法的引入學堂,嚴格的術科訓練使女性的自我摹寫成為可能。一九二0年之后,美術專科學校招收女生,科班教育促使女性繪畫技能迅速成熟。伴隨西洋繪畫技法的引進而開始流行的自畫像,催生了這一代女性的自我感、身份質詢意識及自我表達愿望,她們經由自畫像而確認自己,建立自我人格。三十年代,女性自我畫像迎來第一個創作高峰期,從事西畫創作的女性作者多數以作女性肖像或自畫像為擅長,呈現女性族群自我表達的沖動及其表達方式的大同小異。這股熱潮一直持續至三十年代末抗日戰爭來臨。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戰爭背景下的中國政治社會區域形成三大塊:國統區、淪陷區和解放區。特殊時期,女性自我摹寫創作趨于沉寂,以抗日救亡為主題的女性形象,漸漸抽離女性自我摹寫內涵,而奔赴敘述主體泛化的宣傳性的民族救亡題旨。此時期,延安解放區的美術創作,女性作者幾乎缺席,畫作上女性形象(女工農兵)的主體虛擬性及政治寓意,幾乎驅除女性自我摹寫的可能性。一九四九年之后,新中國美術致力于建立自己的一套樣式。五十至七十年代,“鐵姑娘”形象風行。在這種局面中,女性藝術家借助“鐵姑娘”著裝隱晦而執著地表現自己,呈現了大時代與小個人的復雜糾纏。八十年代解凍之后,“個人”終于又回到畫面上。但一開始,那些“自我”形象依然有工農兵著裝。九十年代才是一個真正的女性自覺的年代:一批新時期后進人大學的女性成長起來,她們同樣熱衷于自我畫像,但內涵多元,技法各異,注重畫像的象征性和精神涵義,至此自我畫像進入一個新階段。一九九五年九月世界婦女大會在中國召開,將女性藝術的自我表達熱潮推向高峰。
從某種意義上說,“自我畫像”構成二十世紀中國女性藝術的一種基本樣式,伴隨著女性藝術從誕生、走向成熟到臻于完善的全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女性的人格身心與藝術表達能力同生共長,經歷了不同的階段性發展,從追求形貌的酷肖到注重精神的寫真,從專注于與自我的對話到摹寫自我心靈受創的情形,顯示了藝術家與“自我”不斷深化的關系。將近百年的女性畫像串聯起來,構成的就是一組系統的歷史視覺圖像資料,一種關于人性的藝術表達。每一件作品都是畫像者生命律動的瞬間定格,是特定歷史情境中的一個鮮活細胞。它既是個體的、精神性的,又是時代的、記錄性的,后者將歷史與個人相遇的情形和盤托出,形象細節之中隱含著歷史的表情。在自傳藝術盛行的年代,人們更關注傳主的自我表達,留意其自我形象、生命足跡被保存的情況,誠如沈從文言及文學自我書寫的情形:“唯轉化為文字,為形象,為音符,為節奏,可望將生命某一種形式,某一種狀態,凝固下來,形成生命另外一種存在和延續,通過長長的時間,通過遙遠的空間,讓另外一時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無有阻隔。”(沈從文:《抽象的抒情》)殊不知,自畫像在留住個體生命的同時,也將畫像者的生存顯現為一個時代的證據。
從“自我畫像”角度考察中國女性藝術的百年歷史,是提綱挈領、有效地觸及女性自我成長、人格確立、身份認同諸問題的一個角度。墨西哥女藝術家弗里達·卡蘿說:“我畫我自己……因為我是我最熟知的主題。”任何看過弗里達自畫像的人,都會為畫中那個孤獨的、痛苦的、自戀的女子所震懾。了解弗里達生平的人都知道,對于弗里達而言,自畫像是她生命的救贖,是她痛苦的出口——那不只是一般意義上的藝術創作,更是與生命息息相關的精神行為。這種情形與“五四”時期在個人主義熱潮感召下問世并走向成熟的中國女性藝術,有相似之處。或者說,二十世紀的中國女藝術家,不少人是從自我畫像獲得生命伸展的途徑和情感宣泄的出口,以此建立自己的生命樣式的。
[《自我畫像:女性藝術在中國(1920-2010)》,姚玳玫著,商務印書館二0一八年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