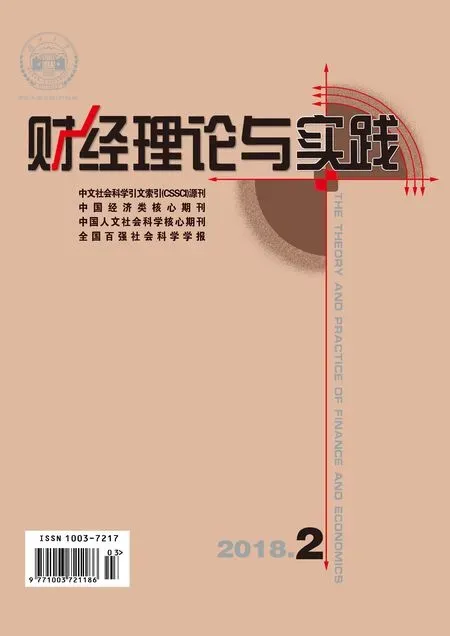能力資本對代際收入彈性的影響
李 軍,曹 儀,2
(1.湖南師范大學 商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2.湖南省教育科學研究院,湖南 長沙 410005)*
一、引 言
“富二代”“窮二代”與“官二代”等網絡熱點名詞受到熱捧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代際收入轉移使身份固化的社會現實。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基尼系數來看,2012-2016年分別為:0.474、0.473、0.469、0.462、0.465。可以看出,基尼系數一直維持在相對高位,收入不平等問題依然很突出。出身不同和代際收入轉移是否加劇了收入差距的不平等?這是學者們關注的熱點課題。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經濟學者開始探討代際收入彈性,通過對代際收入彈性的測度,可以量化父母和子女成年以后的經濟關系,反映出未來收入不平等的趨勢。早期Francis Galton通過回歸來測度兩代人之間的不同特征,社會學家們也陸續(xù)對代際關系進行測度,其中Becker 和Tomes(1979)通過計算兩代人之間的經濟關系定義了代際收入彈性[1]。代際收入彈性測量的是父母和子女在成年以后的收入關系。Mercan和Barlin(2016)認為,代際收入彈性可以為人們闡明一個低收入家庭要提升到社會均值需要經過多少代的時間[2]。因此,代際收入彈性更加側重反映社會收入公平的未來變化趨勢。基于此種假設,研究者認為基尼系數與代際收入彈性之間存在正相關[3],收入公平與收入機會公平之間也存在正相關。然而,上一代人的經濟不公平通常也會傳遞到年輕一代[4],為了尋求更加完善的制度來幫助社會的貧困階層改善生活,需要充分理解這種代際傳遞的內涵。
Becker和Tomes(1979)從家庭經濟學和人力資本投資理論的角度,提出父輩將一部分用于自身的消費對子女進行人力資本的投資,繼而從子女成年后所獲得的經濟收入中收益。基于此理論框架,Becker和Tomes構建了代際收入流動的理論模型,這一模型在國內外經濟學研究領域一直沿用至今。
家庭之間代際收入的聯系可以表示為一個簡單的回歸模型:
Ychild=α+β×Yfather+φ×A+ε
(1)
其中,Ychild和Yfather代表了子女與父親永久性收入的對數形式,變量A代表了模型相關的其他控制變量,比如子女的年齡等變量。選取合適的控制變量可以有效的降低生命周期造成的測度偏誤。β則代表了代際收入彈性。β值越低,父親和子女之間的收入流動性就越高。
理論模型假定兩端的收入變量都必須是永久性收入。想要獲取個體的永久性收入,必須先獲得個體一生的收入數據,然而,由于數據的缺失,國外早期的研究學者在計算代際收入彈性時通常采用單年收入來作為父親、子女永久性收入的估計值。Mazumder(2005)利用單年收入估計出美國代際收入彈性系數為0.2。在近年的研究中,Mazumder(2015)利用40歲左右父母15年的收入均值,計算出美國的代際收入彈性高于0.6。
由于個體的終身收入服從一個倒U型的分布,因此,收入觀測值所處于的生命周期會對彈性的估計產生影響。當父親收入的觀測值處于收入的波峰時,就會得到一個下偏的估計。Grawe(2006)認為哪怕對同一個國家使用相同的數據進行估計,由于選取的樣本年齡段不同,估計值也會產生偏差。同樣,Haider and Solon采用子女早年收入的觀測值進行估計也同樣對估計造成影響。生命周期的偏誤會產生一個下偏的代際收入彈性估計值。因此研究者通常尋找合適的工具變量來修正這種向下的偏誤。
一些國內學者對中國代際收入彈性做出了估計。何石軍等計算了2000、2004、2006、2009年中國的代際收入彈性分別為0.66、0.49、0.35、0.46[5]。韓軍輝利用滯后(前期)數據作為當期數據的工具變量計算了中國代際收入彈性為0.446[6]。丁亭亭(2016)利用Jorgenson-Fraumeni未來終生收入法和工具變量法得出代際收入彈性的區(qū)間估計,計算出中國1988、1995、2002、2007年代際收入彈性分別大于0.262、0.483、(0.466, 0.544)以及(0.483, 0.554)[7]。雖然研究學者采用不同的估計方法會對結果產生不同的偏誤,但是都一致反映出我國目前處于低流動性社會,經濟狀況優(yōu)秀的家庭會將這種優(yōu)勢傳遞到下一代。
國內外學者對代際收入流動的傳遞機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父輩經濟收入對子輩經濟收入的直接傳遞;二是從人力資本、社會資本、財富資本等方面探討代際收入的傳遞機制;三是通過個體能力、基因遺傳等不可測因素研究影響社會的代際收入流動。
人力資本是體現在勞動者身上的一種資本類型,它涵蓋了勞動者的知識程度、技術水平、工作能力以及健康狀況。陳杰、蘇群(2016)認為以受教育年限為代表的人力資本投資在我國代際收入流動之間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人力資本的解釋力為17%[8]。通常,父母的人力資本對子女經濟收入的影響主要通過兩種途徑:一種是高人力資本的父母通過其對社會經濟市場的認識直接幫助子女獲得職場的收入優(yōu)勢[9];另一種是父母通過言傳身教或者耳濡目染,間接的提高了子女的人力資本,從而幫助子女的經濟收入得到顯著的提升[10]。
社會資本是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的一種表現形式,以社交網絡為中心,基于相互幫助和相互合作來產生共同利益。Bian (1994)指出在中國以家人和親戚為主的天然強聯系極大的影響了個人的就業(yè)。這種強聯系與弱聯系構成的社會網絡對個人就業(yè)產生了重要影響,進而對代際收入產生影響[11]。邸玉娜(2014)認為父親的工作會通過影響子女的個體特征對子女的經濟收入產生間接的影響,機會不均等是子女收入不均等的顯著影響因素[12]。子女可以通過父母的社會資源,謀求更多的就業(yè)機會,從而對子女的經濟收入帶來顯著的影響。
父輩的財富資本會對子女收入水平產生重要影響。陳琳和袁志剛(2012)認為,財富資本能為所有者提供經濟收益的資源或者權益,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增長,資產泡沫使得家庭的財富資本對子女收入產生了重要影響[13]。一方面,富家子弟會比寒門子弟擁有獲得更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家庭的財富水平越高,子女在進入職場時可選擇的權利也更多,獲取財富的途徑也更廣。
周興、張鵬(2015)認為代際間的職業(yè)流動是影響代際收入彈性的重要原因。雖然子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會帶來子女職業(yè)的向上流動,但是兩代人之間的職業(yè)繼承性會較高的阻礙社會的代際流動[14]。譚遠發(fā)(2015)認為政治資本是影響子女工資收入的顯著因素,在控制家庭規(guī)模和父親受教育年限之后,擁有“官二代”背景的子女受教育年限要顯著高于“非官二代”,父母的政治資本幫助子女將人力資本更加有效的轉化成為職業(yè)優(yōu)勢,獲得收入的顯著增長[15]。
一些學者在建立代際收入彈性的計量模型時,通常使用可觀測的外部變量。也有些學者認為教育程度、個人特征等外部變量已經不足以說明個體之間的收入差距。張曉寧(2017)認為能力貧困(包括生產經營能力、就業(yè)能力、知識與技術的獲取能力以及社會參與能力)是導致勞動者收入貧困的重要原因[16]。謝凱彥(2015)通過構建空間計量模型,從社交能力的角度證明了能力對個體經濟收入的影響[17]。
事實上,所有這些可觀測的變量都是個體能力的外部表現形式,在估計代際收入彈性時,忽略勞動者的能力將會帶來極大的偏誤。然而包含遺傳因素在內的個體能力不可度量,在前期的研究過程當中,通常將個人能力歸納到誤差項ε中,并將這種由于忽略了個體能力而導致的估計偏差定義為“能力偏差”。
本文結合前人的相關研究成果,對勞動者的能力資本進行重新定義,通過項目反應理論,將勞動者的外部可測變量轉換為勞動者的能力資本。利用微觀數據庫對能力資本在收入的代際傳遞之間產生的中介效應進行實證分析,從能力資本的角度探索代際收入的傳遞機制,尋求合適的解決方案[18]。
二、理論假設與實證設計
孔繁軍(2005)針對企業(yè)在生產中的獲利能力提出了能力資本的概念,認為企業(yè)的能力資本是一切利潤形成的本源,并認為能力不僅具備自身的價值,同時也擁有著價值增值的功能,能力的價值在經濟勞動結束以后得以體現[19]。李曉曼、曾湘泉(2012)將個體的能力引入新人力資本理論的范疇,認為教育水平所代表的傳統人力資本往往會帶來人力資本效應的有偏估計[20]。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對能力資本進行了新的界定,認為能力資本是勞動者賦予并所有的,在獲取人力資本、財富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勞動過程中得到體現,是勞動者學習能力、工作能力和社交能力共同作用的結果,并最終幫助勞動者創(chuàng)造經濟價值的資本。
因此,我們可以得到假設1:
H1:子女的能力資本將對子女的經濟收入產生顯著的影響。
人的一生中包含著各種能力形成的階段,Gluckman和Hanson(2005)通過探討環(huán)境與基因的相互影響,發(fā)現個體的能力可以通過后天的努力而得到提升,遺傳因素將受到環(huán)境的作用。勞動者的能力資本將隨著家庭培養(yǎng)和教育投入而得到較大的改變,經濟收入高的家庭在早期子女能力發(fā)展的關鍵期可以提供更好的環(huán)境,進行更高質量的能力培養(yǎng)。
因此,我們可以得到假設2:
H2:父輩的經濟收入將對子女的能力資本產生顯著的影響。
根據Spence(1973)提出的信號理論,信號理論認為教育水平并不能產生直接的經濟收益,而是作為勞動者學習能力的強信號獲得市場的認可,市場依照勞動者的價值支付相應的報酬。而父母和家庭在子女能力資本的培養(yǎng)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經濟收入高的家庭可以為子女提供質量更好的教育,增加子女獲得高水平教育的概率,培養(yǎng)子女的學習能力,同時在父母保證經濟來源的前提下,子女可以通過更多的社會實踐來鍛煉自身的工作能力,獲取更高的社交能力。
因此,我們可以得到假設3a、假設3b、假設3c:
H3a:父輩的經濟收入通過影響子女的社交能力提高子女的經濟收入;
H3b:父輩的經濟收入通過影響子女的學習能力提高子女的經濟收入;
H3c:父輩的經濟收入通過影響子女的工作能力提高子女的經濟收入。
美國心理測量學家Lord(1952)針對測驗與態(tài)度的關系提出了項目反應理論。項目反應理論也稱為潛在特質理論,認為受訪者在問卷項目上的反應同受訪者的潛在能力之間有特殊的關系,根據受訪者回答問題的情況,通過構建反應模型推測受訪者的潛在能力。本文采用目前廣泛應用于心理測量領域的logistic模型,根據受訪者在有關社會資本、人力資本、財富資本問卷項目上的回答情況,計算出受訪者的社交能力資本、學習能力資本、工作能力資本和綜合能力資本。
本文采用的計量模型為:
Ychild=α+β×Yfather+φ×abilitychild+ε
(2)
其中,Ychild為孩子收入的對數,Yfather為父親收入的對數,abilitychild為孩子的能力資本。對代際收入彈性進行估計時,為了能更加直接的顯示勞動者的能力資本對經濟收入的影響,abilitychild為涵蓋了子女社交能力、學習能力、工作能力的綜合能力資本。
利用短期收入作為長期永久性收入替代值的模型被稱為經典變量誤差(CEV)模型。經典變量誤差模型假設臨時收入與永久性收入的關系如下:
yit=yi+vit
(3)
上式被稱為收入的動態(tài)方程,yit表示個體i在t時期的收入對數;yt為永久性收入的對數,vit表示yit對yi的測量誤差,被假設與永久性收入無關,是個白噪聲過程,斜率恒為1。在CEV的模型假設下有:

(4)

假設孩子真實的永久性收入方程為:
Ychild=α+β1×Yfather+β2×Ei+ε
(5)
其中Ei為父親的受教育水平,λ為永久性收入和受教育水平的相關系數,則:
(6)
由此可見,IV估計會產生向上的偏誤,因此IV估計值可以作為代際收入彈性系數的估計上限。因而,最小二乘法和IV估計法為代際收入彈性的估計提供了上下限。
三、實證分析
(一)數據來源與計量模型
本文使用數據全部來自北京大學“985”項目資助、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執(zhí)行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CFPS數據的調查對象為中國25個省(市、自治區(qū))滿足項目訪問條件的家庭和家庭中滿足訪問條件的家庭成員,目標樣本規(guī)模為16000戶,于2010年展開正式的訪問。CFPS采用內隱分層的方法抽取多階段等概率樣本,綜合考慮到了中國社會的背景差異,本文采用了CFPS調查2010、2012、2014年的數據,篩選刪除了未滿18歲、未參加工作的樣本,如果一個家庭有兩個以上的孩子,本文只選取第一個孩子的數據,產生了300到400對家庭樣本。由于在三年的調查中,有新的家庭加入,舊的家庭退出,因此挑選出連續(xù)三次參加了訪問的家庭,共150對配對數據。以2010年、2012年、2014年父親和子女收入的三年平均值作為永久性收入的替代值,以修正單年數據造成的向下偏誤。
社會資本的衡量較為復雜,一般使用政治身份、單位性質、職業(yè)和行業(yè)等來衡量。本文選取衡量社會資本的變量為:是否具備行政管理職務、有無直接下屬、在工作中管理下屬人數、是否入黨、工作單位性質、收入在本地的地位、個人社會地位、家庭社會地位等變量。
人力資本一般包括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健康、培訓和遷移,在以往的研究中,通常使用教育和健康來衡量人力資本。選取衡量人力資本的變量為:工作中是否使用外語、工作中是否使用計算機、使用互聯網學習的頻次,是否經常讀書、閱讀量、教育層次、健康狀況、身體是否不適、是否有慢性病、過去一年是否住院、是否經常鍛煉身體等變量。
財富資本以家庭財產衡量,包括房產現值、金融資產等。本文選取衡量財富資本的變量為:常住房當前市場價、除住房外還有幾套住房,其他房產市值、現金存款總額、金融產品總價、收入總額等變量。
此外,本文將社會資本、人力資本與財富資本合并為受訪者的綜合資本。
通過前文介紹的項目反映理論模型,利用受訪者在上述項目上的作答情況,分別計算出受訪者的社交能力資本、學習能力資本、工作能力資本與綜合能力資本。
(二)基于能力資本的代際收入彈性估計
采用父親社交能力資本、學習能力資本和工作能力資本為工具變量,并對工具變量進行弱工具變量檢驗,計算得出偏R2為0.2126,Minimum eigenvalue statistic值為12.6871(>10),因此認為所選工具變量并非弱工具變量。

表1 父親的社交能力資本、學習能力資本和工作能力資本的弱工具變量檢驗
進一步對工具變量進行過度識別檢驗,過度識別檢驗的原假設為:所有工具變量都為外生變量。檢驗統計量Sargan值為2.41886(P=0.2984),接受原假設,因此認為所有工具變量均為外生變量。驗證得知,父輩的社交能力資本、學習能力資本和工作能力資本可以作為父輩經濟收入的強工具變量。
當忽略子女的能力資本,只對父輩的對數收入均值(Income_father)、子女的對數收入均值(Income_child)進行建模時,計算出R2為0.2612,代際收入彈性為0.71,模型認為代際之間的流動相對固化。

表2 無控制變量的代際收入彈性系數IV估計
由于不同能力資本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影響,能力資本與個體其他外部變量均高度相關,為了避免變量之間產生共線性問題,模型只引入涵蓋子女社交能力資本、學習能力資本和工作能力資本的綜合能力資本(c_ability)。此時,代際收入彈性從0.7143迅速下降為0.4299,同時子女能力資本的回歸系數達到0.227(P值<0.01),R2提升至0.3567,模型的解釋力大大增強,假設1得到證明,提高子女的能力資本能夠顯著的提升子女的經濟收入,提高社會的流動性,實現收入的機會公平。然而子女能力資本的回歸系數依然小于代際收入彈性系數,由此可見,代際之間收入流動相對固化依然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
此時,工具變量法為代際收入彈性的估計提供了上限0.42996。當采用最小二乘法對模型進行估計時,得到結果如表4所示:

表3 以子女能力資本為控制變量的代際收入彈性系數IV估計

表4 以子女能力值為控制變量的代際收入彈性OLS估計
此時,最小二乘法為代際收入彈性系數的估計提供了下限0.426843。可以認為,真實的代際收入彈性處于[0.426843,0.42996]之間,估計區(qū)間的寬度非常小,僅為0.003117,因此,基于能力資本的代際收入彈性區(qū)間估計具有非常高的精度。
(三)父輩的經濟收入對子女能力資本的影響
為了驗證假設2的正確性,以子女的綜合能力資本為因變量,父輩的經濟收入為解釋變量進行建模。結果如表5所示:

表5 父輩經濟收入與子女能力資本的回歸模型
父輩經濟收入的回歸系數為0.2614(P值=0.018<0.05),因此認為父輩的經濟收入可以顯著的提升子女綜合能力資本,假設2得到證明。
(四)子女社交能力資本、學習能力資本和工作能力資本的中介效應分析
為了探索子女社交能力資本、學習能力資本和工作能力資本在代際收入傳遞中的影響,利用2014年的單年數據對代際收入模型進行分析。雖然采用單年收入數據會對代際收入彈性估計產生較大的向下偏誤,但是這并不影響本文識別代際收入流動的內在傳遞機制。因此,對本文提出的假設3a、3b、3c進行中介效應分析,為了使模型的估計更加穩(wěn)健,本文采用bootstrap中介效應分析,樣本重復抽取1000次。計算結果如表6所示:

表6 子女社交能力資本、學習能力資本和工作能力資本的中介效應分析
注:Bootstrap replications (1000)
只有社交能力資本的bootstrap置信區(qū)間[-0.0144805,0.0060949]包含0,學習能力資本的bootstrap置信區(qū)間[0.0146524,.0447639]、工作能力資本的bootstrap置信區(qū)間[0.0005357,0.0188997]均不包含0,因此假設3a不成立,假設3b、3c均成立,認為社交能力資本的中介效應不顯著,學習能力資本、工作能力資本的中介效應顯著,此外,父輩經濟收入的直接效應顯著,說明學習能力資本與工作能力資本為不完全中介效應。學習能力資本的中介效應達到33%,工作能力資本的中介效應達到10.22%,學習能力資本與工作能力資本對代際收入傳遞的解釋力達到了43.22%,其中學習能力資本的解釋力更大,因此父親的經濟收入主要通過提升子女的學習能力來提升子女的經濟收入。
四、結 論
本文利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庫對能力資本對代際收入彈性的影響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子女的能力資本是影響其經濟收入的重要因素,通過提升其能力,可以弱化代際收入傳遞的不平等。能力資本在代際收入內在傳遞機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父輩的經濟收入可以顯著的提升子女綜合能力資本。經濟條件富裕的家庭能夠給子女提供優(yōu)越的學習環(huán)境,通過提升子女的學習能力與實踐能力最大程度提升子女的能力資本,幫助子女獲取進入勞動力市場后的收入優(yōu)勢。
教育在勞動者能力資本的后天培養(yǎng)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依據Erikson有關能力的階段性培養(yǎng)理論,20歲以前均為勞動者能力資本高速發(fā)展的關鍵期,因此政府應當加大基礎教育的投入,尤其要促使義務教育進一步均衡發(fā)展,讓每一位寒門學子都能得到公平的教育機會。同時,政府還應當大力發(fā)展公共職業(yè)教育,或者為社會職業(yè)培訓機構提供一定的資金支持,降低勞動者的培訓費用,彌補因上一代社會差距、財富差距不同而造成的機會不平等。
參考文獻:
[1]Becker G S, Tomes N. An equilibrium theory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9,87(6):1153-89.
[2]Mercan M A,Barlin H.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elasticity in Turkey: a new estimat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Business & Social Science, 2016,5(3):30-37.
[3]Corak M. Income inequality,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3,27(3):79-102.
[4]Lefranc A, Ojima F,Yoshida T. Intergenerational earnings mobility in Japan among sons and daughters: levels and trends[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14,27(1):91-134.
[5]何石軍,黃桂田. 中國社會的代際收入流動性趨勢:2000-2009[J]. 金融研究,2013(2):19-32.
[6]韓軍輝. 基于面板數據的代際收入流動研究[J].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0(4):21-25.
[7]丁亭亭,王仕睿,于麗. 中國城鎮(zhèn)代際收入流動實證研究——基于Jorgenson-Fraumeni未來終生收入的估算[J]. 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6(7):83-97.
[8]陳杰,蘇群. 代際視角下機會不平等與農村居民收入差距[J]. 統計與信息論壇,2016(6):64-69.
[9]李晚蓮.社會變遷與職業(yè)代際流動差異:社會分層的視角[J].求索,2010(6):62-64.
[10] 邊燕杰,蘆強.跨階層代際流動是否增加人們的社會資本——基于中國綜合社會調查的分析[J].求索,2016(12):103-112.
[11] 薛寶貴,何煉成. 代際收入傳遞:一個文獻綜述[J]. 經濟資料譯叢,2015(1):64-76.
[12] 邸玉娜. 代際流動、教育收益與機會平等——基于微觀調查數據的研究[J]. 經濟科學,2014(1):65-74.
[13] 陳琳,袁志剛. 中國代際收入流動性的趨勢與內在傳遞機制[J]. 世界經濟,2012(6):115-131.
[14] 周興,張鵬. 代際間的職業(yè)流動與收入流動——來自中國城鄉(xiāng)家庭的經驗研究[J]. 經濟學(季刊),2015(1):351-372.
[15] 譚遠發(fā). 父母政治資本如何影響子女工資溢價:“拼爹”還是“拼搏”?[J]. 管理世界,2015(3):22-33.
[16] 張曉寧,金楨棟.收入貧困與能力貧困:扶貧對象的識別深化[J].中國經貿導刊(理論版),2017(29):25-26.
[17] 謝凱彥. 社交能力會影響個人收入嗎?[D].濟南:山東大學,2015.
[18] 梅海平.收入不平等、消費結構紐曲與公共政策選擇[J].湖湘論壇,2017(2):100-105.
[19] 孔繁軍. 能力資本概念分析[J]. 中國經濟問題,2005(1):75-79.
[20] 李曉曼,曾湘泉. 新人力資本理論——基于能力的人力資本理論研究動態(tài)[J]. 經濟學動態(tài),2012(11):1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