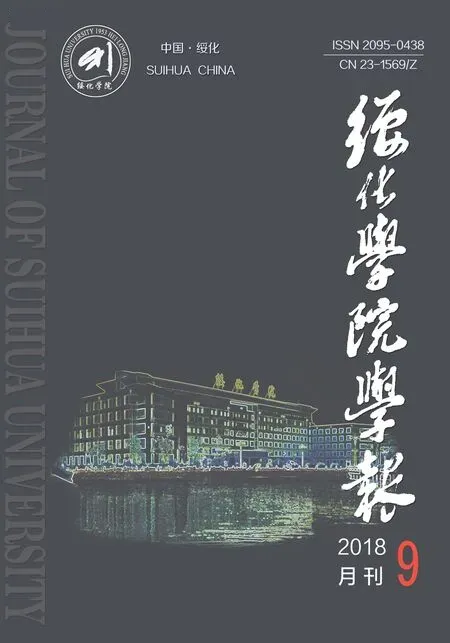新時期廬隱小說創作研究的回顧與思考
張黎黎
(宿州學院音樂學院 安徽宿州 234000)
廬隱原名黃英,1899年出生于福建省閩侯縣。在“五四”時期的文壇上,她是一位引人注目的女性作家。1921年,文學研究會在北京成立時,她是參加成立大會的唯一一位女性,她較早地開始了文學創作。縱觀她短暫的一生,從1921年在《小說月報》上發表處女作《一個著作家》到1934年去世為止,她以獨特的角度和深切體驗,為新文學留下了大量小說作品,同時也奠定了自己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一、廬隱小說研究的前期背景
關于廬隱小說的研究起步較早,20世紀20、30年代就出現了較多的評述文章,如1923年3月10日《小說月報》署名方卓的文章。該文作者對廬隱小說《彷徨》從思想上到藝術上給與簡短評價,他認為:“全文只用一個秋心做主人,由他一個人的煩惱,通信、找事、訓課各種工作,便把中國現代教育屆的情形和盤托出來了,這是何等經濟的文學手段”,同時,他指出該文在藝術上“只有秋心一個人,可以說是一種獨語”。[1](P46)1923年12月10日,《小說月報》署名音奇的文章認為,作者《麗石的日記》“以簡明的筆觸,把復雜的事情,復雜的思潮在這短小的字里行間表現出來”,文章也指出了小說的缺點“首尾兩段雖然簡單得好,然而這樣寫下去,似乎要減少讀者尋味的興趣。”[1](P63)最初的這些評論都是以讀后感形式出現,而且談論的只是廬隱單篇小說,但是評論者已經注意到這位女性作家的風格特點,并對她的創作給予了肯定性評價。
由于廬隱過早地離開了人世,而她的那些篇幅眾多的小說和散文,解放以后也沖來沒有得到過再版的機會,再加之后來文學上“左”的思潮的影響,她的姓名和作品,就隨著時光的流逝,而逐漸被人們淡忘了。這一時期的廬隱研究進入到一個低潮期。
這一時期,關于廬隱創作的論述,沒有單篇論文發表,只在文學史中有一些零星介紹。在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中,關于廬隱的論述僅寥寥數語,指出她的小說創作反映了時代面貌以及青年的苦悶。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用了相對較多的篇幅對廬隱的文學創作作了簡單的介紹,同時指出她的創作生活領域狹窄,由于自身經歷和叔本華厭世哲學的影響,使她的小說帶上了悲觀厭世的色彩。而同期林志浩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認為他的作品中具有反封建的意味。
事實上,有關廬隱研究的發展并不是一帆風順,由于廬隱的早逝,其小說創作的研究也逐漸降溫,由于建國以后以至文革時期文學環境的影響,廬隱小說研究也隨之停滯下來。新時期以來,廬隱研究逐漸獲得了人們的重視,研究角度更加新穎,呈現問題也更加深刻,取得了一系列比較有價值的學術成果。
二、廬隱小說研究的深化期
20世紀80年代初期,由于長期以來廬隱被忽視的狀況,人們幾乎忘記了廬隱作為一個在“五四”時期與冰心齊名的作家的存在。1982年2月,北京師范大學出版了肖鳳的《廬隱傳》,這是有關廬隱生平的第一部詳細傳記,除介紹了她生平外,對她的作品也作了扼要評介。這本傳記的出版開始引起人們對廬隱的注意,漸漸揭開了新時期廬隱研究的序幕。
較早地關注廬隱小說的論文是夏中華的《廬隱小說創作論略》。該文簡要地論述了廬隱小說創作的思想內容,指出其小說創作的現實主義特色,肯定了廬隱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王家倫的《廬隱簡論》,論述了廬隱小說創作在思想內容上側重于對社會和人生的探索,藝術上濃厚的自敘傳色彩和凄婉動人的風格。沈其茜的《一位曾被人們冷落了的女作家——廬隱》“廬隱繼承了五四新文學現實主義的美學原則”[2]。這些論文盡管較為全面地論述了廬隱的小說創作情況,但是仍然沒有突破前期已有的框架。
(一)女性主義視角與廬隱小說研究。新時期以來,隨著國外女性主義批評方法的引入,廬隱的小說研究也走向了深化,不再單純地從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角度,展現其小說創作在五四時期的時代精神。而是從男女兩性的差別和歧異出發,以女性獨特的視角和體驗透視其小說內外隱藏的深層因素。
這方面具有開創性意義的是1989年孟悅、戴錦華的專著《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這是中國第一部系統運用女性主義立場研究中國現代女性文學史的專著。該書對廬隱的文學創作進行了詳細論述,認為廬隱的小說創作呈現了“五四時代新女性的命題:男權的社會結構/女兒的生存方式”[3](P46)。這種全新的視角,突破了以往關于廬隱小說的評述模式,展現了一個長期被忽視或者被有意回避的話題,為后來的廬隱研究開辟了一個嶄新的領域。
沿著這一思路,劉思謙的《娜拉言說——中國現代女作家的心路歷程》一書,從女性心理和女性體驗的角度,展現了現代女作家在當時復雜語境中的內心掙扎與靈魂喊叫。該書結合廬隱的生平與創作,揭示出其內心苦悶與孤獨的性別根源。
歲涵的論文《彷徨歧路的拓荒者——廬隱女性意識及其價值》,[4]從當時的時代語境出發,分析廬隱具有女性意識的話語姿態并展現了這種姿態的歷史處境,可以說是一篇比較有深度的學術論文。
閻純德的《試論中國女性文學的多元形態》一文,對目前學術界針對女性文學廣泛采用的女性主義批評方法保持了審慎的態度。[5]這篇論文從中國文學自身的實際出發,還是比較客觀地論述了女性主義和20世紀中國女性文學之間的關系。
肖淑芬的《廬隱: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位女權主義作家》[6]旗幟鮮明地將廬隱的文學創作全面的界定為具有女權主義特征的個性寫作,給廬隱的文學創作和文學史地位以崇高的評價。
(二)比較研究視野下的廬隱小說研究。近年來,從比較的角度對廬隱小說創作進行考察,也出現了一些比較有價值的成果。較早的是蒯瑞峰的《冰心和廬隱創作比較觀》,[7]該文對兩位作家的小說創作進行了比較。從總體上看,這篇論文還是比較準確地概括了廬隱和冰心創作上的異同點。
關于廬隱與其他作家的比較,如程玖的《廬隱和蕭紅抒情小說主題比較論》、宋劍華、楊姿的《女性悲劇命運的自我言說——廬隱、蕭紅、張愛玲小說創作的文本意義》、蔣明玳的《女性意識覺醒的真實寫照——廬隱、丁玲女性文學創作之比較》等,這些論文從多個角度展現了廬隱文學創作的價值,更說明了進行多向度比較在廬隱研究中的可能性。
(三)廬隱小說的方法論研究。近年來,也出現了從文體角度來研究廬隱小說創作的論文。如韓國學者奉仁英的論文《廬隱的書信體和日記體小說的敘事性分析》,該文認為:“20年代書信體日記體小說完全克服了晚清新小說作家的艷情性,在敘事方式和敘事內涵兩方面都創造了文學的現代性。”[8]許志英、張根柱的《生命活動的藝術結晶——論廬隱作品的情感結構與其文本形式的對應關系》一文,對廬隱小說的文本形式(日記書信體形式與詩化散文化傾向)與其心靈結構(存在和逃亡的矛盾)的對應關系作了研究和探索。在兩篇文章都立足于廬隱小說的本體,做出獨到而又深刻的分析,是非常可貴的。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發表在《中國現代文學叢刊》上的兩篇文章,王翠艷的《女高師校園文學活動與現代女性文學的發生》與張莉的《從“女學生”到“女作家”——第一代女作家教育背景考述》。前者以20世紀20年代初中期文學刊物、婦女報刊及女高師校史資料為依托,選取北京女子高等師范文藝研究會與《文藝會刊》、廬隱、王世瑛、隋玉薇與文學研究會、蘇雪林與《益世報·女子周刊》為個案,從學生自組文藝社團、進入新文學主流中心及介入大眾傳媒三個角度梳理了女高師學生的文學活動與現代女性文學發生之間的密切關聯。后者以第一代女作家教育背景的考述為立足點,展現了第一代女作家浮出歷史地表的過程及其原因。這兩篇文章雖然都沒有全面地涉及廬隱的文學創作,但是它給我們一個深刻的啟示:那就是廬隱的生平經歷、及其文學創作作為研究的外圍因素,對于一個新的問題的揭示與引證作用。
四、對廬隱小說研究現狀的思考
盡管新時期以來,廬隱小說研究出現很多有價值的學術成果,使得廬隱研究走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化階段,但是目前我們可以明顯的感覺到,關于廬隱小說的研究出現了新一輪的停滯。通過統計近年來關于廬隱的研究文章發現:廬隱的相關研究大多停留在女性視角和作品的感傷藝術風格這兩個方面,盡管在寫法上和表述上有所不同,但關注的焦點和解決的問題甚至是相近或相同的,研究文章在質和量上都有大幅度下降。這當然與廬隱本人的文學創作有一定關系,比如其小說創作視域的狹窄等,但也反映了研究者自身在學術研究上的某些懈怠。
具體來說,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深入思考:
首先,關于廬隱小說創作的研究,歷來在政治社會學和女性主義兩大闡釋體系下已經比較成熟,再加上廬隱小說創作先天上的局限,因此目前對這一研究很難有實質性的推進。近幾年出現的有關研究成果中也可以明顯地看出來,很多論文基本上還是以往觀點,只不過是換一種說法、換一種表述。可以預言,在沒有出現超越政治社會學和女性主義闡釋體系的情況下,這種研究上的停滯將不是短時期現象。
其次,廬隱小說并沒有喪失研究價值,仍然有研究空間。以前從比較這一角度研究的文章,較多的是與現代女作家比較,可比性的取得大多是因為他們生活在同一時期,都是女性作家。如果突破這一角度,完全可以在更加廣闊的空間和范圍內進行比較。比如,可以打通現當代,從女性情感和女性體驗這一角度,將廬隱與當代作家進行比較,透視不同歷史時代女性體驗的復雜性。今后對廬隱小說的研究需要轉換視角,這也無形中加大了研究難度。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廬隱研究近些年在推進上有一定難度,但是作為其他研究的外圍因素,還是很有價值。比如將廬隱的生平經歷、及其文學創作作為論證的材料加以運用。總體來說,研究的停滯不代表停止,甚至可以說,這種停滯有可能是在為另一輪研究的高潮蓄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