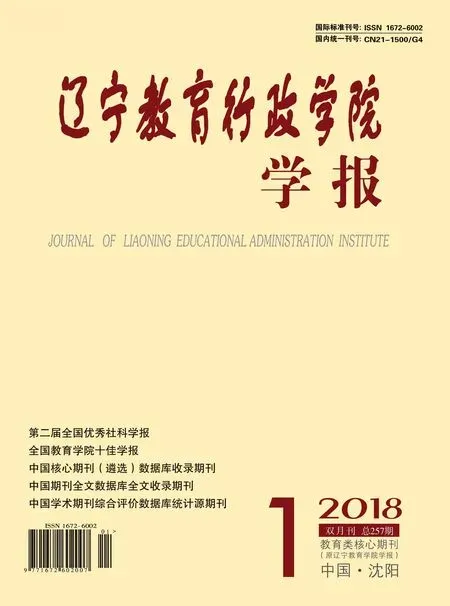貼地飛行的文學轉身
——論顏歌“平樂鎮”小說創作
許寶丹
大連工業大學,遼寧 大連 116034
文學評論家白燁曾在《南方文壇》的評論文章中這樣評價及注解顏歌:“既常常湮沒于青春文學之林,又具有明顯的先鋒性和靠近純文學寫作,因而既未在青年學生讀者中真正火爆起來,也未能得到主流文壇的應有關注。……她的文學追求與藝術趣味,已遠遠超越了她所身屬的80后群體的以青春文學為主的寫作,但因為未能進入主流文壇與文學批評的視野,尚不為更多的人所了解和熟知,她的努力更多地帶有一種獨自探索的意思和孤軍奮戰的況味”。[1]從《良辰》《異獸志》到《桃樂鎮的春天》,顏歌想象力的奇幻瑰麗確實驚艷,但如何讓幻想鏡像進一步堅實和精確,不只虛浮半空更值得思考。《五月女王》和《聲音樂團》從朦朧中初造文學世界——從平樂鎮的嘗試到用復雜的四層雙向邏輯結構做出小說交響樂的形式,在一次次的獨自探索和自我設限、挑戰中,顏歌在構筑自己文學原鄉、文學風格的道路上左奔右突。直到《收獲》雜志上《段逸興的一家》(后更名為《我們家》)的出現,及后期《平樂鎮傷心故事集》的出版,她于重重積累中推開了“平樂鎮”的大門,在語言、敘事、謀篇布局上體現出胸有成竹的從容和肆意。在表現故鄉生活的通俗的現實主義創作中,實現了藝術修養、文體意識和語言自覺的初步統一和成熟。
一、地域特色和方言的主動介入
《我們家》和《平樂鎮傷心故事集》都是以城鄉結合部——平樂鎮為故事發生和人物活動的背景,而平樂鎮的原型就是作者的家鄉四川郫縣皮筒鎮,故事里的各色人物俱是生于斯,長于斯,操著本地方言歌哭于斯。兩部小說之所以廣受贊譽的一個最重要因素就是大量方言的介入,而且入得自然、酣暢、一氣呵成。作家阿來在評價這部小說時用了兩個跨越:一是作者把筆觸從自己身上轉移到別人身上去。在小說中放棄自我,進入他人,進入這個社會和世界。這是身為一名80后作家很好的轉身,經歷這種轉變很有可能失敗,但顏歌看似很輕易地完成了這樣一種跨越。二是對方言的處理和駕馭。以方言入文學的現象早已有之,從中國新文學的百年發展歷程來看,當年胡適以“活語言”的角度稱許運用方言創作的《海上花列傳》是一部不朽之作,活用吳地方言的《儒林外史》也別具神采,更以理論家極具遠見的態度提倡作家用方言創作,創作出有中國特點的活的文學。[2]新時期以來,運用方言進行創作也不乏一些優秀的文學作品,但近些年來,方言文學的創作頗顯沉寂。2015年茅盾文學獎獲得者金宇澄的《繁花》以滬語寫就,突破了北方語言在文學創作語言中的主導和壟斷地位。顏歌的方言創作在展現人物精神世界和心理神采的挖掘方面還是有欠缺的,但她主動選擇方言介入文學創作,并讓行走活動其中的男男女女和其自身構筑的文學世界真實可信,毫無滯澀之感,不能不說是驚喜。
文學有地域性似乎很早就為人們所注意。《文心雕龍》中稱北方早出的《詩經》為“辭約而旨豐”“事信而不誕”,是質樸的“訓深稽古”之作;稱南方后起的《楚辭》為“瑰詭而惠巧”“耀艷而深華”,將“奇文郁起”的原因歸于楚人之多才。[3]斯塔爾夫人在《從文學與社會制度的關系論文學》中認為,西歐文學可以分為南方文學和北方文學。北方文學中常見的形象和思想是有關生命的短促,對死者的尊敬、思念和崇拜,足以使人們的思想進行最深刻的沉思。南方文學樂于表現追憶的形象,有更廣泛的興趣,對思想的專注,會產生熱情和意志的奇跡。[4]承繼斯塔爾夫人的19世紀法國文藝理論家丹納在《英國文學史》序言中提出文學決定于三個因素,即種族、環境、時代。嚴家炎先生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從地域(區域)文化的角度來分析作家的創作和文學的發展,在地域文化與文學的交互作用中,加深人們對不同文化特質的理解。新世紀由于文化熱的興起,對地域文化與文學和文學創作關系的研究并不少,但主動根植于此方面汲取養分進行創作的作家卻不多,特別是在80后這一代作家身上更是鳳毛麟角。李娟的散文以新疆的阿勒泰和當地哈薩克游牧人的生存經驗為肌底,用自己在這片土地上的體驗和經歷進行感知、思考,渾然天成、質樸感人。曹乃謙的作品帶著雁北高原的原生態和泥土氣,說著筱面味兒的方言綻放著獨特的魅力。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舌頭,顏歌的《我們家》和《平樂鎮傷心故事集》用潑辣俏皮的四川方言一一展示著川西小鎮上時代的悄然變化和人們生活的家長里短,在充斥著文學腔和抒情味兒的敘事里,呈現出蜀地的勃勃生命力。難怪《收獲》雜志編輯在最初看完《段逸興的一家》后告訴顏歌“我想吃一碗肥腸粉了”,會讓她由衷地安慰和喜歡。
從《我們家》葷素不忌的方言敘事,坦然直白的展示到《平樂鎮傷心故事集》里方言敘述的內收和節制,以及與生活口語、古體詩的糅合試驗,顏歌袒露著平樂鎮的骯臟、粗俗和混亂,并用自己內心的強大和熱愛發掘著隱藏其中的美好和詩意。富有地域特色的平樂鎮敘事啟發并矯正了顏歌,帶給她文學給養上的自信,進而找到適合自己的寫作之路,形成自我的風格,從更深層的意義上看,它更催生了顏歌文學創作的自省和文學生命力意識的萌發。
二、形式上的先鋒與意蘊上的“回鄉”
顏歌在小說創作上一直具有某種強烈的探索意識,可以說是一位在創作上有“野心”的作家。她在不同的文體和形式中調試著自己,寫作在一定層面上是顏歌自我的設限與突破,是對自我的治愈與挑戰。從早期古代的神話小說創作,到帶有魔幻現實主義的《異獸志》,再到懸疑色彩濃厚、回環式復雜結構的《聲樂樂團》,進而到進行語言試驗采用通俗現實主義手法創作的《我們家》《平樂鎮傷心故事集》。顏歌曾說過讀者對她來說是似有似無的存在。她從小在家庭教育中所受的文學熏陶和培養起來的文學素養,加之碩博階段比較文學研究帶給她的扎實的理論基礎,使其在文學創作上有一種潛在的精英意識,反映到小說創作中,便帶有一種先鋒意味。先鋒派之所以稱之為“先鋒”,主要體現在形式領域里的標新立異和開拓創新。顏歌小說的先鋒意識主要表現在結構上,并集中在其前期小說創作中,但現實意味較強的《我們家》《平樂鎮傷心故事集》仍在形式手法上體現出先鋒意識。
以病殘兒童視角切入,以他們的眼光和口吻敘述故事,用“不可靠敘述”將作者對現實的審視和自我的表達隱匿在病殘兒童視角下。《我們家》以一個缺位并且不在場的精神病童“段逸興”作為敘述者,圍繞著給奶奶過八十大壽這一主線,對陸續登場的家庭成員之間隱藏的秘密、情感的糾纏、關系的對立與依附、親情的破裂與聯結進行了直白而冷靜的展現,糅合語言上的俏皮潑辣、葷素不忌,隱去道德審判色彩,在某些場景中形成一種近似荒誕的喜劇效果。《白馬》在視角上與《我們家》有一定的承繼與互相關照。全篇以“我”為第一人稱視角作為敘述者,因常能看到綴在人身后的白馬而在某種程度上有心理問題,通過“我”的眼睛窺破并展開了長輩們之間的陳年情欲秘事和姐姐的早戀之事。只不過《我們家》是忍俊不禁后的心酸與嘆息,而《白馬》是一個與孤獨為伴的少女的自我成長陣痛。另外,顏歌的小說常在結構上呈現出一種“反向閱讀”的“元小說”文體形式,有點兒類似于先鋒小說作家馬原的“敘述圈套”的寫作方式。[5]《我們家》在敘述上并非小說常見的順序或倒敘結構,而是過去與現在不斷交織往復的推進式進程。顏歌在談及她的平樂鎮小說創作時,立意要探討如何解決真正意義上的虛構這一命題。《我們家》《平樂鎮傷心故事集》通過對時間和空間的拼接重組,打破虛與實的邊界,使人們在閱讀的虛實之間,重新尋找走向真實的途徑。
雖然這兩部小說在創作的形式手法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先鋒意識,但在整體的意蘊上卻體現了某種精神上的“回鄉”傾向。《五月女王》以前的作品,人們看到在顏歌華麗空靈的語言、絢爛的想象力、寫作的才情稟賦之下,似乎總有著雕琢和刻意的痕跡,這是青春期成長和書寫避免不了的“為賦新詞強說愁”式表達。但《我們家》和《平樂鎮傷心故事集》的寫作初衷,是顏歌在美國做訪問學者期間對故鄉的一次回望,是“漂泊”已久的一次轉身,恰似“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像習武之人突然打通任督二脈,顏歌調度著活潑俏麗的四川方言,用白描的方式寫小鎮的混亂、粗俗,小鎮人之間的算計、磕絆,寫時代變換下這里的人們用自己的方式消化著生活帶來的苦辣酸甜。克制和樸素的語言背后,品味得到顏歌的溫情和體諒,也扯著讀者們的“心顛顛”。正如福克納筆下的約克納帕塔法縣,馬爾克斯筆下的馬孔多,沈從文筆下的湘西,老舍筆下的北平,在向文學先賢們致敬的同時,顏歌找到了一種確立自身精神原鄉的表達,并在表達中有著從容和文化自信之氣。正如她自己所說,少時總是想著趕緊長大離開這里,但現在哪兒也不想去,這兒是我的伊甸園,而我充滿喜悅的在此地翻找詩意。[6]
三、輕逸的文學審美質地
《我們家》和《平樂鎮傷心故事集》毫無疑問是純文學創作,并且也得到了主流文壇的關注,在創作和作者主體選擇上體現了“輕逸”的文學審美傾向。意大利小說家、美學家卡爾維諾致力于倡導一種“輕逸美學”,他指出“我的工作常常是為了減輕分量,有時盡力減輕人物的分量,有時盡力減輕小說結構與語言的分量”,[7]用“一種深思熟慮的輕”從不同的角度和邏輯看待世界,認知并體驗世界,表現作家所處時代和現實所裹納的沉重和苦難。這一觀點和沈從文秉持的悲劇表現觀念形成某種映照性說明,“神圣偉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灘血一把眼淚,一個聰明作家寫人類痛苦是用微笑表現的”。[8]顏歌的“平樂鎮”小說在文學審美傾向上暗合了卡爾維諾的“輕逸”美學精神,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顏歌小說中四川方言的運用,呈現一種灑脫輕快,充滿節奏和韻律感的特質,加之“不確定敘述”手法,這兩點是小說“輕逸”美的重要推手。方言的選擇運用實現了和人物特點的精準對接,而且語言是思想的殼子,這些方言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小鎮人物的生活態度和處世哲學。“我爸爸”薛勝強整日操著“怪話”,在經歷了替哥哥頂罪、輟學做學徒、老婆出軌、女兒得了瘋病、自己心臟病不時發作等一系列生活變故和打擊下,仍常把“算逑了嘛”“要得公道,打個顛倒”掛在嘴邊安慰自己,體現了面對苦難把日子過下去的豁達。雖然為了推動情節發展和實現結構張力,大量臟話和情欲描寫有淪為輕佻之嫌,但小說的創作意圖和落腳點卻不在男女私情的暴露上,其在內涵上承繼了現代四川文學和巴蜀文化的調笑傳統。《平樂鎮傷心故事集》里五個故事,五個女子,流露著悲劇的意味,似乎故事的結尾都應該添加一句“她們都回到家去,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場”,但方言的運用在敘事和結構上起到了很好的平衡和調節作用,把悲喜調節到一個適當的調值,它比《我們家》在內涵和意蘊上“沉重”一點兒,但卻是“哀而不傷”的。
對于“宏闊感”“史詩性”“家國命運”式的苦難書寫,顏歌在心理和創作上都保持一定的距離,就創作心態和意圖而言,她說“我不需要它表達圖景,呈現意向,隱藏結構,更不用說傳達什么道理,它只是一個陪我度日的小玩意兒”,[6]這也體現了顏歌創作主體自我選擇上的“輕逸”美學傾向。雖然離卡爾維諾所倡導的在對苦難和沉重充分把握和理解的基礎上,舉重若輕地展現生機盎然的美學追求還有不小的距離,但顏歌勇于在寫作“大歷史”“主旋律”的環境下,不斷探索屬于自己的表達方式和敘述風格,這對于一位年輕作家來說是值得肯定的。既審“厚重”之美又賞“輕逸”之美,是文學審美內在發展多樣性的應有之義。
《我們家》和《平樂鎮傷心故事集》是顏歌將文學寫作與現實社會這一大課題相融合的嘗試性表達,在語言、文體和構筑自身文學世界方面有著清醒并自覺的意識,是其文學貼地飛行的一次成熟轉身。三十歲以后,顏歌稱自己來到了一個作家寫作的幼年時期,作為一個作家的故事才剛剛開始,又是興奮又是不安。隨著生活閱歷和文學視野的雙重拓展,顏歌還將會帶來怎樣“嗒嗒踩著大家心顫顫”的作品,值得期待。
[1] 白燁.才女顏歌[J].南方文壇,2007(4).
[2]崔劍劍.〈我們家〉——80后文學的第四個方向[J].學術交流,2014(3).
[3] 嚴家炎.20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總序[J].理論與創作,1995(1).
[4] 陳鳴樹.文藝學方法論(第二版)[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5]徐勇.“鬼魅”顏歌——顏歌小說論[J].西湖,2014(3).
[6] 顏歌.平樂鎮傷心故事集[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
[7] 伊塔洛·卡爾維諾著,肖天佑譯.美國講稿[M].上海:譯林出版社,2012.
[8] 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17卷)[M].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