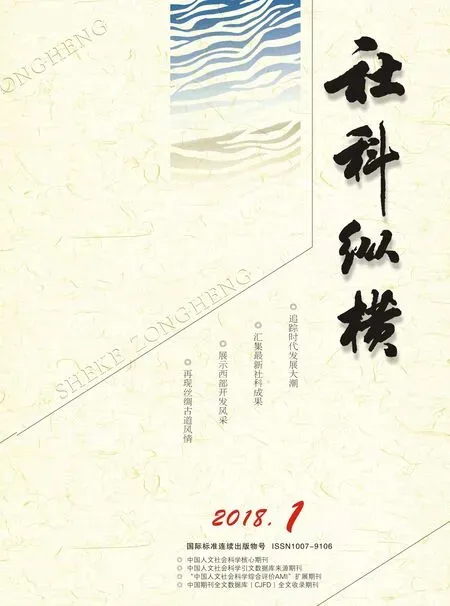海德格爾存在論思想的生態維度
馬成昌 司皓君
(黑龍江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黑龍江 哈爾濱 150027)
我們通常稱海德格爾哲學為基礎存在論,因為它開啟了根本不同于傳統形而上學關于人、物、自然的全新思考,繼尼采之后對兩千多年的哲學傳統進行了一次凌厲地解構。這種對人、自然以及二者關系的新闡釋蘊藏著豐富的生態思想,由此帶來的是一種根本不同于環境倫理學的新視野以及對其立場、觀點與方法的建基、豐富與矯正,從而對克服人類中心論與科技萬能論,轉換人與自然的交互方式,解決環境倫理學與人類生態建設所面臨的諸多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海德格爾在反對胡塞爾先驗自我這一近代主體哲學的過程中,以希臘式哲人的姿態力圖消解傳統形而上學的主客二元論與人類中心論,無論是前期對此在(Dasein)之在世方式、對物之上手性、對周圍世界的分析,還是后期對無、本有(Ereignis)等一些重要概念的分析都充分顯示了海德格爾解構傳統形而上學的決心和力量。在他存在論思想的哲學運思中蘊含著豐富的生態思想,這種生態思想的重要特點在于:它是以存在論的方式來守護自然而非環境倫理學所說的價值論方式;正如作為此在之本質的生存不是一個倫理學問題,人類所面臨的生態環境問題也不是簡單的倫理道德問題,而是一個存在問題;正如存在關系先于和高于認知關系,存在論的生態學也同樣先于和高于生態倫理學。這種存在論中所包含的生態思想貫穿于海德格爾哲學的始終。《存在與時間》以現象學方法建立了此在之生存論樣式,構筑了人與世界全新的存在方式,即此在的在-世界-之中-存在(In-der-Welt-sein),世界作為周圍世界而存在,從而以現象學方式實現了人與世界的原初統一。海德格爾直面人類的生存處境,重新審視人、物、自然、大地、世界以及人與人、人與世界的關系問題,反思現代技術主義泛濫的形而上學根基,矯正人類現存的生存方式,重新處理人在世界中安居的位置,實現天、地、神、人的四重游戲與守護,使人類詩意地棲居于大地之上。
一、自然即是涌現
海德格爾哲學的生態維度在于通過對人與自然的全新理解,闡明當下人類生存危機的根源在于西方傳統形而上學之中,因此,根本的解決之道是克服傳統形而上學,重新理解人、自然以及二者的關系。在海德格爾看來,通常人們理解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即是主體與客體的對象化關系,而這種關系又來源于傳統形而上學的認知性思維模式,但這種思維模式卻是此在生存的派生性樣式而非原初樣式。此在的本質是生存(Existenz),存在關系高于和先于認知關系,然而我們卻遮蔽了這種原初關系,兩千多年來一直躑躅于派生性的認知關系的束縛之中,無論是觀念論還是實在論都囿于“人是理性的動物”這一傳統的認知思維方式。海德格爾以此在(Dasein)來解構傳統形而上學中作為主體的人的概念,此在是在-世界-之中-存在(In-der-Welt-sein),海德格爾以此來表達人與世界的共屬一體性,這個“在之中”并非指空間意義上的如桌子在教室中這種“在之中”,而是指“我已住下、我熟悉、我習慣、我照料……我居住于世界,我把世界作為如此這般熟悉之所依寓之、逗留之。”[1](P67)此在與世界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并不是說一面是此在一面是世界,兩者相對立,而是此在先于世界而存在,此在在認識世界之前就已經與他的周圍世界渾然一體了。海德格爾所說的周圍世界中的世界很顯然不是一個通常的空間概念,而是一個存在論概念,只有在世界中對存在領悟的基礎上才有對存在者的照面與反思。“此在只有在它的在世的一定樣式中才能發現這種意義上的作為自然的存在者。”[1](P81)
很顯然,海德格爾看待自然概念的立場不同于自然科學,因為后者將自然看作是可以控制、計算與利用的對象;也不同于生態倫理學,因為生態倫理學將自然擬人化,進一步加強而不是消解了主體形而上學的絕對優勢地位。在海德格爾看來,前兩者的立場都深深扎根于傳統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中,都是對存在者的尋求而非對存在本身的探究。通常我們總是習慣于從能量、資源的角度去看待自然,把它們當作現成在手之物:森林是木材資源,河流是旅游資源,山川是礦產資源,風力是發電資源。在這種狀態下,那個洶涌的自然,撫育我們的自然,使我們閑然自得的自然,都隱而不顯。周圍世界之物在與此在的親熟關系中徹底脫落,以現成在手的方式而被揭示與規定,從而下降為一種次級的派生關系。一切都變為可以訂造的自然,而忽視了它們作為上手狀態的存在特性。實際上,自然不是單純的廣延,不是客體的總和,不是現成在手之物。
海德格爾認為,人類以三種方式呈現自然,即理論的自然、實踐的自然與原始的自然。理論的自然即對象性的自然,它將一切都看作是可以被計算和控制的客觀存在物,一切都處于現成在手狀態(Vorhandenheit),這是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其二是實踐的自然,即作為周遭世界(Umwelt)、使我們寓于其中的自然,人類時時處處在煩(Sorge)中與之打交道,時刻處于上手狀態(zuhanden);其三是原初的自然,它不僅處于上手狀態,而且就是各種自然現象之總和,如各種藝術作品中所描寫與謳歌的河流、幽谷、藍天、白云,麥浪、蜂鳴等各種自然現象。以海德格爾常舉的錘子為例,錘子的上手性、好用性、它的錘擊的適當性使它成其為錘子;而當錘子不好用,不上手,如過輕、過重、錘子柄松動或折斷時,不能正常錘擊東西的時候,我們馬上便與之產生了距離,而對之采取理論觀察的對象化、專題化姿態,這時才有了對它的反思與認識。藝術家所呈現的各種器物如荷爾德林的詩句、梵高畫中的農鞋展現的都是原初的自然。海德格爾以他所擅長的詞源學方法追溯了自然概念的原初意義。希臘意義的自然即Physis,在其思想的開端處其意為涌現、顯現、開啟自身,根本不同于后世自然(Natur)所說的某物,恰恰相反,某物只有在Physis的澄明中才能夠表現其外觀。希臘的Physis即為荷爾德林所說的神圣(das Heilige),后者實為前者的詩意表達,即自然源于神圣的混沌,是無所不在的創造一切者,自然是充滿神性之所,是諸神的逗留之地。在海德格爾看來,三種自然觀體現的是對存在之真理的三種理解方式,即詩性之思、主體形而上學、基礎存在論,詩意的存在方式高于實踐的存在方式,實踐的存在方式高于理論的存在方式,而我們以往對世界的理解則完全本末倒置了。“認識無非就是在-世界-中-存在的一種方式,確切地講,它還根本不是在-世界-中-存在的一種首要的方式,而是在-世界-中-存在的一種被奠基的存在方式,它從來都只是在一種非認知行為的基礎上才是可能的。”[2](P224)然而,不幸的是這種次級的主體性、對象性、認知性的思維方式在近代以來卻大行其道,進一步加深了對存在的遮蔽,導致的是技術主義的泛濫。
二、技術即是構架
通常我們把技術的本質看作是人類征服自然與利用自然的工具,體現的是人類在與自然打交道的過程中自身能力的增強,是人類自身不斷完善不斷提高的標志。如果說傳統形而上學是從存在者之真理出發來理解技術的話,那么海德格爾則從存在之真理出發來理解技術,將技術看作是存在之去蔽的方式。海德格爾認為,傳統思維方式將技術工具理性化,將對存在的領悟變為對存在者的計算,由原初的對存在的去蔽演變為對存在本身更進一步的遮蔽,最終導致技術對地球的全面控制,也導致人類自身的全面異化。海德格爾所言并非聳人聽聞,我們想一想時下的人工智能在與人類競爭中的全面勝利就會預感到,在不久的將來它對地球包括對人類的統治可能會成為現實。而這在海德格爾看來,從最根本上說,就是傳統形而上學將對存在的探究演變為對存在者思考的結果。
海德格爾認為,技術對地球的全面控制是人類面臨的最大危險。因為它已使地球不再是可供棲居的原初地球,人也不再是原初的人。地球被貶抑為我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能源寶庫,人類在貌似成為地球主人的同時,不僅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美好家園,而且自身也變為可以被控制、開發、利用的一種新的資源即人力資源。海德格爾用構架(Gestell)來稱謂這種技術主義的肆意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一切都被技術有序地安排到固定的位置上,這種安排自身構成了固定的組織框架,每一物都失去了其獨立自存性,一切都變得千篇一律,都可以成批地被訂造出來。
為此,海德格爾同樣進行了他所擅長的詞源學追溯,技術一詞來源于希臘的技藝(techne)一詞,但已完全不同于后者。技藝(techne)是一種去蔽方式,是一種真理呈現方式,不是我們所說的單純的創制活動,不是工具、手段之類的東西。“techne是指將存在者帶到眼前,即特地將在場者作為在場者從隱藏狀態帶出來,以便將其帶入到它在其中顯現的去蔽狀態的跟前來。”[3](P46)它的原初意義就是“使其自身呈現”、“將其帶到面前”。技藝是去蔽的一種方式,但不是現代控制意義上的去蔽,而是自身呈現、自身涌現意義上的去蔽。而技術則是無休止地向地球提出無禮要求,迫使其提供可供開發、利用、儲存、消費的各種能量與資源,進而成為被我們算計,以我們的需要為導向的而被制造出來的各種商品。同理,人本身作為一種資源也成為了一種可訂造之物,使人變成了非人,造成了人自身的異化。人類無節制地追逐著技術所帶來的各種制造結果,并且以這樣一種尺度來處理所從事的一切事物,也包括對其自身的處理,并貫以科學管理與地球主人之名樂此不疲。然而這卻是我們現代社會的最大危機,我們將因此失去我們的生存家園與我們自身的獨立地位。究其根本原因則是兩千多年來形而上學思維方式所導致的必然結果。
海德格爾通過對技術本質的批判來呈現作為去蔽的真理,從而使人們領會到存在真理之運作。在傳統形而上學思維方式下對存在者真理之探求的極致就是當前技術主義的泛濫:技術以構架的形式運作,成為唯一的去蔽方式,將包括人在內的一切事物都納入訂造之中,視為持存之物。但哪里有危險哪里就有拯救。恰恰就是在這種極端的危難中,在人類對技術的瘋狂與由此帶來的迷失中,人類生存的歸屬性與本真性開始顯露出來。這種拯救來自于對希臘人關于技藝的原初體驗。技藝是一種藝術的創制,是對存在之真理的順應,是一種美與詩意地創造,人類將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之上。
三、詩性之棲居
技術世界將一切存在者納入了計算與規劃之中。面對技術大潮的咄咄逼人之勢,我們是否能夠以另一種方式逗留于這個世界,為自己開辟出另一種生存可能性,從而立身于這樣一個技術統治的世界而又免于它的過度危害。海德格爾將這樣一種美好愿景稱之為“詩意地棲居”。技術將自然看作是任它予取予求的對象,將其當作資源庫,在這種情況下,自然不再有其自身的形象,失去了其獨立自存性,而變為任人宰割的對象,如為了滿足人類各種欲求而出現的改道的河流、被削平的山巒、人工裝飾的景觀、轉基因的產品等。技術已然綁縛了人類衣食住行以至物質與精神活動的所有方面,人類已然不知何謂棲居。海德格爾將棲居(wohnen)看作是天、地、神、人四方的相互開啟、相互游戲、相互保藏與相互守護。天空的升騰與疏朗,大地的深沉與保藏,神性的奧秘與無限,人類的辛勞與有死。四方沒有哪一方是中心,也沒有哪一方被邊緣,四方相互守護,相互應和,一同構筑了人類于其中的世界,這便是棲居。在棲居中最重要的特點就是保護,一種相互的保護,一種非對象化的守護。“在拯救大地、接受天空、期待諸神和護送終有一死者的過程中,棲居發生著對四重整體的四重保護。”[4](P159)這可以看作是海德格爾嘗試開辟的一種新的生存方式。海德格爾以藝術的從容來抵制與反抗技術的強制、泛濫與肆虐,棲居不是技術的裁制,而是藝術的應和,在這種應和中人是自然的守護者,而非自然的主宰者。在棲居的方式上海德格爾提出了詩意地棲居之思,在某種程度上是終于一死之人存在于大地的基本方式,相對于理性之人將一切對象化的人類中心論生存方式,它是對存在之真理的應和。此在不僅以非概念的方式運思,更是以非對象性方式逗留于大地之上,這明顯有別于囿于對象化思維的環境倫理學所處理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并且提供了一個更為根本的生態維度。在技術叢林密布的壓抑中,海德格爾用他的詩意棲居開辟出了一片疏朗的林中空地,這片林中空地便是人類所期望的生存家園。
海德格爾認為,人的本性不是絕對的理性存在物,不是在對象化過程中得以呈現自身,不是存在的占有者;人的本質是生存,即綻出之生存,人的偉大命運是存在的守護者。在自我涌現的世界中,在詩與思中,人是地球的逗留者、棲居者、守護者與應和者,海德格爾的思想主旨即是在棲居中守護存在之真理。
由此觀之,海德格爾存在論所生發出的生態思想完全不同于環境倫理學,后者承認自然有其內在的價值,而前者則明確否定這一維度。“通過把某物評價為價值,被評價的東西僅僅被容許作為人之評價的對象。”[5](P411)按照海德格爾的觀點,環境倫理學的價值評估已經將存在者作為現成在手的東西,已經主體化為可以計算的對象,而不是一種上手狀態,一種讓存在者自行存在的狀態。當我們把某物看作是與人類具有同等價值的時候,我們并不是提高了某物的尊嚴而是大大降低了它的尊嚴。誠然,環境倫理學并非直接降低了環境的尊嚴,它只是在將其看作對象之物、給定之物的意義上降低了尊嚴,這個環境就是大自然之總和、地球之整體。環境倫理學的環境是已經給定的、可供利用的自然資源的總和或者說是存在者的集合,是有待保護的對象意義上的外在的自然,并非海德格爾所說的環境,“它已被先行揭示,且它是我們對存在者的回溯所由之出發之處——我們與這存在者打交道,逗留在存在者那里。”[6](P220)按海德格爾的理解,作為意蘊整體的周圍世界,它是高于和先于任何倫理學與實證科學所規定的存在者集合意義上的環境的,他所說的環境即是我們時刻在煩忙與煩神中與之打交道的處所與家園。
結語
對海德格爾來說,最根本的不是環境倫理學所說的改變人對自然的態度,而是人與自然的互動方式。因為環境倫理學在批判人類中心論、技術萬能論,強調自然價值與人類自身價值的平等性時,存在著一個強烈的理論預設,那就是把自然看作是對象的集合體,將存在視為存在者,歸根結底仍然是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所以,從最根本地意義上來說,人、自然及其二者的關系問題不應該在認識論的意義上來理解,而應該在海德格爾存在論的意義上去理解。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解決人類生存所面臨的種種理論與實踐問題。
[1]海德格爾.陳嘉映,王慶節合譯.存在與時間[M].北京:三聯書店,1987.
[2]海德格爾.歐陽明譯.時間概念史導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3]海德格爾.孫周興譯.林中路[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4]海德格爾.孫周興譯.演講與論文集[M].北京:三聯書店,2011.
[5]海德格爾.孫周興譯.路標[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6]海德格爾.丁耘譯.現象學之基本問題[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