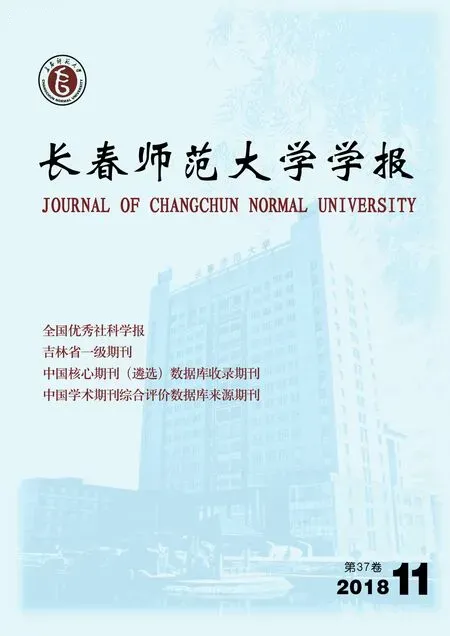瑪格麗特·杜拉斯“印度系列”文本間互文性研究
張 來
(東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吉林 長春130024)
瑪格麗特·杜拉斯是現當代法國文壇上極具代表性的作家。作為“新小說”流派的代表人物,杜拉斯于1964年發表了她一生中最為珍愛的作品《勞兒之劫》(法文:Le Ravissement de Lol V. Stein,又譯《勞兒的劫持》或《勞兒·維·斯坦茵的迷狂》)。這部作品一經問世,便引起文學界的強烈反響。法國精神分析大師雅克·拉康在1965年公開發表文學評論《向瑪格麗特·杜拉斯致敬——論〈勞爾之劫〉》,并在文中對杜拉斯的這部作品大加贊賞。然而,關于女主人公勞兒·維·斯坦茵的故事并沒有隨著《勞兒之劫》的出版而結束。1966年的小說《副領事》、1971年的小說《愛》、1973年的電影劇本《印度之歌》和《恒和之女》相繼問世以后,杜拉斯筆下關于“勞兒”的故事才真正講完。由于故事背景都圍繞印度支那展開,作品人物存在似有似無的重復性,中外的文學評論家和杜拉斯研究專家習慣于將《勞兒之劫》《副領事》《愛》《印度之歌》《恒河女子》這五部作品統稱為杜拉斯的“印度系列”。
然而,“印度系列”作為杜拉斯文學創作的巔峰卻很難像其所著《廣島之戀》《情人》等作品那般容易為大眾所接受,原因在于這五部作品的情節設計極為獨特,表達主旨極為抽象,人物的語言和對話極為破碎,常常只有與上下文毫無關系的一個詞,甚至是一個字。同時,其故事發展顯得缺乏邏輯,給廣大讀者和研究者造成了一定的理解障礙,因此曾一度被評價為內容空洞、缺乏主題的失敗作品。在這種背景下,嘗試利用文本間的互文性理論對“印度系列”五部作品進行整體分析和解讀顯得尤為必要。
一、故事發展的互文性
互文性又稱“文本間性”或“互文本性”,是一種源自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文本理論,近年來廣受歡迎。該理論的概念最早由法國符號學家、文學批評家朱麗婭·克里斯蒂娃在其《符號學》一書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許多行文的鑲嵌品那樣構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轉化”。也就是說,每個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文本與文本之間都是彼此的鏡子,每一文本在形成過程中必定要經過對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轉化。不同文本之間相互參照,彼此牽連,形成一個開放網絡以供人無限延展。杜拉斯“印度系列”中的五部作品實際上就是相互改寫、補充和擴展的關系。每一部作品都不能單獨作為一個文本被闡釋,否則將會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遭遇幾乎無法逾越的困難,難以理解作者想表達的真正含義。
杜拉斯這五部作品之間的內在聯系絕不僅僅在于故事背景的雷同,甚至也不完全在于主人公的重復。實際上,《勞兒之劫》講述的是年少時在訂婚舞會上親眼目睹未婚夫背叛的勞兒的故事,以及她在遭遇殘忍拋棄后的一系列瘋狂舉動。《副領事》講述是的法國駐拉合爾的年輕副領事官在愛上大使夫人后陷入絕望直至開槍殺人的故事。《愛》更像是一出舞臺劇,為讀者呈現了一個慘遭拋棄的瘋女人、一個故地重游的旅行者和一個瘋囚犯在海灘上的行走與對話。《印度之歌》實際上是小說《副領事》的劇本,1975年在杜拉斯親自導演下拍成了電影。《恒河之女》則是小說《愛》的劇本,以更為舞臺化、立體化的方式呈現了三個主人公之間的復雜關系。因此,杜拉斯《印度系列》的五部作品之間的真正聯系其實在于文本間的互文性。
首先可以明確的是,在“印度系列”五個文本中,《勞兒之劫》應被視為中心文本,是整個故事的始發點,也是對幾個人物特點、性格進行分析的參照母本。在《勞兒之劫》中,主人公勞兒在十九歲那年被未婚夫當眾拋棄。經過一段時間的靜默之后,勞兒與一位音樂家閃婚,生育三個孩子,移居他鄉過起了看似正常的生活。十年后一次偶然的機會,勞兒隨丈夫搬回故鄉,并在街上偶遇兒時閨蜜塔佳娜。一些看似已經被勞兒遺忘的記憶慢慢浮出水面,侵蝕著勞兒的人格和生活。勞兒故意制造了與塔佳娜的重逢,成功引誘了塔佳娜的情人雅克·霍德,并且享受于躺在旅館后面的黑麥田里透過窗戶偷窺二人偷情的過程。在雅克的陪同下,勞兒回到十年前被未婚夫拋棄的舞廳里,一切記憶都變得鮮活起來。隨后,勞兒最后一次躺在黑麥田里偷窺雅克和塔佳娜的私會,疲憊不堪地睡去了。《勞兒之劫》這部小說為讀者呈現了開放性結局,對于勞兒“疲憊不堪地睡去”,杜拉斯沒有給予任何定論。關于勞兒為什么要搶奪閨蜜的情人,是不是已經陷入瘋狂,以及睡去之后的勞兒在醒來之時會恢復正常還是進一步淪陷,似乎只能在《愛》中找到一絲答案。因此,《愛》可被視為《勞兒之劫》的一種續寫,其互文性在于對人物形象的補充和對故事結局的交代。雖然作者杜拉斯在《愛》中完全沒有提及三個主人公的名字和身份,但細心的讀者仍然可以從微妙的人物關系和對話中發現,曾遭遇情變的瘋女人應該就是勞兒。這個瘋女人始終跟著一個瘋囚犯,他也許就是雅克·霍德。而跟在瘋女人身后,試圖通過故地重游來尋找當年記憶的旅行者就是勞兒的未婚夫麥克·理查遜。三人一同在勞兒的故鄉S海市行走,似乎互不相識,又似乎在尋找著共同的記憶。瘋女人已淪為欲望的奴隸,哪個男人要她她就跟誰走,多次懷孕,孩子生出來也不知父親是誰,于是直接拋棄在荒郊野嶺。當瘋女人和旅行者重新回到舞廳,關于十年前那場背叛和拋棄的記憶席卷而來。旅行者哭泣著問瘋女人那個當年拋棄了她、與情婦遠走高飛的未婚夫是不是已經回來,瘋女人只漠然地回答:他已經死了。
《愛》實際上很難被定義為傳統意義上的小說。正如法國評論家克里斯提安娜·布洛-拉巴雷爾所言,在《愛》的創作上,“瑪格麗特·杜拉斯的作品比以前任何時候都缺少通常的情節支持和傳統的敘述話語”。甚至不夸張地說,這部作品是一部沒有情節、沒有人物塑造、更沒有敘事邏輯的文本,語言常常時斷時續,處處透著殘缺和破碎。無主題、無主線、無人設等特點使得《愛》一旦作為獨立文本,幾乎不存在可閱讀性。唯有結合《勞兒之劫》的人物特征和情節發展,才能依稀推理出《愛》中的人物身份和對話含義。讀者一定要通過《愛》才能知道《勞兒之劫》中勞兒是否瘋狂以及結局如何,同時一定要通過《勞兒之劫》才能知道《愛》中的人物身份和看似荒唐、無邏輯的對白背后的真正含義,這便是存在于這兩個文本之間的互文性。在《愛》的“劇本”《恒河之女》中,勞兒的故事由畫外音講述,并且也沒有交代主人公的名字。對于《勞兒之劫》中勞兒在黑麥田中疲憊睡去這一突如其來、令人匪夷所思的結局,《恒河之女》給出了較為明確的交代:“救護車來到黑麥田把她接走”,但勞兒的“記憶喪失了”,成為了“灰燼”。
二、人物塑造的互文性
《副領事》與《勞兒之劫》之間也存在著微妙的互文性聯系。《副領事》中雖然也有勞兒,但只是以一個瘋女人的畫外音形式出現。電影《印度之歌》將《副領事》的故事搬上熒屏,其開頭與結尾都是瘋女人勞兒的歌聲,凄涼、悲切。《副領事》的主人公是因工作失誤被上級從拉合爾調任到加爾各答的年輕副領事讓-馬克·德·H。他本就是沉默寡言、性格內向的人,因在拉合爾被人指證而貶職到加爾各答,所以遭人排擠,只得處處小心畏縮。在加爾各答領事館舉辦的舞會上,他遇見了法國大使夫人安娜-瑪麗·斯特雷特。從見到這個女人的第一刻起,他便神魂顛倒、無法自拔,以至于在舞會上變得更加局促緊張。大使夫人是加爾各答最美的女人,卻公然與年輕男子麥克·理查遜保持情人關系。長相丑陋的副領事由于愛上了永遠無法得到的人而陷入極度的絕望中。當情感的沖動沖昏了理智,他失態地向大使夫人表白。遭遇拒絕和羞辱后,他當場失控大聲尖叫,向鄰居家發瘋一般地開槍,最終被安保人員強行拖出舞廳。實際上,《副領事》中大使夫人安娜-瑪麗·斯特雷特的形象對于杜拉斯的讀者來說并不陌生。在早先出版的《勞兒之劫》中,勞兒的未婚夫正是因為在訂婚舞會上對這位大使夫人一見鐘情、難以自拔而當眾背叛和拋棄了勞兒,與這個年長女人雙雙離去。杜拉斯在《勞兒之劫》中對安娜-瑪麗的形象進行了細致的描寫:她那“舉手投足一動一靜中的優雅”令人不安,身穿“一襲黑色連衣裙,配著同為黑色的絹紗緊身內襯,領口開得非常低”。她有著一頭棕紅色的秀發,如同海上夏娃。這個極度性感、風姿綽約的女人帶著“死鳥般從容散漫的優雅”與“發自身心的果敢”走入了未婚夫麥克的視野。杜拉斯在此處用大段的篇幅、華麗的辭藻展現了一個不折不扣的“femme fatale”(法文,意為“有著致命魅力的女人”),不禁令人想起王爾德筆下令希律王神魂顛倒、言聽計從的莎樂美,和古希臘神話中擁有一切天賦并令男人瘋狂的潘多拉。因此在《副領事》中,杜拉斯并未花費多少筆墨對這個充滿魅力的女人進行描寫。這體現出《勞兒之劫》的文本在對《副領事》的理解和闡釋中起到了關鍵的互文性效果,使得《副領事》中的人物形象更加豐滿,情節發展也因此變得合乎邏輯。
與此同時,《勞兒之劫》的文本與小說《副領事》和電影《印度之歌》之間的互文性聯系也體現在對勞兒當年的未婚夫麥克·理查遜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在《勞兒之劫》中,杜拉斯只向讀者交代了麥克是大地產主的獨子,無所事事,卻讓原本性情冷漠的勞兒情竇初開,陷入了熱戀之中,不惜中斷學業與之訂婚。而麥克這一形象真正呈現在讀者面前,是在1975年拍成了電影的《印度之歌》中。麥克作為大使夫人的情人也出席了使館的舞會,始終伴隨在大使夫人左右。這個由英國青年演員克勞德·曼扮演的男子英俊、高大,風度翩翩,非常紳士,有著耀眼的金發和湛藍的眼仁。此人物一登場,《勞兒之劫》的讀者們便可以立刻明白勞兒這個情感上極為淡漠的少女為何會對他一見傾心,以至于在被他拋棄后陷入瘋狂。
此外,《勞兒之劫》中的舞會與《副領事》和《印度之歌》中的人物情感也存在互文性聯系。《勞兒之劫》中,十九歲的勞兒親眼目睹未婚夫愛上大使夫人無法自持,想要挽回愛情卻無能為力,因為她深知當安娜-瑪麗進入到麥克視線的那一刻起,麥克的眼中便不再有她這個未婚妻。因此她只能在舞廳的角落里靜靜注視這一切的發生,仿佛經歷著一場暗無天日的凌遲。直到凌晨舞會結束時,眼看著未婚夫跟隨者安娜-瑪麗毅然決然地離去,她終于爆發了,尖叫著喊著毫無邏輯的話語,最終昏倒在地。對于勞爾來說,這是一場因愛而產生的絕望。而這種絕望在年輕副領事身上有一種近乎同質的體現。《印度之歌》中,安娜-瑪麗在無意間成為副領事的一生所愛。當她無情地拒絕和蔑視副領事的表白,這種打擊對于年輕副領事來說其程度不亞于《勞兒之劫》中親眼目睹愛人背叛給勞兒帶來的折磨和摧殘。一場“無法挽回的愛”和一場“永遠得不到的愛”,其本質都是注定令人絕望和瘋狂的愛。這種愛令人戰栗、瘋狂、喊叫,無論對于脆弱的勞兒還是對于年輕的副領事,都是毀滅性的,因此他們才會有相似的反應。杜拉斯或許有意或許無意地向我們展現了愛與絕望的二重奏,勞兒與副領事看似演繹著各自不相干的故事,實際上卻訴說著同樣的悲劇。通過勞兒的瘋狂,我們可以理解副領事的瘋狂;通過副領事的絕望,我們可以理解勞兒的絕望。這便是《勞兒之劫》與《副領事》和《印度之歌》之間更為深層的互文性聯系。
三、結語
至此我們可以發現,杜拉斯《印度系列》作為其先后發表的五部作品的集合,并不單純意味著人物的重合和故事背景的相似。從首先發表的作品《勞兒之劫》展開,杜拉斯通過其他四部作品進行了補充、續寫、擴展和交代,使得每一部作品似乎都無法成為獨立文本,必須結合其他幾部作品才能得到較為深入、合理的闡釋。因此,對“印度系列”的整體解讀和分析應建立一種向心的圓圈思維模式,《勞兒之劫》為中心文本,《愛》《副領事》《印度之歌》及《恒河女子》則圍繞著《勞兒之劫》進行滾動輸送。《勞兒之劫》的故事脈絡和人物性格、情感不斷向周圍幾個文本進行投射并提供基礎參照,而其他幾個文本也對《勞兒之劫》進行有機反射、補充。與此同時,作為外圍的四部作品之間也存在著極大的內在關聯性和動態互補性。五個文本間的互動關系并非單一、單向、平面的,而是豐富、多向、立體的。
實際上,文本之間的互文性聯系是基于符號的游戲,也是語言的能指與所指之間能動、巧妙的相互作用關系。《印度系列》中五個文本之間互相為彼此的“鏡子”,如羅蘭·巴特所說,“在一個本文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種多少能辨認的形式存在著其他本文”,在每一個文本的能指背后都蘊含著由五部作品共同砌成的具有豐富內涵的所指。正因為此,以互文視角闡釋杜拉斯的《印度系列》才具備某種意義上的必要性。也只有基于互文性理論的文本分析,才能為杜拉斯的“印度系列”提升可讀性與可研究性,使廣大讀者與文學研究者充分意識到其偉大與精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