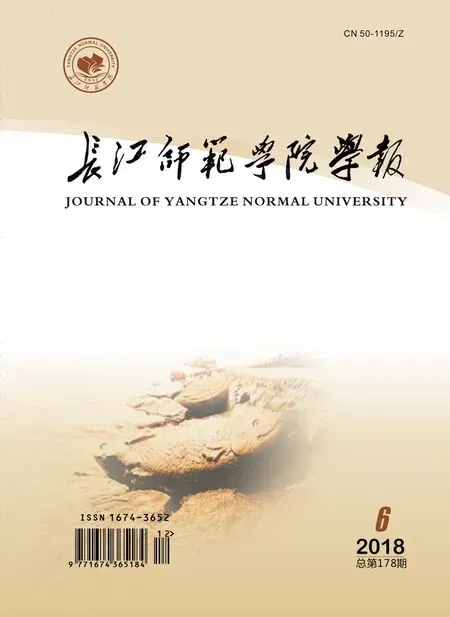民國時期來川女傳教士的角色審視
——以華西協合大學為中心
王 銳
(上海大學 文學院,上海 200444)
傳教士研究是一個具有重要學術和現實意義的話題,國內外學術界出現了大量相關成果。在傳教士群體中,女性傳教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相比較而言,關于女傳教士研究仍存在著不足:首先,女傳教士研究較男傳教士數量少,其性別角色往往被忽視;其次,研究具有區域性意義的四川女傳教士的成果更少,且大多只簡單論述其事業及影響等,未仔細從性別角色角度探討;最后,國外的研究成果大多站在西方的立場,缺乏中國的研究視角。本文聚焦于民國時期四川地區的女傳教士群體,以華西協合大學為中心,以“女性”角色為切入點,考察女傳教士在各項事業中、閑暇時的社會觀察中的表現,以及她們與男性傳教士、四川女性的碰撞,進而探討她們的性別優勢、限度和四川社會的影響。這有助于我們進一步了解、認識四川女傳教士,并為其他地區女傳教士的研究提供借鑒。
需要說明的是,1910年3月11日,華西協合大學正式成立。1911年,受到四川保路運動的影響,華西協合大學的教學一度停滯,直到1913年恢復教學。1950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華西協合大學,1951年,人民政府從外國教會手中正式收回了教育主權,華西協合大學改名為“華西大學”。因此,以華西協合大學為研究中心的時限大致與民國時期(1912—1949)時間一致,但是受傳教士個人生平的影響,本文的“民國時期”與嚴格史學意義上的民國時期有略微的出入①民國時期是從中華民國建國(1912)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1949),而本文的“民國時期”大約要追溯到民國建立之前的若干年。。
一、民國時期女傳教士來川傳教的概況
1901年12月31日,重慶海關海恩斯(W.C.Haines Watson)在一份關于十年(1892~1901)重慶海關情況的報告里提到,來川傳教的人數每年都在增長,且女性傳教者居多,并統計到英、美、法、加等國有九大教會在四川境內活動,男女傳教士共有315人[1]。到1910年,“外國教會增加到十三個,傳教士增至五百一十五人”[2]7。到1920年,在四川地區的傳教士有543人,其中女傳教士339人。1910年,由加拿大英美會,英國公誼會、圣公會,美國浸禮會、美以美會五大教會團體聯合主辦的華西協合大學成立,成為這個時期傳教的中心,“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傳教士以華西協合大學為基地,開始向四川地區開拓布道、教育、醫療事業”[3]12。傳教士留下了珍貴的歷史文獻、檔案等,他們不僅是四川地區教會大學的創辦者與教育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四川政治風云變化的見證者、醫療與衛生事業的開拓者。
(一)女傳教士來川傳教的原因
1.民國政府、四川軍閥的支持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宣告成立,就任中國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及不少革命黨人都曾有基督教信教背景。1912年3月,孫中山在致函教友康德黎夫人時說:“我們正在謀求中國實行宗教自由,而在此制度下,基督必將繁榮昌盛。”[4]同時蔣介石與其夫人宋美齡同為基督教徒,蔣曾命四川軍閥保護傳教士,“1927年2月25日,蔣介石令軍閥劉湘部確保外人的生命財產安全”[5]。鑒于此,四川軍閥為了“親近”蔣介石,紛紛保護傳教士。1927年,在軍閥劉文輝給華西協合大學畢啟的一封信件中,他承諾將保護“外人”,特別是華西協合大學外籍教員的生命財產安全[6]。因此,較為寬松的環境使得傳教士們紛紛到四川各地進行傳教。
2.四川地區傳教活動對女性傳教士的需求
1877年,因中英《煙臺條約》的簽訂,英國基督內地會在重慶設立了四川第一個布道點,此后許多差會來到四川,并且1899年的華西傳教會議“緩解了各派教會的矛盾,協調了關系,調動了傳教士的積極性……四川各地基督教呈現出旺盛的發展勢頭”[7]。這吸引著各地傳教士包括女傳教士來到四川。1878年,克拉克夫人成為第一位來到四川的女性傳教士,加拿大女傳教士饒珍芳(Muriel J.Hock?ey),也就是下文提到的伊莎白的母親“先后于1912年、1913年來華傳教,1915年在成都結婚”[8]377。饒珍芳屬于加拿大衛理公會華西會。
基督教認為,婦女占到人口的一半,要完成基督世界,婦女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在四川地區,婦女當然是一個人數眾多的群體,且由于婦女本身的特征與家庭位置,容易受到教義的感染,并在家中潛移默化地影響其他家庭成員。因此,各差會非常重視對四川婦女的傳教。但是由于傳統封建禮儀的束縛,如“男女授受不親”“男女有別”“男女不可同堂”等,男傳教士不便于對四川婦女進行教義的宣揚。于是,各差會派遣大量女傳教士給四川婦女進行教義宣講。由于女傳教士們能更容易接近婦女,接近她們的生活,并“消除四川婦女的憂慮和戒心”[9],從而達到傳播教義的目的。
3.大部分已婚女傳教士隨丈夫來到四川進行傳教
四川地處中國西南邊陲地區,地理位置獨特,“蜀道難,難于上青天!”正是對四川地區特殊地形的形象描述。但是這塊土地擁有數千萬的“異教徒”,使得源源不斷的西方傳教士跨過千山萬水來到這里。女傳教士莫爾思夫人(A.K.Morse)和其丈夫醫學傳教士莫爾思來到四川時,曾繪下了長江三峽的艱險圖貌。19世紀末20世紀初,“基督教各差會大力向中國西部發展勢力,一批又一批為實現‘中華歸主’的傳教士涌入四川”[2]5。對于一部分已婚女傳教士來說,像莫爾思夫人跟隨自己的丈夫一起來到四川傳教也是自然而然之事。
當傳教士在成都興建華西協合大學之后,英美會的客士倫和他的夫人入住了“華西壩”(華西協合大學建成以后,“華西壩”這個名字就有了)。據載:“1902年2月,一個陰雨蒙蒙的下午,一對外國夫婦搬進了在這里的新家。”[2]15像這樣跟隨自己的丈夫來到四川的女傳教士還有羅成錦夫婦(Robert?sons)、麥爾生夫婦(Carsons)、杜煥然夫婦(Stewarts)、周芝德夫婦(Johns)以及啟爾德夫婦,她們都陸續居住在華西壩,并成為華西協合大學的老師。在華西壩住宿環境的不斷改進之下,“公誼會的石恒勵夫婦(Silcocks)也來了,還有美以美會也搬來了柯理爾小姐(Miss Clara Collier)和約斯特夫婦(yosts) ”[2]16。
(二)來川女傳教士的身份、目的及指導思想
民國時期來川的女傳教士,由于傳教事業在醫療、教育等方面的發展,對女傳教士的要求也有所提高。華西協合大學的女傳教士教職員工畢業于其國內著名的院校,擁有豐富的學識,“華西協合大學的教員都是由各教會選派,分別來自英、美、加三國,所代表的有劍橋、牛津、多倫多、耶魯等西方院校”[3]12。如華西協合大學的加拿大英美會女傳教士啟希賢是醫學博士、美國衛理公會女傳教士滿秀實是芝加哥大學皮膚科專業畢業的高材生。
女傳教士來到四川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傳播教義,利用自己的性別優勢更好地傳教;另一方面可能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價值,她們試圖證明,作為女性,一樣可以像男性一樣有一番作為,渴望真正的男女平等,“赴海外傳教,猶如拓荒探險,雖險猶榮,能得到社會的肯定,心理的補償”[10]。何況,當時以華西協合大學為傳教基地,能夠為來川女傳教士實現價值、得到社會肯定。除此之外,很多已婚的女傳教士來到四川,可能更多是為了相夫教子。
“婦女工作為婦女”思想是這一時期女傳教士來華傳教,也是來川傳教的指導思想。貝內特認為:“女性傳教士通過教育,培養中國女性成為醫生和護士,使中國女性能在封建傳統為女性所限定的角色之外發揮自己的作用。”[11]因此,來川女傳教士把自己在國內的帶有“女性主義”特征的思想,即女性也可以有作為的思想帶給她們,而深受傳統封建思想迫害的四川婦女就成為女傳教士的傳教對象,使她們能夠在教育、醫療、慈善事業等領域有所作為。
二、民國時期來川女傳教士的“女性”角色
(一)布道、教育事業中的“女性”角色
1.布道事業中的“女性”角色
女傳教士大多成為男性傳教士布道的“助手”,特別是已婚的女傳教士往往是其丈夫的助手。但她們發揮了“女性”角色特有的魅力,如能更好地接近女性,這是男性傳教士所不能及的。華西協合大學的傳教士,雖然受不同教會的派遣,但是“他們‘為主作功’的目的是相同的,不僅以自身的言行、舉止,如家庭禮拜等,著力表現基督人格與生活,而且直接地對學生進行基督訓練”[2]23。如當時任華西協合大學教師的啟真道和費爾樸(D.L.Phelps)等就在家中組織英文查經班等,主要是吸引學生的參加,而這時候就需要發揮女傳教士“女性”角色的作用。啟真道等人組織查經班的同時,由“外籍師母聚集喜歡唱歌的學生,訓練唱詩班,慶祝圣誕節等”[2]23。“外籍師母”亦指男性傳教士的夫人,可見在布道中,女性傳教士確實扮演著助手角色,以自己的“女性”角色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女傳教士以自己“女性”的角色面向四川地區的婦女,在四川婦女參加集會、廟會時進行布道,以及通過邀請到家庭、創辦婦女圣經學校等進行布道。論者指出:“成都婦女有一種特別的嗜好,好游廟者十分之七。”[12]于是女傳教士利用性別優勢,向她們布道,“我們在集市的這一天舉行基督布道會來吸引婦女入教,同時我們也直接進入婦女的家庭來宣傳基督”[13]。在《華西教會新聞》中,女傳教士Miss L.M.在總結1918年綿竹地區的基督婦女工作時表達了上述做法。
女傳教士除了進入婦女家庭布道,也邀請婦女來到自己的家庭中布道,向她們介紹教義內容。在進行家庭式的布道時,更能夠看到女傳教士作為“女性”對四川婦女的影響,從四川婦女的反應可以有所了解,“如果唯一的基督教女傳教士能夠在這里多待上兩年時間的話,我也許就不會剃發成為一個尼姑”[14]。從創辦于1934年的成都協合婦女圣經學校畢業的學生,大都從事著與教會事業相關的工作,這樣一來既培養了女性基督布道員,又使得這一部分的四川婦女有了工作,并獲得了一定的工資酬勞。
2.教育事業中的“女性”角色
女傳教士創辦了一系列的女子學校,招生的對象是一些貧困或被遺棄的女孩。成都華美女子中學在建校初期,招收的多為處于社會下層的女孩,并且“許多剛入校的學生,學校提供食物、衣服和路費等”[15]。對于這種情況,女子學校受到很多四川人的歡迎,因為這減輕了很多家庭的負擔,使很多原本不能夠讀書的女孩有了一定的出路。1924年,華西女子教會大學成立并與華西協合大學進行合作教育,女傳教士們在該校任職,教授學生醫學、教育、藝術等方面的內容。1928年,任教于該校的達伍娜(Miss Downer)為藝術系的學生教授鋼琴,并且“同事發現達伍娜把時間與精力都用在了女子大學的教學和華西協合大學外語系的管理上了”[16]。像達伍娜這樣的女傳教士有很多,她們培養了一批具有現代意識的女性人才。
女傳教士從事的教育類別不同于男傳教士。根據“華西醫科大學及其前身在校的外籍教職員表”[17]統計:女傳教士劉延齡夫人(AGnew.M.C)、楊濟玲夫人(Best.G.C)、啟希賢、啟爾德的夫人以及她的女兒啟靜卿在醫科供職;安德勝夫人(Anderson.E.M)、白明道夫人(Mrs.Bayne.P.M)、布禮士夫人(Mrs.Brace.A.J)、客士倫夫人(Mrs.Carscallen.C.R)在文科供職;林則夫人(Lind?say.A.T)在圖書館供職……經統計發現華西醫科大學的外籍志愿表中,其工作基本上集中在醫科、文科、圖書館、英語,其中從事文科和醫科的較多,而只有兩位女傳教士即徐維里夫人(Sewell.H.G)和丁克生夫人(Mrs.Dickinson.F)在理科供職。男傳教士的工作領域除了涉及在醫科、文科、圖書館、英語之外,還集中在理科、牙科、行政部門、宗教、教育,特別是學校行政部門和宗教科,這些工作幾乎全部都是由男性傳教士擔任,如下文提到的伊莎白的父親饒和美,于1928年“出任華西協合大學的教務長”[8]2。因此,華西協合大學一些重要的行政部門和關乎基督傳教的宗教科都由男傳教士主導,女傳教士主要從事醫科、文科和美術等學科的教學,比如1934年華西協合大學的美術系系主任為女傳教士安德勝夫人。
基于華西協合大學任教的傳教士對中國做出的貢獻,他們經常受到政府的嘉獎,但大多數都是男性傳教士。據載:“政府褒獎牙科創辦人林則(A.W.Lindsay),博物館創始人戴謙和(D.S.Dye);畢啟更是因為多方面的貢獻,先后受到袁世凱以及國民政府的嘉獎與褒獎。”[3]從華西協合大學傳教士人事檔案來看,“華西協合大學并不給予傳教士的妻子以薪水,不管她是否在大學任教”[3]。因此,客觀地說,在教育事業中,女傳教士在很多方面都處于一種弱勢或者被忽視的狀態,雖然西方宣揚男女平等,但女傳教士的待遇低于男傳教士,“戴德生給予十余名英國女性以極低的待遇后,令她們深入內地”[18]。在女傳教士群體里面,差會也給予未婚傳教士以更多的支持。華西協合大學的教師大多由英、美、加各差會指派來校,加拿大英美會女傳教士啟希賢是啟爾德的妻子,她和莫爾思等人是華西協合大學醫科的創始人,“1914年,她與莫爾思等人創辦大學醫科,任藥理學、毒理學教授”[2]75。作為醫科的創始人之一,啟希賢擁有卓越的醫學學識和作為西方“女性”的一種敢于挑戰困難的魄力,這就不同于傳統的中國女性,打破了中國傳統社會“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
(二)醫療、慈善事業中的“女性”角色
1.醫療事業中的“女性”角色
由于民國時期的中國婦女囿于傳統意識,是極不愿意讓外國男性醫生醫治疾病的,當時的華西協合大學的醫科匯集了一批學識淵博的醫學教師,并且從事著醫療、護理的工作,啟爾德家族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據載:“有些家庭二三代人都在華西壩傳教任職,如啟爾德家族三代人都先后在華西從事醫學教育和醫療、護理工作。”[2]52啟爾德的妻子啟希賢,是加拿大英美會的女傳教士,也是醫學博士,“1896年,她在成都惜字宮街創建仁濟女醫院,是四川最早的女醫院,為婦女治病”[2]75。女醫院希望將教義傳達給每個來看病的婦女[19]。她專為婦女治病,為四川婦女來醫院就診提供了方便,體現著女傳教士身為“女性”的優勢。此外,很多傳教士家族幾代人都留在了四川,除了本身傳教的目的,她們兼顧著孕育下一代的職責。在醫療事業方面,除了西方的女傳教士的貢獻之外,還有受到教義感染的中國女教徒的付出,而華西協合大學第二任校長張凌高的女兒張君儒便是一個。張君儒是虔誠的基督教公誼會徒,原來屬于美國美以美會,“張君儒是一位杰出的兒科大夫,她早年在成都惜字宮女醫院工作,后來創辦四川醫學院兒科”[2]56。
女傳教士的供職單位主要是在有關婦女的科室與部門,如婦科、產科,擔任護士等,這可能和她們自身性別有關,也和四川地區婦女的特殊狀況有關。如美國衛理公會女傳教士滿秀實,她“看到四川女性生產多沿用舊習,于是她深感有推廣接生新法之必要,立即返回美國學習產科專業,畢業后回到四川”[20]614,并創辦了婦產科醫院。由于她們從事婦科、產科,減少了四川婦女疾病的痛苦,提高了四川婦女的醫療條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幼兒的健康。由于女傳教士創辦的女醫院是專門針對四川婦女的,因此就職醫生的工作科室也多由女性負責,“英國女醫生盧華棣為進一步擴大在潼川地區的醫療事業,建成新婦女醫院,醫院設有住院部、產科接生室和隔離室等”[21]。在醫療事業中,女傳教士針對四川婦女的需要,主要從事婦產科,并在此基礎上創辦了很多護士學校,吸引四川婦女來學習。
2.慈善事業中的“女性”角色
女傳教士的救助對象也是從“女性”角色出發,主要針對婦女與兒童,創辦了慈善性質的孤兒院等。據載:“1911年,蘇格蘭福音會在四川開設的孤兒院里有十二名孤兒,其中一名是來自農村的女盲童。她原先是由其祖母照顧,然而在祖母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后,由于家庭的貧困,祖母把女盲童交給了教會,她相信教會能夠照顧好自己的孫女。”[22]這說明四川婦女還是比較信任女傳教士的。位于閬中的圣公會福音女孤院,“1904年由澳大利亞女傳教士貝永光創辦,收養被遺棄的女童并教她們學習文化等,1931年由美國女傳教士賈美玉主持”[20]480。除了以上的例子,還有很多類似的孤兒院,確實救助了不少四川地區的孤兒。
(三)來自基督世界的女性觀察者:伊莎白(Isabel Crook)與《興隆場》
1.伊莎白在四川的情況及《興隆場》背后的故事
1915年12月15日,伊莎白出生于成都的“加拿大傳教士家庭”[23],一出生就與華西協合大學結緣。其父饒和美在華西協合大學文科任教,其母饒珍芳接受華西協合大學的安排,管理當時的成都私立弟維小學,并且新設了一所幼稚園。父母在四川的停留使伊莎白從小生活在四川。1933年,伊莎白返回加拿大學習心理學與人類學。1938年,伊莎白決定回到四川作人類學調查。1939年,伊莎白回到成都,得到教會的資助,“開始在四川阿壩理縣附近的一個少數民族村莊進行社會調查”[23],她說:“雖然我從小受的是基督教育,但我一直關心的不是教義,而是人,特別是那些窮苦的人。”[23]
興隆場屬于璧山縣,民國時期屬于四川,現隸屬重慶市。在興隆場的鄉建實驗區進行社會調查是伊莎白的任務之一。1940年,“加拿大婦女差會批準伊莎白在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工作,任務之一就是在鄉建合作實驗區調查研究適合鄉村教會發展的道路”[8]378。伊莎白在理縣進行社會調查期間,“相遇著名的社會學、人類學家晏陽初、李安宅、葛維漢等人,并參與在興隆場的鄉建實驗區,這是抗戰時期四川鄉建運動的一部分”[24]。值得一提的是,另外一位華人女傳教士俞錫璣,當時以“‘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農村工作部工作人員的身份,前往四川”[8]376。最后伊莎白與俞錫璣在興隆場的鄉建實驗區相遇了,開始了題為《興隆場》的社會調查。《興隆場》是抗戰時期關于興隆場農民生活的社會調查,也是伊、俞兩人嚴謹觀察的結果。
2.基督世界觀察者“女性”角色在《興隆場》的體現
作為一份社會調查,《興隆場》是由伊、俞兩人觀察到的興隆場世界組成的充滿了“本真性與樸實感”[25]251的作品。通過這部作品,可以看到來自基督世界觀察者“女性”角色的一些特殊表現。
19世紀40年代,興隆場是處于抗戰大后方背景下的封建世界,充斥著“男女有別”等封建思想,這些本來對于社會調查是極其不利的。但是,伊與俞幾乎沒有遇到什么難題,她們在書中淡及她們進行調查的優勢有:“調查者本人均為女性,且長期共處之后已為當地人所認同。”[8]6伊與俞因為性別優勢不僅可以親密無間地接觸到興隆場的女性,也能夠接觸到中小家庭的男性戶主與年輕男人。這樣的特殊優勢使伊莎白與俞錫璣能夠開展自己的事業,除了社會調查之外,還開展教會事業,如開辦幼兒園、婦女識字班等。伊莎白在當地福音堂開設貧民千字班,免費招收當地貧困孩子并教他們識字。據伊莎白當時的學生曹洪英回憶,“在她十多歲時,有一個外國女人來到她家,叫她去學校讀書,而這個人就是伊莎白。來到學校之后,班上四十多人全是女生,伊莎白在學校教授文藝課”[26]。另一個學生張敬文回憶,“伊莎白時常圍一根圍巾,說話總是輕言細語的,很喜歡交朋友并在長隆回龍橋認了一個名叫朱顯珍的干姐姐”[26]。
角色認同使基督世界的女性觀察者觀察到更多關于女性的問題。伊與俞在角色認同的驅使下不自覺地關注女性并傾向將女性作為受訪者。有論者指出,“童養媳問題在《興隆場》一書中有大量記述”[25]251,并涉及到休妻賣妻、偷情亂倫等問題,關于婦女在家中的地位、婚姻狀況,與婆家人、丈夫之間的關系問題也記錄得比較多,如“孫陶氏的故事”[8]41。當然也觀察到重男輕女的社會現象,如將女嬰溺水等。此外,由于婦女喜歡談論家長里短、婚喪嫁娶、生老病死等,“從其口中更容易聽到對于生活艱辛的訴苦與抱怨”[8]5,這就彌補了觀察的不足,從而增加更多的資料。伊與俞有一位好朋友,是她們雇來幫忙的彭嫂,書中對她的描述是“年近50的彭嫂是個寡婦,認識的人多,消息靈通”[8]6。于是,她們從彭嫂那里得到更多不為人知的消息。
由于伊莎白與俞錫璣同時都是傳教士,她們在興隆場的觀察中,會著重記錄到有關教會的事物,如圣誕節與教堂,教會在醫療、教育事業方面的作為,教會與興隆場基督教徒和百姓的關系,教會與政府之間的關系等。在醫療事業方面,來自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的護士朱小姐經常給興隆場的婦女接生,興隆場的百姓有什么病情,也愿意主動去診所找朱小姐。在教育事業方面,衛理公會在璧山縣開設了璧山淑德女中,很多想讓女兒接受新式教育的家庭就將孩子送在這里。同時,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也開辦了幼稚園,并有當地的女教徒在里面幫忙做事。很多時候教會也會擔當起仁慈基督的角色,如幫助生產后無人照顧的產婦等。
不過,教會與百姓的關系似乎也是復雜的,很多百姓會向教會尋求幫助,如找教會幫助逃避兵役[8]304,由于教會有著特殊的政府背景,可能鑒于這種原因,很多百姓會假裝是基督教徒。
3.來自基督教世界的觀察者性別角色比較
女性傳教士觀察到的世界在很多內容上能夠深入到百姓生活的內部,特別是更加容易接近婦女。在華西協合大學任教的男性傳教士徐維里(W.G.Sewell)的《龍骨:一個外國人眼中的老成都》一書,主要描述的是19世紀20年代成都普通百姓的生活故事,如挑水夫、賣花女、剃頭匠、農夫、農婦等。《龍骨》對四川女性的描寫大多是宏觀的、客觀的,比如彈棉花的家庭主婦、細心養蠶的農婦們、絡絲繅絲的婦女、磨黃豆的妻子等[27]。伊莎白與俞錫璣共同完成的《興隆場》則是從“女性”角色出發,因而更多地觀察到有關女性的問題,如上文論述過的“童養媳、休妻賣妻”等問題,這可能由于作者能以“女性”身份與四川女性接觸,并從她們那里得到很多有用的信息。但是,他們都能觀察到當時四川女性大多是被封建教化毒害的群體,徐維里在書中說道,“那個時代的特征是傳統社會仍在茍延,婦女絲毫不被提及,女孩在家中幾乎不算數……她們只是男人延續家庭的附屬品”[27]139。因此,作者在《興隆場》一書中始終透露著對四川女性悲慘境遇的認識與同情。
(四)女傳教士眼中的民國“亂世”景況
民國時期,四川地區處于抗戰大后方,女傳教士深入四川農村開展了廣泛的社會調查。伊莎白的《興隆場》是一份關于抗戰時期四川地區農民生活的調查,書中寫道:“那時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正處在相持階段,兩年前國民政府剛剛被迫遷都重慶,將四川作為指揮全國抗戰、向各戰場輸送人力物力支援的大后方。”[8]2在這樣的情況下,四川農村經濟處于崩潰的邊緣,但是“下江人”的到來也創造了巨大的商品和市場。因此,“1938年至1942年是帶給他們大動蕩、大艱苦、也是大希望的五年”[8]2。作為“女性”傳教士的伊莎白在書中如此描述當時四川農村地區的情況,表現了她對當時的政治時局有一定的了解與關心。伊莎白還說:“我從小就經歷過四川地區的軍閥混戰,還經常撿子彈殼玩,因此并不害怕戰爭。”[23]筆者認為這體現了一位女傳教士面對政治動亂的一種氣魄,除了抗日戰爭,伊莎白也經歷過軍閥混戰,以至后來的解放戰爭與新中國建設。事實上,在抗日戰爭中,女傳教士與女基督教徒也參與其中,“成都基督教女青年會與成都市婦女會等12個婦女團體,組織抗日宣傳隊到城鎮動員婦女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28]101。
三、性別的優勢與限度:來川女傳教士的社會影響
(一)來川女傳教士作為“女性”對四川婦女的感情
女傳教士與四川婦女之間建立起了類似于“姐妹情”的關系,能夠從“女性”的角度去關注同情當地婦女。在川女傳教士工作的對象是廣大同性姐妹,她們秉承基督平等、博愛的精神介入社會現實,比如反對纏足、納妾、重婚等一系列惡習。
隨著對四川感情的加深,很多女傳教士將其視為自己的第二個故鄉,沖破了傳播教義這一層動機。比如伊莎白,盡管她多次回國,但大半生在中國度過。伊與她的女學生始終都有著書信之間的聯系,自第一次到四川璧山縣興隆場之后,后來的幾十年里她曾多次回到這里,與自己的學生見面,如上文已經提到伊莎白在興隆場學生的回憶以及她的一個干姐姐朱顯珍。
(二)性別的優勢:來川女傳教士的社會影響
第一,在教育實踐中,女傳教士利用性別優勢,創辦了四川地區最早的女子教育。女子教育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三常五綱”“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牢籠枷鎖。女傳教士無論是作為教員還是工作人員,能更好地與女性學生接觸,使教育事業得以順利進行。因此,在女傳教士創辦的教會女子中學、大學中,如當時著名的華西女子教會大學和成都華美女中等,誕生了一批具有現代意識的四川女性。這在客觀上提高了四川婦女的知識水平,沖擊了封建傳統社會中國不合理的教育制度。民國時期的四川婦女“就是這樣在耶穌基督的福音中開始接受現代啟蒙教育的,教育啟女性之心智,去女性身上千年塵垢”[29]26。除了專門的女子教育,各差會的女傳教士還利用性別優勢創辦了很多婦女識字班,使處于社會底層的婦女具備了一定的文化程度。民國時期出現的職業女性,相當一部分來自于教會女子學校,她們畢業以后主要從事與傳教、教育、醫療等相關的職業。
第二,在布道與慈善事業中,來川女傳教士因是“女性”,所以更加關心與同情四川的同性姐妹,女傳教士針對處于社會底層受到纏足傷害的婦女,大力宣傳反對纏足,“近12個月內,在本縣四鄉分發天足會書多冊,且張貼天足會單于城內之墻壁通衡,律眾觀覽。本城教會不準父母纏小女之足,而父母亦樂順從”[30]。啟希賢也曾“擔任成都天足會的會長,積極宣傳廢除纏足的惡習”[31]41。同時女傳教士反對納妾、重婚、童養媳等,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會風氣,提高了四川婦女的社會地位,使她們不至于完全處于“男權”之下。并且,一部分女子在女傳教士開辦的女子學校中畢業后,有了正當的職業,這證明了“女性”也可以如男性一般在社會上有一席之地。
(三)性別的限度:來川女傳教士的社會影響
由于基督教傳教士主體仍然是男性,女傳教士不可能獲得與男傳教士絕對平等的權利,這一時期活動于四川的女傳教士也是如此。因此,受自身教義的影響,女傳教士在倡導四川女性解放有其局限性,也受到其性別的限制。
第一,在教育實踐上,女傳教士雖然能夠利用性別優勢做出一定的貢獻,但性別的限度也導致一些弊端,限度來源于基督的教義與身為女傳教士的職責。首先,基督女學教育目的有其明確的宗教性,即將在教會女校就讀的女孩培養成“本地”的女傳教士、合格的中國基督教妻子與母親。其次,教會女校的課程設置,也包括其他教會大學都設置了宗教課程并從事一些宗教活動,比如華西協合大學在創辦前期設置了宗教課程,直到后來四川政府接收了華大的教育權。因此,教育事業帶有很強的傳教目的,女傳教士在任職期間是沒有辦法超越的。
第二,女傳教士在解放婦女、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中的作用有明顯的限度。女傳教士受到保守福音派思想的束縛,她們“輸出女性主義,而非女權主義”[32]。她們充分認識到中國的封建傳統的長久影響,并不主張四川婦女追求真正的男女平等與女權,而是更多地希望皈依基督的四川婦女成為一位賢妻良母。女傳教士幫助四川婦女免受纏足、童養媳等的毒害,讓她們走出家庭與深閨,擁有可以與男性同樣的機會,但這大多并未涉及到女權與封建傳統,女傳教士也認識到傳統意識的強大,且很難輕易改變。
第三,在實踐中,女傳教士雖有性別的優勢,但四川地區的傳統觀念與基督有很大的差異,所以不免有其限度,“當傳教士為老鄉們哄搶印有《圣經》故事的傳單而歡欣鼓舞時,卻很快發現他們只是為了用這些紙張來糊鞋底”[2]8。很多百姓受到自身知識水平與封建傳統思想的束縛與制約,無論男女,還不能接受基督福音,在很多時候她們參與教會活動只是為了得到基督福音施與的一些小便宜,比如免費的食物等。所以,女傳教士性別上的優勢存在一定的限度。
四、結語
民國時期,來川傳教士以華西協合大學為基地開始向四川地區傳播基督教義,作為來川傳教士的組成部分——女性傳教士有其自身的特點與作為。由于當時來川女傳教士人數眾多,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群體。
女傳教士到四川大多是因為傳教事業的需要,但是筆者認為她們更多的是為了實現在國內不能實現的理想。無論是在教育醫療和慈善事業中,還是作為觀察者,女傳教士都有其自身的“女性”角色,這種性別角色突出表現在與四川女性的交往中。女性傳教士來到四川后,性別優勢使之能夠更好地接觸到當地女性,開展一系列與女性有關的教育事業與解放婦女的活動,這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封建觀念習俗,培養了一批具有現代意識的四川女性,提高了她們的社會地位。當然,女傳教士畢竟是傳教士,因此她們無法逾越這重身份。所以,在很多實踐活動中,仍有著明顯的基督教烙印。總而言之,在民國時期,女傳教士在四川的各項事業中扮演著一個具有多重功能的“女性”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