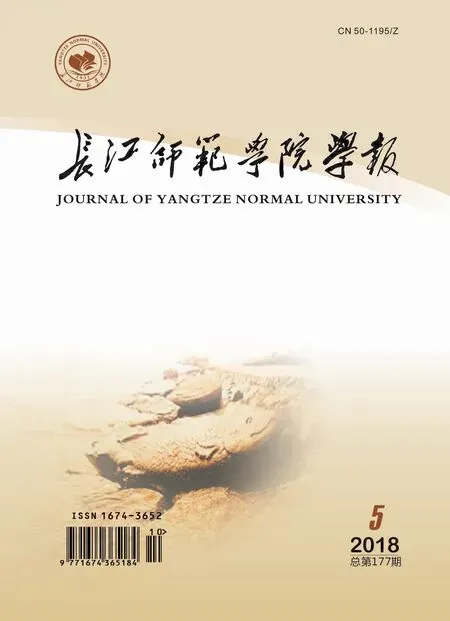“天理”、圣人與學者
——朱子“圣人觀”的基本建構
王新宇
(香港科技大學 人文學部,香港 999077)
朱子說:“圣人是人與法為一,己與天為一。”[1]1474“天理”是理學“自家體貼出來”的“天道”,學者則代表著一切有志于“學為圣人”的普通人,圣人溝通二者之間,為天人關系的核心與紐帶。在朱子哲學中,天人關系不僅表現出鮮明的理學色彩,又兼取古今學術之通義,而形成自己獨具特色的天人之學,這些思想與圣人之學相結合,便組成了朱子心目中的圣人。本文意欲以天人之學為討論的重心,描述出朱子“圣人觀”的基本建構,同時亦可會通我們對于朱子天理學說的認識。何謂“觀”?觀者,諦視也,從這個解釋上講,說“圣人觀”又是頗不恰當的,因為圣人之于儒者,絕不僅僅是一個“觀想”的對象,如同佛教信徒之觀想法門,而應該是孜孜不倦的學習、修養過程。然“觀”字畢竟設置了一個彼我之間的主客區分,即儒者與圣人之間,確乎存在一個距離,這個距離是可以通過學習與修養所拉近的。關于朱子“圣人觀”的研究,正是立足于此:儒者與圣人,當然存在一個距離,但這個距離的拉近不在其他,而正在于學者自身之“學為圣人”。學者的標準是圣人,而圣人所遵循的,莫非天理而已。
一、圣人與天理
(一)圣人本天
“圣人本天”,語出二程。伊川曰:“《書》言天敘,天秩。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圣人本天,釋氏本心。”[2]可見伊川此語本是為了說明儒釋之別。事實上,這句話可以成為理學乃至儒學的一個諦當注腳。這里的“本”意即“以天為本”,圣人是以天為源頭的,在理學則是“天理”。而包括佛教在內的一些學術,其源頭可以說是“心”,而“天”的超越意義幾乎沒有或者說轉為其次。這即造成了不同學術對于“圣人”定義的差異性,其后的心學之所以與程朱理學有異,也在于其以“心”為本的特征。“圣人”作為一種人格,不僅僅是儒學或是中國學術的孤義,各大學術傳統都有“圣人”或是類似“圣人”的概念,并以“圣人”作為人格之典范與表率,但儒家、理學的“圣人觀”之獨特處,首先便在于“圣人本天”。圣人的根據和源頭不在超自然的神,不在覺悟的心,而只在“天”。讓我們再回到伊川的那句話,他說:
《書》言天敘,天秩。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
“天敘”語出《尚書·皋陶謨》:“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孔安國曰:“天次敘人之常性,各有分義,當敕正我五常之敘,使合于五厚,厚天下。”[3]151“敘”同“序”,五常作為人的道德本性,其源頭則為天的秩序所規定。二程以“天理”綰合之,“天理”即“天”之理則、秩序,二程之說,可謂稽古而來。天有是理,非惟圣人可以循而行之,然圣人之行,即《中庸》所謂“安行”,故能為“道”。普通人利行、勉行,皆是跟從圣人所循之道,而圣人之道,即本于“天理”。可見,“圣人本天”不僅說明了圣人的源頭,也同時說明了此源頭的特性。“天”提供了至善的法則,而成為萬事萬物的根據和來源,即“天理”。理學家之所以如此定義“天理”,是依據于他們對天地生成變化的深刻認識,朱子在《大學或問》里有一段經典的表述:
在學生“互動解疑”過程中,教師要穿插到各個小組中根據組內交流討論的情況進行適時的指導點撥,重點關注技術動作重難點的解決情況和需要展示的問題。
何為“無心”處?“無心”處即是我們此前一再強調的天地、圣人之“無為”。何為“有心”處?“有心”處便是圣人與天地同樣具有“成化”之效。我們需要同時明白“無心”與“有心”,才能明白為何在“無為”的德性中,化成了這一至善豐滿的人文世界。理學家當然不會像道家那樣順著“無為”繼續說下去,乃至于“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9]15,而一定要在“無心”之中說出“有心”。天地以生物為心,圣人則亦同此一心,這顆心便是“仁”。這便將“天理”下貫為人心。因此,在朱子、在理學家的心目中,圣人即是這樣一個上合天地、下化人文的形象,而這個形象一定是充滿了一顆溫熱的仁者之心的。也只有如此,圣人才不至于高高在上,乃至于“不可為”,而能成為每一個愿意“學為圣人”的學者效法的對象。
何種經濟決策事項屬于“重大”呢?即重大決策事項、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項目安排、大額度資金的使用,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三重一大”,通俗的理解“重大”主要是講兩個方面,一是金額的大小,金額還分是預算內的資金預算外的資金;二是事項的性質的嚴重程度,針對全校性的和某一個群體的都屬“重大”。而我們審計“重大經濟決策事項”主要是審查學校的重大事項決策制度的制定和執行情況,學校重大事項決策制度是否建立健全,包括:(1)是否明確了論證研究的內容和程序。(2)是否根據重大事項的種類、范圍和金額標準細化決策權限和決策程序。(3)是否制定了相應的執行跟蹤、監督檢查和責任追究等保障制度。
朱子意,天地之間莫非陰陽二氣和五行的分離結合,陰陽五行是“氣”,是造化的材料,萬物皆以之而成。陰陽五行又必須“有是理”,此即所謂“太極”,是造化的來源和發動者。“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1]1,此“理”在天即天地生生之意,在人則有所謂“健順仁義禮智之性”。這是依據儒學傳統所發展而出的天地人物的生化觀。圣人作為人物之“出類拔萃”者,當然也由這樣的條件孕育而成。只不過圣人是“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于其間”[5]1,將此“天理”之至善完滿地充實于己身的人。因此,無論圣人是怎樣完滿的人格,都必須是根本于“天理”的。同樣我們亦可說,只有完滿地體現了“天理”的,才可謂之“圣人”。
綜合世界馬拉松大滿貫賽事來看,成功的馬拉松賽事需要挖掘城市文化內涵,依托合理的路線設置,采用專業的賽事運營團隊和強烈的服務意識,結合慈善活動塑造賽事品牌,獲得商業青睞來尋求馬拉松賽事的長久發展。
不僅如此,“圣人本天”是圣人得以確立的前提,更決定了人的學習方向。朱子說:
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為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后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為甚”者,皆謂此也。若不于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為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為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于理乎?且如釋氏擎拳豎拂、運水般(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為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為主宰,故不免流于自私耳。前輩有言,圣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6]1288
此段論人修養之方甚詳。圣人“安行”,在人則需“窮理”,否則便無法“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5]1。朱子意,人在學習時須先窮理,然后此心乃有所準則。考其源頭,則因為“圣人本天”,圣人將“天理”自然做到了極致,成了所有人的榜樣。那么學者既然是“學為圣人”,也必須像圣人一樣以“天理”為準則,來規范自己的心。如果只是以己心之是非為是非,則難免流于自私,也失去了圣人之學的基本原則。明了于此,我們便可以更加清楚為何理學要以“格物窮理”為最基本的修養途徑。每一件事物都蘊含了“天理”,圣人之所以為圣人,正是將事事物物之理都通明于心,同時以此而為出處之準則,學者效法圣人的最好方法,就是像圣人那樣去做到“明理”。
又寫作“留幕”。《釋名·釋衣服》:“留幕,冀州所名,大褶下至膝者也。”這里“留幕”指的是冀州這個地方稱“大褶下至膝”這種服飾為“留幕”。也就是說,衣服的“大褶”覆蓋了膝蓋,蘊含了“覆蓋”這一義項。《駢雅訓纂·卷三》:“留幕,大褶衣也。”考其音韻地位:留,屬來母尤韻,“絡”,屬來母鐸韻。“留”“絡”一組詞的韻部聯系屬“旁對轉”,讀音同樣相近,因此可以判斷,二者為一組連綿詞。
(二)圣人與天合德
“圣人本天”,除了說明圣人的源頭與依據以外,還彰顯了另一層重要涵義,即:圣人與天理是自然合一的,也即伊川所說“循而行之,所謂道也”。圣人最好地履行和實現了“天理”,故而在圣人這里,“本天”的另外一面即是合于天,圣人在各個方面都表現為與“天”的一致性。與漢儒在“自然”義上說明天與人的一致性不同(將漢儒之說一概視之為陰陽五行學說下的延伸實為不妥。“人副天數”中所蘊含的道德性是無法忽視的,然而無可否認的是,相比宋儒以“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聯系天人,漢儒的側重畢竟有所不同),宋儒更多是從“道德”義上立說,而圣人即是在德性上與“天”最為融合的。這一特征在理學中十分顯著,而其淵源可以說在經典中比比皆是,理學無非是將此道理講明而已。圣人將“天理”做到了極致,則自然表現出“天”所能表現出的一切德行和作用,而說明這一一致性,無疑便成為溝通天人的最佳途徑,因為人只有在窮盡了“天理”之至善的時候,才能將自身的德行完滿地顯現,這也就是《易》所言的“與天地合其德”[7]96,即周子(周敦頤)所說的“立人極”[8]6。《易》與《中庸》是宋儒最為關注的直接闡釋天人之學的經典,而朱子“圣人觀”在圣人與“天理”關系上的根據,亦來自于它們。
例如,朱子之注解《中庸》時不斷突出了圣人與“天理”同一的特質。《中庸》曰:“薄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5]35薄厚、高明、悠久皆是天地之道,而載物、覆物、成物都是天地之用,這里雖然是說天地之道的“至誠無息”,但是圣人之道已經包含在其中了,故而朱子在注解這一部分的時候,用了“圣人與天地同用”“圣人與天地同體”來結合天地之道。而《中庸》引《詩》之后以“文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作為結尾,亦可見其雖是“言天道也”,但同樣是在“言圣人之道”。朱子在注解《中庸》之時多次體現了這一特點,如其中部分章節雖是“言人道也”,但同樣是“圣人之道”的表彰。可見,圣人是溝通天人的樞紐,在德行上圣人與天地同體同用,故圣人與天地一般有發育萬物、化成人文之用。朱子在解上文所引“與天地合其德”一段時也說:
人與天地鬼神,本無二理。特蔽于有我之私,是以梏于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無私,以道為體,曾何彼此先后之可言哉?[7]96
氣化爐高壓氧氣切斷閥主要用于氧氣輸送管路以及氧氣吹掃管路快速關閉或者開啟。由于介質是氧氣,具有助燃性能,閥門一旦發生熱量累積、泄漏等,容易引發燃燒甚至爆炸,從而會嚴重影響裝置的平穩運行,因而氣化爐高壓氧氣切斷閥對閥門的密封性能、材料選擇、使用壽命等性能有非常嚴格的要求。
人生于天地,本來即是“無二理”的,這是自然之道。在現實情況之下,卻只有圣人做到了“無私”“以道為體”,因此惟有圣人與“天理”相合。普通人“蔽于有我之私”,在“天理”之間摻雜了氣稟與物欲,難以完滿地體現之。這既是造成圣凡之別的原因,也為“圣人可學”打開了門戶。《易》與《中庸》作為表現“圣人同天”的最佳范例,將圣人在德性上與“天理”的一致性刻畫無余,朱子也用了極大的努力來使得這一特征在自己的注解中體現出來。
(三)圣人有心而無為
圣人與“天理”在德性上的同一性,使得圣人體現并完成天地之德,而此過程則同樣因為二者的同一而表現為一致,即與“天”一樣,圣人的一切行為和表現都是“無為”的。《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圣人也。”[5]31“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作為圣人的特質是非常顯著的。朱子注曰:“圣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5]31圣人之德與“天理”為一,體現為這一“無為”的特征。不僅僅在德行上如此,事業上亦然。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5]163朱子注曰:“無為而治者,圣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5]163圣人與“天”一樣,在化育萬民之時都是無所作為的。這個意義不僅在朱子處是如此,在整個中國學術的傳統中也比比皆是,《老子》所謂的“我無為,而民自化”[9]154也是此意。
在前期研究中,首先以日語假名為序,抽取了原始詞匯庫中所有IT領域新詞。根據“硬件類”“軟件類”“一般技術類(操作與使用)”“專業技術類”等進行內容分類,建立日語詞庫。然后逐一核對并確認日語詞庫中各詞所對應的漢語詞匯,建立漢語詞庫。最后通過數據處理統合為“漢日語IT領域新詞對比詞庫”(下稱:“對比詞庫”)。本文所探討的“IT領域新詞”,只限于計算機應用與信息技術層面的新詞,不包括網絡傳播及網絡交流層面的各種“網絡語言”及“網絡流行語”。
相比《老子》而言,在朱子這里更加鮮明的特質是,在首肯圣人之無為之時,一定要突出圣人之“有心”,此即“圣人有心而無為”。此語同樣出自二程,伊川曰:“天地無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無為。”[1]4透露出的意思有兩層。前一層意思便是在說“圣人與天合德”,圣人與天地呈現出了一致性,即天地雖然無心,但卻“成化”,此即天地之心;圣人雖然有心“成化”,但卻“無為”,此即圣人之心。第二層意思即是要明白圣人之所以為圣人處。人皆有心,但只有圣人可以“有心而無為”,這即是因為圣人完滿地體現了“天理”,于是“圣人之心”才能夠成為一顆“無為”之心。圣人的這顆“無為”之心并不是毫無作為,而只是像天地一樣“無心成化”,好像什么都沒有做,但卻什么都完成了。《中庸》曰:“《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5]40“篤恭”即是“無為”,“天下平”即是“成化”,朱子謂之“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5]40。
現階段,主管部門并沒有安排統一的管理人員,不能對基層地區的小型農田水利工程進行針對性管理。工程建設完畢后,后期缺乏有效的維護與管理不僅會造成資源嚴重浪費,還會極大的影響水利技術的發展。
合同歸口管理部門已提報的合同進行跟蹤督辦,提高審批時效性,可規定全流程最長審批時間以控制審批過程。如遇特殊、緊急合同需當天審批完成的,可由承辦部門向歸口管理部門提出說明及督辦申請,由歸口管理部門進行緊急督辦。
那么,既然圣人與天地同有“無為”之能,為什么需要突出“有心”呢?為什么說“圣人之有心”即圣人之所以為圣人處?圣人和常人一樣,一定有“心”,但圣人之心卻表現出“無為”的特質,因而能夠與天地合德。又因為圣人本天,天地也自然有一個“心”在那里,雖然天地事實上是“無心”的,但“無心”卻能成化,正好說明了天地的“有心”,天地之“心”即天地之主宰義。“無心”的天地造化出了山川四季、人文萬物,不正說明了天地也有一顆生生之心嗎?由此可見,天地與圣人都兼具了“有”“無”兩方面,說“無”,是為了言其“無為”之德,說“有”,則是為了言其“成化”之功。所以朱子要說:
綜上,我們可以知道,“圣人本天”是朱子“圣人觀”的首要前提,如果不以“天理”為準則,不僅圣人沒有了一個認定的標準,學者也將沒有了一個效仿的對象。如果人人都以自己心中的是非善惡為唯一標準的話,就將導致理學最為擔心的后果,因為常人之心,難免為“氣稟”所雜,而儒學一直以來遵循的“天道”法則也將失去意義。朱子的“圣人觀”即可謂沿著這條儒學傳統中最基本的方向而來,只有確立了“圣人本天”的前提條件,才能繼續展開對圣人的體認和學習。
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說不得。[1]5
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后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后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后有以為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后有以為魂魄五臟百骸之身。……[4]507
總之,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國玉米育種水平和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有著巨大的上升空間。因此,要有效地改善玉米育種水平,就必須要進一步重視玉米育種工作,并且需要加大資金投入和技術引進,只有這樣才可以更好的解決問題,突破瓶頸,真正的實現增產增收。
以上一節,筆者對圣人與“天理”的關系做了一個簡單的梳理。圣人首先是根本于天的,這是圣人的依準,若無此依準,便不能理解圣人的標準和原則。其次,圣人與“天理”是具有同一性的,這個同一性在朱子處鮮明地體現在德性上,圣人作為德性上的完滿者最好地體現了純善無惡的天理。在此同一性之下,“圣人有心而無為”的特質則將理解推進到更加深刻的層次。圣人與天地一樣都是“無為”的典范,但卻“有心”,這是圣人參贊天地化育,同時作為人文世界的最高楷模所必須的屬性。圣人之心將天地之德內化為人的德性,并進一步具體為諸多的道德條目,從而成為學者們效法的指標。朱子心目中的圣人是一個表現“天理”并與“天理”合而為一的人格形象,同時又具備了一個化成天下的功用和仁者之心。事實上,此圣人的標準是極高的,因為“本天”與“同天”絕非輕易可以取得,但這并非意味著無法達到,這顆“圣人之心”便成為溝通其與普通學者的媒介。下面便將順此而討論圣人與學者的關系,以見朱子的“圣人觀”是如何貫穿天人而建成其基本架構的。
二、圣人與學者
圣人作為天人關系之間的紐帶,一邊是至善無惡之“天理”,一邊則是“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5]3的常人。上節我們已經探討了圣人與“天理”的關系,本節則將重點論述圣人與“學者”的關系。此處之“學者”并不僅僅限于理學家們或是傳統世界中的士大夫,一切有志于從事“圣人之學”或欲“學為圣人”而未能的人都可以算作“學者”,而并不以此為志的人當然也符合“民之秉彝,好是懿德”[10]284,只是其心尚且處于“有時而昏”的狀態,“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5]3,故而也算在“學者”之列。
圣人與學者的差別,體現在“理”與“氣”、“理”與“欲”的距離上,而理學所希冀的修養目標,即是“心與理一”的狀態,學者之所以未能達到這一狀態,原因即在于“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分析這兩個方面,將是研究學者所以不同于圣人的重點。再者,雖然學者可以通過修養達到“心與理一”的目標,但是圣人的境界仍舊是不易企及的,正如天與人之間畢竟有所差異,這是多種因素導致的必然結果,在理學則體現為對“圣賢之別”的討論。“圣賢之別”是朱子學的重要課題,也成為理學家們體認圣人的重要方式,而賢人相對于圣人而言同樣屬于“學者”,故而在本節的最后將重點提及這一題目,以完成朱子“圣人觀”之基本建構。
(一)氣稟與人欲
“氣稟”與“人欲”并論,見于朱子《大學章句》首章對“明德”二字的注解,朱子曰: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5]3
到了家門口,蔣大偉把車停好。鄭馨跟蔣大偉走到門口,他叮囑鄭馨:我媽要問你是誰的話,你就說是顧客。鄭馨說:我本來就是顧客。蔣大偉說:我媽要問為啥把顧客帶回家來了?你就說錢包丟了!鄭馨看了他一眼,沒說話。蔣大偉又說:我媽要是再問為啥把顧客帶回家吃飯,你就說——鄭馨生氣了:不就是吃你一碗面條嗎?不讓吃拉倒!扭頭就走,蔣大偉急了:回來!想跑是不是?你跑了我找誰要錢?好好,你愿咋說咋說。
“明德”為天所賦予人的純善無惡之性,在人之心則為明德。以理論之,每個人心中的明德都應該是光明不昧的,如寶珠一般。然而現實的情況是,不同的人因為氣稟的限制,再加上人欲的蒙蔽,往往使得此一光明照徹的“明德”昏昧不明,如寶珠之陷于泥沙。雖然從人性皆善的根本義上說,“明德”并不會因此消失,但現實上的昏昧則是難以避免的,而這正是造成常人不同于圣人的原因。所謂:
以理言之,學者若能變化氣質,“以復其初”,則必定可以拉近甚至消弭掉自己與圣人之間的距離,從而達到“心與理一”的狀態,成圣的目標就此達成了。然而在朱子看來,圣人絕非如此輕易就可以做到,甚至可以說,圣人是極難做到而竟至于做不到的。非但如此,圣人本身也會因為時運、氣數、稟賦等等的差異而各自存在著限制:
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資,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況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其可勝言也哉![4]507-508
此兩端實在是常人通往成圣之路的兩大障礙,朱子以“理氣”“理欲”分言,也正是為此。二者相較,氣稟之拘更多是被動性的,因為不同的人本就具有不同的氣稟,類似于今天我們所謂的“性格”。周子將人的氣稟分為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即是此意[8]32,惟圣人可以得其“中”。孔子四位高足各具一性之所偏,“愚魯辟喭”,也是如此。因此理學要講“變化氣質”的工夫,來矯正每個人氣稟之偏,而恢復一理渾然的狀態。
相比于氣稟,“人欲所蔽”則更具有積極性。所謂“欲”,類似于張子(張載)所說的“攻取之性”,即今天所說的“欲望”。“欲”之說也具有悠久的儒家傳統,孟子所謂“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聲也,有同聽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5]336。此即人所具有的普遍的欲望。欲望為人人所有,雖圣人亦不能無,而“人欲”則更甚一層,“人欲”是人陷溺于欲望之后果。“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1]224再明白不過。圣人所以不同于學者的地方,并不是在于圣人“無欲”,而在于圣人之欲正得其“中”,如孟子所舉的“公劉好貨”“太王好色”的事例。常人則欲過其度,使之變為成圣的阻礙。
這實在是一件無可奈何之事,所以宋儒以前,讀書人只要做一賢德君子即可,至于或賢或愚,或明或暗,乃由“才性”決定之,非人力所可扭轉,宋儒發明圣學之功,則在“變化氣質”。故朱子引舉陳了翁之語:
只是氣數到那里,恰相湊著,所以生出圣賢。……[1]80
近期我國電力工業的發展,仍然是以燃煤發電為主。由于燃煤機組不斷完善,電廠規模不斷擴大,導致粉煤灰排放量急劇增長。1985年火電廠排灰渣總量達3 768萬t,到1995年增加到9 936萬t,到2007年粉煤灰排放量達到3億t。按全國平均計,每增加10 MW裝機容量,每年將增加近萬噸粉煤灰的排放量。到2010年粉煤灰排放量已達到3.3億t。按目前的排放狀況和利用水平,沖灰用水量和儲灰廠占地將增加一倍,分別達到30多億噸和6.6萬多平方米。對于我們這個水資源缺乏、可耕地人均占有率很低的國家來說,如何作好粉煤灰的利用和處置確實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在對學生進行“你選擇職業的主要依據是什么”的問題調查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經濟收入,占41%;其次是個人價值的體現,占36%。總的來看,畢業生就業和擇業趨于務實。
人之稟氣,富貴、貧賤、長短,皆有定數寓其中。……[1]81
氣稟與人欲——正因為有了這兩方面的阻礙,圣人與學者之間就產生了深刻的差距,而“學為圣人”也必定不會是一條輕易的路,更不消說氣稟與人欲往往還會聯系在一起。如朱子說漢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為”,但同時卻又“不能勝其多欲之私”[1]3226,這兩方面其實存在著深刻的聯系,不同的氣稟會造成不同的人存在著相異的欲望,漢武帝“天資高,志向大”,但因為“無真儒輔佐”,以至于天資、志向不能很好地導向正理,這一看似褒義的氣質反而成為“多欲”的憑借。除此之外,人的氣稟因為是消極地領受,又常給人以命定之感:
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1]69
這句話,幾為理學家之共識。而學者所以能打通這條成圣之路,向著圣人邁進,也正是得益于“道學之功”,雖然氣稟與人欲無論矯正哪一個,都絕非易事,但朱子的偉大貢獻,則在于正視二者存在于絕大多數人這一事實的同時,義無反顧地勇敢變化之。言其難變,為圣人難做之事實;言其可變,則為“天理”賦予每個人所當有的可能。我們須同時明白這兩點,才能于明辨圣人與學者之別的同時,扎實做著“明明德”的工夫。這也是朱子“圣人觀”帶給每一個“學者”的期許和激勵。
(二)圣賢之別
在瞬態短路工況,阻尼系統的負荷能力按考慮,對應額定容量相間不對稱突然短路的最高溫升和溫度值分別為72.2 K和125.2 ℃;單相對地不對稱突然短路的最高溫升和溫度值分別為65.7 K和118.7 ℃。
上古天地之氣,其極清者,生為圣人,君臨天下,安享富貴,又皆享上壽。及至后世,多反其常。衰周生一孔子,終身不遇,壽止七十有余。……[1]79
此言圣人因不同時代的氣數而有時運、遭際之別,說明了圣人之間亦存在著氣稟的偏差。對此孟子已有明言,孟子說:“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5]365堯舜湯武同為圣人,已自有此分別,而且這個分別是極其醒目的。我們前面一再說過,圣人是自然地做到“與天合德”的,所謂“安而行之”,那為何還會存在一個“身之”的過程?可見即便圣人之間也難免存在不同。朱子釋之曰: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5]365
同為圣人的湯武也需要從事復性的工夫,但他們確實是儒家傳統所公認的圣人。如果加上后一句“五霸,假之也”,則更好理解。堯舜湯武雖有性之、身之之別,然“及其成功一也”,與五霸相比,圣人在德性上表現出無可挑剔的一致性。堯舜湯武之間,可能只是圣人分量的差異,而與五霸相比,則是是與非、理與欲的迥異,這二者之間是絕難同日而語的。何況,孔子已有“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5]68之語,圣人之別,從來是儒家傳統所正視不諱的,而這也成為朱子“圣人觀”的重點。
不獨如此,孟子對于圣賢之別的論述還有很多,例如,孟子一面傾慕伯夷、叔齊、柳下惠,認為他們都是圣人,一面又說:“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5]242可見二者氣稟皆有所偏。有的儒者解釋說“隘與不恭”并不是為瑕疵夷惠而發,而是二子之流弊所至,也就是說并非批評二子有此偏失(此明道語:此非瑕疵夷惠之語,言其弊必至于此)。朱子卻說:
世之所謂清者,不就惡人耳;若善辭令而來者,固有時而就之。惟伯夷不然,此其所以為圣之清也。柳下惠不屑之意亦然。夷隘,惠不恭,不必言效之而不至者,其弊乃如此。只二子所為,已有此弊矣。[1]1299-1300
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必有不恭處。道理自是如此。孟子恐后人以隘為清,以不恭為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1]1300
隘與不恭,是二子氣稟之偏本來如此,孟子以“圣之清者”“圣之和者”來形容他們,也存在這個意思。朱子此論,只是就事論事,并不因此而貶低伯夷、叔齊與柳下惠作為“圣之清者”“圣之和者”的圣賢之資,而同時亦從他們氣稟的偏失處,對學者的修養工夫起到了警戒的作用。這也是宋儒喜論圣賢氣象的第一重意思,“見賢思齊”,且賢者本身的氣稟之偏也正恰可以成為學者自己修養時的教材。如朱子注《論語》“賢賢易色”章曰:
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茍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5]50
朱子先說賢賢易色、事父母、事君、與朋友交死者乃是“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可見子夏所突出此四者確為修養、學問所首重的。于是朱子說,能做到如此的人,不是“生質之美”,就是“務學之至”。“生質”即稟賦卓越,自然如此者,如圣人;“務學之至”則是所有人都可以通過修養、學習做到的。朱子將此兩方面包括在內,可謂立言之謹,也使得子夏這句話的義理得到了充分的顯豁。然而子夏身為大賢,立言不免因其氣稟之偏而有所弊,《論語》中數見不鮮,此處也是。故而朱子在最后引吳氏之說曰:
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辭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于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后為無弊也。[5]50
這里便將子夏此語的缺失以及可能造成的流弊都說出來了,比較孔子的“行有余力則以學文”便能更加體會二者的差別。朱子在這里細心體認子夏之語的重要意義,同時不忘將其與圣人之言進行比較,以見圣人之圓融與大賢之棱角,這就是宋儒體會“圣賢氣象”所要做的工作,也是第二重意思。體會“圣賢之別”是為了更好地把握“圣人氣象”,從而更清晰地展現圣人之所以為圣人的種種特質,而對賢者進行正直而不失忠厚的評判,并不妨礙學者向賢者學習。因此,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朱子承襲了儒家傳統以及理學家們體認圣賢氣象的方式,這不僅是朱子“理氣論”的必然結果,因為除了圣人以外的賢者們必然也會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氣稟之拘”。同時,體會“圣賢之別”也是理學修養做工夫的必修課程,《近思錄》以“總論圣賢”為尾篇,不僅有著“道統”相傳的意義,更是學者“切問近思”的必要內容。
本節以圣人與學者為討論的主題,重點分析了學者之所以不能優入圣域,在于其存在著“氣稟之拘”和“人欲之蔽”,造成如此結果的原因有很多,而此兩者不僅是學者與圣人之間存在距離的合理解釋,也是學者就此從事圣學工夫的出發點,如果學者一方面能夠從事“變化氣質”“存天理去人欲”等一系列理學工夫,便可以將二者的影響彌合到最小,從而向著成圣之路邁進。另一方面,氣稟、時運等因素因為天人關系的復雜原因很難消除,所以在圣人與學者之間還存在著一個特殊的關系即“圣賢之別”。賢者相比普通學者而言,已經是從事圣學工夫并更加接近圣人的人,但是他們同樣存在著種種病痛和缺失。理學非常關注這些區別,這并非有失于忠厚,而是從此來更好地體會圣人的氣象,見得圣人地步之不易,從而給修養工夫提供更多的鞭策與指引。朱子繼承并完善了這些思想,并將其融入到自己的解經與講學事業中去。
三、結語
通過以上兩個方面的論述可見,在朱子看來,圣人必須是以“天理”為源頭和根據的。圣人合于天道,故與“天理”合一,此“合一”乃是自然為之,不待修為,故而與“天理”一般,圣人也是無為的。這個“無為”是相對于常人之“有為”來說。另一方面,圣人雖無為,卻因其為人而有心,此圣人之不同于“天理”處。圣人之心將“天理”化為人心之“仁”,從而成為人文化成的主體。那么,對于學者來說,人與天的差別就表現為“己”與圣人的差別,欲想“學為圣人”,便要從事一系列的修養工夫,從而達到“心與理一”的境界。在所有從事于此工夫的人之中,賢人又是極為突出者,因此我們需要重點討論“圣賢之別”。這樣,朱子的“圣人觀”便是一個天人相貫通的整體,不僅有從天到人的向下一路,也具備了由人至天的“上達”之道,這正是朱子學問“下學上達”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