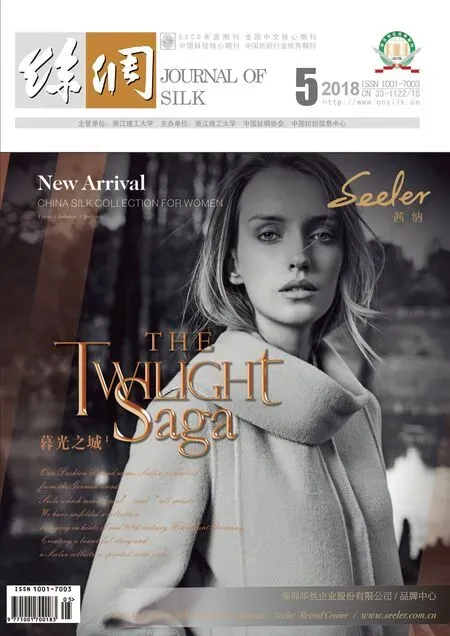從絲織品用途看唐代蠶桑政策
劉 芳, 宋 超, 張建琴, 黃世瑞
(1.山東理工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山東 淄博 255000; 2.南京信息工程大學 科學技術史研究院,南京 210044;3.嘉興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浙江 嘉興 314001;4.華南師范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廣州 510006)
中國作為世界蠶業唯一的起源地,是世界上最早發明養蠶取絲的國家[1],早在殷代甲骨文中就有“桑”“蠶”“絲”“帛”等文字[2]。絲織品作為衣之源,作為稅收之源,關系民生國計,作為絲織品源頭的蠶桑必然引起歷代統治者的重視,尤其是唐代蠶業政策有利生產發達[1]。蠶學家尹良瑩[3]先生認為:“有唐一代之蠶業,堪足稱為完美。”這與唐代統治者的蠶桑政策緊密相關。綜合看來,學術界對唐代蠶桑政策的研究尚不全面、不系統,涉及蠶桑政策的內容散見于研究文獻,其中,蠶業通史研究關注政府對蠶桑生產的政令,涉及蠶桑政策的如蔣猷龍《中國蠶業史》[4],周匡明《蠶業史話》[5],尹良瑩《中國蠶業史》[6],周云庵《陜西古代蠶桑業發展概說》[7]等論著,研究蠶桑絲綢的斷代史學者會將蠶桑發展的原因之一歸結為有利的蠶桑政策,如盧華語《唐代蠶桑絲綢研究》[8]76-81,董明《試述唐宋時期皖江地區紡織業的發展與繁榮》[9],姜穎《山東絲綢史》[10]110-112等論著。目前學術界對唐代蠶桑相關研究,尚未有蠶桑政策的專門著述。唐代是絲綢史上的高潮期,絲織品在唐代經濟與貿易、政治及社會文化生活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本文在考據唐代相關史料的基礎上,試從絲織品用途這一角度對唐代蠶桑政策進行探索,以管窺蠶桑政策概貌。
1 唐代絲織品的用途
經濟貿易方面,一方面絲織品是國家稅收的主要來源。唐代前期主要的賦役方法是租庸調,所謂庸是指可以通過繳納絹布代替力役,其時綾、絹、絁是主要稅源,《舊唐書(食貨上》載:“賦役之法: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則隨鄉土所產,綾、絹、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絁者,兼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11]2088唐后期改行兩稅法后,綾絹仍是交納的對象,隨著時間的推移,實際需要交納的綾絹更多。《全唐文》載:“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匹當錢三千二百文,今者納絹一匹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于二矣!”[12]4750另一方面絲織品在唐代可以充當貨幣,發揮流通手段等貨幣職能。唐代皇帝敕令規定錢帛兼行[13-14],其年十月六日敕:“自今已后。所有莊宅,以馬交易,并先用絹、布、綾、羅、絲、綿等,其余市價至一千以上,亦令錢物兼用,違者科罪。”[15]1627陳寅恪[16]260先生就曾指出:“唐代實際交易,往往用絲織品。”唐代不僅在國內實際交易中將絲織品作為貨幣使用,在東西方交易中也強力推行使用絲織品。吐魯番文書中的許多和糴賬目表明,在絲綢之路上唐政府以和糴方式將大量絲織品攤派給民戶。絲織品在東西方貿易中除了作為商品交易外,還會充當國際貨幣職能,趙豐[17]204先生就認為:“從當時西域的情況來看,流通著三種通貨:一是銀幣……一是銅幣……另一就是絲織品。三種通貨都符合馬克思所說的支付手段、購買手段、社會財富材料三個職能而足以充當國際貨幣。”唐代在絲綢之路上流通著大量作為貨幣的絲織品。
政治方面,絲織品可以作為軍資、官員俸祿、恩賜賞品等。絲織品作為軍資,《通典·食貨六·賦稅》載:“自開元中及于天寶,開拓邊境,多立功勛,每歲軍用日增。其費糴米粟則三百六十萬匹段,給衣則五百三十萬,別支則二百一十萬,饋軍食則百九十萬石。大凡一千二百九十萬(原文“一千二百六十萬”,有誤)。”[18]111自開元中及于天寶,絹布作為軍費支出合計1 100萬匹段,唐制:凡賜物十段,則約率而給之:絹三匹,布三端,綿四屯[19]82。折算起來,1 100萬匹段合絹330萬匹、布330萬端、綿440萬屯,絹綿合計770萬匹屯,占全部軍費1 290萬匹、端、屯,石的59.69%。絲織品作為官俸,唐代慣例,百官俸祿可以實物折充,因此,支付官員的俸祿往往會錢帛兼半:睿宗時“官員日增……太府之布帛以殫,太倉之米粟難給”[11]3062。穆宗詔令:“宜令戶部應給百官俸料,其中一半合給段匹者,回給官中所糶粟。”[15]1667太和七年一月戶部侍郎庾敬休建議:“應文物九品以上,每月料錢,一半合給段匹絲綿等。”[15]1667被采納,詔令實行。絲織品充作賞賜品,唐代賞賜物品主要指絹綿布,據不完全統計,僅《舊唐書·本紀》所記賜品中,明確提到或涉及絹帛者,凡74次,每次賞賜絹帛數從2匹至數十萬匹段不等;對一般官吏個人的賞賜,一次也是數十、數百匹絹帛不等[8]161。
社會文化生活方面,唐代服飾雖有等級之分,但上至達官貴人,下至流外庶人各等級皆可服絲織品:“三品已上,大科綢綾及羅,其色紫,飾用玉。五品已上,小科綢綾及羅,其色朱,飾用金。六品已上,服絲布,雜小綾,交梭,雙紃,其色黃……流外及庶人服綢、絁、布。”[11]1952絲綢除充當衣料,用于制作扇子、屏風、帳、被等外,還作為饋贈品及文化藝術的載體。
2 絲織品用途與蠶桑政策的關系
蠶業內部絲織品、蠶、桑是一條互為條件和相互制約的供需鏈,這三者都直接或間接受到蠶桑政策調節作用及政治文化影響。絲織品用途廣度受限于絲織品產量與質量,而絲織品的產量與質量則受限于蠶桑的產量與質量。因而絲織品的用途廣度與絲織品的產量與質量都受限于蠶桑的產量與質量,受到蠶桑政策調節作用和影響。當時絲織品尤其是高貴絲織品在經貿、政治、社會文化生活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一直受到統治者高度重視,作為絲織品基本原料來源的蠶桑生產必然需要加強政策調控。
為獲取更多更好的絲織品,唐政府出臺相關的蠶桑獎勵政策:《蠶桑萃編》[20]6b記載了唐代開元年間侍妾與宮女因養蠶獲絲甚多獲得賞賜的故事。《舊唐書逸文》[21]19b載,唐大歷年間韓景輝因為養冬蠶成繭這一創舉,獲得了終身免除徭役的嘉獎。《太平御覽》記載:“天寶年間,益州獻三熟蠶,緊厚白凈,與常蠶不殊。”[22]3675這一養蠶成就可能也與唐代獎勵蠶桑的政策有關。
唐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保證絲織品基本原料的來源,為保證政策措施的貫徹落實,唐政府將蠶繭產量與各級地方官員政績考核掛鉤。《舊唐書·尹思貞傳》中記載了這樣的一則故事:神龍初,尹思貞……出為青州刺史,任上有政績,使其所轄青州境內有蠶一年四熟,黜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八月至青州,看著青州蠶繭感嘆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于此乎!”特表薦之……奏課連最[11]3110。此則故事一方面說明各級地方官員是發展蠶桑的主要力量,其對蠶桑的重視程度直接影響蠶桑產量;另一方面說明蠶桑產量是考核官員政績的一個要素,關乎地方官員的升遷,側面反映了國家對蠶桑的重視程度。
因此,絲織品在現實生活中用途廣度與巨大需求量,影響唐代統治者對蠶桑生產的重視程度和政策調控情況。
3 唐代蠶桑政策
唐初高祖即提出了“輒有勞役,義行簡靜,使務農桑”這一指導蠶桑生產的思想,這一思想后來成為唐代最高統治者重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具體體現在倡導重蠶思想的皇帝詔敕中。為了使重蠶思想與皇帝詔敕得到貫徹落實,唐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蠶桑的政法措施,作為朝廷政策措施的執行者,唐代各級地方官員積極促進蠶桑發展,使得唐代蠶業堪稱完美。
3.1 皇帝詔敕:倡導重蠶思想的至高權威
唐初,唐高祖頒布兩道詔書《罷差科徭役詔》與《申禁差科詔》強調:使徭役有節,役民有制,使務農桑[12]33。其中《申禁差科詔》重申《罷差科徭役詔》的內容,明令如不遵詔令執行,重加推罰。唐太宗以隋煬帝擾民廢業為鑒,強調少興土木,勿擾蠶事,他認為:“多營池觀,遠求異寶,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蠶織,田荒業廢,兆庶凋殘……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12]128后世承接李世民的這一思想,為保證民得耕耘,女得蠶織,唐代皇帝頒布了許多與敦勸蠶業,勤課種桑有關的敕令。
唐代皇帝有關蠶桑的詔敕中較為典型的是常袞代唐代宗起草的《勸天下種桑棗制》[23]577,其中規定:“天下百姓,宜勸課種桑棗,仍每丁每年種桑三十樹。”帶有強制性的成分,主要目的是保證蠶食的來源,從而保證絲織品原料的供應。為保證詔令的順利執行,《勸天下種桑棗制》規定官員:“躬親勉率,不得擾人,務令及時,各使知勸。”
唐代皇帝倡導重蠶思想最具代表性的詔書當屬唐憲宗時期頒布的《勸種桑詔》[12]645,詔書開篇即強調:“農桑切務,衣食所資。”切務:急務,當務之急的意思。與《勸天下種桑棗制》對種桑的規定稍有不同,《勸種桑詔》強調:“諸道州府有田戶無桑處,每檢一畝,令種桑兩根,勒縣令專勾當。”造成不同的原因當歸咎于均田制的破壞與兩稅法的實行。與《勸天下種桑棗制》相較,《勸種桑詔》對官員勸種桑的要求更加嚴苛,不僅勒縣令專勾當,將百姓種桑情況列入官員的年終政績考核,兼令兩稅使同訪察。與《勸天下種桑棗制》最大的不同在于,《勸種桑詔》明令禁止采伐桑樹,如桑樹被采伐,“委長吏重加責科”。保證桑樹順利生長的同時,保證了桑葉供應,從而保證絲織品的順利生產。
與《勸種桑詔》明令禁止采伐桑樹相比,唐武宗在《加尊號赦文》[12]814中強調砍伐桑樹用于買賣所帶來的后果,以達到保護桑樹的目的。為滿足“給事郊廟之服,奉繭稱絲之稅”對絲織品的需要,赦文認為應該設置法律條文保證蠶桑的生長,如果不遵從,恣意買賣,就會視為違敕罪。
以上《勸天下種桑棗制》《勸種桑詔》與《加尊號赦文》均強調政府官員在勸課蠶桑中要積極作為,唐睿宗在《申勸禮俗敕》中認為勸課農桑乃是州縣長官職責中的重中之重:“勸課農桑,牧宰之政,莫過乎此。”[23]570牧宰所指乃州縣長官,其中牧指州官,宰指縣官。唐睿宗此道敕令強調州官的首要政務是勸課農桑。
3.2 政法措施:貫徹重蠶思想的基本依據
為保證“重蠶”思想得到貫徹,唐代采取了諸多勸勵蠶桑的政策措施,其中較為典型的措施是采取一切以蠶務為重,將蠶桑放在其他事務之上,這一政策措施是由蠶桑的生產規律決定的。南宋趙孟堅《采桑曲》載“桑椹紫來蠶務急”生動描述了蠶務一刻不能誤的情景,唐代統治者以詔令的形式規定農桑時節政府官員需以農桑為重,多方配合農桑,保證農桑生產按時有序的進行。唐玄宗《禁妨農詔》[12]336中明確強調將農桑放在其他事務之上,命令停止影響農桑的力役及不急之務,若農桑時節百姓有不穩便事須處置,則動用朝集使,由中書門下與所司商議后向帝王報告。
如遇天災人禍,為保證養蠶活動的順利進行,唐政府會采取開彼倉儲,時令貸給,蠲減徭賦等措施。自唐高祖始采取輕徭薄賦的蠶桑政策,根據百姓的受災程度采取不同程度的減免措施,唐代初年規定:“凡水、旱、蟲、霜為災害,則有分數:十分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租、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若桑、麻損盡者,各免調。若己役、已輸者,聽免其來年。”[18]77高祖之后的皇帝延續了高祖輕徭薄賦的蠶桑政策,且在高祖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其中尤以玄宗為甚:正值養蠶月份,河南北舊谷向沒,新谷未登,唐玄宗下《賑恤河南北詔》[12]313要求開彼倉儲,時令貸給。徐泗之間絲蠶不熟,在庸課已納的情況下,唐玄宗下《給復徐泗等州詔》[12]349,要求放免地稅。河東河北,官人職田,既納地租,仍征收桑課,唐玄宗認為田樹兼稅,百姓將不堪重負,遂頒布《禁地租外征桑課敕》[12]394命令禁止地租更征私課。《遣祠南郊華岳溫湯敕》[12]377載,唐玄宗篤信道教,遇水旱災害,憂心農桑之時,會祈禱上蒼惠及百姓。唐代其他帝王也有采取諸多勸課蠶桑的舉措,如唐宣宗針對夏州等四道土無絲蠶的實際情況,頒布《給夏州等四道節度以下官俸敕》[12]843,做出地絕征賦的決策。
為提高各級地方官員勸課蠶桑的積極性,唐代頒布了許多與蠶桑相關的獎懲措施,如唐睿宗頒布的《誡勵風俗敕》[23]570強調“又屬當首夏,務在田蠶”,首夏即始夏,初夏,是指農歷四月,正值養蠶時節。唐睿宗在這道敕令中強調,若能勿擾田蠶,使百姓安居樂業,家有余糧,會得到提升,若政績尤為突出,將得到更高的提拔;相反,若為政苛濫,戶口流移,盜賊四起而不能自治,輕者年終貶考,重者非時解替。
除政策措施外,對于種桑數量及各級地方官員按時課農桑予以律法規定,也是唐蠶桑政策措施的一大特色。中國著名蠶學家尹良瑩在其《中國蠶業史》第五節“歷代蠶業勸勵”中指出:“唐代對于桑樹,尤加保護。”[3]這一點不僅體現在前文所述皇帝詔令中,在具有強制性的唐律中也有體現,《唐律疏議·戶婚》強調:“依〈田令〉:戶內永業田,課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棗各十根以上。土地不宜者,任依鄉法。”唐律規定:“里正按時授人田,課農桑,諸里正,依令:授人田,課農桑。若應受而不授,應還而不收,應課而不課,如此事類違法者,失一事,笞四十。若于一人失數事及一事失之于數人,皆累為坐。”[26]249用刑法保證授人田,課農桑按時進行。對于累計違法者,從里正,到縣令,再到州官,均有相應的懲罰規定。種桑通過法律明文予以約束,使桑樹按時種植,并得到有效保護,保證蠶有食源,民有衣穿,國有稅源。
3.3 地方官員:落實政法措施的主要力量
唐代各級官員是落實“重蠶”思想的主力,是朝廷政策措施的執行者,其對蠶桑的重視程度,直接影響帝王“重蠶”思想發揮的效能。唐代最高統治者制定的蠶桑政策要真正得到落實,必須得到各級官員的鼎力支持。因此,唐代蠶業的繁榮興旺與各級地方官的積極作為密切相關。唐代許多地方官員任職期間重視蠶桑生產,積極作為,勸課農桑的故事,流傳頗廣,在唐代蠶業發展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裴漼是絳州聞喜人,有惠政,甚為當時所稱,人吏刊石頌之。太極元年,受自高祖以來所實施的道教政策及道教信仰的影響,唐睿宗為金仙、玉真兩公主造觀及寺等,時屬春旱,興役不止,影響蠶時,裴漼認為,春旱時節,朝廷大興土木,興役不止,使民不得務農桑,影響農桑收成,導致災情嚴重,戶口流散,進而危及社會穩定,上疏要求停造觀寺[11]3128-3129。
要使蠶桑豐收,除不誤蠶時,還須勿擾蠶務,否則會造成蠶桑虧損。劉思立,唐高宗時曾任職侍御史,員外郎,宋州寧陵人,于時河南、北大旱,敕遣御史中丞崔謐,給事中劉景先分道賑贍,劉思立在《諫農時出使表》[12]1565中詳細指出敕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贍會致使勞民傷財,強調蠶功未畢之時,詔令官員分道巡視賑贍,會延誤農桑之務,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失,諫言秋后閑時進行。
唐朝宰相來濟通過齊桓公的故事講解馭下之術時,諫言唐高宗春不奪農時,夏不奪蠶工,以此達到勿失蠶時,勿擾蠶務的目的:帝嘗從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游,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蠶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馭下之宜也。”[24]4032
《唐廬州刺史本州島團練使羅珦德政碑》[12]4884-4885中記載了廬州刺史本州島團練使羅珦在廬江勸之藝桑的故事,羅珦的德政,使廬江從“田稀翳桑”變成“藝桑畝畝”。碑文顯示,羅珦對廬江實行的是綜合治理,涉及不好學而酷信淫祀,豪家廣占田而不耕,人稀而病于吏眾,藝桑鮮而布帛疏濫等弊政,針對藝桑鮮、布帛疏的弊政,羅珦勸之藝桑,以行賞罰,最終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數年之后,環廬映陌,如云翳日。
顏真卿在《梁吳興太守柳惲西亭記》[12]3429一文記載了縣令李清請修湖州烏程縣南水亭的故事,修西亭過程中種桑畜養,盈于數萬,可謂是李清發展蠶桑的政績。《唐故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12]7822中記載了韋丹在任江西觀察使期間鑿陂灌田,益勸桑苧的故事。《魏府狄梁公祠堂碑》中記載狄仁杰:緩賦寬役,勉農勸桑[12]6302。大順時人王保和在《唐撫 州羅城記》一文中稱:“臨川古為奧壤,號曰名區。翳野農桑,俯津阛阓。”[12]8626太常奉禮郎刁尚能在《唐南康太守汝南公新創撫州南城縣羅城記》中描述撫州屬縣南城“人繁土沃,桑耕有秋”[12]8623。寶歷、大和年間,章孝標《送張使君赴饒州(一作送饒州張蒙使君赴任)》詩云:“饒陽因富得州名,不獨農桑別有營。”[25]5752袁州經韓愈等人的努力,呈現出“有村皆紡績”的景象。
4 結 語
絲織品用途廣泛,涉及經貿、政治及社會文化生活等方面,對唐代經濟社會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作為絲織品源頭的蠶桑生產必然引起唐代統治者重視,唐代統治者實施一系列促進蠶桑生產的政策措施。皇帝通過發布詔敕頒布政法措施體現貫徹其重蠶思想,依據蠶桑政法措施,地方官員積極有為保護和促進蠶桑生產,對蠶桑發展起到巨大作用。因此,正是唐代有力實施蠶桑政策,使蠶桑生產發達質量堪稱完美,從而保證絲織品滿足經貿、政治外交、社會文化生活等各方面需要。
參考文獻:
[1]劉芳. 唐代蠶業研究[J]. 自然辯證法通訊, 2013,35(5): 49-55.
LIU Fang. Study on sericul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J]. Journal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2013,35(5): 49-55.
[2]劉芳, 宋超. 唐代已有“蠶蟻”一詞[J]. 中國科技史雜志, 2015,36(3): 364-365.
LIU Fang, SONG Chao. The Tang dynasty already had the word “newly-hatched silkworm” [J]. The Chinese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5,36(3): 364-365.
[3]尹良瑩. 中國蠶業史[J]. 中央大學農學院旬刊, 1930(63): 10-14.
YIN Liangying. History of sericulture in China [J]. Journal of College of Agriculture of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1930(63): 10-14.
[4]蔣猷龍. 中國蠶業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JIANG Youlong. History of Sericulture in China [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 Press, 2010.
[5]周匡明. 蠶業史話[M]. 上海: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1989.
ZHOU Kuangming. Sericulture History [M]. Shanghai: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1989.
[6]尹良瑩. 中國蠶業史[M]. 桃園:中央大學蠶桑學會, 1931.
YIN Liangying. History of Sericulture in China [M]. Taoyuan: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Sericulture Institute, 1931.
[7]周云庵. 陜西古代蠶桑業發展概說[J]. 中國農史, 1989(3): 67-72.
ZHOU Yun’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sericulture in Shaanxi province [J]. Agricultural History in China, 1989(3): 67-72.
[8]盧華語. 唐代蠶桑絲綢研究[M]. 北京: 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5.
LU Huayu. On Silkworm Mulberry and Silk in Tang Dynasty [M]. Beijing: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5.
[9]董明. 試述唐宋時期皖江地區紡織業的發展與繁榮[J]. 中國農史, 2014(2): 54-64.
DONG Ming. Study on development of Wanjiang weaving industry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J]. Agri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 2014(2): 54-64.
[10]姜穎. 山東絲綢史[M]. 濟南:齊魯書社, 2013.
JIANG Ying. The History of Silk in Shandong [M]. Ji’nan: Qilu Press, 2013.
[11]劉昫. 舊唐書[M]. 北京: 中華書局, 1975.
LIU Xu. Jiu Tang Shu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5.
[12]董浩. 全唐文[M]. 北京: 中華書局, 1983.
DONG Hao. Quan Tang Wen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13]李埏. 略論唐代的“錢帛兼行”[J]. 歷史研究, 1964(1): 169-190.
LI Yan. On popularity of money and silk in the Tang dynasty [J]. Historical Research, 1964(1):169-190.
[14]史衛. 從貨幣職能看唐代“錢帛兼行”[J]. 唐都學刊, 2006,22(3): 1-5.
SHI Wei. Money and silk in the Tang dynasty in terms of currency function [J]. Tangdu Journal, 2006,22(3): 1-5.
[15]王溥. 唐會要[M]. 北京: 中華書局, 1960.
WANG Pu. Tang Hui Yao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0.
[16]陳寅恪. 元白詩箋證稿[M].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1.
CHEN Yinke. Yuan Bai Shi Jian Zheng Gao [M].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17]趙豐. 唐代絲綢與絲綢之路[M]. 陜西: 三秦出版社, 1992.
ZHAO Feng. Silk and Silk Road in Tang Dynasty [M]. Shaanxi: San Qin Press, 1992.
[18]杜佑. 通典[M]. 北京: 中華書局, 1988.
DU You. Tong Dian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8.
[19]李林甫. 唐六典[M]. 北京: 中華書局, 1992.
LI Linfu. Tang Liu Dian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2.
[20]衛杰. 蠶桑萃編[M].北京:中華書局,1956.
WEI Jie. Qintessence of Sericulture [M]. 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1956.
[21]岑建功. 舊唐書逸文[M]. 刻本. 1842(清道光二十二年).
CENG Jiangong. Unofficial Pieces of Jiu Tang Shu [M].Block-printed Edition.1842(Qing Dao Guang 22 Years).
[22]李昉. 太平御覽[M]. 北京: 中華書局, 1960.
LI Fang. Tai Ping Yu Lan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0.
[23]宋敏求. 唐大詔令集[M].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59.
SONG Minqiu. Tang Da Zhao Ling Ji [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59.
[24]歐陽修, 宋祁. 新唐書[M]. 北京: 中華書局, 1975.
OU Yangxiu, SONG Qi. Xin Tang Shu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5.
[25]彭定求. 全唐詩[M]. 北京: 中華書局, 1960.
PENG Dingqiu. Quan Tang Shi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0.
[26]長孫無忌. 唐律疏議[M]. 北京: 中華書局, 1983.
ZHANGSUN Wuji. The Criminal Law of Tang Dynasty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