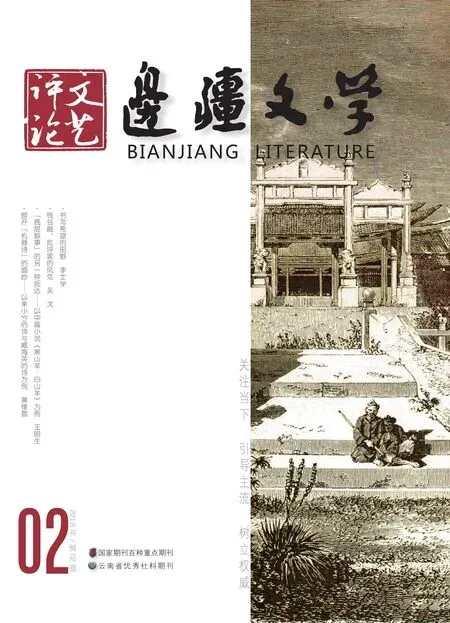掀開“機(jī)器詩”的面紗
——以來小兮的詩與臧海英的詩為例
黃維盈
熟悉詩壇的人都知道,來小兮和臧海英,其實(shí)是同一個(gè)人。“來小兮”是臧海英曾經(jīng)使用過的筆名。“來小兮的詩”和“臧海英的詩”,卻是兩個(gè)不同概念。據(jù)臧海英本人在《臧海英:我得做我孤注一擲的事》一文中披露:
“從小討厭自己的姓。2010年接觸網(wǎng)絡(luò),重新寫詩,就想起個(gè)美好的筆名,與自己不想要的命運(yùn)分開,于是有了‘來小兮’。那幾年,我躲開現(xiàn)實(shí),寫的都是虛飾出來的詩意。后來意識(shí)到不能再那樣寫下去,開始直面現(xiàn)實(shí)、死亡與個(gè)體命運(yùn)。越來越不喜歡‘來小兮’。那是2014年,我覺得我開始真正走近詩歌。
我把2014年當(dāng)作自己寫作的一個(gè)界碑。也是那一年,試著給《人民文學(xué)》投稿,打印寄去的,一周后竟然收到朱零的短信。發(fā)表前,他建議我改回本名。那組詩在當(dāng)年9月的《人民文學(xué)》發(fā)表。我正式回到‘臧海英’。現(xiàn)在,越來越喜歡我的姓。”
臧海英以“來小兮”為筆名發(fā)表的詩作,反應(yīng)平平。恢復(fù)本名后,便聲名鵲起,相繼獲得華文青年詩人獎(jiǎng)、《詩刊》新銳獎(jiǎng),參加青春詩會(huì),接連出版了兩本詩集。
2014年確實(shí)是臧海英成名的界碑。真名和筆名分道揚(yáng)鑣,不是換湯不換藥,而是創(chuàng)作理念的嬗變,文本的華麗轉(zhuǎn)身。也就是說,臧海英的成功,不是因?yàn)楦拿撬皶r(shí)擺脫了“機(jī)器詩”的梏桎,脫胎換骨,達(dá)成了鳳凰涅槃,浴火重生。
“機(jī)器詩”是我最近頻繁使用一個(gè)的概念。主要是指那些與機(jī)器人“創(chuàng)作”的詩歌高度相似的詩。這些詩最明顯的特點(diǎn),就是各自為政,隨機(jī)分行。“機(jī)器詩”的最高綱領(lǐng)是亂寫,主謂賓搭配不出問題就算大功告成。
我在多篇文章說過,判斷一首詩是不是“機(jī)器詩”,有一個(gè)辦法最簡(jiǎn)單易行。一首詩如果正讀、倒讀,或者將詩句隨機(jī)打亂,重新組合仍能讀得通的詩,這種無頭無尾、無因無果、無情無義,可以隨便攪拌成“語言糨糊”的詩,就是典型的“機(jī)器詩”。故作高深的修辭背后,其實(shí)沒有任何思想成分。
有的詩人認(rèn)為“機(jī)器詩”最大的缺陷,是不能敘事。我認(rèn)為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夠準(zhǔn)確。實(shí)際上,機(jī)器詩能敘事,只不過它的敘事只局限于一句短語,而且,這些短語之間永遠(yuǎn)是并列關(guān)系,而不是遞進(jìn)關(guān)系。所以這種詩即使怎么隨機(jī)打亂它的排列順序,都能勉強(qiáng)讀通。“機(jī)器詩”寫作和陌生化寫作,完全是兩碼事。前者是東施效顰,東拼西湊,后者則經(jīng)過了思考,注入了思想養(yǎng)分。
竊以為,來小兮的許多詩作,都可以歸類為“機(jī)器詩”。老作家苗時(shí)雨曾寫過一篇《來小兮的詩為什么不易懂?》解讀來小兮的詩。
《啞默》其中一節(jié):
鐘擺倒向夜的一側(cè)
我吞下黑暗,也被黑暗吞沒
在彼此的身體里,我們陷落,陷落到更深的黑里
某一刻,我們是一個(gè)人
食指抵在唇上。噓。不說“影子”“空”
或更多
點(diǎn)評(píng):這里的意象,“影子”與“空”,廢棄的詞,乃至肉身、唇上、食指等,不僅奇絕、濃縮,而且它們的串聯(lián),兔起鶻落,急劇地移換、銜接與流轉(zhuǎn)。然而,恰是這樣的意象和意象組合,表達(dá)了詩人的靈魂在夜的咬噬和“更深的黑里”,隨著“鐘擺倒向夜的一側(cè)”,在一次次吞沒中,終于敞開了生命的本真,直面人生的空茫與虛無……
《聽雨記》第一節(jié):
夜在咬噬
瓦罐里傳來我的嗚咽
我廢棄的詞,一遍遍跳入深水
人群里,有我無處安放的
肉身。它褪下紅裙
斜睨我的窗口、
我窘迫,與盛大的空了
點(diǎn)評(píng):這首詩,從“夜在咬噬、瓦罐里傳來我的嗚咽”,到“我廢棄的詞,一遍遍跳入深水”全過程,象征了人的青春易逝、好景難再的悲慨與自己療救。適應(yīng)此種情境,她的話語是跳脫的、激蕩的,充分揮灑了動(dòng)詞、名詞的作用,并且長(zhǎng)短句搭配靈活,婉轉(zhuǎn)有致,從歡快、熱烈,到沉寂與哀思,表現(xiàn)了一個(gè)年輕女性生命的綻開、躍動(dòng)與沉落……
《花瓣》:
在傷口里。沉醉
風(fēng),打開殷紅的那支
五天里,涂唇,涂心,涂指甲
二十天里,沉然,失血,一點(diǎn)點(diǎn)潰破經(jīng)過那里的蔥蘢,和愛
這易碎的,小狂歡
慫恿她一生的雨水,來。去
四月里,她將驚醒于一場(chǎng)分娩
她抱著空殼子,成為自己的類癥
——白藥片
點(diǎn)評(píng):“詩人創(chuàng)造的這一‘白藥片’的意象,在隱喻中,揭示了傷痛是世界的唯一真實(shí),也是生命在‘失血’和‘潰破’之外唯一的存在:我痛即我在!映現(xiàn)靈魂的掙扎、奔突、撕裂與紛亂,意象突兀、并置、連接,跨跳與轉(zhuǎn)換,疊加與對(duì)峙。由此意象群落形成不規(guī)則的組合方式,造成了一種新異的、奇特的,多維立體的時(shí)空感。這種意象架構(gòu),擺脫了生活原樣的局限,在更廣闊的虛幻中,多側(cè)面、多層次地聚合詩人的主觀意緒和心態(tài),使她獲得更大的創(chuàng)作自由。”
讀了上述評(píng)論,不知你做何感想?如果你認(rèn)為苗時(shí)雨講得確實(shí)有道理,這充分說明:那些貌似“客觀公允”的詩歌評(píng)論,確實(shí)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因?yàn)椋厦娴奈淖郑m然是苗老師原創(chuàng),卻經(jīng)過了我的“移花接木”。也就是說,我把苗時(shí)雨老師評(píng)論A詩的文字,全部套用來評(píng)價(jià)C;把評(píng)論B詩的文字,全盤移植過來評(píng)介A;把評(píng)論C詩的文字,全部用來評(píng)介B。
我之所以做出這個(gè)“試驗(yàn)”,不是對(duì)苗時(shí)雨老師不尊重,而是希望大家都能認(rèn)真反思一下:為什么會(huì)出現(xiàn)這種情況?
評(píng)論文字和作品文本完全脫節(jié),能夠隨便張冠李戴。司空見慣的解讀套路,充斥一些紙媒和平媒的版面。讀者已是耳熟能詳,見怪不怪。
贊美楊玉環(huán)的話,用來贊美趙飛燕,靠譜嗎?不靠譜。把贊美楊玉環(huán)的話,用來贊美豐腴的女人,保準(zhǔn)八九不離十。句子各自為政,不知所云的機(jī)器詩,基本上是同一路貨,所以任何寬泛抽象的評(píng)論,都能套用在它們的身上。
在這里,我之所以把苗時(shí)雨的話進(jìn)行套寫,將文字“擊鼓傳花”,不是偷懶,而是為了讓大家充分看清那些“懸浮評(píng)論”的本質(zhì)。一些頭頭是道的點(diǎn)評(píng),其實(shí)什么也沒有說——充其量只是說了一大堆正確的廢話。讀完這些騰云駕霧的評(píng)論,你會(huì)發(fā)現(xiàn),評(píng)論老鼠的詩,拿來套評(píng)大象,并沒有什么不妥。
“機(jī)器詩”亂寫,評(píng)論者亂評(píng)。這就是當(dāng)下常見的詩評(píng)亂象。讀者若不信,可以自己親自操刀,把來小兮上列三首詩,一行行重新隨機(jī)組合,變成另外三首詩,看看這些詩讀起來,是不是和原詩差不多?
值得慶幸的是,吃盡“機(jī)器詩”苦頭的“來小兮”,終于“意識(shí)到不能再那樣寫下去,開始直面現(xiàn)實(shí)、死亡與個(gè)體命運(yùn)……”沒有聽信評(píng)論者的一面之詞,沒有一條道走到黑。于是才有了今天聲譽(yù)日隆的臧海英。
來小兮的詩,大都可以隨機(jī)分行,打亂再讀;而臧海英的詩,若隨機(jī)打亂,重新分行,就會(huì)“潰不成軍”。因?yàn)椋嬲脑姼瑁撬枷氲摹安⒙?lián)”,而不是文字的簡(jiǎn)單“串聯(lián)”。這就是“來小兮”與“臧海英”的本質(zhì)區(qū)別。
《為母親守靈》:
給長(zhǎng)明燈添了燈油后,父親哭了
哭著哭著,哭成了一個(gè)孩子
抱住我哭。哭著哭著,哭成了一對(duì)兄妹
哭著哭著,哭成了兩個(gè)孤兒
在死去的妻子面前,丈夫“哭成了一個(gè)孩子”,這是夫妻情;在女兒面前,“哭成了一對(duì)兄妹”,這是父女情。丈夫失去妻子,女兒失去母親,父女二人同病相憐,“哭著哭著,哭成了兩個(gè)孤兒”。這里面的痛苦交織,哀怨交加,通過不同的角色轉(zhuǎn)換,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宣泄。挽聯(lián)式的表現(xiàn)手法,言簡(jiǎn)意賅,紙短情深,讓人過目難忘。“為母親守靈”這一主題從而得以遞進(jìn),賦形,深化,充分彰顯了詩歌的感人力量。
《城中河》:
河水污染了
我扔石塊,它吞了下去。我扔更大的石塊,它又吞了下去
我停下來。我暫時(shí)還沒有更多的石塊
臧海英的這首短詩,究竟要表達(dá)什么??jī)H僅是寫詩人對(duì)環(huán)境污染的反抗嗎?我看未盡然。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首勵(lì)志詩,是對(duì)命運(yùn)不屈不撓的抗?fàn)帯1砻娴奈锵笫恰俺侵泻印保[喻的意象,應(yīng)當(dāng)是“世間人”。我們來到世間,會(huì)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和挫折,身心遭到“污染”,于是會(huì)本能地反抗,不斷地“扔石塊”,尋求各種解決辦法。不斷地抗?fàn)帲粩嗟馗冻觯瑫r(shí)不斷地妥協(xié)。這就是人類的命運(yùn)。“我停下來”,不是向逆境屈服,向命運(yùn)求饒,而是基于“暫時(shí)還沒有更多的石塊”。全詩意境,雖然有沉重之感,但最后有了“我停下來”“我暫時(shí)還沒有更多的石塊”兩句托底,整首詩一掃悲觀絕望的霧霾,詩人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情懷和浪漫主義情懷水到渠成,呼之欲出。通過“城中河”,俯察“世間人”,我們看到的是淡泊樂觀、積極進(jìn)取的人生。沒有故弄玄虛的修辭,沒有牽強(qiáng)附會(huì)的說教。平中見奇,淡處知濃,苦中有樂。《城中河》的思想價(jià)值顯而易見。
《求救者》:
她抓住我的手
說她離婚十年,身體不好
孩子叛逆,工作又丟了
說著說著,就哭起來
哭著哭著,就緊緊抓住我的手
要我為她找個(gè)男人,找份工作
找到快樂
就像我擁有他們
就是他們
她放開我的手
傷心的背影,像一件空蕩蕩的衣服
我承認(rèn),我掏不出
自己都沒有的東西
分給她
臧海英的這首《求救者》,詩意與詩思一脈相承,分行文字的有機(jī)生成順序,誰也無法將它們隨便打亂。這就是傳統(tǒng)詩藝的力量。
現(xiàn)代的詩人,大都經(jīng)過了“詩道尊夷”這一關(guān)。我們學(xué)習(xí)西方詩歌,陌生化寫作方面建樹頗豐,豐富了詩歌創(chuàng)作的表現(xiàn)手法。但許多詩人,對(duì)陌生化寫作的認(rèn)識(shí)出現(xiàn)了較大的偏差,混淆了主觀創(chuàng)作與機(jī)械創(chuàng)作的界限,淪為徹頭徹尾的“機(jī)器詩寫作”。
“機(jī)器詩”最明顯的特點(diǎn),就是句子與句子之間,永遠(yuǎn)是并列關(guān)系。它可以敘事,只不過是東一句,西一句,純屬東拼西湊,將文字的主謂賓搭配好了,就萬事大吉;搭配得不夠好,瞎貓遇死鼠,歪打正著,出現(xiàn)一些似是而非的句子,評(píng)論家們就會(huì)如數(shù)家珍,進(jìn)行無限拔高的解讀。
而真正的好詩,句子與句子之間,應(yīng)當(dāng)是遞進(jìn)關(guān)系。源源不斷的思想注入,給讀者以無窮的遐想,無盡的啟迪。同一個(gè)詩人,不同的創(chuàng)作手法,來小兮的詩,可以隨便打亂來讀;臧海英的詩,你就不能隨便打亂。這就是“機(jī)器詩”與常態(tài)詩的本質(zhì)區(qū)別。
來小兮走過的彎路,許多詩人其實(shí)正在走。這也是那么多詩人會(huì)站出來替“機(jī)器詩”站臺(tái),竭力捍衛(wèi)“機(jī)器詩”的深層原因。“機(jī)器詩”原形畢露,這類詩人的文本深度將不復(fù)存在,面臨迅速解體的命運(yùn)。這也正應(yīng)了那句著名俗語:“海水退了,才知道誰沒穿褲子。”
竊以為,推本溯源,西方詩歌才是“機(jī)器詩”的真正源頭。縱觀一些諾貝爾獲獎(jiǎng)詩人的作品,有相當(dāng)一部分作品是“機(jī)器詩”。
2011年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得主特朗斯特羅姆的詩,是許多讀者比較喜歡的一個(gè)諾獎(jiǎng)詩人,然而他的一些代表作,卻帶有明顯“機(jī)器詩”特征。堪稱“機(jī)器詩”創(chuàng)作的范本。為了讓讀者領(lǐng)略一下“機(jī)器詩”的魔力,下面我將特朗斯特羅姆的一首代表作《憤激的沉思》隨機(jī)打亂:
原詩:
風(fēng)暴讓風(fēng)車展翅飛翔
在夜的黑暗里碾磨著空虛
你因同樣的法則失眠
灰鯊肚皮是你那虛弱的燈
朦朧的記憶沉入海底
在那里僵滯成陌生的雕塑
你的拐杖被海藻弄綠
走入大海的人返回時(shí)僵硬
倒讀:
走入大海的人返回時(shí)僵硬
你的拐杖被海藻弄綠
在那里僵滯成陌生的雕塑
朦朧的記憶沉入海底
灰鯊肚皮是你那虛弱的燈
你因同樣的法則失眠
在夜的黑暗里碾磨著空虛
風(fēng)暴讓風(fēng)車展翅飛翔
先讀一、三、五、七句,再讀二、四、六、八句:
風(fēng)暴讓風(fēng)車展翅飛翔
你因同樣的法則失眠
朦朧的記憶沉入海底
你的拐杖被海藻弄綠
在夜的黑暗里碾磨著空虛
灰鯊肚皮是你那虛弱的燈
在那里僵滯成陌生的雕塑走入大海的人返回時(shí)僵硬
先讀二、四、六、八句,再讀一、三、五、七句:
在夜的黑暗里碾磨著空虛
灰鯊肚皮是你那虛弱的燈
在那里僵滯成陌生的雕塑
走入大海的人返回時(shí)僵硬
風(fēng)暴讓風(fēng)車展翅飛翔
你因同樣的法則失眠
朦朧的記憶沉入海底
你的拐杖被海藻弄綠
這首《憤激的沉思》,無論正讀、倒讀,還是混讀,亂讀,意思基本差不多,都能讀得通。無非是八個(gè)互不關(guān)聯(lián)的句子的機(jī)械組合,按照數(shù)學(xué)原理,它可以隨機(jī)組成幾十首詩。然而,它要表達(dá)什么,隱喻什么,悉聽尊便。句子之間,并沒有構(gòu)成任何關(guān)系。所謂“憤激的沉思”,實(shí)在不知道詩人到底“沉思”了什么。詩中出現(xiàn)了意象,但并沒有生成相應(yīng)的意境。每個(gè)句子比喻中的本體和喻體,模棱兩可,含糊不清。詩人傳遞給讀者的,儼然是一張張語法修辭的“空頭支票”。這里隨機(jī)列出幾種讀法,不是跟特朗斯特羅姆大師過不去,而是希望讀者能真切地看清這些分行文字的游戲本質(zhì)。
究其實(shí),“機(jī)器詩”的通病,是一些西方詩歌最常見的毛病。詩中只要出現(xiàn)“暴君”“獨(dú)裁者”“上帝”“專制”這些大詞,馬上就會(huì)有評(píng)論家如獲至寶,蜂擁而上,搜索枯腸去提煉詩歌文本中根本不存在的“批判精神”。這情形有點(diǎn)像街頭的流浪漢對(duì)美女傻笑,我們的詩評(píng)家卻一廂情愿地詮釋為“高超的求愛技巧”。“機(jī)器詩”的機(jī)械組合,和街頭傻子“笑”的癥狀,都是一種“預(yù)設(shè)”的行為,根本沒有任何主觀思想感情可言。你硬要妙筆生花,洋洋灑灑解讀出什么“質(zhì)感”“張力”之類,讀者只好敬而遠(yuǎn)之,決不會(huì)吃不了兜著走。
我們知道,詩歌創(chuàng)作的最終目的,是言志抒情。早在一千五百年前,著名的文學(xué)理論大師劉勰,曾在《文心雕龍·情采》一文中批評(píng)過那些“鬻聲釣世”、“言與志反” 的虛偽之作,對(duì)當(dāng)時(shí)虛情假意的“機(jī)器詩”進(jìn)行了切中肯綮的批評(píng)。以下是劉勰這段話的原文翻譯:
“從前詩人的詩篇是為了抒情而創(chuàng)作;漢代辭賦的作者寫作賦頌,是為了創(chuàng)作而虛構(gòu)感情。用什么來說明這點(diǎn)呢?我們知道《詩經(jīng)》中國(guó)風(fēng)和大雅、小雅的創(chuàng)作,有情志,有怨憤,于是把感情唱出來,用來諷刺上位的人,這就是為抒情而創(chuàng)作。可是漢代辭賦的作者,心情精神并不郁結(jié)憂悶,只是隨便運(yùn)用夸張的言辭,沽名釣譽(yù),這就是為了創(chuàng)作而虛構(gòu)感情。所以為抒發(fā)感情而創(chuàng)作,語言簡(jiǎn)練,寫出真實(shí)的感情;為了創(chuàng)作而虛構(gòu)感情,文辭浮華,內(nèi)容雜亂而虛夸。而后來的作者卻學(xué)習(xí)訛濫的文風(fēng),忽略輕視寫真實(shí)的感情,拋棄了遠(yuǎn)古時(shí)代國(guó)風(fēng)、大小雅的作者的好傳統(tǒng),效法近代的辭賦,所以抒寫真情的作品越來越少了,追求辭藻的作品越來越多。所以有的人熱衷于高官厚祿,卻空泛地歌詠山林水澤的田園隱居生活,有的人一心牽掛著繁忙的政務(wù),卻虛假地?cái)⑹鋈耸乐獾那槿ぁ_@些文章中真實(shí)的思想感情都不存在了,全是和內(nèi)心完全相反的東西啊!桃樹和李樹不會(huì)說話,但樹下卻形成了小路,那是因?yàn)樗邢闾鸬墓麑?shí);男子雖然種植了蘭草,但并不芳香,那是因?yàn)樗麤]有和花相應(yīng)的情味。就是草木這樣微小的東西,也要依靠美好真誠(chéng)的感情,憑借香甜的果實(shí),何況以抒情言志為根本的文章呢,說的話和情志相反,這樣的文章難道可以相信嗎?”。
劉勰認(rèn)為:辭藻是用來美化言辭的,而文章的巧妙華麗卻本源于性情的真摯。所以情理是文章的經(jīng)線,文辭是文章的緯線,經(jīng)線要端直之后緯線才能織上去,情理要確定之后文辭才能暢達(dá),這是寫作的根本。如果文采泛濫,文辭詭異,那情和理就會(huì)受到掩蔽。像用裝飾有翡翠的綸線垂釣、用肉桂做釣餌,反而釣不到魚。要能夠建立規(guī)格像選擇體裁那樣來安頓思想,要能擬定一種基本的格調(diào)來抒發(fā)感情,感情確定之后才配合修辭,思想端正之后才運(yùn)用辭藻鋪陳開去,使文章既有文采又不掩蓋內(nèi)容,材料雖然廣博但并不淹沒作者的感情,這樣的文章就會(huì)閃耀發(fā)光,一切妖容冶態(tài)就會(huì)被掃除。
哲學(xué)大師笛卡爾有句名言:我思故我在。用它來評(píng)判“機(jī)器詩”,也恰如其分。真正的好詩,能夠讓讀者感受到詩人的思想脈絡(luò)、精神路徑,而“機(jī)器詩”是沒有思想靈魂,沒有生命力的。不同時(shí)代有不同的“機(jī)器詩”,古代有采濫忽真的古詩,現(xiàn)代有空穴來風(fēng)的“機(jī)器詩”。來小兮的詩和臧海英的詩,可以說是中國(guó)新詩這枚“硬幣”正反兩面的一個(gè)縮影。同是一個(gè)詩人,這么寫能得到讀者認(rèn)同,那么寫就會(huì)走進(jìn)創(chuàng)作的死胡同。原因有多種,但我覺得,“來小兮”和“臧海英”之間最重要的分野,就是“機(jī)器詩”。如果說來小兮的深度代表了“機(jī)器詩”爛泥塘式的深度,那么,臧海英則昭示著明凈小溪的深度。前者烏煙瘴氣,裝神弄鬼,后者清新雋永,清晰可辨。
為什么我們要花大力氣認(rèn)清“機(jī)器詩”的真面目?因?yàn)樗呀?jīng)涉及到了現(xiàn)代詩歌的評(píng)判標(biāo)準(zhǔn)問題。“機(jī)器詩”的深度是無中生有的。機(jī)器詩的“深度”,就是句子隨機(jī)分行組合的“深度”。所以那些喜歡寫“機(jī)器詩”的作者,拼命向讀者鼓吹“第二次創(chuàng)作”。打個(gè)通俗的比喻:“機(jī)器詩”就像瘸子,走路一瘸一拐,天生的缺陷大家心知肚明就是,但你偏要把瘸子走路姿勢(shì)美化成小品表演,吹捧為成“大師”,這就是人品和詩品問題了。

陳 彬 小院時(shí)光 油畫 60×80 cm
礙于情面,大家裝聾作啞,不掀開“機(jī)器詩”的面紗,讀者就不能看清它的尊容,看透它的本質(zhì)。詩歌批評(píng)就不可能提供令人信服的判斷,詩評(píng)權(quán)勢(shì)化、圈子化、人情化就會(huì)大行其道,真正的好詩就會(huì)被合理屏蔽,形同劣幣光明正大驅(qū)逐良幣。“機(jī)器詩”最明顯的特征是“詩道尊夷”,東施效顰,照葫蘆畫瓢,以套寫為能事,把晦澀難懂當(dāng)成深度,故弄玄虛,以其昏昏為榮,使人昭昭為高。寫出的東西,自己都沒搞清楚,卻指望別人明白。沒有必要的文字鋪墊,沒有水到渠成的思想延伸,沒有立心鑄魄的大境界,唐詩宋詞的高度,不是靠亂叫幾聲“李白兄”“杜甫兄”就可以達(dá)到的。說白了,一堆沒有思想內(nèi)核、缺乏精神靈魂的“機(jī)器詩”,不管貼上古詩什么標(biāo)簽,這個(gè)“章”那個(gè)“貼”的,都是照貓畫虎,得其表而喪其里,與蒲松齡老先生批評(píng)過的“禽獸之變”如出一轍:“詐幾何哉?止增笑耳。”
只有徹底掀開“機(jī)器詩”的面紗,精準(zhǔn)摸出“機(jī)器詩”的底牌,揭穿它拙劣的炮制套路,才會(huì)舉一反三,將那些同質(zhì)化和程式化的詩歌理論打回原形,讓真正的詩歌批評(píng)擁有一席之地,重建評(píng)判標(biāo)準(zhǔn)與尺度,發(fā)揮甄別、遴選的作用,讓更多的優(yōu)秀作品脫穎而出。
當(dāng)然,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的探索和嘗試,誰都難免不走彎路,關(guān)鍵是有沒有發(fā)現(xiàn)的眼光、有沒有糾錯(cuò)的勇氣。《禮記·中庸》云:知恥近乎勇。寫過“機(jī)器詩”不要緊,明知故犯、文過飾非才是詩人的恥辱。相信越來越多詩人,會(huì)成為下一個(gè)臧海英,跟“來小兮”告別,跟“機(jī)器詩”劃清界線,放下包袱輕裝上陣,從容按下新詩兩個(gè)一百年的創(chuàng)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