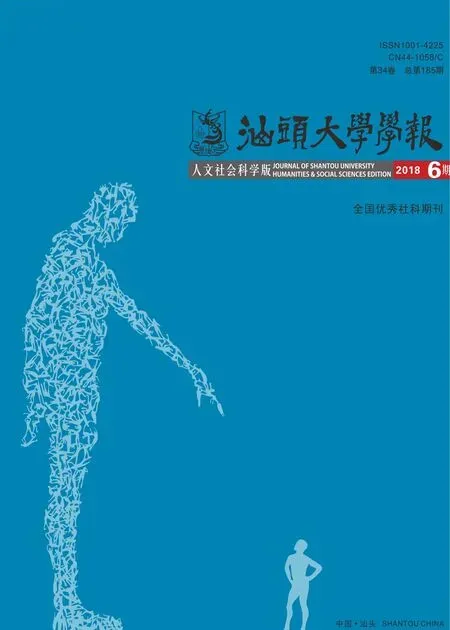誰的魯迅?以及新時期中國的魯迅研究
——以王富仁先生的魯迅研究及精神特征為中心
李 怡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四川 成都 610064)
今天,我們討論魯迅,不得不時刻清醒地明確地面對一個基本事實:魯迅早已經離開了我們。所有的研究歸根結底都不過是“我們”與魯迅的對話,或者說,是研究者的魯迅,但是這樣說,并不意味著我們遠離著魯迅,相反,其實,每個研究者都是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回到魯迅,發掘和提煉魯迅的某一精神特質,而這樣的提煉在另外一方面包含了研究者所置身的社會歷史與文化狀態,這樣,遠去的魯迅就不斷與當下展開對話甚至思想的交鋒。所謂“竹內魯迅”之名由此產生。據說,最近中國學界也出現了諸如“錢理群魯迅”的概念。
要梳理魯迅研究之于新時期中國的特點,特別是中國學界最近三四十年面對魯迅的態度,關注王富仁的魯迅研究走向是一個比較好的案例,這不僅因為王富仁先生已經去世,思想已經完成,可以供我們完整地解剖、闡述,更因為他在魯迅研究中的開闊與敏銳直接聯系著最近三四十年中國學界的種種動向,王富仁從不回避種種的思潮,努力通過自己的魯迅研究方式直接或間接地回答著這些思潮,由此,其關于魯迅的陳述就具有了十分鮮明的當下指向,或者說在王富仁這里,提煉的魯迅精神明確地參與了中國當代文化,激活了的魯迅介入中國當代文化,這是怎樣的一種景觀啊!
應當說,王富仁所感知和提煉的魯迅精神具有十分豐富的內涵,這里僅僅只討論其中的一點,即他如何發掘和推進魯迅的“啟蒙”精神。并且不斷通過回應對啟蒙的挑戰,深化著啟蒙的內涵。
在對王富仁先生的追悼與緬懷中,高頻率出現的詞語是“啟蒙”,的確,這可以說就是對先生畢生學術思想追求的精確概括。從《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到“魯迅視角”下的中國現代作家研究、思潮研究,再到最近數年熔現代與傳統于一爐的“新國學”研究,其實都折射出一種去除蒙昧、再認自我的精神,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啟蒙”精神。“啟蒙”(enlightment)的本義是“照亮”,是以理性質疑外在的權威,重新確立人的價值和主體性。1980年代,王富仁以“思想革命”反撥已成權威的“政治革命”,可以說是以現代理性重塑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基礎,“回到魯迅那里去”其實就是“回到研究者獨立的理性那里去”。
從那以后,“啟蒙”便成為了王富仁學術追求的內在靈魂。在王富仁的文字中,我們常常感到了一種全面反思和重建中國文化的宏大氣魄。他仿佛總是在不斷拔除和拭去我們習焉不察的種種蒙昧、陰霾和偏見,不斷將一片片嶄新的藝術空間鋪展開來。也就是說,在學術活動中“持續啟蒙”是王富仁的基本姿態。
問題在于,新時期以來的當代中國啟蒙文化遭遇了嚴重的阻擊,被質疑、被批判恰恰是1990年代以后啟蒙文化的歷史命運。在這個時候,“持續啟蒙”的王富仁顯然是孤獨的,但是最值得注意之處在于,孤獨以及孤獨者的悲劇并不能真正概括王富仁的學術狀態。因為,我們清楚地看到,正是在“啟蒙文化”色彩暗淡的歲月里,王富仁展現出格外堅定的意志力,他不僅沒有從思想啟蒙的立場上退卻,不僅沒有通過對新思潮的迎合來順應歷史的“發展”,反而繼續將理性的反思推進到了越來越多的學術領域,在不同的方向和層次中夯實“啟蒙文化”的地基。
1990年代,他對魯迅這樣評述:“魯迅作為一個中國的啟蒙主義者的歷史地位是不可忽視的,模糊了他的思想的啟蒙主義性質,也就模糊了他與他的思想先驅者們的思想聯系,模糊了他的思想的社會性質和民族性質,模糊了他的理性選擇的清醒性和確定性。”“他的生命哲學與西方存在主義哲學有著一系列共同的特征,但二者又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說西方的存在主義者高舉著生命哲學的旗幟離開了十八世紀的啟蒙主義思想,魯迅則高舉著生命哲學的旗幟更堅定地站立在中國啟蒙主義的立場上,并且義無反顧,把‘五四’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旗幟一直舉到自己生命的盡頭。”[1]
這顯然是在正視生命哲學的意義上重新認知“啟蒙-反啟蒙”的復雜關系。所有對啟蒙的質疑邏輯都忽略了王富仁的啟蒙追求其實是建立在一個更為磅礴的生命關懷、生命體驗的基礎之上,而不是歐洲19世紀啟蒙文化那樣單薄的“理性自信”,對生命的關懷與深入的體驗從一開始就注定了王富仁將沿著啟蒙之路走向一個意想不到的遠方,質疑者根本沒有發現一個深層的王富仁,與“洞見”聯袂而生的果真是觸目驚心的“不見”。
王富仁最早的學術活動是從跟隨薛綏之先生寫作魯迅作品賞析開始的,這種以個人感受為基礎的閱讀欣賞活動引導他嘗試通過感性的生命體驗來貼近魯迅的心靈世界。正是有了這一番的感性生命的應和,才最后導致了對魯迅小說的重大發現——所謂“偏離角”——思想闡發與政治闡發的內在矛盾,“偏離角”的發現當然顯示了他巨大的理論建構的勇氣,但這一建構的前提卻首先是他作為批評家的特殊的感知能力。王富仁后來對新時期的啟蒙派魯迅研究的評述,其實就是他自己的學術基礎:“這時期魯迅研究中的啟蒙派的根本特征是:努力擺脫凌駕于自我以及凌駕于魯迅之上的另一種權威性語言的干擾,用自我的現實人生體驗直接與魯迅及其作品實現思想和感情的溝通。”[2]的確,他的博士論文《〈吶喊〉、〈彷徨〉綜論》固然氣魄非凡,邏輯嚴密,但人們同樣會為書中那到處閃光的精細的藝術感覺而嘆服:在關于《藥》墳上花環的論述中,在關于《一件小事》的主題辨析中,在關于魯迅小說文言夾雜的語言特征的剖析中……1990年代以后,王富仁將較多的精力轉向宏闊的文化文學研究,但與此同時,他也從未中斷過對文學作品的感受和鑒賞,從《補天》《風波》到《狂人日記》,他不時推出自己細讀文學作品、磨礪藝術感受的佳作;從《中外現代抒情名詩鑒賞辭典》《魯迅作品鑒賞書系》到《聞一多名作欣賞》《中國現代美文鑒賞》,他似乎對各種各樣的鑒賞工作滿懷著興趣。其欣賞范圍甚至跨出了現代,直達中國古典文學。他連續不斷地在《名作欣賞》雜志上推出關于中國古典詩歌名篇的解讀,嘗試著王富仁式的“新批評”,這些文字更自由更無所顧忌地傳達了他的種種新鮮感覺。
到了1990年代中期,王富仁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模式提出了深刻的反省,他先后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的“正名”問題》和《對一種研究模式的置疑》兩文。前者提出:“迄今為止,中國現代文化研究,其中也包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存在的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基本概念的混亂”,“它的概念系統只是中國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各種不同文化概念的雜亂堆積”。[3]這里實質上是闡發了一種絕不同于當下許多文化研究工作者的嶄新的思路,即無論是外來文化還是傳統文化都不可能也的確沒有成為現代人的基本生存原則,只有深入到現代人的生命體驗中去,才能找到真正屬于他的文化選擇;后一篇文章則將中西文化與知識分子個人的關系,描述為“對應點重合”,“重合”的基礎當然還是個體生命的體驗。[4]
作為一個無比自覺的啟蒙者,王富仁不是將啟蒙作為一面招搖的旌旗,一處堅守不移、傲視他人的成果的高地,而是將啟蒙看作一個充滿活力,能夠不斷介入現實、回答當下生存問題的思想的資源,而啟蒙本身也處于被不斷認識、不斷開掘、不斷敞露深層肌理與內在創造力的過程之中,它不是完成于18世紀的法國,不是取法于康德的思想,也不是結束于后現代的質疑,停步于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它與現代中國人的命運相遇了,重新面對了中國歷史的問題,被新的知識分子所發現,再一次被注入了思想創造的能源,可以毫不夸張地說,王富仁的啟蒙探索是啟蒙文化一次空前的深化和發展,是在啟蒙遭受巨大阻擊的時代的一次思想“激活”與“重啟”。
如果說《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是在中國現代文學的格局中論證魯迅的啟蒙價值,那么《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則是在整個現代中國文化的格局中發掘知識分子的啟蒙精神。這是王富仁對1990年代啟蒙文化的第一次擴展性的推進。
一部《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納入了20世紀中國學者對魯迅的研究,納入了整個中國現代學術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精神流動的恢宏圖景,對其中各種細節的勘探和回答就是對現代文化的反思和批判。王得后先生認為這篇長文首先打動了他的便是“作者的寬厚”,[5]其實,在歷史現象理解的“寬厚”之外,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更有王富仁思想堅守的立場。在《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中,王富仁多次論及魯迅作為“社會派”知識分子的獨立價值,論及魯迅研究中“社會派”與“學院派”的差異。所謂的“社會派”,就是以對中國當代社會現實的體驗為基礎而不是以某種時髦的理論為基礎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格外重視自身的現實生命感受與社會文化感受,將所有的學術追求、理論的建構都牢牢地建立在這一感受的基礎上,所謂“啟蒙”的歷史使命就是由這些極具現實關懷的知識分子來承擔的。在現代中國這個生存難題遍布、生存空間狹小,常有原欲態的生存,缺少個人的特操、缺少精神的信仰、無處沒有做戲的“虛無黨”的時空環境中,大概也常常是這些充滿社會生存實感的知識分子觸及著最有“質地”的真實。從王富仁對于“社會派”的闡發與激賞中,我們也分明地感受到了他自己的人生與文化取向,盡管他自己也依然生活在高等院校的圍墻之內,還在繼續地完成著一所學院所要求的“學術”。在1990年代,王富仁的思想學術方式是以自己的理解為基礎,完成著向“學院”之外的社會派精神的暗移。正如樊駿先生所指出,這里出現的是一個奇特的思想家,因為“一般學術論者中常有的大段引用與詳細注釋,在他那里卻不多見,而且正在日益減少。”[6]王富仁這種逸出學院圍墻,更廣闊更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愿望與他作為學院內知識分子的學術方式——對歷史的理性敘述——形成了頗有意味的對照。他完成的是學院式的課題,傳達的卻是胸懷天下、心系蒼生的社會憂患。在這個“消解啟蒙”、自我“規范”的時代,王富仁卻依然介入社會、擁抱啟蒙,真可以說是一種來自“絕地”的“孤絕的選擇”。絕地,險惡孤絕之地,當開啟現代精神又遠遠沒有完成的啟蒙在當下的學術語境中遭遇了空前的消解,“絕地”可能就是一種形象化的描繪。身居絕地,還要繼續自己的理想,這里需要更大的學術勇氣與學術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