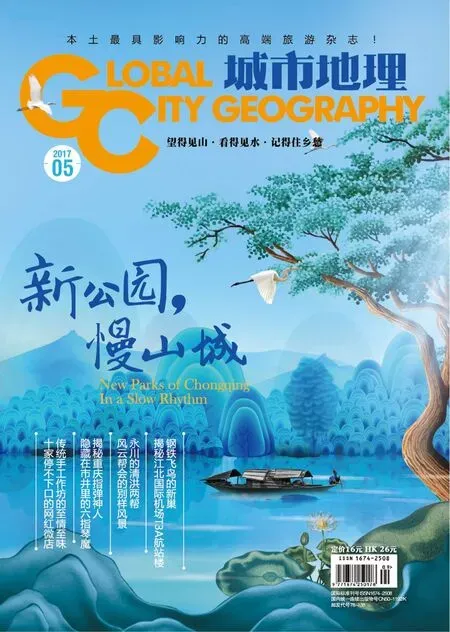在熟悉或陌生的南京
父親經(jīng)常拿我開玩笑說:你出生后幾個月就去過好幾次南京了!可我去的是兒童醫(yī)院,得了百日咳。事實上小時候到南京一次很稀罕,這種稀罕讓我始終認定自己是農(nóng)村人,離開鄉(xiāng)下去南京或其他地方,是人生目標。后來我陸續(xù)到過棲霞山、長江大橋、玄武湖動物園、中山陵和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還被專門帶著路過金陵飯店,并仰視一番。在相當長時間里,我對這些景點的位置顛三倒四,猶如今天第一次去某個大城市并終生不來第二次一樣。
從1997年開始,我一直在南京,二十多年時間足以讓我把大方向上的景區(qū)地點弄清楚,但很多細節(jié)依然不甚了解,在特定區(qū)域里完全是個陌生人,如夫子廟一帶、奧體新城一帶,還有另外幾片。因為去得太少,顯得像個外地人——那么問題來了,作為本地人,卻對很多地方全然陌生,這是個人的原因,還是城市過分發(fā)展的原因?是喪失了探索城市的熱情,還是它確實沒有任何特色、也不在生活范圍之內(nèi)?是南京真正的古今并蓄、繼往開來,還是一個人本不需要生活在南京這種體量的城市?
當這些問題總是涌現(xiàn),城市和人的關系就成了一大命題,畢竟,“落腳城市”是必然,所謂的故土因為拆遷和變遷都不復存在了。我寫過很多關于童年和故土的小說,如今完全不想再寫。必須誠實一點,我們回不去了,其實也不愛它。
回到問題本身,在南京,本質(zhì)上和多年前一樣,是一個巨大的村莊,我生活在其中一個角落,在一小片區(qū)域里活著:廣州路以南、模范馬路以北、中央路以西、虎踞路以東。概括其中值得一去的地方,是頤和路民國建筑群和幾所大學的本部。
同時,因為工作學習、走親訪友等緣故,我會路過更多的地方。這些地方無法羅列,事情有不可測的一面,朋友的所在往往也出乎意料。
此外,出于個人的喜好,有一個不遠不近、看似毫無關系的地方我特別熟悉,一有空就去轉(zhuǎn)轉(zhuǎn)。這地方就是紫金山和掛在它腳下的玄武湖。從1997年開始偶爾爬山,到畢業(yè)后結婚前那幾年瘋狂爬山,再到最近幾年頻繁帶女兒爬山,我自詡鉆研紫金山20年,不敢說了如指掌,但確實知道大量不為人知的山路小徑。
上述三段經(jīng)歷,基本上概括了一個城市和一個人的關系:第一段是日常生活,從農(nóng)村搬遷到城市,與社會發(fā)展同步;第二段是職業(yè),因為工作等緣故,總能去一個陌生的地方,參加一個充滿愚蠢的滿足感的會議或者飯局,誤以為自己還有前途;第三段則是愿望或者自我彌補,紫金山的精華不在于風景和名勝,不在于壯觀或奇特,在于那里有大面積的可以長時間走下去的荒山野嶺,對應著童年的丘陵和成年后對孤獨的需求。這三種狀態(tài),基本上可以滿足一個人和一座城市的關系,有立體感,有虛榮心,有集體活動的樂趣,有獨自行動的條件。但沒有更多了,一座城市不會給一個人提供更多、更深層次的感受,只有特定的人和事才可以,只有“人文”才可以。
在紫金山和在市區(qū)一樣,走著走著就會遇到一些歷史遺跡,南北朝或者南宋的,明代的,更多則是民國的。這其實是一件沒辦法的事,因為這就是南京。明代與民國在今天的南京本該無處不在,雖然事實上相關事物越來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