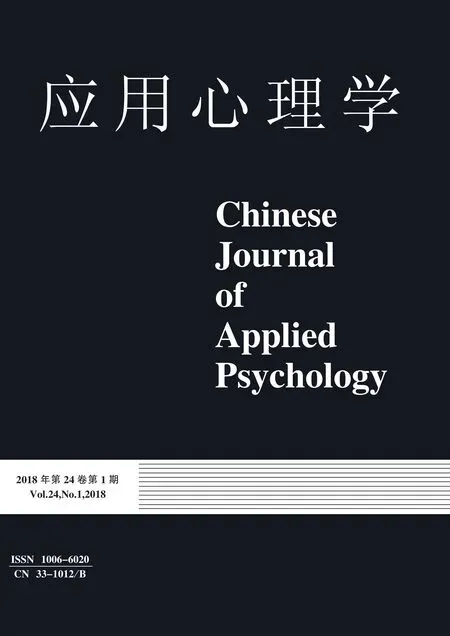德行領導、關系與創造力:權力距離的調節作用*
王永躍 張 玲 張書元
(浙江工商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杭州 310018)
1 問題提出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導致產品生命周期持續縮短,新產品、技術或思想的出現將改變整個行業的發展態勢,創新能力逐漸成為組織成功的關鍵要素(Jafri,Dem,& Choden,2016)。作為組織創新能力的微觀基礎,沒有員工的創造力就不會有組織的創新成果。因此,如何有效激發和提升員工創造力,是關系組織生存與發展的大事,也是產學兩界共同關注的重要議題。
員工創造力是指員工在工作中產生關于產品、程序和質量等具有創造性、新穎的想法或觀點(Amabile,Conti,Coon,Lazenby,& Herron,1996)。已有的研究表明,影響創造力的因素包括:(1)個體因素,如自我效能(Ma,Cheng,Ribbens,& Zhou,2013)、人格以及情緒智力(Jafri et al.,2016)等;(2)環境因素,包括:與工作相關的因素,如工作復雜性及同事支持(Liu,Jiang,Shalley,Keem,& Zhou,2016)等;團隊層面因素,如領導風格等(Gu,Tang,& Jiang,2015);組織層面因素,如組織創新氛圍等(Chen & Hou,2016)。
在影響員工創造力的環境因素中,領導是最為直接的因素之一(Ma et al.,2013),因為員工往往通過對領導行為的解讀來選擇合適的行為。在諸多領導類型中,西方文化背景下衍生出的倫理型領導對員工創造力的影響近年受到了研究者的關注(Chen & Hou,2016)。然而,同樣是關注領導者的道德表現,根植于東方文化的德行領導與員工創造力的關系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Wu,2012)。令人困惑的是,即使在為數不多的實證研究中仍存在著不一致的結果。有研究者認為德行領導對激發員工創造力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許彥妮,顧琴軒,蔣琬,2014;Gu et al.,2015),而另一些研究認為此兩者之間并不存在顯著關系(陳璐,高昂,楊百寅,井潤田,2013)。
以上混淆的結果不僅造成中國本土領導理論發展的阻滯,也導致管理者在實踐應用時常常無所適從。本文推測,造成以往研究結果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有兩個。第一,以往較少有研究同時探討兩者關系間的作用機制和邊界條件;第二,在研究中國情境下的組織公民行為(如創造力)時應考慮中國文化特征因素(Farh,Earley,&Lin,1997),而以往研究忽略了從這一角度來探究兩者之間的關系。
根據Farh等人(1997)的觀點,本研究認為探討德行領導對員工創造力的影響機制和邊界條件時,選取反映中國社會文化特征的變量,可能是進一步厘清此兩者關系的理論突破口。本研究期望在理論上為拓展中國本土化領導管理理論做出貢獻,同時在實踐上為中國企業有效地激發員工創造力提供對策。
本文將通過建立一個有調節的中介模型來分析中國文化背景下德行領導對員工創造力的作用機制。首先,德行領導因其高尚的個人操守,正直廉潔、以身作則的樹德行為,構建了可信的、支持性的、安全的工作氛圍,有利于激發下屬創造力。其次,由上下級關系概念來透視領導與員工行為的關系已成為中國式管理研究的最佳進路(王忠軍,龍立榮,劉麗丹,2011)。德行領導有助于與下屬建立親密的私人關系,且在高質量的上下級關系中,領導會給予下屬更多工作與情感上的支持(Zhang,Deng,Zhang,& Hu,2016),從而為員工表現創造力提供了必要條件。由此本文推測上下級關系在德行領導與員工創造力之間起到中介作用。最后,作為一種價值觀傾向,權力距離在中國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文化情境變量(陳璐等,2013),可能會影響到下屬對領導者行為的敏感程度,從而影響到上下級關系。即德行領導通過上下級關系激發員工創造力的過程可能會受到員工權力距離的調節。
1.1 德行領導與上下級關系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體現了古人對領導者德行品質的推崇。德行領導是指領導者表現出較高的個人操守和道德修養,尤其是仁厚誠摯、對下屬一視同仁、關心下屬成長等的樹德行為,以贏得員工的尊重、認同和效仿(鄭伯塤,周麗芳,樊景立,2000)。研究表明德行領導對員工的工作表現和態度會產生積極影響(Wu,2012)。
上下級關系是指組織中員工通過工作范圍之外的互動行為與其領導建立的非正式、特殊性的私人關系質量(Law,Wong,Wang,& Wang,2000)。受儒家“特殊主義”文化影響,員工密切附屬于基于“人際關系”所建立的社會秩序,“私人關系”在中國組織成員的人際交互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劉詠梅,鄒意,衛旭華,2017)。人際互動表面上遵循工作中的角色規范,而事實上,與上級隱而不宣的私人關系才是更重要的主導因素(王忠軍等,2011)。
本文認為德行領導對上下級關系有積極影響。一方面,為了更好地發揮領導效力,上級會與下屬建立密切的關系(Weng,2014)。在中國,即使是展現出正直、無私等道德品質的德行領導,受“面子”文化的影響,也不可避免的會基于人情法則把部分員工劃為自己的“圈內人”,與他們有更密切的私人交往。在與下屬的交往中,德行領導表現出對下屬真正的關心,并且尊重、信任他們。這些行為幫助德行領導與下屬建立更高水平的聯系。另一方面,員工普遍重視和期望與上級建立并維持良好的私人關系(Zhang et al.,2016)。受“關系取向”文化的影響,下屬希望通過逢迎、幫領導辦事等策略,成為領導的“圈內人”,以獲得更多資源。當員工示好的對象是德行領導時,其平易近人、不擺領導架子、為人厚道的處事方式,在與下屬產生更多互動的同時也贏得了下屬的信任和尊重,從而建立起高質量的上下級關系。綜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德行領導對上下級關系有正向影響。
1.2 上下級關系的中介作用
社會交換理論認為,交換雙方會依據所得來回報對方提供的資源。德行領導在與員工交往中表現出的以身作則、真誠、關愛與公平對待被員工視為是領導向部屬提供支持性的交換資源,作為回報,員工會把維護組織的有效運行視為自己的義務。而創造性活動的開展正是承擔這種義務的一種具體的行為表現。因而本文認為德行領導對員工創造力有正向影響,Gu等人(2015)的研究也支持了這一點。
然而德行領導對員工創造力的直接影響有限,大部分還可能會通過某種“橋梁”作用來對員工創造力產生影響。在強調人情文化的中國情境下,相比于工作中的正式交換關系,與上級在工作外建立的私人關系對下屬角色外行為(如表現創造力)影響更大(Weng,2014)。鑒于領導者有能力去構建一種相互信任的人際關系,提高上下級關系質量,本文預測上下級關系可能在德行領導與員工創造力間起到中介作用。
古人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來而不往非禮也”。根據社會交換理論,當感知到領導的良好對待時,員工往往會用積極的行為來回報領導。首先,與領導有著高質量上下級關系的下屬對組織有較多的責任感,在工作中愿意付出更多努力以促進組織的有效運行,因而他們會更愿意表現創造力。其次,高上下級關系意味著雙方遵循更深層次的互惠原則(Law et al.,2000)。員工愿意付出超過職責范圍的努力,積極地投入到具有風險性的創新活動中去,以期回報領導友善的行為,在上下級關系中實現互惠的責任。最后,高上下級關系表明領導和員工建立了“特殊”的關系,這些員工是領導的“圈內人”。領導會給“圈內人”提供更多資源、信息支持,因而他們有更多資源來更好地表現創造力。因此,上下級關系與創造力正相關,結合前述德行領導顯著提升上下級關系和創造力,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2:上下級關系中介了德行領導對員工創造力的影響。
1.3 權力距離的調節作用
權力距離作為一種文化價值觀,是指人們對組織中權力分配不平等情況的接受程度(Furrer,Liu,& Sudharshan,2000)。鑒于領導在任務分配、考核等工作中具有相當程度的主觀性,下屬權力距離的不同可能會導致下屬對領導行為的敏感程度不同,于是本文推測德行領導對上下級關系的影響可能受到下屬權力距離的調節。
具體而言,高權力距離的員工謹遵“上尊下卑”的傳統思想,接受自身在權力和地位上與上級的差距。對他們而言,上級在組織中統籌資源的分配,下屬依賴上級獲得資源并完成工作是理所應當的,因而對上級的行為不敏感。即使上級展示出較高的德行品質,下屬也不會在工作之外和上級進行較多的溝通交流(Aycan,Schyns,Sun,Felfe,&Saher,2013)。而低權力距離的員工傾向于相信自己與領導一樣都是組織不可或缺的一員,往往不會認同組織權力的不平等分配,會將上級視為可以接近的,期望與上級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因而他們的心理和行為更有可能受領導行為的影響。德行領導者所傳遞出尊重、關懷、重視等積極的情感以及平易近人的態度滿足了他們對領導的期待,從而更有可能因信任、尊重領導而與領導建立高質量的上下級關系(Aycan et al.,2013)。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3a:權力距離調節了德行領導與上下級關系之間的關系,即低權力距離強化了德行領導對上下級關系的影響;反之越弱。
進一步地,由于權力距離調節了德行領導對上下級關系的作用,且上下級關系中介了德行領導與員工創造力的關系,本文認為權力距離也調節了上下級關系在德行領導與員工創造力關系之間的中介作用,具體表現為被調節的中介模型。權力距離越低,德行領導通過上下級關系傳導的對員工創造力的效應就會越強。據此,提出如下假設:
H3b:權力距離調節了上下級關系在德行領導與員工創造力之間的中介效應。即當員工的權力距離水平較低時,上下級關系的中介作用得以增強。
2 研究設計
2.1 數據收集
本研究采用異源評價法對浙江與上海的12家高新技術企業進行數據收集,其中,員工創造力由其直接主管評價,德行領導、上下級關系和權力距離則由員工自評。問卷發放前,研究人員先與各企業負責人對問卷發放流程與參與問卷調查人員名單進行商定,每位主管需對3~5名直接下屬的創造力進行評價。最終確定了86位主管與350名員工作為調查對象。為降低員工填寫顧慮,所有問卷均為匿名填寫,并在填寫完成密封后直接交予各企業負責人并郵寄給研究生,由研究生完成配對工作。最終回收員工問卷307份(回收率87.7%),領導問卷76份(回收率88.4%)。剔除無效(重復作答或缺失嚴重)問卷后,獲得有效員工問卷275份(有效率89.6%),有效領導問卷69份(有效率90.8%)。其中,員工樣本中,男性156人(56.7%);年齡以25~30歲為主(42.3%);教育程度以本科為主(44.0%);工齡以3年及以下為主(35.3%)。
2.2 測量工具
德行領導采用鄭伯塤等(2000)的9題單維量表,5點評分。樣題如“我的領導為人正派,不會假公濟私”。本研究中該量表的α系數為0.91。
上下級關系采用Law等(2000)的6題單維量表,5點評分。樣題如“在工作之余,我會給領導打電話或者去拜訪他”。本研究中該量表的α系數為0.83。
權力距離采用Furrer,Liu和Sudharshan(2000)的4題單維量表,5點評分。樣題如“人與人之間的不對等是人們所期望并想要的”。本研究中該量表的α系數為0.83。
員工創造力采用Farmer,Tierney和Kung-Mcintyre(2003)的4題單維量表,5點評分。樣題如“他/她會優先嘗試新觀念或新方法”。本研究中該量表的α系數為0.92。
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工齡可能會對員工創造力產生影響(李銳,凌文輇,柳士順,2012),因此本研究將這四個變量作為控制變量。
除德行領導量表采用國內量表外,本次研究中運用的其余量表皆為國外學者開發的量表。本研究采用回譯法對英文問卷進行了翻譯,確保問題清楚、準確。
3 結 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首先,采用Harman單因素分析對模型進行檢驗,結果沒有單一因子析出;然后對數據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四變量的題項分別分布在各自維度,四因素累積方差解釋量為71.21%;最后,分別構建四個SEM進行比較,結果顯示四因素模型(χ2=247.33,df=224,GFI=0.93,TLI=0.97,CFI=0.98,RMSEA=0.048)擬合效果最優,并且采用“加入非可測方法變異因子”的方法,將共同方法因子作為第五個變量納入SEM,模型變化不顯著(χ2=272.34,df=201,GFI=0.92,TLI=0.96,CFI=0.98,RMSEA=0.05)。綜上,本研究中雖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共同方法偏差,但是共同方法偏差并不嚴重。
3.2 相關分析
表1顯示了本研究中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和相關系數,從中可看出,德行領導(r=0.37,p<0.001)和上下級關系(r=0.39,p<0.001)分別與創造力正相關,德行領導(r=0.47,p<0.001)與上下級關系正相關。這些結果為后續假設檢驗提供了初步支持。

表1 均值、標準差及變量間的相關系數
注:N=275。零階相關。*p<0.05;**p<0.01;***p<0.001。下同。
3.3 假設檢驗
根據中介效應檢驗步驟(結果見表2),首先檢驗德行領導對上下級關系的影響(β=0.45,p<0.001,M12),回歸系數顯著,假設1被驗證;隨后加入中介變量,德行領導對員工創造力的影響效應有所減弱,但仍然顯著(β=0.25,p<0.001,M23),表明上下級關系在德行領導和員工創造力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Sobel檢驗的結果進一步表明上下級關系在德行領導和員工創造力之間的間接效應顯著(Z=4.95,p<0.001),假設2得到驗證。為檢驗假設3a,把德行領導和權力距離做中心化處理并計算兩者的乘積項。交互效應項對上下級回歸系數顯著(β=-0.28,p<0.001,M14),假設3a得到驗證。
為進一步解釋權力距離的調節模式,進行簡單斜率分析。員工權力距離水平較低時,德行領導對上下級關系的影響顯著(β=0.50,p<0.001);員工權力距離水平較高時,德行領導對上下級關系的影響不顯著(β=0.11,p>0.05)。
為了檢驗假設3b,即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本研究采用Preacher,Rucker和Hayes(2007)的條件間接效應檢驗程序。從表3可以看出,當員工的權力距離較低,德行領導對員工創造力的間接效應在95%水平上的置信區間分別為[0.07,0.19]和[0.13,0.35],間接效應顯著,表明當權力距離較低時,德行領導經由上下級關系對創造力產生的影響更高,假設3b得到驗證。

表2 層級回歸分析
注:X×W=德行領導×權力距離。除M24的ΔR2是在M22上的R2改變量外,其余模型的ΔR2均是在前一個模型基礎上的R2改變量。

表3 權力距離的條件間接效應檢驗
4 結果討論、研究意義及展望
4.1 結果討論
首先,本研究驗證并深化了德行領導在中國情景下對員工創造力的積極作用(Gu et al.,2015)。這可能是由于德行領導給員工提供了關愛、公平等支持性資源,促使員工產生回報心理,激發其表現創造力。其次,結果表明德行領導會促進上下級關系的提高。這可能是因為德行領導高尚的行為贏得了下屬的尊重與認可,有助于上下級之間建立親密的私人關系。第三,研究發現上下級關系在德行領導和創造力之間的部分中介作用。這可能是因為上下級關系是一種強調工作外的社會交換關系,要將這種社會交換關系轉化為創造力,還需要其它因素的共同作用。已有研究證明了建言行為(Chen & Hou,2016)、內在動機(Liu et al.,2016)以及自我效能(Ma et al.,2013)等都是領導影響員工創造力的中介變量。最后,本研究發現權力距離緩沖了德行領導對上下級關系的作用。這可能是因為我國“人倫為本”的思想強調尊卑等級制度,表現為組織中的員工認同并愿意接受領導與下屬之間的權力分配不平等。
4.2 理論意義
首先,本文響應Farh等人(1997)的呼吁,通過有調節的中介模型設計,系統地分析了中國文化背景下德行領導對員工創造力的影響機制及邊界條件,研究結果深化了當前該領域的研究,豐富了中國本土化領導理論。其次,基于社會交換理論,以往研究從西方情境下提出的建立在工作職責上正式的領導-成員交換關系(LMX)來探究德行領導與員工創造力的關系(許彥妮等,2014),卻忽略了中國情境下與領導工作之外建立的私人關系在兩者關系之間可能的紐帶作用(王忠軍等,2011)。本研究表明德行領導行為部分通過上下級關系來間接地影響員工創造力,該結果是對以往采用LMX作為中介解釋機制研究的深化和有力補充。最后,權力距離在中國組織中普遍存在(陳璐等,2013),本文將這一文化情境因素引入德行領導有效性的研究中,為德行領導的作用機制和邊界條件提供了有力解釋。
4.3 管理啟示
首先,領導應更多地采用德行領導方式,通過自己的一言一行與下屬構建高質量的上下級關系,從而激發其創造力。在工作中,領導應表現出以身作則、一視同仁、懲惡獎善等一系列具有較高道德水準的行為以贏得員工的尊重和信任;在工作外,領導應關心員工生活并及時給員工提供幫助。第二,在權力距離較大的中國,德行領導更要充分發揮人際和情感技巧,建立良好的氛圍。德行領導應當營造平等、鼓勵成員創新的環境,降低員工的權力距離感,減少員工顧慮,使員工能以一種主人翁的心態投入工作當中。最后,在強調領導德行垂范的中國文化中,組織應為培養和發展德行領導提供一定的人力資源管理方案。組織應開展道德宣傳,給領導者提供相應的培訓,同時應增加德行在領導績效考評中的比重,如在獎勵、升職中優先考慮領導德行。
4.4 研究局限和展望
第一,變量間的因果關系驗證受到橫截面數據設計的影響,因此后續可考慮采用時間序列來研究。第二,上下級關系在本研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未來的研究應探討更多變量,如心理可得性等(王永躍,葛菁青,張洋,2016),以全面揭示德行領導與員工創造力之間復雜的中介機制。最后,除性別、年齡、工齡及教育程度外(李銳等,2012),研究表明智力水平等員工個體特征也可能對創造力表現造成影響(Ojha,Indurkhya,& Lee,2017),因此在未來研究中應控制這些個體因素,從而進一步理清德行領導對員工創造力的作用機制和邊界條件。
5 結 論
德行領導對上下級關系有顯著正向影響;上下級關系部分中介了德行領導對員工創造力的影響;權力距離調節了德行領導與上下級關系之間的關系;權力距離調節了上下級關系在德行領導與員工創造力間的中介作用。
陳璐,高昂,楊百寅,井潤田.(2013).家長式領導對高層管理團隊成員創造力的作用機制研究.管理學報,10,831-838.
李銳,凌文輇,柳士順.(2012).傳統價值觀,上下屬關系與員工沉默行為.管理世界,3,127-140,150.
劉詠梅,鄒意,衛旭華.(2017).關系質量對個體揭發決策的影響:權力的調節作用.應用心理學,23,175-184.
王永躍,葛菁青,張洋.(2016).授權型領導、心理可得性與創新:組織支持感的作用.應用心理學,22,304-312.
王忠軍,龍立榮,劉麗丹.(2011).組織中主管-下屬關系的運作機制與效果.心理學報,43,798-809.
許彥妮,顧琴軒,蔣琬.(2014).德行領導對員工創造力和工作績效的影響:基于LMX理論的實證研究.管理評論,26,139-147.
鄭伯塤,周麗芳,樊景立.(2000).家長式領導:三元模式的建構與測量.本土心理學研究,14,3-64.
Amabile,T.M.,Conti,R.,Coon,H.,Lazenby,J.,& Herron,M.(1996).Assessing the work environment for creativity.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39,1154-1184.
Aycan,Z.,Schyns,B.,Sun,J.M.,Felfe,J.,&Saher,N.(2013).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of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A 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 of prototypes.JournalofInternationalBusinessStudies,44,962-969.
Chen,S.Y.,&Hou,Y.H.(2016).The effects of ethical leadership,voice behavior and climates for innovation on creativity:A moderated mediation examination.LeadershipQuarterly,27,1-13.
Farh,J.L.,Earley,P.C.,& Lin,S.(1997).Impetus for action:A cultural analysis of justice and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in Chinese society.AdministrativeScienceQuarterly,42,421-444.
Farmer,S.M.,Tierney,P.,& Kung-Mcintyre,K.(2003).Employee creativity in Taiwan:An application of role identity theory.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46,618-630.
Furrer,O.,Liu,B.S.C.,&Sudharshan,D.(2000).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ulture and service quality perceptions:Basis for cross-cultural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resource allocation.JournalofServiceResearch,2,355-371.
Gu,Q.X.,Tang,T.L.P.,& Jiang,W.(2015).Does moral leadership enhance employee creativity? Employee identification with leader and 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 in the Chinese context.JournalofBusinessEthics,126,513-529.
Jafri,M.H.,Dem,C.,& Choden,S.(2016).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employee creativity:Moderating role of proactive personality and organizational climate.BusinessPerspectivesandResearch,4,54-66.
Law,K.S.,Wong,C.S.,Wang,D.X.,& Wang,L.H.(2000).Effect of supervisor-subordinate guanxi on supervisory decisions in China: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InternationalJournalofHumanResourceManagement,11,751-765.
Liu,D.,Jiang,K.F.,Shalley,C.E.,Keem,S.,& Zhou,J.(2016).Motivational mechanisms of employee creativity:A meta-analytic examination and theoretical extension of the creativity literature.OrganizationalBehaviorandHumanDecisionProcesses,137,236-263.
Ma,Y.,Cheng,W.B.,Ribbens,B.A.,& Zhou,J.M.(2013).Linking ethical leadership to employee creativity:knowledge sharing and self-efficacy as mediators.SocialBehaviorandPersonality:anInternationalJournal,41,1409-1420.
Ojha,A.,Indurkhya,B.,& Lee,M.(2017).Intelligence level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creative tasks:A pupillometry study.CreativityResearchJournal,29,78-85.
Preacher,K.J.,Rucker,D.D.,& Hayes,A.F.(2007).Addressing moderated mediation hypotheses:Theory,methods,and prescriptions.MultivariateBehavioralResearch,42,185-227.
Weng,L.C.(2014).Improving employee job performance through ethical leadership and “Guanxi”:The moderation effects of supervisor-subordinate guanxi differentiation.AsiaPacificManagementReview,19,321-345.
Wu,M.(2012).Moral leadership and work performance:Testing the mediating and interaction effects in China.ChineseManagementStudies,6,284-299.
Zhang,L.,Deng,Y.L.,Zhang,X.,& Hu,E.H.,(2016).Why do Chinese employees build supervisor-subordinate guanxi? A motivational analysis.AsiaPacificJournalofManagement,33,617-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