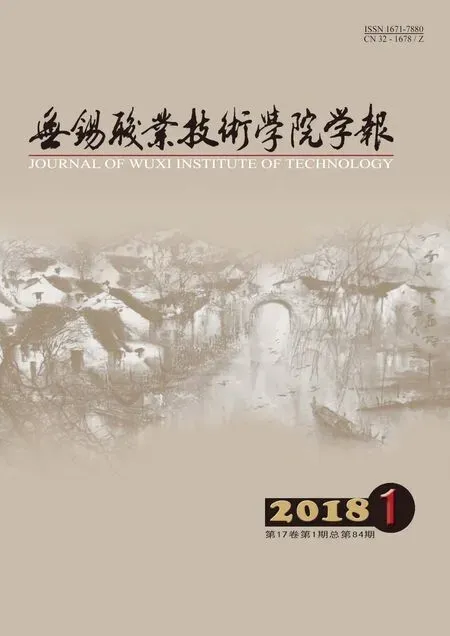社會轉型期的犯罪問題及其法律二元結構應對
王小米 宋 鵬
(蘭州大學 法學院, 甘肅 蘭州 730100)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快速發展,人們的價值觀念隨之更新,人口流動更加頻繁,打破了原有的傳統社會結構,鄉土社會受到重創。社會轉型中,傳統價值觀念和傳統社會秩序受到挑戰,各種社會矛盾空前激化、相互碰撞、綜合反應,因而不可避免地滋生了大量形態各異、紛繁復雜的犯罪問題,這就亟須法律的懲治,亟須建設法治化社會。顯然,單純的一元觀已無法緩解這些社會問題,亟須使用法律二元結構來幫助解決。
1 社會轉型期犯罪問題凸顯
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我國遭遇了體制轉型、社會結構變動和社會形態變遷。”[1]社會轉型期的種種變化使我國社會完全處于一個新時代,它與以往的歷史時期全然不同。社會轉型期翻天覆地的變化既給我們帶來了一定的發展機遇,同時也使我們面臨許多嚴峻的挑戰。
在我國的社會轉型期,由于相關制度設施和法律的滯后,人們的適應時間明顯增長,這種變更與動蕩使得各種矛盾凸顯并加劇,導致犯罪頻發,類型多樣。研究表明,我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犯罪率不斷上升:1988年,全國刑事犯罪案件立案82萬件,相比于1987年同比增長45.1 %;而在1989年,全國刑事犯罪案件相比1988年又上升了30%左右;從1988年至1992年五年間,全國法院共受理一審刑事案件2016357件,平均每年上升7.9%;1993年,全國刑事犯罪案件數量比1992年增加24%,1994年,全國刑事犯罪案件總數比1993年上升了7.3%。截至2008年,犯罪人數約為35萬人[2]。這些犯罪問題呈現出經濟犯罪突出、新型犯罪層出不窮、流動人口犯罪占較大比重、犯罪主體低齡化等特點。
2 法律二元結構
談到法律二元結構,避不開的問題是法律結構論,即如何界定法律概念以及如何劃分法律結構。法與法律之間的界線劃分是一個長期存在且飽含爭議的問題。從古典法學的角度而言,法和法律之劃分主要有迥然相異的兩種主張:一是法和法律之一元論,它認為法和法律相同,認為它們均為國家權力機關制定并認可,是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行為規范的總和。二是法與法律之二元論,即法與法律并不相同,“法為法律之載體,法律為法之外部表征,法律必須吻應法之規約,唯其如此,法律方為嚴格意義上之法律。”[3]
這兩種不同的界定必然導致對法律結構的劃分不盡相同,即形成了法律結構一元論與法律結構二元論兩種觀點。由于中國在歷史上長期以小農經濟為主,缺乏法治文化,所以鄉土社會是我國最主要的社會形態,也是研究我國法律結構繞不開的重點背景。鄉土社會中的人們在我國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基于習慣,不斷在利益沖突中磨合,自發形成了鄉土社會自身的、得到鄉土社會中人們普遍自覺遵守和信奉的民間秩序規則——民間法。同時,國家法作為由國家權力機關制定并認可的,強制實施的國家層面的行為規范,也同樣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由于中國社會的特殊性,民間法與國家法的法律二元結構問題是中國法律結構研究的重中之重。
3 法律二元結構缺位對社會轉型期犯罪問題之影響
民間法與國家法的關系問題在社會轉型時期尤為凸顯,只有二者之間進行良性互動,相互融合吸收,才能使得社會平穩過渡。民間法作為一種社會秩序,其形成是自發發展的結果,在熟人社會中,人們自發形成了一套存在于國家法之外的行為規則,這種秩序早已根深蒂固,內化于心。國家法作為一個國家法律制度建設的基礎,同樣應嚴格遵守,但現實是,我國國家法與民間法并非是和諧、良性的互動關系,二者充滿了沖突與對立,法律二元結構的缺位對我國社會轉型期犯罪問題有著巨大影響。
3.1 導致犯罪問題頻發
民間秩序存在于中國廣大的鄉土社會中,它的基礎是生活在特定生活圈子里的人們的血緣關系,即熟人社會里存在的自然秩序、內在秩序。隨著社會轉型的發展,國家秩序、國家法滲透進鄉土社會,這種陌生的秩序形態和意識觀念顯然有悖于人們的傳統價值觀念,無法真正融入人們的生活之中。“外部規則經由持久的教育業已內化為穩定之習慣。人類的禮儀、習俗之所以能得以遵守與存續,就在于內心之守持,而非外在之強權。因而,該秩序強調修身養德,使人內心澄明寧靜。”[4]
法律絕非亙古不變之規則,相反,它具有鮮明的境域性。因此,并不能希冀每個人都能熟悉這與時俱進的法律。帶有強制性的國家規范、國家秩序顯然無法約束鄉土社會或特定區域里的一切不法行為,通常民間秩序對人們的約束力要比國家規范對人們的約束力更強勁。這導致了民間秩序與法律秩序的斷裂,也導致了民間秩序與官方秩序的斷裂。這種落差必然會導致原本符合民間秩序的行為觸犯國家規范,構成犯罪,周而復始,人們在這種沖突與矛盾中掙扎、探索,違法與犯罪行為是不可避免的。
3.2 導致犯罪行為復雜化
由于法律二元結構的缺位,國家法與民間法的相對對立與脫離而導致犯罪行為中的違法性相互交錯,較為復雜。具體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既違反國家法律,又違反民間規則的違法行為。這種違法行為在社會轉型期有其新特點,其成本包括顯性成本和隱性成本,顯性成本即為投入到違法活動中可以直接顯現的成本,而隱性成本則是投入違法活動的時間和受到法律懲罰的風險。人們在實行這一類型的違法行為時無時無刻不在比較成本與收益,只有當收益大于成本時人們才會進行違法活動,尤其是懲罰這一隱性成本不會過高時。
懲罰這一隱性成本又可以分為法律懲罰和社會懲罰。在一定程度上,人們對社會懲罰的畏懼甚于法律懲罰。在大傳統社會中,人是被分化在單位、村莊里的,在這種熟人社會中,一旦誰做出了違法行為或是這個圈子里的人們所不齒的行為,惡名便會馬上散播開來,導致這些人社會地位下降,喪失社會機會,所以在大傳統社會中,社會懲罰往往更加有效和嚴厲。而我國在社會轉型中,人口流動加快,熟人社會轉變為陌生人社會,人身依附關系轉變為勞動合同關系,人事檔案降低了約束作用,社會懲罰無論是量還是度都被大大削弱。所以,違法行為的隱性成本在轉型期大幅度下降,成本收益差大幅上升,犯罪率自然上升。
第二,違反了國家法律,但是符合民間規范的規定,也就是說,這類違法行為在國家法律與民間規范沖突之時,選擇了民間規范。隨著時代的變遷,文明的不斷發展,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不可避免地發生沖突,即使是在同一時期,由于兩種文化對立,也時常發生沖突。文化沖突必然導致行為沖突,而違法行為就是行為規范之間的沖突。
第三,在民間規范的空白地段對國家法律的違反。這種違法行為往往是在人們一無所知的狀態下發生的,對于國家法律的違反,并非出于本意。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由于人合性而不自覺地接受更多民間軟法的規范,而非國家法的規范。所以,對于國家法知之甚少的民眾往往因在民間法的空白地段失去行為指導規范而違反國家法。
4 社會轉型期的法律二元結構建設
社會轉型是各種社會形態不可避免的必經之痛,在這個特殊的階段,面對各種社會矛盾和犯罪問題,法律作為社會基本規范顯得尤為重要。因此,把握好法律的二元結構與多元化視角是平穩度過社會轉型期的良策。具體而言,可通過如下途徑進行法律二元結構建設。
4.1 堅持法律多元化視角
我們應批判單一的法律觀,應意識到除國家的法律體系外,還存在非國家的法律體系,即軟法。而這些法律體系分別存在于人類社會的不同時代或者不同層面,并通過迥然相異的方式對人類的活動施加影響,繼而聚合為相互依存、交互作用、紛繁復雜的法律巨系統。堅持法的多樣性顯得尤為重要,應樹立二元的法治觀,國家法與民間法并存,注重民間法在法治建設中的作用。
4.2 深入研究法律結構理論
既應當認識到法與法律、民間秩序與國家法的區別,又應當認識到它們的相互依存。法是法律的原型,法律是法的反映。法治建設必須建立在一定的法律理論的基礎之上,而作為一個重要的法學理論,法律結構理論對于法治建設的目標定位、內容安排、策略選擇和效果評價等均具有極大的指導意義。因此,必須加強對法律結構理論的研究,以便對其形成清晰而科學的認知。
4.3 著眼于社會需求
社會需求是立法的前提與基礎,沒有社會需求的法律是沒有意義的,立法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產物。法是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充分反映,也是影響立法的因素。社會理性的正常化和情感的正常化有時是不匹配的,立法應該充分考慮社會的多方情況和滲透在人們生活中的種種道德、習慣、宗教、文化等因素,而非閉門造法。要想了解社會需求,就要做好需求調查,深入民間,深入鄉土社會,切實了解當地的民間秩序和權威價值觀念,逐步滲透、改造與國家法相背離的民間法,將國家秩序融入民間法中,讓國家法與民間法相互補充。
4.4 審慎地進行民間法的改造
在治理模式上,鄉土社會完全不同于市民社會,國家法對鄉土社會中的人缺乏親近感,人們對其敬而遠之,鄉土社會中發生作用的往往都是鄉規民約。若一味地將國家法強加于鄉土社會,必將適得其反,導致秩序的量與質不符,大量規則形同虛設,從而使法律的應有功能難以得到充分的釋放。
[1] 劉祖云.從傳統到現代: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研究[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53.
[2] 楊尚威.轉型期犯罪問題及其控制模式探討[J].現代法學,1996(4):57.
[3] 秦強.法律結構論與鄉土社會中的法律結構[J].湖南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7(5):24-27.
[4] 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