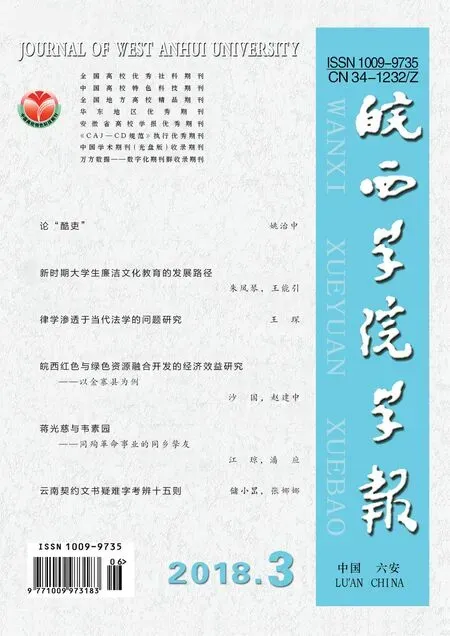李鴻章“寓禁于征”禁煙政策評析
劉 燕
(遼寧大學 歷史學院,遼寧 沈陽 110000)
煙毒泛濫問題是中國近代最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學術界對于近代禁煙史作了不少研究①,但多從宏觀角度入手,對近代以來的三次禁煙運動進行整體研究,以政府行為為主,極少涉及個人。晚清肱骨大臣李鴻章在近代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學術界對于他的研究成果頗豐②,而關于李鴻章的禁煙主張則少有人注意。本文試對這一問題進行嘗試性探究,以期拓寬對李鴻章及禁煙史的研究。
一、李鴻章“寓禁于征”禁煙政策提出的背景和動機
(一)國內煙毒屢禁不止
鴉片(Opium),俗稱大煙,是從罌粟汁中提煉出來的具有麻醉功效的藥品,但長期吸食,極易上癮,甚至中毒。罌粟唐中期始由阿拉伯商人帶入中國,主要作為觀賞花卉。宋明時期,始將鴉片作為藥物進行食用。明萬歷十七年(1589年),鴉片開始列入關稅表中,準其輸入,稅銀每十斤二錢。之后稅率屢次提高,但輸入量卻因需求不斷而不減反增。清初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開海禁,并將鴉片作為進口藥材進行收稅。到雍正七年(1729年),由于販賣和吸食鴉片的人日益增多,危害日顯,清政府頒布了首個禁煙詔令,規定對販鴉片者“收買違禁貨物,枷號一個月,發邊衛充軍”;對私開煙館者按照邪教“擬絞監候”;對包庇走私以謀利的兵役“照枉法律治罪”;對監管失職的官員“均交部嚴加議處”[1](P16)。乾隆繼位后,也下旨申明“鴉片為此地所嚴禁之物品”[1](P18)。但這些法令都沒能制止鴉片的蔓延。乾隆年間(1736—1795年),吸食鴉片的方法迅速由沿海傳入內地,各地很快出現了一些專賣鴉片的煙館,甚至京師一帶已有販賣鴉片者。鴉片如瘟疫一樣,在全國各地蔓延。到乾隆后期,每年有數千箱鴉片運入中國。面對這一嚴峻情形,嘉慶帝決心嚴令禁煙,“不準再有帶鴉片入中國之事”[1](P22)。他為此多次頒布嚴禁鴉片的諭旨,可惜嘉慶年間的禁煙舉措也未能達到預期的成效,鴉片走私進口的規模越來越大。道光帝繼位,三令五申嚴禁鴉片入口,然“吸食販賣偷漏放縱如故”。據統計,從道光元年至道光七年(1821—1827年),平均每年進口鴉片4708箱;從道光七年至道光十四年(1827—1834年),平均每年進口增加到18712箱;從道光十五年至道光十八年(1835—1838年),平均每年進口高達35445箱[1](P329)。道光十九年(1839年),為使禁煙有法可依,軍機大臣等議定《查禁鴉片煙章程三十九條》,這是清政府頒布的最為嚴厲的禁煙法令。然而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政府被迫簽訂《南京條約》,開放通商口岸,使得朝野人士對于禁煙的努力全然空擲。“香港成為鴉片輸入之中心,沿海各口岸均成為鴉片貿易之市場”[1](P81),清政府的禁煙政策名存實亡。進口鴉片供給量的激增,催生了數量龐大的癮君子,鴉片供不應求。本土罌粟的種植開始興盛,“種罌粟畝所出,視農田數倍,……官民皆有所利,以至四處蔓延”[2](P2)。“各省種罌粟者,連阡接畛,農家習為故常,官吏亦以倍利也,而聽之”[3](P300)。可見廢農田而種罌粟的情況屢見不鮮。國產鴉片的產量猛增,大有替代進口鴉片的趨勢,李鴻章正是以此為依據,提出了“以土抵洋”的政策。
(二)清政府被迫簽訂“準許鴉片輸入中國合法化”條約
咸豐六年(1856年),為了擴大在華利益,英國聯合法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腐朽的清朝軍隊在戰爭中節節敗退,英法聯軍勝利在望。英國為了擴大鴉片貿易規模,攫取財富,派遣額爾金為全權特使,以期通過談判并簽訂條約的方式,達到鴉片貿易合法化的罪惡目的。因為太平天國運動而元氣大傷的清政府,又被英法聯軍攪得焦頭爛額,只希望能與英法早日達成“合議”。咸豐八年八月(1858年8月),咸豐帝密令中方議和代表大學士桂良,在談判中可以同意英方全免洋貨關稅與鴉片弛禁等無理要求。十月,英方代表額爾金在談判中正式提出了“鴉片貿易合法化”的要求。十一月,雙方正式簽訂“議和”條約,即《通商章程善后條約》。該不平等條約的第五款明確規定,允許鴉片納稅進口:“向來洋藥(即鴉片)……不準通商,現定稍寬其禁,聽商遵行納稅貿易,洋藥準其進口,議定每百斤納稅三十兩。”[1](P109)這就意味著清政府公開承認鴉片貿易合法化,英國這一罪惡而又無理的要求終于在戰爭的炮火下得以實現。罪惡的鴉片貿易不僅使中國白銀大量外流,而且不斷摧殘著國民的身心健康。清代政府對于鴉片一直主張嚴禁,《通商章程善后條約》的簽訂,對中國政府的禁煙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清政府既同意了鴉片貿易的合法,自然不能違背條約嚴禁鴉片。李鴻章意識到不能公開“塞源”,而“遏流”就更難實現了,倒不如“寓禁于征”,提高鴉片進口關稅。如此既能遏制國民購買力,又能增加稅收,一舉兩得。
(三)國庫空虛財政困難
兩次鴉片戰爭導致的巨額賠款,使清政府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再加上長達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國運動,使得全國十余省份陷入戰火之中,嚴重影響各地的稅收。清廷為了鎮壓太平天國,軍費開支巨大,“各省庫儲支絀,歷年欠餉積至一百八十余萬兩”[4](P212)。李鴻章就曾因軍費問題多次上奏朝廷,稱“淮、滬、揚、鎮等營軍食缺乏”,“教練各營餉項,暨采買軍火籌款,為數甚巨。所收關稅,入不敷出”,且“各口所收稅銀,按月盡數撥解樹字營軍餉,并無絲毫存儲。所有前項參價銀兩,委實無款可籌”[5](P497)。他還提及,交戰各省“慘不可言。小民耕種失時,流離轉徙”[6](P326),根本無暇農桑。光緒初年綿延數省的“丁戊奇荒”,更是雪上加霜。時任山西巡撫的曾國荃道本省“無余款可抵目前之急”,且“現在東漕急需運費,各郡輜重牛具急需籌備。無一項可以稍緩須臾者”[4](P722)。此外,為了學習西方以求自強,洋務派不得不向朝廷籌借餉需,因“地方著名瘠苦,并無額外可籌之款”,“進款愈少,出款愈多,遂至羅掘一空”[4](P921)。甚至內務府需用的銀兩都因“蘇省辦理軍務,各前道經收稅銀盡數湊解軍需,以致未能照解”[5](P497)。為了扭轉財政赤字,清政府想方設法進行搜刮,甚至首開厘金之稅,但都杯水車薪,未能真正解決。作為肱骨大臣的李鴻章,一方面清晰地認識到國庫空虛的現狀,一方面出于興辦洋務籌建新式水軍的需要,建議朝廷對鴉片弛禁,并附重稅,借以緩解財政緊張入不敷出的窘境。他在寫給同僚閻敬銘的回信中痛心疾首,“海內困窮已極,理財又難得其人”,“內外庫儲俱竭,部款固無可請,……財賦素雄者,今亦寅支卯糧,毫無儲積”[7](P186)。
二、李鴻章“寓禁于征”禁煙政策的主要措施
李鴻章對當時國際國內環境多方考量后,于光緒七年六月十六日(1881年5月9日)上奏朝廷,他認為“洋藥流毒甚深,既難驟然禁止,只可先加厘稅,借以稍濟餉需,而煙價較增,吸者或漸減其癮”[8](P394),同時他又擔心“厘稅加增太重,恐致偷漏愈多,亦須統盤籌計”[8](P394)。針對這種境況,李鴻章大體提出了三方面政策:
首先,設立洋藥公司管控鴉片進口途徑。李鴻章認為香港乃是“洋藥偷漏之源”,各省實施的禁煙政策不過是“截流”而已,“凡事清其源則用力少而程功易,截其流則需費多而收效寡”[8](P395)。因此,他在奏折開篇就提出“查洋藥系由印度先到香港,然后分運進中國各口。香港為英國屬地,中外奸商即于該處私相授受”[8](P394)。中轉環節監管無措,使得大量鴉片“不經新關,不收稅厘,而由沿海各項民船漁艇零星潛運內地,且多不入有關卡之正口”。據他推算,每年運至香港的九萬四千多擔鴉片,除去運銷越南、新加坡等處的一萬擔外,應有八萬四千余擔繳稅入關,但是,實際報稅的僅有六萬九千擔左右,可見至少有一萬數千余擔鴉片走私入內地[7](P448)。然“各省濱海之區,袤延萬余里,河港紛錯,沙岸無垠,勢難處處設卡”[8](P394)。為了解決這一難題,李鴻章在奏折后附有《議設洋藥公司片》,主張在香港設立洋藥公司,與英屬東印度公司簽訂合同,限定每年運往香港的鴉片數量,統一歸該公司承買并發售內地各口,不允許私人徑運,借以從源頭解決香港偷漏稅厘之禍。至于該公司應交稅厘,“則明立保結,嚴定章程”[8](P399),一切事務聽官員主持,保證毫無偷漏。這樣不但“歲餉頓增數百萬”,而且可以裁撤各省口岸及內地關卡的巡船,節省國庫開支,一舉兩得[8](P399)。
其次,規范內地轉運關卡嚴防偷漏。李鴻章指出,洋藥厘稅較重,勢必會造成偷漏者眾多。一方面,內地路徑四通八達,偷漏者詭計多端,更有亡命豪強之徒結幫販運,執持兵器強行闖關。而且,鴉片拆箱之后,輕小便攜易夾帶,即使通過關卡也不易搜檢;另一方面“走私者即偶被查出,但分給時值十中之一二,……已足償數月之辛金,未有不縱放者”[8](P394-395),甚至出現“署一年州縣缺,不如當一年厘局差”的現象[4](P851)。雖在香港設立洋藥公司最為省力,且效果最佳,然香港作為英國屬地,設立公司一事,還需要英國總督首肯才可實現,因此規范內地轉運關卡,嚴防偷漏必須先行。他提議,在海關設立關棧,鴉片進關后全部存入棧內。關棧由清廷管理,與洋人無涉。華商需要購買時,赴海關厘局交足捐稅后,到關棧領取。同時,所有口岸轉販鴉片的華商字號,必須先繳費銀五百兩購買部帖才能開設。并令五家聯保,實行連坐,一家偷漏,全部同罰。這樣,一方面領部帖要繳費且厘捐較重,轉販者勢必減少而利于稽查;另一方面出資領貼者為了保護自身利益,自然會自發舉報私販者。此外,設小輪船在海面巡緝,零星偷運者一經發現全貨充公,整船販運囤積者必重懲。
最后,加增鴉片捐數“以土抵洋”。咸豐八年(1858年)鴉片貿易合法化以后,清政府在上海設局抽厘,外國與本國煙商在各口岸進行鴉片貿易,需按議定稅則納稅。對外國鴉片每百斤征銀30兩外,另向購進鴉片的華商加增稅厘50兩,鴉片進入內地以后,按照國貨再征收厘金。對于進口鴉片的稅厘問題,中英雙方主張相悖,清政府希望通過提高鴉片稅厘以限制進口,同時也增加關稅收入。而英國政府則希望減輕鴉片稅厘以擴大對華的鴉片貿易,攫取巨額財富。光緒七年(1881年),南洋通商大臣左宗棠奏請大幅度加征鴉片稅厘,如此鴉片的價格自然水漲船高,“價貴癮輕者必戒,癮重者必減,由減以至斷癮尚可期”[8](P397)。李鴻章完全贊同左之主張,并進一步提出增加捐數,“必須各省議定,統歸一律”,中央下旨核定日期后,各地同時開辦,以免“一口獨重,奸商趨避”[8](P395)。他還建議鴉片既不能禁,還不如大量種植罌粟以驅逐進口鴉片。“土煙之毒,究比洋藥為輕,而民財亦不外耗,倘將來洋商無利可圖,洋藥漸不來華,再增土煙厘稅,亦加厲禁,尚未為晚。”[8](P396)即暫弛土煙之禁,國產鴉片不分產地,一律按照進口鴉片稅數三分減二征收,以奪洋商之利。
三、李鴻章“寓禁于征”禁煙政策的實施與影響
為了將“寓禁于征”付諸實際,李鴻章進行了多方努力。此前中英《煙臺條約》規定,“洋藥入口時,由新關派人稽查,封存棧房或躉船,俟售賣時洋商照則完稅。并令買客一并在新關輸納厘稅,以免偷漏”,但關于征收的具體數目并未達成共識,只寫到“應抽稅厘若干,由各省察勘情形酌辦”[4](P256)。為統一稅數,并提高鴉片進口關稅,李鴻章多次與英國公使威妥瑪進行談判。他始終主張“百一十兩,不可再減分毫”[9](P80),并在送交威妥瑪的《會議洋藥稅厘并征專條》中明確寫道:“洋藥運進中國口岸,每箱除正稅三十兩外,擬加征銀八十兩,稅、厘并征,應合銀一百一十兩。”[9](P82)但是,英國政府擔心加厘過重會導致鴉片滯銷,所以堅持“九十兩無可再加”。李鴻章“連日與威使往復辯論,幾于舌敝唇焦”[9](P87),英國最終允至百兩。在此基礎上,又經過出使英法大臣曾紀澤的不懈努力,終于在光緒十一年六月初七(1885年7月18日),會同英國外部大臣沙里斯伯,在倫敦簽訂《煙臺條約續增專條》,明確規定進口鴉片一律“按照每百斤箱向海關完納正稅三十兩并納厘金不過八十兩之后,方許搬出”[4](P1964)。次年朝廷下旨“洋藥稅、厘并征一事,……均于本年正月初八將舊捐截止,即于初九日在新關并征”[10](P225)。這一政策改變了以往鴉片進口的混亂情況,化零為整,抑制走私,有效保障了清政府的財政收入,緩解了燃眉之急。對于在香港設立洋藥公司一事,李鴻章特派馬建忠親到印度進行詳談,“使印度歲出鴉片或專售于中國國家,或專售于中國所指為承攬之人,通盤交易,無須輾轉于他商之手”,這樣“中國于進口洋藥無虞奸商之偷漏,貴國于出口鴉片亦歲有定項之可收”,“斯為兩全之策”[9](P83)。但由于印度公司憂慮甚多,這一計劃無疾而終。然而李鴻章提出的“鴉片箱數立有定額,每歲遞減,約積至二三十年之久減完,自然禁絕”,為“清末新政”時實行的鴉片輸入逐年遞減埋下了伏筆。光緒十六年(1890年),總理衙門和戶部奏請整頓土藥稅厘,李鴻章大表贊同,稱此舉“既可裨益餉需,且亦收回利權之一助,并可以征為禁,隱寓崇本抑末之意”[4](P2735)。不僅如此,征收土藥稅厘還可革除歷年積弊,防止地方征多報少,偷漏稅款。從此,土藥稅收成為清政府一大稅收來源。
“寓禁于征”政策的出發點是為了禁煙,然而實際上并未起到禁煙的作用,甚至更加劇了煙毒的泛濫程度,其所造成的嚴重后果,遠超于清政府既得的眼前利益。一方面,這一政策沒有真正限制鴉片的進口量,中國的鴉片進口數量持續大幅度上漲,鴉片的進口數量始終是中國對外進口貨物的第一位。鴉片進口的不斷增長,使清政府白銀繼續大量外流,這些沉重的經濟負擔最后還是落到了中國廣大人民身上。另一方面,“以土抵洋”大大助長了國內罌粟種植的興起,對國產鴉片的泛濫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消極作用。各地官員為了增加稅收,甚至鼓勵民眾種植罌粟。到1890年代末,全國每年鴉片產量高達60萬擔,是同期進口鴉片的10倍。而且,在土藥價格低廉且便于買賣的催化下,煙毒從上流社會向普通百姓蔓延,以致二三十年間,上至達官貴人,下至普通百姓,都成為煙毒的受害者。
四、結語
李鴻章的禁煙政策既是時代的產物,也是自身的需要。從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到被迫同意鴉片貿易合法化,無一不是強權即公理的體現。國際地位的低下使得中國基本喪失了外交乃至內政之主權,深諳此境的李鴻章不敢斷然與英國翻臉,只能委曲求全,“寓禁于征”。這是大時代的選擇。同時,作為提倡學習西方以求自強的洋務派領袖,李鴻章又有著提高鴉片稅厘以濟餉需的需要。他在奏折中就明確指出:“至天津所收洋藥厘金,向供海防練軍兵輪船薪糧及地方善舉之用。……擬此后洋藥進口,除海關每百斤收稅銀三十兩外,……以六成劃補天津從前收款,解交津海關庫,仍為軍餉船糧善舉等用。”之后他也曾多次奏請朝廷“于藥厘項下自歸關并征之日起,每箱提銀十六兩作為道庫洋務要款之用,庶足維持成局”[10](P55)。今天看來,李鴻章的禁煙政策弊大于利,但我們不能脫離當時的時代環境,全盤否定他的功勞。清政府整頓海防,配備新式兵器,建設近代海軍,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增加后的鴉片稅厘,“海防經費,始有專款可支”[4](P1557)。
注釋:
①相關研究有王宏斌:《清末新政時期的禁煙運動》(《歷史研究》1990年第4期);王宏斌:《試論中國禁止鴉片煙毒的經驗與教訓》(《中州學刊》1995年第1期);王金香:《南京國民政府初期的禁煙》(《民國檔案》1996年第2期);吳春梅:《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與清末的禁煙運動》(《江海學刊》1998年第4期);張龍秀等:《中國近代三次禁煙運動之比較》(《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方俊:《中國近代的禁煙運動》(《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馬德坤:《論清末禁煙諭旨與禁煙新政》(《唐山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王明星:《晚晴政府兩次禁煙的不同成效及原因探析》(《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呂鐵貞:《民國時期中國政府內外并舉的禁煙禁毒立法與實效》(《南京大學法律評論》2013年第2期);王宏斌:《兩次鴉片戰爭期間禁煙的困境——以“重治吸食”為中心的考察》(《歷史研究》2013年第1期),等等。
②詳見立早:《近年來李鴻章研究綜述》(《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2期);戴仕軍:《李鴻章研究概述》(《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A1期);章育良等:《近百年來李鴻章研究著作述評》(《湖南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王秀麗《李鴻章研究綜述》(《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盛海生:《百年來李鴻章外交思想研究綜述》(《廣西社會科學》2017年第8期),等等。
參考文獻:
[1]于恩德.中國禁煙法令變遷史[G]//沈云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臺灣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3.
[2]王亮,王彥威.清季外交史料(10)[G]//沈云龍.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臺灣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6.
[3]中國史學會.鴉片戰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
[4]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4.
[5]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2)奏議二[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6]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3)奏議三[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7]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32)信函四[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8]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1)奏議九[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9]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33)信函五[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10]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12)奏議十二[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