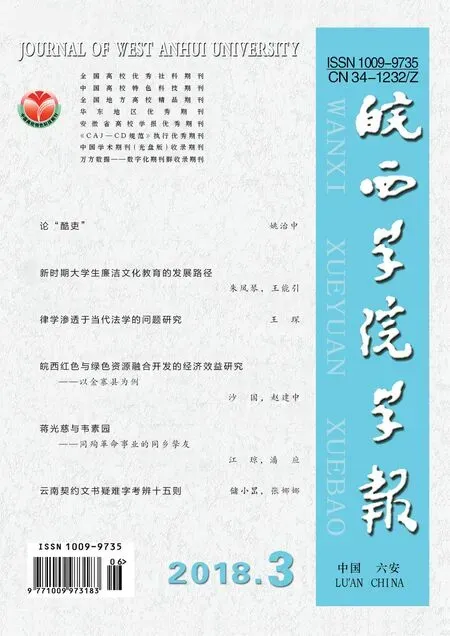論方方小說的主旨意象
——以《桃花燦爛》《萬箭穿心》為例
李 賢
(1.蘭州大學 文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2.蚌埠學院 文學與教育學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方方的小說有著世俗人生的煙火味和濃郁的武漢味,眾多相關的研究論文早已論述過。近些年,她的很多作品改編為影視劇,相比較而言,她的影視改編大多忠實于原文的意義,商業性、娛樂性的元素較少,在她眾多的小說中,《桃花燦爛》和《萬箭穿心》兩篇被改編為電影的作品不算是她文學藝術成就最高的,但這兩篇小說分別代表了方方在兩個時期對文學敘事藝術的探索,能夠代表她在小說創作時對主旨意象選取的視角。無論長篇還是短篇,無論是哪一類題材,方方的小說中總有一個貫串全文的主旨意象,并且,這一主旨意象在影視改編時也會作為一個凸顯的元素呈現在影片中。意象作為詩歌的載體在方方的小說中呈現,從早年的《風景》到長篇《水在時間之下》,幾乎都有一個貫串全篇的意象,而這一意象與文本表達的內涵相一致。方方小說的故事性很強,呈現出灑脫、爽朗、云淡風清的敘事風格和情感節奏。而在她幾乎所有的小說中,都會借助意象來反映文本中主要人物的命運,比如《隨意表白》中的“船”;或是暗示人物的心理活動,比如星子心中、眼中的“桃花”;或是表達作家個人的道德價值判斷,比如《行為藝術》中的“云”。就其表現世俗人生的意象而言,有兩個不同的體系:一是世俗人生的詩意想象,一是瑣碎日常的恒久堅韌。
一、世俗生活中的“塵”與“逸”
方方曾經在訪談中談到了她作品中的“搬運工”情結,這固然是與她早年的生活經歷有關,個人情感的表達來自于潛意識的經驗,“經驗本身具有令人滿意的情感性質,因為它擁有內在的、通過有規則和有組織的運動而思想的完整性和完滿性”[1](P40),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這一敘述視角的獨特。能夠自由地觀察時代萬象,能夠自由地轉換評價標準,能夠真實地接近生活真相,體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表現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生活是“新寫實”小說的特征之一,方方的創作大致延續這一主線,從個體觀察類型,以微觀反映宏觀。《風景》是這一流派的代表性作品,同時也是方方的代表作。文本中的“風景”讓讀者感受了人性難言的一面,那些細致入微、幽暗深邃的心理描寫以及淡然的敘述語言賦予文本虛實相生的雙重空間,自然的與人生的;客觀的與情感的,而統領全篇的“風景”在小說中則成為一個寫意兼具寫實的意象。《桃花燦爛》講述了一個發生在搬運站的故事,將單調的生活寫的熱鬧而又意味深長,以三個年輕人的情感糾葛為中心輻射性敘述。粞是故事的緣起,這一青年男性在搬運站中集合了眾多的焦點,在文本中被作者賦予了多種可能性,他的一生以及“粞”這一名字的內涵充滿了象征意味。“桃花”是這篇小說中出現最多的意象,在文本中的作用猶如張愛玲筆下的“月亮”。文本中第一次桃花出現是在星子的記憶中,粞接上大學歸來的星子,在公共汽車上,“星子心里忽地涌出了一樹樹的桃花,那一年的桃花開的分外燦爛,如云如霞,如火如荼”[2](P12)。而粞并不知道星子心中這夢魘般的桃花是他和她之間隱形的鴻溝。直到星子上大學時才告訴粞,那時“倉庫大門口一大排桃花正開的十分粲然。這些燦爛的桃花便同水香講述的那一切一起深刻地留在了星子的腦海里”[2](P39),桃之夭夭,灼灼其目,桃花從此烙印般在星子的腦海里。“成團成簇的桃花匯集成的云影。在那陰云之上,如火如荼地開放著無數艷麗的桃花”[2](P49)。每次想到粞,眼前就會浮現“桃花何其燦爛”[2](P65),直到粞的生命快要走到盡頭時,“如火的桃花在星子的腦海中為一片空白所替代”[2](P75)。桃花最后一次出現是在粞去世一周年時,星子與別人結婚卻生下了粞的孩子,粞的母親發現這一秘密并取名為“旸”,星子沉默中又見“一片桃花開放成云霞”[2](P75)。與第一次所見到的“粲然”不同,這一發現對星子而言意味著什么?敘述至此結束,留下一個開放式的結尾,讓故事在讀者閱讀接受中繼續。方方不厭其煩的描寫“桃花”的狀貌,這一由實而虛的意象主導了粞和星子的關系走向,每到關鍵的時刻就有“桃花”出現。在平緩的敘事節奏中,一些耐人尋味的對話反復出現,文本的深層含義很難確切的界定,故事前后或者說作者想要傳達的觀點有著內在的矛盾性。桃花是橫亙在星子和粞之間的障礙,當這個障礙消失時,粞的生命也到了盡頭;星子本是粞的精神寄托與夢想,當粞的多年夢想變成現實時,粞卻不在了;但最終粞的生命又以似乎最為理想的血緣方式通過星子延續了;星子是很多人的遙望,但她打破了這個期待,成就了現實的人生。這樣的結尾暗示的是什么,是成長中理想的實現與失落?還是精神的虛幻抵不過實在的安慰?無論是“風景”還是“桃花”,讀者能感受到方方善于以相反相成的意象傳達現實人生中塵土飛揚的一面與精神境界中詩意灑脫的一面,體現了人性中的“丑就在美的旁邊,畸形靠近著優美,粗俗藏在崇高背后”[3](P30)這一雨果在《克倫威爾序言》中提出的浪漫主義創作原則。在日常生活中,桃花意味著春天,代表著希望,詩經中也有“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的美好。而方方賦予了“桃花”別樣的內涵,桃花是三個年輕人不得不面對的人生現實,桃花是他們三人之間永遠解不開的情結,桃花是他們人生中“得到即失去”的一個寓言,這種打破常規思維的意象構成了文本的內在張力。
二、瑣碎日常的“恒”與“韌”
方方小說中除了“搬運站”系列還有知識分子系列,尤其是對那些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知識分子形象有較為細致的描寫,如林教授、嚴航等。這些形象與池莉的《小姐您早》《來來往往》和劉震云的《一地雞毛》中的知識分子形象有相似處。都是寫日常生活中尋求改變卻又似乎永恒不變的輪回以及面對似乎永無止境的人生困惑時西西弗斯一般的柔韌。
《萬箭穿心》是方方新世紀以來的創作,敘述了李寶莉悲劇的一生,表現了艱苦的生活與堅韌的生存。李寶莉是菜農的女兒,只上過小學的她長得很漂亮,嫁給了大學生馬學武,馬學武分到一套新房子,她以為幸福生活從此開始,卻變成苦難的開始,馬學武跳江自殺,李寶莉靠著“扁擔”養活公婆和兒子,兒子考上大學,有了體面的工作,她被兒子趕出了這個讓她“萬箭穿心”的房子。這篇小說中的意象很多,“房子”和“扁擔”是主要意象,前者象征著“安身之處”,后者象征著“立命之技”。扁擔的意象在文本中第一次出現是李寶莉到漢正街辭工那天準備加入“扁擔”時,李寶莉看見“雨越下越猛,幾個扁擔披著雨衣挑著貨,飛起地跑”[4](P199)。這一幕也是她以后十幾年的生活日常。母親到漢正街看見的是 “李寶莉正一根扁擔挑兩麻袋貨,汗流浹背地朝小河邊疾走”[4](P200)。茶館服務員眼中的她“是頭一個帶著根扁擔喝茶的女扁擔”[4](P208)暗含了她性格的兩面性;她的名字被“挑貨的扁擔”指代時,性別在世俗眼中消泯,是一個扛起生活的工作者;她被稱為“女扁擔李寶莉”時,強調了女性在這一行業內的辛苦。病愈后返回漢正街的李寶莉經歷了人生的又一次重大打擊,她“扛著扁擔,穿過曲里拐彎的街路和密密麻麻的店鋪,覺得就好像正看著一臺大戲”[4](P225)。以隱晦的筆法表達李寶莉的心緒,她曲里拐彎的人生又何嘗不像一臺大戲?艱辛與苦難并未磨滅一個城市勞動者樂觀的天性,“只要寶莉一來,滿街都能聽到她的笑聲”[4](P247)。文本中還有一些對“扁擔”呈現形態的描寫,“杵著”“舉著”“拿著”“扛著”,這些相關描寫展現了“一種小說特有的隨筆藝術”[5](P85)。同時也凸顯了意象的內涵,因出現背景的不同而有著特定的意義。扁擔的物理性質決定了方方選取時的象征意義,而從世俗普遍的觀點看,它本應該和男性聯結在一起,具有承擔生活重擔的意義,它是壓力的象征。一個漂亮的女性用一根扁擔挑起一家四口人十多年的生活,用一根扁擔供養了兒子大學畢業找到體面的工作,為爺爺奶奶買了別墅,她被趕出家門,“李寶莉用她討生活幾十年的扁擔為自己挑了一次貨”[4](P247)。日復一日的重壓磨損了她當初的容顏,磨滅了性格中的鋒芒,唯一不變的是隱忍而堅韌的生活態度,用扁擔培養了兒子之后又要養活自己的后半生。“萬箭穿心”中,扁擔是她生存的來源,支撐著她的精神世界,更是她的人生隱喻。
三、人性與生存的非詩意敘述
人性的復雜在文學作品中以不同的文體被闡釋,方方的闡釋是非詩意的,盡管她小說的情感風格是爽朗、明快的,但對人性與生存的敘述是明朗之下的暗流,從未停止對人性的探尋,以及對生存意義的追問。《桃花燦爛》中對星子、水香、粞三個年輕人心理活動的描寫呈現了人性的微妙,有研究者指出星子和水香代表了男性世界的兩種愛,但我更傾向于她們是代表了作者的價值判斷以及女性自身的兩面性,內斂含蓄與張揚怒放的生命集中于一體。如果從傳統的倫理觀出發,星子、水香和粞之間的故事中水香的做法是應該受到質疑的;而在粞、亦文、星子三者之間,星子的做法無疑是受到質疑的;如果從星子、水香的角度來看,粞是她們痛苦的制造者;而從粞和星子的角度出發,一切似乎又發生的合情合理。一個故事關聯著另一個故事,環環相扣中,每個人都成了他人痛苦的根源,但每個人又因為他人而痛苦著,讀者很難做出倫理道德的判斷。這一效果與小說的敘述視角有關,方方是從兩個不同的視點寫一件事。而“從兩個不同的視點觀察同一個事實就會寫出兩種截然不同的事件”[6](P65),這種敘述在表達人性的復雜性時有較好的輔助作用。
如果說《桃花燦爛》著重探析人性,《萬箭穿心》則著重是敘述了非詩意的生存以及家庭中的人倫。李寶莉的父親在當初看房子時的話一語成讖,是萬丈光芒變萬箭穿心的悲劇,她的人生也就在搬新家的時候開始了變故。李寶莉十多年的辛苦并未換來兒子的諒解,也沒能改變公婆對她的態度。兒子一直認為是母親讓他失去了父親因而從內心拒絕為他辛苦的母親,公婆認為是她的潑辣導致了兒子的早逝,在這個特殊的家庭中,她卑微的承擔著生活的重擔。在文本中有一個細節,因天氣不好,寶莉比平時早了一點回家,見家中無人很詫異,就走到公婆房間看兒子的獎狀,祖孫三人開門時的說笑聲因見到她戛然而止,并被質問“你跑我們房間做什么”?祖孫三人外出是去餐館為爺爺過生日,卻沒有告訴她,因為“我們自己屋里人過就行了,這不是用你賺的錢”[4](P202)。李寶莉的難堪與不甘無處訴說,畢竟兒子是她的希望,她不能惹他們生氣,“從小到大遇事都不忍自己性子的李寶莉,現在卻只剩下了一個忍字”[4](P207)在改編的影片中也有一個細節,兒子的早餐很豐盛,李寶莉的早餐是一個饅頭,一邊拿著扁擔下樓一邊拿著饅頭快速的咀嚼。作者以不同的細節描寫展現了她的生存困境,經濟與精神上的雙重壓力,尤其是當學業優秀的兒子終于有了體面的工作后卻將自己的母親趕出家門。這最后的“一箭”未能擊垮她,“人生是自己的,總得要走完”[4](P246)她以這樣一種淳樸、堅韌的生活態度完成了苦難人生的涅槃式重生。在方方的小說中還有一個奇特的模式,當矛盾激化時,會用一個生命的“缺失”或是美德的“缺失”去解決問題,而這個“缺失”的主體大多是男性。比如《桃花燦爛》中的粞、《琴斷口》中的漢漢,這兩個中篇的結構和故事都差不多,漢漢比粞更符合人們傳統的評價標準。他們生命的缺失是另一種在場,依然蘊含著“得到就是失去”這一邏輯。《刀鋒上的螞蟻》中畫家魯昌南本是一個具有那一時代所有美德的男人,后來差不多變成忘恩負義的人,作者未置一詞非議,只是側面敘述。方方通過這樣的方式讓讀者在閱讀中與她共同思考人性與生存的非詩意一面。
四、古希臘悲劇命運觀的演繹
人的意志與命運的沖突是文學作品常見的主題。按古希臘人的觀念,命運是不可知的,是不可抗拒的,是冥冥中的一種巨大的力量。而人的行為與意志,常常處于與命運的悲劇性沖突之中。《桃花燦爛》中隱含著一個“得到即失去、失去即得到”的悖論模式,在《萬箭穿心》中有個“復仇”的循環模式,小寶為爸爸復仇不認母;奶奶爺爺為兒子復仇不認兒媳,似乎李寶莉需要贖罪,她帶著贖罪的心態拼命而又卑微的承擔生活重負。有了體面工作的兒子卻將她趕出家門,帶著爺爺奶奶去別墅生活,形成一種鮮明的對比,這中間作者預留了很多難言的空白。李寶莉將這些視作“命”,“如果我出生就是來還債的,我還就是了”,就連命運也在向她復仇。在埃斯庫羅斯的《俄瑞斯特斯》三部曲中的人物都被復仇女神所控制,一環扣一環地將自己置于一系列的家庭悲劇,這里的命運是神的力量。在《萬箭穿心》中,對李寶莉來說,命運就是馬學武,他有文化,那條街上最漂亮的李寶莉嫁給了他;他分到一套新房子,只有小學畢業的李寶莉覺得自己當年的選擇是對的;李寶莉的父親參觀新房子時發現了“萬箭穿心”;搬到新家后發生的一系列事情都是父親話語的注解。一個潑辣但畢竟柔弱的女性從事男性都嫌累的扁擔,養活四口人,培養了一個大學生。卻依然被當作“外人”,直到被趕出安身之地。她當初渴望住上樓房,她得到了,新房子卻像個命運的潘多拉之盒,冥冥中注定她又將被趕出去。這里依然隱含著“得到即失去”的模式。
方方對古希臘悲劇命運觀的演繹增加了“人”的因素,李寶莉是在經歷了家庭事變之后才改變了自己的性格,每個人都是悲劇的制造者,又都是悲劇的承受者。作者避免了單一敘述視角引起的主觀判斷,在一個綜合性的社會自然環境中,審視人心、人性,“疏遠、孤獨、隔膜——這種種不可見的東西把我們束縛在生存圈內,只有人類才有這樣的生存圈”[7](P41)。在星子、水香、粞三人之間的交流中正解多于誤解,各自在自我遐想中疏遠,孤獨的個體在隔膜中越走越遠,直到一人消失不見,才又在冥想中尋求永遠不再歸來的美好。李寶莉和馬學武之間的隔膜、和兒子小寶之間的隔膜、和公婆之間的隔膜,他們疏遠她,她的做法被視為“贖罪”。方方在寫命運悲劇時更多是強調“人”的因素,因為隔膜、孤獨、以及人性中不太美好的一面所形成的日常生活悲劇。按照夏目漱石的文學觀念,“大凡文學內容之形式,須要【F+f】。F代表焦點的印象或觀念,f代表附隨那印象或觀念的情緒。”[8](P4)這里既有作家創作時的情感傾向又有讀者閱讀時個人的判斷,方方小說中的情感傾向或改編后的影視作品中的情感傾向也大致體現了這樣的創作規律。
五、結語
在小說中借助意象來寄托某種情感是中國文學作品中常見的表現手法,方方的作品在寫實的同時,還有浪漫主義的表現,以主旨意象表達作品的主要內涵是她中短篇小說中常見的藝術現象。她選取意象時注重所選意象的物理特征,以及最大可能的引申意義,或是相反相成的組合,或是具有某些共同屬性的比擬。虛擬的呈現與寫實的敘述相結合,寫世俗生活中的人們安穩現實的一面和偶爾超脫時的虛幻,以及對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尋。通過對日常瑣碎事情的刻畫,探析人性的隱秘,“得到即失去”的情節模式是對人生悲劇命運的另一種呈現,這是不得不承受的生命之重。主旨意象的運用增加了方方中篇小說的藝術魅力,她的這一藝術特征被延伸并在影視劇中以直觀、可視、立體的圖像形式凸顯。
參考文獻:
[1]杜威.藝術即經驗[M].高建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2]方方.桃花燦爛[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92.
[3]雨果.雨果論文學[M].柳鳴九,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4]方方.萬箭穿心[M].北京:東方出版中心,2012.
[5]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M].董強,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
[6]張寅德.敘述學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7]薩特.薩特論藝術[M].歐陽友權,馮黎明,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
[8]夏目漱石.文學論[M].張我軍,譯.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