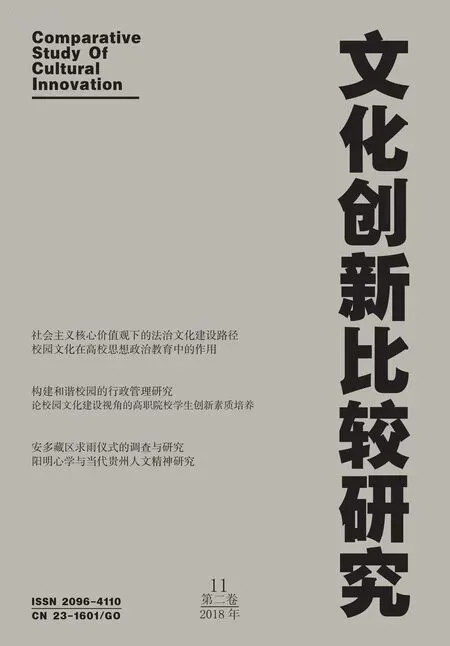《我的安東尼婭》中異化的黑人形象
楊敏
(湖北中醫藥大學外國語學院,湖北武漢 430065)
《我的安東尼亞》(My Antonia,1918)是凱瑟被評論最多、獲譽最多的一部長篇小說[1](P17)。過去,評論家多認為凱瑟的邊疆小說流露出懷舊的心理。如今,凱瑟研究多從美國文學史、美國黑人音樂、女性主義理論等角度進行解讀,然而從后殖民角度解讀甚少。凱瑟作品長期以來被視為鄉土文學代表,然而其信件、演說、作品中充滿異域風情、多元的移民文化世界是白人和北歐移民的世界。殖民話語創造出黑與白之分。凱瑟小說中東歐、亞洲移民、墨西哥裔、非裔、猶太裔美國人一直是殖民話語受害者。
1 焦慮的白人
從時間上說,凱瑟出生在內戰后的新南方,童年時期成長在祖父的柳蔭谷,家里亦是有不少的黑人奴仆。但從精神和生活樣態而言,她生在極具傳奇色彩的舊南方。弗吉尼亞是多位總統和內戰英雄的故鄉。此外,19世紀90年代,美國社會由重建時期步入后建時期。對于白人和黑人來說,這都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期。一方面,南方白人一直在與自己不再是奴隸主人的現實抗爭,北方白人也憂心忡忡地目睹黑人種族對白人文明的滲透。在階級、性屬領域已深感自身男性氣質遭受威脅的中產階級白人男性在種族領域也面臨同樣的威脅,他們害怕黑人種族的自由解放和崛起將摧毀白人種族的優越性。另一方面,從奴隸轉變為自由民的黑人不斷涌入北方城市。這個時期被譽為美國歷史上文化焦慮的高潮期。 《我的安東尼亞》(My Antonia)(1918)發表于美國進入一戰期間,此時國內也正充斥著文明排外、仇外情緒的時刻。怪物化的“他者”
小說中黑人鋼琴家達諾爾[](D’Arnault)的“異化”他者形象與白人優越性之間的張力體現出權力話語運作意義和種族文化意義。他在公共領域內的形象與19世紀黑人秀中的黑人藝人形象無異,受到白人的觀看和嘲弄。小說中,吉姆對諾爾的個人感官正是凱瑟對弗吉尼亞童年的回憶。“那是一種親切柔和的黑人的嗓音,就像我記得在很小的時候聽到過的那種嗓音,帶著馴良奉承的腔調。他的腦袋也長得像黑人;簡直沒有后腦勺;耳朵后面除了剪短的羊毛似的起褶的頸子外,什么也沒有(MA 284)”。凱瑟寫到小鎮的冬天“使人感到陳舊、骯臟、衰老、陰沉”,只有一件事打破了這種沉悶、單調的生活:“那就是黑人鋼琴家瞎子達諾爾到鎮上了”(MA 282)達諾爾在三月份來到了黑鷹鎮,他代表著“打破黑鷹鎮三月份沉悶單調生活”的力量。他給小鎮帶來了熱情和活力。
“聆聽他演奏,觀賞他演奏,就是看一名黑人用只有黑人能用的方式在獲取快樂。他彈奏起樂曲來永遠是一個粗野而驚人的黑人奇才......這種節奏感不但充滿了他那暗無天日、昏天黑地的腦海,而且不斷折磨著他的肉體”。(MA 287)
“身體是承載意義的物質性再現,也是各種可能性的實在化表現”[3](P416-417)。達諾爾出生在很南邊的一個種植園,雖然說那里的奴隸制事實上已經不存在,但其精神卻仍在延續。(MA 285)。他的母親是一個“年輕健美的黑人女傭”(MA 285)。兒時,達諾爾是一個“丑八怪的黑人小孩”。盡管成年后,他是一個音樂奇才,演奏風格粗野而奇妙。阿蒙斯(Ammons)批評這段描寫“種族主義十分明顯——副詞‘粗野’(barbarously)以及對‘節奏’(rhythm)和‘昏天黑地’(dark)的強調都是如此”[4]58。凱瑟的作品與她所處的時代在知識、政治和社會的各方面有著密切的關系。她始終未能擺脫種族優越感,這些充滿歧視性的字眼正是白人主流話語對黑人傳統形象的定位,帶著強烈的種族主義歧視。
2 種族霸權實踐
美國歷史中1913年前后,雜志和出版物禁止一切涉及黑人的內容,除非以漫畫諷刺或是進行辛辣抨擊。白人對黑人的貶損亦體現出白人性在認知暴力基礎上,對具有種族逾越可能的黑人性任意進行壓制和監管的事實-一種比嘲弄更為嚴重的種族霸權實踐。達諾爾的音樂是黑人文化的象征。
“達諾爾展開身子,撲在鋼琴上,開始彈起舞曲來,汗珠兒在他卷曲的,在他仰起的面孔上閃閃發光。他看上去像一個光閃閃的快活之神,渾身是強壯、野蠻的血液”。(MA 289)這里達諾爾象征著生育之神 ——“一個光閃閃的非洲快樂之神,渾身是強壯、野蠻的血液”(MA 289)。如此一來,達諾爾滿足了白人文化中對黑人的論斷與期待。達諾爾為這個談性色變的小鎮注入了活力。達諾爾身上承載著白人試圖壓制的欲望,白人運用這種壓制來界定自身。小說中黑人的存在只為解放被壓抑的白人欲望,這正符合19世紀傳統的種族主義論斷:從生物學上看,黑人生來注定是低等人、十足的野蠻人。在性方面他們更加“原始”、“肆意妄為”、“無拘無束”。盡管小說中對于達諾爾的描述也賦予了一些自尊,“約翰尼指引著達諾爾走了進來。達諾爾不肯讓人牽著”(MA 283)。但通過吉姆·伯登的視角,凱瑟的種族主義思想仍然占據上風。正如他在現實中的兩位原型,達諾爾可以如布恩般自強自立,展現他的自尊自愛。但是凱瑟卻將他賦予了瞎子湯姆的種植園背景,以及畸形的身體特征。盡管達諾爾拒絕別人的牽引,最終他還是被塑造為傳統的、黑人根深蒂固的形象,淪為陰暗的、原始的、動物般的“他者”,以此掩蓋白人對性的恐懼和焦慮。凱瑟正是利用這種怪物性描寫滿足了19世紀白人讀者群的“期待視野”。面對這些不公正壓迫與歧視,1964年,著名黑人運動家麥克蘭·愛克斯在其題為“黑人的革命”著名演講中指出:“美國是一個殖民力量,它剝奪了我們一等公民的身份,剝奪了我們的公民權,事實上就是剝奪了我們的人權,從而殖民了兩千兩百萬非裔美國人”[5](P197)。
3 結語
在西方作家眼中,有色人種和少數族裔往往是“異己”的他者,是西方文明陪襯下的“文化構想物”。凱瑟讀者多不愿將凱瑟小說與種族主義、仇外情緒、親歐立場聯系起來。她們將凱瑟理想化來塑造一個使人安心的美國歷史和文學版本。然而,文學作品很難穿越社會主導話語編織的權力大網。凱瑟的創作亦無法離開她所處的時代,也無法超越社會主流的影響。
(注釋:本文未特別注明出處的引文均出自維拉·凱瑟著,周微林譯的《我的安東尼亞》,北京:外國文學出版社,1983年。My Anonia以下縮寫為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