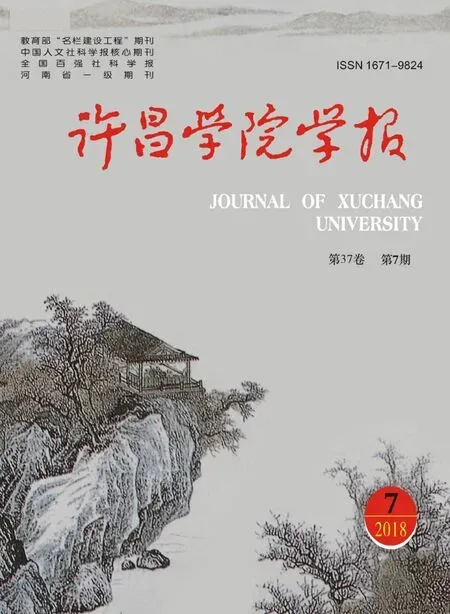王仲犖先生二三事
齊 濤
(山東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王仲犖先生(1913—1986),浙江余姚人,20世紀30年代初,為章太炎先生及門弟子。太炎先生去世后,隨章夫人湯國梨先生并其他幾位太炎弟子共同創辦太炎文學院;1942年起,任教于重慶中央大學師范學院國文系;中央大學返回南京后,任教于文學院中文系;1947年應聘至青島山東大學。此后至1986年去世,一直任教于山東大學。2011年,我曾應《文史哲》之約,介紹過仲犖先生的學術與學問,故在此僅就仲犖先生之學術精神與人文風范略述一二,可與前篇互見。
一、文史兼通的學術涵養
眾所周知,王仲犖先生是著名史學家,從他的學術道路上卻可以看到,他屬于“半道出家”者,而且他在長期的學術研究中,并未局限于學科制約,而是亦文亦史,左右兼通,融會人文,自成氣象。
仲犖先生在史學界以治魏晉南北朝史而聞名,在傳道授業中,卻并不要求弟子們局限在魏晉南北朝史或某一領域之內。記得考取先生的碩士研究生后,我們三位學生一起去先生家,先生為我們選定了三個不同方向的碩士學位論文選題:一個是對韋莊詩詞進行校注,一個是以《冊府元龜》校勘《史記》,一個是對劉劭的《人物志》進行校注。而且他對我們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對韋莊詩詞的校注要仿李善注《文選》的體例,重在明典;以《冊府元龜》校勘《史記》要補上中華書局《二十四史》校點中的一個不足;為《人物志》作注則要厘清魏晉時代人才觀的進展與變化。
我選了校注韋莊詩詞這一方向。先生將他早年所著《西昆酬唱集注》交給我學習。在先生的親自指導下,我歷時三年,完成了《韋莊詩詞校注》,畢業答辯之時,才明了先生的良苦用心。先生在回憶為《西昆酬唱集》作注時曾不無感慨地對我說:箋注工作“單靠《佩文韻府》是不行的,我就得一部一部書翻檢詩句的出處,如《毛詩》、《左傳》、《論語》、《孟子》、《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晉書》、《麟臺故事》、《初學記》、《太平御覽》、《世說新語》、《穆天子傳》、《西京雜記》、《酉陽雜俎》、《莊子》、《列子》、《楚辭》王逸注、《玉臺新詠》、《樊南詩文集》馮浩注、《文選》李善注、《全唐詩》等,一天一天地翻檢,翻檢得很詳細,不但解決了注釋問題,也充實了自己,打好了基礎”[1]590-591。我的最大收獲也是打下了基礎,對于我們這批“文革”十年中走過來的學生而言,這種基礎性的國學訓練又更具有特殊意義。先生為另外兩個同學所選碩士論文方向其實也有異曲同工之義。
仲犖先生的學術起點是《西昆酬唱集注》和聯綿字辭書的編纂。在《西昆酬唱集注》初稿草成后,先生即計劃編成一部聯綿字辭書。當時《辭通》和《聯綿字典》尚未面世,以一人之力,編如此一部辭書,實屬訓詁學的一項浩大工程。先生晚年曾回憶道:
在朱起鳳《辭通》(它是1934年出版的)未出之前,我也想仿明朱謀瑋《駢雅》例,編一部書,單收聯綿字,每天搞一些,搞了萬條以上,《十三經》、《前四史》、《晉書》、南北十史和兩《唐書》,都搞了,《楚辭》、《昭明文選》也搞了,當然還有絕大部分書中的聯綿字,還來不及輯錄,計劃是二十來年寫成。當時沒有卡片,是寫在廢賬簿的反面,大概寫滿了十七八厚本。
遺憾的是,此稿先是被先生存于余姚故居,后又寄存于親戚家,待先生1946年重返余姚時,已散失無存。先生曾感嘆道:
這一部稿本,我是準備搞到唐五代為止的,工作量太大,收集的資料才十分之三四,倘使手稿存在,還須投入大量工作量,盡管《辭通》與符定一的《聯綿字典》行世,我還是能從別一個角度來完成這個著作的。稿已迷失,我也集中精力放在史地方面,就不想從事訓詁語言之學了。
盡管如此,這項工作對先生扎實的小學功底的奠定,功莫大焉。
先生史學研究的起點是《北周職官志》的編纂。起初,先生準備編《兩晉會要》和《南北朝會要》,后聽說泰興朱銘盤先生已經編成,遂輟筆不編。在章太炎先生指導下,開始了《北周職官志》的編纂。草成之后,又進行了《北周地理志》的編纂。該兩書名為《北周職官志》和《北周地理志》,實則是涵括了整個北朝的職官與地理之志,意在填補南北朝諸史中的一個重要闕失。
不過,先生1942年秋應聘到重慶中央大學任教時,卻又是師范學院國文系的教席,擔任大一國文課。1945年秋,被聘為國文系副教授,中央大學遷回南京后,進行院系調整,師范學院國文系并入文學院中文系,先生亦轉至中文系任教。到1947年夏,中央大學中文系解聘了若干名受進步學生歡迎的教授,有朱東潤、吳組緗、蔣禮鴻諸先生,仲犖先生也在解聘之列。當時青島山東大學校長趙太侔聞訊趕到南京,延攬諸賢,先生轉至山東大學文學院,次年被聘為教授。
1949年6月,青島解放后,山東大學成立歷史研究所,趙紀彬先生任所長,邀先生至歷史研究所任研究員,進行中國古代農民戰爭史的資料整理工作。不久,歷史研究所撤銷,成立了歷史系,先生轉至歷史系任教,主要擔任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的教學。自此,先生一直從事歷史學的研究與教學。轉行不久,便成就卓然,成為國內史學界頗負盛名的史學家。
何以如此?先生治小學所打下的深厚功底,教授國文所積淀的文獻素養,加之先生所繼承的浙東學派“六經皆史”的傳統,為其文史雙修提供了良好的根基。先生良好的文學素養和濃重的文學情結,使其在歷史研究中平添助力,別開生面。比如先生在史學研究中大量引入了古典文學的元素,把文學史與文化史作為斷代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在以詩證史、以史論詩方面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
以《隋唐五代史》為例,全書洋洋百萬余言,文化史部分占了1/3強,其中,詩史、詞史又占了文化部分的2/5,達15萬字左右,僅完整引述的唐五代詩詞就有千首以上,若單獨成冊,即是一部完整的唐五代詩史。即便如此,王先生仍然意猶未盡,他在該書“前言”中寫道:
唐代的詩歌文學,是唐代文化的精華。在拙著中,初唐詩只略作介紹,盛唐幾位大家,敘述較詳。我是喜歡中晚唐詩的,所以敘述中晚唐詩特詳。但是受到篇幅的限制,作品是介紹了,對于作品的分析,卻只能俟諸異日,另成一書了。
在《隋唐五代史》一書中,討論史實之時,王先生能以詩為證,引詩入史,解決了若干疑難,在討論詩人詩作時,則以史證詩,大大加深了對詩作的認識,甚至厘正了詩人與詩作中不少傳統問題。
我完成了碩士學業,繼續從先生攻讀博士研究生時,先生為我確定的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韓偓詩校注與研究》,我初時有些不解,先生說:“做韋莊詩詞時,以校注為主,研究為輔,做韓偓詩要以研究為主,以校注為輔。”韓偓是唐末重要的詩人與政治家,曾任唐昭宗的翰林學士和宰相,是唐末歷史的親歷者,而且,其詩作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對當時重大歷史事件的記錄。注韓偓詩作,必須以史注詩,研究韓偓的時代,又可以詩入史。更為重要的是,在論文的寫作中,先生引領我以韓偓為線索,對唐末五代歷史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認識,要求我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把唐宋之際作為重點,把握唐宋變革,不要拘于隋唐五代與宋元明清的生硬劃分。先生這番鞭辟入里的教誨是在30多年前,慚愧的是,先生曾以金針度我,我卻鴻蒙未開,未能持續著力于唐宋之際。
先生雖由文入史,但對于文學之鐘愛始終未減,去世前不久,還對我說,待手頭工作完成后,要集中精力,編寫一部《唐宋文學史》。以先生渾厚的國學積淀,加之俯視唐宋社會變革的歷史視角,先生之《唐宋文學史》必當別開生面,獨樹一幟。惜天不假時,未能遂愿。
先生之于文,并非從研究到研究,紙上談兵,他自己也工于聲律,詠唱酬答,清雋自然。記得1985年秋,我購買了一本陳寅恪先生的《寒柳堂集》。先生看到后,頗為感觸,在扉頁上題詩道:
柳色遙山入夢青,去年今日到江亭。
縱然海底游塵起,還喜流鶯隔座聽。
一丈紅塵淺底揚,白丁香雜紫丁香。
宣南遺事成談助,盲鼓當年未擅場。
先生說,這是十多年前與周振甫先生唱和之作,用的是陳寅老《和陶然亭女子題壁》韻。先生詩作留存頗多,《華山館叢稿續編》中收有數十首。先生之詩,清雅脫俗,自然成章,詩人風骨躍然而出。
二、通古今之變的學術視野
先生自20世紀50年代初即專注于歷史研究,他承擔的課程是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他的研究重心也同時放在了這一領域,成就斐然。但是,他又從未把自己的視野局限于這一時期,從未給自己的研究劃定專業范圍,而是致力于通古今之變。從理論到考據,從先秦到近代,都留下了先生探索的足跡,其探索在許多領域中都能成一家之言;至其晚年,更是達到了孔子所言“從心所欲,不逾矩”。唯此,方成就了國學大家風范。
先生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嘗試將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理論用于中國古代史研究,他發表在《文史哲》1954年第4期的《春秋戰國之際的村公社與休耕制度》一文,在國內史學界首次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探討了中國歷史上的村公社問題。知名經濟學家吳大琨先生曾回憶道:
我作為一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教學研究工作者,是第一次從他那里認識到應當怎樣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考察中國古史分期問題的重要性的。那時候,仲犖教授和我都是《文史哲》的積極撰稿者,我們討論過的一些問題,或者在討論中想到的一些問題,事后把它寫下來,就成了《文史哲》上的文章。在當時王仲犖教授所發表的許多文章中,我認為發表在1954年4月號《文史哲》上的《春秋戰國之際的村公社與休耕制度》一文,是極為重要的,因為他第一次以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探討了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村公社制度的性質和作用。仲犖教授在文章中說:“許多世紀中,村公社的繼續存在,成為古代專制國家停滯性的堅強基礎。所有村公社的成員,只能成為土地的使用者——他的占有,也是經由勞動實踐過程為前提之下發生的——而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公社社員既不是公社土地的所有者,那么,他本身就會變成公社的財產,也就會變成專制君主變相的奴隸。他們把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結合了起來,完成著自給自足的生產,他們要經常地向他們的統治者貢獻力役,也貢獻物品。這些公社成員們,在身份上雖是‘自由’的,在經濟生產上也是獨立的,但這并不等于說這些公社成員們所受的剝削和壓迫就比奴隸或以后的隸農們來的輕,在某些情況下,他們所遭受的壓迫和剝削,也許還重得特別厲害。在這種特殊生產形態里,自由人生產還是占重要的地位,奴隸的勞動不能盡量代替自由人的勞動,這樣,不但阻礙了奴隸形態的發展,也會阻礙了以后農奴形態的充分發展。”我認為仲犖教授這段話是十分精辟的,他所說的“特殊生產形態”,實際上,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所以,我認為,王仲犖教授應該說是中國歷史學界第一個以他獨立的研究證明了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理論適合于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他的這一貢獻,在學術上的意義是很大的,盡管他自己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2]75-76
以此為起點,仲犖先生還積極參加了古史分期大討論,成為魏晉封建說的重要代表學者。此外,仲犖先生還就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多次發表論述,先后發表了《從茶葉經濟發展歷史看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特征》《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以前的江南絲織業》《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以前的江南棉紡織業》等論文,是新中國成立后較早進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的學者之一。先生發表于《文史哲》1953年第2期的《從茶葉經濟發展歷史看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特征》,是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大討論中的重要代表作。文章“從茶葉經濟發展這一特殊角度來論證中國在鴉片戰爭前為什么不會出現資本主義社會,中國的封建社會為什么延續得比較久。文章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征是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與封建經濟政治體制的強固結合,由于這種結合,更加強了封建階級對于茶農與制茶手工工人的殘酷剝削,阻礙了手工業向工場工業的發展,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生長,后來更由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保持了封建統治”[3]30。這篇文章被嚴中平先生譽為研究明清經濟史的創新之作,具有很強的方法論意義。先生則謙虛地認為:“中平教授是《中國棉紡織史稿》的作者,我受到他的啟發和幫助,于是也熱情地參加我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尤其茶葉經濟這篇文章,基本觀點受到中平教授的影響很大,他真是我的良師益友。”[4]前言2兩位先生的學者風范足垂后世。
寬闊的理論視野使先生的研究視角不斷拓展,新作迭出,與之同時,先生仍著力于考據之功,除早年的《北周六典》與《北周地理志》外,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先生還對敦煌文書、鮮卑與代北姓氏、中國古代物價等問題進行了系統考證。
先生對敦煌文書的考釋由兩部分構成:一是對譜牒殘卷的考釋,包括《〈唐貞觀八年條舉氏族事件〉殘卷考釋》《〈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考釋》《敦煌石室出殘姓氏五種考釋》等。二是對地志殘卷的考釋,包括《唐天寶初年地志殘卷考釋》《〈貞元十道錄〉劍南道殘卷考釋》《〈諸道山河地名要略第二〉殘卷校釋》《〈沙州都督府圖經〉殘卷考釋》《〈沙州志〉殘片三種考釋》《〈敦煌錄〉殘卷考釋》《〈壽昌系地鏡〉考釋》《〈沙州伊州地志〉殘卷考釋》《〈西州圖經〉殘卷考釋》《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考釋》《〈西天路竟〉釋》等多種。前一部分收錄在《華山館叢稿》中;后一部分則匯為《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一書,經夫人鄭宜秀先生整理后,199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先生的敦煌文書考釋主要是還原式考釋。考釋以雄厚的文獻與史學功底為基礎,廣征博引,補白祛疑,為敦煌學研究做出了艱巨而有效的基礎性貢獻。王先生對于自己敦煌文書的有關考釋工作還是比較滿意的。他曾對收入《華山館叢稿》中的幾則考釋評價道:“有關敦煌石室發現的氏族志文章,一共寫了三篇……這幾篇文章,也有扎實的,如果顧步自憐的話,我是較為滿意的。”[4]前言2這是王先生唯一一次對自己的學術研究進行評價。
對鮮卑與代北姓氏的考證屬專題性考證,有《鮮卑姓氏考》《代北姓氏考》兩文,意在條理北魏、西魏時代,在鮮卑先改單姓又轉用復姓的大變動中,各姓氏及相關集團的沿革、變化狀況。如先生所言:“自北魏孝文帝改鮮卑復姓為單姓,西魏相宇文泰又改鮮卑單姓為復姓,當西魏、北周之世,庾信有詩云‘梅林可止渴,復姓可防兵’,則改復姓之影響之大,固有關鮮卑化漢化勢力之消長,非獨一姓一氏之單語復語之變換而已也。犖既寫定《北周六典》,于西魏北周復用鮮卑復姓事,雖不得不略一提及,但言之不詳,故今復為《鮮卑姓氏考》,別成一篇云。”[5]1在《代北姓氏考》一文中,也有類似的表述。需要說明的,這兩篇考證文章合計10余萬字,均作于先生的晚年,無論是從史料的網羅殆盡看,還是從考辨中抉隱索微的功力看,都屬考證文字中的上乘之作。先生本人對其也很看重,有幾家雜志多次索稿,均未果。他多次說過,這兩篇文章要收到《華山館叢稿》的續編中,一部論文集應當有相當數量的未發表過的有分量的文章,不能只炒冷飯。
先生對中國古代物價史料的收集與考證是其學術生涯的最后一節。至1986年6月先生仙逝前,先后完成了《〈管子〉物價考》《〈韓非子〉物價考》《〈戰國策〉物價考》《〈越絕書·計倪內經〉物價考》《〈史記·貨殖列傳〉物價考》《漢代物價考》《漢晉河西物價考》《魏晉南北朝物價考》《唐五代物價考》《唐西陲物價考》《于闐物價考》,宋代與遼金夏的有關物價資料也大致收集完畢。上述考證或資料已由其夫人鄭宜秀先生匯為《金泥玉屑叢考》一書,中華書局1998年出版。
三、學者風范與愛國情操
仲犖先生是真學者,終生潛心學術,固守學術良知,但他又不是躲進小樓成一統的書齋居士,一生充滿愛國情懷,恪守君子之道,報國之志始終如一。
多年來,先生除了研究、教學之外,沒有任何其他愛好,終日在小小的書房孜孜研讀,極少下樓,常常每日能完成三千言。而且,先生的所有研究都不找人代勞,從翻檢史料、摘錄卡片,到以繁體豎排譽錄文稿,全部都是親力親為。最讓人景仰的是先生終日樂在其中,流連忘返。其故交朱季海先生曾寄詩云:
聞道年來懶下樓,書城高筑又埋頭。
古城艇子渾忘卻,不及盧家有莫愁。
先生答詩曰:
神仙自是愛居樓,慚愧捧心未著書。
風雪連天冰百丈,木蘭雙槳正愁予。
正是有如此高貴的學術品格,先生在50多年的學術生涯中,真正做到了視名利如浮云,不伐名,不自矜,固守學術良知,從不以“樸”示人。
先生在生前從不申報任何獎項,也未申報過什么項目,更不彰揚自己的學術與學問;相反,在一些情況下,寧肯學術成果不能出版,也堅守自己的學術良心,不隨波逐流。其夫人鄭宜秀先生曾回憶先生《曹操》一書修訂版的過程:
……《曹操》,1956年曾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建國后國內第一部有關曹操的著作,在當時產生了較大反響。在嗣后進行的關于曹操評價的大討論中,上海人民出版社又擬再版此書,請仲犖先生加以修訂,先生抱病對此書進行了系統的修訂,吸取了客觀的內容與評價,但沒有應景的成分。在再版后記中,先生認為:“替曹操翻案,是有必要的,因為這是使歷史真面目還原。但是,我們也不能因為擁護這一新說法,而把曹操那種殘酷的性格完全抹掉。如果把曹操所屬的那個生活烙痕抹掉,那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由于種種原因,該書未能再版。[6]前言2
先生固守學術良知方面最為集中的體現還是“不示人以樸”。前已述及,先生的兩部斷代史自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歷時30年才全部完成;其《西昆酬唱集注》與《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更是歷時40余載,反復修訂,方正式出版。以這三種著作為例,先生的研究早在20世紀40年代已達到了較高水平。1945年秋,先生申請副教授之職,重慶中央大學師范學院國文系主任伍叔儻在審讀了先生送審的《西昆酬唱集注》和《北周六典》后認為,只需將前者送教育部即可,而后者升教授也可以了。只是因為先生執教國文系,不能用此書送審。當時的教育部在請專家審查后,即聘先生為中央大學副教授。盡管如此,先生仍將這些書稿反復修改了30多年。
仲犖先生在學問上特別推崇章太炎先生的“雙軌并進”。他認為:“章先生的學問是雙軌并進的。他有純學術的著作,也有和國家民族息息相關的著作。從這一點看,就也懂得章先生為什么這樣向往顧亭林,亭林既有《音學五書》這樣純學術性著作,但也有供國家民族可以借鑒的像《日知錄》這樣的著作,雙軌并進,是并行不悖的。”[1]592
仲犖先生的學術道路也遵循了這樣一條“雙軌并進”之路,既有純學術性的《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等等,又有因應時代要求,參與古史分期問題、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等學術大討論,意在為國家、民族提供借鑒的成果。此外,仲犖先生為了在新中國的建設中貢獻一份力量,還進行了若干應用性頗強的研究,曾發表《古代中國人民使用煤的歷史》《古代中國人民發現石油的歷史》,把歷史記載中的煤炭與石油產地進行了系統梳理。先生曾回憶道:“我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山東大學學報《文史哲》上,曾發表過《古代中國人民發現石油的歷史》一篇短文,曾把中國古代記載石油的分布地區,作一概括的介紹,企圖說明只要我國地質探勘工作能展開,遲早有條件卸下貧油國那個帽子。”[7]239
需要指出的是,仲犖先生的愛國情懷與報國之志,來自他對民族歷史與命運的深刻洞察,來自他與國家與民族命運的同氣相通。遠在20世紀30年代,抗日戰爭爆發后,仲犖先生由上海輾轉香港、海防、河內,遠走昆明,投奔章太炎先生的盟兄弟,時任云貴監察使的李印泉先生,直接效力抗日大業。仲犖先生因環境不適,染上惡性瘧疾,在昆明期間,發作了不下七八次,奎寧針、奎寧片成為經常使用的藥物,最厲害的時候,體溫高到41攝氏度,神志昏沉。無奈,只能離開云南才能解決。恰在此時,重慶中央大學發來聘書,先生決定離開云南,前往重慶。
此時,日軍攻下泰國、緬甸后,又進入滇西,攻陷騰沖,進逼保山。龍云所部駐守保山的旅長龍奎垣不僅不抵抗,反而將保山洗劫后,縱火焚城,倉皇后撤。李印泉向重慶國民政府請纓,前往發動民眾,配合軍隊,確守怒江一線。見此形勢,仲犖先生毅然收起了中央大學的聘書,投筆從戎,隨同直奔前線。對這一段經歷,先生曾回憶道:我們一行人行至龍王塘之后,林蔚(時任國民黨軍令部副部長、入緬軍事顧問團團長,也撤至滇西)派人告訴印泉先生,日軍一千多人已搶渡怒江,希望印泉先生趕快撤退,印泉先生趕去司令部開會,回來告訴我們這個消息。當時許多人多勸印泉先生跟著顧問團撤退,印泉先生沉吟不語。我在天子廟坡受凍后,惡性瘧疾復發,到了龍王塘,燒發得更高,正在打針服藥,印泉先生派人來請我,征詢我的意見,我把我的看法坦白地告訴他。他比我長三十多歲,又是我老師的盟兄弟,我們稱呼他為“印老”。我說:“印老出來是抗日的,今天日軍進攻滇西,印老來了兩三天就撤回去,這絕對不可。如果形勢緊急,可以和總司令部(宋希濂任集團軍司令)一起撤退。中國的軍隊在滇西的有四五萬人,渡江的敵人只一千多人,一定能夠把他們打回去。但保山是前線,支持半個月一個月后,無論印老、無論總司令部都應退到大理,那是滇西后方重鎮,居住在那里,比較適宜。還有隨從印老來保山的人太多了,前方軍事形勢瞬息萬變,愿意回昆明的,不如讓他們回去一些好。”印老模仿《三國志》曹孟德的口吻說:“正合孤意。”后來一一照這辦了。渡江的一千多日軍,遇到我方堅強的阻擊,很快退去。一個多月以后,前線局勢轉穩,我們隨印泉先生退到大理。我在大理又發了一次燒,住了一個月,就回到昆明,由諸祖耿先生前往大理,接替我的工作,我就買車票前去重慶了。
抗戰勝利后,仲犖先生雖隨中央大學遷回南京,但對于國民政府已經失望,采取了不合作態度。國民黨政府成立國史館時,張繼出任館長,他是章太炎先生的盟兄弟,想物色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去參加修史,章夫人湯國梨先生推薦了仲犖先生等人,并寫信讓先生去見張繼。礙于師母之命,先生前去一見。見過之后,再也未曾參與國史館的任何活動。比較一下十幾年后先生十分欣然地參加《二十四史》的點校工作,真是天壤之別。他在借調校點《二十四史》行將結束之時賦詩云:
十年素榻半凝塵,借調于今又幾春。
抖擻風云誠盛事,爾來正愧有閑身。
這種精神狀態與先生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學術領域的“雙軌并進”,做經世致用之學,是一脈相承的,凸顯了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憂國憂民、救世愛國的人文情懷,這也是對中國傳統士大夫精神的傳承與升華,值得我們尊敬與學習。
先生在《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曾說,此文題名是抄襲魯迅先生的《太炎先生二三事》。弟子懶惰,也借用此意,將這篇緬念文字名之曰:《王仲犖先生二三事》,尚祈先生不責。
WangZhongluo’sPatriotismandAcademicResearch
QI Tao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Mr. Wang Zhongluo is a famous historian. In his long-term academic research, he was not confined to discipline restrictions. He was distinguished in the research of both history and literature. Mr. Wang also has an academic vision of mastering changes of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He has made explorations from the theory to the textual criticism, from the pre-Qin period to modern times as well as from academic issues such as the issue of the period of ancient history, the mode of production in Asia, to the sprouting of capitalism. He has created philosophy of his own in many fields. He has also left behind great achievements for later generations, including both the purely academic booksThesixchroniclesoftheNorthernZhouDynastyandTheGeographicalChroniclesoftheNorthernZhouDynastyand achievement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n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Throughout his life, he was full of patriotic feelings, and he followed the way of the gentleman and the dedication of his country. In his later years, he also achieved what Confucius said “do whatever he likes and does not transgress what is right” and made a national study.
Keywords:Wang Zhongluo; historian; both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cademic vision; salvation and patriot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