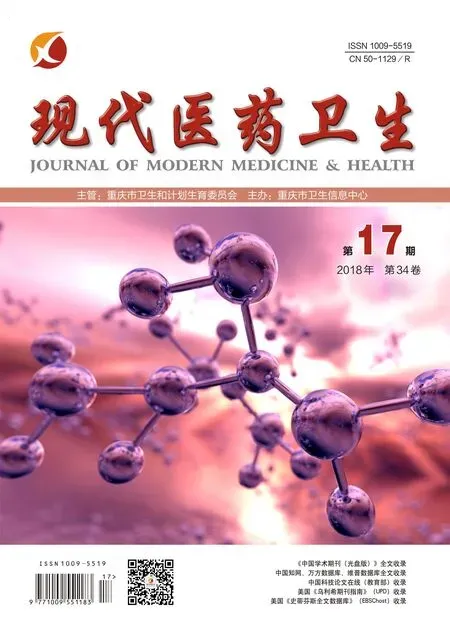異常肌反應在面肌痙攣微血管減壓術中的應用進展
張 杰 綜述,謝宗義審校(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神經外科,重慶400010)
面肌痙攣(HFS)是一側面部表情肌發作性地不可控抽動,并且常以運動支中顳支、顴支支配的肌肉抽動起病,向下發展至頰支、下頜緣支的支配區域,嚴重者甚至有頸闊肌受累,抽動頻率、持續時間可進行性加重[1-2]。HFS可以導致一系列的社交問題,發作性瞼痙攣也會使閱讀、駕駛、工作等受到干擾,發展到最后甚至可以引起患者的嚴重心理障礙。面神經的微血管減壓術(MVD)現普遍開展,能明顯降低絕大部分患者的肌肉抽動頻率、程度、持續時間等,且可使部分患者的癥狀完全好轉,總體來說極少出現并發癥,有助于患者回歸正常生活狀態[3]。異常肌反應(AMR)是一種僅對HFS患者行神經電生理監測時可得到的肌電反應波形,可作為該疾病的診斷依據,且在MVD中有相當確切的指導作用。MVD術后的監測結果變化對臨床癥狀的改善情況有一定的評估作用。本文就其術前、術中及術后的應用進展進行綜述。
1 AMR定義及機制
AMR僅能在HFS患者中通過肌電監測發現。AMR會在面神經運動支的一個分支受刺激時產生,也能在運動支的其他分支支配的肌肉處得到記錄[4]。AMR的確切機制仍然存在爭議,目前有科學爭論且廣泛作為試驗指導的假設有2種:外周假設指出,軸突間傳遞發生在血管神經壓迫處,該處的面神經脫髓鞘改變導致順向的軸突間傳導沖動產生“側方擴散”現象。而最新研究表明,AMR的起源為假突觸傳遞發生于面神經的血管壓迫部位而不是面神經核團;中心假設則認為在壓迫處的血管產生有節律的搏動并影響該處面神經的軸突,長期產生逆向信號而導致面神經核團的高興奮性[5]。2種學說能解釋MVD中電生理監測中的部分AMR變化,以及臨床結果中的延遲治愈等現象,但AMR的確切機制仍有待進一步探索。
2 AMR支持術前診斷
HFS的診斷主要依靠臨床癥狀,若有典型的一側HFS表現,同時影像學檢查(如MR增強)排除原發性病變,以及MR水成像明確有神經血管關系壓迫,即可基本確診。同時,HFS發作時,體格檢查中可發現典型的“Babinski-2征”,即痙攣側額肌、眼輪匝肌同時收縮,同側眉毛明顯上抬,同時眼睛閉合,這一體征特異度極高,但敏感度欠佳。另外,由于AMR是HFS患者的特征性肌電波形,可用于鑒別面部其他的異常功能性運動障礙。如果肌電圖監測中可見自發的同步高頻波形,則進一步支持HFS的診斷[6]。
由于部分患者在術前不能監測到AMR,目前其原因尚不明確,可能與HFS發生機制相關,故其有時難以作為證據,但結合上述因素,確診HFS并不困難。
3 AMR術中監測的意義
面神經在腦內各段均有可能受血管壓迫,其中以出腦干區(REZ)最常見,其他包括面神經在腦橋表面走形的部分、腦池段及內聽道段等,各處的神經受壓均可能導致HFS。因此,明確血管壓迫的位置并對其進行充分神經血管隔離是提高MVD治療效果的最重要步驟,術中AMR監測的效益歸功于一定條件下對責任血管的尋找及對神經血管完全隔離與否的確認。
在MVD術中,當可疑血管與該處面神經隔離完全后,若AMR在肌電圖上的波幅明顯減小或無法再監測到,則此血管可以明確為責任血管,可避免識別錯誤或遺漏。同時,AMR在肌電圖上的上述改變即表明神經血管隔離充分[7]。良好的AMR應用可以有效地指導手術進程,對于責任血管在REZ的患者,分離責任血管并墊上Teflon棉后,若AMR消失,則可以結束手術;若關顱后AMR再次出現,應再次開顱減壓,因為絨球、小腦等的解剖復位可能導致新的責任血管再次壓迫面神經;若血管壓迫位置不在REZ,應認真探查面神經其他各段是否有可疑的壓迫血管,并進行充分的神經血管隔離,之后若AMR仍存在,且余下振幅仍大于50%者,則需行神經梳理術[8]。若行完全的神經血管隔離后,且在肌電圖上仍能監測到AMR,則行神經梳理術可以極其有效地改善患者的臨床表現。雖然短期內患者可能較容易發生面神經麻痹,但絕大部分患者長期隨訪時均能自行好轉[9]。另外,有極少數患者的責任血管為靜脈,由于臨床數量較少,難以形成有統計學意義的結論,故其更多AMR特點有待進一步臨床研究。
由于術中AMR監測可以幫助判斷責任血管,避免不必要的解剖、牽拉等,減少神經血管損傷,因此并發癥產生較少,但監測本身對MVD的臨床結局并無太大影響[10]。同樣,即使不行術中AMR監測,患者術后的臨床治愈率在1周和1年以上隨訪的結果分別為83.33%、94.2%,與行AMR監測的患者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11]。盡管術中AMR監測并不能直接影響手術結果,但其臨床應用價值仍然被廣大學者認可,其作為一個特異性指標,在MVD中起客觀的指導作用。但由于AMR在術中的可變性,導致其無法使每例患者受益,隨著對HFS和AMR機制的進一步研究,AMR可能有更實際的效用。
4 AMR指導二次手術
HFS的MVD效果明顯,有患者在手術結束后痙攣即可消失,但也有患者在術后數周、數月甚至1年后癥狀才逐漸緩解,其在臨床上稱為延遲緩解。對于這類患者,是否行二次手術及手術時機是神經外科醫生關注的重點。其中,術后AMR監測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有學者認為,延遲緩解的根本原因在于減壓不完全,包括責任血管的遺漏(尤其是被大血管遮擋的小血管)、Teflon棉滑落、填塞不當等。因此,對于術后痙攣沒有立即緩解的患者,可在術后第1天行AMR監測,若AMR存在,則短期內再次手術減壓可明顯改善預后;若AMR消失,則可隨訪觀察[12]。另外,由于Teflon棉不能被吸收,時間久后會黏附于面神經,致使分離困難,從而增加手術風險和并發癥發生率,甚至可能切斷面神經,因此建議二次手術越早進行越好。為確保減壓充分,術中需仔細解剖面神經各個分區,尤其是面神經延伸至內聽道處的探查;完全分離面神經營養血管,若術中血管痙攣則暫時停止手術,待緩解后再次操作[13]。
也有學者認為,二次手術不宜過早進行。對降低神經興奮性一類抗驚厥藥敏感的患者而言,面神經核過度興奮可能是其主要致病機制,這類患者在術后需要數月來使面神經核恢復到正常興奮閾值,繼而出現延遲緩解。因此,如果患者術前對抗驚厥藥物敏感,且術后癥狀持續,二次手術至少需延遲3個月以上[14]。
HFS的MVD術后癥狀緩解不滿意,絕大多數是由于減壓不充分引起。為解決其根本原因,有必要行二次手術,尤其是術后AMR仍然存在的患者。有研究指出,行二次甚至多次手術的患者,其中大多數患者能有持續的痙攣緩解,即使相對容易發生并發癥,患者總體而言能獲得良好的生活質量,且其與年齡、再次手術時間、痙攣復發時間等無關。手術最好由有經驗的外科醫生操作[15],手術時機目前仍存在爭議,但無論早期還是晚期手術,臨床預后均能得到明顯改善。
5 AMR對預后的評估
已經明確AMR在HFS MVD中的必要性,其對臨床預后的評估一直是研究的熱點,但仍然存在著爭議,爭議內容包括AMR在MVD中的早期消失對臨床預后的影響,以及術后AMR消失是否預示較好的臨床預后等。因此,明確AMR變化與臨床預后的關系可進一步評估患者的臨床結局,為再次手術的必要性提供更精確的指導。
5.1 術中AMR早期消失與預后的評估 術中AMR監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MVD的效率。但遺憾的是,若AMR在神經血管減壓前(包括硬腦膜打開前后及隨后的腦脊液釋放等)消失,且直到手術結束時仍未再監測到,則表示此類患者將不能受益于AMR對責任血管的判斷和是否減壓成功的確認。減壓前后的AMR消失與臨床預后的關系逐漸被學者所重視。
由于AMR在減壓前消失且不再出現,術中監測對手術將無任何指導作用,因此,隨后的責任血管尋找、減壓充分與否等只能依靠術者的經驗。有學者認為,術中AMR早期消失可能是由于面神經壓迫程度較輕,因此,此類患者術后HFS更有可能即刻緩解。同時,由于壓迫簡單而減少了某些不必要的操作,故發生的并發癥較少[16]。然而,另一項前瞻性研究結果指出,在術后1周、3個月AMR在減壓前后消失與臨床結果無明顯關聯,而術后2年及以上AMR在減壓后消失組的痙攣緩解情況較好[17]。
術中AMR早期消失的原因尚無定論,其與臨床預后的關系在不同研究間也大相徑庭。但是早期AMR消失對手術操作者而言并不是一個好消息,其沒有客觀指標的指導,一切僅能憑借經驗,為避免手術失敗,需要進行更仔細和更完整的解剖及減壓。因此,外科醫生的經驗和術中認真仔細的操作也對手術的成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即使AMR早期消失,仍需繼續監測AMR,以免AMR在余下的手術過程中再次出現,避免責任血管遺漏,指導充分減壓。
5.2 術后AMR消失對預后的評估 HFS患者行MVD后,大多數患者即不能監測到AMR,也有患者出現AMR的波幅減小甚至較術前無改變。
經過充分減壓后,17%的患者會殘留AMR。這些患者在術前并沒有典型的臨床或電生理特點,且術后AMR消失與否與并發癥沒有明顯關聯[18]。有學者針對隨訪時間、術后效果等條件進行嚴格的納入和排除原始資料,最后匯總1 301例樣本進行meta分析,對于減壓術后隨訪3個月及以上、AMR全部消失的患者其HFS緩解率是部分或沒有消失患者的2.48倍[19]。因為AMR與血管壓迫的相關性,術后AMR即消失表明REZ區的責任血管搏動產生的直接刺激消除,因此在短期內隨訪中有著較好的臨床結局。由于神經血管壓迫部位的長期病理生理改變,使得該處面神經產生微損傷,因此,即使充分減壓后AMR可能仍然存在,但隨著數月對微損傷的完整修復及面神經核高興奮性的逐漸穩定,HFS癥狀逐漸好轉。因此,術后AMR消失與否和長期預后并沒有明顯關聯[18,20]。
術中AMR監測對臨床預后的評估作用有限,MVD術后AMR消失的患者中有89%的患者能夠被治愈,即使AMR術后仍然存在,也僅有24%的患者HFS無好轉[19]。在充分減壓后,即使AMR存在也不一定預示臨床預后不好。
6 監測方式的發展
有時AMR在減壓開始直到結束均不能監測到,或者即使在減壓之后典型波形持續存在,又有術中波形不穩定或被手術操作影響等,均使其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為增加AMR的監測率、穩定性等,提供更有意義的手術指導和預后評估,學者提出了新的聯合監測方法。
“最佳監測”:刺激患側面神經顴支,在同側的其他所有運動支分支處接受記錄,這樣即使一支波形消失或不穩定,其他分支處可能監測到相應波形,可提高AMR陽性檢測率和對減壓結果預言的準確度,減少延遲治愈的發生[21]。“雙重監測”:同時刺激顴支、下頜緣支,且同時在相應分支支配的肌肉處接受并記錄肌電圖,雙重監測的AMR檢出率較高,相比傳統監測更加敏感。就結局來看,雙重監測的患者無論術后AMR消失或存在都有著較好的臨床效果[22]。聯合ZLR監測:ZLR僅在術中刺激責任血管的時候出現,并且減壓成功后即消失,其客觀指導作用更直接、更精準,相比單一的AMR監測,聯合ZLR監測能提供更多有效信息,在以椎動脈為主要壓迫血管的“串聯型”患者中,術中ZLR監測對責任血管的尋找更是起決定性作用[23]。鑒于AMR可能在減壓前即消失,此時對判斷責任血管和減壓成功與否的幫助非常有限,聯合ZLR監測能提供更有價值的術中指導,尤其是可能存在多根責任血管的時候[24]。
在改進監測方式的同時,某些影響監測結果的因素也應該避免,但某些因素的改進和具體化能讓監測更加有效。傳統刺激強度范圍大多為1~30 mA,由于范圍較小,可能忽略AMR某些模式的改變,為達到AMR的引出閾值,推薦刺激強度范圍增加到1~100 mA,這樣可以提供更精確的臨床評估作用[25]。另外,即使氣管插管后繼續行部分神經肌肉阻滯麻醉,其對AMR的監測成功與否并沒有影響,并且在LSR監控過程中,如果保持麻醉后肌肉松弛監測的T1/Tc比例為50%,還能減少肌電圖上自發波幅的產生,提高監測精確性[26]。
7 小 結
綜上所述,AMR對于HFS的MVD指導意義巨大,但AMR變化對臨床預后的關系仍然存在著爭議,有待研究更加全面和有效的監測方式。在進一步明確HFS和AMR機制后,AMR監測指導下的MVD才能進一步改善HFS患者的臨床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