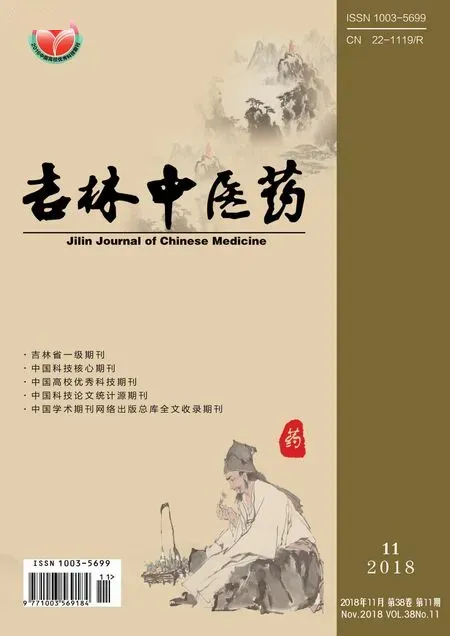《傷寒雜病論》從“精”“神”辨治思路之我見
王興凱,呂翠霞,王光澤,張慶浩
(山東中醫藥大學,濟南 250014)
《傷寒雜病論》辨治詳細而全面,用藥精當,治法多樣,其辨治理論不僅涉及六經、八綱、臟腑經絡,亦涉及其他方面。深入挖掘《傷寒雜病論》辨治理論對于臨床指導辨證、確立治法具有重要意義。筆者從“精與神”這個小層面談一下學習《傷寒雜病論》的體會,以期給臨床辨治疾病帶來一些啟發。精與神作為人體之寶,在人體中所處的狀態,對于陰陽、氣血的調和,疾病發生發展變化的趨勢及辨治疾病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深入了解精、神的含義及關系對臨床辨治、預防疾病具有重要指導作用。
1 精和神的含義及關系
神發于心,其在肝氣溫升之時,神未顯旺,此時顯現的是肝所藏的陽魂。精藏于腎,其在肺氣清降之時,精未充盈,此時先凝結的是陰魄。《素問》:“隨神往來者謂之魂,并精出入者謂之魄。”陽氣初升,未能化神,先化其魂,陽氣全升,則魂變而為神。魂是神的初始之氣,所以魂隨神而往來。陰氣初降,未能化精,先化其魄,陰氣全降,則魄變而為精。魄是精化生的初始基礎,所以魄并精而出入。精和神的化生是精微物質在氣的升降運轉流動中實現的,最終藏于腎和心。“精”和“神”在中醫學中有特定的內涵。廣義的神是指人體整個生命活動的外在表現,狹義的神是指人的精神意識思維活動;廣義的精是指人體內的血、津液及先天之精、水谷之精、生殖之精、臟腑之精等一切液態精華物質,狹義的精是指具有繁衍后代作用的生殖之精,藏于腎中,亦稱腎精。以下所論及的精和神是狹義的精和神,亦即“心神”“腎精”[1]。精和神在生理上相互依存:腎中所藏之精充足則能上養心神,有精則有神,精足則神旺;同時神旺則可斂降心火不至過亢而通過少陽膽之相火下暖腎水使腎精充足得固。其次,精和神在病理上相互影響:一方面如腎精損耗太過,則無力上養心神,心神失養則不安而對心火失去有效的制約,而使心火上炎太過,同時少陽相火不能下潛去溫暖腎水,腎水失溫而過寒則會使腎氣的固攝之力減弱,從而加重腎精的流失;另一方面,如心神自身出現問題,心神失常,心神不安,則不能有效地制約心火,使心火不能正常下固腎水,神不交于精,心神、心火浮越過度而產生一系列心神失常的病證。另外,由于腎精和心神的特定關系,心神可以直接作用于腎精的封藏和施泄,這是通過腎氣來實現的。
由于心藏神,腎藏精,心屬火,腎屬水,神和精的關系也是心和腎關系的表現形式。人體在正常生理狀態下,心腎相交,水火既濟,則表現為精守神藏。若精不守,神不藏,出現比如失眠、焦慮、健忘、心律失常、卵巢早衰、遺精、早泄、小兒遺尿等疾病則是由于心腎不交、水火不濟的病機因素。而究其根本則在于脾胃之中氣。陰升陽降,權衡制約在于中氣,中氣衰敗,升降失職,肺金、腎水收藏失職,肝木、心火生長之氣郁滯,脾氣下陷則精不交神,膽胃之氣上逆則神不交精,此精神分離而疾病作。陽神上揚飛蕩,所以產生驚悸、失眠、健忘等病;陰精馳走不藏,所以產生遺精、早泄等病[2]。
2 從精和神辨治疾病在《傷寒雜病論》中的體現
2.1 桂枝加龍骨牡蠣湯證 《金匱要略·血痹虛勞病脈證并治》曰:“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陰頭寒,目眩,發落,脈極虛芤遲,為清谷亡血,失精。脈得諸芤動微緊,男子失精,女子夢交,桂枝加龍骨牡蠣湯主之。”[3]男子失精,女子夢交是主證,在脈象上可以表現為“芤動微緊”。“芤動”是指芤脈,為陰血虧虛,陽氣浮越之象;微緊指的是虛弦的脈象,此處主虛寒、營衛失和。精液久瀉,不僅造成陰虛,陽氣亦因之而虧損,進而累及脾胃之中氣。脾胃為陰陽升降,精神相交、調和的樞紐,中氣虧損,陰陽、精神升降調和之道路受阻[4]。腎精不能上升交于心神,心神得不到腎精有效的滋養,造成心神虛弱不能有效地制約、調控心火,而心火浮越;心火為君火,君火浮越,是因相火之浮越;君相之火浮越,心神亦受擾而不安[5]。《素問·生氣通天論》曰:“陰陽之要,陽密乃固。”今陽氣浮越,不能下潛固攝,產生目眩、發落等癥,并進一步加重了腎精的走泄。同時下焦陽氣受損,又得不到君火之使相火的下潛溫煦,而產生少腹弦急、陰頭寒、男子失精、女子夢交等癥。針對此證,仲景用方桂枝加龍骨牡蠣湯治療。桂枝加龍骨牡蠣湯由桂枝湯加龍骨、牡蠣組成。治療精神不交的失精病為什么要以桂枝湯為基礎方呢?其一,此病是虛勞之為病,陰陽氣血不足且處于失衡狀態[6]。徐忠可在《金匱要略論注》中說:“桂枝湯外證得之,能解肌去邪氣;內證得之,能補虛調陰陽[7]。加龍骨、牡蠣者,以失精夢交屬精神間病,非此不足以收斂其浮越也。”因此得知仲景用桂枝加龍骨牡蠣湯治療精神不交的失精病,取的是桂枝湯補虛調陰陽的功用。其二,精神不交、失和也是心腎不交病機狀態的體現。心腎不交不僅是心腎二臟功能失常、不和,亦與全身各臟腑功能升降失常有密切關系。而脾胃中氣為陰陽升降、心腎相交的樞紐,脾胃氣血充足,中氣升降功能正常是陰陽水火心腎相交的重要保證[8]。桂枝湯可以調補脾胃中氣,中氣升降功能復常,則進而使心腎相交通[9]。而此方的關鍵之藥在于龍骨、牡蠣。龍骨,《本草新編》載:“收斂浮越之正氣……及婦人帶下崩中,夢寐泄精。”牡蠣能收斂潛陽,《海藥本草》載:“主男子遺精,虛勞乏損,補腎正氣,止盜汗,去煩熱,能補養安神。”這里用龍骨、牡蠣一是鎮驚安神,二是收攝陰精。陰精內收不泄,自可上交心神;心神安定復常,心火下潛,心神亦可下交腎精。精神相交,中氣健運,失精之病乃止。
2.2 黃連阿膠湯證 《傷寒論·辨少陰病脈證并治》303條曰:“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臥,黃連阿膠湯主之。”[10]此證由于腎精、心血素虧,腎精虧少,不能上交滋養心神,心血虧虛,不能涵養心神,心神虛弱不安,不能有效地制約、調控心火,心火上炎亢盛,進而擾及心神[11],心神不能安定下潛交于腎精,君火亢炎則少陽膽之相火亦隨之上浮,故而出現心中煩、不得臥等癥。此病偏重于神不交于精,心火獨亢于上,心神不安,故治療重點亦偏于心火、心神,使心神安定,神交于精則諸癥自愈[12]。仲景方用黃連阿膠湯,方中黃連、黃芩清降上炎之心火、少陽之相火,除煩熱。《本草新編》載:“黃連,味苦,寒,可升可降,陰也,無毒。入心與包絡。最瀉火,亦能入肝。大約同引經之藥,俱能入之,而入心,尤專經也。治火眼甚神,能安心,止夢遺,定狂躁,除痞滿。”《長沙藥解》載:“黃芩,味苦,氣寒,入足少陽膽、足厥陰肝經。清相火而斷下利,瀉甲木而止上嘔,除少陽之痞熱,退厥陰之郁蒸。”阿膠為主,配伍芍藥、雞子黃,可以滋養腎陰、腎精,補養心血,同時亦可降心火,安心神。心血得充,心神亦得養,心火斂降,心神亦得安定,故而心神得以下潛交于腎精,神交于精,故煩擾、驚悸、失眠等癥俱消。此方用藥妙在雞子黃,因此藥用治精神相交的必要條件即中氣脾胃樞紐,中氣健運,升降復常,則精神相交之道路通暢;中氣斡旋,陰陽升降、精神相交“動力”亦充足。《長沙藥解》載:“雞子黃,味甘,微溫,入足太陰脾、足陽明胃經。溫潤淳濃,體備土德,滋脾胃之精液,澤中脘之枯槁,降濁陰而止嘔吐,升清陽而斷泄利,補中之良藥也。”
2.3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證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112條曰:“傷寒脈浮,醫以火迫劫之,亡陽,必驚狂,臥起不安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主之。” 傷寒脈浮,邪氣在表,而醫以火劫發汗,致使汗大出,陽氣亡脫。汗為心之液,亡陽則心氣虛,心氣虛則心神無所憑使;心惡熱,火氣通于心,火邪內迫,神被火迫而不守,則心神浮越,故而驚狂,起臥不安。此證病機偏于神不交于精,先是火劫發汗,使汗大出,耗傷心之液即離中之陰;心為陽中之太陽,心神在心中之所以能靜守安定不僅由于腎精的上交滋養,亦因為心之液即離中之陰的涵養。現心液耗傷,心神所處“沖虛之境”已然破壞。另外,火邪內迫,心神直接受擾,故而心神浮越不能安定沉潛。還需要注意的是,此證病機不僅是心神浮越不安、神不交精,還有心之陽氣的損傷衰微,且將有亡脫之勢。因火劫發汗致大汗出,心之陽氣亦隨大汗出而外瀉過度,致使心陽受損衰微欲脫[13]。仲景治此證用方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桂枝湯用芍藥是取芍藥的酸斂之性,此證因迫汗外泄,津液既亡,無液可斂,且用之亦降瀉陽氣,所以去芍藥。用桂枝、甘草溫復受損之心陽;加龍骨、牡蠣既能收攝浮越不安之心神,又能固澀收斂衰微欲脫之心陽。心神安定沉潛下交腎精,心陽得以斂固,則驚狂自止。《長沙藥解》載:“龍骨,味咸,微寒,性澀,入手少陰心、足少陰腎、足厥陰肝、足少陽膽經,斂神魂而定驚悸,保精血而收滑脫。牡蠣,味咸,微寒,性澀,入手少陰心、足少陰腎經,降膽氣而消痞,斂心神而止驚。”蜀漆味辛能去胸中邪結氣,此處用之是由于此證火氣內迫心包,須逐邪而安正氣。
2.4 百合地黃湯證 《金匱要略·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脈證治》“論曰:百合病,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復不能食,常默默然,欲臥不能臥,欲行不能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用聞食臭時,如寒無寒,如熱無熱,口苦,小便赤,諸藥不能治,得藥則劇吐利,如有神靈者,身形如和,其脈微數”“百合病,不經吐、下、發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黃湯主之”。百合病是由于外感熱病之后余熱未清,或情志不遂郁熱傷陰,使心肺陰虛內熱,百脈失養未和而致的以精神恍惚不定、口苦、小便赤、脈微數等為主癥的病證。此病偏于神不交于精,此時腎之陰精未耗傷尚能上交心神。心中之陰液即離中之陰乃心神所處之“宮城”,也可稱為“沖虛之境”。此時,心中之陰液受外感病余熱或郁熱耗傷而生虛熱,故心神所處“沖虛之境”被打破,同時又受虛熱擾動,腎精雖能上交,卻不能改變心中陰液損傷、虛熱擾動的病機。所以心神不能安定沉潛下交腎精且功能失常,產生精神恍惚不定,行動、飲食、語言失常等癥[14]。仲景對百合病的辨證亦很精細,若百合病不經誤治,則用百合地黃湯治之。方中百合可除心肺之煩熱而滋養心肺之陰液,并可安神益志,使心神靜守下交腎精。《本草新編》載:“百合,味甘,氣平,無毒。入肺、脾、心三經,安心益志,定驚悸狂叫之邪,消浮腫痞滿之氣,止遍身疼痛,利大小便,辟鬼氣時疫,……又治傷寒壞癥,兼能補中益氣。”《長沙藥解》載:“百合,味甘、微苦,微寒,入手太陰肺經。涼金瀉熱,清肺除煩。”生地黃汁重用,以清心肺血分之虛熱,補養離中之陰、肺之津液,是故“宮城”恢復、虛邪祛除,心神得以靜守沉潛,功能亦恢復正常,則諸癥自止。《本草發揮》:“潔古云:生地黃性寒,味苦,涼血補血,補腎水真陰不足,治少陰心熱在內。”
2.5 桂枝加桂湯證 《金匱要略·奔豚氣病脈證治》曰“師曰:病有奔豚,有吐膿,有驚怖,有火邪,此四部病,皆從驚恐得之。師曰:奔豚病,從少腹起,上沖咽喉,發作欲死,復還止,皆從驚恐得之”“發汗后,燒針令其汗,針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小腹上至心。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主之。”
神發于心而交于腎,則神清而不浮搖。神不交精,故生驚悸,而其根源由于膽胃之不降。厥陰肝木上行,而生君火,少陽膽木下行,而化相火。相火之降,依賴于胃土,胃氣順降,陽隨土蟄,相火下根于腎水,所以膽氣充足而心神安謐。相火即君火之佐,相火下秘,則君火根深而不飛動,所以心定而神安。胃土不降,相火失根,虛浮驚怯,神不交精,心神不寧,這是因為君相同氣,臣敗而君危,所以陽魂動搖而心神飛蕩。胃土之不降,是由于脾土之濕。神不交精,君相之火炎于上,腎水沉寒,驚悸不愈,陰氣凝結,時間越久越堅固,歷年增長,狀如懷子,稱為奔豚。悸動出現于臍下,則根本振搖,奔豚發作。
患太陽表證,發汗后,表仍不解,又用燒針的方法逼迫發汗。一汗再汗,表仍不解。這是因為神不交精,少陽相火不能下根腎水,腎中陽氣不足,素寒陰盛。且發汗過多,耗傷心之陰液,使心氣不足。從針孔外入之寒氣挾腎水陰寒之氣乘心虛而上沖,故必發為奔豚[15]。治療時,仲景采取在針處結核上各灸一壯,以斷其外寒內入之路,然后內服桂枝加桂湯。方中重用桂枝,以降上沖陰寒之氣,并可溫復受損之心氣、腎中之陽氣[16];生姜、大棗、甘草調補脾胃中氣,使中氣強健,升降功能復常,胃土順降,少陽膽木之氣亦隨之下行,神下交于精道路通暢;芍藥斂降少陽膽之相火,使相火下根于腎水。諸藥合用,使腎水溫煦,陰寒凝結之氣溫散,脾胃得健,陰陽調和,相火下秘,君火根深,神精相交調和,心神安謐,沖逆亦止[17]。
3 結語
精、氣、神在中醫被稱為人體的“三寶”,特別是精和神的密切關系在機體生理、病理上具有重要意義。精神正常相交,對維持機體臟腑正常生理功能,調整氣化具有重要作用。另外,精與神的關系狀態在疾病發生發展變化的病機趨勢上亦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18]。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中對疾病的辨治也很注意兼顧精與神的狀態,如桂枝加龍骨牡蠣湯證、黃連阿膠湯證、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證、百合病、奔豚氣病桂枝加桂湯證等。
《素問·生氣通天論》中記載:“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精與神正常相交也反應了機體的陰陽平衡協調[19],故臨床診治疾病注重調整機體陰陽平衡協調的同時,調和精神的狀態,使精神正常相交,則陰陽亦能隨之而順調,對于縮短病程、增強療效、精確辨證具有重要意義。例如臨床遇到病機復雜的疾病且有神志異常的表現,在調整心神的同時兼顧精和神的關系狀態,使神下交于精,精神相交調和,而不僅僅是安神,如此治療效果則會明顯而迅速。神非重鎮而不能下潛,故用藥常選龍骨、牡蠣等。另外還須兼顧心神下潛的“通路”及膽胃,若“通路”不暢,臨床常選用半夏、芍藥等順降膽胃,條暢“通路”[20-24]。遇到虛勞失精、早泄等疾病,辨證屬腎氣虛不固者,治療不僅要補腎固精,同時兼顧精和神的關系狀態,使精上交于神,調和精神,則治療效果要比單純補腎固精明顯,臨床常選用桂枝、附子、龍骨、牡蠣、茯苓、甘草、芍藥等,如此則腎水溫、肝脾升、精神相交調和而病證止。所以我們學習《傷寒雜病論》辨治理論和方法的同時注重兼顧精和神的狀態,調整精神相交,便可在臨床診治疾病時如虎添翼,顯示中醫之“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