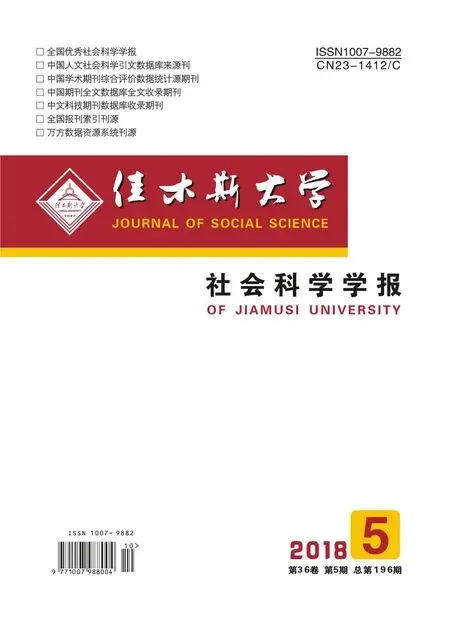寂寞的吟者*
——論呂新小說的歷史文化蘊含
王 宏
(太原學院 中文系,山西 太原 030012)
初識呂新,是他的那部《阮郎歸》。文字的酣暢有致,章節的舒展有度,故事的舒緩自如,使人愛不釋手。一路“讀”來,發現呂新一直保持著“在路上”的心態,他總是在不斷地超越著自己,嘗試著不同的寫法。從早期那個“初來乍到,迎頭碰面像個大姑娘似的,微笑著點點頭,羞答答地同你擦肩而過……”的作者呂新。[1],到后來那個大刀闊斧行走在新形式邊緣的“第一個讓世界知道晉北山區”的作家呂新[2],再到現在這個“能夠呈現文學史‘意義’”[3]的作家呂新,他一直默默地行走在創作的邊緣,“在潔凈、安寧、簡單的環境里生活、寫作……依靠想象和感覺,虛構出新的長中短篇小說”。[4]借用李銳的話,“呂新就是呂新。呂新靜靜地躺在自己不曾被污染的純凈當中,一任語言的溪流淙淙遠去。”[5]
一、尋覓,在時間的長河里尋找空間的縫隙
呂新在與王春林的對話中,坦言中國1970年代對他有著特殊的意義,“最讓我放不下的還是七十年代,正是我成長的時期,每次想到那個時期,腦子里就會有無數的頁碼排列著擁擠著,想通過一個出口出來,就象我們國家火車站的檢票口和出站口一樣。那些頁碼上的內容密密麻麻,有些具體的段落、敘述、描寫,甚至其中的對話,我常常都能清楚地看見,甚至瞥見有的是未來哪一本書里的東西。”[6]
作者揀拾起一片片散落在民間的“文革記憶”,把它們艱難地縫合連綴在一起。正如他在《白楊木的春天》獲獎時所說,“我想要說的就是,歷史不應該被遺忘。”與1980年代風行的傷痕小說、反思小說截然不同,呂新似乎無意對整個社會,尤其是官方社會展開血淚控訴,他更多地把目光投向民間,投向那一片片遼闊的農村,投向那純樸得快要被人們遺忘的鄉情民意。
《掩面》的主題,顯在的是“尋父”,潛在的是尋找親情、尋找自我。隨著少女的一路尋來。因為敘述者的不同,所以父親的形象也千變萬化、截然不同,或懦弱無能命運多舛,或溫情脈脈甘于命運,或頑固落后不思進步……唯獨沒有大義凜然的英雄形象。盡管父親年輕時也曾經義無反顧地投奔了革命,甚至差點為了革命喪失了寶貴的生命。這種悖反,既是父親的性格使然,更是時代使然。如果說少女一開始是滿懷信心的,那么隨著尋找的深入,她陷入了彷徨,有些不知所措。這一個個突如其來的打擊,讓她措手不及,因為尋找父親的同時,她也在確認著自己的身份——她不滿意現實強加給她的“黑五類子女”,她企圖把自己尋找成根正苗紅的“紅衛兵世家”。沒想到,結果會自取其辱!于是,最初的“父親想象”在眾人的唾液中土崩瓦解,她的尋找原動力自然而然地分崩離析。不但如此,還面臨著自我的崩潰:一個革命敗類的后代,一個革命背叛者的子女,一個革命不忠者的信徒。這樣的人,注定只能成為被批判的對象。原本清高獨異的自我,此時只能落荒而逃,感恩戴德地感謝社會讓她回歸群體讓她擁入上山下鄉的大潮。可以說,尋覓而不得,反而失去自我,是《掩面》這部小說最大的悲劇。
同樣的尋覓出現在《下弦月》中。徐懷玉拋家舍業與女友蕭桂英匯入艱難的“尋夫”之途,走街穿巷、翻山越嶺。嚴冬時節,她們走過了一個又一個村莊,卻始終未能尋找到逃亡在外的丈夫林烈。與《掩面》相同的是,這“尋”,本身就是一種隱喻:尋找親情、尋找未來、尋找希望……不同的是,這里的“尋”,更多呈現出民間的溫情。盡管有以供銷社為代表的冰冷的官方話語,但更多的卻是充滿溫馨的鄉情話語,如陌生大娘的一壺熱水、素昧平生的獸醫大哥的接納……更加難得是在這一路尋找中,她們收獲并加固了難能可貴的“友情”——蕭桂英舍棄了自己難得的幾天假期,甘愿陪女友踏上尋夫歷程,而且她很清楚,她們所尋找的這個人是國家是政府正在通緝的現行反革命犯。要知道,文革期間是一個人人自危的時代。每個人看似每時每刻都在解剖自己,又無時無刻不用繭來包裹自己,惟恐被他人拋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小說里就有黃奇月對外來者——上一屆工作隊遺留下的“親情隔閡”“相互猜忌”“相互懷疑”的批判和揭露。所以,這里的“尋覓”,無形之中就有了“尋找友情”的命題。
《白楊木的春天》中的曾懷林又何嘗不是在“尋覓”。尋覓安謐,尋找不被打擾,尋求一方被白楊樹包裹起來的凈土。
不僅作品人物在尋覓,而且呂新自己也在尋覓。正是這在尋覓中,呂新看到與眾不同的風景:盡管上層政治意識形態丑陋不堪,但民間卻不失其溫情,親情、友情、人情正悄然滲透于冷酷之中。
同時,懷著悲憫情懷,呂新為作品中的人物總是設置了一個個獨異的空間,一個個被社會棄置的空間。而正是這“棄置”,給了人物以休養生息的憩園,以喘息的機會。曾懷林的家安置在一個遠離他人的荒郊,一圈白楊木不僅增添了幾分美景,更重要的是從他人的視線中逃離,能暫得幾分自由。徐懷玉的家更是奇崛,幾間烈士陵園深處的小屋,使他們與鬼雄相伴,再加上一條又陡又長的坡路直接將塵世的喧囂拒之門外,而他們卻可以俯瞰城中的蕓蕓眾生。
更有象征意味的是,作者在小說中設置的“桃花源境”。
《白楊木的春天》,作者營造了一個桃花源般的世界——隱蔽的菜場。那是一個別樣的世界,所有的人都是一律平等的過客,都被一視同仁。更有意味的是,它絕對稱得上是“曲徑通幽”。在經過了那么漫長的尋找,走了那么多曲里拐彎的路途,等到達時才發現實際上這個菜場就隱藏在平時路過的路徑之后。作為一個象征世界,它隱含了太多的東西:美好、純真、善良、潔凈……一個沒有任何污垢的原世界。在那樣一個冷酷似鐵的時代,有這樣一個溫馨世界的存在,不僅透露出作者歷史觀——歷史是有其兩面性的,官方與民間,并不是截然分割的,而是潛在地扭纏在一起;而且暗示出作者的寫作期望——在時間的長河里,企圖尋找空間的縫隙。
尤其是最后,作者安排了一個耐人尋味的“邊緣世界”,一個冰天雪地包圍的山村——云崖,它有著舊時“天高皇帝遠”的蘊意。只是文革時期,國家強權并沒有放過一寸一毫,仍然利用“宣傳隊”滲透到這里。它的進駐就直接暗喻著作為巡視檢查人員的的到來,意味著國家政策的直接下達。盡管村長王果才例行公事般地盡心盡力地同時也有幾分不耐煩地投入這場“神圣而重大的祭祀”,但是,村民自有他們對付的辦法。因為宣傳隊的“娛樂只是附帶的小部分難以避免的功能。有時候這種功能想努力地淡化,消減,卻也沒辦法做得更干凈,更徹底,總還是能讓人分享到一些娛樂的果實”。于是,他們有了自己的“狂歡”,那是純屬于民間的不屬于官方的“狂歡”——村民們只是把宣傳隊的宣傳當成是“表演”是“演戲”,看熱鬧一般地滿足著自己的審美。至于宣傳隊到底宣傳了什么,他們不在乎也不在意。這完全背離了宣傳隊的直接使命。可以說,這是非常有意思的官方啟蒙與民間被啟蒙的交鋒,很難說清,在這里哪一方是正哪一方是野。
《下弦月》中林烈在被剝奪做“人”的權利,放逐人世之外后,逃亡了很多地方,但所到之處都是陰云密布。他不知所歸。迷迷糊糊中,他又流亡到了十多年前曾經下放的山村。盡管已經是人不人鬼不鬼,但還是被老村長黃奇月認出,黃冒著危險將他安置在了距離村落不遠的“棄置地”。在“夏秋天兩季,顏色繽紛,紅綠黃紫”的灌木叢中,在“圓乎乎的繞來繞去”的丘陵之間,那里有一塊流亡人的樂土。正如《白楊木的春天》里是“曲徑通幽”,這里也不過“距離上深澗僅有五六里,距離胡漢營也不過十里”,是一個“孤懸在世界以外和時間以外的地方”。身心疲憊瀕臨死亡的林烈終于能夠在這里休養生息,慢慢舔舐遍體的傷口。
這些桃花源境猶如海市蜃樓,架空于人世之外。既是作品中人物身心養息之處,也是作者呂新精神的后花園。它隱喻了無數東西:獨立、自由、平等、溫情……是作者對外在殘酷世界無聲的抗爭,是作者企圖在時間的縫隙里尋找自由空間的愿望。正如魯迅所說,“愛夜的人,要有看夜的眼睛和聽夜的耳朵。”呂新靜靜地行走于時間空間之外,悄然而理性地回首著中國1970年代那一段酷烈的歷史,正如《白楊木的春天》在《十月》首刊時“編者的話”里所說,呂新“超越簡單的概念和感觸,對當時的環境和精神進行理性的還原”,完成著他“有意味”的歷史敘述。
二、叩問“失語”的知識分子群落
在《掩面》《白楊木的春天》《下弦月》等回溯歷史的小說中,呂新首先本真地展現了政治畸形時代國家強權統治下的知識分子的不幸,他們不僅物質受困——難得有吃飽的時候,唯一的改善是可能就豬皮作成的餃子、火中的燒土豆;而且精神上面臨的困境——被長久以來堅信不疑的組織拒之以門外而產生的信仰危機;不被他人容納的“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要到哪里去”的存在危機。在長久地被放逐的過程中,以曾懷林、林烈、石覺、孫渡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陷入了迷惑、彷徨和不知所措,作為知識分子群落中的一員,呂新靜靜地叩問著筆下每一個知識分子的精神良知:在遭到外界集體閹割的狀態下,“失語”的知識分子也試圖保持著自身的話語。曾懷林即便是在被裸體搜身的境況下,還慶幸這個北方小城對他的“寬容”——至少沒有慘忍地非人道地檢查他身體的隱私部位。院子里那棵正繁花似錦開得紅紅火火的海棠樹,讓他感覺到人間尚有些許溫暖。所以,即使再難再累再不堪,他也堅守著“思考”的習慣。“我思故我在”。于是,便有了他與落難的原縣長車耀吉關于知識分子在當時困境下如何解脫的一場對話:
無論從哪一個方面來說,跑肯定是不對的,而找一個山高水遠的把自己藏起來更是可笑的。或許,只有等待才是最應該做的,也是僅能夠做的。
“就像坐在一列沒有燈光沒有明確行駛方向的夜車上。”車耀吉對曾懷林說。
“等待什么呢?”曾懷林問,“等待天亮?等待到站?”
“當然是形勢的變化。”
“形勢會有變化?”在曾懷林的眼前出現了路兩旁的灰色的樹林,墳墓,吃草的牛馬。
“按照唯物主義的觀點,世界首先是物質的,那也就是說世界是時刻都在運動著的。既然在運動,怎么可能會沒有變化?運動有時會以一種極其緩慢的方式進行,那也只是我們用肉眼觀察到的一種現象,從另一個方面來看,也許并不緩慢。”
“根據物質不滅定律,現有的很多東西也并不會因此消亡。”
“但它們極有可能會轉化為別的事物。我們寄希望于什么呢,不就是這個么?”
盡管曾懷林是悲觀的,車耀吉是樂觀的,但這場討論,或者說這兩個知識分子的深層次的“思考”交流,至少讓曾懷林“乘坐沒有燈光沒有明確行駛方向的夜車的那種感覺逐漸變得清晰起來了”。也許“剝奪”是最好的辦法,正如解放初車耀吉他們所做,但他們目下正是“被剝奪”的對象。
這場對話,既揭示了歷史長河中革命的血腥丑惡與身處其間的人的無可奈何地承受,也表現了知識分子無論環境怎樣苦劣,都試圖極力維持他們的“內在話語”。很多年前,魯迅曾經感慨中國是個“無聲的中國”,希望每一個中國人都開口說話,“將自己的真心話發表出來”,“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7]當時魯迅有是感于強權壓制下,“文言文”嚴重阻礙了普通老百姓的“話語權”。文革期間,中國再次經歷了一次“無聲”,這次“無聲”是知識分子的被迫“閉口”,被強行剝奪了“話語權”。一個階層,一個群落,如果失去了公開發言的權利,失去了正當的話語權,也就意味著將要失去屬于自己的獨特記憶,將要從這世界上慢慢淪亡。
更為深刻地是,作者毫不隱晦地表現了他們身上的知識分子情結——與世俱來的清高。這是自古以來知識分子就具有的天然品性,在文革這樣一個特殊的對知識分子進行回爐改造的時代,也并不能清除它的痕跡。這一點,突出表現在曾懷林對待老宋的態度上。盡管老宋費心費力地給曾懷林的家圍上了籬笆,種上了樹,但他對老宋的尊敬只是表面上.深夜捫心自問,“他把老宋看作是朋友了嗎?他拷問自己,結果是沒有……他內心深處的那道白楊木柵欄卻從來沒放老宋進來過。”正是他的深夜自問,無形中道出了另一個真理:一個人的精神領域是不可能完全被強權統治的,它屬于個體的私密空間。一道白楊木柵欄,是知識分子最后的心靈屏障,也是作為人的個體的最后的盾牌。
可是,如果一個人“失語”太久,就會面臨嚴重的精神危機,比如還有沒有生存的價值?呂新在“樂觀”地表現了知識分子身處困境仍不忘堅強、不忘斗爭之時,也把更多的筆墨深入他們的內心,寫出他們的精神危機——外部勢不可擋的政治大潮在摧殘了他們身體的同時,更多摧毀的是他們的內心。他們中很多人不僅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甚至開始質疑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這才是最悲慘的。《下弦月》中,民間能人黃奇月帶給死亡絕境中的林烈不僅僅是吃食,是蔽身之處,更多的是“精神食糧”——生的意志。
“老黃。”
“嗯?”
“你看我的定量,我在這個世上的那點兒定量,是不是也早就用完了,沒有了?”
……
“你叫我分析,我就給你分析一下。你現在每天還有飯吃,那就說明這世上還有你的定量,至于那飯是從哪來的,先不要管他,管他是從哪來的,飯吃到了你的肚子里,就說明那份定量還是你的,如果不是你的,你是吃不到你的肚子里的,你信不信?”
“你說的好像也有道理呢。”
正是黃奇月無微不至的照顧和寬心,使林烈重拾做“人”的信心。在這里,民間不僅僅是官方歷史的補充,它有著它自己的自足性和完滿性,而且某種程度上承擔著拯救官方的重大歷史使命。
要警惕的是,當國家機器被系統地用來剝奪公民的記憶時,那么公民記憶就面臨著被“重塑”的絕境。而“極權統治剝奪臣民的記憶之日,便是他們受精神權役之始。”[8]《下弦月》中,有這樣的對話:
“好多東西,你以為忘了,其實沒忘,只是平常不提,讓別的一些東西給壓住了,遮擋得嚴嚴實實,其實它們都還在。”
“老黃,你這話我信。可是一個人要是長期處于一種被追攆著的狀態,會什么都想不起來,會什么都不記得。”
所以,在肉體經受壓迫之時,如何避免精神也被奴役思想也被重塑,是每一個身處逆境的知識分子都應該思考的命題。呂新借助他筆下的人物,給出了形象的答案:肉體可以妥協,思維不能妥協,必須極力保持“獨立思考”的“內在話語”。
三、是“文學”,亦是“哲學”
呂新的小說,一路讀過去,會發現很重的哲學氣息,作者借小說文本解說著他的哲學觀念。而這形形色色閃爍在文本中的思想點滴,欲說還休。
《掩面》采取了非常巧妙的“形式言說”。文本表面看似是對話,又不是完全的對話;看似是獨白,又不是完全的獨白,而是一種潛在的對話體。這種潛在的對話形式,作為一種被遮蔽的交往哲學,主說人不僅無視受話人的存在,更抹殺其所說對象的存在意義。五個主說人口中的父親形象各不相同,到底哪個是真的?或者說各個階段的父親串連起來才是一個真實的父親形象?這個父親是徹底“掩面”的,是被遮蔽的,正如現在少女的主話權被剝奪一樣。在哲學命題里,交往是一種言談張力,是一種凸顯主體與他者共同存在的社會性結構,是一種可能達成共識的社會性關聯。可惜,《掩面》里的五對交往關系,都沒有形成真正的交往。
根據巴赫金的對話理論,獨白是不等待也不產生回應的話語,而對話是呼喚并通常引發答復的話語。因此,對話側重于受話人的感應,要形成一種互動關系,形成一種雙向交流。而《掩面》里的對話只是自說自話,說話人根本不理會受話人的感受,只是一種無謂的單向輸出。
無論是巴赫金的對話理論,還是馬克思的交往理念,都異曲同工,道出少女在被剝奪對話權的同時,也在逐漸失去社會交往的權利。無論說話人出于怎樣的心思,少女最終都沒有與說話人產生對話,零星的幾句插話,不過是說話人進行獨白式說教的話頭。于是對話轉為對白,這本身就是一種不平等,是一種隱含剝奪,少女無可避免地陷入失聲境地。少女顯在的失聲過程,正好應證了父母隱形的失語歷程。
常規來說,主體自我只有在與他人的不斷對話中才能逐漸建立,《掩面》里的少女無形之中被剝奪了對話的權利,也就沒能建立起完整的自我,最后只能認同別人的看法,被迫投降,放棄尋找父母的努力,下鄉做了插隊知青。這就是為什么整個文本看似是少女尋找父母的過程,其實是認同父母、確認自我的過程。可惜,這兩個過程均告破滅。另外,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失鄉的過程,少女對父母、對自我的確認,緣于沒有最后的精神家園,但千辛萬苦之后,卻仍然面臨無鄉的困境。因此,為了彌補此自我空白,呂新在第五章用了三首“詩歌”來隱晦了表現了少女的情感。
另外,通過這種獨白式的絮叨,還潛藏了一種不平等——隱含作者與作品人物的不平等,作品人物成為隱含作者解說的對象。人物越是侃侃而談,越是袒露其無知,就越能通過字里行間暗含的嘲諷語調感知到作者對他的批判態度。《掩面》中的四個分述人,分別代表著天命論、官本位、機械唯物論、小農意識等不同的生存哲學,借助于他們各自的嘴,呂新完成了對他們的嚴厲批判。比如,第四個敘述人機械唯物論生存哲學的荒謬,就是通過她自己的獨白完成的:她自己在大喜之夜,要求與丈夫共同學習毛主席著作;自己一歲大的孩子看到蔣介石的照片,叫了聲“爺爺”就遭到她的一頓毒打,說是混淆階級陣營;當孫渡女兒稱她阿姨,她拒不接受,說這個稱呼抹殺了斗爭,體現出無原則的調和。
《下弦月》利用的是“時空錯置”,逃亡中的犯人林烈是正解,以“供銷社”為中心的公眾形象則是負解。在逃亡中,時間混沌,空間模糊,“只有白天與黑夜之間尚有明顯的界限,其余全部攪成一團,不再能看到本來的面目。”“村莊統統都無一例外地形同海市蜃樓”。猶如飄蕩在幻境,人的思緒也捉磨不定,最能接近事物的真諦。回首自己的人生,林烈驀地發現:
“事情的順序應該是自上而下地開始的。就像一座塔,先是在最高處的塔尖上有了一些細小的動靜,最高處有人在掰手腕,但沒有人注意,事實上也不會有人注意到。從一座塔的塔尖上掉下來幾粒沙子,誰能看見,誰又能注意得到?令人吃驚的是它的所有的步驟或者說方法,就算是自上而下地開始的,那也應該是一層一層地下來,最后到達塔的底部,然后再從底部向周邊蔓延,燎原,這才應該是正常的步驟和次序。但是這一回,奇就奇在它直接從塔尖直達底座,底下哄泱泱燒著了,然后火勢和濃煙才又一層一層地往上走。”
這是對國家政策獨具特色的解讀,頗有傳播學的意義。一語中的,道中文革的發源所在。
供銷社是呂新在小說中設置的一個官方空間,作者以酣暢淋漓的語言,模仿農民的口吻,闡釋了文革時期的國家形勢國家政策,文革的主流意識形態化身為“農民的唯物哲學”:
“階級斗爭無時不在,無處不有”。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的貨物,如頭發,豬鬃,羊毛,杏仁,野兔和黃麻草之類,絕對不能收,因為他們的東西也是腐朽的,表現出絕對的排外、絕對的愚蠢。
“滿足于虛假的市場繁榮”。供銷社里平紋布、帶耳朵的鐵鍋、餅干、古巴紅糖……,進了多少就還有多少,人們購買的僅僅是生活必需品,就連布鐵鍋、紅糖也屬于奢侈品無人問津。可見當時的物質生活水平有多低。萬年青卻閉上眼睛,進行瞞和騙,說人們把供銷社當成自己的家,當成自家的倉庫和集市。
“人的生命是如此輕賤”。供銷社里的糖,廣大的貧下中農的孩子們,無錢能買。售貨員偷吃了供銷社的幾塊糖,最后被上綱上線,只能上吊自殺。更為荒唐的是,為了杜絕吃糖事件的再次發生,他們計議來計議去,竟商定擬用一個“糖尿病患者”!于是,尋找糖尿病患者全城啟動。
“工作作風堪憂。”在每一個領導干部眼里,貌美的陳美琳是他們可以染指的尤物,也是可以隨意丟棄的性具。當然,我們的萬年青同志也抵擋不了誘惑,不過不是有染陳美琳,而是成為上級葉柏翠的掌中物。
正如石覺所說,“一場聲勢浩大的風暴里面,不知道包藏著多少個人恩怨和各種無恥的小動作。我有時候甚至覺得整個世界,所有的歷史,是不是就是由這些東西構成的?”歷史某種程度上成了“行私利逞私欲”的勾當。
正是借助“供銷社”這個污濁的空間,呂新把嚴肅的高高在上的政治拉下神壇,拉到世俗,讓讀者看到一幕幕怵目驚心的“惡俗哲學”,完成了正義與丑惡的反轉。
四、消解與重構“先鋒”
從1986年《那是個幽幽的湖》走入文壇以來,呂新就一直沒有放棄他的先鋒創作。無論是《葵花》《石灰窯》,還是《撫摸》《阮郎歸》,甚至近幾年的《掩面》《下弦月》。只是,細細解讀呂新的作品,總有那么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呂新似乎在解構“現代”“后現代”中重構“先鋒”,即消解與重構并存。
《掩面》采用第一人稱多角度敘事的方式來呈現主人公的命運歷程。這種敘事方式產生了一個“我”、“你”、“他”多方面的敘述關系:你接受到的我,只能是他口中的我。這一切依賴于“他”的舊時認知記憶和現時話語加工。最終形成的后果是,真正的“我”只能掩面站在“他”敘述的最后層面,默默地忍受被宰割的命運。當然,“我”到底是什么樣子,“你”最終也無法弄明白搞清楚。這種第一人稱多角度敘事的方式切中了“歷史在還原的過程中被篡改”的命脈。作者有意識地采用了“去理性”的敘述方式,企圖還原歷史的無理性性。所以,文本中的少女對于父母到底認知了多少,很難說清楚。
于是,本來應該具有強烈主觀性的第一人稱敘事,在《掩面》中悄然轉化為傳統的客觀的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稱敘事。當然,也就失去了第一人稱敘事這一現代敘事方式本應具備的真實性、親切性和自然性,變得冷酷而嚴峻。
為了反抗這種冷酷,呂新又采用了小說與詩歌雜糅,形成一種“跨文體”寫作。整部小說共有六章,前四章以及最后一章是小說文體,而第五章“黑色筆記本”則采用了詩歌的表現形式,寫有三首詩,分別以“家”“失蹤的革命者”和“上山下鄉”為標題,記錄了“1967年5月”、“1968年2月”和“1969年4月”少女尋父途中的心緒。前四章被訪者話語的密集和少女話語的稀少形成鮮明的對比。很大程度上,因為少女身份的被壓制,話語權的被剝奪,使文本在內在情感上陷入失衡。為了彌補敘述上的不均衡,為了給少女的一個表達、紓解和反駁的機會,也為了彰顯少女地位的重要,小說第五章特辟一詩歌體例。這其中,既蘊含了少女對父母的思念、對家庭的渴望、對現實的不滿、對真相的揭示,更寄寓了作者對人物處境的同情和對現實黑暗的憤慨。正是借助于詩歌的抒情性、音樂性和形式的分行性,使第五章非常突兀地呈現在讀者面前,也啟發了讀者做深層次的思考,從而把握文本的主旨。
他們都不在
而一個正常的家庭 是聽不到
那種細微聲音的 鑰匙
用小蟲子般的聲音和你說話 匯報家里的情況
句子破碎、錯落、參差不齊,形象地展現了一個眾聲喧嘩中寂寞冷靜的家。少女作為這個家唯一的主人,她的孤獨、她對父母的思念、她對家的渴望,萬千情愫悄然從詩句中走出。當然,細細品味也不無對社會的憤慨、被放逐的無奈和凄涼。這些詩是少女心靈的狂歡,大無畏地消解了“五人敘述組”為代表的官方立場的話語主權,顛覆了其革命信仰和存在哲學。
《下弦月》更是在“供銷社歲月”的章節里,采用第一人稱敘事方式,借人物萬年青自己的嘴,真實地呈現官方話語的荒誕,形成一種隱在的客觀批判。
而且,《下弦月》更值得稱道的是“拼帖”手法的采用。《掩面》借五個人的敘述來拼湊一個主人公形象,如果說這是一場簡單的“拼帖”游戲,那么到了《下弦月》,作者已經能夠十分嫻熟地運用著這種技巧,并將它發揮到極致。
拼帖,原是一種繪畫技巧,后發展到文藝創作,成為后現代文學作者慣用的一種敘事方式,他們充分利用生活中的各種“碎片”,如俗語、新聞、剪報等,將其轉化成文學作品的組成部分,以呈現生活的原生態。上面說到的“跨文體寫作”,實際上也可以看成“文體拼帖”。呂新在《下弦月》中,既化用了來自西方的拼貼技術,又將自己對歷史的體會充分揉搓進去,變成獨具特色的拼帖敘事。文本一共采用了三個主拼帖,一個是徐懷玉走遍周遭城市鄉村,尋找丈夫林烈,但無果而歸;另一個是林烈一路逃亡,最后在黃奇月的幫助下總算是暫時有了避難之所;還有一個是以萬年青為首的供銷社的興辦和發展。第一個拼帖,真實地反映了文革所造成的知識分子家庭慘局,親人天隔一方,生死渺茫,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第二個拼帖,既有民間俠文化,又有古代的桃花源空想,還有西方烏托邦的影子。在揭露文革給知識分子造成巨大的身心傷害的同時,也作為各種文化的載體,使作品更具厚重感;第三個拼帖,則是當時的官方話語在偏遠山村基層行政層面的貫徹和實施,體現了文革話語對普通老百姓的精神無孔不入地侵蝕。它們既截然不同,又各有聯系,同時并存于當時特殊的時代。如果說前兩個是主框架故事拼貼,具體形象地體現了作品的主題,那么第三個則作為前兩個的補充,與其形成話語拼貼,既顯示了官方話語的彌滿性,也顯示了民間俗話語的威力性,如作為官方話語的化身萬年青和葉柏青共同投降于“性”的欲求,某種程度以人性為主要組成部分的民間俗話語以其勃勃生機絕對地解構了官方話語。
具有呂新特色的是,作者借助主要人物徐懷玉、林烈之間的夫妻關系,以及地域的重疊(林烈流落的地區正好是供銷社所在的區域,徐懷玉尋夫也正好在這一地帶),很自然地消解了拼貼敘事固有的凌亂性、分裂性和片斷性。同時,借助主題的嚴肅性或多或少地消解了拼貼的戲仿性。在此基礎上,呂新充分發揮了拼貼的自由性和靈活性,利用人物、事件、時間、空間的轉換,使各種話語相互交鋒,展現了廣闊的社會圖景。
除此之外,作品還有許多與主拼貼交纏在一起而相關性不大的人物事件。作為“補丁敘事”,它們既豐滿了主體故事,也自成體系,表現了文革帶給廣大蕓蕓眾生的苦難,從側面控訴了官方意識形態的無處不在。如朱瑾為了存活,穿著內襯綴滿口袋的大衣,除夕在醫院里賣蜂蜜,由一個純粹的高雅文化的代表蛻變成俗得不能再俗的俗人;石覺三次入獄,不過是因為提醒領導讀錯了字,由一個風流倜儻的書生催化成潦倒的“擭煤工”;蕭桂英作為小學教師,難抵校長的壓迫,慢慢地被侵蝕墮落;林烈周圍的同事、難友一個個相繼莫名其妙地失蹤、死亡……
作為先鋒作家,呂新不僅一直行走在先鋒的邊緣,在作品中默默地進行著他的先鋒實驗,既汲取西方現代派后現代派的營養,又不失中國語境,形成別具一格的先鋒特色;而且一直行走在歷史的邊緣,以潛在的現實視角去透視歷史敘事,就在對歷史的還原中又解構歷史,使歷史成為復雜的融合當下與當時的文化空間:官方與民間并存、文學與哲學并存、強制失語與獨立思考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