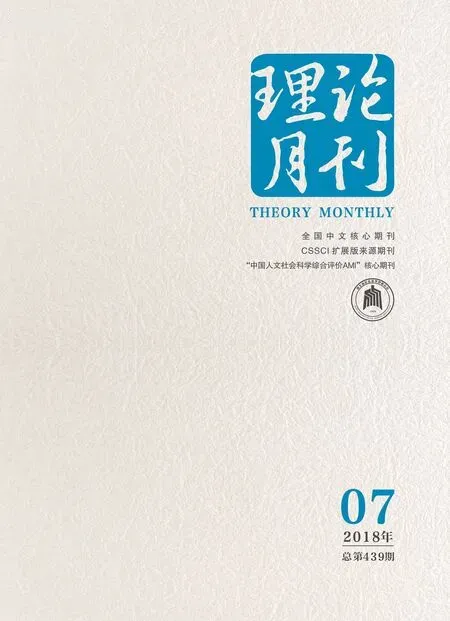論當代大陸新儒學的“修正異端”思維
□ 譚紹江
(1.華中科技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2.湖北經濟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 武漢 430205)
當代大陸新儒學(家)是一個組成較為復雜、思想極其活躍的思想家群體①狹義的定義主要指參加了2004年貴陽儒學會講的蔣慶、陳明、盛洪、康曉光等人(參見:張世保著《大陸新儒學評論》,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3月版,第1頁)。《新世紀大陸新儒家研究》中增列了干春松、黃玉順和張祥龍三人(參見:崔罡,等著《新世紀大陸新儒家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1頁),郭齊勇教授所列包括“湯一介、龐樸、張立文、余敦康、蒙培元、牟鐘鑒、陳來、楊國榮、郭齊勇、吳光、李存山、張祥龍、顏炳罡、景海峰、吳震、黎紅雷、朱漢民、張新民、蔡方鹿、舒大剛等”(參見:郭齊勇《如何正視中國大陸儒學的新發展》,載中華孔子網2017年7月9日)。最廣義的定義則是“中國大陸凡是持儒家價值立場的人都應計入”“至于大陸新‘儒學’,則只是大陸新儒家當中的一部分人的學術,即其思想理論方面的建樹”(參見:黃玉順《也論“大陸新儒家”——回應李明輝先生》,載《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4期,第50頁)。。基于日益濃厚的傳承發展優秀傳統文化的社會氛圍,這一群體的規模不斷擴大,而學界對其研究亦不斷增長。如何透過當代大陸新儒學(家)紛繁復雜的理論表象來把握其本質性的思想脈絡,成為研究者們日漸聚焦的問題。筆者不揣淺陋,擬從傳統儒學本有的一種“修正異端”思維視角切入,對當代大陸新儒學(家)做一種扼要分析,從某種角度把握其發展脈絡,以期就教于方家。
一、傳統儒學“修正異端”思維及其影響
博大的寬容精神和情懷是儒家思想的主旨,大家熟知其貴“和”、重“寬”、求同存異等理念,但這并不意味著儒家思想中沒有對“異端”進行排斥的內容。苗潤田教授指出,“排斥異端也是儒家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1](p201)。儒家絕非無原則地一味追求“和”,“正如其他思想、學說、學派對儒學的批判和排斥一樣,它對那些異端學說也具有強烈地排斥和批判精神,我們甚至可以說,勇于向異端說‘不’是儒家的思想傳統”[1](p202)。綜觀傳統儒學發展歷程,其“修正異端”的思維可以大致概括為三種表現。
第一種表現是對不吻合儒學精神的言行進行批評指責,屬于儒學初創時界定思想內涵的必要方式。《論語》中有不少類似言論反映了孔子的這種“修正異端”思維,如“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論語·公冶長》),“是可忍,孰不可忍”(《論語·八佾》)等。顯然,只要不合“仁”“禮”精神,無論思想、言論和行為,孔子都絕不姑息。
第二種表現是對“非儒學”之學派進行批判,兼及嚴格的思想劃分。先秦大儒孟子、荀子都是典型代表。孟子對“非儒學”的異端邪說進行批判,尤其體現為對楊、墨之道的拒斥:“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圣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孟子·滕文公下》)。荀子撰有《非十二子》,以自身所代表的孔門“正宗”思想,對其他流行思想包括思孟一系的儒學思想,都進行了嚴厲批評,一定程度引發了儒學內部“正宗”“異端”之爭。漢代大儒董仲舒主張“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專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唐代許多儒家學者力辟佛老,延至兩宋時期,“二程、朱熹均以佛教為主要的異端”[2](p227-228)。
第三種表現則是在儒學派別內部進行矯正式批評,兼及儒學派別之爭和批判思想“異化”的傾向。這種思路以陽明及其后學的做法為典型,他們批判“異端”側重以儒學核心思想為標準,來對某人或某流派的思想言行進行考察。王陽明提出帶有強烈平等意識的“良知說”,并以“良知”為標準來定位“圣”“愚”:“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3](p49)進一步,王陽明對“異端”進行劃分:“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4](p107)王陽明是將“良知良能”當成了判斷“異端”之標準,推動了這一標準的普遍適用性。陽明后學王龍溪繼續推進這種思維,言道:“夫異端之說,見于孔氏之書。先正謂吾儒自有異端,非無見之言也。二氏之過,或失則泥,或失則激,則誠有之。今日所憂,卻不在此,但病于俗耳。世之高者,溺于意識;其卑者,緇于欲染。能心習見,縱恣謬幽,反為二氏所嗤。有能宅心虛寂、不流于俗者,雖其蹈于老釋之偏,猶將以為賢,蓋其心求以自得也。學者不此之病,顧汲汲焉惟彼之憂,亦見其過計也矣。”[5](p122)他將“病于俗”當作了“異端”的突出問題,反映當時儒學思想、儒學人物言行出現的“異化”傾向。鑒于長期以來儒學作為古代王朝官方意識形態和科舉考試的必考內容,許多儒學從事者便把研習儒學當成了加官晉爵、欺世盜名的工具,背離了儒學宗旨,正是應該大力批駁的內部“異端”分子。同時,彼時在官方層面獲得主導地位乃是儒學內部的朱子學系統,陽明學以官方朱子學系統為“異端”,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派別之爭。反過來,在朱子學人物的眼中,“作為對朱子學的反動,陽明學本身恰恰可以說是儒學內部的異端”[6](p127)。從歷史事實來看,“陽明學確實被作為異端邪說而于嘉靖年間三次遭到官方的明令禁止”[7](p250-270)。
傳統儒學這些“修正異端”之表現雖然有所不同,“但殊途同歸,都是儒者為維護儒家核心價值觀而針對違背儒家核心價值的對象進行的批判”[2](p227-228)。傳統儒學這種“修正異端”思維對近現代包括當代儒學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20世紀誕生的現代新儒學中已然具有這種鮮明的“修正異端”意識,例如牟宗三先生的“道統”與“判教”意識就很突出。在他的理論中,宋明理學中“心學”一系的思想被確立為儒學思想的“大宗”正統,其他的儒學思想則被判為“歧出”。包括宋明理學中重要的“理學”一系也受到降格處理,連朱熹本人也被稱為是“別子為宗”。到了21世紀,當代大陸新儒學興起過程中仍然以“修正異端”意識來提出復興儒學目標。在當代大陸新儒學代表人物蔣慶等看來,牟宗三先生所代表的現代新儒學(或稱“港臺新儒學”)也是“歧出”,是需要修正的“異端”。
二、“修正異端”思維下蔣慶等對現代新儒學的批評
蔣慶等對牟宗三為代表的現代新儒學的批評可以概括為三個主要方面:一是現代新儒學極端推崇“心性儒學”而忽略了“政治儒學”;二是現代新儒學的哲學進路主要是西方式而非儒學的進路;三是現代新儒學的價值追求服從了西方文化而未保持儒學本色。
第一方面批評是從“問題意識”角度展開的。蔣慶認為,人類的學術都來自心中焦慮——一類是“實存性的焦慮”或稱“生命的焦慮”,一類是“制度性的焦慮”或稱“政治的焦慮”。“生命的焦慮”的對象是“生命的價值、存在的意義、人格的增進和道德的完善”[8](p8),而“政治的焦慮”的對象是“政治的價值、制度的意義、規范的設立和政制的改進”[8](p8)。兩種焦慮正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問題意識”,按其分析,“心性儒學”的研究出發點是“生命的焦慮”。蔣慶明確指出,現代新儒學所關注的對象“主要是生命與心性,用哲學上的術語來說,就是個人的存在、形上的本體和以生命心性為歸依的抽象的歷史文化。這從唐君毅先生的代表作《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牟宗三先生的代表作《心體與性體》《政道與治道》等新儒學的經典著作中都可以看到”[9](p20)。對這樣的思路,蔣慶并未根本反對,“新儒學關心生命心性,還儒學的本來之義,本無可厚非”[9](p20)。他所不滿的是現代新儒學將這種思路推到了極端的地步,“這種極端化的傾向使新儒學不能越出生命與心性一步,而是萎縮在生命與心性的領域內優游涵泳,潛沉玩索,最終未能開出新儒學所希望開出的新外王”[9](p20)。這種極端傾向導致了四種嚴重的后果,“極端個人化傾向使新儒學不關注社會關系,極端形上化傾向使新儒學不關注具體現實,極端內在化傾向使新儒學不關注禮法制度,極端超越化傾向使新儒學不關注當下歷史”[9](p24)。正是從批評現代新儒學的“極端化傾向”出發,蔣慶提出自身從“制度性的焦慮”發源的“政治儒學”主張。一方面,“政治儒學”在歷史上就是儒學的主體,他認為,“儒學從其誕生之日起就是‘政治儒學’,儒學最關心的就是廣義的政治問題,即使宋明儒學談‘心性’亦是談政治的一種方式。儒家所依據的‘六經’就是專談政治之經,其‘今文經說’都是‘政治儒學’”[9](p14);另一方面,中國的現實和未來也迫切需要“政治儒學”,他迫切地呼喊,“儒學不僅在過去,而且在現在和將來都注定要思考政治,要在政治中確立其義法,創設其制度,證成其秩序,實現其理想,最終要在歷史中建成體現天道性理的政治禮法制度,使孔子之王心王道落實于人間也”[9](p14)。
第二方面批評從哲學層面展開。蔣慶認為,現代新儒學的哲學進路主要是西方式而非儒學的進路。以牟宗三先生為例,他最具獨創性之理論是“良知坎陷”說。蔣慶則通過研究發現牟先生這一學說與正統的王陽明“致良知”學說存在根本差異。他分析指出,牟先生將“良知”理解為“一西方哲學意義上的理性概念”[9](p63),時常被等同于康德意義上的“道德理性”或者黑格爾意義上的“絕對精神”[9](p63);但是,陽明所說的“良知”主要是一“生命境界,而非理性概念”[9](p63)。牟先生重視的“坎陷”說,狹義上講就是黑格爾哲學中的“自我否定”“辯證發展”等含義[9](p69),廣義上講則是“轉折”“曲折”“暫退一步”等含義[9](p69),這些說法同樣與陽明的“良知”不相配合。蔣慶指出,“在陽明看來,‘良知’是道,是天理,是心之本體,是天地主宰……故必須通過‘致良知’的功夫除去私欲私意對‘良知’的障蔽,使良知……能在與事物交感接應中正確地判斷是非善惡”[9](p70)。這樣一來,牟先生“良知坎陷”的說法問題就比較大,“故依陽明,‘良知’只可‘呈現’而不可‘坎陷’,因為如果良知‘下落’‘暫退’而不能‘常覺恒照’,‘良知’就不能在應物中正確地判斷是非善惡”[9](p70)。從這種哲學層面批評出發,蔣慶也對牟先生進行了儒學式“判教”:“牟先生在中國儒學傳統中判程朱為歧出,尊陸王為正宗,并在陸王學理的基礎上來會通康德哲學,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故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牟宗三的良知學說仍然是一種‘王學’,盡管是一種‘歧出的王學’。”[9](p52)這種評價有一種“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感覺,耐人尋味。
第三方面批評從價值取向層面展開。在蔣慶主張的“政治儒學”理論中,儒學討論政治的價值取向,必須是以中國文化為底色的,“儒家所談的政治是植根于中國文化淵源的中國式的政治,而非源自西方文化的民主政治”[9](p14)。在這樣的理論對照下,現代新儒學孜孜以求的從“內圣”開出“民主”“科學”的“新外王”進路自然十分刺眼。蔣慶指出,“當代新儒家把儒家的外王事業理解為開出由西方文化所揭橥的科學和民主(所謂‘新外王’),如此則儒學不能依其固有之理路開出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政治禮法制度,即儒家式的外王大業”[9](p13)。按照這樣的思路發展,現代新儒學不僅違背了儒學根本宗旨,甚至有淪落的危險,“若依當代新儒家‘儒學第三期發展說’儒學果能開出科學和民主,則儒學必喪失其自性而不成其為儒學矣,何發展之有”[9](p13)!值得注意的是,蔣慶雖然批評現代新儒學思路中的“西化”危險,但是他也并不完全拒斥西方文化,“這里所說的開出新外王……是開出體現儒家政治理想與價值原則的政治禮法制度。這一制度與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有重合也有區別:所謂重合,是指儒家的價值原則與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不完全沖突,儒家按照自己的義理可以肯定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某些價值,二者是某一階段的同路人;所謂區別,是指按照儒家的三世學說與大同思想,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只是小康之世的產物,并非盡善盡美,儒家追求的是比民主制度更高的政治理想,二者的目標不同”[9](p13)。從其論述中可以發現,蔣慶在價值認同上采取了一種動態的“階段論”觀點。這種觀點沒有將儒學和西方文化完全劃分為截然相反的陣營,而是以儒學政治理想為最高價值和最終追求來劃分人類社會發展階段,將西方文化的內容(主要是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納入社會進程之中給予部分認可。因此,他對現代新儒學的批評就不是單純的立場“站隊”,更多的是對“走偏者”的一種提醒:“所以,新儒學開出的新外王應該既包括西力民主政治的可欲成分,又包括儒學政治理想的傳統成分,而不能一味向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看齊。”[9](p27)他非常在意的是按照現代新儒學這種“走偏”的路線,最終導致“西化”的結局,“當代新儒家有‘變相西化’之嫌,當代儒學則有淪為‘西學附庸’之虞”[9](p13)。在此基礎上,他反復強調現代新儒學具有“異端”色彩的“歧出”問題,認為他們“背離其固有理路求發展,發展只能是歧出或變質”[9](p13)。
蔣慶對現代新儒學“歧出”的批評獲得了部分大陸新儒學代表人物的支持。陳明指出,“港臺新儒學關注的是中西的問題,大陸新儒學關心的是古今問題。”[10]具體來說,“港臺新儒家處理的中西問題是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關系,是在面對西方文化強勢威壓時對自己文化傳統進行某種論述和論證,以重建其知識和價值上的合法性”[10]。現代新儒家時刻面臨西方文化的強大壓力,迫使他們的全部思考打上了深刻的西方烙印,“在他們那里西方是思考的語境,不僅問題是它們給出的,參照系也由它們提供。像馮友蘭以新實在論講理學、賀麟用新黑格爾主義講心學,最典型的則是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和唐君毅四君子宣言講的內圣開出民主科學的新外王的問題”[10]。大陸新儒學后起代表干春松對海外新儒學(港臺新儒學之學生,屬于廣義的現代新儒學的范疇)也有類似評價指出:“海外發展的新儒家因為地域和問題視野的關系,導致他們對儒家的價值的肯定度越發地弱化。”[10]他以劉述先先生說過的“他們這些在美國大學教書的那些人不具有像牟宗三、唐君毅等身上的擔負,即那種文化的擔當”[11]為例評價道:“如果一個儒者沒有文化的擔當,那么他與其他的研究者的區別在哪里?……在我看來,正是因為卸下了‘負擔’,使得新儒家的問題關切越來越‘稀薄化’,這樣的學者是否可以被冠之以‘新儒家’是可以討論的。”[11]在這里,干春松直接質疑了海外新儒學代表人物的“新儒家”身份,批評力度較大。
三、“修正異端”思維下大陸新儒學內部的相互批評
大陸新儒學作為一種思潮,其內部觀點差異較大,相互之間存在批評,同樣也呈現出“修正異端”的思維特點。參照傳統儒學“修正異端”思維的表現,大陸新儒學內部的相互批評主要表現有二:一是思想觀念層面的批評,二是實踐層面對可能的“異化”傾向的警惕與批評。
從思想觀念層面批評來看,主要表現為大陸新儒學論者之間直接對話、交鋒。黃玉順就思想的貫通問題對蔣慶“明體達用”①參見:黃玉順《儒教與形而上學問題》,載《湖南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第17頁。此文帶有對話性質,作者黃玉順教授發言時,蔣慶亦在當場傾聽,認可黃玉順“明體達用”的總結,并告知其所謂“體”指的是“圣賢”。、陳明“即用見體”的思想觀點進行質疑。在黃玉順的分析中,這兩種思想都存在著對“體”的形而上學預設不夠牢固的問題,“還沒有觸及的觀念層級,是說的一種‘前形而上學’的、為形而上學‘奠基’的觀念層級”[12](p18)。這就使得“明體達用”“即用見體”都有無法徹底貫通的缺陷。具體落實到現實中就會出現在“用”上得到推行,但是在“體”的層面“老百姓不買賬”,無法普及的尷尬。他很通俗地質問陳明:“你怎么能保證你所‘見’的就是儒家的‘體’?你如何能保證你建立的就是儒教、而不是一般的禮儀公司?這是‘即用見體’面臨的一個嚴峻的問題”[12](p17)。同樣質問蔣慶:“你盡管把它(蔣慶認定的以‘圣賢’為‘體’)搞得非常的宏偉,非常的神圣,非常的漂亮,可是老百姓不買你的賬,你也是沒有辦法的比如我剛才說的,老百姓要辦婚禮、喪禮,他就不選擇儒教,你有什么辦法?”[12](p17)在這種批評中,黃玉順給出他的建議,認為儒學思想之“體”應該以“生活”為指歸:“這個先行的本體本身、主體本身,是如何被給出的?這就必須‘復歸生活’,回到中國人當下所置身其中的生活樣式之中這種生活樣式。”[12](p18)這種“生活樣式”內涵包納十分豐富,歷史文化傳統的積淀、現代性、全球性等因素全部包括在內[12](p18)。
張祥龍和蔣慶就政治儒學的“普遍主義”(uni?versalism)性質有過數個回合的直接對話。張祥龍的觀點中,“普遍主義”所指的是一種認為凡是有價值的東西都可以在忽略時空條件差異的情況下“無差別”地推廣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13](p190)。這種“普遍主義”視野中,自然科學的命題就比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命題更符合要求,“形式化的、有唯一解的數學命題”[13](p191)是最符合要求的。而以此來審視蔣慶的“政治儒學”,張祥龍就發現了一個悖論:“就蔣慶對于港臺新儒家的批判而言,政治儒學肯定不是普遍主義;但就他本人提出的主張看來,似乎又有普遍主義之嫌。”[13](p192)蔣慶認為儒家文化中本有屬于自身特色的“大一統的政治禮法制度,此制度維系中國兩千多年,創造了人類政治史上的奇跡”[9](p93),明確反對牟宗三等現代新儒家將西方政治制度當作唯一標準的“普遍主義”思路;蔣慶所論述“王道政治”的“三重合法性”有“民意的合法性”“文化的合法性”和“超越的合法性”三個維度,其中前兩個維度都與中國的歷史文化有密切聯系,也不是“普遍主義”思路。但是,第三個維度“超越的合法性”卻帶有了普遍主義的嫌疑:“超越的神圣本源上則永遠不會變!這就是天不變道亦不變之‘道’,也是人類政治的終極關懷與最后希望”[9](p340)。張祥龍指出,這里所講的“不變”就很可能蘊含了“超出所有經驗變易,達到像邏輯真理一樣的無時空可言的‘不可能錯’”[13](p198),也就正是一種普遍主義思維。張祥龍甚至進一步質問蔣慶,“這樣的‘不變之道’與牟宗三講的‘常道’有什么哲理上的差別呢”[13](p198)?另外,蔣慶在論述“儒家文化是先進文化”的文章中也有“普遍主義”的說法,“看這個規則能否被更多的人接受,看這個規則被更多的人接受后,能否給所有的群體帶來最多的福利。如果全人類都能接受,能給全人類帶來普遍的福利,那么,就是一個能普遍化的規則,因而就是一個好的規則”[13](p199)。張祥龍分析認為,如果蔣慶不能對這些帶有普遍主義的論述合理化解的話,其政治儒學的核心看法,特別是對牟宗三等的普遍主義批評就很難成立了。對于張祥龍的質疑,蔣慶給予了積極回應,主要有兩個觀點。一個觀點是用“時中智慧”來解釋“政治儒學”,認為其既不是普遍主義的,也不是特殊主義的;既是特殊主義的,又是普遍主義的,“政治儒學”不能用非此即彼的形式邏輯來解釋[13](p192)。另一個觀點是將“普遍主義”分成了“優質普遍主義”和“劣質普遍主義”。西方的現代性是一種傲慢狂躁的浮士德式的“劣質普遍主義”,中國的“政治儒學”是一種優質的普遍主義[13](p193)。張祥龍對蔣慶的觀點繼續回應,他不同意“優質普遍主義”的說法。因為按照嚴格的“普遍主義”(universalism)來說,并無“優質”而言[13](p215)。當然,張祥龍認可“儒學既非普遍主義,也非特殊主義”的說法,并進一步分析這種“非普遍主義”的本質就在于,“儒家之道德首先不是‘準則’與‘規范’,而是人生境域本身的時機關系所構成”[13](p216)。對此說法,蔣慶最終未能給予滿意回應[13](p223)。
從實踐層面的警惕與批評來看,主要表現在楊國榮、李存山等大陸新儒學代表人物批評蔣慶、陳明等所主張的“政治儒學”“公民宗教儒學”主張。
楊國榮主要從歷史發展的視角來審視。以歷史發展而言,“政治儒學、儒家憲政等試圖基于儒學來治理今天的中國,這卻是一種非歷史的進路,顯然難以行通”[14](p53)。他認為,“政治儒學”一整套的制度設計都只是在中國歷史上發生過社會治理方面行之有效的作用,“但在當今社會中對其加以復制,則未必可行”[14](p53)。要在當今社會發揮效用,必須接受當今社會現實中發生的變化,“科技的發展、社會的演進、政治體制的變革,等等,這些方面的變化內含其必然之勢。同時,現代社會的變遷,包括經濟上從自然經濟走向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這不是孤立的變化現象,事實上它也會影響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政治、文化、價值觀,倫理行為、日常生活,等等。實際上,今天我們可以處處看到的這種影響”[14](p53)。主張“政治儒學”的研究者們之所以在實踐層面提出那些復古的主張,原因就在于無視這些變化的現實,“以單向的情感認同,將儒學過分地加以信仰化、形上化”[14](p54)。就值得警惕的傾向來看,楊國榮認為,儒者們“沉溺于高頭講章,或情感認同壓倒理性考察,看似陳義甚高,實則容易將儒學推向玄虛之境”[14](p57),這些做法很可能導致“無法真正把儒學內含的深沉意義揭示出來,相反,倒是會使儒學遠離現實生活并變得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14](p54)。這顯然就違背了從儒學創始人孔子就十分重視的“入世”主旨。毫無疑問,“這不是有益于儒學,反而可能有害于儒學”[14](p54)。
黃玉順也對“政治儒學”的具體主張提出警告。他把蔣慶的“政治儒學”的實踐宗旨總結為“創教”,是想要“把傳統的儒學改造成標準的現代宗教,甚至想把它建構成一個‘國教’——國家的宗教”[15](p50)。對這種“政治儒學”的言行所造成的實踐后果,黃玉順的批評很嚴厲。他一方面認定,“至少就政治儒學而論,比起20世紀的現代新儒家來,當今的大陸新儒家整體上是退步了”[15](p51)。另一方面更直指其中“危險的政治傾向”[15](p51),“特別是個別人不僅倡導威權主義,甚至主張專制主義、極權主義,反對自由、平等、民主等現代文明價值,不禁讓人想起魯迅的說法——‘幫忙與幫閑’,實則是幫兇”[15](p51)。他還分析了這種危險傾向的實質有個人原因,也有集體原因。從個體上講,那些大陸新儒家個人或者是糊涂——“真睡著了”,或者是別有用心——“裝睡著了”。從集體上講,則是受到“狹隘民族主義”思潮影響。他們以“‘中西對抗’來掩蓋‘古今之變’的人類文明走向,借‘反西方’之名,行‘反現代’之實,用‘文化’來拒絕‘文明’。這些都是當前‘儒學復興中最值得警惕的傾向”[15](p51)。黃教授的上述分析有其見地,但他的用詞多少帶有“誅心”的色彩,有主觀臆斷成分。
李存山也對“政治儒學”提出的“庶民院”“通儒院”和“國體院”三院制的制度設計提出了異議。他的分析基于中國傳統文化而來,根據傳統文化“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的思想來講,“天和民是一致的”[16]。但是,蔣慶主張的“三院制”設計中卻批評民主制度是“民意合法性一重獨大”,因此主張在“庶民院”之上再建立兩個機構:體現“天道之超越神圣合法性”的、由儒教公推之大儒終身任職的“通儒院”和體現“歷史文化合法性”的“國體院”[16]。李存山指出,這種“三重合法性”的結構在中國文化中沒有“合法性”的依據。因為,“天雖然是最高信仰的對象”,但是由于有“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的原則,所以,最終而言,“天是以人民的意志為意志的”[16]。那么,蔣慶所設計的要建立一個凌駕于民意之上的“天道之超越神圣合法性”,這就沒有傳統儒學思想的根據,一定意義上也帶有“異化”傾向。
鞠曦對陳明等人的“回到康有為”理路展開激烈批評。在2016年的“首屆兩岸新儒家會講”活動中,陳明提出“超越牟宗三,回到康有為”觀點,受到部分大陸新儒學代表人物批評,鞠曦的言辭尤為激烈。他認為,歷史中的康有為是一個政治投機者,“無恥篡改儒學、偽造孔子托古改制”[17](p41),根本不是真正尊崇儒學之人。現在陳明等人抬出康有為來為自身“儒學宗教化”尋找根據,正是一種政治野心的顯現,“不過是托古改制的儒賊之渾水摸魚,以便在當代復興儒學的大潮中,實現‘康黨’的政治野心”[17](p41)。同時,他們將現代新儒學巨擘牟宗三當作超越對象,也反映了他們“舍棄儒學的哲學理性而對儒學進行宗教化”的錯誤思路,背后是其“學養不足從而訴諸非理性的宗教化”[17](p40),屬于“托儒學而求私利的個人目的”[17](p40)。從宏觀危害上講,他們將人類文明必須要以哲學、科學理性發展的道路倒退回依靠非理性的宗教來發展,美其名曰“文化民族主義”,“不僅是理性之倒退,更是文明之反動”[17](p40)。從微觀危害來看,陳明在對儒學六經都不通的前提下,主張一種機會主義色彩的“即用見體”,屬于典型的現代偽儒學,“蒙蔽了一些學養不深的青年學者,造成了很壞的影響”[18](p25)。顯然,鞠曦在這里言辭激烈的批評是將陳明及其所謂“康黨”當作“異化”嚴重的壞典型了。
綜之,當代大陸新儒學作為一種思潮,確實鮮明秉承了傳統儒學所帶有的“修正異端”思維特點并有充分的表現。從思想本身發展脈絡來看,大陸新儒學早期代表人物在一種“修正異端”思維下對現代新儒學(港臺新儒學)展開的批評,推動了大陸新儒學思潮的展開。另一方面,“修正異端”思維在大陸新儒學思潮內部引發的相互批評,更是一再引起思想界的熱切關注,同樣從廣度和深度層面拓展了這一思潮的繼續發展。一定意義上,這也正是某種儒學應有的“和而不同”發展狀態。當然必須指出的是,過于激烈的“修正異端”式批評確實對于當代大陸新儒學思潮的整體向心力造成削弱,某些極端批評言論蘊含著“撕裂”這一群體的可能。如何在這種內部交鋒中保持住思想的活力,又能加強同一群體之間的共識與凝聚力,為新時代中國思想文化建設做出更大貢獻,是當代大陸新儒學思潮所要注意的焦點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