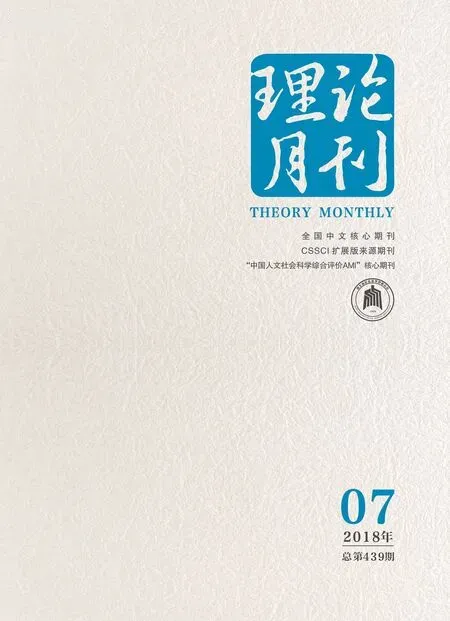異地養老者的互動困境與虛擬互動實踐
□薛 爽,尹海潔(.哈爾濱工業大學 人文社科與法學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5000;2.哈爾濱工業大學(威海)思想政治理論教學部,山東 威海 264209)
異地養老,是我國近年來出現的一種新的社會現象、社會趨勢。這一現象背后,是具有相當數量的老年人在退休之后選擇離開原住地到其他地方生活,這些老人被稱為異地養老群體。有資料顯示,我國60歲及以上的異地養老群體規模已經接近1800萬[1](p60)。國內外學者研究發現,老年人選擇異地養老的主因包括:宏觀社會結構性因素的變動[2](p45-48)、家庭共同體內分工與支持的需要[3](p52)[4](p663)和老年人自身對宜居地氣候環境的向往等[5](ps232)。顯然,對生命歷程各不相同的老年人來說,異地養老究竟受哪種因素主導不會完全一致。但是,絕大多數異地養老者都會面臨一個共性問題,即,因由自然空間的改變而造成社會空間的隔斷以及社會關系網絡的重建。親友故交的老地方與舉目無親的新環境,成為拉扯老年人身體、情感、心理的兩個端點。能否快速、順利的熨平新舊兩地在社會互動方面的劇烈波動,盡快融入新環境,成為確保老年人異地生活質量的重要因素。
一、“身體在場”的現實互動困境
傳統的互動論者均重視互動的情境,對“互動”的基本預設就是行動各方在時空維度上的一致性。涂爾干在對宗教儀式的研究中強調群體的人身匯集于同一地點[6](p60);戈夫曼在《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現》的引言中明確設定,互動指個體面對面的“在場”互動[7](p12);柯林斯進一步強化這種觀點,認為面對面的“在場”互動,是行動的基本場景和行動者的基點[6](p19)。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際互動都能夠實現“在場”,當個體所處的時空條件發生改變時,“身體在場”便不具有現實可操作性。自古至今,生活實踐中的多種“非在場”的互動形式,例如依托信鴿、各種形式的暗號、信件、電報、廣告、電子郵件等實現的互動,同樣能夠傳遞信息,但時空拉長、內容受限。這說明,“在場”并非是互動完成的必要條件;而“非在場”又必然面臨一定的困難以及信息與體驗的折損。
當今社會流動性增強,流動人口與原有社會交往對象之間存在著“身體非在場”的現實互動困境。與其他年齡層的流動人口相比,老年流動人口面臨的互動困難更大。參照表1,綜合個體生命歷程和社會互動的時空變遷兩個角度分析發現,首先,退休事件使老年人經歷了兩種變化:其一,時間維度上,他們普遍經歷了個體生命周期的階段性過渡,既由以生產為重心的階段向以生活為重心的階段轉變;其二,空間維度上,人際互動的空間場域快速萎縮,老年人基本脫離了生產場所,社會互動空間回歸至家庭和社區。退休事件造成時空的雙重轉變,帶來的是社會交往網絡的縮小。劉燕發現,年齡與社會網絡規模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年紀越大,親密接觸的人的規模會逐漸減小[8](p73)。其次,移居事件會讓深處其中的老年人經歷社交網絡和社區環境的“換血式”改變,老年人原有的、熟悉的互動空間進一步萎縮至家庭,不得不在“陌生人社會”中面臨社交生活的各種不確定性[9](p70)。而那些身邊沒有子女和親友的“候鳥”老人,移居后,能夠滿足“身體在場”這一前提且熟悉的對象只剩配偶。國外研究發現,一旦喪偶,老年人會選擇再次移居,移向機構照料或是向成年子女靠近,而無論是哪一種選擇,老年人的新生活環境注定是陌生的[10](p40)。由于我國老年人口流動的趨勢與發達國家日漸趨同,那么,未來我國可能會有越來越多的喪偶老年人選擇在異地的陌生環境中生活,這為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務提出了挑戰。
如前所述,在“退休”“移居”“喪偶”等一系列個體生命歷程“軌跡”的作用下,老年人與原有社會互動空間逐漸隔離,熟悉的互動對象越來越少,漸漸“不在場”。而身體所在的“新環境”,充斥的幾乎都是陌生人。由此,我們認為,異地養老群體實際面臨著雙重的現實互動困境,即,熟悉的人不在場,在場的人不熟悉。

表1:個體社會交往的時空變遷對照
那么,如何破解這雙重的互動困境?我們觀察到,為緩解移居初期的情感焦慮,在實踐上,現時代的異地養老群體,首先會積極選擇借助技術優勢實踐“身體非在場”的虛擬互動。這一行為選擇策略符合柯林斯從理性行為人角度得出的觀點,在互動儀式市場上,人們的最終目標是在社會互動中最大化的追求情感能量,而非個人的經濟收益[11](p153)。或許,虛擬互動具備使身居異地的互動主體實現情感與體驗最大化的可能。變化發展的實踐,督促我們重新檢視互動論者的理論設定。當代學者已經提出,在信息互聯的時代,物理空間上的身體共同在場并不是互動儀式發生的必要條件[12](P38)。互聯網為社會互動提供了新的平臺。20世紀90年代,國外學者提出,互聯網絡的興起與普及,為老年人實現社會交往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避免其與社會隔離[13](358-378)。國內的研究結果也呈現出相似的結論,根據社科院與騰訊公司聯合做的一項調查結果分析,互聯網和社交軟件有助于增加家庭內部代際間的互動頻率[14]。
在當今中國巨大的社會實踐場域下,老年人與虛擬互動方式的結合,或許具有某種現實性和必然性;而身居異地的老年人與虛擬互動方式的結合,則具有某種迫切性。這是異地養老者共同的情感需要和現實需要,然而這一過程卻并不容易。涂爾干認為,當我們試圖理解一種社會現象時,既要探究現象產生的原因,又要對它所具有的功能進行解釋[15](p105)。
二、資料搜集與研究個案介紹
參考學界對異地養老的界定[16](p20)[17](p375),本研究將異地養老界定為老年人離開常住地,到其它地方(跨越縣市)相對穩定的居住和生活的一種養老模式;將異地養老者界定為,年齡在55歲以上,離開常住地、到其他地方相對穩定的居住和生活三個月以上的老年人。
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山東省威海市逐漸吸引了大量外來老年人口。綜合來看,老年人大量涌入的重要拉力因素包括:第一,優越的自然環境。四季分明,是公認的適合老年人養老的宜居城市;第二,經濟發展與家庭網絡的作用。威海市的產業布局和調整吸引了相當數量的省內、鄰省和東北地區的勞動力來此就業,由于生活成本遠低于大城市,外來勞動力較容易在此扎根,在家庭主義和家庭網絡的作用下,勞動力的遷移又帶動了老年父母的隨遷。目前,威海市的異地養老群體已經初具規模,因此,本研究以這些老年人為研究對象,采取立意抽樣結合熟人網絡的方法發展訪談對象,盡量保證訪談對象的差異性和典型性,最終實地訪談21戶共33位老年人。圍繞研究主題,采用半結構式訪談和參與觀察搜集資料。
訪談對象的基本情況如下:年齡上,中低齡老人居多,55-59歲組有4人,60-69歲組有18人,70-79歲組有7人,80-89歲組有4人;有4戶喪偶;學歷層次中等偏上,大專及以上有19人,高中或中專有9人;退休前的職業多為教師、技術人員和行政管理人員;單位類別以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為主。居住方面,18戶(老年夫妻)在威海有單獨居住的自購房,1戶與子女同住,2戶租房;子女情況,有4戶沒有子女在當地生活,有10戶是老人隨子女遷居而來,有4戶是老人先來然后子女隨遷,有3戶是老人和子女一同搬來;社會關系方面,有5戶在搬來前,當地有除子女以外的其他親友;來源地方面,10戶來自黑龍江,3戶來自吉林,2戶來自山東省內,其余來自遼寧、北京、河北、湖北、甘肅和新疆各1戶。
訪談對象的基本特征,比較符合已有研究中對老年網民特征的描述,即,使用互聯網和手機比較積極的老年人具有一定的群體特征,他們在年齡、視力、教育水平和經濟狀況方面具有明顯優勢[18](p68-70),退休前主要為腦力勞動者[19]。
三、異地養老者的虛擬互動實踐
基于對訪談資料的整理,我們發現,多數訪談對象在剛搬來時會經歷一個內在和外在的適應期,會感到:不喜歡(個案09)、孤獨(個案03)、寂寞(個案14)、苦惱(個案16)、老想回家(個案19)等負向心理反應,也有訪談對象表示初來幾年每年都得回家(個案15)。訪談發現,異地養老者的社會交往對象往往滯留在原住地。因此,他們在新居住地的社交生活具有如下共性特征:一方面,移居初期社交范圍大大萎縮,基本上經歷過不適應階段;另一方面,為應對不適,他們普遍選擇使用虛擬互動媒介與原有生活世界保持聯系。
(一)虛擬互動——打破“在場互動”的行動策略
虛擬網絡的普及,將更多潛在的互動主體從線下拉到線上,再由線上反饋至線下,實現了線上線下多種溝通方式的融合。威爾曼認為,相比于現實中的人際互動,虛擬網絡互動具有打破空間限制、富有創造性和直接的特點,它能維持強、中、弱不同強度等級的社會關系,因而,它可以同時為專業化關系和寬泛的關系提供信息和社會支持[20](p213)。
依據CNNIC(2017)發布的報告,截至2017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是7.51億,60歲以上老年網民占比4.8%,經計算共有3604.8萬,50歲以上的網民達到7960萬人[21](p13-19)。老年網民的整體規模已經非常龐大,老年網民參與網絡互動的形式也趨向多元化。訪談發現,異地養老群體使用的互動媒介主要包括:電話、微信、QQ、電子郵件等;信息交換方式主要有:文字、圖片、語音、小視頻、視頻等;互動的對象主要是親朋好友等原有的社會關系。綜合來看,QQ、微信視頻和電話是老年人在遠距離互動中更為中意的方式。這也印證了學者的研究發現,即,老年人接受和使用現代信息溝通工具的重要考慮因素是滿足需求和支持可用性[22](p1081-1099)。
虛擬互動在老年群體的社交活動中具有優越性和非同尋常的意義。首先,虛擬互動具有便利、便宜的優點,使不同經濟地位的老年人都有條件使用[23](p423-445);其次,聽覺和語言能力下降會影響老年人的社交活動[23](p423-445),而虛擬互動突破了文化和書寫的障礙,簡化操作過程,降低操作難度,使得不同文化層次的老年人都易于掌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虛擬互動打破時空界限,讓老年人與親朋摯友間實現遠距離的親密互動,滿足情感需要。因此,虛擬互動成為老年人移居后首選的社會交往策略。
多數訪談對象表示,現在通訊便利,極大程度上緩解了他們移居后的焦慮,也正是因為已經感知到現今社會通訊的便利,他們才能義無反顧的離開家鄉來到陌生的地方居住,虛擬互動媒介增加了他們移居的信心。與移居相伴隨的是,那些原來很少參與網絡互動的老年人,在移居后,參與網絡互動的動力和時間都大大增加。虛擬互動已經成為他們移居后日常生活中的習慣,是社交生活的重要形式。從訪談來看,移居行為對老年人參與虛擬互動起到了促進作用。
(二)虛擬互動的形式和內容
老年人在移居后與原有的社會關系展開了多種形式的虛擬互動,不同的互動模式與內容體現出異地養老群體多元化的社會交往需求。
1.與重要他人的日常聯絡。柯林斯在《互動儀式鏈》的中文版序言中提到,互動儀式具有時間性,不會永遠持續,但它的力量可以通過高度的關注和情感的不斷重復而持續體現[6](pxvii)。現實中,多數異地居住的老年人通過持續的關注與情感投入,實現與“重要他人”的情感聯絡。這些重要他人包括子女、兄弟姐妹、朋友和同事等;互動內容以詢問身體狀況等生活化的日常問候為主,內容比較寬泛、籠統;個體與重要他人之間以點對點的互動形式為主;根據個體的情感需要,互動頻率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相較而言,家庭內部代際之間的互動頻率更加頻繁。與重要他人的日常聯絡,是異地養老者最主要的互動選擇。
就是一種牽掛。我小女兒在東北,這么遠,就惦記、想。要是幾天沒來個微信,不給發個小視頻啊,就開始擔心了!這不就是一種牽掛嗎?(個案01,W阿姨,60歲)
我很重視家庭。我弟弟,要是時間長了沒聯系,我就著急,得打電話問。妹妹,我也經常跟她微信,要不我就覺得想念她們。我跟侄女聯系的也挺好。(老伴插話:她用微信和各方面聯系!)(個案19,W老師,女,80歲)
2.小群體內部的情感凝聚與自我呈現。群體為生活于其中的人們提供尊敬、愛和保護[24](p38)。異地養老者通過虛擬互動的方式與不同的社交群體保持緊密的聯系。研究發現,這一類型的互動多發生在熟人所形成的非正式群體之中,包括親屬群體、鄰里同學同事朋友群體等;也包括在原住地加入的各種協會等正式組織。總體來看,單個小群體內部的成員數量有限,互動的目的主要是凝聚成員的情感、增加歸屬意識,并通過群體歸屬與認同來強化個人的自我認知。
我在威海有好幾家親戚,在韓國也有很多親戚。30號,在韓國,我二嫂的外孫子結婚,我們家人在網上都溝通,在韓國的都去參加婚禮,可心齊了。這太遠了,近了我也去參加婚禮。家庭挺和睦的(個案13,L阿姨,65歲,朝鮮族)。
戈夫曼發現,謹慎的表演要根據信息狀況來進行,以適應現實情況[7](p189-190)。如果互動對象發生改變,則前臺的控制策略也會做出適時調整。比如,與認識越久的人在一起,個體越會放松嚴格的前臺控制;反之,與新認識的人在一起時,個體就會適時的加強對前臺的控制。因此,老年群體一旦進入新環境、接觸新的互動伙伴,便會有意識的加強對個人形象舉止的管理;更進一步,如果新環境下的互動伙伴對個人形象的管理標準更高,移居老年人會不同程度感受到壓力,外在壓力會促使個人提高內在標準,追隨和效仿他人,這種改變會助力新加入者盡快融入新的環境。現實中的印象管理也有利于樹立更好的形象、展現更好的自我。從訪談來看,異地養老者具有明顯的印象管理的需要,女性老年人的這種心理傾向會更加突出。據多位女性老年受訪者自述,首先,穿戴方面,她們會花費更多的時間、精力和金錢,投入到衣著的顏色、款式、搭配上,也適當化妝,因為“大家都這樣”,良好的形象有利于融入新集體;其次,言談舉止方面,比以往更加文明、有禮,重視和注意交往的尺度以及別人的評價,因為“不能被別人笑話”。這些自我約束與自我提高,有利于在移居地加速社會融入的步伐,同時,個人形象和生活狀態的改善與提升,也成為移居生活比較理想和成功的有效依據。網絡時代,全新的生活狀態可以借助網絡快速、準確的傳播到原住地的社交圈中,在更大范圍內實現印象管理。
在老家時,從來沒化過妝,也不去買衣服,成天就上班下班。到這后,這些人(朝鮮族老年協會會員)不少都去過韓國,回來后穿戴什么都不一樣了。那就得跟隨吧,穿戴比以前華麗點,也知道化妝了。我姑娘在網上給她們(老家的外甥女)發照片,說我媽年輕了,知道化妝了!(個案14,L阿姨,68歲,朝鮮族)
基于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遠距離互動的內容不僅局限于個體情感的需求與滿足,還囊括了互動雙方應盡的責任和義務,并通過對個人“義務”的履行,來獲得尊重和自我實現。訪談中幾位子女不在身邊的老年人,仍然會借助互動的機會,給予晚輩提醒、囑咐,甚至勸誡、警告,認為這樣的操心是正當的和必要的。這顯示出,老年人對家長或長輩的責任和權威的認同,并通過“技術賦權”持續性的實現[25](p97)。訪談中,多數老年人承認這種認同感在逐漸下降,但都明確表示在關鍵問題上還會堅持。這表明,移居隔開的是家庭內部代際間的空間距離,但無法割斷緊密的代際情感和責任。
我們倆都商量好了,管到兒女,第三代不管,人家都有父母,你參與了人家還不一定聽進去,聽了人不一定那么做。頭些日子老頭兒跟兒子視頻時說兒媳婦的鞋太多了。過后我說再別說了。他說最后一次了!他知道說得多了,有自知之明(個案15,Z阿姨,75歲)。
3.對特殊事件的分享與共謀。人們與熟悉的、信任的、志趣相投的對象互動,彼此分享重要的、私密的信息。這暗含兩層意思:一方面,由于信息的私密性限制了互動范圍,因此對于某些特殊事件、特殊領域信息的分享與討論,將參與互動的各方與未參與互動的其他人區分開來;另一方面,信息的傳遞方向則將互動中信息傳播者和接收者的地位、資源加以區分。前者框定了固定的互動對象,后者激發了互動雙方的興趣。在信息社會,借助虛擬網絡,異地養老者完全可以和不在場的重要他人實現志趣層面的互動,獲得“自我實現”和“暢快體驗”[26](p108)。而對于生活中棘手的特殊事件,異地養老者也可以通過網絡與親友共同討論、分析,及時地獲得情感支持和智力支持。
下午絕對不出去,我得節約時間,電腦看不完!我北京有同學,一般看不著的都給我傳,像這個周末,啥也沒干盡看這些消息了。你像韓國的崔順實,敘利亞兩派,怎么回事?我就找資料看,關心國際大事……家長里短的事我管不了也沒興趣管(個案19,L老師,男,80歲)。
我今天拖完地,跟朋友聊了一個多小時微信,說女兒的事(離異),現在也想趁年輕再找,關鍵在這認識的人太少了。她(朋友)說要不還是回來,老家朋友多啊!我們百思不得其解,G(女兒前夫)為什么要這樣,沒有任何原因,說翻臉就翻臉,而且翻臉時特無情!我們統一認為他外邊有人了。我朋友還說,Z(女兒)當初就不該同意離婚,就要G把事情說清楚,他現在說的根本不能算離婚的理由!(個案18,W阿姨,60歲)
通過分析,我們發現,虛擬互動具有工具性、情感性和信息性等多重面向,并且,其所傳遞的信息、表達的意向和承載的功能都是多維的,它已經成為異地養老者的生活方式、重要的溝通途徑和寄托內心的精神依靠。借助網絡技術,異地養老群體實現了提供支持和獲得支持的雙向可能。
四、對虛擬互動實踐的多維功能分析
(一)打破在場限制,聯通過去與現在
在“身體不在場”的困境下,異地養老群體靈活、現實地采用多種形式和內容的虛擬互動。在全新的時代背景下,虛擬互動有助于異地養老群體長久地維護原有的社會交往對象,并通過網絡互動的優勢拓展和鞏固新的互動空間。
1.維護功能。虛擬互動方式成為異地養老群體與親友保持聯絡、互通有無的最主要、最便利的方式,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聯通過去。虛擬互動滿足了老年人回歸所屬群體的心理需要,借由電子媒介保證了原有生活世界的連續性。正如帕特南的研究發現,“電話促進了老朋友之間的閑談”,并且,“通過電腦溝通加速了人們在各個局部中心、私人社區之間的行動,在各種組織聯系之間迅速而頻繁地切換”[27](p195-196)。社科院與騰訊公司的調查顯示,所有依托社交軟件進行社交的受訪老年人,其社交對象中必然會包括家人和親戚,六成左右受訪老年人的社交對象會包括同事、鄰居和同學。可見,老年人網絡互動的對象主要在熟人社交圈中[14]。移居拉開的只是空間距離,借助虛擬網絡這個全新便利的載體,異地養老者可以把原本被空間割裂的熟人社交挪移到互聯網上,來滿足自己的社交需求。正如訪談對象所說“無論身在何處,該聯系的還得聯系,不能斷的”!
虛擬互動的正功能在老年人移居初期發揮的最明顯,之后會一直持續。我們前文所提到的所有內容都體現了受訪者利用虛擬互動方式與原有社會關系保持聯系。異地養老者用實際行動和效果打破了“身體在場”的理論限制。然而,虛擬互動的功能不僅指向過去,亦指向未來。
2.拓展與鞏固功能。國外學者已經發現,具有關系導向的虛擬互動平臺能夠幫助老年人獲得更多的社交機會,獲得更多的情感支持以及信息支持[28](p168)。電話、互聯網等媒介不僅僅連接過去,它在多位受訪者的新的生活世界中也發揮著作用。老年人在遷入地社區逐漸發展出固定的、有深入交往的伙伴后,其對遷入地的接受漸漸由自然環境層面深入到社會層面,這也意味著個體開始真正適應并融入新的社區。此時,老年人依舊會發揮虛擬互動聯通過去的正功能,也會利用其優勢,在新的社會空間中發展和鞏固新的交往對象,實現虛擬與現實的互相促進。訪談對象提到,在當地參加了老年合唱團并建立了微信群,平時成員之間會頻繁的交流,比如過年會派發紅包搶紅包、集體旅行回來分享照片等;成員生病住院,會去探望,彼此間也會通過電話、短信、微信等方式慰問或陪伴。在新環境下,兩個人是否建立了虛擬互動關系,甚至成為老年人自認為社會關系拓展成功的依據。例如個案13(L阿姨,65歲)提到:
當地人,有個叫W某的,俺倆微信了,夏天時候。還有一個W姐,政府機關退的,原來跟我這個樓那個樓的(距離),俺倆挺好的。
研究發現,虛擬網絡平臺為利益相關者提供了方便的互動空間。在共同利益和問題面前,虛擬網絡平臺能夠凝聚更多人的力量,發動集體智慧共同尋找解決方案,主動維權。例如,個案08提到所住小區(外來老年人較多)成立了業主委員會,并建立QQ群,利用這一互動平臺,業主們集體商討物業、管理等方面的事宜;個案17提到小區業主自發建立了微信群,叫“好鄰居”,主要目的是集體維權,商討怎么辦理房產證的事,因為已經入住十多年了還沒有任何說法,而當時的房地產開發公司已經倒閉。對異地養老群體來說,在遷入地,虛擬互動空間的多維功能還有待開發和利用。功能的拓展需要異地養老群體和社區工作者的想象力和長期實踐。可以肯定的是,在初步度過適應期后,虛擬互動在拓展和鞏固社會關系方面的積極功能會越來越大。
(二)虛擬與現實之間的張力
在移居的各個階段虛擬互動都能夠發揮重要的作用,但暴露出的問題也不能回避。研究發現,有個別異地養老者,存在虛擬互動擠壓現實互動的問題。
在電話時代,人們擔心,電話雖然緩解了孤獨感,但也減少了面對面的社交[27](p192)。進入互聯網時代,人們對虛擬互動所具有的兩面性的擔憂更加嚴重。從生活時間分配來看,異地養老群體如果一味執著于與原有親朋摯友的線上聯系,則必然會擠占線下時間;從生活活動的地點分析,老年人使用虛擬網絡更多的是在室內,過多的虛擬互動勢必會壓縮現實中室外活動的比例。這樣的結果,隱藏著諸多不利。首先,個人身體方面,長時間保持相同姿勢使用電子產品對老年人的視力、脊椎、血液循環等都不利;其次,減少發展新社會關系的機會,對融入新生活空間不利。在受訪者中,雖然這種現象僅是個別存在,但仍值得注意。從個案19介紹的生活時間分配來看,每天的戶外時間僅限于早上一個小時,周末偶爾會到女兒家吃頓飯,其余時間全在家里上網看帖子、跟朋友交換信息或看電視節目,對拓展新的社交關系沒有任何興趣。
對異地養老群體來說,利用現代網絡媒介與原有社會關系保持聯絡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可行的互動途徑。虛擬互動使得互動時間變得更加隨意,打破了面對面互動的時間限制。但互動空間由移居前原本的現實與虛擬空間的混合結構基本萎縮至移居后虛擬空間的單一結構,且受溝通設備取像范圍的限制,失去了面對面互動時對空間、環境、表情……的全景式掌握,這是虛擬互動的一個重要缺憾。甚至有些高齡老年人根本不使用網絡媒介,根本無法實現虛擬互動;若不積極開拓現實社交空間,他們將變成真正孤獨的人。因此,虛擬互動再好,也不能代替現實互動。正如帕特南的總結,電信通訊和傳統社會聯系應該互為補充,而非相互取代[27](p192)。
五、小結
“在場”是互動論者的基本理論前提,但也面臨著挑戰。當下我國頗具規模的異地養老群體,在移居初期面臨著雙重的互動困境:熟悉的人不在場,在場的人不熟悉。為化解困境,異地養老者選擇的互動實踐策略能夠給予我們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啟發。基于對訪談資料的分析發現,移居初期,異地養老者傾向于借用移動通訊、互聯網基礎上的虛擬互動方式與原有社會關系保持聯系。互動的形式和內容包括與重要他人的日常聯絡、小群體內部的情感凝聚與自我呈現、特殊事件的分享與共謀。虛擬互動的功能在兩條路徑上分別展現:一方面,維護了原有的社會關系,使異地養老者原有的生活世界得以延續;另一方面,借由虛擬互動的優勢,拓展和鞏固了在場的社會關系,體現了虛擬與現實間的相互促進。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異地養老者的生活實踐中,存在著虛擬互動擠壓現實互動的現象,這對老年人的生活健康和社會適應都不利。簡而言之,雖然虛擬互動對異地養老群體很重要,但無法取代現實互動的地位。
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建議,老年人個體、家庭、社區應合理利用虛擬互動與現實互動方式,發揮二者的合力優勢。首先,在移居初期,老年人可以盡量利用虛擬互動平臺與原有社會關系保持持續、穩定、深入的聯系,原住地的親友也應多多關心、聯絡異地養老者,緩解因“熟悉的人不在場”而產生的情感空虛和焦慮。其次,老年人在移居前,要做好心理準備,充分評估移居后的生活變化及其影響;移居后,快速調整心態,在生活時間分配上應多安排戶外活動時間、參與多人活動和集體活動,在遷入地主動拓展社交空間。再次,對于外來老年人聚集較多的社區,應秉持一種積極的社會管理理念,借助智慧社區平臺搭建起針對外來老年人的線上和線下的互動互助平臺,從社區的角度幫助外來老年人發展和鞏固新的社會關系,緩解移居初期心理上的不適,盡快融入當地社會,最終幫助他們提高異地生活的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