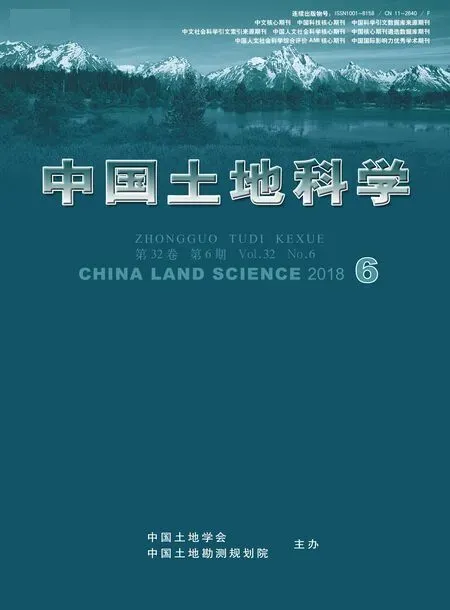經典案例邏輯中的準征收理論和實踐:中美差異和政策選擇
張 鵬
(廣東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廣東 廣州 510320)
1 引言
對準征收的理論探討源自對于土地產權的保護。準征收是指當政府或其授權的機關出于公共利益對財產權利的行使進行限制,或提出義務,導致財產權人無法正常對財產進行使用和收益,使得財產價值遭到貶損,從而具有等同于征收效果的一種行為或制度。土地準征收實踐源于政府對土地的管制行為,而后者被認為是為了健康、安全和公共福利目的國家行使的一種合法和正當的警察權力,它是土地政策的基本工具,且是其他國家政策的輔助性工具。過去,部分人認為,為了公共利益,土地管制是一種簡單的、廉價的、易行的公共政策,根本不需要補償,如農地保護利益歸屬全社會而成本被少數人承擔。這種認為管制沒有任何社會成本的計劃經濟式思維,不僅容易導致過度管制從而損害財產權和“財政幻覺”,而且導致社會不公。
從保護財產權的視角看,國家或政府的存在就是讓國民充分享有財產權利,在現代市場經濟下,只有承認和保護財產權,才能維護社會交易秩序,激勵公民從事有益于社會的各種活動,促進一國財富的不斷增加。作為重要財產權載體的土地,亟需從改善國家土地管理方式、緩解社會沖突或保護公民利益角度,加強對準征收制度和政策的梳理、國際對比、檢討和修正。本文通過對美國準征收的理論和案例實踐梳理,試圖得出中國可借鑒的經驗。
2 國內外研究現狀
從財產權理論發展趨勢看,在現代社會快速發展、資源稀缺和利用外部性增加的趨勢下,財產權的內涵處于動態的界定中[1]。社會經濟發展彰顯了對財產權保護的強烈需求,但財產權往往擔負著一定的社會義務,二者需要一種平衡。與傳統的土地征收構成對公民土地財產權的完全剝奪不同,當代的準征收以更加普遍和更加隱性的方式對土地權利構成界定或侵害。
準征收本質上是對財產權的限制,雖具有正當性,但不是無條件的。周家維等認為對不動產財產的限制,應當遵循正當、合法、合理、合比例原則,以最大限度地達到自由與限制的平衡。適度限制應該具備5要素,即目的的正當性、公益性,限制行為的法定性,程序的正當性,限制功能的輔助性,手段的適度性(比例原則)[2-4]。但上述觀點都沒有考慮到艾潑斯坦所言的管制給受影響者帶來的暗含補償問題。對政府管制行為何時構成準征收并給予補償研究方面,約瑟夫、費希爾等有較多研究[5-7]。特納等從經濟學的效率視角,以模型的方法對準征收和補償的激勵、效率、風險等角度做過研究[8-18],但經濟學的研究是存在不足的,希度等指出了社會學理論在準征收研究中的重要性[19]。中國學者對準征收的性質、判定標準、補償等也做了不少研究[20-26]。
綜上,從學理上看,土地征收和管制(準征收)都屬于國家擁有的一項基礎權力。準征收和財產權是一對孿生問題,他們都不能離開對方單獨討論。準征收介于征收(補償)和警察權行使(不補償)之間。重要的一點是:在討論準征收問題時,部分研究者假定土地權利中的土地開發權的性質和歸屬是清晰的。實際上,對此學術界并無統一觀點。土地開發權定義、歸屬或者基本土地權利內容是土地權利是否遭受損害的討論起點。如果沒有權利的起點,后續的研究缺乏根基。由于各國制度、文化、觀念等存在較大差異,對土地權利的內涵或初始權利的界定認識不同。以土地管制為例,管制的目的是公共利益,是讓人民最大可能多地分享利益。管制必須確定合理的界限,如果管制武斷地拿走必要的權利內涵并缺乏有效救濟,那么整個土地權利制度、征收制度、規劃管制制度的權威、效率和公平、公民的遵從和守法效果都將大打折扣。
3 美國關于準征收問題的理論和法律實踐
作為一個聯邦制國家,美國的土地管理權力主要分配給州及地方政府。作為一個判例法傳統的國家,雖然各州土地和規劃法律亦以成文法的形式表達,但美國對準征收的規定不是以法律條文,而是更多以州憲法精神、法官判例等得以體現并被人們所遵從。回溯20世紀的法律演化過程,主要通過一些關鍵案例和法律實踐的梳理,可以發現美國法律對管制、財產權、準征收問題的基本理論演化脈絡。
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都是保護和征收財產權重要的憲法依據。征收條款的含義是,如果一個人擁有私人財產,那么政府可以征收,但是必須是公用且必須受到公正補償,按照市場價值補償。任何層級政府的土地管制和規劃行為是要受到聯邦憲法征收條款規制的。
從定義上看,在學術界準征收也被稱為管制性征收、反向征收(Inverse condemnation)、沒收性征收(Confiscatory taking)、推定的征收(Constructive takings)。但最為常見和典型的名詞還是管制性征收(Regulatory taking)。這個詞語在20世紀早期得以確定,它和準征收可認為是同義詞。早在1922年賓州煤礦案(也可叫馬龍案)中,法院判定“當財產可被限制到一定程度,但一旦走得太遠,就構成征收”,這種征收被描述為推定性(constructive)或管制性征收。本案是管制性征收概念形成的標志,該案告訴人們,管制有可能等于物理征收,當管制走得太遠,那么等于物理征收需要補償①參見美國最高法院判例:PENNSYLVANIA COAL CO. v. MAHON。260 U.S. 393 (1922) “The general rule ... is,that while property may be regulated to a certain extent,if regulation goes too far it will be recognized as a taking”。,這也是判定準征收的一個重要的標準。
3.1 財產權保護理念和實踐的歷史分期
財產權保護和準征收構成一枚硬幣的兩面。美國的土地管制及財產權保護理念和實踐(包括征收和準征收)可分為4個關鍵時期:
(1)奠基期(1900—1928年)。典型案例包括海達切克對色巴斯坦案(1915)、馬龍案(1922)和歐幾里得案(1926)。1915年對政府管制尚沒有限制,1922年政府的管制可能被質疑,可能走得太遠,此時要么補償,要么取消管制。本案判定政府管制走的太遠而需要補償或取消管制。到了1926年認為制定分區并列出許可用途是一個管制可接受的方式,并沒有走的太遠。(2)沉寂期(1929—1977年)。典型的是鉑爾曼案(1954),這和后來的博勒騰案(1981)和凱洛(2005)案判決遙相呼應。這也可能和美國在此階段急于發展經濟有關。1954年案例認為政府可以征收土地從私人轉移到私人,只要是為了推進公共利益,且當原來的土地處于衰敗的區域,是合法的。(3)邊界界定期(1978—2000年)。警察權和征收的邊界處于界定期。典型的案件是諾蘭案(1987)、多蘭案 (1994)、第一英格里希案(1987)和盧卡斯案 (1992)。此時,政府的管制行為受到嚴格審查。賓州車站案認為應該對過分熱心的政府管制要施加限制,實際上,這些限制是否能真正挑戰政府管理私人財產的方式仍存在疑問。(4)2001年至今。典型的案件是泰浩—西拉案(2002)、凱洛案(2005)和Stop the Beach Renourishment(2010)案。2002年判定地方土地管制是正常和預期的政府功能;2005年判定政府可將土地從私人轉移到私人手中來推進公共利益,只要以經濟發展和創造就業的名義即可,不管最初土地是否屬于衰敗地區。在這里,征收和準征收被視為具有類似特性,可以認為準征收是一種特殊的征收,且合理的管制逐漸擴大。
3.2 美國準征收的學理分類
不同類型準征收有不同的判定標準或嚴苛程度,學理分類是實踐的總結。如果將管制性征收稱為反向征收的話,可分為三大類:
(1)物理占有。當政府對不動產進行永久性物理占用時,就會發生物理占用征收,無論多么微小或占用的是什么,占用者可以是政府授權的第三方,不一定是政府。這種情況最典型的例子是一個不動產之下建設了新地鐵,對不動產的安全造成了影響或潛在影響,業主可舉證要求獲得補償或征收。
(2)管制性征收。這是一種最典型的征收。又可分為兩大類:①類型征收(categorical taking):一種情況是其經濟價值全部被拿走;一種情況是本身征收(per se),發生在被物理占用的情況,典型的如Loretto案中。②非類型征收(non-categorical taking)。一般發生在政府施加的管制對財產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但未失去全部經濟價值,這時需要進行檢驗性判定,是否構成征收。
(3)捐(exaction)。當業主向政府申請建筑許可時,常被要求捐獻土地或金錢、提供地役權等各種形式的義務,如果不合理,就可能構成因捐而發生的征收,這常見于業主申請建筑許可時。
4 準征收14個經典案例中的邏輯
美國關于管制性征收有最為經典的14個案例(以下皆為簡稱):歐幾里得案(Euclid)、馬龍案(Mahon)、蘇特姆案(Sutum)、克石通案(Kestone)、盧卡斯案(Lucas)、洛瑞拖案(Loretto)、泰浩—西拉案(Tahoe-Sierra)、賓州中心案(Penn Central)、諾蘭案(Nollan)、多蘭案(Dolan)、昆茨案(Koontz)、帕拉佐洛案(Palazzolo)、第一英格里希案(First English)、林格案(Linge)①這些是規劃法中最經典的案例,都可以在網絡公開下載法院判決和法官判決詞。如https://www.oyez.org/。。回顧這些判例有助于摸清如何尋找管制和征收之間的界限和邏輯。
從14案的法院判決統計結果看,政府管制勝訴5次,被管制的使用者勝9次。從案件發生的年代看,1920年代2個,1970年代1個,1980年代4個,1990年代3個,21世紀4個。從政府行為類型看分為以下三類:(1)管制法令或暫停令:歐幾里得、馬龍、盧卡斯、泰浩湖、帕拉佐洛、第一英格里希、林格案;(2)附TDR的管制:蘇特姆、賓州中心案;(3)捐的要求:諾蘭、多蘭、昆茨3案;(4)物理入侵:洛瑞拖1案。提出的重要概念或理論有:走的太遠、可移轉發展權、對法律本身挑戰(facial challenge)、對法律適用挑戰(as applied challenge)、成熟、剝奪了財產所有者的使用權利、經濟互惠、實質性促進合法的國家利益、物理占有、必要地聯系、施加的條件和新開發所引發的負擔或影響之間大致的比例、管制對產權的負擔的嚴重性。這些案件的共性都是政府在面對財產權人使用財產、使用發展權或開發財產時,予以管制或提出條件所導致。
由于準征收類型多、涉及因素多,給確定判斷標準帶來巨大困難。劉海平認為歷來的判例也是沖突的,聯邦最高院重點考慮三個要素:(1)經濟上的影響(對財產價值的減損);(2)對公民合理投資期待所干預的程度;(3)政府行為的性質。很多情況下,法院往往就是依據公平正義的標準,這還是一個實質性公正程序問題[27]。
劉連泰提出了最重要的幾個基本概念工具:實體性正當程序、權利束、平均利益互惠原則[28]。它們和警察權的概念一起,構成了分析管制性征收的基本元素,通過元素與元素的組合,構造了確定管制性征收的坐標系:實體性正當程序是手段和目的構成的坐標系(判斷阻止財產有害利用的管制是否構成征收),平均利益互惠是負擔與利益構成的坐標系(判斷提升公共福利的管制是否構成征收),權利束是被剝奪的利益與財產的全部利益構成的坐標系。聯邦最高法院不過是交替適用三個坐標系來判斷管制是否構成征收(廣譜適用的坐標系)[29]。這三個坐標系不僅極為重要,而且反映了管制問題的本質屬性。
綜合14案,有7個根本性原則或因素體現在法官的判案邏輯中:(1)是否本身征收;(2)是否成熟;(3)是否走的太遠和存在財產利益;(4)是否存在合理聯系和大致比例;(5)是否物理占有;(6)發生時間;(7)是否通過三因素檢驗。
一般而言,一旦構成侵入,很容易判定構成征收,此外,判定構成征收的觸發點還有管制是否構成一個持續或暫時性對私人財產的入侵。物理干擾容易判定征收這個爭議不大,如羅雷托案6∶3的壓倒性意見,多蘭案、諾蘭案也觸及這個紅線。結合上述對反向征收的分類,發現準征收檢驗的難點是管制性征收和捐引發的征收兩大類,其中關鍵是非類型征收。
再進一步看,法官對準征收判案的內在邏輯和征收條款的內在精神是非常一致的,二者之間存在共性的東西①征收的一般憲法保護原則有三個:公共利益、正當程序、公正補償。。一是對公共目的的強調,這和政府行為的性質有關——是否實質性促進了公共利益,也和地主遭受負擔和管制帶來社會收益合理性和對比有關(類似比例原則)。二是對正當程序的強調,如合理聯系、大致比例、是否成熟之類的檢驗。憲法的正當法律程序條款從兩個方面同時保證了防止國家濫權和釘子戶損害公益的情況發生。正當法律程序是指公平和固定的程序。某種程度上正當法律程序只不過是憲法變相為政府實施警察權力開了一個口子。三是對補償公正性的重視,這方面的檢驗較多且復雜,如可移轉發展權補償、互惠原則、負擔義務相稱、基于合理預期的投資等。第三類補償檢驗最為重要和困難,留給法官的自由裁量權最多。
總的來說,法律本意不是拒絕政府管制,而是對財產的限制一旦構成征收必須補償。首先,政府的行為必須基于公共利益,這是一個并不困難的前提,因為很少被違反。其次是政府的行為不能剝奪地主所有經濟價值,這類似公正補償原則。政府不能將公共利益的借口施加給單個人來承受,管制是對一般大眾的,且公共利益和義務之間要合理聯系且大致成比例。現代社會里,管制往往會給地主造成經濟損失,所以給地主有沒有補償性利益以此來免除補償的責任是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體現了公正補償原則。
5 中美差異下準征收對中國的政策借鑒價值
正如劉海平所言,準征收及其公正補償條款將政府從一個權力機構轉變為一個理性人:政府在決策過程中必須平衡收益和成本,這不僅有利于防止政府權力的濫用,也有助于保證政府的管制行為符合社會的總體利益[27]。
5.1 中國的準征收類型
長期以來,中國是一個重視公權力而忽略私權利的國家,政府享有權力,但對承擔相關的責任不夠重視,以公共利益的名義,在出臺一系列的法規、法令、命令等時沒有動機去考量成本與收益,很容易對私人的財產權利造成過度侵害。那么中國到底是否存在明顯的準征收?對比3.2節對準征收的分類,至少可以推定以下情況中,中國存在準征收的可能。
第一類是國家法律法規所致。如羅靜靜認為中國在土地利用管制立法上補償制度缺失,如《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第12條規定的土地使用的年限限制,《森林法》 《文物保護法》 《自然保護區條例》有關條款都一定程度上產生了準征收,并對公民的私人財產權益造成了侵害[22]。本類準征收類似于非類型征收,因為畢竟管制并未消除土地的全部經濟上有益的使用。
第二類是在申請用地、規劃等許可證時被要求捐地用于建設學校或公交站等公共設施或直接繳納有關配建費用,可視為一種“義務型”管制。如果在土地招拍掛時附加有該義務,那么這種義務本質是地價的組成部分,且一定限度的義務對開發商可能是有利的,不應該定性為缺乏“合理聯系”或“不成比例”,不構成準征收;但反之,過度設定義務則有準征收的嫌疑。還有一種類似情況是政府對已經頒發的規劃許可進行修改,且修改減少了初始的權利,如容積率。
第三類是類似于物理入侵,例如地鐵等市政工程如果導致建筑物發生沉降或斷裂等損壞,強行將有關管道、電纜、道路等通過特定土地,則構成準征收,但以有償方式設定地役權的除外。
除此之外,是第四類具有模糊性的政府行為,主要表現為過度的管制(但政府并不認為過度,且在主流意識形態下,被管制者的剝奪感并不強),如:(1)用途管制制度下,即使土地被規劃覆蓋并準許非農用途,依然不能轉換用途,規劃用途并不是土地的內在權利,換言之,土地幾乎沒有初始權利,只能通過征收、出讓諸環節來轉換用途。此時,土地雖然并沒有被剝奪全部的經濟價值,但不具有任何用途選擇的權利,涉嫌構成嚴重的管制。(2)對集體建設用地的入市限制。現狀是建設用地,不需要用途轉換,不涉及危害公共利益(耕地保護),仍然被禁止進入房地產領域。類似的例子還有宅基地,宅基地只能轉讓給本村人,這種限制購買者的方式實際上使土地價值失去絕大部分。上述兩種情況在長期的法律運行下,被認為是合法的為了公共利益目的的管制。
5.2 中美兩國的制度差異
那么,中國是否可以借鑒美國的準征收制度或者部分借鑒?筆者認為部分對財產權的保護精神和糾紛裁決等制度是可以借鑒的,但有必要首先認識兩國基本制度的巨大差異。
(1)美國的法院對立法和行政的制衡力量很強大。法院可以通過法官的判案對立法行為、法律條文進行詮釋,對政府的行為合法性進行裁決,從而對公民權利的保障非常有力,且最高法院的權威性非常高。中國的法院很少對法律的合憲性、地方法規的合法性進行裁決,而是更多地交給行政機關來解釋法律或以條例等方式立法,而正是此類行為構成了準征收的大部分。
(2)美國的準征收是建構在分區為特色的土地干預制度之上的。美國的州政府擁有很大的權力并將有關土地管理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最典型的土地規劃管制工具包括綜合規劃、分區、細分和官方地圖。一般而言,分區法是立法行為,非常詳盡,規定了每一塊土地的多種用途選擇(而非一種),以及規劃條件等。在此制度下,土地具有基本的權利,尤其是基本的土地發展權屬于地主,只要符合法律和規劃管制條件,申請開發一般能獲得批準,所以判斷準征收具有起點(基點)。中國建立了規劃制度,但相關的土地市場、土地供給、土地征收等制度并不默認土地權利人具有開發權。同時土地發展權制度尚屬于法律空白,土地發展權及其他建筑許可批準權(包括自由裁量權)幾乎都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所以對管制和許可等具體行政行為何時走入準征收的判定具有更大的技術難度。
(3)土地制度差異。美國土地以私有制為主,土地的權利束比較完整,且無限期。中國虛化所有權,公民擁有的只有使用權,權利束定義不夠清晰,不夠完整,有限期,且更容易受到政府的干預。另外,土地管理制度差別也比較大,美國的土地市場是壟斷競爭結構,地方政府絕非唯一的供給主體,而中國的地方政府一般是唯一的一級市場供給主體。在征地方面,美國多數采用購買而很少動用征收,而中國則普遍使用征收方式獲得新增土地供給。另外,美國地方財政一般靠房地產稅,而中國一般靠土地財政,這使得地方政府的行為激勵明顯不同。
5.3 美國經典案例的借鑒價值
(1)不斷探索警察權和公民財產權保護之間的合理界限。社會發展階段和理念決定了美國對財產權保護的力度是很大的。無論是從典型的馬洪案提出的“走得太遠”,還是現代社會發展需要的、必要的和細微的“捐(exaction)”的義務。在管制領域,很多的案例中,實際對財產權的干預強度并不大,如洛瑞拖案、多蘭和諾蘭案,仍然被判定構成征收。
無論是征收、準征收還是土地管制,都是圍繞土地權利和國家(集體)公權力的平衡問題展開。征收行為具有明顯的權利剝奪特征,且以補償為“唇齒條款”而具有可辨別性。土地管制對權利的部分剝奪具有隱蔽性和漸進性,是私權利和公權力角力的結果。土地作為一種市場資源和要素,必須結合其特性,將權利放置于特定的市場條件下進行判定,才具有更強說服力。現代社會發展已經逐步揭示,土地發展權作為土地的一項權能,受制于并對抗管制的功能日益凸顯。考慮中國的法律體系和社會理念,目前準征收判定的重點應該立足于土地基本發展權的定義方面,否則很難說政府的管制或行政許可侵犯了財產權—太過—從而需要補償。在中國,在賓州中心案構建的普遍三準則——對訴求者的經濟影響,顯著地干擾了基于投資的預期,政府行為的特征,適用存在困難:第一,管制很難說對地主產生了什么經濟影響,因為地主對自己的權利稟賦并不清楚,只是感覺受到了影響;第二,更難說存在“基于投資的預期”,買什么的土地就有什么樣的權利,變換用途永遠掌握在政府手中,缺乏確定性;第三,政府行為多數具有公共利益且很少提供互惠利益,如是否可以使用TDR工具,這需要政府提高土地管理市場化水平。
(2)土地利益以及給權利人造成的損失和負擔是考慮的重點,在管制同時應該給予適度的明示或暗含的權利補償。一般地,管制都能或多或少地給土地權利人帶來普遍利益,但是決不能讓限制的代價由特定權利人承受。在管制的同時,給予當事人適當的現金或權利補償,如給予發展權或可交易發展權(TDR)。如此,政府的大部分管制行為可免除補償義務。
(3)現代國家應該對自己的行為的目的和效果進行謹慎地審查。對包括土地在內的私權利進行保護與國家保留的征收公權力是伴生的。作為警察權的管制亦不例外。基于生態環境、社會公平等考慮的用途管制本身沒有錯誤,但是違背“平等”、“比例”原則的幾乎完全剝奪被管制者發展權的管制卻是不合理的。另外,只要有公共利益就不會構成準征收是一個極端錯誤的認識,這一點在盧卡斯、諾蘭和洛瑞托案表現的非常明顯。某種意義上,保護財產權也是公共利益。尤其是在林格案中,奧康納法官發表法院一致意見認為,法院需要“糾正路線”,并明確指出,在阿格斯提出的“實質性推進”公式不適用于確定一項管制是否達到違反第五修正案下的征收。征收條款對管制的挑戰必須基于管制對產權的負擔的嚴重性,而不是管制在促進政府利益方面的有效性。
另外,地方政府在房地產開發過程中,不能任意設定額外的公共設施配件或繳費義務,如果確需設定,一定要讓開發者獲得的利益和負擔之間達到一個“合理的大致比例”且二者之間是有聯系的。
(4)準征收和征收適用同樣的法律保護原則。即公共利益、正當程序和公正補償,但對準征收而言,公共利益是一個最弱的原則。即使有公共利益,還要看管制利益給權利人造成的損失的對比關系。法律“本身的挑戰”和“適用挑戰”、成熟性的問題,都是程序性標準,要通過設置正當程序來保護公民利益。實質性正當程序就是公平正義。不能剝奪地主所有經濟價值、有沒有補償性利益給地主,則是公正補償原則的體現。而將法律原則落到實處,還需要進一步的制度供給,如市場構建、糾紛裁決、利益表達等。最后在司法領域,有必要加強法院對行政機關立法和行政行為的司法裁決,否則,只靠政府自律或內部監督,公民的財產權保障力度很難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