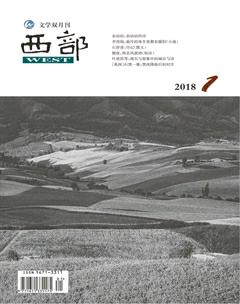驛道上的過客
洪忠佩
從來沒有走得這么難。我覺得我不是在前行,而是在后退——向著山村時間與空間的后面退,那樣急切與刻不容緩,生怕去晚了,前方山村的人和事就不見了。在我眼里,驛道與村莊不僅有一根流轉的連線,還有當下一個難解的死結。
一
走進大秋嶺已近臘月,綿延的山巒曾有過怎樣憾人的秋色,在我心中仍然是個謎。據說,大秋嶺“以山勢秋秋蹌蹌,騰驤磊落而名”,那應是秋天山野色彩很有氣勢的一種飛躍與奔騰吧。古時,山村能夠想到這樣句子的人,想必是喝了不少墨水的。
大秋嶺上的貓兒刺(枸骨)是青的,草卻枯了,楓香的樹葉落了地,而黃枝(黃梔子)、羅英(金櫻子)黃的紅的吊在枝頭,特別醒目。許是腳步聲驚擾了茅叢中的雉雞,撲地飛出一群。遠處,分明有一只白色的錦雞在林間慢悠悠地散步。麻雀與黃瓜鳥(綠鸚嘴鵯)更是熱鬧了,一路都是它們靈動的身影。麻雀和黃瓜鳥個體不大,聲音也細碎,但歡快地啄著蟲豸的神情是一樣的。
跨在路上的半山亭,已經塌了一半,破敗得不成樣子了,橫梁露著半截,椽都斷了,瓦礫滿地都是,亭頂現出一片天光。即便這樣,亭內的光還是有明暗。半山亭,原本是供過往路人歇息的場所,顯然,這樣的功用已經不復存在了。
這,只是山嶺的荒僻嗎?
不盡然吧。
山風吹來,陽光濾過樹葉,蜿蜒的石嶺一路光怪陸離。腳踩在枯葉上,沙沙地響。徒步上嶺,講究的是腳力與耐力。我的腳步是緩的,不疾不徐,這樣走似乎特別適合徒步驛道。山岔口嶺洞(永濟洞)的出現,尤其是洞壁上刻著的《永濟洞記》,著實讓我心生歡喜。“婺北六十里,有大秋嶺,延山里而峻,行者飲倦。其北麓有大小二洞,不可以涉。先是靈泉公伐石為橋,嶺之頭筑洞……于佑于佑于興公,素知為紀其長歲月,以徽其濟之永也。”《永濟洞記》是一位名叫汪夫卷的人在萬歷甲戌年(1574)十月撰的,記的是先祖靈泉公與興公建橋筑洞的事跡。
在此前,有多少人讀過這樣的文字呢?
遺憾的是,我讀到的是風化的版本。這沉靜遼闊的山野,還有多少人和事在風化?我無從查考寫《永濟洞記》作者的生平,他應是山野村莊文字優秀的代表。
實際上,永濟洞不是從山體穿過的,而是用青石卷砌的,整體的樣貌像城門洞,抑或關隘,洞頂卻長滿了免枧(檵木)、栲樹、櫟樹、荷樹(木荷)以及黃檀。《永濟洞記》上說,北麓有大小二洞,可除了嶺洞(永濟洞),另外一洞卻不知所蹤。在徒步大秋嶺前,對面山從港頭至大汜的斑竹嶺我穿行了,沒有發現青石卷筑的嶺洞,一路上只有三座路亭(其中兩座亭頂已經坍塌)。
順著永濟洞下,是去汪槎的山嶺,橫過洞口,拐彎,則是通往大秋嶺村的小徑。其周邊呢,有“羅嶺十八肩,肩肩叫黃天”的說法,可見嶺的陡峭與村民出行的困難。我對肇奇兄說,既然徒步在大秋嶺,何不去大秋嶺村中走一遭呢。
山嶺與小徑,似乎是埋在大秋嶺村的伏筆。能夠聽到狗吠與雞鳴,貼在山上的大秋嶺村就展現在眼前了。與周邊的港頭、汪槎、大汜相比,六十多戶人家的大秋嶺村格局顯得小了。村舍倚著山,板壁的,磚墻的,混搭在一起,有的木柱作撐,屋底直接是空的,而有的前屋二樓幾乎與屋后的路面齊平。然而,大秋嶺村的始祖在明朝末年從慶源遷到這里時,對村莊布局是否是同樣的構想呢?他們很難想到一脈相衍,村莊幾百年后會如此擁擠。
或許,高聳的香樟、楓香,開鑿的石池以及廢棄的石礎、石磨、陶罐是村莊最初的遺存。
一間小得不能再小的閣樓,一塊水泥板連接路面,柜臺也沒有,貨在木架上散堆著,這應是我看到的最小的百貨店了。店門敞開,店的主人卻不在。
偶爾,我在村巷里遇到了兩個上山砍柴的婦女,其中一個是早年從汪槎嫁到大秋嶺村的,她的三個子女都在外地打工。家里有女人,鍋灶就不會冷。在村口的池塘邊,我還遇到了年過八旬的詹樹慶老人,他挑著一擔糞,應是剛剛從菜園歸來。
逼兀,局促,遲暮,倦怠,缺少人氣,是我對大秋嶺村的第一感覺。詹時女老人的喘息與她拉手鋸的聲音一樣,時斷時續。她坐在門前的木凳上,艱難地鋸著毛竹當柴火。老人說,兒子在外地打工,自己病了,媳婦只好回來照顧她。去縣城住了幾天醫院,好點就回來了,能夠動就做點事,兒子媳婦養家糊口不容易。一頂毛繩帽遮住了老人的腦袋,她抬頭的時候,我看到她渾濁的雙眼含著淚水。
嚇呼,嚇呼,手鋸能夠鋸斷毛竹,卻鋸不斷老人的孤獨。老人撩起布滿油漬的圍裙擦了擦眼淚,無奈地嘆了口氣。
巷口老屋的磚墻,倒了一截。那豁口,一如老人殘缺的牙床。
二
皴裂的手指,有三道血紅的傷口;裸露的手背上,也有了細微的裂痕。老人不管不顧,還是若無其事地背起塞滿了蘿卜菜(蘿卜纓子)的菜籃,佝著身子走了。狹長的田埂,瘦小的身體,讓裝滿蘿卜菜的菜籃更加臃腫。
如此倉促的相遇,還沒容我打聽老人的姓名與年紀,老人就走遠了。她那皴裂的傷口,讓我感到了來自山村寒冷的尖銳。
村,建在山坳拱起的地方,塘窟的村名也恰如其分。三四十戶人家,圈在一塊土坦周邊,倒也密集,好比是大家冬天里圍著火爐盆烤火。土坦上堆滿了杉樹圓木,還有竹篩竹盤里曬著的番薯干(紅薯干)。向著村頭的平鼻嶺走,山坡地上是高矮不一的茶園。像天外的“飛來石”,一塊巨大的山石斜斜地聳立在路邊(約莫有兩層樓那么高,六十度傾斜)。挨著巨石,還有村民傳說的“仙人洞”。民間道聽途說的神話故事多了去,還是村民老張的一句話實用,“仙人洞”呀,是村民上山躲雨的地方。
老張在平鼻嶺馱樹,正好在“飛來石”旁歇氣。六十三歲的他,從山上馱來的杉樹圓木大約有一百三十斤左右。他的腰與肩膀混淆了他的年齡。
雖然是冬天枯水季節,山澗里依然淌著水響。陡,是平鼻嶺的標志。石韋、矮腳茶(平地木)、絡石藤(絡石)、石林珠(鐵角蕨)、箬皮(箬葉)、猴猻刮屁股(雞血藤),隨著嶺邊石縫長。一個六七歲的小女孩,拖著兩根刀柄粗的雜樹棍,一腳深一腳淺地迎面走來。
我問她,怎么不放在肩膀上馱。
她仰著紅撲撲的臉,羞澀地應道,馱不動哩。
在城里的孩子覺得書包與課業負擔重的時候,山里的小孩已經跟著母親上山馱柴了。
這,便是城鄉孩子的差別之一吧。
嶺邊的杉樹林,密而直,根根都是一梢線。林中的杉樹,大的都可以取材做房屋的木柱了,小的還只有木笐般粗。越往上,灌木、喬木混雜,落葉的、常青的都有。在密林中的嶺上繞來繞去,真的有點像上山的蛇行。
山脊上的石亭,從掛在亭壁上的“功德排(牌)”上看,還是八年前村民自發修繕過的。按照婺源的民間信仰,石亭中設有神龕,供奉地方菩薩——泗州大圣。不知是何緣故,神龕在修繕時散失了。我由此想到在下港頭關帝廟前一位村民磕頭作揖的樣子,我問他拜的是什么菩薩,他搖搖頭,轉身走了,留給我只是一個躬身的背影……與亭相連的石屋,早已塌了。據說,石屋曾經住著一位姓張的燒茶人,于是便有了石屋茶亭的來歷。亭邊的石井被枯葉堵了,但還可以看到水痕。如果時間退回五十年前,石屋有人施茶,石亭有人歇腳,還有人在亭中背起行囊繼續上路。
而消隱的,只是亭中的燒茶人嗎?
在這樣的山野石亭之中,恍惚時間是靜止的。亭前,立著一塊青石的山林禁碑。那碑上的年代,是我未曾到過的。因此,青石的石碑給我展現的不僅是風雨剝蝕的一面。
我翻過平鼻嶺,是要去石屋坑村—— 一個落在安徽休寧地界,從婺源甲路與清華遷去的村莊。在石屋坑村,一口純正的婺源話,是村民最好的胎記。
三
雨霧。叢林。荒徑。
落葉與腐殖土厚厚的一層,一徑往上都是野豬經過的痕跡。橫亙路邊的原木、樹兜,長出了一朵朵的菌類,像開在樹兜原木上的花朵,紅的鮮潤,白的純凈,讓徒步的路上有了活脫脫的喜感。背風向陽的坡地上,還有穿山甲挖出的新土。老齊一邊走一邊琢磨,總覺得不對勁,他掏出手機給新嶺下村的老張打電話,說山路有岔口,像是迷路了。老齊是西源茶坑人,在石峽林做茶多年,曾好幾次帶我進山訪古,去尋找西源村莊的歷史積層,但遇到這樣的情形還是頭一次。老齊覺得冒著雨霧走了這么長的山路,找不到青石洞(永新亭),總是歉疚。是呀,當年廣為人知的“大路”,怎么就逐漸被人遺忘了呢?
原準備從朱家村進塢上嶺去紫云亭與天竺庵,在朱家祠堂門口被村里老人勸住了,說是雨霧路荒,進不得山,于是改道走了新嶺。出乎意料的是,新嶺也荒得夠嗆,狗脊、貫眾、懸鉤子、牛郎擋(南五味子)、芭茅、荊棘、絡石藤(絡石)以及蜘蛛網交織一起,每走一段都是對步行者勇氣與毅力的考量。麻雀、長皮鳥(壽帶鳥),還有雉雞喳喳咕咕地叫得歡,它們像山澗里潺潺的流水,只聽見聲音,卻很難看到它們的蹤跡。新嶺建有嶺腳亭、嶺脊亭、腰亭三座石亭。嶺腳亭的“助銀碑記”上,依稀能夠辨出俞姓和胡、王、金姓捐銀人名以及“清乾隆十三年(1748)吉旦”等字樣。在遙遠的年月,新嶺嶺脊亭是由思溪村“思本堂”買下嶺上的山場,把林木的收入用來作為住亭人員燒茶的支出的。為了燒茶方便,嶺脊亭邊還專門鑿了“冷水窟”(一眼泉)。而這些,都像山徑一樣荒蕪了。往山上走,個別路段還殘存驛道的痕跡,有的路段直接被土石覆蓋了。檵木、楓香、栗樹、楮樹、栲樹、樅樹,共同組成了山路邊的林相,偶爾還夾雜在幾株梧桐與檉籽樹(油茶),交合、遮蔽。天陰,霧重,荒徑在樹林里穿行,前方仿佛幻境。有青石板的臺階,長出了苔蘚,缺失了青石板的土路,有腐葉覆蓋。盡管小心翼翼地走,還是感覺到滑。空氣中除了雨霧的氣息,還有腐殖土的氣息。驚喜的是,走在這樣的山林中,飄飛的落葉美得叫人咂舌,黃色的、紅色的,緩緩地飄落,宛如蝶影。迷惑與幻覺,是我在林中穿行時首先想到的詞匯。
九里嵐培十三彎是一個籠統的說法,其分別與秋口梓槎、浙源沱口、清華大塢交界,山與山之間都有古驛道相連。驛道三五里之間,建有路亭,路亭中設有神龕,大多供奉的是婺源的地方菩薩——泗州大圣。相傳,泗州大圣是婺源鄉村的地方菩薩,護佑著一方山鄉的平和與安寧。神龕簡樸,只在一塊青石上刻有“南無泗州大圣尊神之位”的字樣。七轉八轉,終于找到了藏于山體用平整的青石砌起的青石洞,殊異的是,神龕中供奉的是一尊石雕的佛像,神龕上刻著“阿彌陀佛”。西源,是一個民間信仰多元的地方,土地廟、社公廟、關帝廟、晏公廟。還有一個村莊不僅有太尉廟,而且直接用太尉廟作了村名。所有這些,都應是山村人精神取暖的地方吧。據說,青石洞的佛像早年曾經被鄰村的一位篾匠偷去賣了。結果呢,篾匠的精神失常了。后來,村民想盡辦法才把佛像請回了青石洞。祖祖輩輩居于山村的村民,在一尊佛像上找到了一份心安。長在青石洞洞頂的樹木,根裸露著,洞前有青石堆起的半截石墻,好比是村莊老屋的照壁。我與老齊站在洞口的雨霧中,靜默不語。
在西源的村莊,我在水口看過許多廟,也看到了禁示碑、養生碑、橋碑、孤魂總祭碑,不去想村莊的歷史過往都難。譬如,太尉廟既是廟名亦是村名,我覺得很難理解。太尉的官銜可上溯到秦漢,為正一品。而偏遠的西源山村,怎么會與太尉有所關聯呢?據說,太尉廟供奉的三尊神像是父、子、孫三代太尉,村名也因此而來。令人疑惑的是,婺源村莊為何僅此一村有太尉廟,父、子、孫三代太蔚又是何許人呢?歷史上,確有“楊氏一門三太尉”——東漢文學家楊修的曾祖父楊秉、祖父楊賜、父楊彪——東漢延熹五年(公元162年)楊秉代劉炬為太尉,熹平五年(公元176年)楊賜官拜太尉,獻帝時楊彪授太尉之職。那遙遠的年月,楊氏與此地有何勾聯,又遺存怎樣的基因,卻不知端倪。鎖口潭的晏公廟,在婺源鄉村也是個特例。晏公(晏戍仔),明代玉封為“神霄玉府晏公都督大元帥”,在民間被奉為一方水神。晏公廟在什么年月,又是怎樣的際遇落戶西源山村呢?從胡家村進長田塢走長田嶺,路邊一塊風化的斷碑引起了我的興趣。石碑是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冬月重修長田嶺刻的,依稀可辨出刻錄的是塢頭、胡家、西源村民的捐款人名。長田嶺最初的建設年月已經無從知曉了,還好,讓我找到了一塊一百多年前重修長田嶺的斷碑,一如讓我看到了久遠年月民間精神的標本。
相對而言,長田嶺比新嶺要完整些,嶺的寬度也不一樣。只是,一路濕漉漉的,落葉太厚,稍不注意,腳下就打滑。在嶺腰的地方,聳著墳冢,墳的規模較大。一位在山地里睡熟了的人,他(她)的墓碑不會長高,而墳周邊的芭茅與雜樹會長。沒有看到墓碑,也不知道埋著的是哪一個村的先祖。墓的主人經年在這里看著嶺守著山,他(她)是否會孤獨呢?會生起這種荒誕的想法,我自己也覺得莫名其妙。老齊告訴我,從長田嶺嶺脊岔口轉下山,還可以走到他的村莊——茶坑。一路走來,只有這一句,老齊的話語說得十分肯定。橫過嶺脊,密林的路邊有路亭,雖然不知道亭名,但亭還是修得比較講究的:三方亭墻都是用青石壘砌的,青石與青石之間沒有任何黏合劑,卻平整妥帖。亭只有人字披的梁,蓋鱗瓦,卻沒有柱。亭內靠石墻的兩邊,設有石塊與圓木搭起的木凳,簡易、實用。盡管如此,給人的感覺還是一種衰敗與荒涼。圍著嶺脊的路亭轉,我沒有找到建亭人的蹤跡,只在亭內看到了“泗州大圣”的神龕。在這樣的山上,隱匿的只是建亭人嗎?
雨霧飄忽,根本打不開視野,即便站在山脊,也看不到九里嵐培十三彎的輪廓。山野寂寥,雨霧中佇立著我與老齊,還有落寞的路亭,高聳的樅樹、栗樹、栲樹、楓香。
四
塔嶺,僻遠、隱秘,自古是進出婺源的五條通道之一。五嶺分別是如今在安徽休寧縣境內的新嶺,婺源縣境內的羊斗嶺、塔嶺、對鏡嶺與芙蓉嶺。“山水吾州稱絕奇,間生杰出當如之。不行天上五嶺路,焉識人間二程詩。”早在元代,詩人方回在《寄還程道益道大昆季詩卷》中就提到了五嶺。清代經學家、音韻學家、皖派經學創始人江永(婺源人),還將婺東一帶的燕子嶺、回頭嶺、譚公嶺、對鏡嶺、芙蓉嶺連成一副饒有趣味的地名對子:“燕子回頭見洋際,譚公對鏡望芙蓉”……沿著青石板砌起的石嶺上塔嶺,兩邊依次是茶樹、檉籽樹(油茶樹)、毛竹、野藤、杉樹、灌木。令人訝異的是,石壁上野趣天然的“牛鼻像”還沒有看到,一匹牛犢竟橫在嶺上,茫然而無辜的樣子,不知它是在尋找茅草,還是找不到回家的路。我從牛犢眼前或身后繞過,它猶猶豫豫的,一動都不動。走過路邊的石亭,澗底就有了潺潺的水響,石板路也緩緩地平了。跨澗的永安橋只有一拱,青石砌成的,規整、平實,石縫里長滿了石韋與青藤。緊貼橋邊,有一棵不知名的小樹,葉面有一層隱隱的霜白,枝頭長著小巧圓實的果,樣子甚是惹人喜愛。
青山相峙,澗底幽幽。遠遠地,瀑布從山崖上跌落,形成粗長的白練,在陽光下銀光閃爍,如凝滯一般。俗話說,有瀑就有聲。然而,我與山崖上的瀑布相隔的距離實在太遠了,只見其景而難聞其聲。沿途的山澗,清流見底。經過水的沖刷與蕩滌,山澗石床呈現著原始的面目,光潔、圓潤,沒有絲毫的苔蘚。臨近公濟橋的地方,有一片相對闊些的坡地,中間是澗水,水邊有落光了葉的柳樹,有枯了葉的芭蕉。邊上,還有一個小木棚。棚是木板與樹皮搭成的,看去有些破敗了,沒有柵欄,木門虛掩著,門內仿佛有關不住的古意。本想沿著荒蕪的小路去木棚探個究竟的,但看到路口有一根干枯的樹枝攔著,便打消了念頭……木棚的主人在山中是種樹、守山,還是狩獵?我是住在文字里的,而曾經住在木棚里的又是誰呢?
石板路伸了下腰,就有一陣陣隆隆的轟鳴聲傳來。到了一拱的梯云橋,百丈沖瀑布便一覽無余。瀑布源于山澗的水流,從山崖交匯的巖口一瀉而下,水流呈扇形散布,急切、洶涌,熱烈而飽滿。奔瀉的水沖入龍潭,似帶著水的呼嘯之聲。扎根于崖縫的免枧(檵木),在飄起的水霧中搖曳,找不到靜止的機會。
冬天能夠有這樣的水量,是得益于這漫山遍野的闊葉林吧。
云梯依山勢而盤旋,一轉一折,向著山的深處蜿蜒。青石板的臺階,臺階邊的石護欄,對于開山辟路的先人來說,是一個歷史性的敘事。據傳,云嶺的路面和石欄桿是上溪村程兆第出資修建的。程兆第的母親經常去齊云山進香,需要途經此地。程兆第看到此處山坡陡峭,路人難行,便下決心修建梯云橋與云嶺。由于修建云嶺的工程量大,上溪村蛟池寺僧人誠一也加入募化出資,才使云嶺得以修復……從溪頭上溪村到安徽交界的塔嶺村,有十里左右青石鋪就的驛道,還有七座石拱橋宛如隱形的路標,路依山勢,橋隨澗跨,把山水與村落景觀鏈接其中。叮叮當當的鑿石聲,早已遠去,山里只有寒冷的風還在漫游。佇立梯云橋時,我想,即便當地人,也無從知曉個中隱姓埋名的出資建設者有多少。
在這樣的山中,我找到了向往的原生地帶。石拱的園口橋,臥波于雙溪合流處,橋的規模大于一路上的石拱橋。據說,過橋隨山路翻山而下,走東流嶺、對鏡嶺,可以到達婺源的龍尾硯(歙硯)產地——硯山村。我曾站在硯山村口想象一位姓葉的獵人,在唐開元時的龍尾山山溪撿到第一塊硯石的情景,如果換成其他人,會對“美人面,嬰兒膚”的龍尾硯石無動于衷嗎?“新安出城二百里,走峰奔巒如斗蚊。陸不通車水不舟,步步穿云到龍尾……其間石有產羅紋,眉子金星相間起。居民山下百余家,鮑戴與王相鄰里。鑿礪磨形如日生,刻骨鏤金磨石髓……不輕不燥稟天然,重實溫潤如君子……不為金玉資天功,時與文章成里美……”遙想江西詩派的鼻祖黃庭堅當年從歙州出發,以一首《硯山行》對龍尾山進行了觀照,四十二行的詩境里,有采石制硯的繁盛,有硯石質地的堅潤,還有硯石紋理的妍麗。隔著八百多年的時空,我無緣與詩祖擦肩,只好與他相向而行,走進了塔嶺的腹地。我之前去硯山村時,比黃庭堅要幸運得多,路不算難走,還走過了村口的復興橋,而他是“陸不通車水不舟”。黃庭堅遠道而來,不是為了寫一首《硯山行》的,而是作為一名官員去督制貢硯……
看到水口高聳繁茂的香樟、楓香、櫧樹、紅豆杉,就意味著要進塔坑村了。塔坑建村于明朝末期,先有江姓遷入,繼有畢姓遷入。村莊倚山而建,錯落有致,中間有一條巖石裸露的水坑。一路走來,我只遇到一位挑著竹篩與火桶去溪頭賣的中年婦女,還有兩個去上小學的學生。
竹與木橫在水坑上,就成了曬場。竹叉竹笐上曬著的臘肉、火腿,飄逸著濃郁的山村人家生活氣息。在我看來,這臘肉、火腿的濃香是對村莊在外打工人員的一種召喚。姓畢的老人說,他們再不回來,家中殺年豬幫襯屠夫抓豬腳的人都沒有了。老畢吐了叼在嘴上的煙蒂,神情茫然,他有一手桶匠的技藝,現在卻沒人請他箍桶了,左鄰右舍和鄰村村民都買塑料桶、塑料盆過日子。
我雖然是第一次到塔坑村,但這樣遠離塵囂的山村似曾相識,卻又無法具體到哪一個村莊。從塔坑往前走,便是通往安徽的羊斗嶺了。頗有意味的是,一塊民國二十三年(1934)九月立的贛皖界碑躺在塔坑一家村民的門口,成了日常的洗衣板。盡管久經時光浸泡,風雨漂洗,但碑石上的字跡依然清晰。
抬頭,我的目光碰到了屋檐下一個空空的燕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