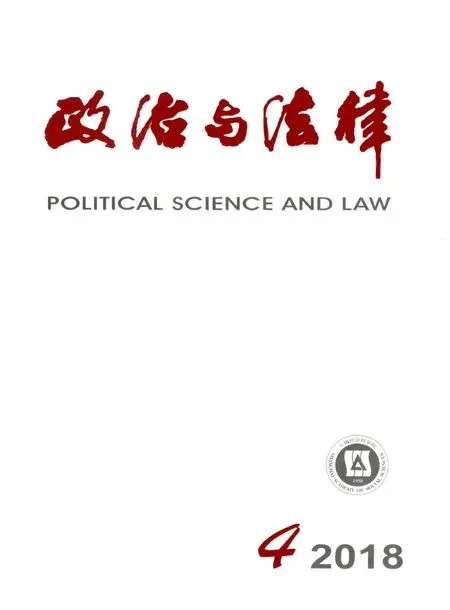論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效適用的三個要素*
——以偵查追訴階段排除非法證據為視角
孫 遠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法學院,北京100088)
一、問題的提出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嚴格適用被學界視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①這方面的代表性文獻有沈德詠:《論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中國法學》2015年第3期;樊崇義:《解讀“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中國司法》2015年第2期;龍宗智:《“以審判為中心”的改革及其限度》,《中外法學》2015年第4期。基于這一認識,2017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聯合出臺了《關于辦理刑事案件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并在業界迅速引發關注。從已發表的大量解讀和評論性文獻來看,普遍關注點集中在《規定》較以往做出了哪些“突破”。比如,《規定》明確要求排除通過暴力、以暴力相威脅和非法拘禁等手段取得的供述,并且對重復性供述的排除這一中國特有問題提供了一定判斷依據。這些也是引發廣泛討論的內容。值得重視的是,當我們評論某一法律文件時,除了應關注它明確規定了哪些問題之外,還應當特別關注哪些是它沒有規定的,因為有時沉默比言說更加發人深省,在這些沉默背后隱藏著更多深層次問題。那么,《規定》究竟對哪些重要問題保持了值得關注的沉默呢?僅就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實體內容來看,②《規定》主要內容可以被區分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實體與程序兩個側面。實體側面內容主要是指在判斷某一證據是否屬于非法證據以及應否排除時,所需依據的標準;程序側面內容主要是指司法機關在適用這些實體性標準進行審查的過程中,所需遵循的一系列提出主張、舉證以及證據調查等程序事項的規則。《規定》的大部分篇幅集中在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適用的程序側面予以規定,而就實體側面來看,未能提供太多足夠明確的判斷標準。它沒有就“毒樹之果”是否應當排除做出正面回應,沒有對實物證據的“補正”與“合理解釋”這兩個概念進一步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闡釋,沒有對可能導致證據排除的“非法拘禁”之具體含義做出界定,也沒有對辯護權、不強迫自證其罪等一系列重大權利之非法證據排除效果予以明確。不難看出,上述缺失意味著《規定》的重心依然還是停留在以刑訊等類似手段違背被告人意志而獲取之口供的排除上。
其實,從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各國和地區的產生和發展的脈絡來看,排除以刑訊手段獲取的口供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算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前身”。以美國為例,自白任意性規則在普通法上早已存在,而且其要求排除之口供的范圍亦遠遠大于以刑訊手段取得者,③See Wayne R.Lafave,Jerold H.Isreal,Nancy J.King&Orin S.Kerr,Criminal Procedure,West,2009,pp.345-349.但當時并無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這一概念。美國學者對該規則歷史的追溯基本上是從1914年的威克斯訴合眾國一案(Week v.United States)開始的,④Tomas J.Gardner&Terry Anderson,Criminal Evidence Principles and Cases,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95,p196.而該案中被法院排除的是非法扣押的文件,與刑訊并無關系。正是在該案之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才得以形成且逐漸豐富,并對其他國家產生重要影響。也正是基于二者不同的發展脈絡,美國教科書一般將自白任意性規則與典型意義上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分開討論。
因此,如果從典型意義上理解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話,鑒于現行法律及司法解釋中存在上述發人深省的闕如,很難說這一規則已經在我國得到確立。那么,本文試圖深入思考的問題便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我國刑事司法多年來一直停留在刑訊逼供的層次討論非法證據排除,而很難再往前邁進一步。對此,學界以往習慣于從理念的角度尋找原因,如認為我國傳統上過于注重實體真實,缺乏人權保障觀念等等。這些當然是有道理的,但并非本文關注的問題。本文試圖尋找法律適用的技術層面原因,在筆者看來,現行刑事訴訟法所確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適用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作繭自縛的方案,在此方案之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不可能得到真正意義上的嚴格適用的。因為在現行法所采用的方案中,欠缺了問題導向、控訴原則、自由裁量這三個對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嚴格適用至關重要的要素。⑤此外,尚有學者從更為具體的層面分析我國法僅僅執著于在刑訊逼供問題上探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原因,如易延友教授將其原因歸結于刑事訴訟法解釋適用過程中的形式化傾向,并主張以實質解釋替代形式解釋。參見易延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立法表述與意義空間——〈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1款的法教義學分析》,《當代法學》2017年第1期。栗崢教授則將原因歸結為我國立法者對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含義的錯誤理解,并主張以立法上的“成套引進”應對之。參見栗崢:《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正本清源》,《政治與法律》2013年第9期。這兩種分別著眼于解釋論和立法論兩個不同層面的看法很有啟發性,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部分真理。然而,筆者認為這兩種觀點均失之片面,應從一個更為廣闊的視野對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方案予以整體審視。這里的適用“方案”既包含立法論層面的問題,亦包含解釋論層面的問題,而且還涉及一系列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適用密切相關的配套制度之因素。筆者的分析將從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一個為人所熟知的“特色”為起點展開。
二、我國非法證據排除模式與西方國家的真正區別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公檢法三機關在各自的訴訟階段,均負有排除非法證據之義務。盡管學界對其合理性存在不同意見,但至少通說認為這是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一大特色,因為西方各國惟有在審判階段方有排除非法證據的問題。⑥參見顧永忠:《我國司法體制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本土化研究》,《政治與法律》2013年第2期。實際上,此種看法并不完全確切,因其混淆了訴訟階段與訴訟職能這兩個概念。
眾所周知,西方各國對于刑事訴訟中的一系列強制處分大多采令狀制度,即由中立的法官對各項強制處分予以事前審查,而控方在申請令狀時,應提供一定證據以證明犯罪嫌疑的存在,并須達到法定證明標準。如果這些證據中有以非法手段取得者,便產生被法官排除之可能,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由此得到適用。從中不難看出,此種排除非法證據的活動,從訴訟職能來看,固然是由承擔審判職能的法院為之,但從訴訟階段來看,則并非發生在審判階段,而是在偵查階段即已展開。因此,西方國家惟審判“階段”方可排除非法證據的看法并不確切,而毋寧是惟有審判“機關”負擔排除非法證據的職責,但該職責之行使和承擔絕不限于審判這一個“階段”。這樣看來,我國《刑事訴訟法》在各個訴訟階段均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做法與西方各國并無重大差別,其真正差別在于規則的適用主體。西方各國無論是審前階段還是審判階段,適用主體均為法院,而我國則由公檢法三機關分別承擔這一職責。對于這一區別亦可做如下概括: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在西方遵循的是一種以審判為中心的模式,而在我國則是通過無差別地賦予公檢法三機關在各自訴訟階段以排除非法證據之義務的模式實現的。
我國之所以采用這種明顯區別于西方各國的模式,其立法本意之一似乎是力求使非法證據排除的適用更為嚴格。然而,若聯系現行刑事訴訟法的相關制度來看,卻未必能達到預期效果。對此,需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展開反思。
第一,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并非在物理上消滅非法證據之存在,其實質在于,當訴訟中準備做出某些決定時,排除非法證據對該決定的影響。在此,非常重要的一點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是以某一具體問題的決定而非某一訴訟階段為依托的。比如,當說在審判階段排除非法證據時,其實我們所要表達的意思是,在給被告人定罪的問題上要排除非法證據。此外,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和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這樣的問題還包括起訴意見、起訴決定以及逮捕決定,國外則還可能包括搜查、扣押等一系列強制處分行為。總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應以具體問題為依托,單純地說在哪個階段排除非法證據是一種無的放矢的含混說法。
然而,刑事訴訟過程中所需做出的決定繁多,顯然不可能期待在所有這些問題上都排除非法證據,而只能選取其中一部分適用該規則。那么究竟應選取哪些問題納入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范圍呢?對此至少應該考慮兩方面因素。首先,鑒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一項成本極大的措施,而被選中者自然應當是那些對案件處理具有重要影響的問題;其次,由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目的在于保障被告人基本權利,那么所選中者自然也應當是與被告基本權利相關的問題。因此,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范圍可以概括為,對被告人基本權利產生重大影響的問題,在對這些問題做決定時,應將非法證據排除于考慮范圍之外。按照這一標準,美國最高法院先后裁定,諸如量刑、大陪審團審查、預審等環節都不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⑦See Wayne R.Lafave,Jerold H.Isreal,Nancy J.King&Orin S.Kerr,Criminal Procedure,West,2009,pp.137-139.但在審判階段的定罪,以及審前一系列強制處分問題上,則均應適用該規則。
第二,在明確了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具體問題之后,另外需要考慮的一個因素是,針對該問題的決定應以何種程序做出。就審判階段而言,我國與西方各國在基本制度架構上差別不大,即由中立的法官在爭議雙方之間以裁判的方式予以適用,但在包括偵查和審查起訴在內的審前階段中,中外差異則顯而易見。
如前所述,西方各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偵查追訴階段的適用,主要是以一系列強制處分的決定為契機,通過法官審查予以實現的,而我國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的非法證據排除,在多數情況下則主要體現為偵查或檢察機關的單方決定。因此可以說,西方各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是以控訴原則為基礎的,而我國則不存在這個基礎。
控訴原則最初是為否定糾問式訴訟下控審合一體制而產生的,其適用對象僅限于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問題,它要求無控訴則無審判,法院不得主動審判未經起訴的案件,即使在法庭上于法官面前發生的犯罪亦無不同。⑧See Michael Bohlander,Principles of German Criminal Procedure,Hart Publishing Ltd,2012,p.24.時至今日,控訴原則之適用范圍早已不限于此,對于那些盡管與定罪量刑這一實體問題并無直接關聯,但事關被告人重大權利的諸多程序問題之決定,亦建立起控訴原則的基本架構。其中最典型者便是強制處分的令狀主義,其實質在于以控訴原則之架構決定某一具體強制處分的啟動,而取代偵查機關單方決定的模式。令狀主義缺失則意味著在強制處分問題上所奉行者實際上仍然是一種糾問主義的體制。其實,對西方各國而言,控訴原則具有比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更為重要的地位,因為某些需依照控訴原則決定的問題,卻未必有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必要。⑨除了強制處分令狀主義之外,屬于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兩大法系的國家和地區的刑事訴訟程序一般在檢察官提起公訴的環節,均設置由司法官對公訴是否符合法定起訴條件予以實質審查的起訴審查程序,這一點所體現的實際上也是在起訴問題上對控訴原則的貫徹。參見孫遠:《刑事訴訟法解釋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52-54頁。
綜上所述,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與西方各國的區別,并不在于審前的偵查追訴階段是否適用該規則,而在于究竟是如何適用該規則的。從西方各國的實踐情況來看,問題導向與控訴原則是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至關重要的兩個因素。其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原理可以概括如下:在以控訴原則決定某些與被告人權利具有重大關聯的問題時,將非法證據置于考慮范圍之外。而我國的情況則存在很大不同,在第一個因素上至少是不夠明確的,第二個因素則更是完全缺失。在本文接下來的部分,筆者將逐一分析我國這些獨特做法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造成了怎樣的影響。
三、范圍:問題導向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適用的問題導向,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其實已有一定程度的體現,但同時也存在很嚴重的問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2款規定:“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其中“起訴意見”應指偵查機關在做出偵查終結結論時所制作的“起訴意見書”,因此,為該款所明確指出的,須排除非法證據的具體問題就包括偵查終結、起訴以及判決。同時,不難看出,這三個決定都算不上那么“具體”,它們只是三大訴訟階段終結之時做出的三個最終結論,這種不甚具體的最終結論是否都足以作為排除非法證據之依托是存在疑問的。因為當我們僅僅試圖以此種最終結論為依托來考察非法證據排除問題時,常常難以判斷某一非法證據是否真正被排除了。這一點在偵查終結環節排除證據時體現得最為明顯。
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賦予偵查機關極為廣泛的權力,主要包括“偵查”一章中規定的各種偵查行為,以及“強制措施”一章中規定的對犯罪嫌疑人之人身自由予以限制或剝奪的各項措施。這些行為與措施在偵查過程中的適用常常并非齊頭并進而是環環相扣的,其中一項措施所獲得的結果,往往成為展開下一項措施的基礎。比如,通過訊問嫌疑人獲得的口供A,可以作為搜查啟動之依據,從而經搜查發現其他證據B,而口供A與證據B又都可以被用來作為據以拘留犯罪嫌疑人的證據。不難理解的是,在前述訊問、搜查、拘留任何一個具體環節的違法都有可能產生非法證據。如果我們以上述各項具體訴訟行為之實施為依托來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話,是相對比較明確的。比如在上述例子中,當以訊問嫌疑人取得的口供A為依據申請“搜查證”以啟動搜查行為的時刻,如果法律要求搜查之啟動不得依據非法證據,那么,當發現該口供為刑訊所取得時,自然就不可能啟動該搜查行為,亦不可能通過搜查取得證據B。然而,當法律未要求在決定啟動搜查的問題上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時,無論口供A是否合法,搜查都是可以啟動的,證據B自然也是可以獲得的。
由于我國刑事訴訟法只明確要求偵查機關在決定偵查終結移送審查起訴的環節排除非法證據,那么在面臨上述情形時,口供A固然可以排除,但證據B,以及在證據B基礎上獲得的其他證據能否被排除就會成為一個引起爭議的問題。如果能夠在諸如搜查、扣押、逮捕等一系列更為具體的強制處分環節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就可以避免上述困境。
不難看出,筆者說的這個問題其實便是西方各國普遍給予極大重視的“毒樹之果”問題。這個問題的困難主要體現在,對于非法取證行為與后續獲得的一系列派生性證據之間的因果關系,法院應掌握何種標準做出認可與否的判斷,并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決定某一派生性證據是否排除。對此,美國先后提出了諸如“獨立來源”“稀釋”“最終必然發現”等規則作為衡量標準,⑩See Stephen C.Thaman,Exclusionary Rules in Comparative Law,Springer,2013,pp15-18.這些標準亦為其他國家和地區在不同程度上予以借鑒。
那么,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在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僅要求于偵查終結環節排除非法證據的情況下,偵查機關將會如何處理這一問題呢?
第一種可能性是,只排除最初非法取證行為所直接獲得的證據,即上述口供A,而對于以之為基礎獲得的證據B等后續一系列派生證據,則采納之。此種做法似乎亦有其法律依據,那就是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并未明確要求排除“毒樹之果”。①對于此種觀點亦存在反對意見。參見易延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立法表述與意義空間》,《當代法學》2017年第1期。如果采取此種做法的話,那么我國現行刑訴事訴訟法所規定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就很難說有太大的價值,每一次以非法證據為依據所采取的后續取證行為都把最初非法行為的“毒素”傳遞到了其他證據當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所欲實現的權利保障目的幾乎不可能達成。②See Stephen C.Thaman,Exclusionary Rules in Comparative Law,Springer,2013,p12.
西方國家在偵查階段每一次強制處分之際,均可憑借令狀主義由法官對警察此前所獲證據之合法性進行審查,其功能仿佛對偵查合法性展開例行“體檢”,一旦發現問題即排除非法證據,并阻斷在此非法證據基礎上進一步取證的活動,及時避免最初非法取證行為之“毒素”對整個偵查程序的進一步“污染”。而在我國刑事訴訟中,每一次強制處分的實施,不僅無法起到對此前偵查行為“體檢”的功能,反而成了將前次違法取證行為進行“洗白”的工具。
其實,當法律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明確適用到每一次強制處分決定做出之際,法律也就不需要特別要求偵查機關在偵查終結之時履行所謂的排除非法證據的義務了。在偵查終結時排除非法證據的做法在西方各國是沒有先例的,在我國卻成為標榜法治的一項法定要求,而從前述分析可以明顯看出,這種要求很難起到實際效果。
第二種可能考慮的做法是,能否要求偵查機關在偵查終結之際排除非法證據時,不僅排除非法取證行為直接取得的證據,即前述例子中的口供A,同時也將以此為基礎取得的“毒樹之果”一并排除呢?這種想法只是在邏輯上可以成立,于實踐中是不可能實現的。姑且不考慮偵查機關因自身訴訟角色所具有的天然局限性,僅從技術層面考慮,此種想法亦對目前人類法律智慧所能達到的最高成就構成重大挑戰。
如前所述,排除“毒樹之果”的標準如何把握是一個異常復雜的問題,即使在美國等西方法治發達國家也只是獲得了一些初步結論,且即使是這些有限的結論也時時處于重大爭議之中。另外還需考慮到,這些西方國家的現行判斷標準所針對的問題比我國當前司法實務中所可能面臨的問題要簡單得多。因為西方國家憑借偵查階段一系列強制處分環節的司法審查,已經最大限度地預先排除了偵查結果中可能存在的“毒素”,換句話說,憑借這種“體檢”式審查,其偵查結果是相對健康的,因此其有限的一些規則尚可應對。我國由于不存在這種機制,等到偵查終結之時再回過頭來試圖厘清各項證據與違法取證行為之間的因果關聯,很可能會發現,最初違法取證行為的“毒素”早已侵入整個案件,此時再憑借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挽救取證行為的合法性,很可能無法做到。
因此,在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要想真正像改革者所希望的那樣得到嚴格執行,并達到預期的立法目的,就必須以更為具體的程序環節為依托,即原則上在每一次作出對被告人的基本權利產生重大影響的決定的時刻,均能做到排除非法證據的影響。否則,在偵查終結時刻,非法證據的影響可能會達到難以收拾的地步。
鑒于前述原因,最高人民檢察院2012年修訂后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以下簡稱:《高檢規則》)第65條、第66條、第67條要求,非法證據不得作為批準和決定逮捕的依據,③《高檢規則》第65條第1款規定:“對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依法排除,不得作為報請逮捕、批準或者決定逮捕、移送審查起訴以及提起公訴的依據。”第66條第2款規定:“對偵查機關的補正或者解釋,人民檢察院應當予以審查。經偵查機關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可以作為批準或者決定逮捕、提起公訴的依據。”第67條規定:“人民檢察院經審查發現存在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非法取證行為,依法對該證據予以排除后,其他證據不能證明犯罪嫌疑人實施犯罪行為的,應當不批準或者決定逮捕,已經移送審查起訴的,可以將案件退回偵查機關補充偵查或者作出不起訴決定。”便具有非常值得關注的意義,《規定》第14條第2款、第3款亦作出了同樣內容的規定。④《規定》第14條該條第2款規定:“偵查機關對審查認定的非法證據,應當予以排除,不得作為提請批準逮捕、移送審查起訴的根據。”該條第3款規定:“對重大案件,人民檢察院駐看守所檢察人員應當在偵查終結前詢問犯罪嫌疑人,核查是否存在刑訊逼供、非法取證情形,并同步錄音錄像。經核查,確有刑訊逼供、非法取證情形的,偵查機關應當及時排除非法證據,不得作為提請批準逮捕、移送審查起訴的根據。”逮捕屬于刑事訴訟中的強制處分,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79條的規定,逮捕條件之一為“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那么《高檢規則》的上述規定便意味著,在檢察院批準或決定逮捕時,若發現用于證明犯罪事實的證據有以非法手段取得者,則應排除之。由此,至少在逮捕環節設置了一道阻斷此前違法取證行為對后續訴訟活動之影響的關卡。
然而,僅有逮捕這一個環節的對非法證據的控制是遠遠不夠的。犯罪嫌疑人被逮捕之前可能已經經歷了訊問、搜查、扣押、人身檢查、技術偵查、拘留等一系列強制處分,可能存在的違法行為與各證據合法性之間的因果關聯很可能早已錯綜復雜,僅憑逮捕這一個環節的審查是不夠的。對于嚴格執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這一要求而言,至少應在一系列強制處分環節均賦予國家機關以排除證據義務,從而及時制止已經出現的非法取證行為對后續取得證據的“污染”。
四、程序:控訴原則
如前所述,控訴原則可以將排除非法證據的職責集中歸于法官之手,同時又可以實現在審前階段與審判階段都能夠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效果。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對于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的一系列強制處分,尚未確立控訴原則,除逮捕之外的強制處分均由各階段主導機關單方面決定。在這種現狀下,就需要進一步分析,這兩種不同的程序設置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造成了怎樣的影響。
對于我國刑事訴訟法采取的模式,首先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是,公檢法三個不同的機關在非法證據排除問題上所作決定的效力。在個案中,針對某一證據是否屬于非法證據,如果是非法證據,其違法性是否已經嚴重到需要排除的程度等問題往往會出現巨大爭議,特別是在我國現行法有關非法證據排除之規定非常抽象化的情況下更是如此。那么,前一個階段所做出的排除或不排除證據的決定,到了后一個階段可否再起爭議,并被后一個機關所否決呢?從法理上看,答案應當是肯定的。非法證據排除屬于法律適用問題,法院對于法律應有最終解釋適用的權力,這就意味著公安機關、檢察院在各自訴訟階段做出的有關證據排除之決定,至少對法院并無拘束力。這不僅意味著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經審查后決定不排除的證據,到了審判階段可以被法院排除,而且甚至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決定排除的證據,理論上,法院在審判階段亦可經審查后重新認可其證據資格。這一點從現行司法解釋的規定亦可推知。《規定》第17條第3款規定:“被排除的非法證據應當隨案移送,并寫明為依法排除的非法證據。”那么,被排除的證據隨案移送至下一個階段之目的為何?恐怕重要目的之一便是為后一階段重新審查提供條件。⑤除 了為后一階段重新審查提供條件之外,可能還有其他目的。比如,非法證據可否在量刑問題上使用以及可否在法庭審判過程中作為彈劾證據使用的問題在我國現行法中尚未有足夠明確的規定,亟需解釋論上的探討。此種做法是必要的,因為我國《刑事訴訟法》第52條課以公檢法三機關全面收集證據的義務,就法院審判而言,只要與案件事實有相關性者,都要收集,然后才是判斷證據是否合法,以及對其展開法庭調查的問題,若法院對于違法性尚無最終確定結論的相關證據一律不予調查,則可能構成對全面收集證據義務的違反。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排除證據的決定與法院在審判階段排除證據的決定,在性質上就完全不同,后者是最終裁斷,而前者則不具有這種性質。吳洪淇博士將檢察院在審查起訴階段排除非法證據的活動稱為“證據把關”,⑥參見吳洪淇:《證據排除抑或證據把關:審查起訴階段非法證據排除的實證研究》,《法制與社會發展》2016年第5期。其實偵查機關所謂“依法排除證據”的行為也是一樣的,可以將其稱之為一種“自我把關”。然而問題是,如果將其稱之為“把關”,那么我國刑事訴訟法在這一點上與西方國家就沒有什么區別了,因為每個國家的警察和檢察官均會對自己準備提交到法庭的證據進行事先“把關”。⑦在 偵查階段由公安機關、在審查起訴階段由檢察機關、在審判階段由法院分別作出排除證據的決定,體現的其實是證據排除規則對控辯雙方當事人的舉證活動所發揮的間接控制作用。即盡管該規則直接規范的是法官的審判活動,但該規則的存在必然也會對當事人的舉證活動發揮間接指引作用。參見孫遠:《刑事證據能力導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頁。一個美國或德國的檢察官如果確信被告人的口供是警察以刑訊方式取得,多半也是不會將其提交到法院去的。西方各國不會把這種控方在審前階段的“證據把關”稱作“證據排除”,并將其與法院在審判過程中排除證據的行為同等看待。
因此,對于中國法與外國法在這一點上的區別可以做出如下概括:一方面,中國法規定了偵查階段的非法證據排除,但這種所謂證據排除其實不過是“證據把關”;另一方面,西方各國的立法盡管基本未對這種偵查階段的“證據把關”做出規定,或許是將其視為一個無需法律規定的問題,但是其偵查階段卻存在另一種意義上的“證據排除”,那就是在令狀主義原則之下,由法官在對控方一系列強制處分進行司法審查過程中所進行的證據審查與排除。此種排除與“把關”之間存在重大區別。為了清楚揭示兩者的差別,在此需要假定一個前提,即我國刑事訴訟法也像西方各國一樣,要求在一系列強制處分環節均排除非法證據。因為如果缺乏這一前提,就無法直接比較兩種模式對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的真正影響。
較容易理解的一點區別是,由于控訴機關與審判機關所承擔的訴訟職能不同,其立場亦不可能相同,由審判機關承擔此項職責更符合客觀中立之要求,⑧參見林喜芬:《論我國審查逮捕階段的非法證據排除問題——基于刑訴法修訂與實踐語境的分析》,《當代法學》2013年第6期。這一點無需多言。與之相比,常常容易被人忽略的另外一個理由在技術層面其實是更重要的,那就是法官在對強制處分進行司法審查過程中做出的是否排除證據之決定,相比偵查機關自身通過“證據把關”做出的類似決定,對后續取得的派生性證據之合法性,可能會產生不同影響。特別是當二者審查決定為不排除相關證據時,其區別更為重要。
仍以前述設例說明這個問題。偵查人員通過訊問獲得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A,然后他憑借口供A申請“搜查證”去搜查犯罪嫌疑人的住宅。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搜查證”由公安局長負責簽發。此時,如果公安局長發現口供A的取得違反法定程序,那么顯然便應依法履行排除該口供的義務,同時又由于再無其他證據支持,則應決定不簽發“搜查證”。如果是這樣的話,則意味著法律得到了正確執行,理論上唯一的疑慮在于公安機關負責人是否能夠忠實履行上述職責。
然而,如果是另外一種情況的話,則可能會出現差異。假設公安局長經審查之后,真誠地認為口供A的取得并未違反法定程序,那么便會簽發“搜查證”。偵查人員搜查過程中又發現并扣押了證據B,此后根據證據B還可能會得到證言C,根據口供A、證據B、證言C等等還可能對被告進行逮捕,并于逮捕之后進一步取得其他證據。那么想象一下,當案件進入審判階段,若法院發現口供A其實是以非法手段取得的,排除口供A固然毋庸置疑,但難以處理的是證據B、證言C以及此后與該口供A之間存在因果關聯的其他證據應否排除。此刻,前述偵查機關在偵查終結環節履行所謂排除證據義務時所面臨的難題,被原封不動地擺到了法院的面前。如果認為應當排除證據B以及此后的一系列派生性證據,那么控方的證據體系可能會瞬間崩潰;反之,如果以派生性證據之取得與口供A之間介入了公安局長以及檢察院的公權力行為,而主張違法性中斷,則又會極大削弱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本應具有的作用。考慮到我國目前偵查活動還存在過于依賴口供,并事實上沿襲“由供到證”的偵查模式,⑨參見李品、黃河:《公安機關“由供到證”偵查模式的制約》,《山西省政法干部管理學院學報》2010年第2期。上述兩個極端之間的抉擇將可能成為實務中時常面對的難題,而且不難預測的是,最終抉擇的結果,很可能是前述第二種方案。
然而,當存在強制處分的令狀主義時,情況便會有很大不同。令狀主義意味著在前述一連串的強制取證行為之間,介入了中立司法者審查的因素,此種介入因素因其性質不同,對后續派生性證據之合法性的影響,可能會與控訴機關的自我審查有所差別。
在“毒樹之果”理論脈絡中,最初的違法取證行為與此后取得的派生性證據之間的因果關聯,可否因某種介入因素的作用而中斷,這個問題被形象地稱為“稀釋”例外。從刑事訴訟的基礎架構,以及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立法目的考慮,司法審查介入所能產生的“稀釋”作用恐怕要遠遠大于偵查機關的自我審查,甚至可以認為后者完全不具備任何的“稀釋”效果。其原因有以下兩點。
第一,現代社會的刑事訴訟是由控辯裁三方訴訟主體參與,訴訟中的一系列重大事項均應在彼此制約的三角結構中予以解決,若少了其中一方的有效參與,訴訟最終決定的合法性便會受到影響。在這個意義上,法官對偵查機關的審查屬于承擔不同訴訟職能的主體之間的審查;相比前者,公安機關負責人簽發“搜查證”的做法則僅僅屬于一種偵查主體內部的審查管理手段,一般情況下,它只能產生內部效力,而不產生外部效力,或者說不產生訴訟法上的效力。因此,在這里,司法審查可以被視為一種重要的“稀釋”因素,而控訴機關的自我審查則難以成為這種因素。與之類似的是,除司法審查之外,被告人的主動行為也被各國普遍視為一種重要的“稀釋”因素,其道理亦在于此。因為被告作為辯方,屬于與控訴機關相對的另外一種獨立訴訟職能承擔者,賦予其主動行為以“稀釋”作用是有正當性的。美國最高法院借以創設“稀釋”例外的王申案(Wong Sun v.United States)正說明了這一點。在該案中,盡管警察早先對被告人的逮捕是非法的,但被告在被釋放之后又主動來到警察局做出供述,美國最高法院就此認為,前次非法逮捕行為的“毒素”因被告的主動行為而得以“稀釋”,該供述具有可采性。⑩Wong Sun v.United States 371U.S.471(1963).
第二,從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目的來看,威懾警察可能采取的違法取證行為無疑是其重要目的之一。①SeeWilliam T.Pizzi,TrialsWithout Truth,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9,p33.這同時也意味著,非法證據排除并非意在威懾法官,由于法官的錯誤卻導致控方由此獲得的證據被排除,對于控方而言也未必公平。美國最高法院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創設的“善意”例外,在很大程度上便是依據此一法理而做出的。②United States v.Leon 468U.S.897(1984).
當然,承認司法審查的稀釋作用,并非意味著一旦有司法審查因素介入,便必然產生違法性中斷,從而賦予派生性證據以證據資格。比如,當法官明知警察提交的口供是刑訊逼供取得,卻仍以該口供為依據簽發“搜查證”,無論如何不可能對搜查取得證據的違法性產生稀釋作用。司法審查本身有資格成為對證據違法性產生稀釋作用的諸多因素之一,控方自身的審查則很難具有這一資格,至于司法審查的這種稀釋作用究竟有多大,則要根據個案的具體情況而定。③參見[美]約翰·W·斯特龍:《麥考密克論證據》,湯維建等譯,中國政法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47頁。這個問題的解決即使在國外亦無絕對明確的規則,而不得不更多地通過個案裁量的方式解決。④當審判法官對某一偵查過程中法官令狀簽發之合法性以及由此取得證據之證據資格進行審查時,非常類似于上訴法官對初審程序合法性進行的事后審查。在各國上訴審程序中,原審的程序違法可能會導致判決被撤銷的結果。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27條亦有相關規定,如根據該條第3項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審理過程中“剝奪或者限制了當事人的法定訴訟權利,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由此可知,并非原審法院所有剝奪或限制當事人法定訴訟權利的情形,均必然導致撤銷原判的結果,只有這些情形達到“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程度時,才會有此效果。那么究竟哪些程序錯誤會達到此一程度,便需根據個案情況予以裁量。在訴訟法學理論上,那些不“影響公正審判”的程序錯誤,被稱為“無害錯誤”,對于無害錯誤在事后審查中無需提供程序性救濟。其原因在于法律只能為當事人提供“公正”的審判,而非“完美”的審判。同樣的道理,當審判法官在判斷偵查所獲證據之合法性時,對于司法審查作為一種介入因素之稀釋效果的衡量,亦須根據個案具體情況展開。
五、方法:自由裁量
以上論證表明,我國刑事訴訟法采用的三機關均承擔排除非法證據義務的做法,看似能夠實現更嚴格地排除非法證據的意圖,但由于審前的偵查和追訴階段缺乏具體問題之依托以及強制處分的司法審查,恐怕不僅很難實現當初的立法目的,反倒會極大限制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筆者以為,法律之所以采用如此方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僅就適用層面而言,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立法者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方法缺乏足夠清醒的認識。
立法者似乎認為,證據是否合法以及應否排除是一個非黑即白的問題,且可以很輕易地作出判斷,既然這樣,那么對于那些應當排除的非法證據,與其等到法官介入之后再排除,還不如在偵查階段就將其排除掉。然而,此種看法過于簡單化了,它將排除一個非法的證據與否定一個不真實的證據這兩種活動等同視之。其實,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常常需要依賴極為復雜的裁量活動,而此種活動恰恰不適宜由承擔控訴職能的機關在審前的偵查追訴階段展開。
(一)裁量作為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主要方法
一種代表性觀點認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模式有兩種,一為強制排除,一為裁量排除,⑤參見戴長林、羅國良、劉靜坤:《中國非法證據排除制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75-76頁。這種區分在某種意義上有一定價值,但是關于此種二分法的真正含義卻多有誤解。所謂強制排除模式與裁量排除模式的區別主要應體現在不同種類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方法上。比如,對于以刑訊逼供方式獲取的口供應當一律排除,這是一種強制排除的模式,幾乎未見任何一個法治國家認可刑訊逼供取得口供之證據資格者,其原因就在于,刑訊逼供的取證方式在法治國原則下,根本沒有正當化的可能性。然而,對于非法搜查、監聽等方式取得的證據以及以非法取證行為獲取的派生性證據是否應當排除,則更多地需要在個案基礎上予以裁量決定。因此,強制與裁量這兩種模式是針對不同的非法取證情形而言的。然而,有大量文獻在另外一種不同的意義上使用這種二分法,即認為它是對一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整體“立法模式”的描述。比如有學者在對美、英兩國的相關制度做出比較之后認為,美國采取的是強制排除模式,而英國采用的是裁量排除模式。⑥參見史立梅、胡長龍:《論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兩種立法模式》,《法學論壇》2001年第3期。亦有學者斷言,美國屬于強制排除模式的代表,而英國、澳大利亞、德國、日本等國都實行裁量排除模式。⑦參見前注⑤,戴長林、羅國良、劉靜坤書,第76頁。此類觀點其實是一種誤解。從整體上衡量一國全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不可能在強制與裁量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評判的。即使被學界視為強制排除模式之典型代表的美國,其法官在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過程中亦時時離不開個案裁量。
其實,強制排除與裁量排除被作為兩個相對的概念本身就是不夠嚴謹的。證據法學者使用這一對概念原本是想描述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過程中的這樣一種現象:某些非法證據的排除問題被法律以相對明確的規則予以表述,從而使法官在此種情況下,可以直接依據該規則做出是否排除證據的決定,它針對的是在長期司法實踐中已經形成定論的一些有限情形。在司法實踐中還會常常遇到另外一種情況,法官面對某一非法證據排除存在爭議時,在法律條文中找不到可以直接適用的規則依據,此時,法官當然不得以法無明文規定為由對該爭議問題拒絕裁判,⑧參見[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學》,丁小春、吳越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58-359頁。于是便須依據從一系列具有相關性的法律原則、標準以及立法目的中尋找決定的依據。上述前一種情形便是我國證據法學者所稱的強制排除,后一種則屬于裁量排除。
如果是這樣的話,把強制作為裁量的相對概念顯然就不是很適當了。這兩種情形之間其實存在一個重要的共同點,即二者均屬于“依法排除”,只不過,強制排除所依據的是法律中確定性較強的規則,而裁量排除所依據的則是確定性相對較弱的原則、標準或立法目的。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在裁量排除的情形,一旦法官從這些原則、標準和目的中得出確定的結論認為該非法證據已經達到應予排除之程度時,則必須排除之。在這個意義上,排除該非法證據的義務對于法官來說也是“強制性”的,否則即構成法律適用錯誤。站在上訴法官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原審法官的裁判違背了某一具體規則化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定(即強制排除規定),還是違背了法律的某項原則、標準或目的(即裁量排除規則),都可能產生因程序違法撤銷判決的結果。
在這個意義上,上述兩種情形均屬于強制排除,只不過前者強制排除的標準可以從法律規則中直接獲得,而后者的標準則須綜合運用各種法律解釋方法后方可獲得。后一種情形下,裁判標準的獲得過程,被我國學者稱為裁量。其實,在法學上,與強制性規范相對的概念應為任意性規范,非裁量。任意性規范所針對的情形與上述意義上的裁量顯然是不同的,因為法官裁量結果若違背法律目的則屬違法,其裁決結果會被上訴法院撤銷,而對于任意性規范,行為人則可以排除其適用,而不存在違法的問題。⑨參見許中緣:《論任意性規范——一種比較法的視角》,《政治與法律》2008年第11期。因此,我國學者所歸納的強制排除與裁量排除之間的區別,其實僅僅在于其排除非法證據之法律依據是否足夠明確。前者依據的是法律明文規定的規則,而后者則不得不更多地依賴明確性相對較弱的原則、標準或立法目的。因此,筆者認為將上述二種情形稱之為“法定排除模式”與“裁量排除模式”是更妥當的。⑩參見孫遠:《刑事證據能力的法定與裁量》,《中國法學》2005年第5期。亦有學者將二者概括為“規則調整模式”與“自由裁量模式”,①參見吳宏耀、魏曉娜:《訴訟證明原理》,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頁。其所表達的含義亦大體相同。
在法學上,“法定”一詞是指法律的“明文規定”,如罪刑法定原則被界定為“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②參見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44頁。“法定”意味著禁止類推。非法證據排除作為一種程序法規則,在解釋適用過程中恰恰是允許類推的。③See Dr.Volker Krey,German Criminal Procedure Law,W.Kohlhammer Publishing Company,2009,p.3.部分學者對于所謂“強制排除”或“法定排除”模式的向往,建立在該模式更有助于嚴格貫徹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維護被告人權利的錯誤想法之上。其實,如果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上真有這樣一種嚴格禁止類推的“法定排除模式”的話,對被告來講未必是有利的。因為現實中偵查機關可能出現的違法取證行為有無限的多種可能性,根本無法預先在法律條文中做出窮盡式規定,此時若不允許類推適用證據排除規則,將對被告權利造成實質損害。④國內很多學者對法定模式的偏好實際上是建立在中國法官在排除非法證據問題上極為保守的現狀基礎上的。例如,所謂美國的“強制排除”模式經常被學界歸納為“規則加例外”的模式,但無論其“規則”還是“例外”的適用,常常均不得不借助于法官的裁量活動才能實現。以本文所關注的“毒樹之果”規則及其“稀釋”例外為例,其含義實際上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清晰。特別是究竟何種情形會產生“稀釋”效果,至今尚未形成完全明確的規則,而不得不綜合考量特定案件中的各種要素,如該非法行為與受到質疑的證據被發現之間在時間上的聯系,“介入情況”的數量和性質,公務不當行為的目的和惡意程度,等等。⑤參見前注③,約翰·W·斯特龍書,第347頁。
其實,與司法實務中可能出現的種種疑難情況相比,美國證據法教科書中列出的那些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及其例外所能直接涵蓋的問題,終究不過是冰山一角,大量爭議不得不根據個案情況,在查明真相與權利保障目的之間展開權衡,才能確定某一證據的排除與否。即使是這些已經形成的規則,也是在多年裁判實踐中逐步積累而成的。⑥筆者曾言及,對于證據資格的規范來說,即使真的存在“法定”這種模式的話,裁量也是走向法定的必然之路。參見前注⑩,孫遠文。美國之所以帶給很多人以所謂“強制排除模式”或“法定排除模式”的印象,只不過是因為其排除非法證據的實踐開始較早,相比一些法治后進國家來說,積累更為豐富而已。迄今為止,其緩慢積累而成的這些成果,其主要功能也不過是為法官在對證據排除問題行使裁量權時,提供一些基本的分析框架,從而盡可能確保司法的確定性,遠遠沒有達到一種“立法模式”的程度。
此外,即使在現代立法技術所能達到的最嚴格意義上使用“法定”一詞,其與“裁量”之間也只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別。因為無論多么明確的語詞,也有其核心部分和邊緣區域的區分,⑦參見[英]H.L.A.哈特:《法律的概念》,許家馨、李冠宜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頁。即使是公認“法定”程度最高的排除刑訊逼供所獲口供的規則來看,亦是如此。警察審訊中的行為究竟是否構成“刑訊逼供”,有時是明確的,有時則不是那么明確。近期出臺的一系列司法解釋花費極大的努力以“肉刑”“變相肉刑”“非法拘禁”,甚至“凍餓烤曬”等詞語去界定何謂“刑訊逼供”,然而試圖以明確條文的形式界定實踐中可能出現的所有“刑訊逼供”行為,此種活動是永無止境的。司法解釋做出的上述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為了回應司法實務中長期存在的一種需求,即希望能夠以明確條文的形式,將需要排除證據的情形予以詳盡列舉。此種需求的合理性是很可疑的,從立法者角度看,它體現的是一種對法官的不信任態度;⑧從 立法論角度來看,此種做法非常類似于法定證據制度之下,以法條明文形式規定證據證明力,以排除法官自由判斷的做法。See John H.Langbein:Torture and the Law of Proof,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p6-7.從法官角度看,該需求體現的則是一種逃避責任的企圖。然而,對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發展完善這一目標而言,離開在個案中勇于擔負起自由裁量職責的法官群體,便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⑨參見何家弘:《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需要司法判例》,《法學家》2013年第2期。
特別是在我國刑事司法現狀之下,法官裁量權的使用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最近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國刑事訴訟法所確立的非法實物證據的排除規則應當被解釋為強制排除模式。⑩參見前注①,易延友文。此種觀點的提出有一個非常好的初衷,即試圖使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得到更加嚴格的適用。然而,這怎么可能呢?現行我國刑事訴訟法無論是在取證規范還是在排除規范上,均處于立法密度嚴重不足的狀態,缺少了裁量因素,所謂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幾乎寸步難行,更何談嚴格適用。這里所謂的裁量就包括取證規范和排除規范兩個方面的裁量。
一方面,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以一系列與取證行為有關的規則存在為前提的,可以說有多少這種取證規則,就有多少條潛在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①參見前注③,約翰·W·斯特龍書,第315頁。因此各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適用,均有一大部分處理重心落在取證行為合法與否的判斷上,且此一判斷過程中,法律解釋是不可避免的。②參見林鈺雄:《最高法院刑事裁判評釋》,元照出版公司(臺北)2013年版,第256-257頁。而我國《刑事訴訟法》針對偵查機關取證行為的規定僅限于偵查一章中列出的有限且抽象的條款,對于實務中可能出現的取證行為之合法性爭議,這些條款常常難以給出足夠明確的判斷標準,需要法官憑借其自由裁量權對法律進行進一步的解釋、續造甚至漏洞填補。正是由于我國法官歷來怠于行使此種權力,使得實踐中大量的實質性程序違法被無視了,由此也從根源上消滅了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得以發展完善的契機,至今依然深陷在刑訊逼供的狹小空間里走不出來。
另一方面,證據合法與否與證據是否排除本身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其考量標準也不可能相同。③參見林鈺雄:《刑事訴訟法(上冊)》,元照出版有限公司(臺北)2013年版,第605頁。德國將二者分別放在證據取得禁止與證據使用禁止兩個問題項下進行討論。所謂非法證據是指以違法手段取得的證據,但鑒于查明案件真相與維護正當程序同為刑事訴訟的目的,不能得出所有非法證據均應排除的結論,某一非法證據是否排除還應綜合考量各種因素才能決定。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54條的規定,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本條中所稱“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補正”“合理解釋”等均屬法官決定排除某一非法實物證據時的裁量因素。④一種代表性觀點認為,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54條規定可以認為,我國刑事訴訟中除非法證據與合法證據之外還存在一種處于合法與非法之間的所謂“瑕疵證據”,即那些取得過程違反了法定程序,但可以進行補正或合理解釋的證據。此觀點是概念混淆的,即將“非法證據”與“應排除的證據”混為一談。然而,時至今日,由于法官裁量權未能有效行使,司法實務幾乎未對上述概念的具體化做出任何有價值的貢獻,以致于《規定》在細化、解釋非法實物證據之排除問題時,幾乎是完全照抄了我國《刑事訴訟法》這一極為抽象的表述。
總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除刑訊逼供等極少數情形下,可以通過較為明確的規則形式予以強制排除(即法定排除)之外,其他均難以離開法官個案裁量的因素,這也意味著明確的法律條文所能起到的作用是相當有限的。目前官方出臺的有關非法證據排除的規范性文件其實已經很多了,而其實施效果非常有效,這也在很大程度上證明了筆者的這一觀點。
(二)控訴機關不適宜行使非法證據排除之裁量權的原因
如前所述,除少數如刑訊逼供等極為惡劣的非法取證行為之外,絕大多數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均需要借助于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方可得出結論,此種裁量決定所需考慮的因素可能涉及全案的各個環節。承擔控訴職能的機關,特別是偵查機關并非開展如此復雜之裁量活動的適當主體。其原因如下。
第一,偵查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職責決定其不適宜承擔此項任務。與直接適用明確的規則相比,裁量是一種更為復雜的決定方式,需要耗費的成本更大。偵查機關的主要職責在于迅速及時地收集證據,若課以其排除非法證據的裁量義務,將會極大地影響偵查效率。仿佛在足球比賽中,裁判員鳴哨示意之前,球員沒有義務反思其前一個動作是否有犯規之虞,否則將極大影響球賽的精彩程度。
第二,偵查人員的專業背景決定其不適宜承擔此項任務。裁量是法律適用活動中更為復雜的一部分,需要更為專業的法律解釋技術,理應由法律專家作出裁斷,而偵查人員的專長顯然并不在此。
第三,偵查機關在偵查過程中占有信息的有限性,使得其難以承擔此項任務。如前所述,證據非法與證據排除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對于某一取證行為是否違法,相對而言可以在該行為發生之時做出判斷,一旦認定該行為違法,自然會導致由此獲得的證據成為非法證據。然而,并非所有非法證據均在排除之列,只有當使用該非法證據將導致嚴重影響司法公正之結果時,排除該證據才是適當的。因此,很多情況下,某一非法取得的證據是否應當排除,在該違法取證行為發生之時是很難做出判斷的。證據排除問題應當放在全案背景下予以考慮,這就意味著,很可能在某一非法證據取得之后,某些可能影響到該證據排除與否的因素尚未出現。比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于1984年的Nix v.Williams一案中為“毒樹之果”規則確立了“最終必然發現”之例外。該案要旨在于,盡管某一證據事實上是從警察的違法取證行為派生而來,因此屬于“毒樹之果”,但是如果警察能夠證明即使不存在違法取證行為,該證據最終也必然會被發現,那么該證據便是可采納的。⑤Nix v.Williams467U.S.431(1984).不難看出,這一例外規則所須考量的因素在警察取得證據之時是無法獲知的。
然而,偵查機關不適宜作為證據排除的主體,并不意味著偵查階段不能作為一個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階段。如前所述,若能確立偵查階段各項強制處分的令狀主義,則可以實現在偵查階段有效實現排除非法證據的目的。⑥需要說明的一點是,無論是在審前階段還是審判階段,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有效適用都離不開裁量,但其裁量標準或有不同。筆者在前文的論述已經表明,審前階段的非法證據排除主要應指在審前決定采取一系列強制處分的環節對該規則的適用。審判階段的適用則主要是在定罪問題上的適用。由于這兩種情形下所欲作出之決定對被告人實際利益影響程度不同,以及不同階段面臨的現實狀況存在差異,兩者在對是否排除某一非法證據問題時所用的裁量標準亦必然存在差別。由于偵查階段必須考慮偵查之有效性,而且偵查階段對某一強制措施的司法審查往往在極為有限的時間內為之,法官往往不可能對證據合法性之審查采取太過嚴格的標準。在審判階段,由于偵查已經終結,不存在偵查效率方面的考量,同時法官在時間和資訊等方面亦有條件對證據合法性做較嚴格之審查。這往往意味著審判階段對證據資格會貫徹更為嚴格的審查標準,某一在偵查階段被法官認可的證據,到了審判階段也許會被排除。當出現這種情況的時候,在實質意義上可以說,偵查階段認可其證據資格的決定是錯誤的。鑒于前文論述的理由,由于西方各國偵查階段排除證據的決定是由法官作出的,從而不會影響此后所取得一系列證據的合法性,但在我國缺乏強制措施司法審查的情況下,則很難具有此種中斷違法性的程序效力。否則,若維持現行法這種偵查機關自行排除非法證據的機制,就會產生如下三方面后果。第一,充其量僅能期待偵查機關排除如刑訊逼供所得口供等少數極為典型的非法證據,多數證據排除規則難以得到充分適用。第二,由于令狀主義的缺失,即使刑訊取得的口供可以在形式意義上排除,但實質并未排除,其所含“毒素”會一步步污染后續取得的各種派生性證據。同時,恰恰基于刑訊逼供所產生的這種實質影響,必將使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于遏制刑訊逼供所能起到的作用大打折扣。第三,此種格局還會對審判階段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嚴格適用產生間接但深遠的影響。即當這樣一個盡管在形式上排除了刑訊供述,但實質上依然深受其影響的案件進入審判階段時,法院面對取證行為與證據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即使欲排除非法證據,特別是一系列派生性的“毒樹之果”,亦無從入手。這樣一來,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便越來越被局限在排除刑訊逼供這一極為狹小的空間里無限輪回。
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規定》第14條在一種非常含混的意義上賦予檢察機關在偵查階段排除非法證據的權力。該條第1款規定:“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可以向人民檢察院申請排除非法證據。對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的,人民檢察院應當調查核實。調查結論應當書面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對確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向偵查機關提出糾正意見。”這一規定的初衷可能是考慮到法律要求偵查機關自行排除非法證據不太現實,特增加檢察院的此項權力。筆者認為,這種規定意義不大。姑且不論檢察機關的糾正意見在法律效力上模糊不清,該條在前述所強調指出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之問題導向上,沒有做出任何新規定,前述偵查機關自行排除證據所導致的違法性擴散的問題,在檢察機關享有此項權力的情況下,亦未有絲毫改變。因此,不難預見,此一規定對于偵查階段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很難有實質性作用。與其如此,倒不如明確賦予檢察機關對偵查階段所有強制處分行為的審查決定權,并以此作為其在偵查階段排除證據的程序空間。盡管此種做法與學界多數意見長期呼吁的司法審查機制還相距甚遠,不過,相對于當前制度而言,至少是向前邁進了一步。
六、結 論
本文論述表明,問題導向、控訴原則、裁量方法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原理中三個不容忽視的要素。當此三要素齊備之時,便可以說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問題上,形成了一種以審判為中心的格局。只不過這里的以審判為中心并非僅限于審判“階段”的中心地位,而是指審判“機關”在各訴訟階段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問題上,均應居于中心地位。在近年來有關刑事司法改革的討論中,多數論者傾向于將嚴格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作為推進審判中心主義改革的重要手段。⑦參見前注①,沈德詠文。然而,現在看來,此種觀點將因果關系顛倒了。二者之間的真正關系毋寧是,只有在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格局之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才真正能夠得到嚴格適用。而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所奉行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適用模式,其實還是在沿襲長期以來的“流水作業式”構造。此種模式最大限度地將本應承擔不同訴訟職能的公檢法三機關予以“同質化”,令其不加區別地參與到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活動中來,頗有幾分“運動式執法”的色彩,看似聲勢浩大,實際上已經將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發展引入一種“僅欲排除刑訊口供而不可得”的惡性循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