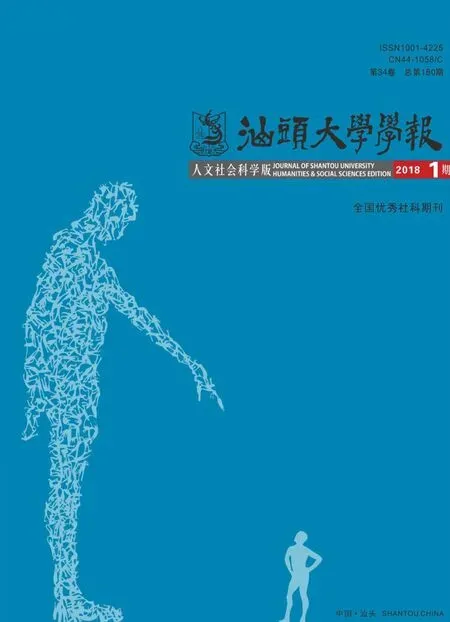試論傳統醫療父愛主義的現代價值
倪晶晶
(汕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廣東 汕頭 515063)
近年來,國內“醫鬧”事件屢禁不止,暴力傷醫事件層出不窮,醫患矛盾愈演愈烈,即使社會一直呼吁建立互信的醫患關系,但不和諧現象依舊大行其道。2016年11月27日,在北京召開的“第二屆中國醫療法治論壇”上,中國醫院協會副秘書長王玲玲教授介紹,2016年全國暴力傷醫案呈上升趨勢,全國發生典型暴力傷醫案例42起,共導致60余名醫務人員受傷或死亡。因而,建立新型和諧的醫患關系刻不容緩。本文立足于傳統醫療父愛主義,分析傳統醫療父愛主義的當代價值,并在此基礎上呼吁給予醫生適度干預權①醫生適度干預權是指:醫生在特定情況下,限制病人的自主權利,實現自己意志以達到對病人應盡責任的目地。,實現傳統醫療父愛關懷的現代回歸。
一、傳統醫療父愛主義和近代醫療自由主義
(一)傳統醫療父愛主義
“父愛主義(paternalism)”又稱家長主義,來自拉丁語pater,意指“家長式的管理原則和做法。像一位父親一樣來統治政府;像一位父親對待其子女一樣為一個民族或共同體提供需要或支配生命的要求或嘗試。”[1]簡言之,就是為了他人益處而干預他人的行為。父愛主義在現實生活中運用廣泛,如法律父愛主義、教育父愛主義。而醫療父愛主義,是指運用在醫療這個特殊領域中的父愛主義,通常表現為——在醫療實踐過程中,醫生憑借專業知識,為患者的最大利益作出最優選擇,甚至在患者及其家屬無法作出正確判斷時,幫助患者做出選擇,并強行要求患者接受。
傳統醫療父愛主義在中國流傳千年,成為傳統醫學的主導思想。究其原因,與它兩個明顯的特征有關。首先,傳統醫療父愛主義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強調“仁者愛人”。“仁”的粗淺解釋是指一種感通、關切、融合的精神狀態。“仁者,愛人”,因此對個體之外發生的痛楚感同身受,好像自己也受到了創傷,十分關切他人傷痛,甚至與他人情感相互融合,這便是“仁”。“醫乃仁術”,因此醫生施行仁術時,要保持一種“醫者父母心”的人文關懷,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去關愛患者,將患者之痛當成自身之痛,把“治病救人”當作自己的天職,樹立“人命之重貴于千金”的基本理念。同時,醫學仁術還表現在醫生治病的態度上,要求醫生以溫和、同情、關愛的態度撫慰患者身心傷痛,對患者充滿關愛和耐心,并且不論身份貴賤,“一視同仁”,對患者做到誠信不欺,按病下藥。這種博愛濟眾的仁愛思想,是傳統醫學的普遍思想,良醫無不如此。
此外,傳統醫療父愛主義還有一個明顯特征——父權至上。在傳統的醫療實踐中,醫生扮演著父親的角色,醫生以仁愛之心像對待自己孩子一樣對待患者,這也就意味著醫生具有家長式的權威。例如,在某些緊急情況下,患者及家屬經受身體傷痛、心理緊張和醫療專業知識欠缺方面的桎梏,無法作出清醒判斷。此時,醫生就會扮演決策者的角色,根據自身經驗及專業知識,為患者健康作出最優選擇,強行進行救治,即使這些選擇有違患者意愿。
傳統醫療父愛主義的上述兩個特征,來源于中國傳統儒家思想的仁愛主義及家國一體的倫理本位模式。以仁愛和父權為核心的醫療父愛主義歷經千年而不衰,成為中國傳統醫學倫理的主導原則。但也因其極度推崇父權至上,即以醫生單方決定為主,不顧患者意愿,使其具有明顯的強制性特征。因而,隨著近代患者人權運動,強調醫患平等、醫療自由等理念的發展,傳統醫療父愛主義逐漸式微,并最終被以尊重患者知情同意為核心的醫療自由主義所取代。[2]
(二)以知情同意為核心的醫療自由主義
醫療自由主義以“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作為核心,字面意思就是基于說明的同意。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醫療行業迅速發展,醫療行業中出現了諸多不端現象,如醫療機構及醫療人員過分追求利益收受紅包、醫生態度冷漠等,使整個醫療行業陷入信任危機。因此,人們開始呼吁病人人權,要求“視患者為人”的權利運動蓬勃發展。此時,患者不再像過去一樣,將自己的生命毫無保留地托付給醫生,而是試圖實現與醫生的平等。特別在手術前,要求醫生告知實際病情及治療手段,從而自行決定是否進行手術,患者知情同意的觀念悄然興起。而作為法律概念上的“知情同意”權,是在二戰后紐倫堡審判(1946)中出現的,為了嚴厲譴責納粹醫生在集中營強迫受害者進行人體試驗的行為,作為對納粹分子輕視、踐踏人權的反思在世界范圍內為人們所認可。我國出于對患者的保護,順理成章地引入知情同意權,并使其成為我國臨床醫療實踐中的顯性原則。
(三)醫療自由主義在現代社會遭遇的挑戰
出于對患者生命尊重的知情同意權被引入我國,本該是歷史的進步,但卻在醫療實踐中,不斷遇到各種問題和質疑。可以說,以尊重患者知情同意為核心的醫療原則,并未能為我國醫療領域頻發的道德問題提供有效指導。不論是曾經轟動一時的孕婦李麗云事件,還是引發公眾熱議的周發芝事件,都與過分強調患者的知情同意權密切相關。縱觀近年頻發的醫鬧事件,其實就是片面強調患者知情同意權的折射。
片面強調患者的知情同意權,在現實生活中遇到諸多瓶頸和質疑,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醫療行業本身是一個專業性極強的領域,醫生群體在對病理成因、病情程度、治療手段的選擇等方面,具有先天不容置疑的專業優勢。由于患者受專業知識的桎梏,即使醫生告知相關病理和治療方案,也可能存在患者及家屬不能完全接受的情況。此時,醫學專業知識的不對稱,就成了患者知情同意權利的天然屏障。其次,在某些特定情況下,醫生為避免醫療非技術因素可能對病人身體和心理造成傷害,影響病人康復,會采取父愛式醫療手段以保護病人利益,如善意欺騙、使用模糊用語等方式。這種出于對患者生命健康的善意保密做法,也在叩問著片面強調患者知情同意權的合理性。再次,我國關于患者知情同意權的法律本身并不健全,如知情同意制度不充分、法律條文太籠統不具操作性、法律規范相互抵觸、知情同意權適用例外規定不完善等[3]。2010年出臺的《病歷書寫基本規范》第10條規定:“對需取得患者書面同意方可進行的醫療活動,應當由患者本人簽署知情同意書。患者不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時,應當由其法定代理人簽字;患者因病無法簽字時,應當由其授權的人員簽字;為搶救患者,在法定代理人或被授權人無法及時簽字的情況下,可由醫療機構負責人或者授權的負責人簽字。”該規定旨在保護患者的生命權利,解決醫生在緊急狀態下進行手術治療的后顧之憂,但充其量只是以部門規章形式出現,因此法律效力極為有限;最后,將患者的知情同意拔高到至高地位,嚴重限制了醫生進行正常的醫療救治活動。例如,在某些緊急情況下,醫生不約而同地將患者的知情同意權理解為手術簽字制度,直接表現為“不簽字,不手術”現象,因而可能嚴重耽誤最佳救治時機。若患者或其家屬不簽字,醫生出于對救治風險的擔憂和恐懼,很可能釀成從見死難救到見死不救的悲劇,此時,患者的知情同意權就異化成了醫生免責的護身符。
因此,將醫療決策權力完全交給患者,絕不是一個簡單的醫療模式的選擇問題,它涉及醫學倫理的基本價值標準:是選擇以醫生仁愛為核心的父愛主義,還是倡導患者自主權利的自由主義,抑或調和患者知情同意權和醫生干預權各自裨益后的綜合。從古今醫患關系的明顯變化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傳統醫患關系總體而言是和諧的,而現代醫患關系總體而言是對立的。傳統醫患關系中,醫生以父愛之心懸壺濟世,本著患者利益最大化原則,主導醫療活動,施行“仁術”;而對患者而言,醫生像父親一樣,是值得信任和托付生命的。因此,傳統醫療父愛主義模式在今天仍具意義,我們有必要重新挖掘傳統醫療父愛主義的當代價值,為化解當前醫療行業的實踐困境提供有效指導。
二、醫療父愛主義的當代價值
傳統的醫療父愛主義的當代價值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傳統醫療父愛主義以仁愛為核心,堅持以人為本。傳統醫學父愛主義就本質而言,是一種利他的愛。因此,其當代價值必須保留這一維度,當代醫生也需以人為本,尊重患者,以有利患者的原則主導醫療活動。另一方面,在傳統醫療父愛主義中,醫生扮演決策者的角色,擁有完全自主權。因此,其當代價值的另一維度,就是要給予醫生適當醫療干預權。并且,醫生適當干預權需以父愛主義為德性前提,醫生需本著患者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實施“仁術”。
(一)以人為本,尊重患者
中國傳統醫學父愛主義以仁愛為基。仁愛的目的是為了病人利益,方式上要求一視同仁,而態度則要求溫和親切。
以人為本,體現在醫生的利他醫德中。表現為醫生會把“患者福祉優先”當成行醫的基本信條,將治病救人看做自己應盡的義務和美德,將患者健康的最大化視作一切行為的出發點。中國古代良醫提出的“易地以觀”的觀點,其實就是利他醫德的表現,因為關心患者,所以站在患者的角度看問題。如清代名醫徐延柞在《醫粹精言》中說“欲救人而學醫則可,欲謀利則不可。我若有疾,望醫之救我者何如?我之父母妻子有疾,望醫之相救者何如?易地以觀則利心自澹矣……故醫雖小道,而所系甚重,略一舉手,人之生死因之,可不敬懼乎哉”。[4]正是這種對生命的敬畏,讓醫生站在病人角度關懷病人,使得病人完全相信醫生,甚至毫無保留地將生命托付給醫生。
與利他醫德相對立的,是充斥在今天醫患關系中的利己主義,表現在醫患之間互不信任。醫生對患者而言是功利的,因此,患者試圖通過送紅包的方式賄賂醫生,以求醫生盡力,即使有德性的醫生表示會竭盡全力,如不收紅包,患者依舊難以心安。而患者對醫生而言,僅是醫療對象,是自己職業收入的來源。但這種觀念上的變化,與改革開放后,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良影響相關。市場經濟滋生出的拜金主義,對醫療行業逐步侵蝕,造成部分醫生忘記自己的神圣使命,使本該施行“仁術”的職業淪為商業的附庸。在以藥養醫的體制缺陷的掩護下,部分醫生昧著良心,以收取患者額外錢財為目的,使患者處境雪上加霜,加劇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局面。此時,父愛主義的利他醫德被精致的利己主義完全取代;一視同仁的為醫之道被亂收患者紅包的現象蠶食不見;溫和親切的人文關懷被急功近利的服務態度沖刷殆盡。久而久之,造成醫生失去本該有的“醫者父母心”的關懷。傳統的醫療父愛主義為當代醫療工作者提供了一種價值視角,教育醫者敬畏生命、救死扶傷,本著利他原則關愛患者,而不是一味金錢至上、利益至上,忘記從醫初心、離棄醫道良心。
以人為本的利他醫德,還應該表現在醫療服務態度上。近代以來,醫療技術迅速發展,部分醫學工作者將醫療活動看成單純的技術活動,把對患者的醫療服務簡單還原為藥物、手術或者各種技術手段的實施,從而淡化對患者生命的尊重。“在醫生看來,患者只是試管里、顯微鏡下的血液、尿液、細胞和各種形態的標本,而活生生的完整人的形象似乎已經完全消失了。這樣疾病便從患者身上分離出來,作為醫生研究的對象,醫術也從醫生身上分離出來成為治療疾病的一種手段”[5]。因此,本該是人與人的關系,異化為醫術與疾病關系,本該是服務便民的醫療行業,退變為需看臉色的行業。但是,正如馬克思認為的,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存在。因此,任何片面地把病人物化、異化的行為都嚴重背離仁愛思想。
傳統醫療父愛主義以仁愛為核心,仁愛的前提就是對人的尊重,這種尊重是對人的價值的全面尊重。病人是具有生理、心理和社會屬性的有機整體,尊重病人就是尊重病人的全部屬性。在醫療技術突飛猛進的今天,醫生更應重拾傳統醫療父愛主義中的仁愛關懷,尊重病人,一視同仁地進行醫療活動。
當然,僅強調以人為本,尊重患者還不夠,醫療父愛主義還需給予醫生適當干預權。給予醫生適當干預權的主張,來源于古今醫患關系的對比變化。但是,不論是今天片面強調患者知情同意權,還是古代片面強調醫生自主權,都有局限性。片面強調患者權利,醫生被動,以致醫生無法按照最佳醫治手段進行救治;片面強調醫生權利,患者被動,易造成醫生專斷,患者諱疾就醫。因此,和諧醫患關系的現代重建的關鍵在于建立相應的協調機制。一方面,實現傳統醫療父愛醫德的現代性回歸;另一方面,需在父愛醫德的基礎上,給予醫生適當的醫療干預權。
(二)醫生適當干預權
2007年11月21日,因丈夫肖志軍拒絕手術簽字,堅持要求醫生給妻子治感冒,而不是生孩子,導致醫生束手無策,眼看李麗云及其腹中胎兒死亡。此事一出,輿論嘩然。有人站在患者家屬立場上,控訴醫院不作為。也有人站在醫院角度,指責家屬愚昧無知。其實事件的關鍵,在于對手術簽字制度和醫生適度干預權的理解。
眾所周知,彰顯現代社會文明特征之一的是契約制,現代醫學默認了這種模式,甚至將此覆蓋到醫療行業的方方面面。現代醫學將尊重患者自主權看成醫學的道德原則,患者知情同意權是患者權利的體現。因此,現代醫療機構順理成章地將手術簽字制度,看成是尊重患者知情同意權的重要表現。醫生所要做的和所能做的,都必須暗含在相關的法律、規定或契約之中,醫生需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權”,否則構成醫療過失。[6]這就做法看似保障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權,其實忽略了醫生的德性。因為此時醫生的治療活動,與其說是自覺實施“仁術”的活動,不如說是一種謀生的職業活動。作為謀生的職業,醫生無需將父愛看作醫療活動的關懷維度,更不需為患者利益最大化,冒著風險違背患者意愿。醫生僅需按部就班完成工作,獲得相應報酬,長此以往,造成醫生漸失人本醫德,醫療干預要么成為天方夜譚,要么成為免責的護身符。從這個方面而言,現代醫學過分強調患者權利,其實某種程度上,為之后醫療道德頻發問題埋下隱患。另一方面,過分強調患者權利,難保有部分患者及家屬,利用法律對患者知情同意權的保護,假借醫療事故之名,弄虛作假,以圖高額賠償金,再加上媒體的推波助瀾,醫生群體被推至道德的風口浪尖,面對嚴重的醫療風險,直接導致醫生的職業品行每況愈下。因此,給予醫生適當干預權十分有必要。
其實,我國早已關注到醫生特殊干預權的問題,但所謂的干預權,僅針對某些特殊情況,如精神病患者、自殺未遂者拒絕治療、傳染病患者的強制隔離等,而日常的醫療道德爭議問題,卻沒得到足夠重視。目前,醫生特殊干預權還不能像患者知情同意權那樣,得到普遍的支持與認可。只有當極具爭議性的個案發生時,才引起一定程度的關注和思考。正因如此,使醫患關系時至今日也得不到有效緩和,甚至愈演愈烈。
傳統醫患關系推崇父權至上,醫生擁有完全的醫療決策權,因此,醫生可無后顧之憂,純粹為患者最大利益進行救治。但今天和過去已大不相同。一方面,當今對患者權利的尊重乃是普遍共識;另一方面,今時今日,整個醫療行業的道德水平,在拜金主義弊病侵蝕下,與傳統相比大相徑庭,因而難保有些無良醫生,會打著醫療干預權的旗號,做出某些越界出格的行為。所以,問題關鍵在于如何實現傳統醫療父愛主義的現代轉型。
三、醫療父愛主義的現代轉型
造成當前醫療糾紛、互不信任等現象是多方原因的綜合,不僅有觀念思想原因,也有法律、機制原因。因此,緩解醫患矛盾、建立新型和諧的醫患關系,實現傳統醫療父愛主義的現代性回歸,需進行多方面的對接轉型。并且在轉型中,建立醫患互信的溝通模式,平衡雙方權利,使醫患關系始終處于和諧穩定狀態。
(一)建立醫患互信的思維方式
據中華醫院管理學會2001年對全國326所醫院調查顯示,醫療糾紛發生率高達98.4%,其中90%是非醫療過錯引起的糾紛。[7]對于原因解釋,醫生群體普遍認為是患者為私利無理取鬧、對醫療活動認識不足、維權意識增強造成的。但患者卻認為醫生唯利是圖、缺乏責任心是主要原因。由此可見,醫患之間缺乏基本信任和必要溝通。因此,醫療父愛主義的現代轉型,亟需轉變醫患互不信任的思維方式,建立雙向互動的溝通機制,這要求醫患雙方共同努力。
就醫生而言,現代醫師需在恪守傳統醫家良訓的同時,培養新型職業道德,將傳統醫道的仁愛精髓融入現代醫學職業道德之中,增強從醫責任心,實現醫療父愛主義的現代轉型。傳統醫德的仁愛精髓包括人本、誠信、有利、公平等原則。孫思邈在《大醫精誠》里說道:“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愿普救含靈之苦。”①孫思邈:《大醫精誠》。由此可見,孫思邈認為醫生需敬畏生命,常懷惻隱之心,并樹立“濟世活人”的職業理想,這與現代社會對醫生醫德的要求不謀而合。也正因如此,古醫才有“臨病人問所便”②《黃帝內經》,《靈樞·師傳第二十九》。的溫和親善做法。反觀當今,雖也強調尊重患者權利,但卻與初衷大相徑庭,醫患之間似乎成為彼此道德的異鄉人,罕見相互關心體諒。時至今日,“臨病人問所便”的做法,僅是醫生問診的工作程序,甚至演變為“只見病不見人”的就診方式,更別說無形中淪為冗長復雜,或枯燥無物的手術簽字同意書。多數醫生似乎沒有正確領會簽字前提是詳細了解患者文化背景、身體狀況、家庭情況后,幫助患者權衡利弊,在其充分了解同意書的基礎上互動交流,為患者生命健康施行醫療行為,而不是簡單羅列一個有關風險、利益的清單,攤在患者及家屬面前,任其決定。“臨病人問所便”的做法其實就是醫學人本、尊重、有利患者醫德的集中體現。古代良醫從職業良心出發,對病人提出合理化建議,故此,“醫者精誠,志存救濟”,患者深信,以命相托。由此可見,古醫恪守的醫學仁術,和現代社會要求培養醫務人員人文精神的職業要求一脈相承。
當然,醫療父愛主義的現代轉型,還需權衡傳統人道醫德和醫生合法收益之間的關系,培養醫務人員樹立正確的義利觀,使傳統醫德的仁愛精髓,在當今醫療市場化大背景下相得益彰,真正實現醫療人道主義與功利主義、社會效益與經濟利益的統一。正如清代名醫徐大椿所云,為謀生計而學醫實不可取,但卻認同醫者通過醫術水平而獲“利”的做法。“況果能虛心篤學,則學日進,學日進則每治必愈,而聲名日起,自然求之者眾,而利亦隨之。若專于求利,則名利必兩失。”③徐大椿:《醫學源流論》之“醫家論”,人民衛生出版社2007年版,95頁。這種把提高醫療水平作為獲取名利的方法,無疑對現代醫學價值觀具有深刻意義。
就患者而言,轉變醫患之間互不信任的思維模式也需患者參與其中。患者需打破傳統醫患之間相互沉默的歷史,改變不信任的就醫心理,在醫生詢問病情時,主動提供病史資料,坦言相關病癥,積極配合治療,并在盡量了解疾病發展規律、治療手段和程序之后,與醫生積極互動溝通,盡量避免不合作或沖突狀況。只有這樣,醫患之間才能增加彼此互諒,為互信和諧的醫患關系的構建提供正確起點,使醫患關系重回正途。此外,傳統醫療父愛主義的現代轉型,還需對接相關法律,保障父愛干預權,真正為實現醫療父愛主義回歸保駕護航。
(二)引權入法,對接法律與父愛
眾所周知,道德和法律是維系社會和諧穩定的兩個重要維度,醫德醫風屬于道德范疇,而權利義務則屬于法律制度范疇。傳統社會中,禮扮演法的角色,醫生克己復禮,嚴于律己;患者以禮相待,恭謙禮讓。因而總體而言,醫患和睦、休戚與共。然而,在個人權利凸顯的今天,傳統的禮樂教化作用已日漸消退,因此,醫療父愛主義的現代轉型,亟需實現醫生父愛關懷和相關成文法制的對接。法律既要給醫生適當干預權提供保障,也需隱含對醫生醫德的要求。
因孕婦李麗云案出臺的《侵權責任法》第56條,可以說是傳統醫療父愛主義實現法律對接的體現。《侵權責任法》第56條規定:“因搶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緊急情況,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親屬意見的,經醫療機構負責人或者授權的負責人批準,可以立即實施相應的醫療措施。”較之前,此規定更加明確了醫療機構在特定情況下的醫療權。立法者試圖通過《侵權責任法》的規范化,實現醫療救治法律與醫療父愛道德的現代“對接”。我們可這樣理解此項規定:當遇緊急情況,醫生無法獲得患者或其家屬的意見時,具有推定其同意進行手術救治的權利,甚至可根據危險程度,不顧患者及其家屬意見,強行進行救治。即使不能得到患者及家屬意見,適當的救治方案仍可執行,這似乎隱含著患者或其家屬可能不同意,醫療機構仍可“忽略”“不顧”而進行救治。由此看見,該規定其實賦予了醫療機構父愛式治療救助權[8]。此項規定綜合考慮了當前的醫患關系,試圖實現患者知情同意權與醫生干預權的平衡統一,保障患者知情同意權的同時,發揮醫療機構的主動性,為實施利他性的父愛救治提供法律保障,雖有不顧患方意愿之嫌,但實際上卻是為了患者生命健康。
此外,對于惡性醫鬧事件,立法者也試圖通過修正原有法規,為保障醫生適當干預權,實現醫療父愛主義關懷的回歸保駕護航。例如,2015年11月1日實施的刑法修正案(九)第31條,將“聚眾擾亂公共、交通秩序罪”,變更為“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情節認定包括“致使工作、生產、營業和教學、科研、醫療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此項修訂意味著“醫鬧”現象今后將載入刑法。同時,該刑種的處罰級別也被提高,從原本的“首要分子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提高為“首要分子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這也就意味著,解決醫患糾紛的法律保障大大提升。令人欣慰的是,經過多方努力,醫患關系的改善已取得明顯效果。2017年2月23日,據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副庭長馬巖介紹,2016年,全國醫療糾紛數量較2015年下降6.7%,涉醫違法犯罪案件下降14.1%。由此可見,用引權入法的方式來保障醫療父愛干預初見成效。
當然,也需注意到,現存的成文法雖明確賦予醫療機構一定的父愛救治權,但也存在諸多問題,如救治程序不甚合理、責任界定模糊等。特別對醫療衛生領域而言,單純的法律規范不僅無益于醫德醫風的改善,甚至還暗藏醫療道德滑坡的隱憂,使醫患博弈愈演愈烈。可見,醫療父愛主義現代轉型關鍵,還是醫德和權利的對接轉型。這就要求在當前醫德醫風建設中,既發揮傳統醫德的文化培育和道德示范作用,又發揮法律規范的監督保障功能。
綜上所述,醫療父愛主義的現代轉型,既需良好醫德為適當干預權提供道德價碼,也需相關成文法律為醫家道德保駕護航。在今天復雜的醫患關系中,不加選擇地將病人的自主權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已滋生出一系列棘手的道德問題。面對今天臨床醫療實踐中的困境,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病人至高無上的權利,重新挖掘傳統醫療父愛主義的當代價值,為實現傳統醫學的父愛主義回歸提供可行之道。
參考文獻:
[1]H·T·恩格爾哈特.生命倫理學基礎[M].范瑞平,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322.
[2]周奕.中國傳統醫療父愛主義思想研究[D].長沙:湖南師范大學,2013.
[3]陳燕紅.困境與出路:我國患者知情同意權法律保護與適用的完善建議[J].河北法學,2014(2):132-137.
[4]費伯雄.醫方論[M].北京:學苑出版社,2013:6.
[5]李東臨,李志宏.對現代醫患關系的初步探討[J].山東醫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1):39.
[6]彭紅.醫患博弈及其溝通調適[D].長沙:中南大學,2008.
[7]梅海嵐.全國326所醫院調查:醫療糾紛發生率高達98%法制日報[N/OL].(2002-02-21).http://english,hanban.edu.cn/Chinese/2002/Feb/110040.htm.
[8]郭春鎮,林海.“對接”的“父愛”——評《侵權責任法》第 56 條中的“醫療權”[J].私法,2011(2):2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