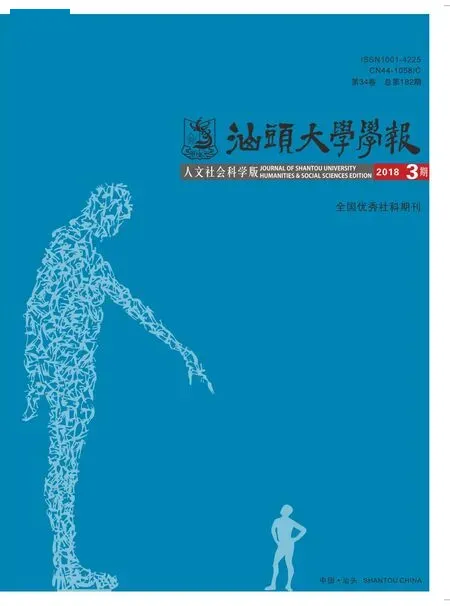中古道教自然審美的觀游途徑
丁 杰 ,江 牧
(1.蘇州大學藝術學院,江蘇 蘇州 215123;2.安徽財經大學藝術學院,安徽 蚌埠 233030)
道教對于自然之崇拜可溯至先秦諸作中關于神山圣人的描述,如《山海經》《尚書》《禮記》《列子》等著。又輔以先秦道家諸內修思想,如“忘座、心齋、抱一”等法。后借兩漢養生內視之術,以導引蓄氣,游歷五藏為目的,如“歷藏、守一”諸法,進而實現意引氣動,內視五藏諸象。魏晉以降,觀游內外自然的觀照法門已成形,且詳備實踐法略,觀其途徑,內傾特征明顯,體現了道教由觀天進而覽地再化身自然的觀游歷程。
一、觀覽天地
忘己觀物(滌除玄鑒、忘座、心齋)作為道家審視大道之美的一種基本范式,被道教有力地吸收并加以改化。老子曰:“大方無禺、大器免成、大音希聲、天象無刑”①“禺”字為“隅”,“大方無禺”即為通行本中的“大方無隅”;“天”字為“大”,“刑”為“形”,“天象無刑”即通行本中的“大象無形”。“世傳今本皆作‘大器晚成’,但老子帛書乙本作‘大器免成’。‘免’‘晚’雖可通用,但孰為本字還需研究。一說‘免’或為‘晚’之借字,然據整句意思來分析又似非‘晚’之借字,而當以‘免’本字解為是。老子二十九章經文‘天下神器’,王弼注:‘神,無形無方也;器,合成也。無形以合故謂之神器也。’器既為合成者,則大器當為免成者,亦即所謂無形以合而使之成者。如此,則與大方無隅、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等文義一致。”高明:《帛書老子校注》,中華書局,1996年,24-25頁。(《老子》第 41章),莊子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莊子·知北游》)均為大道至美的絕佳詮釋。而道教之于自然的看法與老莊思想一脈相承,葛洪在《抱樸子內篇》中開宗明義:
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1]1
在對“玄”做出定義②“此論玄為宇宙之本體,尤著重于玄道。”王明《抱樸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1960年版,4頁。后,葛洪又將其進行描述:
眇乎其深也,故稱微焉。綿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其高則冠蓋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電馳。或倏爍而景逝,或飄而星流,或漾于淵澄,或霏而云浮。因兆類而為有潛寂而為無。……故玄之所在,其樂不窮。玄之所去,器弊神逝。[1]1
葛洪將老子口中的“道”轉化為“玄”,又以“微、妙、高、曠”等修辭來突出“玄”的神秘性,“玄”即“道”。此處葛洪已將“玄”看作自然之本,它關乎晝夜更替、四季輪轉,是天地運行之基、生生繁衍之源,故人于“玄”而言只可感悟,莫能詳觀。但感悟自然是需要途徑的,這個途徑便是老子口中的滌除玄鑒,即做到胸中無我,進而觀照自然。此處之“我”與老子所言之“五色、五味、五音”并無二致,均代表了審美主體的現實環境,若不將其拋開,則無法進入自由的審美境界,更加不能體悟到自然的其樂不窮。
在此前提下,道教對于自然的欣賞便有了具體的實現途徑,即抽離現實去觀察自然,如此便可感受天地之大美。其實西方對于自然的欣賞與道教的出世性思想有共通之處,西方美學將人對自然的審美活動界定在一個有效的距離之內,認為只有在這種有效的距離內,主體對客體才能產生審美。20世紀初瑞士裔人愛德華·布洛(Edward Bullough)的“心理距離說”即是這種觀點的代表。他以海上遇霧①布洛以上海遇霧時的兩種心理狀態來說明審美產生的途徑,其一是沒有拋開現實環境對心理的影響,而無法對海上起霧這一景觀產生審美;其二是抽離現實環境,以非利害性的心態來觀賞迷霧,則產生了審美。Bullough,E.(1912).‘Psychical Distance’as a Factor in Art and as an Aesthetic Principle.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5,87-118.為例,說明了心理距離對于審美行為的作用,而產生心理距離的前提是審美主體必須從自身現實環境的利害關系中抽離出來,這一理論揭示了審美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狀態與關系。但是過于強調主體性原則的審美思想與道教對于自然的審美仍具本質區別。
其一,道教并非將自然視為獨立的審美對象。西方對于自然的欣賞始于將自然看作一件藝術品,人與自然是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在這種關系中,人占據了核心位置,因此人對于自然的理解僅限于自己的內心情感。此時的自然是人化了的自然,對于自然的欣賞也只會映射為對自己的欣賞,亦或稱作對自然的“移情”,艾倫·卡爾松(Allen Carlson)將此稱為“對象模式②卡爾松將“對象模式”定義為按照“藝術形式化”的要求來觀照自然。比如將自然看作一座雕塑,欣賞這座雕塑的感官屬性、突出式樣乃至表現性等等。但他同時指出,在這種模式下審美主體需要借助自身所積累的自然知識體系來對自然進行觀照。他以鯨為例,人們在觀看鯨這一自然現象時所感受到的美是在將其歸為哺乳動物的前提下形成的,如將鯨看作魚類,則只會產生不協調的奇怪感。Carlson,A.(1979).Appreciation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37,267-276.另卡爾松在《自然與景觀》中亦對該模式作諸論述,“我們能夠如同我們欣賞布蘭諾西的這件作品那樣(注:布蘭諾西為抽象雕塑家,此處所指的作品為《空間飛鳥》),欣賞一塊石頭或者一塊浮木:我們實際上或在想象上將這些物體同周圍環境分開,并只關注它們的感官屬性及其可能具有的表現屬性。自然物體經常在這種方式上進行欣賞。進而,這種模式符合自然物體的某些事實,如同非寫實的雕像,它并不客觀反映著周邊的現實環境。”艾倫·卡爾松《自然與景觀》,陳李波,譯,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年版,26-27頁。(Object Model)”的欣賞行為。而道教在對自然的觀照過程中將自然看作一個整體,并非將其視為一件藝術品,道教也從來不會將自然進行孤立,單獨作為一個對象去評論或欣賞,而是將它與人密切關聯,即天、地、仙、人四者協同共生的有機體。道教自然觀中始終包含人的因素,如《云笈七籖》:
真氣清成天,滓凝成地,中氣為和,以成于人。三氣分判,萬化稟生。[2]7
氣清高澄,積陽成天;氣結凝滓,積滯成地。九氣列正,日月星宿,陰陽五行,人民品物,并受成生。[2]8
又《太上洞玄靈寶天關經》:
天地之氣交,然后人及禽獸草木,飛蠕動,森然皆生。[3]925
在道教看來,天地生于氣,氣又三分,再化萬物,其中自然包括人。
其二,無論基于空間或精神范疇,道教均認為人與自然無法割舍③道教認為宇宙的結構就代表了萬物的結構,宇宙的秩序也代表了萬物的秩序,通過將天、地、神、鬼、仙、人諸者雜糅在這個結構與秩序中,就形成了道教的秩序體系,一切都可以在這個合理、合法的體系中運化滋蘗,誰也不能獨善其身。如《真靈位業圖》中所列的神鬼譜系就形成了一個相當完整的結構與秩序,它囊括了神與鬼、天與地、仙與人等不同等級的對應范疇。可參,《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道藏》第3冊,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年版,272-282頁。該譜系被后世稱作道教第一個完整神譜,它的出現說明了道教宇宙結構與秩序的形成是建立在“其一,中國古代的宇宙圖示之上;其二,乃基于‘生存’與‘死亡’的二元對立觀念。”葛兆光:《道教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60頁。這一背景體現了道教宇宙觀的整體聯動特征。另外,柳存仁也論述過相關內容,可互為參照。柳存仁《道教前史二章》《中華文史論叢》第五十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219-223頁。,其審美狀態并非如欣賞風景般的遠觀自然。這一點亦迥異于西方的自然審美范式。西方通常將自然視為一副風景畫來欣賞,這種退一步來看世界的方法有似拿著一副畫框來圈定自然,畫框內的自然元素猶如一副迷人的風景畫,欣賞者與風景之間需要有一段距離,才能使框選之自然成為風景畫,即如畫性[4]132-133。此間,人的主體地位似乎得到了削弱,僅以旁觀者的視角去欣賞自然,但畫框的存在仍體現了主體在欣賞過程中的主觀性結果,人之于自然的主體地位沒有絲毫變化。而道教將自然看作一場時空歷程,其間諸因素每環相扣,因果通連,人在面對自然時,無法任憑主觀意向對其進行刪選或切割。如《太始經》:
于幽原之中而生一氣焉。化生之后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乃化生三氣。各相去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共生無上也;自無上生后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乃生中二氣也,中三氣也;中二氣、中三氣各相去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三合成德,共成玄老也;自玄老生后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乃化生下三氣也;下三氣各相去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三合成德,共成太上也。[2]8
幽原中生一氣,一氣化三,共生無上;又化五氣,共成玄老;再分三氣,合成太上。道教之自然世界由氣化生,每氣再分,連環相生,每次化生均歷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其空間之廣袤,歷時之彌久,不可感量。《太上老君開天經》稱其“無形無象,自然空玄,窮之難極,無量無邊”[2]10,故道教不會將多維之自然看作二維的風景畫,僅憑視覺系統對其感知。又《上清三天正法經》:
天圓十二綱,地方十二紀。天綱運關,三百六十輪為一周;地紀推機,三百三十輪為一度。天運三千六百周為陽勃,地轉三千三百度為陰蝕。天氣極于太陰,地氣窮于太陽。故陽激則勃,陰否則蝕,陰陽勃蝕,天地氣反。天地氣反,乃謂之小劫。……天運九千九百周為陽蝕,地轉九千三百度為陰勃。陽蝕則氣窮于太陰,陰勃則氣極于太陽。故陰否則蝕,陽激則勃。陰陽蝕勃,則天地改易。天地改易,謂之大劫。[2]8
天地之氣極于陰而窮于陽,若陰陽相悖,則天地不調,謂之劫運。在自然孕化的過程中,諸因素不僅連環相生又遵規循法,不僅變化無窮又休戚相關。道教將自然賦予了因果關聯的動態屬性,人無法獨善其身,亦不可將其分割孤立。因此,人無論從何種維度均無法與自然保持距離,更不能任由主觀意向將其圈選,使之成為被畫、被攝、被選的自然,目光僅集中于被選范圍,除此以外的自然則不予關注。
其三,道教對于自然的觀照,是在將自然看作“自然”的基礎上形成的,不會視之為主觀情感的投射物或獨立的審美對象。因此道教更多的是通過參與自然的方式來實現對自然的審美。如道教的修行場所雖多位于名山大川之中,但這種改造并非是對自然的破壞,而是協同式的參與。此模式中,人的關注焦點沒有集中于改造之處,相反,改造自然的目的是讓人更好地關注自然本身,思悟自然的造化之功。如同人們去欣賞天然風化的巖石一般,在感受巖石所傳遞的美感同時亦察覺到了狂風的力量,這是風與石的交互作用,也是對自然全面關注的結果。此論可由道教對諸自然世界的描述中得以印證,道經中多有關于自然世界的記載,如《洞玄靈書》:
國土皆凝水精,琉璃灌地而行,國有寒池縱橫五百里,池有玉芝,一國男女飲食池水,面如玉脂,初無疾病,無有憂愁,壽三萬歲,無有中夭,命終之后,骸骨不灰,萬年亦無臭爛之氣。[5]12
由該描述可感受道教對于自然世界的全面關注,這種關注以多點齊觀的視角展現,自然諸征運化通流,有因必果。如郁單國男女面若玉脂,緣飲國內池水;池水又具寒凍之征,緣國土凝聚水精,遍地冰凌。故國人生時膚色冰潔,亡后骸骨不敗,尸氣不臭。道教不僅關注于郁單國人的體貌,更將視線分散在與此普遍聯系的自然特征上,以聯動的視角去審視自然。因此關注自然現象并非僅集中于所見之處,而是將視點由所見之處向外擴散,與周邊諸因素發生關聯,產生互動,進而實現對自然規律的觀照,即自然而然。又《云笈七籖》:
瀛洲在東大海中,地方四千里,大抵是對會稽郡,去西岸七十萬里,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名之為玉醴泉,飲之數升輒醉,令人長生。洲上多仙家,風俗似吳中,山川如中國也。[2]194
在道教的精神畫卷中,天、地、仙、人和諧共生,他們其樂融融又生生不息,這是自然本體的力量,即道的力量,它既是潛在的,又是無窮的,只有關注于天地運化的規律,才能以自然的心胸去觀照瞬息萬變的自然世界。
二、探游山水
漢晉之際,世間多災禍,隨之儒學衰微,玄道興起。世人多慨于世事無常,苦日無邊,故道教中人急欲建立一套自己的天地觀,以獨立于儒學為代表的官方輿圖體系,借以證明“新天”取代“舊天”之合理性①時局動蕩,易產生宗教運動與政治運動合一之現象,即所謂之救世運動,故道教中人欲強調對天的祭祀權可以轉移,由“三天正法”(新天)取代“六天故氣”(舊天),以證明新秩序的合理及合法性。王宗昱《道教的六天說》,陳鼓應編《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六輯,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版,22-49頁。另參,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其中亦對漢晉之際的末世劫運論作諸論述。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李慶,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387-432頁。。借助輿圖方位,道教將人間世界神秘化,指出世間存有諸多仙人居治之境,如治、洞、地等,且常冠以具有象征意義②道教將諸天地以特定數字進行歸序,是對其教義中宇宙結構與秩序的數字化表述,是由“數”而“類”的思維概括與邏輯推演,這一現象背后體現的是道教對于宇宙秩序的追求,對秩序價值的肯定,以及一整套由具有象征意義的數字所代表的“差序格局”的世界觀。此論可與葛兆光在《中國思想史》第一卷中的觀點互為參照,他以“儀式、象征、數字”三者之間的關系來揭示中國早期思想觀念中的宇宙結構與秩序,并對宇宙秩序的數字化表達進行了論述。“一些象征的反復使用與日益抽象,就逐漸形成一些固定的、神秘的、由數字表示的概念。這些數字是古人對現象反復歸類的結果,他們把‘相似與相近的歸為類,序為數,這類與數,一經一緯,便成了初民認識世界的基本方法。’(龐樸《六峜與雜多》,陳平原、王守常、汪暉編,《學人》第六輯,江蘇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這種由‘數’而‘類’的方法,在商周時代雖然還屬草創,但已經頗有神秘性與權威性。這些看上去并沒有什么特別道理的‘數字化概念’,由于它得到古人心目中的宇宙天地秩序的支持而擁有天然的合理性。”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60-61頁。的數字將其歸序,這些神圣數字的背后往往具有濃郁的宗教色彩③《云笈七籖》天地部論及道教諸天,常冠以36、72等數字加以歸序,使天地之數對應相生,反映了道教宇宙世界的結構與秩序,并以此證明該宇宙秩序的合理與合法,此表述方式含有一定的宗教目的,故神圣性明顯。《云笈七籖》卷二十一、卷二十二,《道藏》第22冊,159-171頁。,是道教精神世界中宇宙新秩序之反映。在此體系中,道教按自己的自然意識,通過探游諸洞天福地來揭示自然之秘寶④東漢末年興發之宗教運動猶如神啟說,乃世間所面臨之劫運,而道教中人則肩負天命,通過探尋神圣輿圖上的名山洞府,來揭示天之秘寶,以重新制定時代秩序。索安《國之重寶與道教秘寶——讖諱所見道教的淵源》,劉屹,譯,《法國漢學》第四輯,中華書局,1999年版,42-127頁。,以達到“與天合”的宗教目的。拋開功利的政教意圖,道教對于名山洞府的探游所反映的本質仍為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揭示,只不過道教將這一關系賦予了神秘性。
其一,道教由對“天”的觀照進而展開對“地”的觀照。道教對于天地的認識是多元化的,二者既非隔絕,亦非合一,而是互通彼此的一對共同體。《紫陽真人內傳》:
天無謂之空,山無謂之洞,人無謂之房也。山腹中空虛,是為洞庭;人頭中空虛,是為洞房。是以真人處天處山處人,入無間,以黍米容蓬萊山,包括六合,天地不能載焉。[6]546
通過山之洞可與天之洞進行互通,所以神仙真人可以做到入無間,即往來天地。《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說救苦妙經注解》:
洞者通也,上通于天,下通于地,中有神仙,幽相往來。天下十大洞、三十六小洞,居乎太虛磅礴之中,莫不洞洞相通,惟仙圣聚則成形,散則為氣,自然往來虛通,而無窒礙。[7]488-489
道教熱衷于探游山水的實踐活動是由“觀天”進而“覽地”的體現,故人間自然被賦予了神秘色彩。此間,道士所探尋的名山洞府絕非文人眼中所見之自然山水,此時的環境尚未被馴化⑤魏晉文人熱衷于游覽山水,但文人眼中的山水是“人文化成”之山水,乃被馴化了的自然,即第二自然。Stein,RolfA.(1943).Jardins en miniature d'Extrême-Orient,le Monde en petit.Bulletin de l'é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Hanoi,Paris),42,1-104.轉引自,李豐楙《洞天與內景:公元二至四世紀江南道教的內向游觀》,《東華漢學》2009年第9期,166頁。,充滿神秘特質。修道之人孤身前往,在一個完全未被馴化的陌生環境中,去探尋天機,尋找可通天的地中仙洞,本為神圣且兇險之事:
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禍害。故諺有之曰,太華之下,白骨狼藉。皆謂偏知一事,不能博備,雖有求生之志,而反強死也。[1]299
故入山之前需博備萬一,葛洪為求道修煉之人準備了諸多法門用以登涉,作為探索自然的實踐活動,《抱樸子內篇》中記載了大量關于如何進入自然,而不被其吞噬的方法。且不論其中之讖諱神鬼,單從方法具則來看,已體現出道教對于自然的全面認識,這種認識是在理解天地萬物普遍聯系的前提下形成的:
當以三月九月,此是山開月,又當擇其月中吉日佳時。若事久不得徐徐須此月者,但可選日時耳。凡人入山,皆當先齋潔七日,不經污穢,帶升山符出門,作周身三五法。[1]299
道教之自然,是天、地、人、時間、空間諸因素糅雜統一,阡陌交縱的自然,故修道之人應天時(觀天),攝地利(覽地),后擇最優方案,通過探游山水來觀照自然,以證明天地之間的對應關系。
其二,道教將天地同化,即“天化地,地化天”。在宗教層面,道教探游山水的主要意圖乃欲極力證明神界與人界新秩序的對應關系,并通過一系列的神圣數字對其編排,如《天地宮府圖》中諸洞天福地的具體數量、位置及特征均與道教諸天之說有所對應,體現了一種將天地同化的意識傾向。
道教諸天中不乏三十六、七十二等數字概念:
又以四方三十六天而取七十二天,……九宮各生八方,而為七十二宮。……九氣分化,各生三天,故為三境三十六天也。[2]161
若按方位,四方、八極、九宮的空間觀念亦多見之,如對“東、南、西、北、中①很多學者都對中國早期天地四方的空間觀做出推論,如張光直以琮為例,認為其形內圓象征天穹,外方象征大地四方,“專從形狀上看,我們可以說琮是天地貫通的象征”。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二集》,三聯書店,1990年版,71頁。又如,李零認為中國的四方觀念早在新石器晚期就已出現。李零《中國方術考》,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104頁。再如陳久金、張敬國認為安徽含山凌家灘出土的刻有四方八位圖案的玉片也是天地四方的象征。陳久金、張敬國《含山出土玉片圖形試考》,《文物》1989年第4期。而東、南、西、北四方的空間觀念有明確記載的現于殷商卜辭中,陳夢家在《殷墟卜辭綜述》中詳細論證了殷人的四方空間觀,“殷人已有東、南、西、北的觀念。……如:‘于西方東鄉-于東方西鄉’(《粹》1252);‘其東鄉-其北鄉’(《鄴三》42.8);‘其自東來雨-其自南來雨-其自西來雨-其自北來雨’(《卜通》375)。西鄉即西向,越語‘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韋昭注云:‘鄉,方也。’卜辭四方順序是東、南、西、北。”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584-585頁。而東、南、西、北的排列順序也與古人觀測天象(天道左旋的斗柄轉向),進而將四方與春、夏、秋、冬四時的物候特征相聯系,以及與四方、四季對應的四神祭祀相關,同時殷人又將自己所處的位置定為中央,與四方并列,稱作“中商”(《乙》9078)。可詳參,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574-599頁。”的方位表述:
今言一天比地四天者,《真人口訣經》云:中斗之中,五斗位者,陽明為東斗,丹元為南斗,陰精為西斗,北極為北斗,天關一星為中斗。[2]160
而道家之地亦名類繁多且廣達五方②道教之五方空間觀念是對殷人空間觀念的延續和發揚,此論可與伊利亞德在《宗教思想史》中所言互為參照,“至于宇宙的結構與節律,自商朝至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各種基本概念之間保持著一種完整的統一性與連續性。對于宇宙的傳統想象是:有一個中心,一根垂直的軸貫穿其間,將天地兩極連接在一起,并由四極而形成此一中央架構。……五個宇宙之數——四極和一個中央……”米爾恰·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宗教思想史》,晏可佳、吳曉群、姚蓓琴,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469頁。另外,馬克斯·韋伯也談論過道教五方觀念的延續性,認為五方觀念是中國自古發展而來,“宇宙起源論的思辨離不開神圣的五字:五大行星(五星)、五種元素(五行)、五官、五臟等等,大宇宙與小宇宙對應(……任何比較都說明,它絕對是中國土生土長的。)”馬克斯·韋伯(Max Weber)《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王容芬,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251頁。:
東方弗于岱,九萬里之外,極豪林之墟。……南方閻浮利,三十萬里之外,極洞陽之野。……西方俱耶尼,七十萬里之外,極浩素之壟。……北方郁單,五十萬里之外,國極朔陰之庭。……中國,直下極大風澤,去地五百二十億萬里,綱維地源,制使不落,土色如金之精。[2]165-166
故天地之間呈對應關系:
天則有三十六天王,以應三十六國;地則有三十六土皇,以應三十六天。[2]166
在這種對應關系中,道教將天地之征進行同化,道士所探之洞府皆與天通,實為“地化天”之體現。如《太上靈寶五符序》中所描繪之山川洞府就與天之洞天存諸多相似特征:
自說初入乃小……當出一千里,不復冥,自然光照,如白日大道……輒有一石井,水味甘美,飲之自飽,不饑。……上所極,仰視如天,而日光愈明,明如日盛中時。又不溫不涼,和氣沖然。聞芳香之氣郁勃,終而不休。及道邊,有房室、亭傳,奇瑋雕鏤,不可目名。既至眾道口,周行廣狹,隱居回,相去可四五十里,四面有玉柱,揭題曰九泉洞庭之墟。其間植林樹盛行,綠葉紫榮,玄草白華,皆不知其名也。五色自生七寶,光耀晃晃,飛鳳翔其巔,龍麟戲其下。斯實天地之靈府,真人之盛館也。[7]317
三、化身自然
由觀天覽地,進而內觀自身,體現了道教將“自然身體化”與“身體自然化”的傾向。道教以天地特征對應人體內部特征,通過探游山之洞庭的外觀之旅,繼而開展觀游人之洞房的內觀超越之旅,最終實現對自然的觀照,即“與天合”。道教攝取了先秦道家的內修之法,如“忘座、心齋、抱一、守一”①早期道家之內修體驗重哲理性敘述,輕具體實踐途徑,泛論較略,故非實踐層面之理論。羅浩《內修:早期道家的主要實踐》,陳鼓應編《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四輯,89-99頁。等法則,又繼承了兩漢時的養生之術,如“歷藏法”與“守一法”②至漢末,養生之法盛行,且備具體之實踐途徑。此論可從當時對巫祝方術的諸多批評中看出這些導引煉藥之風的盛行。如曹植在《辯道論》中就批評方士多虛妄。曹植《曹植集校注》,趙幼文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187-189頁。又如王充在《衡論》中也對這些巫祝方術嚴厲指責,參見《衡論》卷二十五《解除》。王暉《論衡校釋》,中華書局,1990年版,1046頁。再如荀悅也在《申鑒》中諷刺“導引蓄氣、歷藏內視”之法的流行,參見《申鑒》卷三《俗嫌》。荀悅《申鑒》,黃省曾注,《漢魏叢書》第26冊,明萬歷二十年新安程榮刻本。,至《太平經》已明確出現了具體的內視途徑,后經諸方融匯提煉,形成了具有濃郁東方特征的內傾型觀照體驗,即“超越的內在性③傳飛嵐《超越的內在性:道教儀式與宇宙論中的洞天》,呂鵬志,譯,《法國漢學》第二輯,50-75頁。”。
其一,道教在天地同構的意識基礎上進一步將人體與自然進行匹配,即人與自然的同構化。道教將天地諸征引入人體內部,如天有四時,地分五行,與之對應,人之藏府亦有四時五行之氣:
然欲候得其術,自有大法,四時五行之氣,來入人腹中,為人五藏精神,其色與天地四時色相應也。[8]464
然天地之氣無相無形,將其引入體內后,若非使之具象化,則無法懸像觀之。故道教以像代氣,化之為人,便可由觀外像而觀內像(五藏之像):
畫之為人,使其三合,其王氣色者蓋其外,相氣色次之,微氣最居其內,使其領袖見之。[8]464
又按五行五色之方位順序逐一對其形進行內視,意引而氣動,目的就是為了控制體內氣息的流動方向:
先齋戒居閑善靖處,思之念之,作其人畫像,長短自在。五人者,共居五尺素上為之。使其好善,男思男,女思女,其畫像如此矣。[8]464
憑借此法,讓體內之氣與天地之氣的運轉相協調,從而實現觀照自然的目的。這便是漢代已盛行的導引蓄氣,游歷五藏諸像的內視之法。歷藏法的形成填補了先秦道家內修思想中關于實踐層面的缺微,經由視覺化的途徑,將自然五方五色諸征化之為形,又借道家守一、抱一諸法則,使五方色諸外形內化,進而實現內視五藏諸形。這一變化將先秦時僅重神思的內修觀向前推進,轉而形成了具有實踐意義的內視法。
其二,道教將天地之外形升華為天地之外景,將人體之內形升華為人體之內景。于“形”而言,僅可視之;換之為“景”,已可觀矣。雖異一字,從審美層面,“形”具有單一特性,故視之為妥;而“景”則包羅萬象,人在其中,可觀可游可賞。漢晉之際,道教已明確提出修行場所具“空、靜”的概念:
使空室內傍無人,畫象隨其藏色,與四時氣相應,懸之窗光之中而思之。[9]14
此概念,既含“洞、房”之雛形,又具“空、靜”之特征,再以具體之形色加以引導,遂將天地之外形籠于一室之中,化而為景,令人“思之”、“念之”、“觀之”、“存之”。與之相應,既然天地之外形可化為外景,則人體之內形亦可化為內景:
黃者,中央之色;庭者,四方之中。外指事,即天中、人中、地中,內指事,即腦中、心中、脾中,故曰黃庭也。內者,心也;景者,色象也。外喻即日、月、星、辰、云、霞之色,內喻即筋、骨、藏府之象。心居身內,存觀一體之象色,故曰內景也。[7]516
《黃庭經》將人體藏府諸內象與日、月、星、辰、云、霞諸色對應,象色合一成為內景。在此基礎上,又將人體分上中下三部,每部分八景,每八景再對應人體諸位,即“三部二十四景”:
靈寶神仙圖曰:上部八真神圖,以洞天元始之氣,化生自然八景上真,在人身中致上元生氣,精心內思,八真見形,千乘萬騎,運致景云,載人上升。……中部八真神圖,以元始靈寶洞玄之氣,化生自然中部八景,在人身中中元官中,致中元生氣。精思八年,八真見景,千乘萬騎,運致神仙羽蓋,飛行太空。……下部八真神圖,以元始靈寶洞玄之氣,化生自然下部八景,在人身中下元宮中,致下元生氣。精思八年,下元八真使千乘萬騎,運致神仙羽蓋,載人俱升七寶林中。[10]564,565,567
其三,道教借觀游自然之洞府進而觀游人體之洞房,以實現遇仙真的愉悅體驗。陶弘景在《真誥》稽神樞篇中對世人難遇仙真有所描述:
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肺也,履之者萬萬,知之者無一。[11]553
世人屢赴金陵,卻無一尋得仙蹤,究其緣由,乃未掌握觀游之秘法。此論秘法,可從周義山求仙歷程中窺之一二。求仙初期,因其拜訪諸名山洞府而得修煉典籍,遂逐一習之,然總不得要旨,未嘗如愿。故黃老君對其言:
子存洞房之內,見白元君耶?君對曰:實存洞房,嘗見白元君。黃老君曰:子道未足矣,且復游行,受諸要訣,當以上真道經授子也。子見白元君,未見無英君,且復行也。……洞房之內,至精之中,有大神不可名,安出紫房,游戲丹田,上通太微,乃下洞玄。小有為白元君,大有為無英君。見白元君,下仙之事也,可壽三千年。若見無英君,乃為真也,可壽一萬年。[6]544-545
黃老君所言要旨,即道教之“三一①道教之三一法以不同方位、不同名諱、不同形象來將人體內部洞府化,以此實現由外而內的觀游審美體驗。“道起于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閑,卻行一寸為明堂,二寸為洞房,三寸為上丹田也。”王明《抱樸子內篇校釋》,323頁。”法,憑此存思內觀,由內視人之洞房來觀照山之洞房、天之洞房,畢見白元君、無英君。故周義山在成仙后言:
唯精思存真,守三宮,朝一神,勤苦念之,必見元英、白元、黃老在洞房焉。云車羽蓋既來,便成真人。先守三一,乃可游遨名山,尋西眼洞房也。此要言矣。[6]564
未得秘法,便無法遇見洞中諸仙,這也是陶弘景所謂世人難尋仙蹤的緣由。反之,若以法眼來觀照山之洞府,所見自有另一番光景:
此山洞虛內觀,內有靈府,洞庭四開,穴岫長連,古人謂為金壇之虛臺,天后之便闕,清虛之東窗,林屋之隔杳,眾洞相通,陰路所適,七涂九源,四方交達,真洞仙館也。[11]553
三一法是道教實現內觀宇宙的基本途徑,又有動靜之分。靜指集中神思內觀一處,即身體的某一部位,進而與該部宮府內的仙真實現交流;動則指由靜觀一處而做到意引氣動,相繼對身體諸位進行觀照,進而實現與體內諸宮府內的仙真實現交流。從內視五藏到內游三田,這一過程體現了道教觀照宇宙的程序,亦反映為道教內傾型的自然審美范式。
四、結 語
從美學的角度來審視道教的自然觀,可以清晰反映出道教在與自然的互動實踐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一,道教反對與自然的對峙關系,而將自身角色設定為自然的參與者,故不似西方傳統美學將自然看作獨立之審美對象。其二,道教在與自然的互動關系中并非占據主導地位,而是協同式的參與自然,在天地人三者關系中扮演了協調者的角色,即通過自身的實踐活動來順應天地運行規律。其三,道教對于自然的觀照乃基于“自然而然”的意識基礎之上,即將自然看作“自然”,關注于自然潛在的運化規律。
在此前提下,道教將天地人諸征普遍聯系與對應,這種聯系體現了道教對于宇宙結構的獨特解讀,對于世界秩序的孜孜追求,以及對于秩序價值的充分肯定。同時,也體現了道教多元的觀察自然的視角。即通過觀覽天地,以對天地形成一套整體聯動的自然觀;進而探游山水,基于該自然觀來參與自然,對其進行探索,以證明天地間的對應關系;遂化身自然,將人體結構與自然諸征進行匹配,并按照自然的運行規律來調整周身的氣息流轉,以實現“與天合”的目的。道教的自然審美從思想觀念到實踐途徑,均表現出強烈的內傾特征,體現了道教深具創造力的審美實踐活動與獨特的生態智慧。
[1]王明.抱樸子內篇校釋[M].北京:中華書局,1960.
[2]道藏:第22冊[M].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
[3]道藏:第19冊[M].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
[4]Yi-Fu Tuan.Topophilia:AStudyof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andValues.EnglewoodCliffs:PrenticeHall,1974.
[5]道藏:第25冊[M].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
[6]道藏:第5冊[M].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
[7]道藏:第6冊[M].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
[8]道藏:第24冊[M].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
[9]王明.太平經合校[M].北京:中華書局,1960.
[10]道藏:第4冊[M].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
[11]道藏:第20冊[M].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