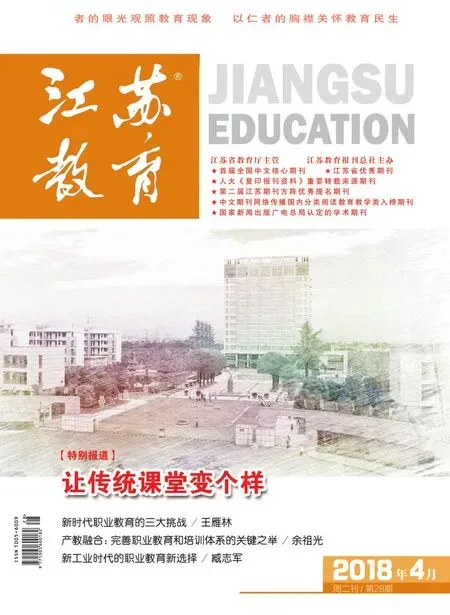新工業時代的職業教育新選擇
/臧志軍
黨的十九大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戰略判斷,顯然,這一判斷是基于對我國當前所處的政治、經濟、社會的重新認識做出的,其中值得關注的一點是對科技革命與產業革命的重新認識。早在2014年,習近平主席就曾在《法蘭克福匯報》發表署名文章,表示“當前全球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呼之欲出”,并重點提到德國“工業4.0”戰略。可以說,新工業時代是中國新時代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新的產業革命也必將帶來職業教育的重大革新。
一、職業教育的工業化特征
(一)前工業時代的職業性學習
早在現代職業教育誕生之前,人類傳承生存技巧、培育職業技能的教育活動就已存在了成千上萬年。對一些仍處于原始狀態的族群的研究表明,部族的年輕人在很小的時候就跟隨成年人學習狩獵技巧,而成年人也會有意識地進行知識和技能的傳授。[1]這種活動顯然是后來的學徒學習的原型。在社會分工達到一定的成熟度后,一些職業開始相對固定下來,逐漸出現師帶徒的現象,特別是在手工業高度發達后,師徒關系成為一種重要的技能傳承結構。與學校形式的職業學習相比,學徒學習具有一些鮮明的特征:
1.學習內容非結構化。師傅很少為徒弟編制結構化的教材,而是隨機地教一些實用技能。盡管會出現一些專門為學徒編寫的教學內容,如為店員學徒編的算術課本、為中醫學徒編的《湯頭歌》,但完整的教材仍不多見,所以總體上學習內容仍然是非結構化的。
2.師傅一般進行技能的整體傳授。俗語“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說明了個人學習主動性的重要性,也說明了在傳統狀態下師傅的技藝傳授與“教育”的標準相距甚遠。師傅一般只通過具體勞動向學徒進行技能展示,而學徒主要通過模仿、反復操練來掌握技能。有調查表明,把技能當作一個整體來教而不是分割成一項項技能點甚至是師傅們有意識的行為,因為他們相信“學徒就是學規矩”,而不僅僅是學習具體的技能。[2]
3.學徒的勞動對象是作為整體的產品。盡管幾千年來人類的勞動分工不斷細化,但只有到了資本主義時代,分工才真正達到極致。亞當·斯密曾對制一根針需18道工序、每個工人只專門從事其中一道工序感到驚奇,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如此徹底的分工對于斯密時代的人來說仍然是稀奇事。有研究表明,我國唐代就出現了唐三彩制作工藝的高度分工,有的工匠只從事掐絲工藝。但總的來說,這只會發生在官方的大型工場中,在民間特別是師帶徒的過程中,學徒的學習任務是完成整個產品,而不僅僅是產品中的某一個零件。
4.學習場景與工作場景同一。傳統狀態下也有少數行會、商會為學徒創造一個集體學習的獨立場,但絕大多數的學徒學習發生在工作現場,是通過“做”來學。當然這與“做中學”還有所區別,后者是通過“做”來學習超越具體場景的抽象知識,而前者只是通過“做”來學習具體技能。
以上的分析表明,前現代學徒學習的最大特征就是“整體性”,從學習內容、學習方法到學習場域都強調整體,而不愿意將其割裂。這是與當時知識體系分工不明確、勞動對象相對簡單等的經驗技術發展階段相適應的。
(二)工業時代的職業教育
韋伯觀察到19世紀的普魯士出現了傳統學徒制的崩裂,大量學徒離開師傅進入工廠勞動,成為技術工人。[3]實際上,如果不是到19世紀末政府強力介入,德國的學徒制也要像英國一樣瓦解了。伴隨著學徒制的式微是職業學校的興起,19世紀后半葉德國機械制造鋼鐵企業舉辦的工廠技校就是典型的職業學校。[4]在資本主義和機器化大生產盛行后興起的職業學校中的學習與傳統學徒學習顯然存在巨大差異,主要表現在:
1.學習內容開始結構化。與工業生產中精細的分工相一致,職業學校對知識進行了細致的分工,分科式課程成為主流。每門課又按照知識邏輯或生產邏輯進行了重新排列。學生只有學完前一階段的知識之后才能進入下一階段的學習,與傳統學徒的非線性學習大相徑庭。
2.每位教師只傳授他所熟悉的那部分知識與技能,所有教師的傳授相加才能構成完整的技能體系。與知識的分科相適應,教師也是分科的。教師只掌握某一工作某一方面的知識和技能,從而成為“專門人員”。
3.學生的勞動對象更多的是某一產品的零件,而不再是完整的產品。由于產業界的高度分工,越來越多的工人只生產某一產品的某一零件,亨利·福特甚至專門為整個過程只需3分5秒的裝配活塞桿的簡單勞動設計了一個獨立的工作崗位。[5]與此相適應,學生也不像學徒那樣需要完成整個產品,而只需完成對零件的學習即可。
4.學習場景與工作場景分離。職業學校的出現對學習場景和工作場景進行了物理分隔,于是職業學校開始努力再造工作場景,但多數嘗試都不太成功。
進入20世紀,電力驅動的大規模生產引發了第二次工業革命,此時生產勞動的分工越發細化,以福特制為代表的大規模生產方式追求技能的極簡化、崗位化。與此相適應,職業學校也開始追求崗位能力培養,集大成者就是誕生于二戰期間的能力本位教育模式(CBE)。它把職業教育活動的起點設定為崗位的能力要求,學生只需要掌握該崗位要求掌握的知識和能力即可。如前所述,大機器生產條件下的崗位設置是高度分工的結果,因此以崗位為基礎的職業教育設計只能帶來知識與技能、學習者與學習對象、學習者與生產對象之間的割裂。這種割裂在馬克思的話語體系里面就是“異化”。
與前現代職業性學習的“完整性”特征相比,工業時代職業教育的最大特點就是“割裂性”,那么這種“割裂式”的職業教育是否能夠適應即將到來的新工業時代的要求?
二、以工業4.0為標志的新工業時代的生產特征和對職業教育的新要求
(一)新工業時代的生產特征
德國人發明了“工業4.0”一詞,他們認為,將來企業建立全球網絡,機器、存儲系統和生產設施融入虛擬網絡-實體物理系統,以相互獨立地自動交換信息、觸發動作和控制,從根本上改善包括制造、工程、材料使用、供應鏈和生命周期管理的工業過程。[6]
這一變化將使工業生產呈現前所未有的特征:
1.真正實現工業生產的靈活性。在工業4.0中,智能工廠擁有端到端的數字化網絡,因此可以開展動態業務,隨之產生動態工程流程,產品形態、生產工藝即使到最后階段也可以改變。企業可以在生產的每個環節考慮個體和客戶特殊需求,從而真正實現“大規模定制”。即使進行一次性生產且產量很低,企業也能獲利。
2.重新定義“崗位”。在傳統工業生產中,崗位是最小的生產單元,所以培養崗位能力非常重要,職業教育也以崗位能力需求為基本參照。而在工業4.0中,智能工廠能夠管理復雜的事物,不容易被干擾,能夠更有效地制造產品,智能產品理解自己被制造的細節以及將被如何使用,從而使生產效率得到極大提高。相當數量的傳統上由人占據的崗位被讓渡給智能設備,人的崗位將變得不再固化。
3.重新定義技術、生產與人的關系。在工業4.0時代,人與技術、人與機器的持續互動成為可能,人將更多地作為一個變量而不是一個常量參與到生產過程當中,即所謂“人在回路中”。那種掌握了簡單技能就能上崗的工作會越來越少,工作能力要求將有可能復雜到打破設計、制造、銷售、維護之間的界限,要求勞動者具有極高的復合型能力。
很明顯,工業4.0在努力追求把簡單的重復勞動交給機器,復雜勞動歸于人類(實際上機器也正在許多復雜勞動上取代人)。前工業時代的生產是整體性的,所以職業學習也是整體性的;工業時代的生產是割裂性的,職業教育也是割裂性的。那么,以工業4.0為標志的新工業時代追求整體性勞動,職業教育該怎么辦?
(二)新工業時代對職業教育的新要求
如果工業4.0描繪的未來圖景能夠實現,那將對職業教育產生革命性的影響。
首先,工業4.0不再需要生產線上的“螺絲釘”,不會再容許由簡單技能、重復勞動構成的崗位存在,人將從生產線上解放出來。智能工廠里的員工將主要是產品的設計者和智能生產系統的管理者,需要相當高的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其次,工業4.0模糊了設計者、制造者、銷售者之間的界限,跨學科能力成為工業4.0時代的人才特征。由于小批量、個性化生產將成為主流,產品的最終形態將與生產者密切相關,而不是像在傳統工業生產中只與設計者有關。每個生產者都將成為產品形態的設計者、創造者,也有可能成為銷售、售后的一環。這種人才素養結構對以分科教學為特征的現代教育顯然是一個挑戰。
最后,工業4.0將加速人才需求的兩極分化。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自動化、智能化技術的引進,美國企業對高端技能崗位需求加大,同時低端技能崗位逐漸消失,大量的一線產業工人被迫轉向第三產業,進而陷入貧困。工業4.0不僅試圖把“動手”的工作交給機器,甚至努力把“動腦”的工作也交給機器,因此有可能會進一步加速勞動者的技能分流。如果不能因勢而變,工業4.0對培養一線勞動者的職業教育而言可能是一種災難。
三、職業教育的新選擇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新工業時代想要變革的就是工業革命以來人與勞動、人與勞動對象的“割裂”或“異化”,把人、技術、勞動放回到統一的、和諧的、完整的場域中。毋庸置疑,職業教育也需要從這個角度來思考自己的未來選擇。
(一)就業導向與教育導向
對于職業教育的功能,至少存在兩種主流的觀點,一種是以促進就業為目的的實質訓練,一種是以改善普通教育為目的的形式訓練。也許,從教育導向到就業導向是一個連續的譜系,不同國家的職業教育功能因為不同的政治經濟背景而在這個譜系里處于不同的位置。那么,中國處于什么位置?
實質訓練觀在我國政府部門乃至職業教育內部有一定的市場,他們認為職業教育就是讓人找到工作的就業教育,所以未來做什么在學校就要學什么。然而這受到相當數量家長的抵制,這些家長對職業學校的教師說:“孩子在學校學什么不重要,只要在學校不出事就行。”這實際上表明了家長對職業學校教育功能的重視,他們相信學技能只是手段,把孩子教育成人才是目的。這其實也是國際職業教育界一直堅持的觀點,早在1998年,第二次世界職教大會就在宣言中強調“職業教育是普通教育的一個組成部分”。
新工業時代正在消滅工作世界的確定性,過多地關注實質訓練和職業教育的就業功能,將培養出一批出了校門就失業的青年人。因此我們建議在未來的體系設計、制度設計中要讓職業教育的功能定位更多地偏向教育一端。為應對這一變化,職業學校也應該在重視就業教育的同時同等重要地開展通識教育、生涯探索體驗和專業基礎教育,為學生選擇升學通道提供幫助。
(二)寬口徑與窄口徑
我國自1952年建立高等教育的專業教育制度以來,高等教育的專業數長期處于上升狀態。1954年發布的《高等學校專業分類設置》中共有257種專業,1963年增加到432種,到20世紀80年代初,全國高等教育實際設置的專業數已達到1300多種,其中僅工科專業數就達到686種,比1954年增長了3.75倍。進入20世紀末、21世紀初,許多反思的聲音指出專業設置過細影響了學生的進一步發展,人才培養定位口徑的寬窄之爭開始傾向于前者,高等教育專業目錄不斷壓縮。職業教育受此影響,專業目錄的數量擴張受到抑制,但由于對接崗位的教育思想沒有改變,職業學校中實際開設的專業、專業方向數量仍然非常龐大。
新工業時代的重要生產特征就是生產鏈、價值鏈的融合,可以說,越為細分的專業口徑越不適合新工業時代對工作的要求。要在根本上解決寬窄口徑之爭,重點在于更新專業建設的“對接”哲學:職業教育應該與產業進步、企業發展對接,這是造成專業越設越多、越設越細的底層原因。在信息化、智能化高度發展的今天,產業進步、工作世界的變化正以超出我們想象的速度進行,如果在幾十年前提對接還較合理,今天再用對接思路發展職業教育就是不合時宜的,在此我們提出專業建設的“融合”理念。
首先,專業設置體現產業、技術融合,應努力消除產業、技術之間的人為割裂,按照融合的思想設計新專業。以物聯網專業為例,許多學校仍然按傳統思路建設物聯網專業,但實際上該專業的就業面向非常寬,學校應打破設計、制造、銷售的界限,同時也打破生產制造、物流配送、公共交通等不同應用領域之間的界限,建設一個全面融合型的新專業。
其次,課程設置體現職業或崗位融合。幾乎所有的一定規模企業都會開展企業內訓,從教育的角度來分析就說明企業家們并沒有把專門技能培訓的職責推給學校,由此可以推知相比崗位能力,他們更加重視員工的通用能力。因此,學校不能盯著企業的某些崗位去開展教學,應該實現專業課程的大融合。
(1)專業基礎課盡量壓縮,且實現功能化。把專業涉及的理論推演、知識性介紹等內容大量刪減,學生能看懂的自己去看,經過努力也學不會的就刪掉;即使是專業基礎課也要讓學生通過完成一個個活的學習任務或創新項目來學習知識,而不是死記硬背。
(2)專業核心課與專業方向課應盡量項目化,學生要以產品實物的制造或實際服務項目的完成進行課程學習。而要實現這個目的,目前的課程劃分難以支持,就會推動課程之間的融合。
(3)形成“課堂項目+課程項目+學年項目+畢業項目”的學習項目體系。學年項目應是課程項目的綜合,推動更大范圍的課程融合;畢業項目則可以有較強的靈活性,讓學生完成與就業相關的實物制造或真實服務,憑借可視化的成績尋找工作。
最后,教學模式應體現過程性融合。學校應學會觀察企業如何生產,努力尋找生產過程背后的教育意涵,然后在學校環境里再造一個更加抽象的教育過程。這個抽象的教育過程不是模仿企業的生產過程,而是模仿企業的問題解決過程。讓學生體驗、了解、掌握如何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形成新模式,才是職業學校應該做的。這就要求學校努力按照企業的生產情境設置學習問題,而不是按照生產過程設置學習任務。
(三)層次與類型
目前的職業教育界已經全盤接受了普職二分法,甚至發展出了“職業教育是一種教育類型”的說法。但如果我們承認職業教育也是教育導向的,那么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終極目標并不存在根本的差異,職業教育就不是教育中的“另類”,而只是教育終極目標的一種實現形式而已。就像足球特色學校通過足球運動培養學生的團隊精神,但能把這些學校看作另一類型嗎?普職之間既非對立關系,也不是層次高低關系,而應是功能互補的關系。目前許多職業學校為普通中小學開設的職業體驗課程就是在補普通教育的短板或缺項。在未來,普職之間可以在差異化、非競爭的基礎上通過課程交換、資源互補等多種形式實現相互連通。而目前在個別地區實施的普職學分融通、學生流動的做法實際上是競爭性的資源重新配置,并不可持續。
對此,筆者建議:不必執著于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之間的差異,也不必執著于強化平行的教育雙軌制,更沒有必要去推動普通本科高校向職業教育轉型,我們真正需要做的是推動課程的分類管理,即開展課程認證,對那些職業傾向明顯的課程開展職業教育化管理,對那些學術傾向明顯的課程開展普通教育化管理。同時積極探索中國特色學分制和能力學分替換的機制,開展多元化的學業能力評價,鼓勵有興趣的學生多選修職業教育課程。
面對新工業時代的新要求,當下職業教育的許多方面都存在改革的必要性。當然,這并不是說職業教育需要回到傳統學徒學習的時代,而是說需要在新的經濟、社會、技術條件下借鑒培養完整知識和技能的傳統經驗,重新把人作為一個整體而不是機器的延伸進行培養。
[1]毛禮銳,等.中國古代教育史(第二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8-9.
[2]朱羊,宋志成.關于商業舊學徒制度的調查和對新學徒制度的意見 [J].勞動,1957(22):17-19.
[3]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北京:三聯書店,1987:24-31.
[4]西倫.制度是如何演化的:德國、英國、美國和日本的技能政治經濟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5-81.
[5]福特.我的生活與工作[M].北京:北京郵電大學出版社,2005:62.
[6]森德勒,編.工業 4.0:即將來襲的第四次工業革命 [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