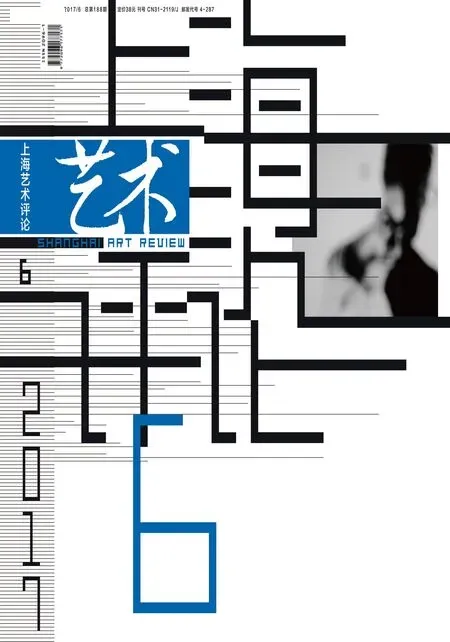從“德國8”出發—學院美術館公共教育及其學術權威
沈 森 姚珊珊
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作為學院美術館有一定特殊性,在“德國8”的展覽中,美術館不僅是美術學院教育的補充,也是連接學院和社會的有效觸手。就中央美院美術館來說,其服務的人群不僅包括校內師生,還包括周邊社區甚至更大范疇的觀眾群體,教育無疑是其首要的職能。憑借美術學院雄厚的學術力量,使它能夠更深入地進行學術領域的探索,與以展覽、學術論壇、講座、工作坊等公共教育途徑帶動研究,促進知識生產。
今夏的“德國8”展覽是德國當代藝術迄今為止在中國最大規模的展示,七座美術館的七個獨立展覽和一場學術論壇,為國內觀眾上演了一場德國當代藝術盛宴。展覽背后,也引發了一次對中德當代藝術的集中討論。作為主辦方之一的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也成了這次研究、討論德國當代藝術的聚集地,通過一系列活動和學術研討,為觀眾提供一次了解德國藝術的公共教育大餐。
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作為學院美術館有一定特殊性,在“德國8”的展覽中,美術館不僅是美術學院教育的補充,也是連接學院和社會的有效觸手。就中央美院美術館來說,其服務的人群不僅包括校內師生,還包括周邊社區甚至更大范疇的觀眾群體,教育無疑是其首要的職能。憑借美術學院雄厚的學術力量,使它能夠更深入地進行學術領域的探索,與以展覽、學術論壇、講座、工作坊等公共教育途徑帶動研究,促進知識生產。也正是由于它在學術方面的學院背景,央美美術館的公共教育對藝術理論和藝術史的深度話題介入度比較高,這也是央美美術館以學院學術帶動美術館公共教育,所形成的一大特色。
20世紀60年代,德國藝術史家維特克威爾(Rudolf Wittkower)曾強調大學美術館有三個功能圈,以此來說明大學美術館與公共美術館的區別,這三個功能圈分別服從于三個不同的對象——社區、學生和院系。一方面,學院美術館和一般的公共美術館有共性,它們都以展覽為主要手段,服務于周邊的社區,與周邊的文化資源和環境形成互動;另一方面,維科特維爾的這種概括同時也道出了學院美術館和學院的關系,以及其自身的優勢:它們區別于一般的公共美術館,服務于院校的研究和教學,同時依托于學院的資源。也就是說,它們一來享受著學院研究和創作力量對美術館的直接滋養,另一方面,擁有著美術學院及其周邊優質的觀眾群體——擁有較高審美能力的藝術專業人士或藝術愛好者。由此,學院美術館能夠成為美術館與美術學院雙重理想的集結地,成為學院教學的補充,也促成雙向度、專業化的美術館知識生產。
藏品、藝術史與公共教育
學院的公信力為美術館聚集了豐富的教育資源,包括藏品資源和外展資源。收藏研究是美術館的重要職能之一,收藏為研究提供對象,研究為收藏提供依據,此二職能的成果再通過公共教育傳達給美術館的觀眾。隨著國內美術館建設熱潮的興起,如今越來越多的美術館開始注重自身的專業化建設。根據一項針對全國重點美術館的調研結果,在這些一類美術館中,已有超過20%的美術館有明確的收藏序列,且該數據在不斷增多,研究和展覽傾向也日漸明晰。例如,從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到中央美術學院,中央美術學院對古今中西的收藏涉及到了美術的各個領域,還借助學院優勢收藏建院以來師生的優秀作品,例如早年留學藝術家的創作及中國當代著名油畫家的作品,能夠比較成序列地反映油畫傳入中國時至當下的發展歷程。

展覽海報
2016年正式對公眾開放的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有包括書畫、染織、陶瓷、家具、青銅器及綜合藝術品六大類的豐富藏品,大多數來自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自1956年以來的收藏,以及校友及社會的捐贈。無獨有偶,故宮博物院呈現著中國古代藝術的序列,中國美術館主要以新中國成立后的藝術發展為線索。相比而言,西方的美術館建設在收藏和展覽研究中積累了更深厚的資源,例如在巴黎,盧浮宮(Musée du Louvre)、奧賽美術館(Musée d’Orsay)、蓬皮杜藝術中心(Centre Pompidou)、東京宮(Palais de Tokyo)形成一條展示法國雄厚藝術收藏和影響力的館際組合:盧浮宮注重展現截止到克羅之前的法國藝術收藏,以此展現法國在文化領域中的穩固地位;奧賽美術館側重于展示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歐洲藝術的發展;現代藝術的展示則集中在蓬皮杜藝術中心;相較之下東京宮則以當代藝術的展示和探索為主。四館共同形成一條銜接良好的美術史發展線路。隨著各館立場的明確,統一在美術館自身的定位之下,豐富、有序的收藏和專業的研究為美術館的公共教育提供了重要資源。
此外,目前藏品展與臨時展覽并行已成為國內諸多美術館所采用的展覽模式,憑借美術學院間的院際交流、院企合作等途徑,學院能夠為美術館帶來諸多臨展資源。如2016年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的開館大展“對話達·芬奇”,經過長期談判得以將達·芬奇的60件手稿真跡從意大利米蘭昂布羅修圖書館運至中國,與清華大學結合自身教學資源制作的裝置模型一同展示。此次“德國8”展覽經過中央美院和德國波恩藝術與文化基金會2年的合作籌備,七個展覽單元共展出了德國上世紀50年代至今最具影響力的55位藝術家的近320組作品,展品分別來自德國杜伊斯堡庫珀斯米爾勒藝術博物館、德意志銀行、漢堡戴希托美術館、雷克林豪森美術館等公共博物館,以及畫廊和私人收藏,也有直接由參展藝術家本人提供的作品。根據7所場館的自身特色分別展示,例如在中央美院美術館的展覽單元“藝術之規——德國當代藝術”中,根據該館對青年藝術家及其藝術的關注傾向,展示了德國年青一代藝術家的作品。學院和美術館的合作促成了許多外展的引進,形成對學院教育的輔助或補充,基于學院美術館自身定位“量身定制”的展覽也有助于其研究和公共教育的拓展。這種舉措得益于學院和美術館自身公信力的作用,同時也有助于公信力持久性的維護。
“理想型觀眾”與美術館的學術權威
除了“內”“外”收藏和展覽資源,學院美術館往往能夠聚攏一批優質的觀眾。首先,如今觀眾在美術館中的地位前所未有。在美術館對公眾開放之初,它為觀眾提供的教育主要基于所展示的實物,往往缺乏交流互動,是一種單向度的知識輸出形式;隨著美術館教育職能受到越來越高的重視,其關注點也從“物”轉向“人”,觀眾在美術館中的學習變得更富主動性,美術館工作者不再對知識進行壟斷,取而代之的是伙伴式的合作關系。有些觀眾會主動在美術館里尋找自己問題的答案,或希望在美術館中滿足特定的學習需求;有些觀眾則希望在美術館里獲取藝術的熏陶,也即隱性的美術教育感染;當然還有觀眾希望在美術館里達到社交、娛樂等目的;同時也有一些硬性的規定所帶來的受眾群體,例如《北京市中小學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施意見》規定,從2014年9月起北京市小學和初中各學科平均應有不低于10%的課時在博物館、紀念館等社會大課堂輔導完成。在這種趨勢和現狀下,美術館的收藏、研究、展覽、公共教育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從目標受眾出發,考慮觀眾的知識背景和接受程度,以此設計自身的研究和展覽。
這種對“人”的關注使得美術館要根據不同的預期觀眾群體調整自己的策略,在收藏、研究、展覽和公共教育上做出不同行為反應。在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看來,不同觀眾的趣味判斷是后天的、決定的,是社會區隔的標志,他認為沒有接受過美育教育的普通大眾不具有對藝術作品的探索能力,因為純粹審美眼光來自家庭背景或學校教育,這是普通觀眾所不具備的。“無疑,大學博物館的定位必須不同于市民博物館。根據它的性質,市民博物館是為廣大公民大眾服務的,而這些公民大眾總是被動接受博物館所提供的菜單。根據它的性質,有委托人控制的市民博物館是保守的,很少成為新思想的實驗地。相反,大學博物館留有或者應該留有廣闊的實驗空間,或者說非正統的決定的空間。而且,根據它的性質,大學博物館會以許多不同形式支持學生的積極參與。”
美術學院為學院美術館聚集了一批具有“純粹審美眼光”的理想型觀眾。事實上不僅是學生,那些聚集在專業院校周邊、有著相關專業背景的人群也是受學院美術館喜愛的理想型觀眾。如此,學院美術館就可以進行理想型的收藏、研究、展覽和公共教育,以更專業的內容帶動研究,更大程度地介入美術史或美術理論的前沿研究。
觀眾、趣味與美育的偏差
憑借中央美術學院和望京社區這個“北京藝術中心”,央美美術館周圍分布著諸多其他美術館、畫廊等藝術機構,除了美院師生外,還有大量藝術家、藝術史家、藝術理論家、批評家、教育家、藝術從業人員或藝術愛好者。該館的公共教育也主要針對這類人群開展。“全球化背景下的德國和中國當代藝術發展”作為“德國8”框架下的一項學術活動,邀請了兩國文化學者和藝術家對“全球時代的藝術交融與本體建構”“德意志精神與我們的體征”“藝術中的德國觀念和中國觀念”“中德兩國的當代藝術與當代藝術教育”等議題進行了討論,側重從文化理論研究和藝術思辨的角度與“德國8”的各展覽單元形成深度配合,而非在普羅大眾層面上推廣這些前沿議題;同樣,2015年中央美院美術館“陌生的亞洲——第二屆北京國際攝影雙年展”期間,邀請來自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的亞洲研究學者,舉辦了一系列針對亞洲議題的社會學講座,席間觀眾寥寥,但大多數是該領域的研究者或院校學生。不過,即便是在小野洋子、大衛·霍克尼這些座無虛席的藝術明星講座中,非藝術專業的普通觀眾也是少之又少。對比中國美術館、國家博物館諸多針對普通公眾或兒童進行的公共教育,便可知學術研討、講座仍是央美美術館公共教育活動的重頭,就內容本身來說,具有較高的專業性,在專業觀眾群體中無疑會受到更多的歡迎。
但對非專業的普通觀眾來說情況就迥然不同了。美國教育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認為美術館的教育使命是教育、審美、社會責任,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學院美術館雖然是學院的構成部分,有服務于院校教育的功能,但“一個全方位、綜合性的大學博物館/大學美術館,在經驗管理上,理想的安排應該要分作兩個部分:一是內部的、學術性的博物館,側重于收藏和研究的功能;另一個是外部的、公眾的博物館,側重于展示和教育功能”。也就是說它同時也應有一般美術館面向公眾提供普及性美術教育的職能。
在2008年文化部發布的《全國重點美術館評估標準(暫行)》中,就對公共教育方面有著明確的評定標準,要求重點美術館“有周密的公共教育工作方案和針對不同觀眾群體的公共教育計劃”。2010年中央美院美術館被評為第一批全國重點美術館之一。在其以往舉辦的公共教育活動中,確實包括兒童、殘障人士等不同群體的項目,但總體看來還是專業性較強的研究型展覽和學術講座、研討活動居多,雖然大多數活動面向公眾開放,但從內容上講仍然是一種精英式的教育。2016年第三屆CAFAM雙年展“空間協商——沒想到你是這樣的”,從主題到策劃形式都在探索新的美術館及策展議題,展覽以協商員取代策展人,試圖在方案創作和實施中呈現民主化的過程,甚至將展覽空間拓展至藝術區、商場、小學、醫院,還通過一系列學術活動和“協商譜系考”在策展理念和觀眾接受之間建立連接,一時間話題不斷。但是對比同一時間在上海舉辦的上海雙年展,南方的觀眾似乎比北方的觀眾更樂于走進展廳、討論展覽、在社交網絡上分享觀展經歷。這一方面得益于上海開放的藝術環境,也依靠一個更穩固的中產群體對藝術更高的接受程度和現實的審美需求。
回到北方,藝術學院的精英對展覽方式津津樂道,他們駐足于某件作品前仔細閱讀學術研究為主、略顯晦澀的展簽前,偶爾會見到幾個“游客”一臉茫然。南北方在展覽學術研究上的一深一淺,受歡迎程度的一冷一熱形成鮮明對比。中央美院美術館的學院背景、特殊的觀眾群體和自身的學術立場,決定了其公共教育在內容上有學術的區隔,大多數情況下,對于專業觀眾的接受不存在問題,但對普通觀眾來說則一定程度上存在供給與需求的偏差。
美術館以展覽吸引多元化的觀眾進入其展覽敘事,在這一環節中美術館處于輔助觀眾學習的位置。因此為觀眾營造良好的教育空間是教育型美術館所需考慮的問題。在這里,觀眾的定義是開放的,即便是深刻的學術議題,也可以通過合理的展示迎接普通觀眾,即便僅僅是為觀眾提供審美上的愉悅或藝術上的引導。回望得益于學院力量舉辦而成的“德國8”展覽,為藝術專業人士們帶來了德國藝術大餐,拓展了該領域學術研究的半徑。而在藝術領域之外面向普通觀眾群體時,學術性的內容與普及性的美術教育之間卻有著永恒的矛盾。如今可以見到活躍在社會中的美術館教育機構在鏈接著這種斷裂,也完善著美術館教育的許多缺口,例如針對特殊群體的教育、專業的兒童教育、館校合作課程的設計或針對不同工作群體的美術館教育等等。館企合作可以作為推動美術館公共教育的手段之一,但對于美術館尤其是學院美術館來說,仍需在自身已有的公信力優勢下,運用學院資源以點帶面地拓展公共教育,在更廣泛的觀眾群體中促進知識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