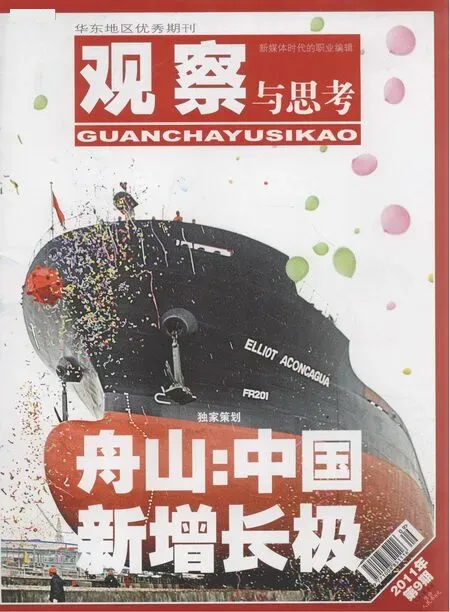改革開放40年:經濟奇跡何以可能
董建萍
提 要:經濟發展的維度是評價改革開放40年的最重要方面。40年來中國人均GDP增長55倍,對世界減貧率的貢獻在70%,中國正在形成全世界最大的中產階級人群。中國的改革是在社會最大共識的基礎上推行開來的,是上下結合、相互促進,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超常規發展動力機制。從高層決策來講,對40年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大推動,就是決定改革、領導改革、實踐改革、保障改革。而民間社會的主動參與,基層政府的勇于擔當和大膽創新,是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社會動因。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40年對于一個國家來講,大致兩輩人的時間,有很多事情可以發生,有很多變化在不經意間已成趨勢。但對于歷史,40年只是一瞬間。作為親身經歷、見證改革開放40年風雨兼程的我輩,總結好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是時代賦予的重大職責。
一、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創造了奇跡
關于改革開放40年歷史評價,可以有多種維度,多種理路。最基本的維度,無疑是生產力發展和經濟增長,這是社會發展進步的物質基礎,是綜合國力增強和人民實現美好生活的最直接指標。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1978年我國的人均GDP是156美元,156美元按當時的匯率大概相當于人民幣1250元。當時世界人均GDP是490美元,那時,80%的中國人口生活在農村,84%的中國人口生活在“一天一美元”的國際貧困線以下。①林毅夫:《2025年中國將步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中國新聞網,2018年4月9日。但到2017年,我國人均GDP是8640美元(大致56160人民幣),增長55倍。
浙江是資源小省,作為沿海前線,在計劃經濟年代國家的投資很少。1978年浙江人均GDP是196美元,大致相當于人民幣1568元。但到2017年浙江人均GDP是92057元,大致相當于14000美元,增長47倍(排全國省區第二名)。杭州2017年人均GDP是113063元,大致相當于17000美元(排世界第42位,國家人均排世界第73位)。①參見林毅夫:《改革開放40年與中國特色理論創新》,《人民論壇》2018年7月(上);《2017年浙江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浙江日報》2018年2月27日。
1978-2017年,這39年間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在9.5%左右。這種連續近40年的接近10%的年增長率,據說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過。40年前,我國85%的人口生活在國際貧困線(1.25美元/天)以下。而多項分析數據認為,到2022年中國的中產階級人數將突破5億(年收入1-3萬美元),成為世界最大的中產階級人群,超過北美人口總和。中國對世界減貧的貢獻率超過了70%。②林毅夫:《改革開放40年與中國特色理論創新》,《人民論壇》,2018年7月(上)。所以,從經濟增長的維度,改革開放40年無疑可以定義為“創造經濟奇跡的40年”,是“中國人民從貧窮到實現小康的40年”,是直觀的可以看見的富起來的40年。當然“富起來”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標準是不斷推高的。
二、改革決策順應時代潮流,契合當心民意
那么,中國是依靠什么力量或者什么方法實現了這樣的增長?一句話,就是改革!
講到改革,筆者認為最重要的在于,這一政治決策順應時代潮流,深度契合黨心民意。就決策高層而言,既要解決當時的困境,又要深謀遠慮于中國社會主義前途命運;就基層社會、民間草根而言,解決溫飽問題、追求好的生活的變革沖動不可遏制。總之,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在社會最大共識的基礎上推行開來的,是上下結合、相互促進,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超常規發展動力機制,不斷推動中國向前發展。
眾所周知,后人給鄧小平冠了個“總設計師”的稱銜,但嚴格來講設計是針對具體方案而言的。中國的改革開放一開始很難說有什么具體方案。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究竟可以改到哪一步?傳統的社會主義所有制“紅線”能不能觸碰?商品經濟的實質是什么?很多問題,我們眼前都是迷霧,只知道從哪里來,但不知道究竟能夠走到哪一步?唯一確定的就是再也不能按照原來的模式進行下去了。當時鄧小平講了很多“這個不是社會主義”、“那個不是社會主義”,但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一直到1992年“南方談話”,他才講了他思考很久的“社會主義本質”論——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③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3、1341頁。馬克思主義不僅要認識世界,關鍵要改造世界。筆者認為,所謂社會主義的外在特征,無論在認知上還是在各國各地區的實踐中,都是一個各有堅持、形式各異的問題,沒有一定之規(講不清楚)。鄧小平的貢獻是,開創了通過本質來認識社會主義的新思路。只要能抓住社會主義本質,實現社會主義本質,就是社會主義。這大大有利于當代世界社會主義破除教條主義迷思,探索新路,釋放活力。而中國經過大膽探索成為典型例證——改革開放使社會主義“起死回生”,煥發生機活力。
回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眾所周知全會最大的歷史功績就是決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我們當時有一個很重要的思想認識成果,就是重提解放生產力④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3、1341頁。。過去習慣上認為解放生產力的任務在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時候已經解決了,生產資料公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相結合,解決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今后只要發展生產力就可以了。后來發現不是那樣,生產力的發展不是某幾種制度的簡單組合可以解決,因此重提“解放生產力”。“解放”是改革之源。解放生產力,按照鄧小平的說法,就是“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①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1頁。,破除體制機制弊端,釋放社會活力。所以,從中國共產黨領導來講,對40年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大推動,就是決定改革、領導改革、實踐改革、保障改革,不斷推動改革從農村擴展到城市,從局部擴展到全局,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政府、文化、社會、自然生態等多個領域,從一般改革、淺層改革發展到全面深化改革,同時不斷創新改革、發展的理念。早期有一鄧式名言:“摸著石頭過河”、“不爭論”,其實質就是拋棄意識形態固有觀念的束縛,允許試錯,因為這是前無古人的事情。所以要說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不是說他有一個多好多完備的方案,而是指他堅持了正確的思想路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堅持了正確的改革路徑(探索漸進,不突破社會穩定底線),堅持了正確的判斷標準(“三個有利于”),堅持正確行使黨的領導(黨管大局,把方向,把管不了、管不好的事還給社會);等等。可貴的是,在40年改革開放進程中,歷任黨中央始終堅持這一基本路線,呼應群眾需求,支持人民創造(“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時堅持問題導向,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在應對復雜局勢和重大風險問題中不斷積累經驗,不斷校正方向(科學發展觀)。正是依靠這種謹慎而充滿中國智慧的定力、領導力、掌控力,改革開放40年一桿紅旗扛到底,在多個歷史的重要關鍵節點都做了相對正確的選擇,探索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從時代的橫斷面看,中國不是一個普通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有自己的社會主義制度基礎,在這種制度基礎上形成了現實的經濟結構和利益機制,是絕不可以一擊推到、一筆勾銷的。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世界上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或者一些政府主導發展的非社會主義國家,按照西方新自由主義實行 “休克療法”。西方理論一貫認為政府乃至國家是個“壞東西”,發展市場經濟就是要徹底擯除政府之手,拒絕一切政府干預。但那些“休克”的國家,基本上都經歷了“失去的20年”,也就是說,轉軌之后經歷了非常黑暗乃至無望的一段時間。而中國的體制轉軌,眾所周知的是“雙軌并行”、“增量先行”,試點先行,政府逐步退出,體制逐步轉接,漸進并軌,所以社會保持基本穩定。當然我們也有代價,也有陣痛。但畢竟中國的改革絕大部分老百姓是即刻獲益的。就執政者而言,重要的是對國家和人民心存敬畏,時刻關注“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滿意不滿意、人民支持不支持”,因而贏得民心,獲得支持,降低改革風險,減少改革阻力。
經過20多年的市場經濟實踐,在目前的頂層話語中,市場經濟的“基礎性”作用進一步提升為“決定性”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這個提法有深刻含義。它表明,雖然我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共同規律,我們必須遵守,市場方向決不會變。有人總結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特征是“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認為中國的經驗價值含量很高,且可復制。
三、改革發展深刻體現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突出特點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將改革開放定義為中國第二次偉大的革命,認為改革開放將帶來觀念、制度、生產方式和人們生活方式的巨大變化,其社會震動的深度和廣度絕不亞于“革命”。這場革命的直接目的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革命的直接對象是一切不符合生產力發展、不符合國情、不符合共產黨為人民服宗旨實現的體制機制,以及一切相應的僵化認識和傳統觀念。就兩次革命比較而言,第一次革命開天辟地,主要是政治革命,解決政權問題和基本制度問題。而第二次革命主要是一場偉大的經濟革命和社會革命,解決中國的發展問題,以及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問題。第一次革命的參與者,主要是中國的先進分子及其信仰群體,不涉及社會大部分人。而第二次革命的參與者,擴展到全中國億萬人民群眾,幾乎所有人都被卷入其中,它的社會動員遠超第一次革命。中國第一次革命的發動、發展,主要依靠中國共產黨的謀略、領導,以及革命隊伍的犧牲和奉獻;而中國第二次革命,如前所述,深刻體現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突出特點,民間智慧、基層擔當在40年的社會進步中發揮的巨大作用,前所未有,堪稱中國歷史之最。
民間社會的主動參與,基層政府的勇于擔當和大膽創新,無疑是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社會動因。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改革是安徽小崗村村民的“紅手印”按出來的,是遍地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沖出來的,是四處游走的義烏小商販們挑擔叫賣揺“撥浪鼓”揺出來的,是類似于“傻子”年廣九那樣的千千萬萬個體勞動者創辦、承包企業做出來的。中國草根社會的確是給一點陽光就燦爛。體制機制的束縛一旦可以掙脫、可以沖破,各種發展“模式”就競相出現,大放異彩。比較典型的有江蘇的“蘇南模式”和浙江的“溫州模式”。蘇南模式以集體經濟見長,溫州模式以個私經濟為主。
1978-1998年,溫州的國內生產總值、工業生產總值、財政收入、外貿出口、農民人均收入等指標,全部翻了5-6倍,年均增長幅度在20%-40%之間。其中個私企業、股份制企業的工業產值占到總量的90%左右,財政收入占到三分之二以上。①宋林飛:《“浙江經濟”與浙江現代化探索》,《踐行“八八戰略”建設“六個浙江”理論研討會論文集(內部文集)》(上),2018年7月,第40頁。這部分增長,國家是沒有投一分錢的。溫州人的特點是講信用、重實體,不放閑錢、敢為人先,還有就是非常抱團、從不抱怨。他們像水一樣,哪里有商機就流到哪里,哪里跌倒就哪里爬起來。40年間溫州也經歷過非常困難的時期。比如1989-1991年間,個私經濟被說成是“和平演變”的經濟基礎,各種指責無端砸來,溫州承受了很大的壓力,但最終挺了過來。還有就是2011年之后的四五年間,因為國內外環境的變化,溫州制造業出口遭遇很大困難,加上當地房地產泡沫破滅、光伏產業和煤礦業等投資失敗,很多企業資金鏈斷裂, 最關鍵是“聯保聯貸”格局造成了危機的迅速蔓延,一家核心企業的債務可以拖垮十幾家企業,三年間房價腰斬,銀行甚至出現斷貸,溫州實際上爆發了局地“經濟和金融危機”。②楊曉宴:《溫州的不良處置和房地產之鑒》,《21世紀經濟報道》2018年7月2日;轉引之《報刊文摘》2018年7月6日。2013年,國家允許溫州進行區域金融改革試點,地方政府強力介入擔保鏈的拆解,調動一切手段進行重整重組,同時保護正常經營的企業。現在,溫州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已經降到全國平均水平之下,溫州經濟貌似失去光環,但仍然充滿韌性。
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離不開基層和地方政府的擔當。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要素。謝高華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浙江義烏的縣委書記。義烏是浙江比較窮苦的地方,當地農民有忙時種田、閑時走街串巷、搖著撥浪鼓沿街叫賣、雞毛換糖的商業傳統。由于思想禁錮,當時義烏政府也不允許這種小商小販,經常沒收商販們的物品。謝高華一到任,就碰到了農婦到縣委來上訪。經過調查和思考,謝高華認為發展商品經濟符合中央精神,于是縣委出臺了全國獨一份的“四個允許”政策:允許農民經商,允許長途販運,允許放開城鄉市場,允許多渠道競爭。這個時間點是在1982年黨的十二大召開之前。不僅如此,義烏政府還在城市主要街道設立了700個水泥臺子,供農民擺攤,1984年這種固定的街邊攤增加到1800個。再以后,政府開始建設統一的小商品市場,沿街攤販入室,“前攤后廠”成型,義烏逐漸發展成為全國著名的小商品市場,商賈云集。圍繞小商品經營的制造業、金融業、物流業、服務業、房地產業以及電商等等都快速發展起來,最終義烏成了今天的國際化程度非常高的“全球小商品第一市場”。義烏人至今感恩謝高華。2017年,義烏商人自發集結了100輛奔馳車,去衢州接85歲的謝高華來義烏參加“義博會”,是日,市民們成群結隊站立街道兩旁,萬人同搖撥浪鼓歡迎謝高華。新華社為此專門發了通訊,分析謝高華為何能得到老百姓的衷心熱愛。謝高華是中國優秀地方干部和基層干部的代表,他們的聰明才智和擔當精神,保護并引領了中國民間社會的發展能量。
“二戰”后,世界上有將近200個發展中經濟體,雖經三代人的努力,到目前為止進入高收入的只有兩個經濟體:臺灣和韓國。絕大多數發展中經濟體長期陷于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中國能不能到本世紀中葉,成為第三個進入高收入的經濟體,值得期待。
總之,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經濟發展在全世界是沒有先例的,這是一條有別于東西方的現代化道路,是中國對全人類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