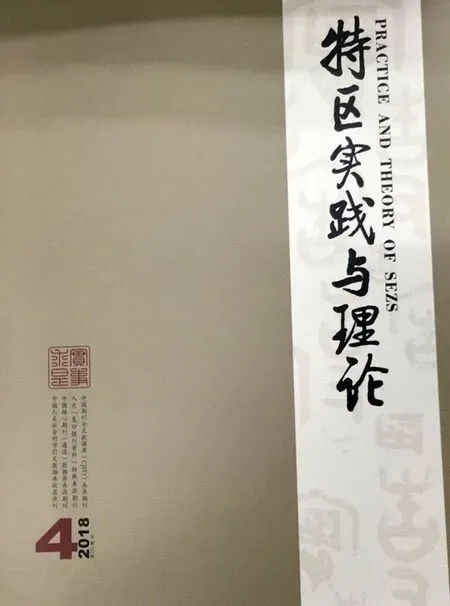儒家信仰與陽明良知之學
林存光
王陽明(1472-1529年,名守仁,字伯安,世稱陽明先生),明代心學思潮的開創者,既是有明一代亦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而富有獨到創見的思想家,更是一位世所罕見的能夠將學術與事功集于一身的偉大儒者。他揭橥良知之學、倡言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之教,使儒家心學大放異彩,為后人留下了一筆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亦產生了深刻而久遠的歷史影響。本文將主要從儒家信仰的角度對陽明良知之學的理論義涵嘗試作一些粗淺的論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性之善,心之靈”:宋明理學家的儒家信仰
美國著名漢學家包弼德曾說:“理學本質的核心是一種信仰——自覺地獻身于某種信念,而不是哲學的陳述或不經明確表述的假設。”①[美]包弼德:《歷史上的理學》,[新加坡]王昌偉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71頁。究其實質,我認為,理學家自覺地為之獻身的這種信念便是對于性之善和心之靈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天理、良知和儒家仁道的信仰。誠如錢穆先生所說:“性之善,心之靈,此是中國人對人生之兩大認識,亦可說是兩大信仰。而此兩大認識與兩大信仰,在孔子實已完全把它揭露了。孔子《論語》常提到‘仁’字,此乃孔門教義中最重要的一個字,其實仁字已包括了心靈與性善之兩義。”②錢穆:《中國思想通俗講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第27頁。如果說孔子之“貴仁”、孟子之“道性善”首先奠定了儒家信仰的義理基調和意義規模的話,那么,宋明理學家則可以說將此儒家信仰更加發揚光大了。他們汲汲于體認天理、發明本心、指點良知,其實都是意在激發和喚醒人對于自身“性之善,心之靈”的認識和信仰,以便能夠使之遵循自己天賦固有的良心善性或道德本性而立身行事。
就中國思想的整個發展歷程來講,漢末佛教傳入,道教興起,釋老之勝場即在心性之修持,然釋氏以人生為幻妄,而老氏所求在長生之術,可以說對以倫常名教為中心的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構成了極為嚴重的挑戰。職是之故,宋代道學思潮興起,作為對佛老二教之挑戰的一種自覺的意識反應,唯有在心性問題上能夠自立根本,方能重塑儒家的信仰或重新確立儒家在中國思想中的正統地位,此乃理有固然、事所必至者。正惟如此,宋代道學思潮的興起及其在后世深入持久地發展演化,始終圍繞并最終要解決的問題不外乎個人身心的修持與安頓,并在此基礎上重建人間的合理秩序。而個人身心的修持與安頓,說到底,乃是“如何成圣”的問題,故如秦家懿先生所說:“理學的最深層面,是成圣的肯定。……‘圣人可學’既是宋儒一致的意思,‘如何成圣’便成為研討問題。朱熹與陸九淵的分歧,在于進學或修身的先后重要性。”①秦家懿:《王陽明》,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第1頁。然而,欲研討“如何成圣”,必須首先解決 “如何能夠成圣”的問題,即“成圣”的可能性或現實性的終極依據問題,這終極依據的問題說到底便是心與性的問題。不首先了解這一點,我們便很難真正認清宋明道學運動或理學思潮的實質意涵及其內部的不同走向和思想異同。
那么,對宋明理學家而言,心性之為心性究竟意味著什么?而心性之修持又究竟為了什么目的?事實上,心性之為心性,并非是一個單純的心性問題,理學家對于心性問題的關注和探究實關乎著他們對于人與社會所作系統反思的觀念,反之,他們對于人與社會的系統觀念亦必須被置于對心性問題的認識基礎之上才是真正可理解的。正如英國漢學家葛瑞漢所說,理學家堅持認為,“人的全部責任是作為社會的一員合乎道德地行事,遵守儒家經典為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設定的種種責任規范”,但他們并非簡單地將這些責任規范作為僵死的教條而為之作辯護,而是將這些責任規范作為活的真理而牢固地置于一種系統連貫、包羅萬象的世界觀或關于人與社會的理論背景之下。換言之,“宋代新儒學哲學家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對人在世界所處位置的這種觀點,他們努力用一種統一的世界圖景給予描述和闡釋”。②[英]葛瑞漢:《中國的兩位哲學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學》,程德祥等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27頁。而所有這些又都與其對于性之善和心之靈的認識與信仰密不可分。對于性之善與心之靈的認識和信仰,歸根結底亦正是理學本質的核心所在。
自北宋周、張、二程之后,道學或理學思潮興起,關于性之善、心之靈的認識和信仰,逐漸在宋明理學家中間獲得了最為廣泛的分享或達成了最具普遍性意義的共識。他們同認“人性本善”或“人性皆善”,如朱子曰:“人性本善,只為嗜欲所迷,利害所逐,一齊昏了。”③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一),王星賢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133頁。而陽明則曰:“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④王守仁:《王陽明集》(上冊),王曉明、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22頁。他們亦同認人心至靈,如《周易程氏傳》卷一曰:“天地交而萬物生于中,然后三才備,人為最靈,故為萬物之首。”⑤程顥、程頤:《二程集》,王孝魚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759頁。朱子又曾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孟子集注·盡心章句上》)陸九淵亦曰:“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⑥陸九淵:《陸九淵集》,鍾哲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73頁。而陽明則曰:“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⑦王守仁:《王陽明集》(上冊),王曉明、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100頁。由此可見,對于理學家而言,所謂的心性之學說到底也就是心靈性善之學,易言之,理學家意義上的心性之學也就是關于性之善、心之靈的儒家信仰與人生學問,程朱陸王之學所同者在此,所異者亦須準此才能得到更好理解。所同者在其擁有共同的關于性之善、心之靈的儒家信仰,而所異者不在性之善方面,而在心之靈方面。而如果說“真正的信仰”并“不是一種迷惑人心的東西所引發的迷狂狀態,它是一種內在的精神狀態,一種深刻的存在感,一種你或者有或者干脆沒有的來自內心的指導,它(如果你有的話)將把你的整個存在提升到一個更高的水平”,①[捷]哈維爾:《真正的信仰》,《讀者》1999年第12期。那么,理學家對于性之善、心之靈的認識和信仰,便正是這樣一種性質的信仰。它塑造了宋明理學家的一種內在的道德精神狀態和深刻的道德存在感,而且作為一種你或者有(良心善性或天德良知之天賦固有,反思以求而存養擴充,或存理滅欲以復其本然固有)或者干脆沒有(為物欲私意蒙蔽而完全陷溺放失掉)的來自內心的指導,它(如果你有的話)把理學家的整個存在不斷提升到一個更高的道德水平和精神境界。也正是對性之善、心之靈的信仰,使理學家的成圣之學或圣賢學問成為一種有本有源的人生學問,②如孟子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后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茍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孟子·離婁下》)而在追求成圣成賢的身心修持的人生歷程中,他們所展現的那種民胞物與、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博大的仁者情懷和高遠境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宏偉的人文理想和政治抱負,以及“義理所在,雖刀鋸鼎鑊,有所不避”、卓然不拔的義理自信和“收拾精神,自作主宰”、壁立千仞的獨立品格,③陸九淵:《陸九淵集》,鍾哲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90、455頁。才是真正可理解的。
二、學為圣賢:人生的根本使命與陽明良知之學的基本義涵
定義“人是什么”或反身性地思考人生的目的和使命,可以說是世界上每個偉大宗教傳統或精神傳統的核心要務,“這表明,了解我們是誰對我們的存在不可或缺”,④[美]詹姆斯·克里斯蒂安:《像哲學家一樣思考》(下),赫忠慧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491頁。作為中國歷史上的偉大精神傳統之一,儒家亦不例外。對理學家來講,關于人生的目的和使命,一言以蔽之,我們來到世上最重要、最根本的便是為了學做人或學所以為人,如張載曰:“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謂人。學者學所以為人。”⑤張載:《張載集》,章錫琛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第321頁。陸九淵曰:“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須是做得人,方不枉。”⑥陸九淵:《陸九淵集》,鍾哲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450頁。朱子則曰:“圣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⑦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一),王星賢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243頁。所謂學做人或學所以為人,也就是學盡人之所以為人之道,為此必須為學以窮理盡心、復其本然之性,方能不“夢過一生”或“不負此生”。⑧張載曰:“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張載集》,章錫琛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第321頁。)就理學家所說做人的道理來講,說到底,也就是本著性善心靈的信仰而努力將人天賦的道德本性自我實現出來以成圣成賢。
倡明圣學,以性之善、心之靈作為成圣的本體論依據,以為學成圣作為人生的根本使命,可以說是宋明新儒學思潮的最大思想貢獻,亦是其思想的根本原動力所在。而理學家之汲汲于講學、窮理、明道、成圣,正是為了要做這樣的圣賢人物,程朱如此,陸王亦不例外。據記載,⑨王守仁:《王陽明集》(下冊),王曉明、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陽明為學立教先后次第分明,雖謂學有三變、教亦有三變,然而,事實上,自幼至老,學為圣賢乃是他始終一貫而未曾完全放棄過的人生追求,而且,隨著人生閱歷的增加,其對于儒家之圣學更能不斷獲得深造自得的親身證悟。
然而,程朱性理之學使程朱所走的是程朱意義上的為學成圣的人生之路,而陽明良知之學則使陽明走上了另一種不同的為學成圣的人生之路。毋庸諱言,他們之間確乎存在著諸多深刻的思想分歧和觀念差異,要而言之,他們對于心之靈或心與性(理)的關系問題、《大學》所謂“格物致知”和圣人之所以為圣的含義均有不同的理解和詮釋。就朱子與陽明之間的思想差異而言,如果說朱子的心性論存在歧心(心之靈)、理(性之善)為二之問題的話,那么,陽明力主“心即理”及其所謂“良知”之學,突出和強調的正是一種心(心之靈)、理(性之善)為一之義;如果說朱子教人“即物而窮其理”的話,那么,陽明則教人只在心(或身心)上做為善去惡的格物工夫;如果說朱子所謂圣人重在德才兼備的話,那么,陽明所謂圣人則是只關乎德性而無關乎才力的。①王守仁:《王陽明集》(上冊),王曉明、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25-26頁。所有這些差異,最終使陽明擺脫了朱子學思想權威的支配性影響,從而能夠自立宗旨、獨立創辟并毅然走上了一條更加簡易直截的依良知而行的成圣之路。而陽明之所以能夠走出朱子學思想權威的支配性影響,歸根結底,亦可以說完全有賴于陽明對“良知”的悟得。也正是因“良知”的悟得,從而賦予了陽明超乎常人的道德勇氣、獨立不倚的學術批判精神和思想自由的思維能力,并真正體現了他對儒家圣賢學問和心性之學深造自得的真切體認和獨到創見。
“良知”一詞并非陽明本人所獨創,而是本源于孟子性善論,宋代理學家既推尊和崇信孟子的性善之論,故亦特別重視并常常論及孟子所提出的良知、良能、良心諸概念,但唯有到陽明那里,“良知”一詞才真正成為其整個學術思想的最根本和核心的概念,既是陽明本人的“立言宗旨”所在,而在陽明看來,更是孔孟以來儒家成圣之學的根本或“學問頭腦”所系,正所謂“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圣圣相傳一點滴骨血也”。②王守仁:《王陽明集》(下冊),王曉明、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1076頁。那么,對陽明而言,良知之為良知,究竟意味著什么呢?扼要而言,我們可將陽明良知之學的基本義涵概括如下:
第一,良知是“造化的精靈”、人人具有的“天植靈根”,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說到底,“良知即是天理”。③王守仁:《王陽明集》(上冊),王曉明、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97頁、第94頁、第67頁、第102頁。
第二,良知之為良知,只是個是非好惡之心,是“人心一點靈明”,是每個人做人的“明師”和“準則”,④王守仁:《王陽明集》(上冊),王曉明、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98頁、第86頁。它原是完完全全、精精明明、光明瑩徹的,隨你如何都不能泯滅;而且,道即是良知,良知即是天理,故良知在人或心之為心,其明覺恒照之功,不在照管道理,⑤如朱子所言,儒家與佛氏的心性修持之學,其同者在“喚醒此心”,而“其為道則異”,即“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為,其異處在此”。(《朱子語類》卷第十七)而在照亮世界,只要你不自欺和信得及,它就會明誠相生、常覺常照,照亮你置身其中的整個生活世界。
第三,良知為人心光明之本體,人人皆有且完全具足、常在恒照而不能泯滅,但除了圣人能夠保全而無障蔽之外,一般人卻“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或“多為物欲牽蔽,不能循得良知”,故“須學以去其昏蔽”;⑥王守仁:《王陽明集》(上冊),王曉明、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58、64頁。為學工夫只在心上樸實用功,或在意念上實落做為善去惡的功夫,而“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即此便是“作圣之功”。⑦王守仁:《王陽明集》(上冊),王曉明、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61頁。
第四,良知在人,具有常在恒照而不能泯滅的虛靈明覺的本質特性;是非之心,為人之價值判斷的根本來源或道德生活的源頭活水。然而,人之靈明本體不免受世俗習心的污染或私意物欲的昏蔽,故須在意念上做為善去惡的樸實功夫,以去其污染昏蔽,復其本體之明。然而,不管怎樣,說本體也罷,說功夫也好,究其根本目的或宗旨,不外教人實實落落依良知而行、循良知而做。因此,良知在人,說到底,必須知行合一并進而融明覺性、是非感與行動力為一貫,這可以說是陽明良知之學的必然要求或題中應有之義,此亦正是陽明良知之學的核心理念或根本信念所在。
依陽明之見,良知之知“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為知孝弟”。①王守仁:《王陽明集》(上冊),王曉明、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4頁。因此,知行的本體必是合一無間而不可分開的,所謂的知而不行或知行分離,乃是由于被私欲私意隔斷所致。陽明曾如是簡明表達他對知行本體的新的認識和理解,即“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②王守仁:《王陽明集》(上冊),王曉明、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4頁。并闡述其立言宗旨曰:“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③王守仁:《王陽明集》(上冊),王曉明、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90頁。顯然,據此宗旨而言,陽明所謂“知是行的主意”、“知是行之始”,其意也正是要教人于意念發動處著實去做省察克己工夫,而其所謂“行是知的功夫”、“行是知之成”,則亦同樣是要教人依著良知躬行實踐、切實去做,故其知行合一之教實是具有強烈現實針對性和“補偏救弊”意義的“對病的藥”,其所針對者便是當時人將知行分作兩事去做的弊病,將知行分作兩事做,則必然導致或冥行妄作或懸空思索的毛病,而其實知行是不可分為兩事,而只能合一并進的,正所謂“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學只一個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④王守仁:《王陽明集》(上冊),王曉明、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13頁。
知行合一乃是陽明悟得吾性自足、心理只是一個之后針對世人將知行分為兩事而教人做的功夫,尤其是教人務必明白一念發動處即是行的道理,并在此處實實落落做“為善去惡”的“格物”功夫。陽明晚年教人“致良知”,則可說是對其早期知行合一學說的重要理論發展和思想升華,從而使其良知之學在義理與實踐上都更為圓瑩透徹。朱子“格物”之說,強調“即物而窮其理”,亦即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在陽明看來,這無疑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故有“析‘心’與‘理’為二”之弊。相反,依陽明之新解,“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而“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故“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由此而言,“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這事實上也就是“合心與理而為一”了。⑤王守仁:《王陽明集》(上冊),王曉明、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41-42頁。總之,心理一個、知行合一、致吾心之良知,這可以說是陽明良知之學的三大要義。
三、“信得良知”:做一個心地光明、純乎天理的人
以上為陽明良知之學的大要。那么,我們究竟應如何認識和理解陽明良知之學的旨趣和意義呢?
宋儒朱、陸之間有“道問學”與“尊德性”之爭,陽明良知之學顯然亦以“尊德性”為鵠的。比較而言,朱子由“道問學”而建立起來的宏大的人文性的學問大廈,盡管亦以學以為己和成德成圣為其根本宗旨,其所謂“格物致知”的目的亦并非意在求取關于外在事物的經驗性知識,⑥如勞思光先生說:“觀朱氏‘格物致知’之說,最須注意者是:朱氏雖就思解一面言‘知’,與日后陽明之以道德自覺言‘知’不同;但‘格物’仍非求取經驗知識之意,且‘格物’之目的并非求對經驗世界作客觀了解,與經驗科學之為求知而求知實不相同。是以,無論贊成或反對朱氏之學說,凡認為朱氏之‘格物’為近于科學研究者,皆屬大謬。”(見氏著:《新編中國哲學史》三卷上,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34頁。)而是擴充和完善本然固有的道德之知,但朱子畢竟強調一個人不能僅僅做一個無見識、沒文化的“好人”而已,尤其是圣人君子必須具備廣泛博大的人文學識(博學),而且,尤其應該德才兼備,才能真正成為治平天下的經世有用之人。而要博學,就必須格物致知、即物而窮其理,故曰:“人如何不博學得!……若是不致知、格物,便要誠意、正心、修身;氣質純底,將來只便成一個無見識底呆人。”又說:“今人只管說治心、修身。若不見這個理,心是如何地治?身是如何地修?若如此說,資質好底便養得成,只是個無能底人;資質不好,便都執縛不住了。”①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一),王星賢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153頁。平心而論,朱子“道問學”自有其不可抹殺的積極價值和客觀意義,盡管“尊德性”乃儒家學問的根本,但人之一切不是都可以化約為德性問題的,如果說人除了是一道德性之存在,畢竟還是一文化性和社會性之存在的話,那么,朱子之“道問學”及其強調才之用的問題便自有其本身的道理。而陽明對于朱子“格物”之說又何以期期以為不可呢?關鍵在于,陽明認為朱子“格物”之說缺少頭腦,缺少頭腦則不免乎“務外遺內,博而寡要”,乃至“玩物喪志”,而其流弊所及真有不可勝窮者,正所謂“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為了補偏救弊,故陽明特拈出“良知”二字以為頭腦以教人,此亦正是陽明良知之學何以要“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的根本用心所在。說到底,也就是教人克制自己的私欲,依循良知之天理而行,因為良知為人心光明之本體,循此良知而行,你就能做一個心地光明、純乎天理的人。
然而,“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決非教人懸空想個本體、空空地去“尊德性”,或者如佛家“明心見性”只是做一個“自了漢”而出來做事都不濟,而是教人務必要“在事上磨練,做功夫”,如此方為“有益”,而且能“立得住”,否則,只會“遇事便亂,終無長進”。②王守仁:《王陽明集》(上冊),王曉明、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113、86頁。故陽明力主于“意之所在”、“意之所發”、“意之所著”或“意之所用”處來切實做“格物”功夫。依陽明之見,只要人能夠“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并實實落落依著此心之天理良知去做,便“無有不是處”,亦“無不是道”;反之,“沉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為喪失良知,一也”。③王守仁:《王陽明集》(上冊),王曉明、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67頁。
陽明從未教人脫離事物而窮此心之天理、實現自我的道德價值或空空地去尊德性,盡管陽明的良知之學“只承認道德行為之價值,而不認為獨立意義之知識活動有何獨立價值”,④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三卷上),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18頁。但并不因此喪失其本身的價值與意義,因為良知在人,關系甚大,推言至極,則可以窮盡萬事萬變,故陽明有詩曰:“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⑤王守仁:《王陽明集》(下冊),王曉明、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694頁。
吾心之良知即是天理,喪失良知,泯滅天理,不知其可也。而良知之為良知,究為何物呢?陽明曰:“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又說:“是非兩字,是個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⑥王守仁:《王陽明集》(上冊),王曉明、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103頁。那么,果真如此嗎?英國大哲學家羅素曾說:“良心是對每個人的個人天呈,它能夠讓人判斷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這個觀點的困難在于,良心隨著時代在變化。今天,大多數人都會認為,只是因為不同意異己分子的形而上學就要燒死他們是錯誤的,而在過去,只要是為了正確的形而上學的利益,這是一個很值得稱贊的行為。研究過道德觀念史的人不會認為良心是一成不變的。因此,我們不得不放棄以一組行為規則來定義德行的嘗試。”⑦[英]伯特蘭·羅素:《哲學大綱》,黃翔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194-195頁。毫無疑問,陽明所謂“良知”,就其發用流行而落實在具體道德行為層面講,也不可能不帶有其時代性的道德意
識及其局限性的烙印,這自然也是其困難所在。然而,陽明良知之學的真義并非到此而止,我們必須繼續深入思考的問題是,除了時代性的道德良心(良知)之外,還有沒有超越時代性的道德良心(良知)?以及究竟何謂真正的道德或道德良心(良知)?梁漱溟先生說:“有存乎一時一地的所謂道德”,但“道德亦原自有真”,而“道德之真要存乎人的自覺自律”,①梁漱溟:《人心與人生》,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三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19頁。一時一地的所謂道德,或隨著時代變化的良心,在過去或許就是要求人們遵從習俗和權威的道德良心,此應被稱作為受世俗習心所熏染的道德良心,決非陽明所謂不離不滯、②即既不離于見聞習俗,又不滯于見聞習俗。光明瑩徹之良知。陽明所謂良知乃指“心之虛靈明覺”,亦即是“所謂本然之良知”,③王守仁:《王陽明集》(上冊),王曉明、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44頁。亦可謂為本源性(本源于心之靈、性之善)的是非之心。陽明曰:“凡所謂善惡之機,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所致其體察乎?”④王守仁:《王陽明集》(上冊),王曉明、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43頁。為什么這樣講呢?因為,唯有吾心本然之良知才是道德之真的體現,才是人類道德生活的真正根基與源頭活水。陽明以“良知”二字為“頭腦”、以“是非”兩字為“大規矩”,并非是要以一組外在的行為規則或一套固定的儀文節目來定義德行,而是以良知來指導和調整具體的行為儀節,⑤王守仁:《王陽明集》(上冊),王曉明、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46頁。“夫良知之于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于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這其中自有深意在,因為“義理無定在,無窮盡”,⑥王守仁:《王陽明集》(上冊),王曉明、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12頁。因為陽明所謂“良知”,“不是教條,也不遵奉教條”,⑦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3頁。亦不教人盲目地遵從權威。正惟如此,故陽明能夠“學貴自得”而發為具有振聾發聵意義的是非之“公”論,其言曰:“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⑧王守仁:《王陽明集》(上冊),王曉明、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72-73頁。正惟如此,故陽明能夠不像朱子那樣念茲在茲地一心要扶持三綱而辟佛老之異端,⑨朱子曰:“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六)而是以自由開放的胸襟、本其光明圓瑩之良知,平視三教,深契妙悟,觀其會通,卓然曰:“圣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⑩王守仁:《王陽明集》(下冊),王曉明、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1085頁。正惟如此,故陽明能夠拋棄先前的“鄉愿”意思而“做得個狂者的胸次”,11王守仁:《王陽明集》(上冊),王曉明、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107頁。亦教人“常常懷個‘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并說“人若著實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12王守仁:《王陽明集》(上冊),王曉明、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94頁。
所謂“義理無定在,無窮盡”,除了要人不把義理當作教條看之外,還有更深一層的意思,這就是要人須“就自己良知上真切體認”而“著實用功”,用功愈久,則見道愈深而終無窮盡,故曰:“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為已知,為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著實用功,便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13王守仁:《王陽明集》(上冊),王曉明、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19頁。由此可見,陽明雖一方面強調良知之明覺而“覺即蔽去”以復其本體光明的“簡易透徹功夫”,①王守仁:《王陽明集》(上冊),王曉明、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103頁。但另一方面卻也深知“去人欲”猶如破山中賊,甚至比山中賊更難破,正所謂“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正所謂“不努力與內心的惡念作斗爭就不清楚它的力量”。②[英] C.S.路易斯:《第十六講 信、望、愛》,何光滬編:《信仰二十講》,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年,第280頁。換言之,只有像朱子所說那樣“扶起此心來斗”,③黎靖德編:《朱子語類》(一),王星賢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206頁。你才能真正明白源自于私欲和惡念的黑暗力量有多么強大。但不管怎樣,陽明相信“良知在人”是“隨你如何不能泯滅”的,只要你真切體認,而且“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工”,④王守仁:《王陽明集》(上冊),王曉明、趙平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66頁。即完全信賴吾心本然之良知,并“循著良知發用流行將去”,人們就能看到道或天理實現的希望,因為道不在別處,就在人心,就在吾心之良知。如果說陽明所謂“良知”,說到底即集中體現了一種將“心之靈”與“性之善”真正合而為一的儒家信仰的話,那么“信得良知”便正是對這一儒家信仰的真實表達。所謂“信得良知”,亦可以說是一種儒家化的良知信仰或良知化的儒家信仰,正是基于這一信仰,陽明先生才汲汲于教人依良知而行,做一個心地光明、純乎天理的人。
綜上所述,陽明良知之學之所以強調“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并切切于要人在良知意念上實實落落做“為善去惡”的“格物”功夫,其目的只在去其私欲牽蔽而實現心靈意志的純化、本然之良知發用流行的自由和道德良心的自覺自律。唯有如此,才能做一個心地光明、純乎天理的人,而做一個心地光明、純乎天理的人,決非意味著做一個心地單純而一無用處的呆子,而是做一個保有向上之心的人。良知之為良知,或良知在人而不能泯滅,正是使吾人之生命能夠保有一向上之機的希望所在,而所謂“向上心”,亦即梁漱溟先生所說,是“不甘于錯誤的心,即是非之心,好善服善的心,要求公平合理的心,擁護正義的心,知恥要強的心,嫌惡懶散而喜振作的心……總之,于人生利害得失之外,更有向上一念者是,我們總稱之曰:‘人生向上’。”⑤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三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3頁。當然,保有向上之心,不是教人只是懸空想個本體,而是必須在事上磨練做功夫,否則,你不可能真正了解向上之心或良知之本體光明的益處及其能夠照亮世界的奧秘。
正是因為體認真切、信得良知,所以陽明能夠從朱子之學權威性的思想形式統制下脫然獲得心靈的解放,也正是因為對吾心之良知有著深造自得的真切體認與深刻信仰,旨在將吾心良知的明覺性、價值判斷的是非感與道德實踐的行動力融為一體、合為一貫的陽明良知之學,才真正能夠在中國哲學史上為儒家圣人之學或心靈性善之學放一異彩,不僅在后世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學術思想影響,而且陽明生前之能成就曠世之事功偉績,亦非徒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