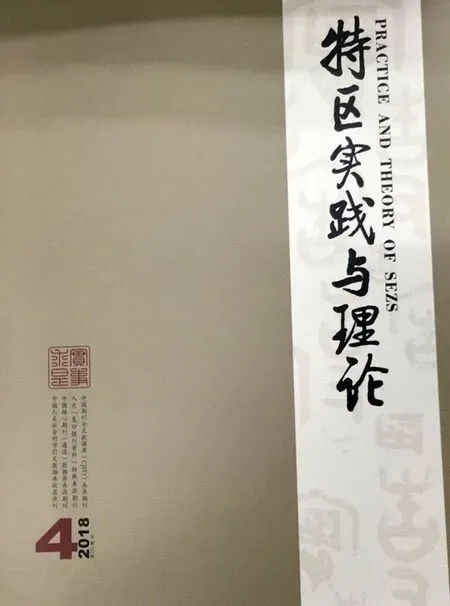廣州起義前后黨的自身建設探析
王定毅
1927年12月11日,中國共產黨繼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之后,又發動了廣州起義。由于敵我力量懸殊和企圖通過城市武裝暴動或攻占大城市來奪取革命的錯誤思想指導,廣州起義最終失敗了。但這次起義作為中共面對1927年革命低潮時候做出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總方針的標志性事件,是對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一次英勇反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一、學術綜述
廣州起義的學術研究始于起義爆發之后不久黨內人士的工作總結。根據中國知網統計,建國以后較早開始研究的是由中山大學歷史系74級《廣州起義》調查學習小組所寫的《紀念廣州起義五十周年》,發表于1977年12月的《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改革開放之后,這個領域的研究逐漸受到關注,在1997年和2007年廣州起義70周年和80周年的時候,達到了一個小高潮。成果也不可謂不多。但這些成果主要集中于起義過程的研究,起義中著名人物的活動研究,或者是中央蘇區對廣州起義的紀念研究等,關于本次起義中黨的自身建設工作,卻很少得到關注。筆者在梳理史料中發現,在這次重要的歷史事件中,雖然中共處于幼年時期,但對于黨建工作卻給予了高度重視,其中的經驗教訓值得借鑒。
二、廣州起義前黨組織加強黨建的做法
(一)加強思想建設
大革命失敗后,加強黨的思想建設,最重要的是堅定黨員的革命信念。正如廣東工作計劃決議案指出的,要求黨員從根本上“掃除舊有機會主義軍事投機等傾向,確定其新的觀念”。①中央檔案館編:《廣州起義》(資料選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25頁。為了做好對黨員的教育工作,廣東省委決定從五個方面來加強,一是黨內訓練刊物及訓練大綱解釋中央政策與決議及省委之決議;二是翻印傳播中央刊物《布爾塞維克》;三是省委定期出版對外刊物,發表政治主張;四是找到適合工農群眾的標語;五是各級黨支部必須開會討論中央政策和省委的決議。①中央檔案館編:《廣州起義》(資料選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25;50;1;7;50;19;26;26;32頁。
根據1927年12月5日廣東省委的報告可知,“《紅旗》出版至第九期,《省委通訊》出版至第四期,《中央通訊》均擬翻印”。②中央檔案館編:《廣州起義》(資料選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25;50;1;7;50;19;26;26;32頁。同期,廣東省委除翻印黨中央出版的《布爾塞維克》外,省市委和黨領導的群眾團體,秘密出版許多刊物,加強發動起義的宣傳工作。廣州市委出版《工農小報》,香港市委出版《鋤出頭》,香港海員支部出版《中國海員》,金屬業工會出版《鎚聲》,街市業工人出版《苦叫》,此外各地還出版了一些小型刊物。這是廣東省委重視黨內教育工作的具體行動。
(二)加強組織建設
1.建立領導機關。為了籌備廣州起義,中共中央首先建立了指揮起義的黨的領導機關。在起義前4個月,即1927年8月11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南方局,“茲臨時政治局請派恩來、太雷、澎湃、陳權、代英、黃平、國燾為中央之南方局,以國燾為書記”。并且指明南方局的職責就是為了發動武裝起義,并決定張太雷為廣東省委書記。③中央檔案館編:《廣州起義》(資料選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25;50;1;7;50;19;26;26;32頁。根據具體工作需要,9月26日,南方局在汕頭召開第一次會議,決定改由張太雷任書記。也就是說,張太雷不僅是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而且是南方局的書記,這樣便于整合資源,統一協調指揮起義工作。
對于起義之后的政權機關,中共中央明確要求確保共產黨在政權中的領導地位,在1927年9月中央給廣東省委的信中指出,如果廣州起義成功,要選出中國臨時革命政府,在成員組成上,要“保證本黨絕對領導為原則”。④中央檔案館編:《廣州起義》(資料選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25;50;1;7;50;19;26;26;32頁。
在建立領導機關的同時,廣東省委也關注基層組織和干部隊伍的建設,提出要建立鄉村支部、工廠支部、軍隊支部。省委還積極培訓干部,1927年12月5日,中共廣東省委政治報告指出,“訓練班已開過三班,41人,第一班11人,多已派赴各地擔任書記、組織等工作,第二班則因廣州準備暴動需人,均已派返,只派出四人至云浮等地”。⑤中央檔案館編:《廣州起義》(資料選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25;50;1;7;50;19;26;26;32頁。基層組織的建設和干部的培訓為發動起義做了重要的組織準備。
2.積極主動發展黨員。在廣州起義前,廣東省委在多份決定中,均要求大力發展黨的組織。如在1927年10月15日廣東省委發布的最近工作綱領中,要求“盡量發展黨的組織和工農革命軍中及工農群眾中盡量發展農民協會與工會,要深入而普遍”。⑥中央檔案館編:《廣州起義》(資料選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25;50;1;7;50;19;26;26;32頁。可貴的是,廣東省委不只是一般的號召發展黨員,而是通過具體的舉措來實現,比如在11月17日的廣東工作計劃決議案中,就提出了兩項舉措,一是要求巡視員的工作之一就是“發展黨員及建立新黨部”,二是舉行增加黨員運動。將發展黨員作為一項運動,可謂是創舉。⑦中央檔案館編:《廣州起義》(資料選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25;50;1;7;50;19;26;26;32頁。
盡管在大革命失敗后,黨員數量急劇減少,但黨組織并沒有因此降低黨員標準,而是始終高度重視黨員發展的質量。這主要體現在:一是要求重新登記黨員;二是黨員除了失業者外,“一律須交黨費”。⑧中央檔案館編:《廣州起義》(資料選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25;50;1;7;50;19;26;26;32頁。同時堅持在一線工作實踐中吸收先進分子入黨。當時處于革命低潮時期,黨員入黨面臨著極為嚴峻的生存環境,是要冒生命危險的。在斗爭實踐中表現突出者,已經以實際行動證明其思想的高度覺悟性。因此廣東省委要求在入黨方面,對于勇敢的工農分子,尤其是在某一次斗爭之后,要大批介紹到黨內來。
(三)發展黨內民主
民主集中制是共產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即使在發動重大起義的關鍵時刻,中共在加強集中統一領導的同時,也積極發展黨內民主。值得關注的是,當時的黨內民主是在多個層面同時展開。如對于重大問題,必須由黨的會議決定,不能由個人獨斷專行,“各種重大問題,必須經會議討論決定,不可由同志個人意見,隨便決定”。⑨中央檔案館編:《廣州起義》(資料選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25;50;1;7;50;19;26;26;32頁。對于黨的政策,必須使黨員知曉,廣東省委鑒于黨員群眾過去常無討論黨的政策的機會,要求各地“必須盡各種可能召集縣委、區委、支部、小組的大會,或代表會,報告及討論黨的政策及實際問題,使同志們能夠了解黨的政策而勇猛地執行”。①中央檔案館編:《廣州起義》(資料選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33;26;53;26 ;166頁。對于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人選拔,要堅持選舉制,“支部書記及小組組長逐漸一律行選舉制”。②中央檔案館編:《廣州起義》(資料選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33;26;53;26 ;166頁。當時的中央對廣東省委甚至提出,對于不稱職的領導人,下級群眾(更多指黨內同志)可以公開批評甚至撤換,“廣東全省的黨務要盡可能實行選舉,由下層黨的群眾選擇他們的指導者,不好的或不中用的同志應無情撤換,使同志、群眾公開批評”。③中央檔案館編:《廣州起義》(資料選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33;26;53;26 ;166頁。
(四)推進巡視工作
1925年,中共四大提出要增加中央特派巡視的指導員,這是中共開始重視巡視工作的標志。1927年11月,在增加巡視員的基礎上,黨中央提出要開始建立各級黨部的巡視指導制度。廣東省委根據中央指示,認真貫徹巡視員制度,各區巡視員組織由省委討論決定,具體職責是:審查各地黨員重新登記;調查各地黨部改組或加強之;發展黨員及建立新黨部;召集會議,解釋政策,使各地黨部明了及議決擁護;巡視員同時為省農民協會之特派員,擔任恢復、加強及發展各地農會。④中央檔案館編:《廣州起義》(資料選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33;26;53;26 ;166頁。巡視員的職權從改組或建立黨部,到審查登記黨員,傳達中央精神,同時是當時黨組織依靠的主要力量農會的特派員。可以看出,巡視員是代表上級黨組織對下級黨組織進行以政治、組織巡視為重點的中央監督管理地方的專門派出隊伍,這對于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強化黨的權威具有重要的意義和長遠影響。
(五)確立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眾所周知,三灣改編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原則。三灣改編的時間為1927年9月底至10月初。而幾乎就在同期,廣東省委在1927年11月中旬也提出了類似的規定。廣州起義前后,黨對軍隊的領導體現在:
起義的指揮權由黨委統一行使。武裝起義是當時黨內最大的軍事行動,黨對軍隊的領導,集中體現在對當時軍隊主要行動武裝起義的領導,否則,黨對軍隊的領導就是一句空話。為了實現對廣州起義的絕對領導,廣東省委要求取消當時的廣州暴動委員會,起義工作統一于廣州市委,同時由廣州市委指定軍事同志來做工農軍事訓練工作。
軍事機關是黨委的內部機構。黨對軍隊的領導,必須構建專門的領導體制予以支撐。在廣州起義之前,雖然也有軍事領導機關,但基本獨立工作,因此,廣東省委在組建軍委的同時明確指出,軍委設于省委之下。軍委雖然負責軍事指揮,但是省委的下設機關,必須接受省委領導。同時,省委還建立了專門行理破壞反動軍隊、組織士兵群眾之工作的反動軍隊運動委員會。
在軍隊內部,要求按照紅軍編制,自上而下設黨代表,軍隊接受黨代表和軍事負責人的雙重領導。
三、廣州起義后對黨建教訓的汲取
恩格斯有句名言,一個聰明的民族,從災難和錯誤中學到的東西會比平時多得多。我們黨的歷史,不僅是艱苦奮斗的歷史,也是不斷總結經驗教訓的歷史。每一次重大行動之后,黨組織均會對本次行動的得失成敗進行總結。雖然廣州起義在黨的建設工作中有諸多經驗,甚至開創性的做法,但也存在著一些不足。
(一)加強黨的領導機關建設
廣州起義失敗,一個突出體現是黨的領導指揮組織能力不足。
廣州起義的決策指揮層當時就認識到了黨在起義中指揮能力不足的問題。參與起義指揮工作的聶榮臻在1927年12月總結到,“在暴動的各種工作中間,幾乎見不著黨,除了個人的亂跳一場而外,沒有一個健全組織的機關來指導一切”。黨的指揮組織能力不足在起義當晚體現得更為具體,雖然已經預料到起義后的第二天即12月12日,敵人必將大力反撲,將是最危險的一天,政治、軍事方面都必須有所應備,但“催促好幾次,已經在十二點鐘后才開會,會中不許討論多的問題,也沒有研究敵我情況,只是決定明晨四時先肅清長堤,再進攻兵工廠、河南。下命令時已兩點多鐘了,結果這個決定等于零”。⑤中央檔案館編:《廣州起義》(資料選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33;26;53;26 ;166頁。當時參與廣州起義的普通人員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參加廣州起義的何振武,在起義爆發后的第四天,即1927年12月15日就總結到,“負責同學失了決心和自信能力,群眾并不是因為軍閥壓迫下失了勇氣不能起來做偉大的斗爭,是負責同學沒有很好計劃和方法及宣傳不能普遍與解釋提起群眾勇敢前進”。①中央檔案館編:《廣州起義》(資料選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94;175;239;240;240 ;264;175;240頁。
當時的廣東省委也沒有諱言自身在起義發生之后的領導不力問題,并認為這是起義失敗的最主要原因,“暴動以后黨的組織幾乎失掉了作用。同志都自由行動起來,無法指揮,更無法去領導群眾,可以說是此次失敗最主要的原因”。②中央檔案館編:《廣州起義》(資料選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94;175;239;240;240 ;264;175;240頁。
廣東省委將領導機關指揮不力歸結為由于各級領導機關工農分子太少,而多被知識分子所把持,“過去黨不能有正確的布爾塞維克化,執行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黨的組織不健全完固,各級指導機關完全是知識分子包辦,工農分子不參加,就有少數參加的,也是一種形式,完全不能起作用,反而受知識分子的影響,而知識階級化”。他們認為,正是因為是知識分子所把持,所以導致在暴動之時,出現“到了緊張的時候,便搖擺不定畏懦退縮”。因此廣東省委認為,要盡快增加工農分子到各級指導機關,切“必須工農分子占多數”。③中央檔案館編:《廣州起義》(資料選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94;175;239;240;240 ;264;175;240頁。這一點總結對當時的全黨認識亦有重要影響,如1928年召開的中共六大就突出強調黨的主要領導的工人身份。
后來的歷史證明,這種認識是片面的,并不符合歷史的實際情況,但指出當時的領導機關領導組織能力欠缺則是正確的。
(二)提出“政治紀律”的命題
政治紀律是黨內最重要的紀律,永遠居于首位。廣東省委認為,過去只有組織紀律,而沒有政治紀律,政治上犯了錯誤,并沒有得到處罰。因此,鄭重提出了“政治紀律”的命題,并認為“鐵的紀律(特別是政治的)是構成布爾塞維克黨主要條件之一”。廣東省委不僅提出了政治紀律,而且嚴格執行了政治紀律,嚴厲處分對于廣州暴動指導機關負責的同志。“如XX同志,是最負責任的,即決定開除省委、廣州市委一切職務,再加以留黨查看三月的處分,其他XXX同志等七人,或開除黨籍,或開除一切職務去做下層工作。”④中央檔案館編:《廣州起義》(資料選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94;175;239;240;240 ;264;175;240頁。廣東省委將執行政治紀律作為“黨的新的精神的開始”,⑤中央檔案館編:《廣州起義》(資料選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94;175;239;240;240 ;264;175;240頁。這充分體現出在黨的幼年時期,黨組織敏銳地意識到黨的政治紀律的極端重要性,雖然中央1928年1月18日否決了廣東省委對幾位同志的政治紀律處分,認為“負責同志不僅堅決執行了黨的政策,且對于這一偉大創造盡了一切的力量”。⑥中央檔案館編:《廣州起義》(資料選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94;175;239;240;240 ;264;175;240頁。這說明雖然中央認為廣東省委給予幾位同志的處分不適當,但沒有否認執行政治紀律主要是執行黨的政策的含義,也沒有否認政治紀律的重要性。
可貴的是,廣東省委提出政治紀律,是結合黨的工作提出的,因此,認為今后“尤其要加緊政治紀律,每個暴動時更應加緊黨的組織,使成為群眾核心和領導”。⑦中央檔案館編:《廣州起義》(資料選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94;175;239;240;240 ;264;175;240頁。可以看出,廣東省委提出的加強政治紀律不是一句抽象的概念,而是要求在實際工作中體現政治紀律,把黨的建設與實際工作結合起來,根本目的還是加強黨的領導。
(三)進一步擴大黨內民主
結合本次起義,廣東省委認為黨內民主今后應在兩個方面予以體現:一是黨內要公開討論一切黨的重要政策和黨內問題,讓每個同志都有發表意見的機會;二是在組織方面實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選舉,并且在選舉會議時,“必須使同志盡量批評過去黨的政策、指導機關和負責同志的錯誤”。⑧中央檔案館編:《廣州起義》(資料選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94;175;239;240;240 ;264;175;240頁。這里實際已經暗含著后來被稱為中共與其他政黨區別的顯著標志之一——批評與自我批評作風。黨內民主不僅僅體現在選舉領導人和討論黨的政策,也體現在能否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是中國共產黨黨內民主的獨特之處。這種批評與自我批評不僅僅在選舉會議中要體現出來,而且要在黨內政治生活中體現出來。廣東省委指出,“過去黨內很少政治的批評,甚至不敢批評,尤其是對于高級指導機關和負責同志”。而在總結廣州起義的黨內會議上,則認真做到了批評與自我批評,“一掃過去小資產階級礙于情面的把戲,徹底批評,從錯誤中找到正確的教訓,能夠自己批評自己,把自己的錯誤,公開在群眾面前,才能得到正確教訓,從這些教訓當中,產生出正確的策略”。①②④⑤⑥⑦ 中央檔案館編:《廣州起義》(資料選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238;175;295;296;296;166頁 。
(四)基層組織建設要下沉支部設置
廣東省委認為,在組織建設方面,要改變以往建立支部的方式,即“改變以前以工會為標準的支部,而建立工廠、作坊、宿舍的支部和街道支部”。②中央檔案館編:《廣州起義》(資料選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238;175;295;296;296;166頁 。這一點意義十分重大,就是要下沉支部建設的層級,將支部建立在穩固的單元之上,如果說三灣改編確立了軍隊支部在連上的原則,那么廣州起義則確定了在最基層社會組織上建立黨支部的原則。
四、廣州起義中黨建存在失誤的原因分析
如果對比黨組織在廣州起義前和起義中黨建方面的做法,則更值得令人深思:
在起義前四個月,即1927年8月20日,廣東省委會議曾對黨建提出了7項要求,即黨的機關應該公開,嚴密黨的組織、執行鐵的紀律,審查黨員,實行黨的民主化,提攜工農同志加入黨的各種委員會指導機關,工農運動會中應盡量以工農同志作領導,盡量吸收在此次暴動中勇敢的工農及知識分子入黨。③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編:《廣州起義》,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8年,第34頁。從要求來看,不可謂不全面,不可謂不有力。
在起義前兩周,在廣東省委發表暴動宣言的同時,起義的主力部隊教導團黨團召開組長聯系會議,積極醞釀暴動工作。在1927年11月底,張太雷在財政廳前附近的一所黨的地下聯絡站召開教導團黨團骨干會議,進行發動工作。組織工作也是到位的。
在起義前一周,鄧中夏回憶說,“黨在暴動前一星期中曾召集了兩次支部書記聯席會議。討論暴動事宜。在各支部中黨又分別召集活動分子會議,討論暴動的方法、罷工的發動和赤衛隊的擴大組織”,④中央檔案館編:《廣州起義》(資料選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238;175;295;296;296;166頁 。“黨的指導機關和工代會特委會、赤衛隊委員會更是日日在開”。⑤中央檔案館編:《廣州起義》(資料選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238;175;295;296;296;166頁 。這一期間,領導組織工作也是有力的。
遺憾的是,起義一旦開始,黨的指揮就明顯不力,很多正常的工作也無法組織起來,如在起義的當天11日和次日12日,“黨召集支部書記聯席會議,亦兩次均流會”。⑥中央檔案館編:《廣州起義》(資料選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238;175;295;296;296;166頁 。在起義過程中,更是被指為“在暴動的各種工作中間,幾乎見不著黨,除了個人的亂跳一場而外,沒有一個健全組織的機關來指導一切”。⑦中央檔案館編:《廣州起義》(資料選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238;175;295;296;296;166頁 。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從整個起義來說,正如我黨已經做出的總結,即當時全國革命處于低潮,反動勢力強大,黨在指導思想上以奪取大城市為中心,機械運用十月革命的經驗,沒有建立農村根據地,因此歸于失敗。⑧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第72-73頁。如果從黨建角度看,筆者認為主要是源于處于幼年的黨還不能將黨的建設很好地與黨的工作緊密結合起來,駕馭復雜多變局勢的能力還比較弱,黨的領導能力還很薄弱。這一點也啟示我們,在加強黨的建設的同時,一定要以提高黨的領導能力為核心,把黨的建設與黨的各項工作緊密結合起來,使之水乳交融而不能成為兩張皮。
廣州起義雖然過去80多年,但它在中國革命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值得永遠銘記,它在黨建方面的經驗教訓也可為今天的全面從嚴治黨提供諸多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