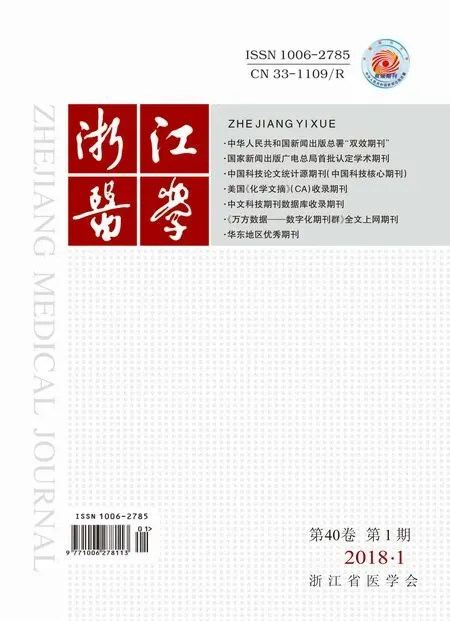血清乳酸聯合降鈣素原檢測用于膿毒癥致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預后判斷的價值
陳露 吳先龍
膿毒癥是一種具有高發病率和高病死率的感染性疾病,是引起ICU和住院患者高病死率的一項常見原因[1-2],膿毒癥能引起多臟器功能損傷和衰竭,其中以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RDS)最為常見[3-4]。近年來,隨著臨床和實驗研究的深入,對膿毒癥致ARDS的病理生理學和分子機制有了進一步了解,并在抗生素治療、疾病早期復蘇和尋找生物標記物等方面進行了探索,但是膿毒癥患者的病死率并未得到很好的控制[5],主要是由于缺乏早期發現和預防膿毒癥致ARDS的監測指標。雖然有研究發現血清乳酸和降鈣素原(PCT)檢測對膿毒癥患者的預后判斷帶來一定的指導價值[6-7],但是對于不同嚴重程度的膿毒癥所致的ARDS的病情評估缺少研究。因此,筆者探討了血清乳酸和PCT檢測對不同嚴重程度的膿毒癥所致ARDS病情監測中的臨床意義,以期為膿毒癥致ARDS的臨床治療及預后評估提供一定的參考價值,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1.1 對象 選取2013年3月至2015年10月入住我院ICU不同嚴重程度膿毒癥致ARDS患者96例,其中膿毒癥致ARDS 45例,男25例,女20例,年齡36~65歲,平均年齡51.29歲;嚴重膿毒癥致ARDS 32例,男18例,女14例,年齡37~68歲,平均年齡53.82歲;膿毒性休克致ARDS 19例,男 11例,女8例,年齡 34~69歲,平均年齡52.65歲。所有患者均符合膿毒癥致ARDS納入標準。引起膿毒癥的原發疾病包括肺部感染48例、急性胰腺炎36例、膽管炎7例、泌尿系感染5例。不同程度致ARDS間性別、年齡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所有患者或其家屬均簽署醫學研究知情同意書。
1.2 診斷標準
1.2.1 膿毒癥診斷標準 依據2003年美國胸科醫師協會及危重病醫學會(ACCP/SCCM)委員的標準[8]。
1.2.2 膿毒癥分型標準 膿毒癥:符合膿毒癥診斷標準。嚴重膿毒癥:膿毒癥伴有器官功能障礙>2個,或者組織灌注不良或低血壓。膿毒性休克:嚴重膿毒癥給予足量的液體復蘇后仍然伴有無法糾正的持續性低血壓。
1.2.3 ARDS診斷 根據最新版2012年公認的Berlin標準[9]:(1)急性起病;(2)血氧合指數(PO2/FiO2)<200mmHg;(3)影像學檢查提示雙肺斑片狀陰影;(4)肺動脈嵌頓壓<18mmHg或無左房壓升高證據。
1.3 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符合診斷標準以及排除標準的患者,且所有確診為ARDS患者前均存在不同嚴重程度的膿毒癥表現。排除標準:(1)年齡<18歲、妊娠;(2)合并神經源性休克、腦血管意外、顱腦外傷患者;(3)除既往有肝、腎功能不全及惡性腫瘤患者;(4)患有血液性疾病;(5)疾病終末期預計24h內死亡的患者;(5)除外其他非感染、病毒、真菌引起的ARDS;(6)患者或家屬不配合者。為了研究結果的可靠性,本研究依據患者癥狀體征,24h動態心電圖及心臟彩色多普勒和胸部X線等檢查,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肺部改變,如心源性肺水腫。
1.4 方法 入院當天24h內采集其靜脈全血,5 000r/min離心5min后收集患者血清,采用免疫化學發光法和化學分析法檢測血清中PCT和乳酸水平。痰標本在清晨患者用清水漱口后再用力深吸氣后咳出的第一口痰進行采集并立即送檢。統計7d內不同嚴重程度膿毒癥致ARDS死亡患者,以評估患者7d內的病死率。
1.5 統計學處理 應用SPSS 17.0統計軟件,計量資料以表示,多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兩兩比較采用LSD-t檢驗;計數資料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血清PCT和乳酸對各型膿毒癥致ARDS以及對患者死亡預后分析采用ROC曲線分析,計算其AUC、截點值、靈敏度、特異度。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96例膿毒性ARDS患者入院時基本資料的比較96例患者中均表現出膿毒癥的基本特點,如發熱,或白細胞增多或減少,心率加快,以及ARDS的基本表現,病情急,痛苦面容,PO2/FiO2均低于200mmHg。3組患者APACHEⅡ評分及7d內死亡患者數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而其他指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詳見表1。

表1 96例膿毒性ARDS患者入院時基本資料的比較
2.2 痰培養結果 96例膿毒性ARDS患者痰培養陽性29例,陽性率為30.21%,其主要致病菌為金黃色葡萄球菌(占37.93%),其次為大腸埃希菌(占31.03%),肺炎克雷伯桿菌(占31.03%),鮑曼不動桿菌、銅綠假單胞菌(均占6.9%),流感嗜血桿菌(占3.45%)。
2.3 3組患者血清乳酸和PCT水平變化 膿毒性休克致ARDS患者血清PCT和乳酸濃度均高于膿毒癥致ARDS和嚴重膿毒癥致ARDS患者(均P<0.05),見表2。膿毒癥致ARDS組7d內死亡2例(4.4%),嚴重膿毒癥致ARDS組死亡8例(25.0%),膿毒性休克致ARDS組死亡12例(63.2%)。對7d內死亡和生存患者的血清指標進行檢測發現,死亡組血清乳酸和PCT水平均高于存活組(均P<0.05),見表 3。

表2 3組患者血清乳酸和PCT水平的變化
2.4 PCT和乳酸對不同嚴重程度膿毒癥致ARDS以及對患者死亡的診斷效能分析 建立血清PCT與乳酸水平對不同嚴重程度膿毒癥致ARDS診斷預測和7d內膿毒癥致ARDS患者死亡預測的ROC曲線,結果見表4。血清PCT和乳酸水平對不同嚴重程度膿毒癥致ARDS的診斷預測能力不一致,兩指標對嚴重膿毒癥致ARDS有著較高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其ROC曲線AUC也最大(P<0.05)。血清PCT濃度診斷截點值在12.728ng/ml時,其靈敏度和特異度最高。血清乳酸在截點值為4.716mmol/ml時,其靈敏度和特異度分別為0.684和0.854,AUC 為 0.728(P=0.005)。

表3 死亡組和存活組血清乳酸和PCT濃度變化

表4 血清PCT和乳酸對各型膿毒癥致ARDS以及對患者死亡預后的ROC分析結果
3 討論
膿毒癥中ARDS病理生理學通常是一系列循環細胞分子和可溶性炎癥調節因子以及多種細胞因子如TNF-α、IL-1等在多種細胞靶位上綜合作用的結果[10-11],這種結果通常會引起一些生化指標如PCT水平的增加,因為這些指標在自身異常免疫、病毒和真菌感染以及局部和慢性感染中通常不會或僅輕微升高,而只在重度細菌感染和多臟器功能障礙中釋放到血液中的PCT水平才會顯著升高,且升高的程度與病情的嚴重程度成正比[12],因而被認為是一項監測膿毒癥并發多臟器功能衰竭病情嚴重程度以及預后的良好指標[13],乳酸是機體代謝過程中產生的一類物質,其在血液中的濃度研究已證實亦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機體代謝狀況和病情的嚴重程度,因而也被作為一項評估預后的重要指標[14]。本研究統計了7d內不同嚴重程度膿毒癥致ARDS死亡患者,對同一類型患者依據相同的治療指南進行處理,并將這些患者依據治療后的生存結局分為死亡組和生存組,故兩組患者在治療方式上無明顯差異,而血清PCT和乳酸預測的病死率不同,可能是與本身病情變化有關。本研究證實了血清乳酸和PCT能夠檢測患者病情嚴重程度,且經過ROC曲線分析表明,將兩個指標聯合檢測能提高兩者的靈敏度和特異度,進而將有助于提高對膿毒癥致ARDS預后的判斷效能。
作為病情監測的生化指標有很多,然而在膿毒癥的病情監測上,早期血清PCT水平就要比曾普遍認為的炎癥標志物C-反應蛋白有著更高的監測價值[15]。盡管細菌培養曾經作為感染性疾病診斷的金標準,但是細菌培養陽性率并不高,而且檢出時間比較長,這在本研究中得到了證實,因此痰細菌培養在臨床上所帶來的意義并不大。盡管不同的指標在臨床中的價值和意義不一,但是目前越來越多的研究和臨床診療均傾向于多種指標聯合檢測,可是對于不同類型的膿毒癥致ARDS,就本研究來說,血清乳酸和PCT在不同嚴重程度膿毒癥所致ARDS中的診斷效能存在著差異,因此,在診斷明確的情況下,應該針對不同程度膿毒癥所致ARDS聯合兩種指標對病情及預后進行判斷。
[1] Umemura Y,Yamakawa K,Hayakawa M,et al.Screening itself for 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 may reduce mortality in sepsis:A nationwide multicenter registry in Japan[J] .Thromb Res,2017,161:60-66.doi:10.1016/j.thromres.2017.11.023.
[2] Banerjee D,Opal S M.Age,exercise,and the outcome of sepsis[J] .Crit Care,2017,21(1):286.doi:10.1186/s13054-017-1840-9.
[3] Husak L,Marcuzzi A,Herring J,et al.National analysis of sepsis hospitalizations and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sepsis in-hospital mortality in Canada[J] .Healthc Q,2010,13:35-41.
[4] Chen C H,Chen YL,Sung P H,et al.Effective protection against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sepsis injury by combined adipose-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nd preactivated disaggregated platelets[J] .Oncotarget,2017,8(47):82415-82429.doi:10.18632/oncotarget.19312.
[5] Sean E Gill,Marta Rohan,Sanjay Mehta.Role of pulmonary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 apoptosis in murine sepsis-induced lung injury in vivo[J] .Respir Res,2015,16(1):109.doi:10.1186/s 12931-015-0266-7.
[6] 王佳,張紅玉.血乳酸和降鈣素原與膿毒性休克的相關性研究[J] .標記免疫分析與臨床,2016,23(11):1257-1259,1282.doi:10.11748/bjmy.issn.1006-1703.2016.11.006.
[7] 薛慶亮,劉杜姣,黃超,等.ICU膿毒癥患者血清降鈣素原的動態變化及其意義[J] .中華醫院感染學雜志,2013,23(24):5927-5932.doi:1005-4529(2013)24-5927-03.
[8] Levy MM,Fin k MP,MarshallJ C,et al.2001 SCCM/ESICM/ACC P/ATS/SIS in ternational sepsis definitions conference[J] .Crit Care Med,2003,31:1250.
[9] Definition Task Force A R D S,Ranieri V M,Rubenfeld G D,et al.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the Berlin Definition[J] .JAMA,2012,307:2526-2533.doi:10.1001/jama.2012.5669.
[10] Calfee C S,Janz D R,Bernard G R,et al.Distinct molecular phenotypes of direct vs indirect ARDS in single-center and multicenter studies[J] .Chest,2015,147(6):1539-1548.doi:10.1378/chest.14-2454.
[11] King E G,Bauzá G J,Mella J R,et al.Pathophysiologic mechanisms in septic shock[J] .Lab Invest,2014,94:4-12.doi:10.1038/labinvest.2013.110.
[12] Deutschman C S,Tracey K J.Sepsis:current dogma and new perspectives[J] .Immunity,2014,40:463-475.doi:10.1016/j.immuni.2014.04.001.
[13] Deuinger R P,Levy M M,Rhodes A,et al.Surving sepsis campaign:internationalgaidelines for management of severe Sepsis and septic shock:2012[J] .Crit Care Med,2013,41(2):580-637.doi:10.1097/CCM.0b013e31827e83af.
[14] Koduru L,Kim Y,Bang J,et al.Genome-scale modeling and transcriptome analysis of Leuconostoc mesenteroides unravel the redox governed metabolic states in obligate heterofermentative lactic acid bacteria[J] .SciRep,2017,7(1):15721.doi:10.1038/s41598-017-16026-9.
[15] 王征,曹濤,秦儉,等.降鈣素原和乳酸動態變化對急診老年嚴重膿毒癥和膿毒性休克患者預后的評估價值[J] .中國實驗診斷學,2016,20(5):741-7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