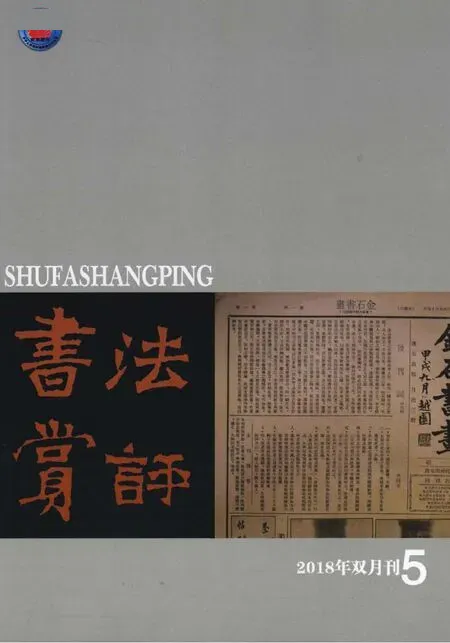中國書法史中 “摹本文化”現象探析
可以說,離開了 “摹本”這個核心關鍵詞,中國書法的歷史鏈條就會出現粉碎性骨折,一部中國書法史也將因此變得支離破碎。 “摹本”已經構成了中國書法史的重要文化現象,今試述之。
一、 “摹本文化”釋義
摹本的前提是因為有可 “摹”對象的存在,簡而言之是有經典法書或書法經典的存在。關于書法經典,張海先生曾有論述,他認為: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必須具備以下品格:第一,經典必然是開創性的和劃時代的。它以一種創造性的書法藝術實踐,開辟了全新的審美境界,承載了一種前所未有的人文精神和時代內涵。它為書法演繹時代精神找到了一種恰如其分、十分完美的表現形式,而且以自已的豐富實踐為這種表現和演繹找到了一種新的筆墨語言……第二,經典必然是在繼承傳統基礎上的變革,而這種變革又是符合歷史和藝術發展規律的。一個書家恰好處在歷史轉折和藝術演變的關頭,時代呼喚變革的精神和創新的實踐,而他又恰恰具備創新的資質和潛能,并且抓住了時代機遇,勇于實踐,大膽革新,那么他就能成為書壇大家,他的作品就會成為經典……第三,經典必須是以創造性的藝術實踐,開辟了一種新的技法體系和風格模式,從而填補了書法史的空白……事實上,不論哪種風格,只要其形式和內容、技法語言和藝術風格能達到高度統一、具有劃時代的、開創性的意義,都是經典。第四,經典必具原創性和極高的開掘價值。我們所說的原創性并非摒棄前人,另起爐灶,而是在規模前人、繼承傳統基礎上的大膽改革和天才創新。歷史上任何一種經典都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有著歷歷可尋的師承關系,但這絲毫無損于作者對于這種風格的原創性。與原創性同樣重要的還有它的開掘價值。因為二者并非一個概念,許多有原創性的風格由于個性特征過于鮮明等原因,其開掘價值和發展空間不大,因而難以成為后人規模的經典。作為一種具有原創性的風格,其開掘的空間越廣闊,作為經典的價值也就越高。[1]
由此,我們不難發現書法經典的幾個關鍵詞,創造性 (獨特性)、楷模性 (能夠作為較好的取法對象)、被開掘性 (可以在此基礎上有所發展)、超時空性 (持久影響)。
經典法書是在歷史的汰劣存良過程中沉淀出來的,經過后世學習者的選擇和實踐證明是可以作為重要取法對象而顯現出來的,是經過眾多學習成功者的認可逐漸被固化下來的,具有持久影響力的典型作品。最初的一些經典法書 (比如甲骨文、 《毛公鼎》等)成為中國書法史上重要的且具代表性的摹本,成為摹本文化的元典。
上古書寫所留下來的書法范本是 “無意于佳”的,漸漸地才有了 “有意為佳”的書法范本。 “隸變”成為古今文字書寫的一道分水嶺,也促使了漢字審美性書寫的涌動。漢魏之際,士大夫對書法的熱愛導致了漢字審美性書寫的大發展,尤其是魏晉以后,隨著 “人的覺醒”和 “文的覺醒”,開始有了專門的書法文論和書法技法的專門研究,書法成為 “家族教育”的重要淵藪,而因此產生了書法名門望族,佳作迭出而影響深遠,誕生了一批我們現在認為的經典法書。這些經典法書為摹本文化的發展積蓄了足夠的營養。王羲之新體的誕生意味著“古”書法的終結,也意味著古文字書法經典的元典時代的結束。隨著唐代楷書的定型,五體書完備了,中國書法又走入一個新的里程碑。書法從家族教育走向學校教育和大眾教育,經典法書逐漸被確立,在這個時候經典法書有了新的文化學意義。
從漢代 “鴻都門學”的藝術教育到唐代科考取仕的 “書言身判”,開啟了摹本文化之旅。唐太宗的 “崇王運動”和僧懷仁 《集王羲之圣教序》的刻碑流傳,以 《蘭亭序》臨摹本賞賜群臣,逝后以 《蘭亭序》真跡陪葬,促使了人們對經典的崇拜和傳播。及至宋代刻帖的出現,米芾 “集古字”而名揚天下,更是洞開了摹本文化的大門。從此,中國書法的發展圍繞著 “經典法書”與 “摹本”展開。
所以, “經典法書”是中國書法發展的基礎,也是 “摹本文化”的核心與基石。所謂的 “摹本文化”就是關于中國書法摹本產生、傳播等所形成的精神財富的總和。筆者以為, “摹本”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摹本指的是對某種法書的臨摹作品或刻字拓片,主要是忠于原作的臨摹作品或刻字拓片,比如書法史上有名的蘭亭八柱、 《十七帖》等。廣義的摹本是指書作的復制品,學習某一法書或法書系列產生的作品,以及模仿其意而產生的作品,包括拓片、影印本、忠于原作的臨本、意臨的作品、集字作品以及模仿法書而缺少自己創新元素的所產生的作品等。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書法史其實是少部分人的書法史,或者說,一部中國書法史就是摹本文化史。
風格是書法家的符號與面具,也是經典法書的標志性體現。從書法史的角度來看,所謂風格往往是以 “風格系統”出現,或者說以 “風格系列”呈現,比如:甲骨文書法系統 (系列)、王羲之書法系統 (系列)、顏真卿書法系統 (系列)、米芾書法系統 (系列)等等。也許這種風格系統尚不能稱之為流派,但它卻成為了 “摹本文化”的重要注腳。
二、 “摹本文化”構成了中國書法文化的主脈
我們爬理一下中國書法史,便會發現 “摹本”是中國書法傳播的重要載體,幾乎所有的書法家都是通過 “摹本”這一重要的中介完成其作為書法家的身份識別。摹本提醒書法學習者以古為徒,向傳統致敬。同時摹本也為書法傳遞正脈和道統提供了保證,并且由于摹本滾雪球似的存在方式,逐漸地汰劣存良、冶煉經典,更深刻地保證了中國書法的純正品格和薪火相傳,也因此形成了不同的子系統。
1.在經典的基礎上衍生出五個書法系統, “而這些系統之間的最大不同有三:即觀念、立場和方式。觀念是思維系統,立場是觀察系統,方式是技術系統。它們建立在語匯系統之上,不同的語匯系統便是不同系統的獨特形式美。”[2]
不同類型的書法范本通過臨摹學習逐漸開枝散葉而衍生為某種類型系統,而中國書法的發展也正是在這些類型系統的基礎上逐漸發揚光大。筆者認為,以秦文字為代表的中國書法系統基本可以劃分為五個子系統:
(1)甲金系統——是以甲骨文、金文等篆書作品為代表及其作為取法對象的書法系統。這一類系統主要以甲骨文、金文拓片、石鼓文、小篆書跡 (拓片)和后來習之有成就者的書法作品為代表。
(2)晉帖系統——是以晉帖為代表及其作為取法對象的書法系統。這一類系統主要以羲、獻父子書法作品和后來習之有成就者的書法作品為代表。唐楷系列、行書系列、今草系列、手札系列等可劃歸為此系統。
(3)魏碑系統——是以魏碑為代表及其作為取法對象的書法系統。這一類系統主要以北魏碑版和后來習之有成就者的書法作品為代表。
(4)簡牘系統——是以簡牘、漢隸為代表及其作為取法對象的書法系統。這一類系統主要以漢代簡牘書法作品、漢隸作品和后來習之有成就者的書法作品為代表。章草系列、隸書系列等可劃歸為此系統。
(5)破體系統——是以碑、帖、簡牘等為取法對象并走碑帖等相融合之路的書法系統。這一類書法作品的重要取法對象為上述四類書法系統的代表作品,在創作中進行了選取和整合而生成的書法作品。
2.唐代的 “集字成篇”和宋代的刻帖、拓片等創建了摹本文化的新篇。漢尚氣、晉尚韻、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態、清尚樸等均是摹本文化的一個注腳,也是摹本文化的集中提煉和邏輯延伸。
古代書法教育的范本主要是 “摹本”,因為即便是 “師帶徒”的方式或家庭 (家族)性 “長傳幼”的方式也都是以執教者的示范作品或其他范本為學習對象進行的,更何況學校性質的書法教育。漢代鴻都門學的興起,除了政治的因素之外,更多的緣由恐怕是漢靈帝對辭、賦、書、畫的酷愛。鴻都門學所招收的學生和教學內容多與太學不同。學生由州、郡擇優選送,多數是士族看不起的社會地位不高的平民子弟。開設辭賦、小說、尺牘、字畫等課程,打破了專習儒家經典的慣例。鴻都門學不僅是中國最早的專科大學,而且也是世界上創立最早的文藝專科大學。它招收平民子弟入學,突破了貴族、地主階級對學校的壟斷,使平民得到施展才華的機會。鴻都門學的出現,為后來特別是唐代的科舉和設立各種專科學校開辟了道路。鴻都門學雖然短命,卻出了一些著名的書法家,他們主要擅長八分書和鳥蟲篆,代表人物有師宜官、梁鵠和毛弘等。
在科考取仕之前,書法等的學習是貴族的奢華,科舉制度之后則是寒門庶士的希望,此后的書法學習才更加廣泛和蔚然成風。 “科舉的名稱和制度雛形實始于隋朝, ‘近隋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策試而已。’……在此基礎上,唐于高祖武德五年 (622年)正式舉行科舉考試…… ‘由于他 (唐太宗)重視書家,許多人因字寫得好而做了官。’初唐的科舉考試和書法教育是統一的。”[3]并且, “當時沒有現代的影印技術,書法作品的流傳主要是摹拓。唐太宗在弘文館中設有專事摹拓的高手如韓道政、馮承素等,用于生產王體書的精良摹本。”[4]一般言,科考只有通過吏部試才能授以官職,吏部試所考為 “四事”,即 “身、言、書、判”,分別指 “體貌豐偉” “言辭辯證” “楷法遒美” “文理優長”。其中, “重要的是 ‘書’與 ‘判’的考試……書法又是試判的關鍵。”[5]書法在科考中的重要地位可見一斑。而從這個時候開始,諸如 《蘭亭序》摹本、 《懷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拓片等作為重要的取法范本粉墨登場,書法的摹本時代已經來到, 《懷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更是開“集字成篇”先河。
關于法帖的問題,本文以 “二王”法帖為例言之。我們現在能讀到的 “二王”法帖并非羲、獻父子的真跡,而是刻帖與摹本。但 “二王”刻帖與摹本卻保證了 “二王”法脈的傳承,因為當失去了 “二王”作品真跡的時候,摹本就成了研究的最好范本。當然 “摹本”也有高下之分,越是接近真跡的摹本則越有價值。而從流傳下來的這些刻帖或者摹本來看,米芾的貢獻是無人替代的。因為過去印刷技術的局限,復制書畫的途徑就是臨寫或摹拓。
米芾曾稱王羲之兩件作品為 “天下第一法書”,一件是 《蘭亭序》,另一件是 《王略帖》。米芾尤其推重 《王略帖》,并說: “吾閱書一世,老矣,信天下第一帖也。”[6]米芾在得到 《王略帖》之后曾作 《王略帖跋》,緊接著又作 《王略帖跋贊》,其重視程度可見一斑。在整個 《寶晉齋法帖》中共有四個 《王略帖》,第一卷有兩個,第三卷有一個,第九卷有一個,并且這四個 《王略帖》是四個不同的版本,由此可見,這些不同的版本中肯定至少有三種是臨本。 “所以,不管至今流傳的版本是否是米芾的臨本,可以肯定地說,從米芾所臨摹過的作品表格中也可以看出,米芾肯定學過而且臨過 《王略帖》,并且臨摹水平非常高,幾欲與原帖真假難辨。”[7]實際上,在 《寶晉齋法帖》中,所收錄的王羲之作品,除了第一卷的 《王略帖》之外,還有第二卷的 《蘭亭序》、定武本 《蘭亭序》 《樂毅論》 《黃庭經》;第三卷中的 《范新婦帖》等22件法帖;第四卷中的 《十七帖》;第五卷中的 《得告帖》;以及米芾所臨寫的王羲之作品,米芾所臨王羲之的作品保留最多的就是在 《寶晉齋法帖》中,這些 “摹本”對王羲之書法的傳承起到了重要作用。毋容置疑,米芾也臨習過 《蘭亭序》。實際上,唐代之后的許多書法家大都臨習過 《蘭亭序》,但是他們學習取法的 《蘭亭序》都是摹拓本,這足以說明摹本的意義。
流傳至今的 “二王”法帖幾乎沒有墨跡本,即便是 《快雪時晴帖》仍然有人懷疑是唐代摹本,其他基本上是刻帖或摹刻。米芾在 《海岳名言》中云: “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己書也。故必須真跡觀之,乃得趣。”[8]按照米芾說法,只有學習真跡,才能領略書家真正的精髓,而米芾卻將所藏晉帖刻石, “《寶晉齋法帖》為崇寧三年 (1104),米芾任無為軍時將平生所藏晉帖刻石于官廨中。南宋時,刻石已殘,當時的無為太守葛祜之根據拓本重刻;后曹之格通判無為,復加摹刻,并增入家藏晉帖與米帖多種,匯為十卷。米芾所臨摹王羲之 《王略帖》就是曹之格后來增補的。”[9]
正因為米芾長于收藏和精于臨摹,素有 “善于偽作”之名。米芾的 “偽作”與原帖相差無幾、足以亂真, “王詵每余到都下,邀過其第,即大出書帖,索余臨學。因柜中翻索書畫,見余所臨王子敬 《鵝群帖》,染古色麻紙,滿目皺紙,錦囊玉軸,裝剪他書上跋連于其后;又以臨虞帖裝染,使公卿跋。余適見,大笑,王就手奪去。”[10]“余臨大令法帖一卷,在常州士人家,不知何人取作廢帖裝背,以與沈括。一日林希會章惇、張詢及余于甘露寺凈名齋,各處書畫,至此帖,余大驚曰: ‘此芾書也。’沈悖然曰: ‘某家所收久矣,豈是君書?’芾笑曰: ‘豈有變主不得認物耶!’”[11]米芾并非刻意作偽者,但他對古人法帖的精準臨摹的確為其“作偽”提供了技法保證,從而在他的 “集古”之路上留下了不少被疑為 “二王”作品的 “偽作”。而實際上這些 “偽作”卻對我們研究 “二王”書法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也為后人學習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本。因為米芾在集古的過程中 “尤工臨移,至亂真不可辨。”[12]“米元章有嗜古書畫之癖,每見他人所藏,臨寫逼真。”[13]這些均表明了米芾臨寫水平之高和對古書畫佳品的鐘愛,當然米芾的收藏目的并不是為了 “作偽”和通過收藏掙錢,而是為了學習,正如米友仁所言: “先臣芾所藏晉唐真跡,無日不展于幾上,手不釋筆臨學之。”[14]“二王”摹本的意義其實是中國書法學習、傳承的態度與方法的意義,米芾復印式的臨寫技術將 “臨帖”的作用和意義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其 “集古字”的態度與方式也成為摹本文化傳播方式。米芾對 “二王”的選擇并使之成為其集古系統中的重要成分,不僅促進了 “二王”法帖的鑒藏、摹刻與傳播,也保證了 “二王”法脈的傳承,還深深地影響了其后的書法發展。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風尚,對于書法的時代特征而言,后人總結的 “漢尚氣、晉尚韻、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態、清尚樸”等正是那一個時代總體風尚的反映,是集體崇尚的凝聚,其中 “摹本”和審美取向成為一個重要的聯結點,是摹本文化的集中體現。
3.當下全國性書法展賽基本上是不同摹本的集中亮相
經過 “五四運動”和 “文化大革命”,書法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的 “書法熱”才把書法拉回到歷史視野。從當時的 “字帖難求”到當下高仿的 “精品摹本”爭寵,實在是摹本文化的大發展。與此同時,全國性的書法展賽更是為摹本文化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從近些年中國書協舉辦的各種展賽所呈現的展廳效應和風格特點來看,傳統碑帖在不斷被喚醒, “民間書法”也被不斷挖掘,并強勢地進入高層次國家級展覽,此現象可謂喜憂參半。因為我們在深刻繼承傳統的同時,卻又無法從碑、帖中破繭而出,抱著 “摹本”處于兩難境地。王鐸書風、明清調、 “二王”手札、拼貼技術等等其實是傳統一些經典法書的一種改頭換面或重新包裝而已;許多獲獎作品如果不看落款的姓名,很難分辨出到底是誰的作品,這是深陷 “摹本”而無法 “出帖”所形成的 “千人一面”的書壇現實;更有甚者,為了在國字號展覽中入展等,有的作者一年只用心打造一幅作品,大量重復修改以求創作效果。這些是 “摹本文化”帶給當下的尷尬,也與我們的創作認知息息相關。
書法的創作大致可以分為層次:①臨寫的作品:這類作品主要來自對他人作品的臨摹,或集字而成的對聯、詩詞等,這類作品可以說是書法創作的初級類型;②借鑒產生的作品:這類作品主要來自對他人作品的借鑒,在臨摹的基礎之上,通過對他人作品中的字的結構、章法形式等的學習、消化、誤讀、重構等創作出的作品,這類作品可以說是書法創作的中級類型;③創新的作品:這類作品是對傳統技法、技巧升華后的產物,是具有原創力的作品。這類作品又可分為兩類:一是對傳統一脈相承,又能食古而化,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能夠出新的作品,如王羲之、米芾、王鐸等人的作品;二是與前人作品有重大區別的創新作品,堪稱真正意義的創作,如學院派、現代派的一些較成功的作品。[15]前兩類創作,主要是依賴摹本而完成,第三類創作則可能成為后來學習的范本。創作的三個層次中,能處于第三個層次的創作者似乎并不多。總之,創作與摹本密切相關。
三、 “摹本文化”對于當下中國書法創新的啟示
1.大量出土的墨跡、拓本和刻字作品等,比如民間書法、經生書、封泥、瓦當等具有濃郁民間氣息的東西,均可以被視為書法學習的范本。
現代影印技術的發展很好地促進了摹本的進一步被挖掘和傳播,也使得摹本文化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高度,尤其是印制精良的高仿作品更是能夠充分顯示作品的細微之處,有近乎觀摩真跡的零距離感,有助于學習者更真實地了解筆墨等的精妙所在。隨著考古的新發現,讓諸多新鮮的 “老物件”迅速進入人們的視野,不僅豐富了書法學習者的取法對象,而且通過對這些范本的學習研究,拓展了 “摹本文化”的容量,產生了摹本文化研究的新視角。
2.專業意識覺醒所產生的對傳統經典的解構與重構,成為一種新的摹本。
隨著毛筆書寫遠離實用,以及書法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對于書法與寫字有了較為明確的區分,也有了專業與非專業的區分。專業化創作與閱讀性書法的根本分野在于對待書法的態度與觀念:是為了視覺審美的滿足,還是為了記載和傳播某些信息資料。在這一過程中,陳振濂先生所倡導的 “學院派書法創作”進行了有價值的嘗試, “主題先行、形式至上、技術品位”其實是一種觀念先行的命題性創作,強化了創造性而與傳統書法那種模糊性創作有意識地拉開了距離,值得關注。其中,主要是對傳統經典的解構與重構,那些成功的作品也成為一種新的學習和參照的對象。
3.現代電子計算機技術對傳統經典的改良與破壞,動搖了傳統 “摹本”之基。
計算機目前已經嘗試參與書法創作,并且當年僧懷仁的 “集字”工作已經為計算機所代替,新的摹本系統呼之欲出。無論是改良也好,抑或是破壞也罷,傳統的摹本之基已然動搖。通過電腦技術實現多種書法字體的日常生活化,把傳統的摹本轉變為電腦里的字庫,甚至根據經典法書中的主要筆畫、結構特征創造出原來法書中沒有的新字,豐富和完善某一家的書法字庫。這種字庫的建立,有利于傳統法書的傳播與認知,增強某一書體的識別度,強化對不同書法家的作品特點的了解,提高受眾的書法接受度和欣賞水平。
“集字”的便捷與泛濫正在蠶食傳統經典的權威性,也為新的摹本的誕生提供了可能性。甚至可以通過電腦設計出樣稿,然后對照樣稿進行 “放大臨摹性”創作。目前,已經可以通過智能機器手進行模仿性的書法創作。有朝一日,機器人或許能夠代替書法家進行書法創作,那么,摹本文化必將呈現出一種新的局面。
4.中國書法的世界性傳播依然需要緊扣 “摹本”這個核心關鍵詞。
中國書法往外傳播的應該是傳統經典和新經典,傳統經典是指已有的普遍認可的經典法書,新經典應該是當代書法大家所創作的被普遍認可的具有代表作意義的作品。對這些經典的學習依舊是 “摹本”,只不過高仿真的復制技術,賦予了 “摹本”新的生命力。現代復制技術讓過去深藏閨中的一些孤本上品能夠走入百姓視野,使得更多的學書者能夠纖毫畢現地學習研究,讓風華絕代的佳作廣泛傳播。
四、如何利用好已進入新模式的 “摹本文化”
“摹本”是中國書法學習、傳承、傳播不可回避的關捩,所以必須學會利用好摹本。摹本的前提是經典,進入新模式的 “摹本文化”仍然離不開經典。與此同時,我們還必須把視野放得更加開闊,比如對現代書法的關注、思考與探索。如何通過 “摹本”傳播中國書法文化?最好的方法便是通過對 “摹本”的學習,進而學習“摹本”背后的東西。
1.廓清經典:進一步把書法史上優秀的經典法書梳理出來,使之分門別類地系統呈現;
2.吃透經典:有選擇地臨習、研究經典,向傳統致敬的最好方式就是繼承并發展之;
3.創造經典:創作經典不可能是多數人的事,只能依靠那些 “少數中的關鍵”和 “關鍵中的少數”,并且對那些不斷探索、可能創造新的經典法書的書法家們多一份寬容,因為探索最容易遭遇的便是失敗,成功只屬于那些失敗后仍舊堅持探索的人。
王冬齡先生可謂當下現代書法探索的一個代表性人物,他曾談到從事現代書法精神的探索與表現,要遵守四個原則和具備三個條件: “第一個原則是要申明現代書法不但不是傳統書法的敵人,而且是盟友,他們是相輔相成的……第二個原則要強調現代書法的終極表現不是要脫離漢字,但允許對漢字進行變形、解構與藝術處理。第三個原則就是推崇多元,多種藝術處理手法……第四個原則是明確指出創作現代書法必須要有傳統書法的功力,有技術含量,這是我們現代書法發展初期中極為重要的條件……在這四個原則下,我認為從事現代書法要有三個條件:一是真正吃透傳統書法,熟練掌握和真正理解中國書法的藝術真諦;二是要有現代的藝術修養,具備現代藝術的知識結構,這樣才能創作出有現代氣質的書法作品;三是必須要有敢于戛戛獨造的膽識和氣魄,要有前瞻性和原創性。”[16]這 “四個原則和三個條件”對我們不無啟發。現代書法已經不可避免地沖到了我們的面前,如何創造新的經典,是必須思考和嘗試的課題,好在有像王冬齡等一批人在探索,這是契機,也是進入新模式的 “摹本文化”時代所無法回避的書法文化現象。時代在變,書法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變,創作書法的觀念、技法與視覺形式也必然隨之而變。但無論怎樣變,都必須真誠面對經典,都必須經過傳統書法訓練,都必須緊扣書法本體,都必須與時代共鳴,而這些新的探索,也必將成為推動中國書法文化傳播的新的催化劑。
只有廓清了經典,吃透了經典,才有可能創造新的經典,除此之外,別無他法。這是 “摹本文化”的本質所在,也是其責任所在。
注釋:
[1]張海: 《時代呼喚中國書法經典大家》, 《光明日報》,2008年7月11日第11版。
[2]楊豪良: 《魏碑的特質及其相關問題探討》, 《書法賞評》,第52-55頁。
[3] [4] [5]楊豪良: 《從初唐科舉考試看其書法教育》, 《書法導報》,2004年3月3日第10版。
[6]水賚佑著: 《米芾書法史料集》,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年,第31頁。
[7]劉藝銘: 《米芾集古論》,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0509,第24-25頁。
[8]米芾: 《海岳名言》,盧輔圣編著: 《中國書畫全書》第一冊第4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年,第976頁。
[9]梁敏: 《米芾 “集古字” 辨析》, 《中國書法》,2012年第7期, 第182-183頁。
[10] [11]米芾: 《書史》,盧輔圣編著: 《中國書畫全書》第一冊第4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年,第974、971頁。
[12]中央文史研究館編: 《談藝集 (上)》,中華書局,2011年,第169頁。
[13]劉正成主編: 《中國書法全集·米芾卷 (一)》,榮寶齋出版社,1992年,第29頁。
[14]岳珂著: 《寶真齋法書贊·米元章臨右軍四帖》,盧輔圣等編: 《中國書畫全書》第二冊第2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年,第303頁。
[15]參閱楊豪良: 《書法創作的三個層次》, 《時代藝術》,吉林美術出版社,2006年,第205頁。
[16]王冬齡: 《現代書法的創作實踐與理論構建》, 《中國書法》,2017年第2期,第57-63頁。